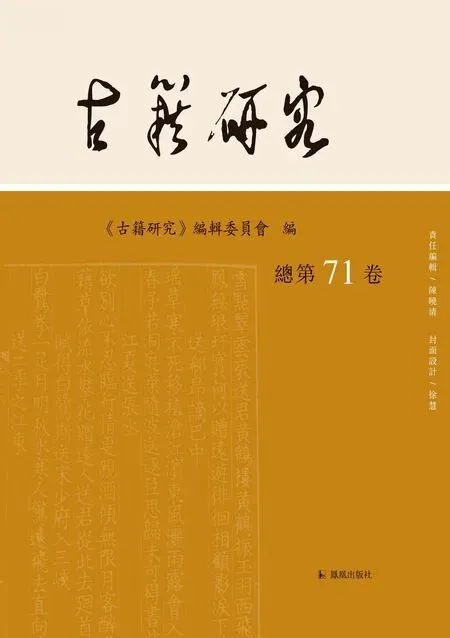新世紀《長生殿》《桃花扇》文獻整理、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王亞楠
關鍵詞:長生殿;桃花扇;文獻;學術史
代表着昆曲傳奇最後輝煌的《長生殿》和《桃花扇》問世後,受到了讀者、觀衆的喜愛和肯定,在有清一代的戲曲舞臺上廣泛、長久地搬演、流傳,對於清代、民國的通俗文學創作産生了比較大的影響,清代、民國間的衆多文人學者也從思想到藝術對這兩部名劇進行了題詠、批評和研究。這些現象和活動都産生和流傳下來豐富的文獻資料,但因爲數量較大、瑣碎而又分散,至今都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視、搜集、輯録和利用。
二十世紀中,對於這兩部劇作的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如劉世珩在清末民初主持和組織刻印暖紅室《匯刻傳劇》時,對於這兩部劇作特别是《長生殿》的有關文獻資料進行了初步搜集和匯輯,主要是吴舒鳧等的多篇序文、吴尚榮等的多篇題辭和王晫等的跋文。但劉世珩在《重刻〈長生殿〉跋》、吴梅在《校正識》中都没有説明這些相對於稗畦草堂刻本新增的序跋、題辭的來源出處(吴舒鳧和徐麟的序可能據光緒十六年上海文瑞樓刻本)。吴梅僅提及校勘時使用了“李鍾元本”作爲參校本“合校數過”,李鍾元其人和所謂的“李鍾元本”《長生殿》未見其他著述提及和著録。作品版本的影印方面,《長生殿》有《古本戲曲叢刊》五集第四函所收的北京圖書館藏康熙稗畦草堂刊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775册所收的版本相同;《桃花扇》有《古本戲曲叢刊》五集第五函所收的“北京圖書館藏康熙三十年介安堂原刊本”,實則是康熙刊本的覆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776册所收的版本相同。另有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79年據劉世珩暖紅室刻本校定重刻的《增圖校正〈桃花扇〉》,一函六册。作品的整理方面,《長生殿》有徐朔方先生的注本、蔡運長的“通俗注釋”本、竹村則行和康保成先生的“箋注”本等;《桃花扇》有賀湖散人的《詳注〈桃花扇〉傳奇》、王季思等先生注釋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本、劉葉秋注釋的《孔尚任詩和〈桃花扇〉》本等。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的近二十年間,學界對於兩部劇作的文獻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一些新的進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作品版本的影印和整理出版、相關文獻資料的整理和研究。
一、 作品版本的影印和整理出版
《長生殿》和《桃花扇》的清代刊本衆多,但版本源流比較簡單和清晰。《長生殿》刊本中的稗畦草堂本、《桃花扇》刊本中的康熙刊本的覆刻本和暖紅室刊本比較常見。進入新世紀以來,又有一些其他的稀見的版本得到了影印出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清彩繪本《桃花扇》,包括堅白道人所繪的44幅彩畫(每出一幅)和太瘦生鈔寫的每出的唱詞,彩畫和鈔寫的唱詞完成於不同時期。作家出版社2009年予以全部影印出版,同時附有劇作全文和中英文的故事梗概。原本和影印的詳情可參看沈乃文《清彩繪本〈桃花扇〉影印序言》(《版本目録學研究》,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不過,彩繪本的價值主要在於藝術方面。
《桃花扇》有蘭雪堂本,初刻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1895),校改重刻於光緒三十三年(丁未1907)。鳳凰出版社2016年對其初刻本予以影印出版,列入《古椿閣再造善本叢刊》,凡一函五册。鳳凰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前有《前言》,對蘭雪堂本做了一些介紹和評價,但其中存在一些錯誤,如《前言》中的以下兩段文字:
《桃花扇》最初的刊本是康熙戊子年即康熙四十七年介安堂所刻,孔尚任時年六十歲,但此本並非最善。此後有蘭雪堂本、西園本、泰州沈氏刻本、嘉慶刻本、暖紅室本、梁啓超校注本等,著名戲曲理論家吴梅先生認爲蘭雪堂本較佳,最接近原稿,他主要是從藝術創作角度研究蘭雪堂本桃花扇,一是論其寫史筆法;二是論其藝術構思;三是曲詞批評。而暖紅室本太過期於盡善,個别做了删改。在桃花扇所有的幾個本子之中,蘭雪堂本的校勘價值較大,業界認爲在版本校勘上蘭雪堂應排首位。蘭雪堂本天頭敞闊,刻有眉批。蘭雪堂本桃花扇的批語也很有特色,批語分眉批和總批兩種,其中眉批779條,比康熙原刻本多出35條,總批69條。這些批語對於桃花扇的主題構思、藝術手法以及人物形象方面有着獨到的分析。
光緒二十一年(1895)合肥李氏蘭雪堂主人李國松以原刻本參校嘉慶本刊刻桃花扇。李國松,字健父,安徽合肥人,光緒間舉人,博雅好古,藏書數萬卷。共五册,卷首一册,正文四卷四册。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年,1907),李氏將初刊本校改後又出了重刊本,在乙未原版上進行了修改。也就等同於第二次印。在《桃花扇考據》增加了少量其他内容。孔尚任在正文劇前列出考據,本是爲了標舉南明的主要史實和史料,並一一參照。而蘭雪堂本桃花扇中的考據,與解放後出版而目前通行的版本有較大不同,而且明顯優於通行本,有重要的校勘價值。(1)《前言》,《蘭雪堂重校刊〈桃花扇〉》,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
第一處錯誤是没有進行詳細校勘,就貶低康熙間介安堂刊本的價值。實際情况是介安堂刊本是《桃花扇》現存刊本中最好的版本,最接近原本面貌,内容最完整,錯誤最少,具有最大的“校勘價值”。《前言》所謂的蘭雪堂本的眉批“比康熙原刻本多出35條”當然也是不符合版本實際的。蘭雪堂本僅比介安堂刊本多出一條眉批,即第十九出《和戰》中的“當此時,解恨息争稍晚矣。何侯生不早計及之。”(2)《桃花扇》第十九出《和戰》眉批,蘭雪堂刊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刊。此外,介安堂刊本第四出《偵戲》的下場詩中的“惟有美人稱妙計”句的眉批作“古今小人,多用美人計。”(3)《桃花扇》第四出《偵戲》眉批,康熙介安堂刊本。而蘭雪堂本作“古今小人多會算計”(4)《桃花扇》第四出《偵戲》眉批,蘭雪堂刊本。,明顯不如介安堂刊本的批語準確、恰切。
第二處錯誤是錯亂了《桃花扇》版本的源流演變。按照刊刻的時間先後,清代、民國間《桃花扇》的重要版本有介安堂刊本、康熙刊本、康熙刊本的覆刻本、西園本、嘉慶刊本、蘭雪堂本和暖紅室刊本。所謂的“梁啓超校注本”並不具有任何版本校勘價值。
第三處錯誤是高估了蘭雪堂本的價值,其實蘭雪堂本刻印的時間較晚,可供版本校勘的價值不大,而且存在比較多的脱漏。蘭雪堂初刻本即乙未刻本删去了《桃花扇·考據》中自“董閬石《蓴鄉贅筆》七條”至“王世德《崇禎遺録》”的文字,其後的“侯朝宗《壯悔堂集》十五篇”及各篇篇目也被删去。重刻本即丁未刻本恢復了所删《考據》中的文字,但第四出《偵戲》闕出批,第十九出《和戰》闕“副净持槍駡上”至“那個怕你”共二十字。《前言》却把蘭雪堂本的這一文字缺陷視爲它的優長之處。
中國藝術研究院藏有乾隆十五年(1750)沈文彩鈔本《長生殿》,原爲程硯秋藏書,一函二册,凡五十出,函套題“長生殿傳奇 清乾隆抄本”。此鈔本卷首附吉祥咒,卷尾附砌末,每出注明身段,應是當時的演出臺本,可供我們考察、研究《長生殿》在當時演出的情况,是極其珍貴的重要史料。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予以影印出版,題爲《乾隆沈文彩鈔本長生殿傳奇》。
近二十年來也有兩部劇作的多種整理本出版。《長生殿》主要有《吴人評點〈長生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國學典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和翁敏華、陳勁松評注本(中華書局2016);《桃花扇》主要有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注評》本(齊魯書社2004)、《云亭山人批點〈桃花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國學典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謝雍君、朱方遒評注本(中華書局2016)和屠青校注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等。
徐振貴主編的《孔尚任全集輯校注評》雖名爲“全集”,却存在較多本不該出現的遺漏,周洪才、朱則傑、張兵等學者已撰文指出。該書在文字、標點、注釋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錯誤。第一册收孔尚任的兩部戲曲作品:《桃花扇》和《小忽雷》。書名既言“輯校”,却没有説明校勘所用的底本和校本,也没有校勘記。而且缺少刻本中的“題辭”、“砌末”和跋語。收録了刻本中的少量眉批和出批,却又將這些批語列入注釋中,也不便查閲。
謝雍君、朱方遒評注本在注釋中也收録了少量批語,同樣與注釋文字混雜,而且標作“暖紅室本眉批”,但其實這些批語在介安堂刊本中便已存在。
《云亭山人批點〈桃花扇〉》和“國學典藏”本《桃花扇》均爲李保民點校,兩書均在封面、書名頁和版權頁標明“云亭山人批點”,前者更直接在書名中點出。但實際《桃花扇》刻本中的批語並非出自孔尚任之手。晚清學者李慈銘最早在其《越縵堂日記·荀學齋日記辛集下》光緒十二年丙戌(1886) 十二月初三的日記中認爲《桃花扇》刻本中的大量批語爲孔尚任自作,後來得到了梁啓超、王季思、徐振貴、葉長海和吴新雷等學者的信從,但或簡單表示贊同,或不能提出確實的證據、論證存在漏洞。筆者已有專文對這一錯誤觀點進行駁正,現再略加申説。李慈銘一生的創作和研究雖涉獵較廣,但主要用力之處和成就在於史學方面,而又重在史學考證,如平步青在《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蓴客傳》中所説:“君自謂於經史子集以及稗官、梵夾、詩餘、傳奇,無不涉獵而無放之,而所致力者莫如史”(5)平步青:《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君蓴客傳》,《白華絳柎閣詩》附,光緒刻本。。李慈銘閲讀和評論小説、戲曲作品體現出兩個特點:第一,他保持着傳統、保守的思想觀念,同古代多數文人士大夫一樣貶低這類作品。偶有閲覽,也是爲了遣悶或寧神。如他在日記中曾言:“顧生平所不認自棄者有二:一則幼喜觀史”,“一則性不喜看小説。即一二膾炙古今者,觀之亦若格格不相入,故架無雜書”。(6)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376頁。此處所説的“小説”,當不包括記述文史掌故的文言筆記小説。又如他稱戲曲作品爲“鄭聲艶曲”(7)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6037頁。。第二,對於歷史題材的或者歷史人物爲主角的小説、戲曲作品,可以發揮他的特長的,如《三國志演義》、“楊家將”故事小説、《龍圖公案》等,他的評價便較爲詳細、深入;而評價無本事、原型可考的作品,便顯得無所用力,或者轉述它書記載,並且不注明出處,或者信口雌黄、妄下斷語。轉述它書記載,而不注明出處的如《越縵堂日記》中所記:“夜閲《燕子箋》。大鋮柄用南都時,嘗衣素蟒服誓師江上,觀者以爲梨園變相。”(8)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6037頁。阮大鋮“衣素蟒服誓師江上”之事,吴偉業《鹿樵紀聞》、夏完淳《續倖存録》均有記述。信口雌黄、妄下斷語,從而産生錯誤。其中影響最大的錯誤觀點便是認爲《桃花扇》刻本中的批語爲孔尚任自作,長久貽誤後學。他平生還曾因性格缺陷與多人交惡,對他人評價多刻薄、主觀。如他曾評價章學誠:“而其短則讀書魯莽,糠秕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變,泛持一切高論,憑臆進退,矜己自封,好爲立異,駕空虚無實之言,動以道渺宗旨壓人,而不知已陷於學究雲霧之識。”(9)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81頁。這一評價當然與章學誠的治學方法和成就嚴重不符,但移用來評價李慈銘自己評述小説(不包括文言小説)、戲曲的方法和結論倒是比較貼近實際情况的。李慈銘爲追求標新立異,没有任何根據地提出《桃花扇》刻本中的批語爲孔尚任自作,是違反古今學術規範的。而後來的一些學者,對於他在日記中隨手寫下的無端揣測的文字,“耳食其言,以爲高奇”(10)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第781—782頁。,不僅不加質疑,反而盲目信從,使這一錯誤較長期流傳,誤導了一些研究者和讀者。

二、 相關文獻資料的整理和研究
文獻資料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對文獻資料進行搜集、整理、考辨和闡釋是開展學術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和前提條件。文獻資料的新發現可以推動研究的新進展,而文獻資料的缺失則會制約研究的深入和提高。學術觀念的變革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則可以幫助擴展文獻資料搜集的範圍、促進文獻資料整理、彙編的方法和形式的完善。戲曲的創作、演唱和研究在中國古代多受輕視和貶低,戲曲史料又更爲多樣而龐雜(包括文字、圖畫、音像和實物),由於思想文化觀念和記録、保存、流傳的技術條件的限制,中國古代對於戲曲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一般範圍狹小、挖掘不深、流傳不廣、散佚嚴重。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隨着西方現代學術思想傳入我國并發生影響,在當時特殊的社會政治文化語境下,戲曲、小説等通俗文學受到空前重視和嚴肅對待,地位大大提升。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戲曲研究興起後,爲開展研究之需,學者們也重視和開始較大規模地、不斷深入地挖掘、搜集、整理和匯輯戲曲文獻資料。民國時期,這項工作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新中國成立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劇碼調查、整理和論著整理、彙編等多個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新時期特别是新世紀以來,國家、高校和科研機構更爲重視戲曲文獻資料搜集、整理工作,也有更多學者在這方面投入精力和心血,取得了更多、更好的成果,如《南戲大典》、《昆曲藝術大典》、《民國京昆史料叢書》、《京劇歷史文獻彙編》(清代卷)、《清代散見戲曲史料彙編》等。從搜集、整理、以供自用到專門輯録、服務學界;從戲曲、小説、曲藝混雜不分(如錢静方《小説叢考》、蔣瑞藻《小説考證》)到專録戲曲史料,從注重專書到擴大到單篇(條)、實物和口述史料,百餘年中對於中國古代戲曲文獻資料的搜集範圍更廣泛,涉及的文獻類型更多樣,分類更細化、準確,整理方法更趨完善,也更便於利用。戲曲文獻學從興起、形成到不斷發展,逐漸走向成熟,成果層次不窮,而且始終與中國戲曲史學、戲曲研究、戲曲理論批評研究的發展相伴隨。
目前較爲全面、系統地搜集、整理和輯録有關單部戲曲作品的文獻資料的資料彙編主要集中在幾部古代的名劇。有路工、傅惜華編《〈十五貫〉戲曲資料彙編》(作家出版社1957)、霍松林編《西厢彙編》(山東文藝出版社1987)、徐扶明編著《〈牡丹亭〉研究資料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侯百朋編《〈琵琶記〉資料彙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伏滌修、伏濛濛輯校《〈西厢記〉資料彙編》(黄山書社2012)、周錫山編著《〈西厢記〉注釋匯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周錫山編著《〈牡丹亭〉注釋匯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等。這些資料彙編可以分爲三種不同的類型。《〈十五貫〉戲曲資料彙編》(作家出版社1957)和霍松林編《西厢彙編》側重於整理、收録同題材文藝作品,包括本事作品和改訂作品。《〈牡丹亭〉研究資料考釋》《〈琵琶記〉資料彙編》和《〈西厢記〉資料彙編》側重於按照史料的内容性質的不同分類整理、輯録有關各劇的文獻材料。《〈西厢記〉注釋匯評》和《〈牡丹亭〉注釋匯評》輯録了一些有關兩部劇作的古代批評文字,而主體是注釋和現代研究論文。而對於代表着昆曲傳奇最後輝煌的《長生殿》和《桃花扇》,至今却没有學人專門搜集、輯録和出版有關這兩部劇作的文獻資料。
近二十年來,對於《長生殿》和《桃花扇》相關文獻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及其成果據其性質和類型可以分爲如下兩類。
第一類是對於《長生殿》和《桃花扇》相關文獻資料的搜羅、整理和研究。在劉世珩編輯、刊印暖紅室《匯刻傳劇》後很長一段時間内,學者們主要在有關兩劇的論著中提及少量常見、易得的文獻資料,而且基本集中在批評研究方面。隨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西方接受美學思想和論著被譯介入我國,並産生影響,研究者擴大視野,開始關注和研究兩劇的流傳、接受和影響情况,相關的文獻資料也得到挖掘、搜集和利用。如朱錦華的博士論文《〈長生殿〉演出史研究》(上海戲劇學院2007)和陳仕國的《〈桃花扇〉接受史研究》(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但前者所搜集、利用的史料僅限於演唱和接受,後者在引用史料時存在大量的諸如錯别字、斷句、標點等本可避免的低級錯誤。《〈桃花扇〉接受史研究》對於某些文獻資料的作者的判斷和論述也存在嚴重錯誤。如第一章第三節“民國時期《桃花扇》刊本”“一、案頭本”所列的第一種初版於1924年6月、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發行的《詳注〈桃花扇〉》的版權頁明確標明“詳注者”爲賀湖散人,其人並非陳仕國所認爲的盧前,自然初版本卷首署名“壬戌孟夏賀湖散人”的序也非盧前所作。此外,《詳注〈桃花扇〉》中收録的眉批皆采自《桃花扇》的清刻本,並非如陳仕國所説的“皆不同於清代刊刻本”(12)陳仕國:《〈桃花扇〉接受史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年,第51頁。。又如王小恒、單永軍等對於《桃花扇》詠劇詩的初步搜集和分析。此外就是多篇研究《長生殿》《桃花扇》的傳播、接受的碩士學位論文。
《長生殿》和《桃花扇》在國外也有比較廣泛的傳播、接受和影響。李福清、王麗娜等曾對國外《長生殿》和《桃花扇》的翻譯情况和研究論著做過零星、簡單的介紹。而這兩部劇作産生影響主要還是在日本、朝鮮半島等國家和地區,日本學者在對這兩部劇作的譯注、研究方面有比較多而突出的成果。日本著名學者青木正兒在其《中國近世戲曲史》中稱《長生殿》和《桃花扇》“並爲清代戲曲雙璧,爲藝苑定論”(13)[日]青木正兒原著:《中國近世戲曲史》,王古魯譯著、蔡毅校訂,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83頁。,這也代表了近現代中日戲曲研究者的一致看法。戲曲作品的跨文化、跨語際傳播、接受是戲曲接受史研究的一項重要内容。而自江户時代中國的戲曲劇本輸入日本,戲曲作爲兼具文學性、音樂性和舞臺性的綜合藝術便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領域,戲曲研究也是近現代中日學術研究現代轉型和成果積纍的重要體現。被目爲經典名劇的《長生殿》和《桃花扇》在日本的接受和研究,是中日文化交流、學術影響的一個具體而典型的案例,具有多重的價值、意義。日本學者對《長生殿》和《桃花扇》的接受、研究前後之間有影響和承傳,借此可窺見日本近現代戲曲研究進展的一些綫索;中日的評論、研究之間也存在借鑒和互滲,共同推動了《長生殿》和《桃花扇》的現代研究。對於國外有關兩劇的資料的整理、評介有仝婉澄《日本明治時期〈桃花扇〉題詠詩輯考》(《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第六輯,2018年12月),對明治時期(1868—1912)多位詩人的有關詩歌進行了初步的搜集、介紹;程芸《孔尚任〈桃花扇〉東傳朝鮮王朝考述》(《戲曲研究》第102輯,2017年7月)鈎稽朝鮮王朝《燕行録》和文人文集中的相關資料,並做了簡要考述。
另有一項特殊的資料,即梁啓超批注《桃花扇》的文字。梁啓超爲《桃花扇》作批註,所據的底本爲刻本,主要形式是“頂批和注解”(14)熊佛西:《記梁任公先生二三事》,夏曉虹編《追憶梁啓超》,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第353頁。。這些批註後來被移録於一種現代的話劇劇本體裁的《桃花扇》版本之上,排印於劇作正文每出的末尾,在1936年被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飲冰室合集》,列爲專集第九十五種,收於第二十和二十一册中。所以中華書局版《桃花扇注》的劇作正文中也存在個别文字錯誤。在卷首另有一篇《著者略曆及其他著作》, 主要評價了孔尚任的另一部劇作《小忽雷》。梁啓超在批註中援引了較大量的詩文别集、筆記、雜著和史書對於劇作人物的原型和情節本事進行了考察和介紹,有較大的參考價值。梁啓超的《桃花扇注》有鳳凰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整理排印本,將注文排於正文相關文字之後,便於閲讀。但正文和注文中都存在大量的錯别字和標點符號的低級錯誤。卷首的《著者略歷及其他著作》中便有以下多處文字錯誤:“感皇恩”誤作“戚皇恩”,“純任自然”誤作“絢任自然”,“誤作”誤作“饌作”,“《芝龕記》”誤作“《芝鑫記》”。
第二類是有關資料的目録的編制,爲進一步的整理、研究提供了綫索。如朱錦華的博士論文《〈長生殿〉演出史研究》的正文後的六項附録,分别簡要羅列、介紹了《長生殿》的版本、研究論著、同題材劇本及演出、折子戲、唱片和録影帶等資料的情况,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三、 對《長生殿》《桃花扇》文獻整理、研究的反思
如上所述,當前對《長生殿》和《桃花扇》的各類文獻資料缺乏全面、系統地挖掘、搜集和整理,而這嚴重制約了批評、研究的拓展、深入和提高。如蔣星煜先生曾發表兩篇文章《〈桃花扇〉在清代流傳的軌跡》和《〈桃花扇〉桃花扇從未被表演藝術所漠視——二百多年來〈桃花扇〉演出盛况述略》,搜集了一些史料,論證該劇“並未絶跡於清代舞臺”,而是經常上演。但文中所用作論據的詩文還不够豐富和充分,而且没有梳理出清代《桃花扇》舞臺演唱的發展軌跡和特點。後有顔健發表數篇文章探討這一問題,但是將《桃花扇》的舞臺演唱和案頭閲讀、影響合併考察,所涉及的詩文史料雖有有所豐富和擴展,但論述不充分,也没有揭示《桃花扇》的演唱由全本戲向折子戲演化的趨勢和原因。而且兩人的文章中存在相同的史實錯誤,即認爲和相信《桃花扇》曾在清宫内上演,康熙皇帝曾親自觀看、稱賞,並興發感歎。但其實至今没有直接、可靠和確鑿的文獻資料可以作爲證據證明這一點。這一記載是從吴梅開始的。吴梅在《顧曲麈談》説: “相傳聖祖最喜此曲,内廷宴集,非此不奏,自《長生殿》進御後,此曲稍衰矣。聖祖每至《設朝》《選優》諸折,輒皺眉頓足曰: ‘弘光弘光,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往往爲之罷酒也。”(15)吴梅:《顧曲麈談》,《顧曲麈談·中國戲曲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8頁。《長生殿》《桃花扇》兩劇確曾進入内廷,並得御覽。孔尚任自己在《本末》中就有自述:“己卯秋夕,内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繕本莫知流傳何所,乃於張平州中丞家覓得一本,午夜進之直邸,遂入内府。”(16)孔尚任:《本末》,王季思等注《桃花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7頁。但吴梅顛倒了前後的時間順序。《長生殿》完成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王應奎《柳南隨筆》卷六記載: “《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王稱之。”(17)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23頁。如果所記屬實,則康熙帝觀看《長生殿》當在康熙二十七、二十八年間。而《桃花扇》的完成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已在十年之後。吴梅既稱“相傳”,又自認這一描述屬於“軼事”,而且不見《顧曲麈談》前其他現存的文獻資料和著述的記載,所以儘管不清楚這一描述的來源,但可以確定它只是傳言,未曾真實發生過。但自從吴梅將其寫入《顧曲麈譚》,這一傳言便在一定範圍内傳播,並爲一些論者接受和相信,在他們的論述中重述或提及。首先便是吴梅的弟子盧前的《明清戲曲史》《中國戲劇概論》,其他還有梁乙真《中國文學史話》、許之衡《戲曲史》講義等。蔣星煜先生還在《〈桃花扇〉桃花扇從未被表演藝術所漠視——二百多年來〈桃花扇〉演出盛况述略》一文中認爲孔尚任在《本末》中所説的“遂入内府”的“内府”指的是“清代掌管宫廷演劇事務的機構,其地址位於今北京市南長街南口。這一結構隸屬於内務府,但内務府設於西華門内,在北面,故此處又被稱爲南府。”(18)蔣星煜:《〈桃花扇〉從未被表演藝術所漠視——二百多年來《桃花扇》演出盛况述略》,《藝術百家》,2001年第1期,第53頁。但其實孔尚任所説的“内府”是泛指宫廷或内廷。
又如鄧小軍在其《董小宛入清宫與順治出家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下部第九章中結合一些詩作,用一章的篇幅考察、論證洪升創作《長生殿》是以唐明皇、楊貴妃的帝妃愛情故事隱喻董小宛入清宫和順治出家。而其實早在1931年梁品如便在其《〈長生殿〉本事發微》(初刊於《津逮》1931年第1期)中依據相同、相似甚至更多的史料做出了同樣的推斷。梁品如的《〈長生殿〉本事發微》初稿撰於1931年4月,刊載於《津逮》1931年第1期,1931年6月發行;又刊載於《工業年刊》1931年第1期,1931年7月發行;後“重訂”於1940年元月,刊載於《經世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6月發行。“重訂”本與初稿本個别字詞稍有差異,“重訂”本篇尾附有署名“一山”即蕭一山的“附記”文字,對文章的内容和觀點做了平允、精當的評價。
因此,很有必要從清代、民國間中國和域外《長生殿》和《桃花扇》的版本、别集、總集、選集、戲曲、小説、曲譜、曲選、筆記、雜著、日記、信劄、方志、檔案和報刊等中深入挖掘、廣泛搜集有關這兩部劇作的成書、刊印、流傳、演唱、接受、批評、研究、影響等的第一手的大量文獻資料,精當選擇,審慎取捨,考辨真僞,精心校勘,妥當分類,有序排列,最後集成爲一部搜羅豐富、内容準確、分類明確、條理清晰、方便利用的資料彙編。集中豐富、系統的資料,使研究者省去許多翻檢之勞,爲研究提供綫索,有利於開拓研究視野,不僅能爲《長生殿》《桃花扇》文獻資料研究提供比較豐富的材料,也可以幫助推動劇作文本研究、批評史研究更加深入發展和不斷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