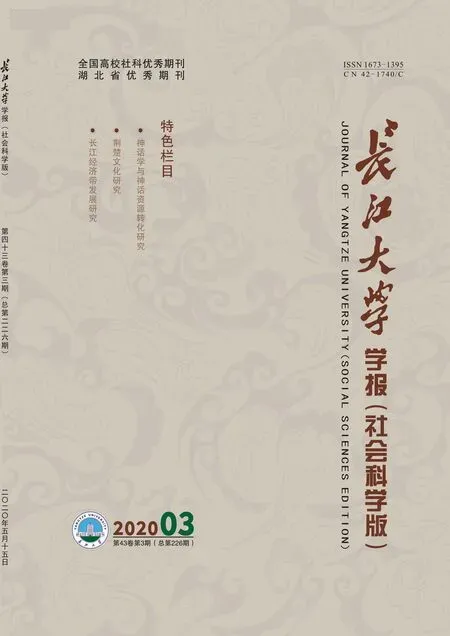秦“安陆”故址新证
王先福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7)
安陆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县级行政区,至迟于战国时期设县,并沿用至今。在传世文献中,安陆设县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为西汉新设江夏郡所辖,东汉因袭,但秦“安陆”不见于传世文献。1975年云梦睡虎地M11出土的《编年纪》为秦设安陆县找到了直接证据[1](P4)。
《编年纪》有四处提到“安陆”:“(昭王)廿九年(前278),攻安陆”,“(秦王政)四年(前243),十一月,喜□安陆□史”,“(秦王政)六年(前241),四月,为安陆令史”,“(秦王政)廿八年(前219),今过安陆。”时代跨度从战国晚期到秦统一初年,前后达60年,其中昭王廿九年正是秦拔郢之年。其后,今江汉平原、随枣走廊和南阳盆地南部都纳入到了秦的统治范围。鉴于《编年纪》将“安陆”与“新城”“宛”“鄢”“邓”“邯郸”等当时其他“六国”的重要城邑并列,其地位显然十分重要。同时,结合秦拔安陆在同年秦拔郢之后的情况看,安陆被秦攻陷之前应该为楚邑,甚至楚县,而从“喜”先后担任“安陆□史”“安陆令史”的自述分析,秦攻陷楚安陆后,最晚于秦王政四年(前243)设置了秦安陆县,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南巡经过安陆。
新近出土文献《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之《水陆里程简》也印证了秦置安陆县的史实。《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抄写年代考证为秦王政三十一年(前216)和三十三年(前214)[2],其中《水陆里程简》多处记载有“安陆”与周边城邑、乡亭的陆路里程[3](P177~279),“安陆”出现的频次也较高,足见“安陆”在当时的地位。而楚“安陆”见于包山二号墓楚简:“十月辛巳之日,不将安陆下邑里人屈犬……。”(简62);“辛未,安陆人陈环、陵人番乙。”(简181)[4](P20~21,30),从简文表述特别是前者表述来看,安陆确为楚县。经研究,包山二号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的公元前316年[4](P333),而秦攻安陆为战国晚期偏早的公元前278年,如此短的时间,加上其时楚秦之间的战争密集且楚国处于败退局势,楚国基本无力他顾,因此安陆县治所的位置应该不会有变化,即秦安陆县继承楚安陆县而来,而楚安陆县的设置时间应该更早,具体时间目前难以考证。
关于秦安陆县故址所在,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一是认为秦安陆县即今安陆县(市),其主要依据是《水经注》关于“安陆故城”的记载。据《水经注》卷三十一记载:“涢水又径随县南,随城山北,而东南注。又南过江夏安陆县西,随水出随郡永阳县东石龙山,西北流,南回,径永阳县西,历横尾山,即《禹贡》之陪尾山也。随水又西南,至安陆县故城西,入于涢。故郧城也,因冈为墉,峻不假筑。”清人杨守敬认为此“郧城”即“安陆故城”,属地为清安陆县城(今安陆县城前身)。[5](P380~381)
二是认为古安陆县在随州淅河镇。主要是今人石泉先生据《水经注》的上述记载考证,认为秦汉晋宋齐梁时期,安陆县在今随州淅河镇,梁末将安陆县治迁至今安陆市附近。[6]
三是认为秦安陆县在今云梦城关“楚王城”。主要通过云梦睡虎地秦墓、楚王城城址等十余个遗存的考古发掘资料分析后得出此结论。如黄盛璋先生“从而证明今天的云梦古城城址是楚安陆入秦后新建或扩建的新地城”,“所以此云梦古城应该就是秦安陆县城”。[7]刘玉堂先生不同意黄盛璋先生“安陆”即“新地城”的观点,但明确“至于秦之安陆县城是否即今云梦古城,我认为可做肯定”[8]。
秦安陆县究竟是上述三地之一,还是另有新地,前人已对传世文献资料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分析,我们主要通过出土文献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考古遗存的调查、发掘资料进行论证。
睡虎地M11秦简《编年纪》虽对“安陆”有记载,但根据该墓墓主“喜”的文字内容,无法直接确定其葬地与安陆的关系。从“喜”的履历看,他担任过“榆史”“安陆□史”“安陆令史”“鄢令史”“治狱鄢”,黄盛璋先生结合文献考证“令史”为秦时“令”的办事人员,地位在县丞之下;“治狱”即“治狱吏”,地位较“令史”高[9]。作为一县之吏的官员,其生前居住于县城内或附近是合理的,而“喜”先后任职于“榆”“安陆”“鄢”等三地,那么他居住在后两地的可能性更大。《编年纪》记“喜”于秦王政七年(前240)“治狱鄢”;秦王政十三年(前234)至二十三年(前224),“喜”从军,并先后参加了攻韩、赵、魏、楚(荆)的多次战争;秦王政二十七年(前220),其子穿耳出生,由于此时秦已统一,他很可能回到了居住地;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今过安陆”。刘玉堂先生分析,当时“喜”“正在安陆,无疑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故才记下这件事。不难想象,墓主死后应葬于安陆境内。”[8]既然《编年纪》所记“喜”的最后一个地名为“安陆”,“喜”生前应该就居住在安陆城内或附近,死后葬于睡虎地墓地。
而且,墓地同时期的秦墓M4出土的两件木牍文书也透露了安陆县与睡虎地墓地的有关信息。睡虎地M4的两件木牍是两封家书,是“黑夫、惊”写给其兄弟“中(衷)”的,信的主要诉求是请其母寄钱和夏衣给战争前线的他们,其中11号木牍记载:“今书节(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禅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来。其丝布贵。徒[以]钱来,黑夫自以布此。”[10](P25)很显然,文中的“安陆”为有丝布坊市的县城,其母、兄住地必定就在“安陆”城内或附近,按照生居死葬的一般规律,作为收信者的“中(衷)”死后下葬于睡虎地墓地,成为M4的墓主,则其生前居所的县治安陆城就在附近,睡虎地墓地也正是安陆城居民的墓地。
同时,睡虎地墓地多座墓葬出土了较多“安陆市亭”方形戳印的陶器,也为二者的关系提供了旁证。第一次发掘的“喜”墓(M11)出土的2件陶瓮(M11︰8、M11︰41)、1件小陶罐(M11︰32)、1件小陶壶(M11︰33)和M14︰2之陶瓮肩部有“安陆市亭”戳印[10](P47~49);第二次发掘的1件陶小口瓮(M33︰37)肩上也有“安陆市亭”方形戳印[11];第三次发掘的墓葬出土陶器中,至少有7件小口瓮(M44︰14、M45︰8及M47︰1等5件)和2件小壶(M44︰22、M49︰21)、1件甑(M44︰19)、1件盂(M45︰49)、1件釜(M44︰25)肩、腹或底上有“安陆市亭”方形戳印[12]。该墓地出土的“安陆市亭”戳印陶器共10余件,随葬的墓葬相对集中,其中M11、M44各4件,M45有2件,M47有5件,M14、M33、M49各1件,时代为秦统一之前的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安陆市亭”戳印的风格十分接近,方形,左右各两字,字体相似,阴刻,以印模方式压盖到陶器上。目前发现的“安陆市亭”戳印陶文仅发现于本墓地及其东南不远处的龙岗墓地(详见后文)出土的陶器上,其他地方尚未发现。鉴于陶器的易碎特性,其在当地烧制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同处睡虎地墓地的M77出土了2137枚西汉文帝前元十年(前170)至文帝后元七年(前157)间的简牍,其内容显示墓主“越人”为西汉安陆县官员。简文内容丰富,包括质日、官府文书、私人簿籍与律典、书籍等,其中多处提到了“安陆”(县),如《质日》类“丙辰,销令豨守安陆”;“庚申,安陆汤沐邑邑除令到”;《官府文书》类“正月庚子,安陆丞毋择告武阳、阳武乡啬父”等[13,14,15]。这些记载间接证明了西汉安陆县就在墓主下葬的睡虎地墓地附近的事实,与《汉书·地理志》所记安陆县相符,表明西汉安陆县正是沿袭秦安陆县而来。
确定了睡虎地墓地与“安陆”的关系后,我们借助考古调查的方法在其周边进行搜索,发现墓地的东侧就有一座大型古城遗址——楚王城城址,且为其周边唯一的遗址。
楚王城城址经过三次调查和三次小规模的发掘,获得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城址位于今云梦县城关镇,平面近长方形,西部稍窄。东西最长2公里、南北最宽1.2公里左右,四周城垣各保存一部分,城址中部有一条南北向城垣,将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城外有护城河,现存北城门;城址四角有高台建筑基址。城内断面可见文化层深度为2~3.5米,最深4.5米。西城内曾挖出排水管道和6口井集中的水井区。城址南垣外脚下发现西周遗存,城内暴露有丰富的东周秦汉时期的遗物。北垣叠压在包含东周遗物的地层上,东城北垣上发现了一座西汉初年的墓葬。由此初步判断,该城始建年代不晚于战国,东城可能在西汉初期一度废弃;东城内还发现东汉、唐、宋墓葬多座,推测东城在东汉时期成为墓区[16]。考古发掘进一步丰富了城址的资料,第一次试掘城址中、南区,确认遗存时代为战国秦汉时期,西城北垣东端由主墙和内外护坡组成,城垣叠压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文化层上,推测建城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城垣上发现了一座西汉早期土坑墓,或许其废弃时代在秦统一后。[17](P153~166)第二次在西城内东、中区发掘,东区为战国、西汉时期遗存,中区为两汉至唐宋时期遗存,似乎均缺乏战国至西汉之间的遗存[18],同时也表明东城很可能在两汉后废弃。第三次选点城址为中、南垣结合部,清理的遗存分三期,分别为春秋、战国中晚期、西汉初期。从发掘资料看,南垣与整个大城建筑年代相同,南垣底部叠压在战国中期地层上,且南垣出土遗物均为战国中晚期,这表明大城的始建年代不早于战国中期,不晚于战国晚期;而中垣叠压在南垣上,其上文化层时代为西汉初期,但城垣夯土内未见晚于西汉初年的遗物,推测中垣建于西汉初期。再根据中垣曾发掘出东汉早期砖室墓来推测,该城的废弃可能在东汉早期或略早[19]。
无论是调查还是发掘,均表明楚王城城址始建于战国中晚期。结合西汉初期墓葬分析,该城北垣很可能在秦末或西汉初年有短暂被废的情况,或与当时的时局动荡相关。鉴于调查或发掘时城垣的高度已被破坏,最高仅残存4米,与实际筑城的高度差距较大,我们推测在西汉初年后,城垣有个增筑的过程,并加筑了中垣。东汉早期及以后墓葬在东城内的发现,证实至少东城应废弃于东汉早期。同时,东城内分别发现的东汉前期[20]和东汉末期墓葬[21](P338)也印证了其废弃的年代不晚于东汉早期。而西城内的文化遗存在两汉至唐宋间出现缺环,表明西城在东汉时期被废弃。据此推断,楚王城城址的始建、使用年代应该为战国中期至东汉早期,城外较为密集的同时期墓地也为楚王城城址的时代和性质提供了依据。
前述睡虎地墓地是城外规模较大的墓地,除了三次发掘的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墓葬外,第四次发掘了29座同等规模、形制和出土随葬器物基本相同的同时代墓葬;2006年第五次发掘了M77,出土漆、木、竹、陶、铜、铅、石器等随葬器物37件,以及2137枚简牍。根据随葬器物形制和简牍纪年分析,墓葬的时代为西汉文帝末年至景帝时期[13]。该墓地出土了大量漆器,秦墓的相当部分漆器上针刻、烙印文字与符号,文字中“亭”“里”“市”等字的出现频率很高,有的地方还加上了地名,如“咸亭”“郑亭”“路里”“钱里”“咸市”“许市”等[10,11,12]。很显然,这种加了地名的“亭”“里”“市”应是器物制作地和输出地或制作者的居住地,但均不见同墓地陶器上的“安陆”地名。结合“咸”指代当时的咸阳看,这些漆器应均为外来品,便于携带和长途运输,说明当时的商品生产已集约化。陶器易碎,基本上只能在本地生产。此外,在睡虎地墓地北侧约200米处的木匠坟曾发掘了20座战国秦汉墓葬,其中部分漆器上也有“亭”“市”等字。[22]
从墓葬分布和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状况看,睡虎地与木匠坟很可能为同一个墓地,其所处的岗地正是楚王城城址外一处战国末年至西汉早期的大型低级官吏、中小地主和平民墓地,应该还有大量墓葬埋藏在汉丹铁路及路旁的铁路货场、火车站下,只是在早年修路时已被破坏。
在楚王城城址外围周边特别是南部,我们陆续发现和发掘了多个同时期的墓地。城址外西南角的大坟头墓地发掘了3座西汉早期墓葬,其中西汉初年的大坟头一号墓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不少漆器有与睡虎地墓地类似的“亭”字等烙印、针刻文字。据墓内一方玉印文判断,墓主为“速”,联想到睡虎地墓地M11《编年记》有“五十六年,速产”的记载[1](P4),或许二者为同一人,若此,两墓地及楚王城城址之间更有紧密的联系[12,23,24]。
城址中段南城垣外450米处的龙岗墓地,分两次发掘战国晚期秦至西汉早期的墓葬15座,其中多件漆器有烙印、针刻文字,5件瓮、2件罐、2件釜、1件盂等10件陶器肩或底部有“安陆市亭”方形戳印,并出土了一批简牍[25,26,27]。
城址东部南约250米的珍珠坡曾发掘了10座战国早、中、晚期和秦末至西汉初年的小型土坑墓[28,29];城址东部南约300米的老虎墩墓地清理出战国秦汉墓葬20余座;城址东部南约400米的郑家湖墓地(龙岗墓地东北约300米)曾先后两次清理70余座战国墓葬[30](P336);位于龙岗、郑家湖墓地之间的江郭墓地于2018年勘探发现墓葬100余座,已清理55座,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
可以说,上述墓地除极少量战国早期墓葬外,时代均从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正好与“楚王城”的始建和繁盛时代相一致。
《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记录了一条江陵—竟陵—安陆—沙羡的东西向干道:
江陵东到井韩百六里。(04-064)
井韩乡到竟陵九十八里。(04-065)
竟陵到郧乡百廿里。(04-77)
郧乡到安陆百卅里。(04-078)[3](P230)
同简另有一条记载“竟陵到安陆二百五十里。(04-215)”[3](P232),正合上述竟陵—郧乡—安陆里程之和,两条记录可相互印证。
按照简单的数学加法,从江陵东出前往安陆的距离为454里,以秦里约合今里415.8米[31](P10~11)计算,该距离约为188.77公里。
江陵即秦南郡郡治,专家们一致认为其在今荆州市荆州区郢城遗址,文献、考古证据十分充分,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按照现行数据分析,从郢城往东(或东北)至今云梦楚王城城址的直线距离约163.5公里,到今安陆市区的直线距离约173公里,而到今随州淅河镇的的直线距离为188公里。很显然,江陵到安陆之间的道路里程不可能为直线,如果考虑到当时这里为古云梦泽地域,道路蜿蜒曲折程度更高,则曲线188.77公里为郢城至楚王城城址的距离似乎更为合理。
楚王城城址第三次发掘的南垣下叠压的战国中期遗存是与建城时代基本同时的遗存,那么,在该城建成前城内外有没有更早的文化遗存?这或许能为楚王城选址建造的背景提供一点线索。
《明一统志》卷六十一《德安府》载:“楚王城在云梦县治东。按《左传·定公四年》,吴入郢,楚昭王奔郧,盖筑此城以自保也。”道光《云梦县志略》卷一《史迹》载:“楚王城,吴入郢,昭王奔云梦所筑。”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云梦县有楚王城在县东,左传定公四年吴入郢,楚昭王奔郧城,因以名。”故传统观点认为,楚王城为楚昭王所筑,其前身或为郧国故城。
从楚王城城址的调查、发掘和清理来看,春秋以前的遗存有三次。被认为时代最早的遗存是1992年在城址内清理的H11,其填土分为两层,出土较多的陶器残片,复原鬲、甗、盆等陶器7件。整理者根据陶器的对比推测,该灰坑下层的时代不晚于西周晚期,上层为春秋中晚期。[32]现在看来,这一时代划分需要重新认识。简报将H11下层复原的鬲、甗与枣阳毛狗洞[33]、沣西张家坡[34]、均县朱家台[35]等西周遗存出土的同类器进行对比,其主要特征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鬲口沿。从类比的相似度来看,H11之A型鬲、甗分别与枣阳周台遗址战国早期A型Ⅴ式鬲、战国中期Ⅴ式[36](P34~101)十分接近,A型鬲整体形制、纹饰还与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仿陶铜鬲(C·126)[37](P203)和庙台子遗址战国时期AⅠ、AⅡ式鬲[38](P177)类似,就是与战国中期的擂鼓墩二号墓之A型仿陶铜鬲(M2︰78)[39](P51)相比,也有较大的相似性,只是后者肩部圆凸,时代稍晚。而H11之B型鬲与宜城郭家岗遗址战国中期晚段AⅨ式鬲[40]相比,整体风格相同,只是本鬲的裆线稍高,时代应较早;由此推断,H11的时代不早于战国早期。同时代或稍晚的遗存是1987年第三次调查在城址南垣外发现的西周遗存[16],因为陶片较少且残,划分时代的难度较大;从鬲口沿卷沿的情况看,将其时代定在西周显然偏早,应与上述H11鬲口沿相近,很可能为战国早期。1992年第三次发掘的中、南城垣结合部的第8层,即第一期遗存被发掘者推定为春秋时期,甚至推定有春秋早期的遗物[19],该层出土的陶器也少而碎,主要为卷沿鬲口沿、深腔鬲足、广肩瓮口沿,以及筒瓦、板瓦残片等。卷沿鬲是战国早期的典型器物,出土的筒瓦、板瓦的时代也相对较晚,不早于战国。也就是说,楚王城城址最早的遗存不会早于战国早期,这与1987年第一次试掘叠压在西城北垣下的文化层时代正好吻合。前述城外珍珠坡墓地时代最早的墓葬也为战国早期,这应该不是巧合。
可以说,不论城址的始建年代,还是城内文化遗存最早时代的界定,都否定了该城曾为春秋时期“郧国城”、楚昭王筑“楚王城”的传统观点。
从城址内发掘的H11等遗存出土陶器的主要特征来看,卷沿微瘪裆深腔足鬲(甗)、折肩(腹)盆、双弓耳罐等显然是曾文化的风格,这从对比的枣阳周台遗址、随州庙台子遗址、曾侯乙墓和广水巷子口遗址[41]等遗存出土同类器的风格可以看出。而弧裆鬲(如H11之B型鬲、86YCYGc⑥︰1)则是典型的楚式鬲。或许“楚王城”在建城前,这里是曾国的聚落,但也受到了楚文化的强烈影响。楚国出于东进的需要,占领该区域后,在这个地理位置重要的随枣走廊南口选择建城,并设“安陆”县。由于此时北部受到来自秦、韩的压力,楚国或许要据此建立郢都(江陵纪南城)与楚王城北约130公里的楚国重要城邑之城阳城[42](P45~46)的联系,从而保证楚国东出北进的重要交通线,秦白起拔郢、楚顷襄王“东北保于陈城”或许正是走的这条线路。城外珍珠坡、郑家湖、老虎墩等墓地就有较多的战国楚墓与之对应。
正是由于楚王城城址城垣的时代沿用到西汉乃至东汉早期,上述城址外多个墓地的时代也基本相同,这一考古证据表明,至少在东汉早期以前“安陆”县治未移动位置。但城址废弃及城外上述墓地很少见到东汉以后的墓葬,特别是不见集中聚葬的东汉以后墓地,这表明,“安陆”县治在东汉早期以后很可能迁离本地了,其后的安陆县治或已一次甚至多次变动。当然,从城址西部仍然发现有两汉、唐宋文化遗存和城外蔡陈村、袁林两处东汉六朝隋唐墓地[30](P338)的情况看,西城内应一直有人居住。而据《隋书》卷三一志二六《地理下》记载,这里在西魏置“云梦”县,属安陆郡,并延续至今,其县治应该就在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