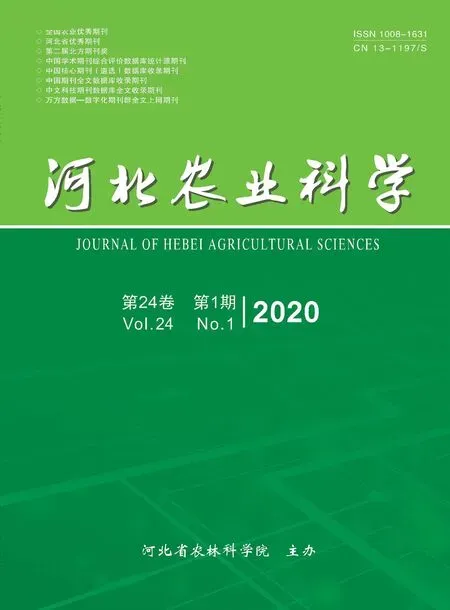基于情感治理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可行性分析
胡博,郝文帅,李平
(1.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北京 100089;2.石家庄学院法学院社会学系,河北 石家庄 050035)
我国已经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是国家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部分,养老问题的解决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的战略部署,并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矛盾日益突出,随着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基于乡土情结和情感纽带的互助养老服务逐渐成为解决农村社区养老问题的新路径。何雪松[1]认为情感治理是以情绪安抚和心理慰藉为目标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情感回应,并从宏观、中观与微观对应社会心态、群体心理、个体情绪理解情感治理的内涵。文军等[2]认为“社区情感治理”的焦点在于通过对社区情感再生产过程的干预来协调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借助对结构性情感、情境性情感和自我关联性情感优化的过程,柔化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重建社区成员间关系并增强成员的社区认同感。成伯清[3]在借鉴西方社群主义的视角基础上切入社会建设中的情感维度,认为社区共同体的实质是共同情感,并探讨了重建共同情感的可能性,并就忠诚之类的情感对社会建设的意义进行了初步分析。王俊秀[4]通过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两各方面探讨社会心态的运行和调控机制,推动社会治理中社会正向情感最大化,实现以社会情感为基础的社会凝聚。虽然学者们对“情感治理”的阐释有所不同,但都关注到社区治理和发展中“软实力”的作用,满足社区的情感需求,注重发挥社区中个人情感和社区凝聚力的作用,从而达到社区的和谐发展。费孝通[5]将中国的农村社会描述成一个“差序格局”,在这个“差序格局”里人们构建起一种基于乡土性的超级信任关系,这种超级信任关系是建立在长达数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下。然而基于这种超级信任关系的互助养老服务,通过激发农村社区老年人的活力和内生动力,在不脱离原有场域和共同体的基础上,通过互帮互助的形式解决农村社区养老问题。作者结合目前我国乡村现状,对情感治理视角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情感治理的3个维度,旨为推动和激发情感治理的效能,探索出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新的突破口,助力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的施行,缓解我国现阶段的农村社区养老压力。
1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内涵和意义
1.1 内涵
互助养老是指采取自愿参加的形式,生活在同一地区的老年人之间相互帮助,进而满足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需求的养老方式[6]。通过引导和动员农村社区老年人积极参与、互相帮助,解决农村社区老年人养老问题。
1.2 意义
一方面,社区互助养老迎合了我国农村社会的现状,老年人之间相互熟悉、相互合作,以邻里、宗族为主要代表的熟人关系,是满足农村社区老年人情感的主要来源。地域性的“安土重迁”深深根植于农村社区老年人的心中,农村社区居民对共同生活的土地具有强烈的恋土情结,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可以满足社区老年人的情感支持。另一方面,在“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传统价值伦理下,发展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是对农村社区家庭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支持和维系。发展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既可以缓解农村社区因劳动力外流而造成的家庭养老服务功能弱化的矛盾,又可以避免因家庭养老服务功能弱化而引起的道德伦理的困扰。
2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的可行性分析
社区情感治理旨在通过对社区居民个体情绪、群体心理和社会心态从多元参与的社区支持网络的思路进行回应和建构,从而达到居民个体情绪的愉悦、人际关系的和谐、社区正能量的传播[7]。情感治理是对社区情感资本的一个重构和利用。而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是在不打破老年人原有的生活区域、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决农村社区养老问题的重要手段,与情感治理本质相同。
2.1 社区关系得以维护与利用
在社区治理任务下,情感治理作为社区治理方式的一种,在维护和利用社区非正式网络的基础上,增强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基础,实现居民互助。我国农村社会是社区居民长期生产劳作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形成的根基是建立在血缘与地缘之上的熟人认同,表面显现为情分或“面子”,深层里确实凸显为将熟人之间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利益关系[8]。因此,在农村社区中会出现基于熟人社会而建立起来的熟人关系和道德准则凌驾于法律框架之上的现象。在熟人关系和道德准则的限制下,会催生出互帮互助的善行义举。农村社区居民受传统礼俗文化的影响,对农村社会中以血缘和地缘为联结的社会关系十分重视,这也使得人们之间构成了由于彼此熟识而产生了相互依赖的利益关系,为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持。
2.2 社会情绪得以引导和支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农村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崛起,个性化需求不断增加。经济收入日益提高的同时,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不断高涨。在参与社区事务中,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当前农村社会主要的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个体在长期社会交往中所体验到和表达着的情绪。一个最大特征便是其“由点到面”不断扩大范围的放大效应[9]。情感治理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注重社区居民主体性的发挥,通过对农村社区居民参与意愿、参与热情的支持和引导,有效提升农村社区老人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旨在通过农村社区老年人互助的方式,既可以激发农村社区老年人社区事务的参与积极性,满足老年人参与社区事务的意愿,又能解决农村社区养老问题。
2.3 共同情感得以重构和提升
熟人社会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内部个体间的熟悉、信任、亲密,信息对称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信息对称更多作为熟人社会的结果状态,信息对称之所以能够得以维持是熟人社会中的公共性和价值吸引力这两种力量在起关键作用[10]。熟人社会的公共性以社区公共情感为主要代表,以社区风俗习惯为主要形式。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情感治理通过利用乡村传统文化节日,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资本,使社区居民通过文化纽带的方式,形成社区凝聚力。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作为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助服务,是以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为基石。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是在增强社区凝聚力的基础上,通过社区老年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而形成的养老服务模式。
3 农村社区面临的情感危机和困境
3.1 农村集体价值体系破碎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钱主义和功利思潮不断涌入,农村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和自我精神不断崛起,自我意识急速膨胀。原有的农村社区集体价值体系在社区居民自我意识作用下受到强烈的冲击并逐渐走向衰亡,而现存的农村社区价值体系则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农村社区现有的乡村价值体系是建立在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基础上的一个相对松散的自我利益的集合,缺乏指导和引领社区居民公益行为的准则与标准,无法引领社区集体行为。
3.2 道德伦理教化功能弱化
农村社区居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农村社区这个差序格局中,道德伦理规范是约束农村社区居民行为的主要方式。随着社区居民自我意识的崛起,社区居民间的社会交往存在功利性,其行为带有明显的目的性。社区居民间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受到强烈冲击,农村社区原有的道德评价准则不断沦丧。道德伦理对农村社区居民的教化功能不断减弱,无法再为农村社区居民之间的行为提供评价体系。
3.3 传统文化凝聚效能降低
优秀传统文化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维系、协调、指导的作用,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体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继承是一个社区强大凝聚力的重要体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推广,以屏幕化为主体的社会化活动严重腐蚀着社区居民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在农村社区中的凝聚功能发挥越来越弱,其中以民俗文化的弱化和消逝为典型代表。农村社区凝聚力的减弱,使得农村社区居民之间的共同情感减弱。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社区逐渐由“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发展。城乡壁垒被打破,城乡互动的增加,冲击着农村社区原有的价值基础和社会结构。农村社区面临着农村集体价值体系破碎、道德伦理教化功能弱化、传统文化凝聚效能降低等情感危机和困境。农村社区情感危机和情感困境的出现严重影响着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实施和推进。
4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实施建议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是建立在农村社区这个极具共同情感的场域之中,是建立在农村社区居民互帮互助的邻里规范和社交原则之上的共益行为,需要以共同情感为基础、以道德伦理为评价标准、以乡村集体价值为导向。基于社区情感和社区信任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和推进,需要情感治理的深入发展。情感治理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在凝聚社区情感、增强农村社区居民社区责任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1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之下,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式,需要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1)要发挥党对社区养老服务的主导作用,发挥党建引领的倡导、整合与协调作用,理顺社区各主体的利益诉求。(2) 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社区价值体系。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和国家价值对接起来,培养农村社区居民的社区责任意识和公共精神,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3) 增强社区共同体意识。通过党建引领作用,把社区居民个人成长与社区治理相结合,激发社区居民的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促使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到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中去。
4.2 着力社会资本培力
在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过程中,要注重社会资本的培力,尤其是社区情感资本的培力。社会情感资本作为一种无形的资产形式,具备了一般资本的特性,需要“投入”和“经营”,从而得到“增值”和带来“收益”,并能够实现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1) 以传统节日文化为载体,以社区共同情感为基础,通过动员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到对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中,增强农村社区居民的认同感。 (2) 树立农村社区道德模范榜样,激活农村社区的伦理道德的准绳作用,重构农村社区的道德评价体系。 (3) 注重社区功能的完善,增加社区居民的幸福感。通过完善社区基础养老服务设施,增强社区居民的专业护理和照顾技能的培训,为社区居民赋能,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4.3 培育社会组织参与
在农村社区开展互助养老服务的过程中,要以农村社区社会组织为组织平台,注重农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参与。社区社会组织是在社区内开展以兴趣爱好、志愿服务等活动,以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民间自发性质的组织,是我国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1) 通过开展主题培训的方式,提升农村社区居民领袖和志愿服务人员的服务技巧和服务水平,使其具有一定的服务能力,提升其服务意愿和服务积极性。(2) 通过公益创投的方式,动员社区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提升社区居民的社区服务意识和团队协作意识。(3) 引导和培育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成立老年协会或者妇女协会等社区内生组织,负责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的管理和运行。
4.4 注重虚实协同发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农村社区开展互助养老服务的过程中,要注重网络平台的应用,注重虚实平台协同发力。(1) 通过制定居民协商议事制度和工作模式,发挥农村社区居民自治的功能,打造线下农村互助养老实体平台。 (2) 通过对网络技术的应用,开通社区居民互助养老服务平台,可以通过网络评选“互助、爱老”模范的方式调动农村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3) 通过搭建网络平台的方式,构建线上农村互助养老虚拟社区,为农村社区在外务工人员提供一个参与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机会,为农村社区互助养老链接多元资源;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宣传忠孝文化和农村社区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提供精确方向,提升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的质量。
农村社会的变革使得农村社区养老矛盾日益加剧。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是建立在共同情感基础之上,以满足农村社区老人情感需要的养老服务模式。在社会交往资本化和社区情感金钱化的背景下,农村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基础不断弱化。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面临情感维系弱化、情感联结形式化的困境。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情感治理的功能作用尤为重要。情感治理不仅能够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动力,还可以推进社区居民的凝聚力。这在同质化较强的农村社会尤为突出。因此,在情感治理背景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具有一定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