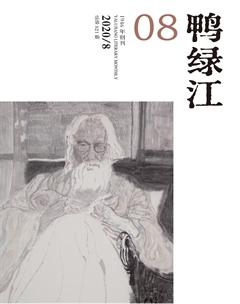伊莎多拉·邓肯:爱过,痛过,自由过
艺术之家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了一篇作文。“……我五岁的时候,住在第二十三条街的一个小房子里,因为没有付房租,不能再住,便搬到第十七条街,不久,我们的钱不够,房东不许延期付款,便又搬到第二十二条街,在那里我们不能安然住下去,于是搬到第十条街……”在全班同学的哄笑声中,老师大发脾气,认为伊莎多拉又在搞恶作剧。这个看起来比其他同学都要小的女孩不是第一次令老师难堪了。她将伊莎多拉带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找来了伊莎多拉的母亲。当母亲读到女儿的作文时,禁不住哭了。她与丈夫离婚多年,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生活,靠音乐教师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伊莎多拉所写的内容都是真的。
伊莎多拉写这些不是因为觉得生活苦。很多年后,她回忆起童年经历,反而很感谢母亲。“我觉得这对于我是一种幸运。她不能替孩子雇请保姆或仆人,因此我在儿童时能发展一种自由的生活,后来一生也没有失掉这种生活。”
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做了一些毛线织品,拿到针织店去卖,但是针织店不收。伊莎多拉就将绒帽戴在头上,手套戴在手上,提着篮子去街上推销。结果东西全都卖出去了,还比母亲预期的价格翻了一倍。勇敢使伊莎多拉早熟,对人生也开始有了独到的认识。她说,“每次听到别人家里的父亲谈论多赚些钱留给子孙,我总觉得他们这种做法夺去了儿女种种冒险的生活。他们多遗留一块钱,便使儿女们多软弱一分。”
十岁的时候,伊莎多拉决定离开学校,因为学校教育令她觉得备受束缚而且乏味。每天晚上,当母亲弹着钢琴或者为他们姐弟朗诵诗歌的时候,才是最令她享受的时刻。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母亲热爱音乐与诗歌。伊莎多拉与她的姐姐和两个哥哥都没有受过太多学校教育,却都遗传了母亲的艺术基因。以至于母亲常常感叹,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实用”之人。但一家人却在富足的精神生活中甘之如饴。辍学之后,伊莎多拉和姐姐一起在家里教授跳舞。她们的舞蹈课不同于古典芭蕾舞课,是一种更新式更自由的舞蹈。伊莎多拉常常会以一首诗歌或一支曲子为灵感创作舞蹈。她们的课很受欢迎。不久,母亲的一个朋友看出伊莎多拉很有跳舞天赋,就介绍她到一位著名的舞蹈教师那里去进行系统的学习。但是伊莎多拉去了三次之后,就再也不去了。因为她觉得那种踩着足尖的舞蹈是反自然的,“非常丑”。她形容芭蕾舞是“呆笨平凡的柔软体操”。她想要的舞蹈不是这样的。“我理想着另一种不同的舞蹈。我还不晓得这种舞蹈究竟是怎样的,我冥想着一种理想的世界,我觉得如果我能得着这世界的钥匙,我就能进去。”梦想已经开始萌芽,此时的伊莎多拉只是19世纪旧金山一个贫穷人家的普通少女,靠阅读狄更斯、莎士比亚,倾听肖邦、贝多芬进行着自我教育,自由起舞出于本能,创作舞蹈源于喜爱。
出于对书中描绘的外面世界的向往,伊莎多拉劝母亲离开旧金山,说自己可以靠跳舞谋生,他们一家一定会过上更好的生活。母亲对小女儿描绘的未来深信不疑,表示愿意跟着她到任何地方去。自此,邓肯一家踏上了漂泊之旅。
然而世界并不像他们在书中看到的那般浪漫美好,伊莎多拉的求職之路也十分艰难,所有的剧院都拒绝了她的舞蹈表演。在芝加哥,为了付房租,伊莎多拉卖掉了身上最后一件值点钱的东西——一个精致的爱尔兰花边领。付完房租后,剩下的钱只够买一箱番茄。这就是他们一星期的食物。为了赚钱,伊莎多拉放弃了舞蹈,在一位演出经理人那里谋得了一个演出哑剧的机会。她跟随剧团来到了纽约。
伊莎多拉在这个哑剧团里待了两年,周薪二十五美元。一家人在纽约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姐姐伊利莎继续教授舞蹈,哥哥奥古斯丁在戏院里做事。另一个哥哥雷曼找到了一份报馆的工作。为了节省房租,他们也把房子租给别人做钟点房。这时候,如果他们没在上班,就必须出去散步。
一个偶然的机会,伊莎多拉结识了青年音乐家雷文,她将雷文的音乐编排成舞蹈,令雷文非常震惊。“你是一个天使,一个女神,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作曲时所想到的。”激动的雷文决定与伊莎多拉一起举办一场音乐会,他弹琴,伊莎多拉跳舞。
音乐会大获成功,轰动了纽约。伊莎多拉成了一位舞蹈新星,上流社会的名媛贵妇纷纷邀请她到自己的家里为各种聚会表演舞蹈。这些表演渐渐奠定了伊莎多拉舞蹈表演的雏形。有时候,她以诗歌为主题。她跳舞,奥古斯丁或伊利莎朗诵诗歌。更多时候,她以著名音乐家的音乐为主题,她跳舞,她的母亲用钢琴弹奏音乐。她按照古希腊雕塑中的装扮确定了自己的着装风格。只穿一件宽大的白袍,浑身没有一件装饰品,赤足舞蹈。
伊莎多拉在纽约渐渐有了名声,但她马上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获得一位艺术家应有的尊重。在众多豪华的客厅表演时,她在那些权贵的眼中,其实与仆人无异。她的收入也没有明显地增加。美国的艺术环境令她失望。二十一岁这年,她决定带着家人到伦敦去追寻梦想。
为了筹集旅资,她开始一一到曾经表演过的富豪之家寻求赞助,但令她没想到的是,收获少得可怜,连买二等舱的船票费用都不够。最终,邓肯一家搭乘一艘运牛的货船抵达了伦敦。
此时,他们已身无分文,只能在格林公园的长椅上过夜。三天之后,伊莎多拉在一张别人丢弃的报纸上捕捉到一个信息。一位夫人正在此地大宴宾客,很巧的是,伊莎多拉曾在她纽约的家里跳过舞。她马上来找这位夫人,告诉她自己已经来到伦敦,在很多富人家里跳舞。夫人很高兴,当即邀请她这个周末过来表演。伊莎多拉成功拿到了一张十英镑的支票。
这次表演令伊莎多拉在伦敦的富豪圈打开知名度,开始有更多的人邀请她去表演。一家人终于在伦敦安顿下来。在这些表演聚会中,伊莎多拉有机会结识了很多英国艺术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伊莎多拉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其他时间,她流连于伦敦的各种博物馆、画廊和图书馆,以旺盛的求知欲汲取着各种知识。在真正成名之前的若干年中,这成了伊莎多拉·邓肯生存和求知的基本模式。其间,她的姐姐和哥哥先后因为婚姻、事业等原因短暂地离开过伊莎多拉和母亲,但最终都又回到她们身边。这个逐渐变成以伊莎多拉为核心的家庭,始终非常重视亲情关系。他们不只有过上好生活的共同家庭理想,也是一个精神共同体,是彼此在艺术上真正的支持者和知音。他们就像一个流动的小小的乌托邦,从不为金钱和物质所羁绊,兴之所至就起身远行,足迹遍布世界。在伦敦待了几年后,邓肯一家又来到了巴黎,后来又到了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直到此时,伊莎多拉的舞蹈才真正走入大众的视野。在布达佩斯,伊莎多拉拿到了人生第一个独舞表演的合同,在乌兰尼亚大戏院,而且是连演30天。
她的人生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此时正是四月,布达佩斯的春天令伊莎多拉沉醉,遍地开满了鲜花,河水闪着金光在太阳下流淌。
伊莎多拉的名字开始响彻欧洲,接下来,在柏林的演出大获成功。在赚了一笔钱后,邓肯一家没有听从演出经纪人马上进行更多巡演的建议,而是做了一个对全家人都更有吸引力的决定——去往他们心中的艺术圣地雅典。
雷曼认为,去希腊的旅程近乎朝圣,因而不能坐舒服的现代客轮,而应该选用更原始的交通工具。于是他们订了一艘小小的邮船。
一路上,一家人特别兴奋。高声吟诵着各种描写希腊的诗歌,像一群快乐的孩子。在渡过古阿奇罗阿斯河的时候,脱下鞋袜在河水里濯足,临睡前谈论苏格拉底、柏拉圖、拜伦和雪莱。
某日黄昏的时刻,他们终于抵达了雅典。向着雅典神庙拾级而上,伊莎多拉感慨万千,“觉得以往的一切生命好像一件微不足道的衣服一样,从我的身上脱去,我仿佛经历了重生,第一次看见了纯洁的美。”
这个理想主义的艺术之家似乎在这里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他们决定在这里建筑一处属于自己的宫殿,成为永久的栖息之地。很快,他们就选好了地址,花高价买下了土地,雷曼按照阿伽门农神殿的样式设计了图纸,然后就雇用工人开始建造。在奠基仪式上,他们请来了一位希腊祭司举办了一场传统的祭祀活动,附近村庄的人都赶来观看了仪式。这个理想的宫殿是个浩大的工程,雷曼负责监工。一家人决定永远留在这里,兄弟姐妹都相约放弃婚姻,彼此终生相守。这段短暂的神话般的时光像一道耀眼的烟花,照亮了邓肯一家的人生,使他们在那一瞬间脱离了凡尘。很多年后,伊莎多拉曾惊讶于这段时光的存在,感慨是激情的青春造就了这不可思议的举动。而在世人的目光中,至少在我的目光中,雅典的岁月,是邓肯一家最性灵的岁月,他们何止是在造梦,更是幻化成了梦本身,美得令人震颤。正是因为这段岁月验证了他们并非凡俗之躯,所以此前此后他们在人间所受的凡俗之苦才更令人心动。站在神庙般宫殿的廊柱间赤足起舞的伊莎多拉形象,自此深深印刻在后世人的脑中,虽然这座虚幻的宫殿从未完工,但这个画面却比任何真实的影像都要清晰。每当提起伊莎多拉·邓肯,这就是她留在我心里最标准的形象。
宫殿建造一半的时候,邓肯一家才发现,这处地址附近没有水源。于是又开始花重金凿井,直至钱财耗尽。雷曼不死心,坚信可以凿出水来,独自留在雅典继续着工程。伊莎多拉重新接了演出合同,带着其他家人离开了雅典。同行的还有十个会用希腊文唱歌的儿童,他们成为伊莎多拉演出的一部分。为了供养他们,伊莎多拉耗费了大量钱财,常常入不敷出。最终她发现,离开希腊后,他们的声音开始丧失昔日的童真,于是买了车票,把他们送回了家乡。
此后,伊莎多拉开始了在世界各地巡回表演的生涯,她的名字和独属于她的心灵之舞开始逐渐被世人所知。
舞蹈学校
伊莎多拉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回家看到有五六个孩子坐在她身边,跟着她的口令在挥舞手臂。母亲很好奇,问她在做什么。伊莎多拉说,这是我的舞蹈学校。母亲笑了,在钢琴旁坐下来,开始为他们弹琴伴奏。创办一所舞蹈学校,从小就是伊莎多拉的愿望。
在把自己的舞蹈同古典舞蹈区别开来之后,伊莎多拉在实践中开始思索自己的舞蹈体系。在巴黎期间,她整日流连在卢浮宫和国立图书馆,一边吸收着其他艺术的养分,一边翻阅有关艺术的各种书籍。后来,她结识了歌剧院图书馆的馆长。这位馆长为她找来了所有关于舞蹈以及希腊音乐和戏剧的书籍,伊莎多拉从这些书籍中系统地了解了从古至今舞蹈艺术的发展历史。她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在融入自己的思考之后,认为对她的舞蹈理论形成最有帮助的有三个人——教育家卢梭、诗人惠特曼、哲学家尼采。
伊莎多拉这样阐释自己的舞蹈教育理念:“普通戏剧歌舞学校所教导学生的,是以脊背骨下为中心点,由此中心枢纽发出四肢身体等等自由动作,但结果是一种呆板机械式的傀儡。此种方法所产生的机械动作,是配不上心灵的表现的。而在我这方面则追求一种心灵的源泉,灌注于身体的各部,使之充满活跃的精神。此种中心原动力,即是心灵的反映。于是我把我一切的精力,集中于此种原动力,这样经过数月之后,我每次一听到音乐,则音乐的各种音节和音波,都好像注射到我内部的此种中心源泉,其所反映的不是理智的背影,而是心灵的背影。此种背影,我可以由跳舞表现之。”此外,伊莎多拉还追求一种原始的动作。“不以自己的意志,根据一种不知不觉的原始的反应,以产生其他很多动作。”在确立自己理论的过程中,伊莎多拉特别喜欢跟艺术家朋友谈论舞蹈,经常会滔滔不绝地讲几个钟头而不知疲倦。讲到兴致高昂处,就起身示范,以验证自己的观点。
1905年,二十八岁的伊莎多拉第二次来到俄罗斯演出,此时,她的舞蹈理论与个人风格基本形成。这次行程中,她结识了伟大的戏剧表演艺术家斯坦尼拉夫斯基,两人经常在一起探讨艺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斯坦尼拉夫斯基的自传中,有大量篇幅谈到邓肯的舞蹈艺术对他的启发,两人可谓艺术上真正的知音。“……从那时以后,凡是邓肯的表演,我没有缺席过一次。我这么急于去看她跳舞,是因为她的艺术激起了内心的艺术感觉。后来我对于她的艺术方法和她的好友克雷格的艺术思想认识清楚之后,我便晓得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因为某种不可知的原因,人们对于艺术都是追求同一自然的创造原则。……我回想起我和她几次的艺术讨论,把我和她表演的方法互相比较,我就觉得我们两人所努力的艺术门类虽然不同,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此时,伊莎多拉的舞蹈在精英艺术家圈子里备受推崇,诗人、作曲家、画家、雕塑家都是观看她演出的常客。这种肯定无疑坚定了她的艺术信念。从俄罗斯回到柏林后,伊莎多拉就和家人一起着手开办舞蹈学校。
然而邓肯一家都不是合格的商人,很多年里,邓肯舞蹈学校都处在破产的边缘,基本是靠伊莎多拉的巡回演出赚得的钱来维持开支。直到巴黎富豪罗亨格瑞出现。
此时的伊莎多拉刚刚与英国戏剧导演爱德华·戈登·克雷格分手,带着他们的女儿独自生活。克雷格在伊莎多拉的生命中有着重要位置,他是第一个真正触动她灵魂激情的人。两个人甚至都认为对方是另一个自己。但克雷格反复无常的艺术家脾气也让伊莎多拉饱尝了伤害。罗亨格瑞的出现,给她带来了以往从未体验过的另一种生活。此前,伊莎多拉的几任男友都是艺术家,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多偏重于精神层面。而罗亨格瑞则在经济上给了她巨大帮助。此后十多年,他都是邓肯舞蹈学校慷慨的赞助者。
两人相识不久,罗亨格瑞就带着伊莎多拉和她的女儿乘上私人游艇前往意大利旅行。展现在伊莎多拉眼前的奢华是她从未经历过的。宽阔的甲板,水晶镶银的餐具,以及五十个人的服务队伍:仆人、厨师、伙夫、水手、大副、船长……为了让伊莎多拉在庞贝古城神庙的月光下跳一支舞,罗亨格瑞甚至雇请了整整一支乐队提前在那里恭候。在伊莎多拉怀孕后,罗亨格瑞更是不离左右,陪同她到美国巡演,之后又乘游艇带着她去埃及过冬。所到之处,她都享受着女王般的待遇。对于经历过极端贫困生活的伊莎多拉而言,这种兴师动众的奢华常常令她感到不安,隐隐感到这种生活不属于她。第二年五月,两人的儿子降生了。
罗亨格瑞向伊莎多拉求婚。伊莎多拉卻说,“一个艺术家结婚,是一件多么蠢的事。我是要环游世界的,你总不能一生都坐在包厢里看我表演吧?”罗亨格瑞回答,“我的游艇可以带着你环游世界,你不必再活得那么辛苦,可以住在伦敦过快乐的日子。”伊莎多拉表示她从未想过要过那样的生活。罗亨格瑞建议至少她可以试试。
伊莎多拉于是住到了罗亨格瑞在德文郡的别墅里。没过多久,她就厌倦了这种无聊的英式乡间生活,重新签订了巡演合同。这段恋情无疾而终。伊莎多拉在回忆录中这样总结了这段生活。“三年中,这种富贵生活给我的经验,是让我得知这种生活是无希望的,自私的。它也证明了一件事,离开了艺术,我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1913年,伊莎多拉的两个孩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她与另一个情人的孩子也在出生后不久夭折。她的情绪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停止了所有演出,独自住在一座别墅里疗伤。最终,是哥哥雷曼把她从伤痛中拯救出来。“伊莎多拉,跟我去阿尔巴尼亚吧。那里需要帮助。村庄都荒废了,孩子们都在挨饿。你还能安心坐在这里顾影自怜吗?”
伊莎多拉跟随雷曼带着羊毛原料来到阿尔巴尼亚。雷曼让阿尔巴尼亚的妇女按照他设计的古希腊式的花样将羊毛织成布匹,并付给她们薪水。他将布匹运到伦敦去卖,然后用赚得的钱在当地开了一个面包厂。雷曼将这些面包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居民,并拿出一部分定期去贫困地区免费发放给没有能力购买食物的人。忙碌的工作冲淡了伊莎多拉对过去的回忆,在帮助别人的快乐中渐渐走出了阴霾。
在罗亨格瑞的帮助下,邓肯舞蹈学校在法国和德国落地生根。在一战期间,学校被迁往美国。1921年,在苏联政府的邀请下,伊莎多拉又前往苏联办学。在有生之年,伊莎多拉为传播她的舞蹈理念耗尽了心力,几乎没有从教育事业中获得过任何财富。但她所倡导的自由精神却随着她的舞蹈传遍了世界。自此以后,舞蹈脱离了狭隘的娱乐功能,使表达深层的精神世界成为可能。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开始具有了与诗歌、音乐、绘画、雕塑同样重要的精神品质。伊莎多拉·邓肯因而被后世尊崇为“现代舞之母”。她在一百年前说过的话,今天听来依然具有钻石般闪光的价值。“我们的小孩,何以要屈着他们的膝头,做那个假意屈服的宫廷的跳舞,或是那种故意浪漫旋转的华尔兹舞呢?反而不如叫他们勇敢地大步走出来,跳着奔着,把头抬起来,把手伸出来,来表现我们祖先那种开拓疆土的精神,那些英雄坚忍的精神,以及他们那种仁爱、公平、政治家的廉洁和母亲爱抚的精神。”
生命中的男人
母亲的经历使伊莎多拉从小就不相信婚姻。她曾仔细研读过婚姻法,认为女性并未在婚姻制度中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激起了她的反抗意识。成年后,她信奉不婚主义,认为女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婚姻,也有权利独自决定是否生育。或许是受原生家庭模式的影响,她很享受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的幸福,成为那个时代不多的未婚母亲之一。
伊莎多拉一生情人无数,这主要基于她自由的天性与爱情观。随着名声日盛,她的情感生活成为普通人热衷谈论和诋毁的话题。但这些从未影响过伊莎多拉价值观上的自我认同。她始终活在凡俗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优秀女性,身处男权社会的精英族群之中,被爱慕、被追求甚至被争夺的机会显然要高于普通女性,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没什么不同。即便如伊莎多拉这样女权意识觉醒较早的人,也无法改变这种现实。所以,她所背负的道德上的灰尘对她本人并不构成意义。这些灰尘实际上只来自普通人的内心,它们的意义在于对平庸的人们生存价值和美德的抚慰。毕竟,每个人活着都需要一些理由和自我说服力。
在伊莎多拉自己的文字记录中,留下了她所处时代很多伟大的名字。以一个女性的目光来看,这些记录都从另一个侧面消解了这些名字的伟大,令他们变得真实可感,离普通人更近。
在巴黎的艺术展上看过罗丹的雕塑作品后,伊莎多拉非常震撼。不久,她去了罗丹的工作室拜访他。她写道:“我去拜访罗丹,正像神话中女神普赛克去寻访山洞里的牧神一样。不过我所追求的不是爱神厄洛斯,而是艺术之神阿波罗。”但见到了罗丹后,伊莎多拉对这场会面的预设就迅速被打破了。罗丹看着伊莎多拉,拿起一小团黏土,在手中不停地捻着。他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发出热气,好像一个火炉一样。不久之后,他捏出了一个女人的胸部,栩栩如生,宛如躺在他的手掌中起伏悸动。后来,两人叫了一辆马车,来到了伊莎多拉的工作室。她开始给他讲述自己的舞蹈理论,兴致盎然。但她注意到,罗丹根本没有在听。“他用半合的眼注视着我,眼里闪着熊熊欲火,接着他带着看作品一样的表情向我走来,他的手触摸过我的唇、我赤裸的腿和脚,开始捏揉我的身体,如同它就是黏土一样……”在如此强烈的爱欲面前,伊莎多拉退缩了。她慌忙将外衣披在舞衣上,请求罗丹离开。事后,伊莎多拉很后悔没有接受罗丹的爱情,觉得这是自己艺术生命的遗憾。她的原话是“我失掉了这神圣的机会,没有把我的童贞贡献于艺术之神,贡献于伟大的罗丹”。但在我看来,或许正是因为她是伊莎多拉·邓肯,才遵从内心拒绝了罗丹。因为,或许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从未被压抑过的天性使她只会因为爱情走入爱情,而不会为了艺术而献身于爱情。
1922年5月,四十五岁的伊莎多拉结婚了。这个令她一生中唯一一次走进婚姻的男人是俄罗斯著名田园派诗人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这一年叶赛宁二十七岁,已经有过一次婚姻,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两人的相识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这样的:1921年11月,苏联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举行了盛大庆祝演出活动。伊莎多拉·邓肯受邀表演了舞蹈。当时,坐在观众席中的叶赛宁对伊莎多拉一见倾心。在朋友的引荐之下,两人相识。为了让伊莎多拉尽快了解自己,叶赛宁当着翻译的面,朗诵了自己的诗歌。伊莎多拉听后,对翻译说:“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觉得很美,因为那是音乐,真正的音乐。”相差十八岁的两人迅速陷入热恋并同居。
这场恋爱是疯狂的,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听音乐,看戏,举行派对。一时间,这对艺术家伴侣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伊莎多拉像母亲般溺爱着叶赛宁,“哪怕叶赛宁头上一根金发受到损害我都受不了”。但叶赛宁很快就暴露出他喜怒无常的诗人气质。他觉得伊莎多拉无法理解他的诗歌,因而对她发脾气。进而发展到对她拳脚相加。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也为了让世界认识叶赛宁,伊莎多拉决定带着叶赛宁离开苏联前往欧洲。正是为了顺利出国,两人在莫斯科注册结婚。
临行前,因为担心乘飞机的安全问题,伊莎多拉写下了遗嘱。“如果我去世,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和所有遗物留给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如果我们同时去世,此项财产遗赠给我的兄弟奥古斯丁·邓肯。”
伊莎多拉與叶赛宁最先抵达了德国,但德国文坛对叶赛宁的诗歌反应冷淡。之后,他们又去了比利时、意大利、法国,依旧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欣赏。持续的冷遇摧毁了诗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开始借酒浇愁,并将不满都发泄到伊莎多拉身上。1922年10月,伊莎多拉带着叶赛宁离开欧洲,回到了她的家乡美国。在这里,邓肯受到了巨星般的待遇,而叶赛宁则沦为了她的陪衬。重新回到欧洲后,叶赛宁的苦闷与日俱增,抑郁症复发。在一次酒后砸毁了酒店的家具后,他被警察带走。伊莎多拉在朋友的劝说下,将叶赛宁从警察局转到了疗养院。1923年8月,身心俱疲的伊莎多拉陪着精神状态极不稳定的叶赛宁回到了莫斯科。
在两人短暂的婚姻中,幸福的时光极短,大部分时间被折磨与伤害覆盖。从情感上来讲,伊莎多拉是那个被伤害得更深的人。叶赛宁的朋友施耐德曾经对叶赛宁说过这样一番话:“在伊莎多拉的房间里,你高声谈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情,以及你使其他两个女人怀孕的事,难道你不觉得这很粗俗吗?伊莎多拉唯一的过错就是对你太好了。你曾多次告诉我你是多么爱伊莎多拉,但你回到莫斯科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表一首献给另一个女人的爱情诗来侮辱她。”按常人的眼光来看,叶赛宁的做法确实不可理喻,也难以原谅,但这或许恰恰说明了诗人渴求理解而不得的孤独与苦闷。他爱伊莎多拉,但伊莎多拉无法填满他那颗空虚的心。他试图寻找其他爱情的刺激,把新鲜的女人当作治愈自己的药物,但他不知道,这种对内心的整合与精神的蜕变只有他自己才能完成,谁也帮不了他。从对艺术的影响而言,这段婚姻对叶赛宁而言显然是失败的。帕斯捷尔纳克对这段感情也有所评价:“叶赛宁是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除了与邓肯出游的那两年,他一直固守俄罗斯的土地,他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这是叶赛宁气质的本质,这与富有创新意识的、开放的、外向的邓肯有着根本的区别。”我觉得这似乎在暗示一种观点——叶赛宁不应该离开他诗歌诞生的土壤,也不应该与邓肯结婚。在两个人中,邓肯无疑比叶赛宁坚强得多,她的事业几乎没有受到情感的影响,而离开苏联的这段经历,却直接损害了叶赛宁继续写作的心态。与邓肯离婚之后,叶赛宁才迎来自己创作的高峰期。诗集《莫斯科酒馆之音》、组诗《波斯抒情》以及长诗《安娜·斯涅金娜》都创作于1924至1925年间。
1927年9月的一天,伊莎多拉·邓肯与朋友参加完一个宴会,乘车回家。途中,围在她颈上的长丝巾卷入了汽车车轮,她的动脉迅速被勒断。一代传奇舞蹈家就这样以一种与叶赛宁相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梦幻般的一生。
【责任编辑】 铁菁妤
作者简介:
苏兰朵,满族,70后,生于吉林松原。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就职于媒体与大学,现居沈阳,职业写作。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作品刊发于《诗刊》《当代》《民族文学》《散文》等杂志。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入选多种文学年度选本。曾获骏马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林语堂小说奖、辽宁文学奖等奖项。有诗歌、小说被翻译成德、日、蒙等多种文字。有小说作品被改编为话剧上演。著有诗集《碎·碎念》,随笔集《曳航船》《听歌的人最无情》,小说集《寻找艾薇儿》《白熊》,长篇小说《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