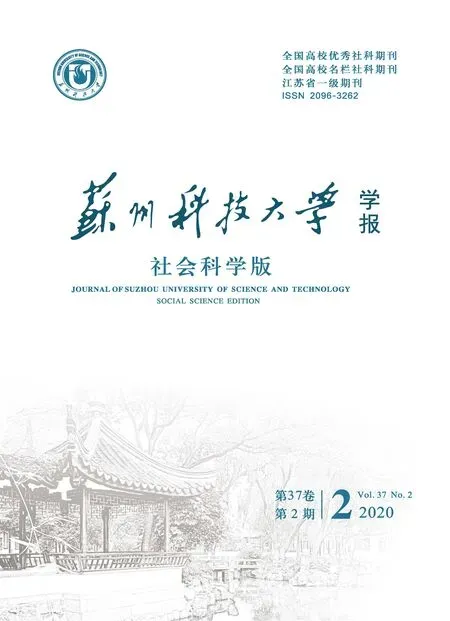论薛家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叙事结构*
郑铁生
(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天津 300270)
现代理论对空间的重视,越来越关注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对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关注空间的社会实践,关注人们在空间的主体性行为,关注社会的再生产。因此,空间构成了浓缩和聚焦社会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红楼梦》叙事演进到第八十回,史、王两家已败落,贾家“内囊尽上”,唯有薛家还保有家底。如果仅从历史时间的流程审视,不会发现《红楼梦》的叙事结构在这里发生重要的转化,但恰在此时,薛蟠第二次打死人,惹出“太平命案”。由此,《红楼梦》的主体叙事演变为薛家,叙事空间充满了薛家破财,疏通官府、打“捞”薛蟠等事件的描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最后走到“一损俱损”的境地。因此,薛家在《红楼梦》后四十回转化为主体叙事形态以后有了极为特殊的意义,对认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的内在结构、生命脉络和叙事肌理十分重要。
一、薛家在《红楼梦》整体框架结构中的两栖形态
虽然空间的表现是客观的,但就其本质来说,也是政治性的。封建时代建筑群式的府邸,富甲一方,与满天下的低矮蓬草茅屋的对比;现代社会富丽堂皇的别墅群与无数城中村的贫民窟对比,可见空间的占有与分割就是政治经济地位的体现,继而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和社会形态。文学再现的艺术世界,既是历史客观世界的投影,也是精神世界的创造。《红楼梦》的故事介绍、展示和叙述了一个官僚豪族群体——“贾、史、王、薛”四大家族: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1]94-95
四大家族具有中国宗族的基本特征:“连络有亲”。贾宝玉的爷爷贾代善娶了金陵史家的小姐,就是贾母;贾母的二儿子贾政娶了金陵王家的小姐,就是王夫人;王夫人的妹妹又嫁给了薛家,即薛姨妈;王夫人的侄女王熙凤嫁给了宝玉的堂哥贾琏;薛宝钗又和贾家的宝玉成亲。他们之间盘根错节,“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1]95。这说明四大家族休戚相关,命运与共,是封建上流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红楼梦》故事的叙事内容。但是作者对待“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命运的叙事方式却各有不同,于是形成四大家族的三种叙事形态。这对于我们解读《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整体结构很关键,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红楼梦》叙述四大家族命运时采用三种叙事形态。
第一种,《红楼梦》的时空结构是百年望族——贾府。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它是由贾家主要人物贾母、王夫人、凤姐、贾政、宝玉和姊妹的主体叙事创造的。从一开始就密针细线地编织贾府的故事,写了五代死去的和活着的老爷、少爷们;写了几辈成群的妻妾、小姐、丫鬟、婆子等女流;写了十几个青年男女的婚姻和爱情的悲剧,一部《红楼梦》就是一部贾府的衰败史。
第二种,史家和王家是潜隐叙事。先说史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1]94-95,“阿房宫”隐喻史家这个官僚家族是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传统房地产业主要原料是砖瓦木石,房地产兴衰周期为半个多世纪。这种特征决定了史家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最早衰败的家族。它的衰败主要通过史家小姐史湘云来贾家串亲戚时流露的史家点滴现状透露出来的,往往易被人忽视。第三十二回,爱说爱笑的史湘云被人问及家计,吞吞吐吐,无人处眼圈都红了。她从贾府回家时每每叮咛宝玉,别忘了提醒老太太时常打发人去接她,因为到贾府可以无忧无虑地同姐妹们一起,在酒宴诗会中怡情任性、高谈阔论;可以暂时躲开自家烦重的针线活计。像她这样的小姐还得为生计起五更睡半夜,表明史家经济的困顿。
贾家被抄,贾政查阅账册才知贾家早已入不敷出,寅年吃卯年粮了。贾母知道后大为惊讶,从她的感叹中也披露出史家的信息:
怎么着,咱们家到了这个田地了么?我虽没有经过,我想起我家向日比这里还强十倍,也是摆了几年虚架子,没有出这样事,已经塌下来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据你说起来,咱们竟一两年就不能支了?(第一百零七回)[1]1908
贾母的话已明确告诉读者,史家早已衰败。这种叙事是断断续续的粗线条的点缀、流露、勾勒,它没有独立的时空结构,如影随形,没有边际,难以捕捉;没有史家的家族史的流程,只是借助史家的一两个人物的只言片语,出现在贾家的时空结构上,形成大的历史潜在的结构,能让我们感知时代的色彩和历史的沧桑感。
作者对王家同样是采用潜隐叙事。最显眼的是王家嫁到贾家的王夫人和凤姐,她们的言行基本是贾家的叙事,偶然间也披露出王家的事情,那就是夸耀王家的豪富——“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1]95。凤姐说她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1]299;凤姐送给亲人的礼物,玩具是波斯国的,茶叶是暹罗国的。由此说明王家在朝廷掌管着对外贸易,包揽了广东、福建、浙江和云南的洋船货物。第七十二回写凤姐与贾琏吵架:
我三千五千,不是赚的你的。如今里外上下,背着嚼说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来说我了。可知“没家亲引不出外鬼来”。我们看着你家什么石崇、邓通?把我王家的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一辈子过的了。说出的话也不害臊!现有对证,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看,比一比,我们那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1]1306
与豪富孪生的就是权势。凤姐叔叔王子腾,始终没有正面出现,但他的存在直接左右着王家的命运,制约着《红楼梦》叙事的起伏跌宕。薛蟠打死人后逍遥法外,靠的是贾家和王家的权势。贾雨村重返官场,为宦升迁,虽说仰仗贾政,而最终还是九省检点王子腾的权势起了作用。第九十六回,贾琏传来王子腾的死讯,“舅太爷是赶路劳乏,偶然感冒风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医调治。无奈这个地方没有名医,误用了药,一剂就死了”,王夫人听了“便心口疼得坐不住”。[1]1740就在传送王子腾丧信之时,元妃病危、去世。这意味着王家最有实权的顶梁柱坍塌了,贾家、王家与皇家的联系断了。对于王家的这种叙事,尽管在《红楼梦》叙事结构的演进中起着“秤砣虽小压千斤”的作用,但它依旧是潜在叙事,“孤立地考察它们本身,是不足以组成结构的,但是许多情节线索从这里抽引出来,而且它们之间形成某种张力,吸附整个情节向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非结构的结构,乃是一种潜隐结构,它们相互呼应,以象征的方式赋予整个情节发展以哲学意义”[2]。史家、王家在《红楼梦》叙事上都十分重要,不仅是贾家历史的张力网,而且展示了独有的文化和社会形态。
第三种,薛家的叙事是潜隐叙事与主体叙事的合一,是两栖叙事形态。前八十回表现为潜隐叙事,后四十回转为主体叙事。薛家的主要人物薛姨妈、宝钗、薛蟠都在《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故事中反复出现,为什么薛家还属于潜隐结构呢?
薛家是大皇商,虽然当家的去世了,儿子薛蟠赖祖父旧日的情分,户部挂个虚名支领钱粮;京城有房舍、钱铺,家中有百万之富,颇为殷实富足。《红楼梦》前八十回,薛姨妈一直在王夫人、贾母的身边,迎奉左右,是贾家的一个典型的附庸人物;其中主要描写她以下几件事:
1.刚在荣国府住下,薛姨妈就拿出宫里做的新鲜花样儿“堆纱花十二枝”[1]163,当着王夫人的面,让周瑞家的送给贾府的姐妹们,还特别嘱咐送给凤姐四枝,很自然地博得王夫人欢心。
2.“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薛宝钗巧合认通灵”是《红楼梦》中的重场戏。宝钗生病,宝玉探望,薛姨妈一见宝玉,“一把拉住,抱入怀中笑说:‘这么冷天,我的儿,难为你想着来,快上炕来坐着罢’”[1]181,亲热至极,宠爱有加。趁宝玉兴致浓,安排宝玉饮酒,既不像李嬷嬷那么直言劝阻,拿老爷威吓他,叫宝玉扫兴;也不全由着他,而是笑着安慰他,又“千哄万哄,只容他吃了几杯,就忙收过了”[1]189,抚慰之,体贴之,写透薛姨妈的奉承。
3.薛蟠挨了柳湘莲的打,薛姨妈“意欲告诉王夫人,遣人寻拿湘莲”,被宝钗批评“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1]851后才罢手。
4.薛姨妈在潇湘馆给黛玉讲月下老人的故事:“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儿,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那怕隔着海呢,若有姻缘的,终久有机会作成了夫妇。”[1]1043这段话顺便透漏贾母想让宝琴与宝玉为配的事情。
从上述几件小事可以看出,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薛姨妈是久居贾家的贵客,也是一位清客,暗中打着小算盘,推动“金玉良缘”的实现。薛家住在贾家最初的动因是要躲“葫芦案”带来的麻烦,而长期不归的深层原因是薛家的掌门人去世了,儿子薛蟠又撑不起家,贾家毕竟有钱有势。薛姨妈要靠着贾家,盼着和贾家联姻。所以,在前八十回中,薛姨妈跟着贾母、王夫人后面,敲敲边鼓,尽显人情的练达;薛蟠与贾家的纨绔子弟混在一起,呼朋唤友,吃喝嫖赌;宝钗生活在大观园,虽然是宝、黛、钗爱情脉络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但她并不主动表达自己的情感,是被动地裹挟在这场“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之争中,何况这属于贾家的叙事内容。因此,薛姨妈和儿女的言行,从不涉及家族命运的选择和主体性行为,薛家没有自己的主体行为,没有实质的内容,在叙事形态中构不成一个独立的家族史。而七十九回之后就大不一样了,薛家所有人都出现在经济破败、命运选择的社会过程之中。薛姨妈就前后操办了薛家三件婚姻大事,第一件是为侄子薛蝌娶了媳妇,第二件是为薛蟠娶了夏金桂,第三件是让宝钗和宝玉完婚;还一直操纵着为囹圄之中的儿子薛蟠脱罪之事,件件都是大事。
薛家在《红楼梦》后四十回进入主体叙事形态以后,形成以薛蟠“太平命案”脉络为主的薛家叙事独立的时空结构。这是实质性的变化,涉及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其基本特征为以下三个方面:
1.薛家在《红楼梦》后四十回转化为主体叙事,其空间表现为家族政治和经济的演化。要说社会地位,薛家过去是靠王家、贾家的权势而获得的影子效应;要说“家底”,薛家曾是大皇商,“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1]95,豪富不在贾、史、王三大家族之下。后来虽然薛家当家人早逝,但家底殷富,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最后一个经济破败的家族。它深刻地揭示了“一损俱损”的四大家族衰败的共同特征——最后都是从经济上走向破败。
2.薛家在《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空间转换,带来了全新的生存体验。薛家无权,在与权势打交道时,只能用银子的输出求得摆平。薛家与贾家共同包装了宝玉和宝钗的“金玉良缘”,在红红火火的喜庆中兑现传统文化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传统社会潜意识的浸润下,孕育一个遵从三从四德的贞洁女子宝钗,使她重蹈青春守寡、养育儿子的老路。这是从精神世界揭示了《红楼梦》悲剧的文化内涵。
3.薛家在《红楼梦》后四十回转化为主体叙事,恰好踏在《红楼梦》整个叙事结构的“黄金分割线”上,即第七十九回和第八十回之间,也是《红楼梦》悲剧史的转折点。前八十回其实只写了贾家,诗礼簪缨、富贵豪奢的贾府“虚架子”撑不住了,时时处处表露在日常的生活中;薛家、史家、王家都是贾府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网结,一个陪衬,一种拓展,最终目的是深化百年望族贾府的历史意蕴。
二、薛家在《红楼梦》后四十回转换为主体叙事
到《红楼梦》第八十回,“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败落还没有完全出现“一损俱损”,贾家还撑着一个空架子,薛家还算富贵,家底尚没有伤筋动骨。《红楼梦》后四十回,从第七十九回转换到多事之秋的薛家与贾家,直到第九十一回,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肌理自然严密的故事。分而叙之:薛家从薛蟠娶妻写起,夏金桂弹压薛蟠,蹂躏香菱,大闹薛家,与薛姨妈拌嘴;宝蟾勾引薛蝌、金桂勾搭夏三,薛家一事未平,又生一事。贾家从迎春误嫁中山狼写起,孙绍祖眼里没了贾府,作践贾府小姐,使迎春“一载赴黄粱”。贾元春生病开启了死丧的氛围,贾府大故迭起,四处弥漫着悲凉之气。薛家与贾家的故事可以概括为“薛、贾家多事之秋”。第七十九回“薛文龙悔娶河东狮,贾迎春误嫁中山狼”,一进一出,大有深意。薛家儿子娶的是“河东狮”,从一进门就搅得薛家鸡飞狗跳,惶惶不可终日;贾家女儿嫁的是“中山狼”,不到一年,千金小姐迎春便被揉搓到命丧黄泉。不管是出还是进,全是败家的征兆。
(一)薛家上升为叙事主体缘由是贾家已靠不住
过去薛蟠打死人,靠贾家、王家;而现在的贾政自身平平,薛家想靠也靠不上了,何况王子腾已死,更没指望了。这些信息首先从薛家冒出,是薛家最无奈最悲哀的事情。夏金桂哭闹着说:
平常你们只管夸他们家里打死了人,一点事也没有,就进京来了的,如今撺掇的真打死人了,平日里只讲有钱,有势,有好亲戚,这时候我看着也是吓得慌手慌脚的了。大爷明儿有个好歹儿不能回来时,你们各自干你们的去了,撂下我一个人受罪。(第八十五回)[1]1559
这些埋怨道出了实情,且入木三分。薛家虽然富足,毕竟是寡妇带着两个子女,没什么社会地位,只好靠着贾、王两家的权势。发生在薛蟠身上的两次命案叙事脉络,便可以折射出薛家的靠山昔日之威,炙手可热;如今势微,自身难保。
“靠不住”包含三种意思:
一是薛家过去一直靠着贾家和王家。薛家进京傍在贾家至今已十年,足以说明过去薛家是能够靠贾家和王家的。薛蟠“太平命案”一出,薛姨妈被衙役唤去,王夫人不放心,赶快派人打探,宝钗劝来人说:“你先回去,道谢太太惦记着,底下我们还有仰仗那边爷们的地方呢。”张俊先生批注:“‘仰仗’二字是眼。薛家平日即仰仗贾府,何况出事之际。”[1]1560正因为过去一直靠着,现在靠不了,薛家才要自己挡事。
二是贾家和王家的确曾靠得住。薛蟠第一次命案发生时,王子腾主动发力,先是邀薛姨妈一家上京,用来约束教管薛蟠;后是帮着贾雨村复官,成为贾雨村在“葫芦案”中徇私枉法的直接动因。在这次案子中,王子腾始终没有只言片语,而贾雨村在判案之后,主动写信向贾政和王子腾报告。这是薛家傍在贾家的根本原因。
三是贾家和王家靠不住,是在《红楼梦》时空结构“黄金分割线”阶段——第七十九回开始表现出来的。从八十回以后披露的事件渐渐看出,此时的贾府已在风雨飘摇之中,只有招架之功,没有回天之力,何以能惠及薛家?首先是元妃病了,贾府听说宫里有一个娘娘病了,引起上至贾母,下至贾琏的关注。张俊先生批注:
元春染恙,贾赦风闻,寓意深远,提动后文。如张新之所批:“本回‘染恙’,九十五回‘薨逝’之兆也。”元春死,贾氏败。……元春乃贾府靠山,故诸人一闻病讯即风声鹤唳。此处渲染,亦以明元春所关非轻。[1]1515-1516
贾家拼出老底迎“元妃省亲”,无非是要昭示贾家的靠山是封建社会最高的权威——皇帝,而现在已失去了。
薛蟠“太平命案”刚发,薛姨妈“托王夫人转求贾政。贾政问了前后,也只好含糊应了,只说等薛蝌递了呈子,看他本县怎么批了,再作道理”[1]1566,表现出他的为难和犹豫,不得已“只肯托人与知县说情,不肯提及银物”[1]1568。贾政的这种态度和他在官场的处境有关,虽为贵妃之父,却仕途失意,终老未得升迁,近因年迈,名利心大灰。贾政既不做贪官,又碍于未来亲家母的面子,不能不办,但事情怕闹大了,又恐受到牵连,因此他不敢贸然出头。由此可见贾府势衰,没了底气。此时的贾府已今非昔比,不再像以前那样“赫赫扬扬”,而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行事上变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第九十九回,贾政无意看到了刑部对这次案件提本的抄件后,暗自担惊,生怕因为当时的说情连累到自己。贾政的这些表现和反应,正是贾家逐渐走向衰微的现实在他心理上的投影。贾家已失去当年炙手可热的权势,失去权力枢纽的地位,没有更多的面子和人情资源。这种江河日下的处境,难有让人再靠的实力。
同薛蝌一道去的人回来报告:“县里早知我们的家当充足。须得在京里谋干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礼,还可以复审,从轻定案。”[1]1567知县全然不卖贾政人情,还公然向薛家“寻租”,收受银子,直等着薛家的银子送到,才将“斗杀”改判为“误杀”。而此后的道台、节度使和刑部,不仅没有顾及皇亲勋旧的贾府,反而乘机刁难,落井下石。人治社会的人情和面子的潜规则,是朝着权力和官员作向心运动,一级高于一级,“官大一级压死人”。因为只有位于权力系统,手中才能掌握荣辱升迁的大权,因此人们总是向上攀附,小官巴结大官。如今连知县都不卖贾政面子,可知在官场的潜规则中,贾政的地位多么尴尬!薛蟠当年在金陵打死冯渊后扬长而去,谁敢捕他?办案的贾雨村还主动献媚贾家、王家,替他们了结命案。而今,薛家从地方到朝中,层层行贿,几乎掏空家底,才算保住性命,人还被拘在案。“四大家族”已今非昔比。
(二)薛家内乱,折腾不断,导致破家
薛家什么时候自立门户,《红楼梦》没有明确写,只是在叙事中被张俊先生发现,他说:
前叙薛姨妈回家时“上车”,此写衙役眼中薛母“势派”,并云让其“进去”,似薛家已另立门户,与贾宅隔断。但前后仍写丫鬟往来,似角门仍可通行。或属暗写,或文有疏漏。[1]1558
《红楼梦》第七十九回以后,薛蟠成家,自立门户,扯开社会空间的一角,有了自己全新的外界交往和生命体验。
薛家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上升为叙事主体,源于人物性格的动力性。当然动力性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甚至是破坏力,“太平命案”是指后者。薛家主要人物薛蟠人性要素的失衡、缺失,每每生事,致家庭内乱,从而延伸出家庭的灾难。正如唐雄山、王伟勤《人性组合形态论》所云:
人与生俱来的人性诸要素,如生存欲、占有欲、责任心、情爱、性爱、同情怜悯心、惰性、嫉妒心、报复心、爱美之心、好奇心、理性、群体性、类性等。人与生俱来的人性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就像大自然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互相矛盾、互相依赖、互相制约与互相平衡的。[3]61
人性诸要素是一个生态性结构。……生态性结构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构成事物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可缺失,一旦缺失某个或某些要素,事物内部就会出现混乱,平衡机制就会打破。同样的道理,人与生俱来的要素都具有不可缺失性,一旦人性的某个或某些要素缺失,人性内在制约与平衡机制就会遭到破坏。[3]67
薛蟠是娇生惯养的花花公子,“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1]100-101。第四回,骄纵成性的薛蟠为抢买一个丫鬟,纵仆行凶,打死冯渊,而后像没事人似的走了。此命案曝光了薛家乃名列“护官符”的“户籍”,也是《红楼梦》社会历史背景的大关节;暴露薛蟠人性结构的缺失,占有欲、性欲强烈到人性失衡,带有破坏性和暴力倾向。
薛蟠人性结构的缺失,是长期在非正常环境中形成的。家有财势,父亲早逝,独根独苗,寡母溺爱,无人管教,亲友放纵,养成弄性尚气、气质刚硬、贪图享乐、愚钝无知而又憨直天真的贵公子性格;加上贾宅族中“那些纨绔气习,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渐渐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1]105。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中对薛蟠的描写不过十回(第四回、第二十六回、第二十八回、第三十四回、第四十七回、第六十六回、第七十九回、第八十五回、第九十一回、第一百回)。从中可见,薛蟠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亦非流氓地痞之流,而是封建末世一个纨绔子弟,不学无术,骄奢淫逸。他平日所为,不是会酒观花,就是聚赌嫖娼;他没文化,显得粗俗,被人称为“呆霸王”,但他对亲友还算有情有义,对母亲、妹妹尚存挂念关爱之心。第六十七回,薛蟠第一次随张德辉外出做生意回来,给母亲带了箱“绸缎绫锦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1]1216,还给妹妹专门买了一箱玩意儿,琳琅满目,各色俱全,喜得母女俩到处派送,惟恐他人不知。薛蟠不只是“滥情人”,还有仗义爽直的一面。他送贾珍为秦可卿做棺木的板材,一掷千金,十分豪爽。因此,宝玉很少和贾珍、贾琏、贾蓉等在一起,却和薛蟠有交往。薛蟠是一个性格丰富复杂的贵族子弟。
第七十九回,薛姨妈给儿子娶妻,是与有通家之好的夏家结亲。夏家与薛家“当年同在户部挂名行商,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薛蟠和夏金桂还“从小儿都在一处玩过”。“夏奶奶又是没儿子的”,见了薛蟠,“竟比见了儿子还胜”,薛蟠也看中“这姑娘出落的花朵似的”。[1]1445-1446夏金桂也是人性结构缺失的人,父亲去世得早,又无同胞兄弟,寡母独守此女,娇养溺爱,养成她施虐、报复、仇杀的恶性。她在娘家时就是“盗跖的情性,自己尊若菩萨,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禀风雷之性。在家里和丫鬟们使性赌气,轻骂重打的”[1]1448,出了阁变本加厉。她一出现在薛家,就把薛家弄了个鸡飞狗跳,不得消停。她“毫无闺阁理法”,隔着窗子和婆婆顶嘴,气得薛姨妈“身战气咽”,只得说:“这是谁家的规矩?婆婆这里说话,媳妇隔着窗子拌嘴。亏你是旧人家的女儿!满嘴里大呼小喊,说的是什么!”[1]1459薛蟠在金桂雌威之下,结婚不到两个月,“气概就矮了半截下来”。薛蟠虽曾“仗着酒胆挺撞过两三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递身子叫打;这里持刀欲杀时,便伸着脖项”[1]1460。夏金桂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千方百计要拔去香菱这个“眼中钉”。先是胡搅蛮缠,强迫香菱改名为“秋菱”;接着施离间计,挑拨香菱和薛蟠的关系,调唆薛蟠毒打香菱;继而又慢性折磨香菱,命她在地上打铺,陪自己睡,“刚睡下,便叫倒茶,一时又叫捶腿,如是,一夜七八次,总不使其安逸稳卧片时”;最后又诬陷香菱要谋害她。这一而再,再而三的虐待折磨,使香菱“内外折挫不堪,竟酿成干血之症”。[1]1453-1460
这一对人性缺失的夫妻,无法相安。薛蟠忍受不了家庭内乱而出走经商,本来就正事干不了,还要惹祸,任凭本能的冲动,发展到行凶杀人,虽说免受极刑,也最终折腾到家境败落。他们性格的缺失造成的人性不平衡性,产生的破坏性,是推动叙事的人物性格的动力性。
(三)薛家内乱引出内外两条叙事线索分支
一条分支是薛蟠的“太平命案”全过程,另一条分支是夏金桂施淫威导致自己死亡。薛蟠的“太平命案”全过程涉及第八十五回“薛文起复惹放流刑”、第八十六回“受私贿老官翻案牍”、第九十九回“阅邸报老舅自担惊”,直到第一百二十回薛蟠被赦罪归家,扶香菱为正。夏金桂之死,涉及第八十回“美香菱屈受贪夫棒”、第八十三回“闹闺阃薛宝钗吞声”、第九十一回“纵淫心宝蟾工设计”、第一百回“破好事香菱结深恨”、第一百三回“施毒计金桂自焚身”。这两条叙事线索分支,都主要是在薛姨妈和宝钗主内、薛蝌跑外的合力下撑起薛家门户,构成薛家的主体叙事;也是《红楼梦》后四十回时空结构的重要内容。
在薛蟠“太平命案”发展过程中,银子是薛家撑起门户的基础。薛家为“捞”薛蟠,采用世俗最赤裸的金钱手段,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去贿赂,打通官府门路。如果说薛蟠在第一次命案中的逍遥法外是权力与权力交换的结果,那么薛蟠第二次命案的死里逃生则彻头彻尾是金钱与权力的交换。从一发案,薛家就一直用银子打点,为薛蟠开罪。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或者说是权力的容器。这就是薛家为什么能够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上升为叙事主体的叙事根据,从而撕开封建社会的一角。薛家上升为叙事主体最典型的特征是开拓了社会空间。
薛蟠的“太平命案”中,死者张三是当地的泼皮无赖,薛蟠与其争斗,将其打死,存在一定的过失行为,但是太平知县在得知薛蟠身份之后,故作正义之态,以“斗杀”罪名将薛蟠监禁起来,实是变相勒索受贿。当薛蝌递上呈子,希望将“斗杀”改为“误杀”时,知县冠冕堂皇,故作义正词严之态给驳了回来,等着薛家送礼。为了替薛蟠开脱,先是薛蝌花钱在太平县请了一个有名的刀笔先生,另外上了一份呈子,试图将薛蟠的死罪免去;接着又花钱保出与薛蟠一同喝酒的吴良,并许以银钱,令他作伪证;同时买通了其他一干涉案证人。两日后,薛蝌差人捎书信请薛姨妈拿出五百两银子做衙门上下的打点费,好使薛蟠在狱中不致受苦。
太平知县将薛蟠依“误杀”定罪,将案件审理结果上报给府中,府里又将报告“准详上转”至道台,没想到道台却不买账,并将知县申饬。薛蟠家人都以为薛蟠不久就可以出狱的时候,案件中途又起波折。第九十一回,薛蟠的一封告急家书道出实情:
男在县里也不受苦,母亲放心。但昨日县里书办说,府里已经准详,想是我们的情到了。岂知府里详上去,道里反驳下来了。亏得县里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顶上去了。那道里却把知县申饬。现在道里要亲提,若一上去,又要吃苦。必是道里没有托到。母亲见字,快快托人求道爷去。还叫兄弟快来,不然就要解道。银子短不得,火速,火速。[1]1661
张俊先生在这里批注:
信中所云县、府、道,乃清王朝地方司法机关中三等审级也。州县为第一审级,除审理笞、杖及徒刑案件,亦审理死刑命案,但须呈报上级司法机关定夺。府为第二审级,审理州县所报之徒刑以上案件。道系第三审级,复审对上所报之刑事案件。薛蟠命案,府已准详,又被道驳,想是“请托未到”。[1]1661-1662
薛家的银两只送到县和府,一时尚未惠及道台,所以道里反驳下来,并将知县申饬,实则要挟分赃,变相索贿。这封家书,逼得薛姨妈急忙叫薛蝌“兑了银子”,“连夜起程”,把人情送至道台。薛家在“太平命案”过程中花掉了十多万两银子,掏空了家底。薛家唯一可资的本钱就是家底殷实,家底掏空也就意味着家族的败落。
另一条是夏金桂之死。以薛蟠出走为界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夏金桂企图弹压夫家,在薛家横行霸道;后一段是她妄图勾引薛蝌不成,转恨香菱,设谋杀人,反误食毒药而致自己死亡。
夏金桂一嫁到薛家,就打算“今儿出了阁,自为要作当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儿时腼腆温柔,需要拿出威风来才钤压得住人”[1]1448。她先是挟制薛蟠,继之欺辱香菱,纵容自己的丫头宝蟾与薛蟠勾搭成奸。这几招让薛蟠彻底服软了,他被夏金桂“闹得无法,便出门躲着”[1]1461。至第八十五回薛蟠第二次打死人被执受审,夏金桂弹压薛蟠的心计落空。正在这时,薛蝌的出现,让寂寞无聊的夏金桂欲火复燃。她想勾引薛蝌,还没来得及,偏被香菱撞见。夏金桂把一腔怒火都倾泻在香菱身上,本来准备用一碗放有砒霜的汤毒死香菱,不料宝蟾掺乎进来,夏金桂喝了有毒的汤而丧命。
薛家内乱是《红楼梦》婚姻家庭的又一种典型。它不是以妻妾成群、妒忌仇恨为主,也不是以封建宗法、男尊女卑为重心;而是突出人性的缺失所酿成的人间悲剧。
饮食男女、追求享受乃人的本性,但若不加以规范和节制,就成了人性的弱点,并产生扭曲与畸形。……人性的弱点还在于,人性本身始终处在自然欲望与社会(文化)欲望、物质欲望与精神欲望的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在诸种对抗冲突、拼搏中把握不好它们之间的平衡或张力,就会造成心理的扭曲和失衡。[4]
薛家内乱,再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宗法世袭特性:封闭保守,竞争缺失。长期稳定的世袭制度使封建社会政权结构变成一潭死水,贵族子弟也在世袭的荫蔽下变得不思进取,慢慢堕落。他们一方面耗尽了祖宗九死一生挣下的家业;另一方面动摇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成为封建社会的自戕品。这种安富尊荣、不思进取的心态成为封建世袭家族子弟的普遍心理。因而,他们不务正业,腐化堕落,为自己家族的衰落埋下了祸根,是四大家族走向衰落的必然因素。
三、薛家主体叙事内涵的历史的社会的意蕴
《红楼梦》的主体故事是从第六回开始的,所以《红楼梦》整个叙事结构的“黄金分割线”应在第七十九回和第八十回之间。从第七十三回至第七十八回是“抄检大观园”的叙事单元,从七十九回至第九十一回是“薛、贾家多事之秋”叙事单元。为什么恰恰在《红楼梦》整个结构的“黄金分割线”上出现薛家的故事?这绝不是一般故事的流转,薛家主体叙事的出现,富有丰富的历史的社会的审美的意蕴,深化了历史本质的映现,提升了《红楼梦》主旋律的高亢。
(一)官场都以“寻租”发财为最终目的是封建政权的本质
《红楼梦》叙事处处离不开官场的内容,胡文彬先生做过全面的介绍:
据我初步考察的印象,120回《红楼梦》里所提到的职官机构、称谓——从中央到地方,上自王公侯伯、三司九卿、下至七品芝麻官,内相外臣、文武百官、军牢快手、番役太监,称谓不下百余种。[5]243-244
将《红楼梦》里提到的职官做一次排队,从而概括出以下三个主要的来源。……《红楼梦》里所写的职官来源之一,是世袭的。……《红楼梦》里多次多处提到科举的事。……捐纳: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国家以授予官职(虚衔或实职)取得捐款的办法,也是官吏来源之一,这种制度造就了大量腐败昏庸的官吏。这些官吏凭藉金钱“捐纳”一官半职,上了任即千方百计敲剥天下黎民以收回成本。他们人无德无才,信奉的就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是祸国祸民的蠹虫。[5]251-252
阴险狡诈的悍吏贾雨村,荒淫无耻的贾赦,道貌岸然的贾政,都是个体形象。而具体细致地展现现实的整个封建官场层层黑暗的,还是《红楼梦》时空结构“黄金分割线”上出现的“太平命案”。薛蟠一案揭示了司法的腐败是结构性的腐败。这是专制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并不是个人的行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古往今来,官吏尤其是司法官吏的腐败,不惟侵蚀蠹害国家肌体,更会滋起天怒人怨,从根本上动摇整个统治的根基。由司法腐败引发社会动荡,并进而导致统治政权覆灭,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规律。
现实的官场都以“寻租”发财为最终目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清代流传很广的一句官场谚语。即使清廉的官员,也要捞上成千上万的银子,至于贪官就更不用说了。李乔《清代官场图记》云:
在“千里为官只为财”的清代官场上,捐官完全是以发财为直接目的。捐官者所以放弃原来的营生而捐官,是因为他们知道“遍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的利钱最好”,做官是真正的一本万利。有个富商捐了个知府,引见时皇帝问他:“既然经商可以致富,你又何必捐官呢?”富商回答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经商获利虽多,但终不如做官获利优厚,而且当商人也不如当官体面,所以我才弃商捐官。”[6]
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在职权范围内大肆敛钱受贿,虽是个人所为,但导致国家政权层层腐败。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腐败,是一种隐性的政权腐败。薛蟠第二次命案中,太平知县是权力“寻租”的典型,他故作正义之态,将薛蟠以“斗杀”罪名监禁起来,实则变相勒索受贿。薛家“捞人”过程的焦点是将“斗杀”改为“误伤”,这样才可以免薛蟠一死。在改轻罪行过程中,表面上抓住吴良这一涉案证人和尸格的主要物证,实质上突出了金钱与权力交换这一要害。“薛姨妈为着薛蟠这件人命官司,各衙门内不知花了多少银钱,才定了误杀具题。原打量将当铺折变给人,备银赎罪,不想刑部驳审,又托人花了好些钱,总不中用,依旧定了个死罪,监着守候秋天大审。薛姨妈又气又疼,日夜啼哭。”[1]1808最后,在皇帝大赦天下的时候,薛家才又花钱买通了刑部,将薛蟠救了出来,从而勾勒出从下到上的“贪官群丑图”。
薛家的“太平命案”独特的历史内蕴就是揭示了封建政权的本质。中国官僚政治史既是一部勾心斗角、相互残杀的历史,也是一部贪污史。做官与发财的统一,权就是钱,钱亦可为权,是官文化的一大特征。
(二)薛宝钗最终成为千百年所形成的社会潜意识浸润下的“僵尸”
《红楼梦》叙事一条主线是宝黛钗的爱情和婚姻悲剧,“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之争演进到第七十八回,也就是抄检大观园之后,王夫人清理怡红院的丫鬟,把晴雯等都赶出大观园,也就意味着“木石前盟”遭受了一场霜冻。从此,“金玉良缘”从背后策划、酝酿、联络走向前台,第八十四回“试文字宝玉始提亲”,一向支持“木石前盟”的贾母对“金玉良缘”开始默认。第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贾母、贾政、王夫人、凤姐商量宝玉、宝钗的成婚大事,为防宝玉闹事,凤姐设计了“调包计”,明里佯迎黛玉,暗里实娶宝钗。张俊先生评注:
凤姐所谓“调包儿”之法,亦称“调包计”,在三十六计中称作“偷梁换柱”。堂堂公侯世家,婚配中竟行此计,不堪之极。……凤姐罪责轻,王夫人罪责重,贾母罪责更重,而宗法社会道德礼法及婚姻制度之罪责,尤为重中之重。[1]1746
除张俊先生在这里指出的“宗法社会道德礼法及婚姻制度”之外,还有像汪洋大海一样的社会潜意识,构成与社会传统心理所适应的传统、习惯、风俗,会抑制、障碍、制约人的行为和性格。这一点更深刻地表现在宝玉与宝钗并不美满的婚姻生活中。宝玉出家,给宝钗留下遗腹子,宝钗成为李纨第二。王夫人与薛姨妈的对话说得很透辟:
王夫人便说道:“我为他担了一辈子的惊,刚刚儿娶了亲,中了举人,又知道媳妇作了胎,我才喜欢些,不想弄到这样结局。早知这样,就不该娶亲,害了人家姑娘。”薛姨妈道:“这是自己一定的,咱们这样人家,还有什么别的说的吗?幸亏有了胎,将来生个外孙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后来就有了结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兰哥儿中了举人,明年成了进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么。他头里的苦也算吃尽了,如今的甜来,也是他为人的好处。我们姑娘的心肠儿姐姐是知道的,并不是刻薄轻佻的人,姐姐倒不必耽忧。”[1]2106
宝钗的性格已决定,她深受程朱理学极力推崇的三纲五常的熏染,再加上千百年所形成的社会潜意识的浸润,必然从精神到肉体受到封建纲常礼教的戕害和桎梏,沦为封建伦理规范而殉道的“僵尸”。这是《红楼梦》悲剧最深刻的一笔,但常常被人所忽视。叶朗先生指出:
在实际生活中,在很多时候,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而是由一种个人不能选择的、个人不能支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决定的。那就是命运。……但是这种由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决定的灾难性的后果,从表面上看,却是由某个个人的行为引起的,所以要由这个人来承担责任。这就产生了悲剧。并不是生活中的一切灾难和痛苦都构成悲剧,只有那种由个人不能支配的力量(命运)所引起的灾难却要由某个个人来承担责任,这才构成真正的悲剧。[7]373
封建宗法社会的道德礼法、婚姻制度,与社会传统心理适应的传统、习惯、风俗,是一种个人不可抗拒的力量。明清以来许多富有进步思想的哲人、诗人、小说家都奋笔疾书,对封建礼教“杀人”的本质进行血泪控诉与声讨。
宝钗是《红楼梦》十二钗中最后走向悲剧的,这也是薛家上升为叙事主体的重要内容。至此,《红楼梦》“有情之天下”的悲剧拉下帷幕。正如叶朗先生所说:
《红楼梦》的悲剧是“有情之天下”毁灭的悲剧。“有情之天下”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人生理想。但是这个人生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被毁灭。在曹雪芹看来,这就是“命运”的力量,“命运”是人无法违抗的。……林黛玉的诗句“冷月葬花魂”是这个悲剧的概括。有情之天下被吞噬了。[7]380
(三)薛家是贾府的影子,最后“一损俱损”
薛姨妈是和贾府同命运、共患难的唯一亲戚,在全书中承担着一个较为重要的角色。她来荣国府,是躲薛蟠第一次惹的命案,几乎全凭借贾府的势力,将这次命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第四回进入荣国府,直到一百二十回,薛姨妈经历了秦可卿出丧、贾元春归省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华场面,也饱尝了贾府被抄、宝玉出走的悲惨情景。她既是贾府衰败的见证人,也是和贾府一同走向衰败的同路人。
《红楼梦》衰败史是以贾府的叙事演进为主体,薛家依附贾家,而且是越来越紧密,宝玉与宝钗成婚,两家快成了一家人。作者写薛蟠“葫芦案”的叙事目的,是透过这个案子的过程展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连络有亲”“扶持遮饰,皆有照应”[1]95,在上流社会权势熏天。案子本身并没有过细的展开,而只有当此案和“太平命案”联系起来对比,才产生更深刻的意蕴。薛家是贾府的影子,薛蟠“太平命案”出了,贾家却靠不住了。两次命案相隔八十多回,已跨越故事全过程的三分之二,叙事时间大约是八年。“葫芦案”是在“元妃省亲”的六年前,“太平命案”是在“贾府被抄”的前一年,这些年正是贾府“虚架子”衰败的暴露过程,是逐渐由内到外显露的时间记录。“叙事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每一篇叙事文章,就会发现时间的重要性在于它牵引着叙事者和读者的注意,操纵着文本展开的脉络。没有脉络就没有生命,没有注意就没有对生命的关怀和理解。”[8]薛家是贾府衰败的隐线,既是“隐线”,就或多或少为贾府大悲剧或铺陈,或渲染,或点睛,总之它的叙事内容不能游离贾家。作者安排薛家上升为叙事主体,薛家的故事恰恰在《红楼梦》整个结构的“黄金分割线”上出现,大有深意。从第七十九回“薛文龙悔娶河东狮”起,作者用了很多篇幅集中写薛家,故事虽然集中在薛家,但薛家并不是《红楼梦》叙事结构的重心。作者宕开一笔,写薛家的“窝里斗”,内生祸乱,正好和贾府的衰败同命运。所谓“四大家族”,《红楼梦》只重点写了贾家,薛家、史家、王家仅是贾府的陪衬和拓展。但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写薛家、史家、王家,最终目的是深化贾府的历史意蕴,形象地揭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规律。
薛家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叙事结构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它包括一个要点:薛家上升为叙事主体,恰恰在《红楼梦》叙事结构的“黄金分割线”上,这是《红楼梦》衰败史主旋律高亢的表现,是时空结构最完美的体现。当史家、王家都衰败后,贾家的“虚架子”还没有赤裸裸暴露出来的时候,把薛家的叙事提到主体地位,一方面写薛家如何破败,一方面透视贾家也在衰败,从而深化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的历史结局。这也是作者曹雪芹整体观的艺术再现,即《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内在艺术规律使之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