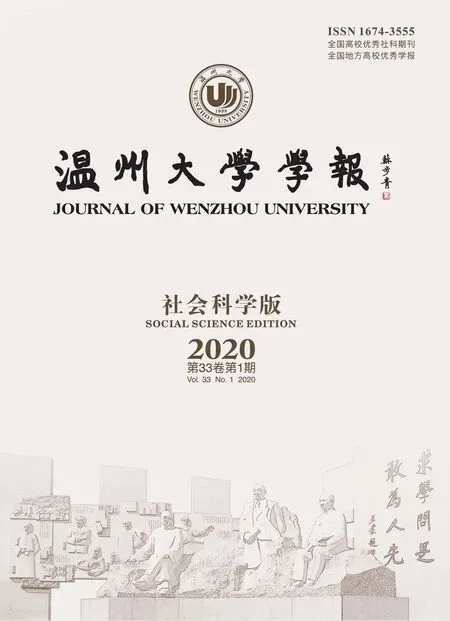朱熹与永嘉学派关于“欲”的思想之分歧
冀晋才,吴妮妮
(1.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2.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经济与贸易分院,浙江温州 325000)
朱子学派与永嘉学派作为南宋时期两个不同的儒学流派,其思想的外在分歧是不甚鲜明的。目前学界的研究注重政治、军事和经济主张上的“性理”与“事功”之别,和本体论上的“理”与“道”的不同。而无论朱子学派亦或是永嘉学派,都同样坚持了传统儒家从“内圣”到“外王”的理论框架、礼乐政刑的政治建构、三纲五常为基础的伦理思想,遂使得无论是形而上的本体论研究,还是分门别类的思想研究,都难以抓住两大学派思想分歧的根源和实质,以至于有些学者将两种思想视为一物。本文以“欲”思想为突破口,试图深挖两派思想建构的起点,从根源和最终走向上剖析双方思想的根本分歧。
一、朱熹与永嘉学派对“欲”的不同认识
叶适总结宋代两百多年治乱得失道:“国家以文治二百年矣,孔子、孟轲之学无所不讲,儒雅高论之士无所不用,《六经》之道庶几其可以行之也,其过于汉、唐远矣,而迂阔之议,犹不绝于世。君以此诮其臣,臣以此病其君,上下相戾而治功不立……其小者学通世务,则钱谷、刑狱不足以深知而徒以纷乱,其大者取三代之不可复行者勉强牵合,以为可以酌古而御今,二者皆足以败事。”[1]675“其小者”概指荆公新学,徒兴利而不加以制约,致使利欲盛行、国家纷乱。“其大者”概指程朱“道学”,徒知复古崇义、高谈义理心性而短于对兴国利民实政的研究,上不能辅助君王安邦定国,下不能修理民政使社会安定有序、百姓生活富足。显然在叶适看来,都是取乱之道,根本原因在于对人欲的处理不合理,一方纵欲过度、一方约束过甚。永嘉学正是基于对北宋以来治乱兴衰的反思,对这两派思想的折中和升华,主张义利双行。可见“欲”是各派思想论争的核心议题之一,而对“欲”的不同思考似也是朱子学和永嘉学观点分歧的真正源头。
(一)理-气-心-性-情-欲:朱熹论“欲”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理-气-心-性-情-欲”是最基础的几个范畴,历来朱子学研究的路径,都重视探讨形而上的“天理”“人性”和“气”,低估了“人情”和“人欲”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朱熹的思想中,虽然“天理”是万物的最高主宰,但其思想体系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而“心”又是“人”一身之主宰,因而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心”。“心”动而生“情”和“欲”,因而“人情”和“人欲”正是“心”的基本内涵。“天理”是基于其上而建构的制约理论。倘若没有“人情”“人欲”的难以节制、泛滥为恶,“天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理”和“欲”正是“心”的两端,一端是善,一端是恶。
朱子学所讨论的这几个基本范畴,除“气”以外都首次集中出现在《礼记》中。《乐记》中说:“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又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礼记·礼运》中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礼记》编纂的基本意图显然是为了论证儒家礼、乐、刑、政的产生原因及其合理性,因而所讨论的最核心问题的是以下两个:一是礼乐政刑的产生原因,即社会普遍的情感泛滥和欲念膨胀不加节制可能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二是礼乐政刑在治理人情、人欲方面的不同目的及合理性。这也正是朱子学的展开思路,即从人性本源出发去论证儒家修身、治国思想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朱熹继承了孟子的“四端”论思想,在孟子认为人心有识辨是非善恶的主观能力、向善之可能性和愿望这些论点之上,更进一步地提出“性本善”思想。
朱熹从宇宙起源和人类产生来论证“性本善”、“恶”非“本性”。朱熹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故发而为孝弟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2]65即阴阳五行之气交感聚成人之形体,人类兼得五行之气,且“得其气之正且通者”,故有感通之能,且生而五行之性兼具。“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故无感通之能。
朱熹继承了张载“心统性情”的观点,此“心”即人的意识,是人之视听言动思的主宰。他说:“心是管摄主宰者,此心之所以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2]97“情”是“心动”产物或表现形式,有“中节”与“不中节”两种情况。“中节”即“情”合于“天理”,“不中节”即“心”失去“天理”的节制而为物欲所控制,流为“私情”“人欲”。比方说满足生存需求的饮食欲、男女之间的正常情感等,属于“情”发之“正”。一旦内心有追求美食、美色的非分之想,便是“私情”泛滥、“人欲”萌发。
事实上朱熹也肯定了人之基本欲望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人欲有“本能之欲”与“过度之欲”之别,或称为“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自然流露的、出于基本生存需求的“欲”,是“天理流行”;超越基本生存需求的“欲”和“心”为外物所诱惑而产生的过度的“欲”,便是“人欲之私”。朱熹将“理欲”归于“七情”之一,是善的,而将“私欲”单独提炼出来,竭力塑造为与“天理”对立的“恶”的一方。“性”本自“天理”,“欲”本自“气禀”或外物之诱,是全不相干的两种事物。因而在朱熹的思想中,“欲”基本是被否定、贬斥的对象。
(二)“欲”源于“性”:永嘉诸子论“欲”
永嘉诸子对“欲”的根源与本质的认识与朱熹不同。薛季宣认为“欲”是“性”所发,无需分公私。他说:“情生乎性,性本乎天。凡人之情,乐得其欲,六情之发,是皆原于天性者也。先王有礼乐仁义养之于内,庆赏刑威笃之于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欲。”[3]360薛季宣不谈公私,而是指出君子小人各有不同追求。先王之“道”并不是非要使所有人都恢复朱熹所谓的“性情之正”,而是创立礼、乐、政、刑诸法,既满足天下人之普遍欲望诉求,又加以规范和约束而不使之过分冲突、泛滥。
陈傅良肯定了薛季宣“性”“情”“欲”思想,以《商书·仲虺之诰》中“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一句来阐述其观点,强调使“欲”有“主”。这里的“欲”“主”与朱熹所论不同,“欲”是普天下人之欲望,“主”是指实际上的万民主宰者——皇帝。他为光宗讲《孟子·滕文公下》中“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一段时说:“‘圣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无明天子也。‘诸侯放恣’者,言上无明天子,则下无贤方伯,凡有国之君皆得自便,纵欲而专利也。”[4]247因此陈傅良总结道:“且夫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4]247这里的“主”便是“明天子”。他继续讲道:“人所以相群而不乱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则上下尊卑贵贱之分定;有父在,则长幼嫡庶亲疏之分定,定则不乱矣。苟无君父,则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苟有争心,不夺不厌,是人心与禽兽无择也。”[4]248在陈傅良看来,情感欲望人皆有之,无所谓公私偏正。有“欲”就会有争心,有实现的愿望。人与人之间的欲望常相互冲突,正是因为有君有父,纲常伦理才有定,社会才能井然有序,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
叶适对薛、陈的思想进一步发挥,他说:“极之于天下,无不有也。耳目聪明,血气和平,饮食嗜好,能壮能老,一身之极也;孝慈友弟,不相疾怨,养老字孤,不饥不寒,一家之极也;刑罚衰止,盗贼不作,时和岁丰,财用不匮,一国之极也;越不瘠秦,夷不谋夏,兵戈寝伏,大教不爽,天下之极也;此其大凡也。至于士农工贾,族性殊异,亦各自以为极而不能相通,其间爱恶相攻,偏党相害,而失其所以为极;是故圣人作焉,执大道以冒之,使之有以为异而无以害异,是之谓皇极。”[1]728这里所说的“极”,可以理解为情感和欲望诉求。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欲望的冲突、不能相互尊重和和平共处,相互侵夺攻伐,才使得天下大乱。圣人因乱世而起,制礼乐政刑诸法以足天下之欲、顺天下至情、和谐万邦,圣人的理想和方法之精义便是“皇极”。叶适的“皇极”与陈傅良所说的“欲”之“主”在内涵上比较相近。
朱熹强调深挖“情”和“欲”的根源,其目的在于让人们认清“人欲”不合于“天理”,是万恶之源,从而明白“穷天理、灭人欲”的重大意义。永嘉诸子则肯定了“人欲”存在的合理性,强调欲求不满和欲求冲突都是引发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们更强调去研究满足、缓和和控制情感欲望的制度和手段。
二、分歧的延伸:治欲主张的不同走向
(一)修身与教化:朱子学的治欲主张
朱熹基于对“人欲”之根源与实质的认识,针对个人和社会,提出了以修身和教化为核心的治欲思想。朱熹认为,自天子至于庶人,做一切事都应当以修身为前提。朱熹指出:“修身是齐家之本,齐家是治国之本。如言‘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之类,自是相关,岂可截然不相入也!”[2]357修身与齐家是一体的,修身正己方能正人,先能正自己家风才能在治国平天下上更有说服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质上说是一件事,即教化。修身是教化自己,齐家是教化家人,治国是教化国民,平天下是教化普天下之人。朱熹给出了修身之目标、进路和榜样。其目标即“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5]92也就是人心听命于道心。
朱熹的修身思想分两个部分,即知与行。一是知,即通过读圣贤书和在具体事务中体认天理;二是行,即用天理去指导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行为。他主张先知后行,并指出修身需要有榜样,要向圣贤学习,抑人欲、存天理,克己自律、反躬自省、大公无私、怀仁天下。“知”即穷理,“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2]152朱熹将儒家关于个人修养、社会教化的理论上升为“天理”,继而告诫所有人,必须用此理格治人欲,方能成人、成德、齐家和平治天下。穷理便是体认天理,明白天理与人欲之别。排空心中之物欲,让心不为外物所诱。穷理分两步:一是虚心切己,就事上体悟理;二是读圣贤书,从书中寻求天理。“虚心”是排空内心之私欲,“切己”便是将日常所见之万事万物与自己紧密关联起来、将为学与发明本心紧密结合起来。朱熹说:“入道之门,是将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久之与己为一。而今入道理在这里,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2]446天理人欲共存于人心,此进彼退、此长彼短,心中私欲越炽,则天理愈昏,因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圣贤们的言行学思合于天理,蕴含在他们的著作之中,因此学者通过读圣贤书去体认天理是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以圣贤之意观圣贤之书,以天下之理观天下之事。”[2]159朱熹认为,只要“知”的功夫做到了,自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依“本性”行事,自觉地去私欲、存天理。
朱熹深刻地认识到了治乱兴衰的根本在于人心,人心之蔽在于“人欲”,故而他将“人欲”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敌,建构了完善的理论体系,并引用广博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去佐证其理论体系。虽然朱熹也说:“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2]148但由于他的大部分思想都在教育人们“穷天理”,在“行”的层面则只是强调“择善固执”,容易诱导人们将大部分努力花费在“知”的层面,而忽视“行”的重要性。
(二)修“实学”“实政”“实德”:永嘉诸子的治欲主张
永嘉诸子从本质上说并不反对朱子学,而是在体悟义理的同时也注重具体事务上学问的研究。薛季宣致陈傅良书中告诫道:“《中庸》、《大学》、《系传》、《论语》,却须反复成诵,勿以心凑泊焉。”[3]313但他反对朱熹“天理与人欲对立、此消彼涨”“只有先穷尽天理,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主张,反对单纯依靠个人不断提高自我修养以灭尽心中之私欲、单纯依靠教化去治理社会普遍的人欲泛滥。他主张通过切合实际的谋略、制度去满足和限制社会普遍的人欲,开创了永嘉学独特的治欲理念。
首先,薛季宣认为“道”是承载于“法”之中的,二者是一体的。“道”是高远而虚幻的,是难以认识的,不建议去花费太多功夫于此。在他上孝宗第一札中说:“夫清心寡欲,恭俭节用,尧舜三代所以治天下,陛下既已身之矣,自宜固守而勿失。……臣愿陛下深思远览,以静养恬,略其小者近者,而图其远者大者。”[3]189-190薛季宣肯定了孝宗的个人修养,他认为孝宗继续保持即可,不需花太多力气在此,凡事要有步骤、有目标,要务实。“道”常存于世用之“法”中,必须立足于时事,从有用无用、为善为恶处摸索“道”的大意。薛季宣不似朱熹,在“道学”与世间其他学问之间泾渭分明,只要是“有用之学”,都加以吸收。比如他评价《老子》一书,说:“读此书者可以轻利欲,祛物我,齐得丧,潜消悔吝于暗暧渺冥之中,在明达之士不可谓无补,则《老子》一书非可废也。”[3]42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朱熹“道统”的一种怀疑。其次,薛季宣先王之道便是用实政去实现和规范众人之“欲”。他说:“情生乎性,性本乎天。凡人之情,乐得其欲,六情之发,是皆原于天性者也。先王有礼乐仁义养之于内,庆赏刑威笃之于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欲。”[3]360再次,在修身进路上,薛季宣更加注重对“法”的钻研,虽然他也认为“学”是必要的,但反对将“学”的方向导向“穷理”。全祖望评曰:“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言其学务求有用于时事,务实之风有别于当世之人。但同时又说其学“大本未尝不整然”[6]1690,言其学合乎儒家王道精神。
陈傅良治欲的主张大致可归纳为两点:一是使“欲”有“主”;二是“负其责”。陈傅良是基于薛季宣“欲”思想而论的。所谓使“欲”有“主”,即将普天下人的情感欲望限定在制度纲常之内。这里的“主”有两层释义,于国的层面为“君”,于“家”的层面为“父”。“君”者制定并主持一国之纲纪,“父”者制定并主持一家之法度,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身份、权利、义务由此而分明,国与家方能和谐有序,即上文所说的“人相群而不乱”。倘若无“君”无“父”,则国法家规无人主持,则等级、身份、权利、义务等必将陷入混乱,人与人之间相互觊觎、阴谋侵夺,国与家必将陷入混乱。显然,在陈傅良的治欲主张里,实施主体是“君”和“父”,实施途径上重在依靠纲纪法度的贯彻实行。这与朱子学所倡导的以自我为实施主体、以个人修养的提升为主要实施途径的治欲主张是截然不同的。所谓“负其责”,实质上是敦促“君”和“父”承担起满足人们基本情感欲望需求,和制约、引导人们过剩的情感欲望的使命。君之责是教化、保育百姓,父之责是教化、养育子女,其道一也。他说:“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驱猛兽,使斯人脱于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相保也,则禹、周公之责不塞。……今敌国之为患大矣!播迁我祖宗,丘墟我陵庙,羶腥我中原,左衽我生灵,自开辟以来,夷狄乱华未有甚于此者也。……二圣人(高宗、孝宗)之责,至今犹未塞也。”[4]250陈傅良对上古圣王功业进行了分析,指出禹、周公之伟大,正在于他们完成了庇护百姓免于灾祸的历史使命,有效地实现了天下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欲望。由此,他诫勉皇帝,不要视“功利”如洪水猛兽,在其位、负其责、有如上功利心才是真正的儒家“王道”。
叶适进一步发挥薛、陈之说,叶适构建了自成一派的永嘉“道统”:自尧、舜、禹、皋陶、汤、伊尹、文、武、周公至孔子,程朱学所重的孟子、子思等皆不在其中。叶适所关注的重点在于他们的治世之法和功德。他指出:“天子以保民为职”[1]846。尧的功德是“允恭克让”和“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一是不谋私利,能礼让贤者;二是任用羲和制作历法,保障百姓生产生活。舜的功德是“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和“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至于思孟学、程朱学所宣称的尧舜相传之“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叶适认为“非本文也”,即不是根本之论。至于大禹治水、皋陶作刑法,乃至周公制礼作乐,皆是因时而作的利民实政,这正是他们的“德”之所在。由此,他便将“事功”取代程朱“性理”之学,成为“道”的核心内涵。其治欲主张可总结为实学、实政和实德三点。
首先,叶适主张君王士大夫当学“实学”,勿空谈心性义理、怡情于诗赋文章。叶适之“实学”可归纳为“皇极”“大学”“中庸”三点。“皇极”,是统摄、沟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之“道”。圣人因乱世而起,制礼乐政刑诸法以足天下之欲、顺天下之情,和谐万邦,圣人的理想和方法之精义便是“皇极”。他指出:“唐、虞、三代,内外无不合……今之为道者,务出内以治外也……守其心以自信,或不合焉,则到何以成?于是三者或不能知其所当施之意,而徒饰其说以自好,则何以为行道之功?”[1]727这显然是在批评朱、陆之学不知事功、经制才是尧舜之道的固有内容,因而既不能正纲常伦理,又难以保育百姓、开拓进取,叶适为学的目的便是补朱、陆之学这一缺陷。“大学”是既能够善其身,又能够济天下的学问。他说:“知足于其身而不及修,不能治天下国家而能顺天下国家之所以治,此学之所谓小也。”[1]730叶适认为“中庸”之道便是肯定万事万物的差异,帮助它们共存共容,否定了朱熹所坚持的“天理”一元论。他说:“道原于一而成于两,古之言道者必以两。……然则中庸者,是以济物之两而明道之一者,为两之所能依而非两之能在者也。”[1]732
其次,叶适主张君王应当修“实政”“实德”,总思路是“义利双行”。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叶适上书论国家兴复大计说:“愿陛下先定其论,论定而后修实政、行实德,变弱为强,诚无难者。”[1]6其“实政”主要是精练大军、历练大臣以及具体的战守之策;其“实德”即改革弊政以养民、保民。修“实政”以切实负起保民养民的责任,君王之“实德”也在于能让百姓生活安定、富足。叶适认为逐欲是人之本性,凝结人心的根本因素在于“利”。他说:“夫天下所以听命于上而上所以能制其身者,以利之所在……是故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则沮天下之望;可广而不可狭,狭则来天下之争。”[1]671因此治国应当首先兴利,足天下人之“欲”。以天下之利役天下之人,以礼法制度抑天下之欲。使人人各得其欲而无争,方能使天下太平。同时他也强调“义”,在足“欲”的基础之上,制定礼法制度去引导、限定天下人之欲望。他说:“为之立其等秩,程其功能,纵而告之曰:‘至于是者取而去之’。”[1]672即告知天下人,想得其“利”须遵其“义”,利诱之、义制之。
三、分歧发生的原因探析
两派思想在“欲”概念范畴上的分歧的发生,源起于两派思想家不同的生活地域和他们学术背景的差异。
(一)生活地域不同
生长地域与经历是两派思想分歧发生的历史起点。南宋初紧张的内外局势下,士大夫们普遍对个人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充满担忧并积极寻求解脱,这是南宋时代思想文化兴起的大历史背景。朱熹生于江西,永嘉诸子生于浙东,因生长地域有别,其经历自不相同,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主张又呈现出很大差异。浙东地区在南宋初年饱经战火洗礼,又时刻面临金军兵锋的威胁,因而浙东思想家有强烈的忧患和求生意识。江西则基本未遭战乱,思想家们忧患不足,且求生意识相对较弱。永嘉诸子中,薛季宣、叶适有过在北方边境地区为官、参加过对金作战的经历;陈傅良有过长期在湖湘为官的经历,他们都直接体会到了战乱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悲惨境遇;因而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让国家富强、如何在与金国的军事对峙中占据优势或取胜等问题。而朱熹、陆九渊则长期生活在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学问而不是做官,因而他们更关注的是社会人心。
孝宗即位初,朱熹上书说:“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举,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7]12752朱熹认为摆在皇帝面前的头等大事是尽弃佛、道以及其他杂学,正心诚意以修帝王之学,即孔孟之学。君王应先穷天理、灭人欲,以正心、诚意为根本之务。主张君王“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使国家走向稳定和富强。至于富国强兵的具体策略,朱熹并无太多建言,似乎也并未引起他的重视。朱熹指出:“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2]2689“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2]2678他认为君心正,万事自然迎刃而解。显然在朱熹看来,方法策略是次要的,致君行道才是国家兴复的根本。
永嘉诸子则更多关注的是社会实际问题,薛季宣上孝宗第一札中说:“臣谓治有本末,政有先后,先所施者,后或可置,本既举矣,末亦可捐。夫清心寡欲,恭俭节用,尧舜三代所以治天下,陛下既已身之矣,自宜固守而勿失。……方今国威未振,民力未支,而虏人之情,传闻常多失实,陛下再造之心虽不可暂忘,而进取之事,其实未可轻议。”[3]189-190薛季宣首先肯定了孝宗的个人修养,认为继续保持即可,不需花太多力气于此。其次他阐明了敌我双方之形势,提醒孝宗不可急功近利,凡事要有步骤、有目标、要务实。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明治道、遴选辅政良臣,以群策群力、辅助皇帝治理国家向正确方向发展。这些意见得到孝宗的赏识,又命他做详细阐述。薛季宣说:“臣闻礼烦则乱,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详求其故,则冗官、冗兵二事,实有以困之也。……惟今法度之弊,臣所知者莫此为大。……陛下必欲仍今日之文弊,以图天下治理,非臣所知。”[3]191-192薛季宣指出了导致宋朝一直贫弱的重要原因是“冗官、冗兵”,可谓正中要害。他认为此时国家之急务是改革“法度之弊”,解决“冗官、冗兵”等弊政,这与朱熹的看法就泾渭分明了。其后他又数次上书论当时之弊政,有害民之政如武昌屋租、德安牛租、温州淹浸田租①武昌屋租:南宋初,随着武昌逐渐成为抗金前线,武昌百姓大批逃亡,官府遂用他们的房屋来安置从他处流亡而来的百姓,并收取一定的租金。多年后,这些房屋大多毁于战乱,官府依然强令百姓交租。德安牛租:岳飞驻军德安时发现百姓耕种无牛,遂将官牛收取一定租钱后租与百姓。后来百姓已不再向官府租牛,但官府依然强令百姓照交牛租。温州淹浸田租:南宋初,温州地区因江湖水位下降或海水退潮会形成一些无主滩涂,官府在收取一定地租后允许百姓在此耕种。后来水位上升,田地被淹,但官方依然强令百姓交租。以上三项本是利民之政,但却被贪婪的官员们所利用,变成害民之政。参见:文献[3]:193。等;有江淮地区授田名实不符的问题,因战乱,此地人员变动很大,有田者不交租、无田者反被勒令交租等问题很严重,既害百姓,亦不利于国家治理;有整饬边境守备、整编军队等任务。陈傅良的进取意识一如薛季宣鲜明,他对于薛季宣思想的发扬之处在于具体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的丰富上。《宋史》言其学“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而于太祖开创本原,尤为潜心。”[7]12886陈傅良做学问之功力非常扎实,诗文皆可为一代宗师,政论皆细致深入而切近时弊,所著《历代兵制》则将历代军事思想无论战略战术、战阵转化、卒伍编练糜不详尽。
(二)学术背景不同
学术经历是两派思想分歧发生的思想起点。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其父朱松(1097 – 1143)是二程门人,从小耳濡目染,受二程思想的熏陶。根据《朱子年谱》记载,朱熹在10 岁时就“在临安刻苦读《四书》,慨然有做圣人之志”[8]59。他后来又先后拜刘子羽(1086 – 1146),刘子翚(1101 – 1147)、刘勉之(1091 – 1149)、胡宪(生卒不详)、李侗(1093 – 1163)等道学名儒为师,学问渊源脉络鲜明、根基扎实。
永嘉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六岁时便父母双亡,由其伯父薛弼抚养。《宋史》载:“从弼宦游,及见渡江诸老,闻中兴经理大略。喜从老校、退卒语,得岳、韩诸将兵间事甚悉。年十七,起从荆南帅,辟书写机宜文字,获事袁溉。溉尝从程颐学,尽以其学授之。季宣既得溉学,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法之制,靡不研究讲画,皆可行于时。”[7]12883薛季宣早年随薛弼宦游四方,在宋金战争中颠沛流离,常从南渡的士大夫们口中得闻抗敌御辱、经略中原之事。常和退役的老兵们探讨岳飞、韩世忠等名将的将兵事迹,深刻体会到了宋金战争中军事上的得与失。后虽曾师事二程门人袁溉,但其学习的旨趣也更重经世致用的具体实用之学,而非潜心心性义理。陈傅良早年出身乡野,并无固定的师承。后受学于薛季宣,方才真正入学术之门,因而在学风上深受薛季宣之影响。叶适从小便十分敬仰陈傅良之学问,师徒四十多年的相处,学问上受到的影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是不言自明的。永嘉学思想旨趣一脉相承,注重经世致用、改革变法,被朱熹批评“功利”[2]2967。
出于上述两方面原因,朱熹和永嘉学派方有后来不同的学术走向。朱熹认为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人心之蔽在于“人欲”,故而将“人欲”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敌,并建构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去针对,提出了广博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去佐证。永嘉诸子本质上同意朱熹之说,但反对朱熹“天理与人欲对立、此消彼涨”“只有先穷尽天理,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主张,反对单纯依靠个人不断提高自我修养以灭尽心中之私欲及单纯依靠教化去治理社会普遍的人欲泛滥。他们主张通过切合实际的谋略、制度去满足和限制社会普遍的人欲,或以利欲诱人为善,开创了永嘉学派独特的治欲理念。
四、小 结
就思想的深度与高度上说,朱子学显然更胜一筹。永嘉学派的“欲”概念基本上是自然存在意义上的人的情感欲望,而朱熹的“欲”有其本体论支撑和形上学依据。朱熹所论之“欲”,既是“理”,也是“气”:属于“理”的部分是“七情”之“欲”,是“性”动,是为“公欲”或“理欲”,是善的;属于“气”的部分是源自“气禀”或物诱,是为“私欲”或“人欲”,是恶的。就逻辑体系上论,朱子学也更加完备,极大地促进了儒家哲学体系的完备和提升。
然朱熹将治学之大把精力集中于体认“天理”、治欲修身,将之视为平生万事之主业,致使多少人皓首穷经、荒于世用,其消极影响不可谓不大。永嘉诸子致力于改革治世、富国强兵,于性理人心亦有基本精神的领会。但他们错看了时势,或错生了时代。南宋朝廷于兴复大业一直摇摆不定,孝宗执政中晚期,耽于和平、不思进取;光宗在位期短,又深受情感波动及疾病影响,于国家大事成就不大;宁宗时又陷入党争,士大夫人人自危、闭口不敢言政。永嘉诸子三代几十年的努力在这样的政局下终止于文字,未得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