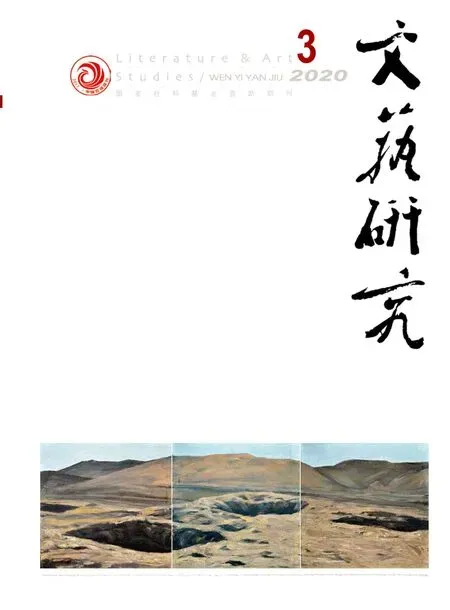中国现代通俗会党小说论
汤哲声
“会党”一词最早出现在晚清,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有关。清代民间社会存在很多秘密团体,如天地会、哥老会等,但这类组织在当时一般被称为“帮会”。孙中山1894年11月24日成立兴中会后,即与这些秘密团体联系。由于一致反对清政府,这些秘密团体开始与兴中会结合,使得这些组织逐步革命化,并被称为“会党”。孙中山曾说:“余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①如果从中国政党成立的时间来考察,那么“会党”应是1894年以后出现的词汇。
“会党”是帮会和政党这两种社会组织的合称。它们有一些共同特征,但帮会主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具有江湖性质,政党则要实现某种社会理想,具有革命诉求。因此,会党小说必须在思想上有革命倾向,在内容上则主要表现江湖恩怨。从这样的标准出发,会党小说是文学史上的独特类别,现代通俗文学史上的黑道小说、镖局小说,如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等,只能称作“帮会小说”,而新文学史上的那些政党小说,如巴金的《灭亡》《新生》等,则只能算是“政党小说”。晚清时期《东欧女豪杰》的发表,引发了以表现秘密会党从事革命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创作热潮,使会党小说成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的亚类型。伴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会党小说的叙事形态也不断演进。对这一小说类型发展过程的勾勒,可以显影某些制约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发展的因素。
一、《东欧女豪杰》的译述与会党小说的基本架构
1902年,《新小说》杂志上连载了岭南羽衣女士著、谈虎客批《东欧女豪杰》,这部小说通过讲述俄罗斯民意党人刺杀沙皇的故事,宣传革命理想,是晚清会党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是译还是述,作者究竟为何人,已有不少论者论述和考证,笔者在此不加分析②。笔者认为,这部小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作为一部外国小说在中国产生影响的,它由外国人、事加上中国演义小说的铺叙、评点组成,是中西小说的杂糅体,其美学特征与晚清很多译述小说相似,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于《东欧女豪杰》的内容,梁启超早在小说发表前,就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7月15日)一文中阐释得相当清楚:
此书专叙俄罗斯民党之事实,以女豪杰威拉、莎菲亚、叶些三人为中心点,将一切运动之历史,皆纳入其中。盖爱国美人之多,未有及俄罗斯者也。其中事迹出没变化,悲壮淋漓,无一不出人意料之外,以最爱自由之人而生于专制最烈之国,流万数千志士之血,以求易将来之幸福,至今未成,而其志不衰,其势且日增月盛,有加无已。中国爱国之士,各宜奉此为枕中鸿秘者也。③
这段文字中有四个关键词。首先是“俄罗斯民党”。该党史称“俄罗斯民意党”,在中国也被称为“虚无党”,主要活动于19世纪70—90年代。反对沙皇的专制主义是该党的宗旨,小组活动、深入民间和暗杀是该党三种主要的行动策略。该党于1881年3月1日成功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遂受到严厉镇压,自此式微。1902年刊出的《东欧女豪杰》是最早将俄罗斯民意党人介绍到中国的文学作品。1903年,梁启超在《论俄罗斯虚无党》中论述这些民意党人,明确表达崇拜之意。从此,中国的革命志士开始推崇俄罗斯民意党,并效仿其激进的革命手段。
第二是“莎菲亚”。后来中国知识界称之为“苏菲亚”。《东欧女豪杰》中的莎菲亚身上具有以下特质:一是贵族出身,其文化修养和生活礼仪使她具有高贵气质;二是具有反对专制主义的崇高理想,这使她有主见、有生活的动力和奋斗目标;三是具有行动力,她是刺杀沙皇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行动成功与她现场的冷静指挥密不可分;四是年轻漂亮,小说这样描绘她:“菲亚生时,白鹤舞庭,幽香满室,母亲李氏心知有异,十分疼爱。菲亚长来,果然秀慧无伦,两岁便能识字,五岁便会吟诗,到了八岁的时候,跟着母亲在格里米亚地方上学念书,真是过目不忘,闻一知十,乐得他的师友,无不把他敬重。不上几年,在寻常中学校领了优等卒业的证书,又再进那高等中学校。到一千八百六十九年,青春十六,正长得不丰不瘦,不短不长,红颜夺花,素手欺玉,腰纤纤而若折,眼炯炯而多情,举止则凤舞鸾翔,谈笑则兰芬蕙馥。”④1905年,同盟会会刊《民报》第2号刊登了苏菲亚的画像,从此那个眼睛妩媚、有神的女人形象进入了中文世界。在《民报》第15号上,廖仲恺这样感慨:“女员之多,虚无党之特色也,岂此极灵秀之气,果独钟于女子乎。”⑤何止廖仲恺,苏菲亚在当时的中国几乎就是“自由女神”,各大刊物充满着对她的歌咏。1932年,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就回忆:“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了的是苏菲亚,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⑥
第三是“出人意料”,这是指情节曲折。一个漂亮的女人进行暗杀活动,题材本身就吸引眼球。且小说着重描写莎菲亚密室策划、发表演说、被捕入狱等经历,情节非常曲折。
第四是“爱国之士”,这也使得小说充满有关平等、自由的政治宣传。《东欧女豪杰》中有很多演说词,介绍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关于自由、平等的思想,强调革命手段的极端化:“原来我们同志,愤世嫉俗,只见当今凡百现象,都与天然大法相反,若不用破坏手段,把从来旧制一切打破,断难造出世界真正的文明。因此我们欲鼓舞天下的最多数的与那少数的相争,专望求得平等、自由之乐。”⑦小说写的是俄罗斯,译介者却意在启发国人,生活于同样的社会环境,俄国人可以这样反抗专制体制,中国的爱国之士为何不可?小说第二回的总批这样写道:“中国人未蒙产业革命之影响,于此事犹懵然也。十年之后,必有大波动。此回略述泰西所谓社会主义之大概,读者幸毋以对岸火灾视之。苏菲亚以千金之躯,杂伍佣作,所至演说,唇焦舌敝,百折不磨,虚无党之精神,全在于是。今日中国所谓志士,乃日日在租界坐马车吃花酒,读此能无愧煞!”⑧可见,以苏菲亚的故事启蒙国人,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意图。
《东欧女豪杰》连载之后,在中国社会反响强烈。从1903年开始,《大陆杂志》《童子世界》《浙江潮》《警钟日报》《苏报》《江苏》等杂志上,介绍俄国虚无党人的文章连篇累牍,特别是1907年,廖仲恺在《民报》上发表《虚无党小史》,产生广泛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介绍和评析俄国虚无党和苏菲亚的文章都会联系起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认为他们的革命方式同样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徐锡麟、秋瑾、汪精卫、黄复生等革命党人,用行动向俄国虚无党人致敬,秋瑾更是被称为“中国的苏菲亚”⑨。
此时中国文坛正在大规模翻译外国小说,有关俄国虚无党人的小说倍受青睐。1936年,阿英在回顾此时俄国文学翻译时曾说:“俄国文学的输入中国,据可考者,最早在清朝末年,那时翻译最多的,是关于虚无党的小说。”⑩阿英还从中国的实际情况解释这种现象:“虚无党小说的产地则是当时暗无天日的帝国俄罗斯。虚无党人主张推翻帝制,实行暗杀,这些所在,与中国革命党行动,是有不少契合之点。因此,关于虚无党小说的译印,极得思想进步的智识阶级的拥护与欢迎。”⑪阿英还进一步指出,大概到1912年前后,俄国虚无党人的小说翻译热潮告一段落,此后进入了翻译契诃夫小说的时代⑫。然而,虚无党小说在中国流行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在晚清为中国创造了会党小说的基本架构,对中国通俗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二、晚清女性主义会党小说与中国的“苏菲亚”
《东欧女豪杰》的价值不仅是提供了一部有关虚无党人的小说,而是其内涵被中国读者予以创造性阅读。正如戴安娜·克兰在《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中指出的,“公众成员没有被概念化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为能够重新阐释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积极主体”⑬。晚清时代的小说家正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对《东欧女豪杰》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对中国读者来说,《东欧女豪杰》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女性革命者形象。果然,在《东欧女豪杰》问世后,一股以女性革命者为主要人物的小说创作热潮开始出现,大约有二十多部作品问世⑭。这类小说有很多名称,如“晚清女界小说”“晚清女性小说”“晚清女性主义小说”等,不过由于小说中的女性都依附于一个组织,笔者更愿意称之为“女性主义会党小说”。
这类小说最主要的特征是塑造女性革命者的形象。小说《女狱花》的女主角沙雪梅的形象就很有代表性:
话说沙雪梅骑在老虎背上,举起纷团花的拳头望它颈上乱打,大虫亦作一个溜地十八滚的势,狠命扑斗。旁边那个艾叶母豹,走过身来,反帮着大虫来咬雪梅。雪梅此内心中愈觉愤怒,双脚在老虎肚皮上狠命一夹,一拳在老虎头上狠命一击,那老虎大叫一声,四足腾起,从山顶上跳到平地。说时迟那时快,雪梅见老虎望空跳去,即将双脚一松,作了一个惊蛇入草的势,斜刺里钻去,攀着一支树枝落下。⑮
凭借高超的武功,沙雪梅杀了虐待她的丈夫并越狱成功,上段引文就是描写她在逃脱路上打虎。自《水浒传》塑造了武松打虎形象后,中国民间流传的英雄人物常有打虎的壮举。小说将打虎英雄塑造为女性,就是想告知读者女性也能成为英雄。
在众多女性主义会党小说中,写社会理想最厚实的是《黄绣球》。主人公秀秋,随夫姓黄,其理想不是妇女自身的解放,而是追求文明、平等的社会制度。她改名“绣球”,勉励自己要使地球锦绣一新。黄绣球努力学习北美农家女美利莱恩,在家乡建立了一个自由村,又在罗兰夫人的感召下,将自由村建设成一个重教育、重文明、男女平等、生活快乐的乡村乐土。为了保护自由村,她还建立了义勇军和女军。她在小说中是引领中国乡村社会走向文明之境的“圣母”。到乡间去、到民间去、启蒙民众、建立新的社会形态,是俄罗斯民意党最重要的政治诉求,也是《东欧女豪杰》最核心的理念。这部小说显然试图在想象的层面将《东欧女豪杰》所表达的理念落实到中国社会。
反抗对女性的社会压迫是这类小说最主要的诉求,这集中表现在对缠足的批判上,几乎每部小说都用较大的篇幅抨击这一现象。当然,这类小说最吸引读者眼球的是主人公的刺杀行动,如杀贪官、杀土豪等,刺杀对象上至执政者胡太后(《女娲石》),下至实施家暴的丈夫(《女狱花》)。刺杀成了这些女性改造社会的途径。无论是女刺客还是女革命家,她们的行动往往依托团体或组织,《黄绣球》中是自由村,《女娲石》里是血花党,《侠义佳人》中是中国女子晓光会,《女狱花》里则是“女杰六人”。在这些小说中,表现组织意识最强烈的是《女狱花》,书中六位女性几乎整日都在讨论革命纲领和如何建党。不过,这类小说所表现出的政治纲领大多不成型,几乎都是有关西方平等、自由理念的只言片语,其来源多为报章或书籍,有些干脆来自梦境。例如,《黄绣球》中的革命理念均来自主人公梦中与罗兰夫人的两次相遇。《女狱花》对革命的理解也很狭隘,主人公建立革命党的目的是:“妹妹想组织一党,将男贼尽行杀死,胯下求降的,叫他服事女人,做些龌龊的事业,国内种种权利,尽归我们女子掌握。”⑯将男尊女卑改成女尊男卑,这样的小说不过是女性“吐槽”的途径而已。
长期以来,中国小说一直充斥着男性话语,即使出现女侠也是男性的附庸,如聂隐娘、红线女等。这类女性主义会党小说将主人公由男性变为女性,实际上是向以男性为中心的创作思维乃至社会伦理规范提出挑战,使得这类小说具有较高的启蒙价值。然而,这些女性主义会党小说的政治理想与故事情节的设计均显生硬,编造痕迹明显。我们或许可以用叙事学理论中的“人物视角”概念对这个问题加以分析。“所谓‘人物视角’就是叙述者借用人物的眼睛和意识来感知事件。也就是说,虽然‘叙述者’是讲故事的人,但‘感知者’则是观察事件的人物。”⑰女性主义会党小说大多由有着激进的革命思想的男性作者创作,他们是文本的“叙述者”,但小说却以第三人称女性视角讲述,她们是文本的“感知者”。这就造成男性“叙述者”潜在的性别歧视意识与女性“感知者”的实际状态并不协调,甚至造成社会认知的错位。中国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形成已久,晚清时代很难找到出身贵族的苏菲亚式的人物,更没有女性主义思想的社会氛围。让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批判缠足是可以的,但让她思考社会改造和体制变革,就显得不切实际,甚至会产生反讽效果。如果男性作者的性别观念根深蒂固,并且编造着女性“感知者”的叙述,这种反讽性就会更加强烈。或许最典型的例子是《女娲石》,这部作品阐述女子为什么能成为革命党人的原因:“女子是上帝的骄子,有一种天赋的能力,不容他英雄豪杰,不入我的彀中……今日世界,教育经济,以及理想性质,都是女子强过男子……男子有一分才干,止造得一分势力。女子有了一分才干,更加以姿色柔术,种种辅助物件,便可得十分势力。”⑱小说强调的女性的天赋能力,即用“姿色柔术”展现魅力。这部小说中的女革命党人都是妓女,所属的组织“花血党”的总部是妓院天香院。以妓院做掩护、以妓女的身份从事刺杀活动,这就是女性革命的具体行动。这样的设计背后,是男性的性别歧视观念。硬搬过来的“苏菲亚”在中国实在有点水土不服。
三、陈冷的虚无党小说“以杀人而救人”
女性主义会党小说是根据《东欧女豪杰》中的女英雄形象创造出来的,另一批作家则热衷探究小说中的俄罗斯民意党,并将其与中国社会批判和改造结合起来。于是,一股虚无党小说的译介和创作的热潮在晚清兴盛了起来,其中成就最高者当数陈冷。陈冷早年游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做过《申报》编辑和《新新小说》《时报》《大陆》等杂志的主编或主笔。他译介了大量虚无党小说,如《俄国皇帝》《虚无党奇话》《爆裂弹》《女侦探》《杀人公司》《俄帝彼得》等,大多发表在他主持的报刊上,使得这些报刊成为当时宣传虚无党最突出的舆论阵地。有趣的是,陈冷自己的创作也充满了虚无党小说的气息,有些作品甚至看不出是创作还是译作。例如,陈冷的《刺客谈》(1906)写一个叫范朴安的书生怎样变成刺杀朝廷大臣钢毒和卖国贼汪秋的刺客。从小说人物的名字和叙述的故事看,这应是一部中国小说,但叙述者却表示这个故事是从外国人“密克先生”那里听来的,似乎有意让读者觉得这是一篇翻译作品,或改编自外国小说。这说明在陈冷心中,译或作没有太大区别。陈冷小说的基本成分是:理想的刺杀者、实践的行动者和惊险的故事。对于虚无党小说,陈冷曾这样评价:“其人勇猛,其事曲折,其道为制服有权势者之不二法门。”⑲陈冷作品的风格也是如此,文笔冷峻而峭拔。传奇的故事加之有特色的文笔,使得他的作品很吸引人。
虚无党小说一般会描写政党的纲领、组织、策略、行动。虽然是同盟会成员,但陈冷似乎对该组织的活动并不熟悉。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转而用土匪代替政党。其小说代表作是《刀余生传》,写一个旅客被土匪捉去,因毫不畏惧,受到匪首刀余生的赞赏。刀余生带着这个旅客参观匪窟的各个地方,如洗剥处、斩杀处、解剖处、货币库、练力场、演戏场等。观赏之后,刀余生发表以下宏论:“世界之今日,竞争愈激烈,淘汰亦愈盛,外来之种族,力量强我数十倍,听其天然之淘汰,势必不尽灭不止,我故用此杀人以救人,与其淘汰于人,不如我先自为之淘汰,与其听天演之淘汰,不如用我人力之淘汰。”⑳小说甚至列出一张杀气腾腾的“杀人谱”:
鸦片烟鬼杀!小脚妇杀!年过五十者杀!残疾者杀!抱传染病者杀!身肥大者杀!侏儒者杀!躯干斜曲者杀!骨柴瘦无力者杀!面雪白无血者杀!目斜视或近视者杀!口常不合者杀(其人心思必收检)!齿色不洁净者杀!手爪长多垢者杀!手底无坚肉脚底无厚皮者杀(此数皆为懒惰之征)!气呆者杀!目定者杀!口急或者不清者杀!眉蹙者杀!多痰嚏者杀!走路成方步者杀(多自大)!与人言摇头者杀(多予智)!无事时常摇其体或两腿者杀(脑筋已读八股读坏)!与人言未交语先嬉笑者杀(贡媚已惯)!右膝合前屈者杀(请安已惯故)!两膝盖有坚肉者杀(屈膝已惯故),齿常外露者杀(多言多笑故)!力不能自举其身者杀(小儿不在此例)!㉑
有趣的是,旅客听完这篇杀人谱后,竟然投身匪窟,被命名为“新刀余生”。
仔细考量会发现,这部小说的结构很特别。它似乎是一部传统的侠盗小说,却又与同类作品有着明显不同。刀余生并非杀人越货、论斗分金的匪盗,而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社会理想和行动纲领的思想者;他的理想不再是“替天行道”,而是进化论和启蒙意识,其目的是造就新国民和新社会;匪窟虽然也是山寨,却有着严密的组织分工,更像一个基地;刀余生的目的是用最极端的手法实现革命理想。同盟会成员陈冷显然发现了当时革命党人与江湖帮派结合的倾向,并通过将匪盗革命化、山寨基地化、语言政党化的方式,为中国会党赋予文学形象。陈冷的小说要比那些女性主义会党小说更加成熟,是俄国虚无党小说影响下的产物,标志着中国会党小说的新发展。
四、江湖黑道、会党秘闻与会党小说的消弭
民国建立后,会党小说沉寂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23年震惊全国的“临城劫车案”,才使这类小说再次兴盛。“临城劫车案”发生不久,姚民哀就据此事件创作了小说《山东响马传》。在这部作品中,小说家把土匪写成了有组织、有纲领的会党义举,延续了晚清会党小说的传统。由于小说的时效性很强,引起很多读者的关注,给姚民哀带来了声誉,也给出版这部小说的世界书局带来了巨大效益。于是在世界书局的督促下,作家延续着《山东响马传》的思路,开始了一系列小说的创作,会党小说在他的手中进入了创作的第二波高峰。
姚民哀的会党小说以1923年的《山东响马传》为起点,成型于1926年的《荆棘江湖》,成熟于《四海群龙记》(1929)和《箬帽山王》(1930),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其小说的会党性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品中会出现一个行侠仗义的组织;二是小说人物或多或少有清末秘密党团、帮会知名人士的影子,而且具有高超的武功;三是小说中穿插了大量帮规、行规的介绍,试图揭露“内部组织盗匪种种秘幕”㉒。1929年,他的小说《四海群龙记》在《红玫瑰》杂志上连载时,赵苕狂作序说姚民哀的小说“党会为经,武侠为纬,珍闻秘史,洒洒洋洋,独树一帜”㉓,这样的评价基本上说出了姚民哀会党小说的特点。
清末会党小说中的政党纲领主要是救国和启蒙,而姚民哀小说中的党纲则与道德准则、阶级斗争有关,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四海群龙记》中有一个“三不社”,要求社员一不做官,二不为盗,三不狭邪。其准则的第一条是:“带有革命色彩之无产阶级,与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开始奋斗。奋斗结果,现尚未定。”㉔《箬帽山王》中的箬帽党党魁杨龙海这样解释该党宗旨:“因为吾中华是农业国,顶要紧的是得到农民的信仰,其次就挨到各厂家的大小工人。据俺的思想,我党要做到,凡是戴箬帽的农、工两项男、妇都信从了本党,才算贯彻党义,达到成功目的,故而叫做箬帽党。”㉕这些党纲显然是作者根据当时部分政党的纲领编撰出来的,用来增加小说的政党色彩。此外,姚民哀笔下的会党大多系统完整,有层级、有职责。例如,《盐枭残杀记》中红帮“国宝山”有正副三堂六部的组织结构,最基层的组织称作“支部”,成员统称“老幺”,部会管支部,支部管老幺,各司其职㉖。
江浙一带在晚清时期是南社和革命党人主要的活动地区,姚民哀当时参加了南社、光复社、中华革命党等很多秘密会党的反清活动。这不仅给他提供了创作题材,也决定了其政治立场。他笔下的秘密会党大多具有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即使写绑匪的《山东响马传》,也将这些绑匪的所作所为写成官逼民反。在《四海群龙记》和《箬帽山王》中,作家更是正面歌颂秘密党人如何扶弱惩强、救世济民。《四海群龙记》中镇江“三不社”首领姜伯先的革命活动,处处影射当时镇江革命党赵声的事迹,只是将赵声写成了青红帮首领。小说发表后,甚至引起部分革命党人的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姚民哀笔下的政党活动很多是江湖秘事。在《箬帽山王》的《本书开场的重要报告》中,作家曾向读者开列了一张自己探访过的秘党历史的单子:
被我探访确实的秘党历史,以及过去、现在的人物的大略状况,也着实不少。除了已经说过的孙美瑶,峒坑的四大王、姜伯先等之外,尚有杭州的马德芳、顾瑞哥,吴江何家六,震泽倪财宝,江阴章少良,南京苏大官,江北伏虎潘凯渠,南通薛老四,无锡沙大,海州云北,徐州桑海山,浒浦葛绣锦,如皋泰州杨家老九、老十、老十一三兄弟,安徽鲍老四,营口计庆星,以及过去的人物如余孟亭、夏竹深、曾国璋、刘贵驹、李达三、郜三、马永贞的妹子、夏小辫子的女儿、范高头的妻子等人所干的事迹。倘经一位大小说家连缀在一起,著作一部洋洋洒洒的鸿篇巨著,可以称为柔肠侠骨,可歌可泣,足有令人一看的价值。㉗
这张单子里的人物身份极其混乱,有革命党人,有侠义之士,也有单纯的土匪。其中很多人当然为革命党做了不少工作,也有些侠义之举,但打家劫舍才是他们的本业。姚民哀将这些人、事混在一起写,而读者也不问究竟,都当作“秘党历史”来看,表明读者并不关心政党的立场,兴趣只在主人公的传奇经历。
为了增强会党秘史的神秘性,姚民哀在小说中还着重写了很多江湖切口。《四海群龙记》中的邓国人每次都被选为开香堂的代表,就因为他除了仗义疏财外,还对党规非常熟悉:“好在他(邓国人——引者注)自己本帮虽属嘉北分支嘉兴卫,其余各帮,如江淮泗总帮、嘉海卫帮、新河四帮、新河六帮、枕前帮等船有多少,兑粮若干,停泊何处,装兑那里粮米,进京打什么旗帜,平日扯何种旗号,吃什么水,以及正副三堂六部,七飞八走,粮船共有多少帮次,船上多少钉,多少眼,三般家法,十大帮规,有钉无眼、有眼无钉、无钉无眼三块板,三棵倒栽树,七叉九弯三不到,三刀八相八仙庵等秘密法规,国人肚子里都滚瓜烂熟,尽可为人代表慈悲。”㉘这段描写中的众多切口使得小说具有浓重的江湖气息,但这些内容能否算是党规却值得怀疑。
沿着这样的创作道路走下去,中国现代通俗会党小说“会”的色彩越来越浓,而“党”的色彩则越来越淡,最终使得会党小说与帮会小说合流。1941年,郑证因连载于《三六九画报》上的《鹰爪王》可以看作会党小说的余波。之所以将《鹰爪王》视为会党小说,是因为这部小说突出了帮会的组织性和系统性,而不同于一般的武侠小说。这部作品中的帮会不同于武侠小说中常见的门派和镖局,它组织严密,帮规森严,属于江湖世界中的黑帮组织。例如,凤尾帮有外三堂、内三堂,“所有老一辈的,不掌职司的,全请进福寿堂,由本帮养老”㉙。每堂有总舵主,下有众多分舵和香堂。为了规范整个帮会,凤尾帮还设立了十大戒律,是一个严密、规范的社会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特意强化了凤尾帮的神秘感,并将森严的组织架构作为基本的叙事线索。淮扬帮帮主王道隆要到凤尾帮“拜山”,必须找到后者总舵所在地。但由于这个帮会组织严密,他必须从基层组织开始寻找,一层层逐级上访,最终才找到总舵所在地——雁荡山十二连环坞。将帮会写成规章齐全、组织严密的类政党组织,表明《鹰爪王》继承了会党小说的余脉。只是在郑证因的笔下,帮会眼中只有小团体的利益,不再有崇高的社会理想和启蒙意识。《鹰爪王》这类作品里只有“会”,却没有了“党”,曾经闪亮一时的现代通俗会党小说也就消弭于江湖和帮会。
五、会党小说与中国传统美学接受
起源于《东欧女豪杰》的现代通俗会党小说,在演变过程中逐渐丧失政治理想和革命色彩,其发展路径令人惋惜。不过,如果从文化传播的过程和通俗文学美学接受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结果也属必然。文化传播的过程就是接受者选择性的接受和增删的过程,哈贝马斯的相关研究虽然是在剖析西方社会,但很多论述具有启发性:
如果说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乃至整个艺术作品都是为市场制造的,并且以市场为中介,那么,这些文化财富和所有那种信息便是极为相似的:即作为商品,它们一般都是可以理解的。它们不再继续是教会或宫廷公共领域代表功能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它们失去了其神圣性,它们曾经拥有的神圣特征变得世俗化了。私人把作品当作商品来理解,这样就使作品世俗化了,为此,他们必须独自沿着相互合理沟通的道路去寻找、讨论和表述作品的意义,这样于不言之中同样也可以产生无穷的力量。㉚
《东欧女豪杰》突出的“俄罗斯民党”“莎菲亚”“出人意料”“爱国之士”等四个关键词,本身就是当时忙于社会变革的革命党人关注的焦点。“俄罗斯民党”指革命组织;“莎菲亚”是革命需要的充满献身精神的女英雄;“出人意料”是指行动策划的严密和效果的彰显;“爱国之士”则是影响社会的启蒙思想家。这四大焦点构成了晚清革命党人对政治的理解,《东欧女豪杰》也就成了他们借俄罗斯民意党人的事迹寄托政治行动纲领的小说译介(或创作)。然而,在读者的阅读中,小说其实只是一种商品,这类作品中革命的神圣性,在图书市场上自然会被消解,而逐渐走向世俗化。
自《东欧女豪杰》后,中国会党小说的发展实际上构造了两大叙事话语,一是晚清的政治话语,二是民国的江湖话语。构造政治话语本来就是梁启超等人发起“小说界革命”的初衷,《新小说》等杂志就是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实验地。之后出现的那些宣扬女性主义的会党小说只是《东欧女豪杰》在中国的政治回响,那些创作者没有《东欧女豪杰》所蕴含的政治理想,只能根据自己的体验进行政治想象、抨击社会弊端。于是,他们抓住了最吸引人的苏菲亚,使得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不断书写女革命党人和女刺客。为了表现革命行动的合理性和纪律性,当时的小说家还为这些革命或造反的女性建党立帮。在《东欧女豪杰》影响下产生的这一大批作品,也就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创造了一个新的文类——会党小说。
陈冷在中国会党小说由政治话语向江湖话语转型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译介了很多有关俄罗斯民意党人的文学作品,但没有对该党的政治主张做更多的研究和阐释,只是赞扬其激进主义的态度和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其实并不真正熟悉政党的运作机制,只能在想象中将党派的社会意识和组织结构放置于匪窟里。由此,“党”和“会”在小说中结合了起来,会党小说的江湖话语也随之诞生。陈冷是当时知名报刊的主编,影响力较大。他的会党小说实际上为中国会党小说设定了三个主要元素:政治性、神秘感、江湖化。
姚民哀和郑证因的作品可以视为陈冷小说的延续。姚民哀以说书人的身份开始小说创作,善于四处打探江湖秘闻。他将有关政党的信息理解为江湖秘闻,因此其小说有更多的江湖气,党派与帮派甚至没有什么差别。郑证因则是位武侠小说家,与政党相比,他更了解天津混混。党派意识在他的小说中极为淡薄,只剩下社会主张和严密的组织架构的躯壳。再加上他们在创作中刻意突出这些组织的神秘性,其笔下的党派就只能与黑帮同调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姚民哀和郑证因追求的理想读者与陈冷不一样,他们总是尝试取悦读者,过多地强调书写传奇故事。至于那些具有党派意识的党章、党规,在小说中则处在较为次要的位置。而女性主义会党小说的作者和陈冷将小说当作启蒙民众的教科书,更倾向于在作品中抨击社会弊病和规划未来蓝图,传奇只是吸引读者的手段。虽然写法比较生硬,但他们的小说还是“党”大于“会”。而姚民哀和郑证因的小说则是“会”大于“党”,甚至只有“会”,没有“党”。最终,这一文体的消解也就在所难免了。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现代通俗会党小说在发展过程中江湖气越来越重?中国美学传统的影响和阅读市场的需求或许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美国通俗文学理论家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他认为“生产者式文本”“自身就已经包含了与它的偏好相悖的声音,尽管它试图压抑它们;它具有松散的、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它包含的意义超出了它的规训力量,它内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㉛。而会党小说恰恰就是在这种不断地填补文本裂隙和创造裂隙的过程中产生出的新的文类。
《东欧女豪杰》就是一部典型的“生产者式文本”,译介者在“生产”这部作品时就留下了很大的裂隙,为中国现代通俗会党小说的产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19世纪的俄罗斯民意党是无政府主义政党,苏菲亚是创党成员。该党成员大多是贵族,提倡到民间去,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他们因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震惊世界,也受到严厉的镇压,其悲壮的献身精神让世人动容。然而问题是,这样的政党行为被纳入章回体小说《东欧女豪杰》中,必然会染上中国式的章回小说的色彩。传奇性和曲折性是中国章回小说的美学特征。为了吸引读者,章回小说大多会以一个悬疑的事件开篇,然后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揭开谜团。《东欧女豪杰》也是如此,目前能看到的五回仅设置了一个悬念,即苏菲亚的失踪和入狱。而俄罗斯民意党的政治纲领和革命理想并没有在小说中得到表现。对中国当时的革命党人来说,他们可以根据文本追根寻源,在阅读《东欧女豪杰》之后,了解并宣传俄罗斯民意党的政治理念,但对很多传统作家来说,这部小说则只是一部来自外国的侠义传奇故事。事实上,从女性主义会党小说开始,中国现代通俗会党小说虽然打着《东欧女豪杰》等虚无党小说的名号,其实质还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传统侠义小说。从这个意义上,称会党小说为中国传统侠义小说的变体,也未尝不可。
为什么中国通俗会党小说最终会演变为侠义小说,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中国阅读市场的需求。自梁启超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学创作不再是伤春悲秋或考取功名的途径,而是具有了很强的社会性。无论是宣传启蒙还是追求市场,读者的接受都是文学创作的目的和动力。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游民文化的社会基础。民国初年,杜亚泉就对中国游民文化有过深刻地剖析,认为中国过剩的智识阶级和劳动阶级会产生游民文化,“即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㉜。游民身上具有革命色彩,往往以反抗的姿态出现,崇尚道义,在中国民间具有很高的魅力。游民文化在中国极为强大,反抗者常常以此进行社会革命,“秦始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㉝。张恨水在论述武侠小说为什么在中国流行时,曾这样分析:“为什么下层阶级被武侠小说所抓住了呢?这是人人所周知的事。他们无冤可伸,无愤可平,就托诸这幻想的武侠人物,来解除脑中的苦闷。”㉞由于特有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结构,中国社会普通市民的公共意识发展得很不充分,与政党政治离得比较远,在晚清民国的社会背景下,读者在阅读会党小说时,会不自觉地将其中的政党理解为帮会。再加上农耕社会“均贫富”的要求在普通民众中很受欢迎,侠客式的反抗总会收获一片喝彩,也使得会党小说更愿意将政党行动描写为行侠仗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现代通俗会党小说的演化趋势,必然是“党”的色彩越来越减弱,“会”的气息则越来越浓厚。
①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920页。
② 有很多学者对《东欧女豪杰》作者进行了考证,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是于必昌的《〈东欧女豪杰〉作者考》(《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
③ 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④⑧ 岭南羽衣女士著,谈虎客批:《东欧女豪杰》第2回,《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⑤ 无首(廖仲恺):《苏菲亚传》,《民报》第15号,1907年7月5日。
⑥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页。
⑦ 岭南羽衣女士著,谈虎客批:《东欧女豪杰》第1回,《新小说》第1号。
⑨ 晚清革命志士宁调元作《吊秋竞雄女侠十首》凭吊秋瑾,其诗之十:“舍身革命苏菲亚,奇气吞胡花木兰。巾帼有君能雪耻,神州愧死百千男。”(杨天石、曾景忠编:《宁调元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
⑩ 阿英:《中译高尔基作品编目前言》,《阿英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56页。
⑪⑫ 阿英:《翻译史话》,《阿英全集》第5卷,第789页,第789页。
⑬ 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⑭ 根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目录》、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等资料的统计,此时“女性小说”大致有五十多部。剔除《最近女界现形记》等写女界阴暗面的小说,那些女性主义的小说至少有二十多部。
⑮⑯ 王妙如:《女狱花》,《女子权·侠义佳人·女狱花(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32页,第740页。
⑰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⑱ 海上独啸子:《女娲石》,东亚编辑局1904年版,第2页。
⑲ 冷血:《序》,《虚无党》,冷血译,开明书店1904年版,第1页。
⑳㉑ 冷血:《刀余生传》,《新新小说》第1号,1904年8月。
㉒ 《山东响马传》广告,《新闻报》1924年6月27日。
㉓ 赵苕狂:《四海群龙记·序》,《红玫瑰》第4卷第36期,1929年1月。
㉔ 姚民哀:《四海群龙记》第4回,《红玫瑰》第5卷第1期,1929年3月。
㉕ 姚民哀:《箬帽山王》第36回,《红玫瑰》第6卷第36期,1931年2月。
㉖ 姚民哀:《盐枭残杀记》,《红玫瑰》第5卷第30期,1929年10月。
㉗ 姚民哀:《箬帽山王》第1回,《红玫瑰》第6卷第1期,1930年3月。
㉘ 姚民哀:《四海群龙记》第10回,《红玫瑰》第5卷第8期,1929年5月。
㉙ 郑证因:《鹰爪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
㉚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成、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㉛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㉜㉝ 伧父(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东方杂志》第16卷第4号,1919年4月。
㉞ 张恨水:《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张恨水散文》第3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