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体育文化的比较研究
——以高句丽与敦煌壁画中的角抵、射猎为例
海梦楠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武汉 430074)
高句丽古墓群和敦煌莫高窟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高句丽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古代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将我国中原文化和西域及域外文化相连接,是古代经济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通道。虽然两地地理位置相距上千公里,亦不属于同类型文化。但体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通过体育活动来研究两地体育文化交流情况,对于深化跨区域体育文化研究,牢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积极作用。
当前关于两地体育、历史、文化的独立研究成果丰硕。杨春吉、耿铁华的《高句丽史籍汇要》[1]将高句丽时期,中原政权对高句丽的记载逐一汇总摘录,便于后人进行历史研究;魏存成在《高句丽考古》[2]里对高句丽的历次考古进程及结果进行了总结归纳,并对相关遗迹、遗址、遗物进行调查研究。对东北地区高句丽体育进行专项研究的成果不是太多,主要有胡承志、杨传彬、于果挥《高句丽体育项目实证考察分析》[3],第一次全面介绍了高句丽遗址及其文物资料中有关古代体育的资料;宋伟《古墓壁画中的高句丽体育文化研究》[4],对高句丽体育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初步研究;隋东旭在《高句丽体育文化研究》[5]中通过对文献和文物的史料分析,解剖了在高句丽流传的体育活动。敦煌学及其敦煌体育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多,陈康在《敦煌体育研究》[6]中对敦煌莫高窟壁画、雕塑及敦煌文献和其周边体育遗物进行考察分析;刘进宝在《敦煌学通论》[7]对敦煌学的诞生,以及它的兴起、形成和发展过程作了全面叙述,吸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敦煌学的研究作了全面论述;李重申、李金梅在《论敦煌古代的游戏、竞技与娱乐》[8]里论述了古代敦煌地区的游戏、竞技和娱乐之间的关系及开展情况等。在CNKI上以“敦煌”“高句丽”“比较研究”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相关研究论文共10篇。其中只有1篇博士论文《高句丽古墓壁画与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比较研究》[9]对高句丽和敦煌的壁画进行了对比研究,但其研究方向为佛教对两地壁画风格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两地的独立研究成果丰富,然而对于两地的跨区域文化研究还属于薄弱领域,特别是两地的体育文化比较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领域。所以本文通过对高句丽古墓壁画和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角抵和射猎运动进行跨区域对比研究,试探究我国古代体育的交流传播情况。
一、壁画中的角抵运动
本文选取角抵运动产生的先秦时期到高句丽灭国的初唐这个时间段,来了解角抵运动的产生、发展历程。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我们发现,角抵产生之初,是作为周王朝“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即“讲武之礼”[10]。同时,《礼记.月令第六》“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11],表明角抵也是周朝选取军士的标准之一。到了两汉时期,社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角抵也随之发展成为一种带有表演特征的娱乐活动,《汉书》记载“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12]。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同政权为了巩固自身的军事需求,百姓也有自保的需求。所以,角抵的军事竞技特性再次凸显,《隋书》“齐文宣受禅之后,又有持钑队、铤槊队、长刀队、细仗队,楯铩队……角抵队”[13]。北齐政权将角抵与其他军事战斗部队并列,反映了角抵的军事特征受统治者重视。及至隋唐,角抵由于社会稳定,民众富强,所以再次成为一种娱乐性的表演活动。《旧唐书》记载“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日昃而罢”[14]。
然而上述文献关于角抵的记载,多为叙述性描写,而缺少对角抵运动的细节性描述,这使得我们对角抵的认识始终不够清晰。而在我国集安地区的高句丽壁画古墓群和敦煌地区的莫高窟壁画群,绘有角抵运动的壁画就包括禹山墓区的角抵墓、舞踊墓、敦煌文书P.2002v等等,这些壁画中对于角抵的具体运动姿态以及服饰衣着有着清晰的描绘。这对于我们认识两地的角抵运动有着重要意义。
(一)相互搏击状态的角抵运动

图1 角抵墓角抵图
角抵墓建于约公元四世纪中叶,因墓室东壁壁画上有角抵图(图1)而得名。画中两个力士相互缠抱在一起,双臂缠绕在对方上身,双腿微曲,重心沉在两腿之间;两位力士身着白色犊鼻裤,头系“顶髻”[15],一位力士东亚人面孔,蓄八字胡,鼻子扁平,另一位力士可能是异域人士,蓄短髭,眼窝深陷,鼻子挺拔而鼻尖弯曲。运动姿态上,两位力士互相扭抱在一起,双手抓住对方的短裤作为发力点,双腿呈前后站位,膝盖微曲。画面右侧,站立一位老者,其面容随壁画脱落无法辨认,但下巴依稀可见白色山羊胡须,手持鸠杖,衣着为平民扮相,衣褐色襦裤。宋伟在《古墓壁画中的高句丽体育文化研究》中认为:老者应为角抵运动的裁判。关于老者的身份,本文认为老者仅是角抵运动的观赏者,而非裁判。《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年始七十者,授之玉杖……玉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16]。自汉以后,中原政权历朝历代都有赠70岁以上老者鸠杖的传统,结合壁画老者平民扮相、手持鸠仗以及出土文物和文献史料,角抵运动均未有“持器”的裁判扮相,所以本文推测老者为角抵运动的观赏者。

图2 敦煌文书P.2002v
作为对比,本文选取敦煌文书P.2002v画卷(图2),该画卷成稿于公元十世纪,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可以发现,敦煌画卷中的两位力士全身赤裸,仅着犊鼻裤,其中右边选手似乎为进攻者,弯腰俯身直扑对方重心处,一手抓住对方大腿,想要对手失去重心摔倒,而另一人降低身体重心,保持身体平衡,双手反抱住对手的腰部,两人互推互搏呈胶着状态。
通过对比两地壁画角抵运动的壁画,我们发现,高句丽古墓壁画中这幅角抵图与敦煌文书P.2002v画卷均是描绘了角抵运动的相互搏击状态。衣着服饰上,两地壁画的力士赤身裸体仅穿犊鼻裤,不穿鞋袜;运动姿态则是双臂缠绕对方,或是搂抱脖颈或是捉拿腰腿,通过上肢的力量收放变化与脚下的脚步腾挪,来实现摔倒对手获取胜利。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体育专著—宋代的《角力记》,有首描述角抵相互搏击状态的诗作,“愚汉勾却白汉项,白人捉却愚人骰。如人莫辨输赢者,直待墙隤始一交”[17]。该诗首句说明皮肤黝黑的汉子抱住了肤色白俊汉子的脖子,次句讲述了肤色白俊汉子捉住了黑皮肤汉子的大腿。这两句诗作的描述,和两地壁画所绘角抵的姿态,几乎一模一样。而唐代《角抵赋》中对于角抵的具体姿态也有描述,“前冲后敌,无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拿,尽是用拳之手”[18]。由于两地壁画画面描绘的内容,与《角力记》和《角抵赋》关于角抵的细节描述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相互近身搏击状态的角抵运动,在高句丽和敦煌两地是基本一致的。
(二)“纠发拍张”状态的角抵运动

图3 舞踊墓角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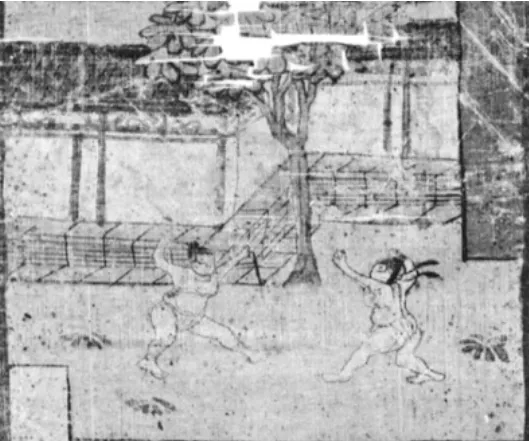
图4 敦煌莫高窟第17窟经幡画
舞踊墓建于约公元四世纪中叶,该角抵图(图3)位于舞踊墓藻井北面第一层叠涩中间。衣着服饰上,两位力士仅穿白色犊鼻裤,蓄八字胡,发式为顶髻;竞技姿态上,二人并未扭抱在一起,而是保持一定距离,左边力士一手伸向前,一手靠近身体,一腿呈半弓字步,一腿伸直,右边的力士侧身,动作与左边力士近似。由于该角抵图位于墓室藻井之中,而墓室所绘一般是墓主人死后的幻想世界,且舞踊墓的藻井内描绘的图像多为进行娱乐表演的仙人以及其他瑞兽莲花。故本文推测,四世纪中叶,高句丽人已经将角抵视作一种不可或缺的娱乐竞技活动,甚至墓主人去世也不愿意放弃观赏角抵活动。
作为对比,本文选取了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经幡画(图4),该画作于唐代,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衣着服饰上,两位力士袒露上身,只穿着犊鼻裤,头戴幞头;竞技姿态上,力士双臂高举,露出自己的胸膛或者破绽,双腿微曲呈半弓字步,降低重心,似乎做好了随时进攻的准备双膝微弯呈半弓步,伺机向对方相扑而去。
通过将高句丽古墓群的舞踊墓角抵图与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经幡画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服饰上,力士只穿传统的犊鼻裤,并不穿其他衣服,唯一区别在于高句丽不戴幞头,而是系顶髻,而中原文化的唐朝角抵,则是戴着幞头;在竞技动作上,两者都是在描绘角抵运动尚未发生身体接触的“纠发拍张”,即力士双臂高举或张开,露出自己的胸膛或者破绽,双腿微曲呈半弓字步,降低重心,又似乎做好了随时进攻的准备。而关于“纠发拍张”的竞技姿态,《角力记》也有记载“宋王敬则,帝令公卿自呈本技所长,敬则红帛纠发拍张……拍张亦角力也”。王敬则用红线系紧发髻,赤裸上半身,振臂拍张,而拍张就是角力。所以高句丽和敦煌两地“纠发拍张”状态的角抵运动几近相同,我们认为,两地角抵运动应属于同一源头。
二、壁画中的射猎运动
射猎运动在人类文明诞生的早期,作为一种食物获取方式而存在。高句丽位于我国东北,其境内长白山余脉穿过,山地众多,森林茂盛,耕地农田不足。这样的地理条件,为他们提供了猎场与制作穹庐、弓矢的木材[19]。同样也使得高句丽人将射猎作为获取食物来源的一种重要途径。而汉代闻名的良弓—“貊弓”,亦是高句丽的特产。所以,作为半耕半猎民族的高句丽善射,既有地理因素,也有传统的习俗原因。
(一)高句丽独特的射猎工具

图5 舞俑墓射猎图

图6 横山罗圪台村元墓射猎图
该壁画(图5)绘于墓室北壁梁枋下,从该壁画中我们可以发现,猎手的箭镞并非寻常的三棱箭镞或四棱箭镞,而是一种短小的管状装置。因为管状装置上有挖空的小孔,在箭射出的过程中,空气通过小孔发出呼啸声响,所以人们将其称之为鸣镝,或是响箭。鸣镝一词最早出现在“鸣镝弑父”的典故中,《汉书·匈奴传》“冒顿乃做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20],最终冒顿通过鸣镝指挥匈奴人射杀了头曼单于,成为匈奴的新单于。
虽然目前没有文献可以直接论证高句丽的鸣镝射猎,但是借助其他时期的相关史实,我们可以尽力还原高句丽的鸣镝射猎活动。在陕西横山罗圪台村的一座元墓内中绘有元代的射猎图(图6),这幅射猎图显示了元代的射猎场景。画中的猎手纵马弯弓,已经箭矢已经瞄准了一头回首四顾的野鹿。而猎手所持的弓矢,应该是鸣镝,其形制与高句丽舞踊墓壁画的鸣镝一致,均是在箭杆顶端置有管状装置,而非三棱锥或四棱锥的箭针族。
关于射猎过程里鸣镝的具体用途,元帝窝阔台的中书令耶律楚材曾写《狼山宥猎》赞美窝阔台巡守“吾皇巡守行周礼,长围一合三千里。白羽飞空金鸣镝,狡兔玄狐应弦死[21]”。这首诗,特别体现了鸣镝在射猎活动中的作用,即主要用来射杀小型动物这一史实。众所周知,捕获的猎物体型越大,猎手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越多,所以武八能“暮乃多之”,一定是捕获了不少小型动物。那么,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鸣镝在射猎过程中,主要是以猎杀小型动物;而高句丽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学习了匈奴鸣镝射猎的习俗。
(二)军事训练和射猎活动的结合
早在西周时期,射猎就是我国中原政权的一种军事训练手段,并将其列入“礼”的范围,维护统治。《周礼.大司马》中记载“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遂以狝田,如蒐之法。罗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阅。前期,群吏戒众庶脩战法……遂以狩田”[22]。这就是“大蒐礼”,即周朝时期的军事训练,通过大司马来指导军士演练军阵和战法,以山野作为战场,以猛兽作为假想敌,从而熟悉军事并围捕猎物,为祭祀提供祀品。而在周朝设置关于射猎的官职,就多达29种[23]。这既反映了周礼的等级森严,也反映了射猎在古代中原文化的重要性。
高句丽在西汉初期,还是汉王朝玄菟郡的一部分。然而到了隋朝,炀帝率领兵强马壮的隋军三征高句丽,均以失败告终,这一战果甚至间接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由此可见高句丽的军事实力强劲。而强大的军事实力除了与经济繁荣程度有关,还与自身的备战水平有关。与中原通过射猎来进行训练军事类似,高句丽也是通过成规模的野外射猎来模拟军事操练,从而提高自身的作战能力,这点在高句丽古墓壁画群里可窥一二。

图7 长川1号墓射猎图(线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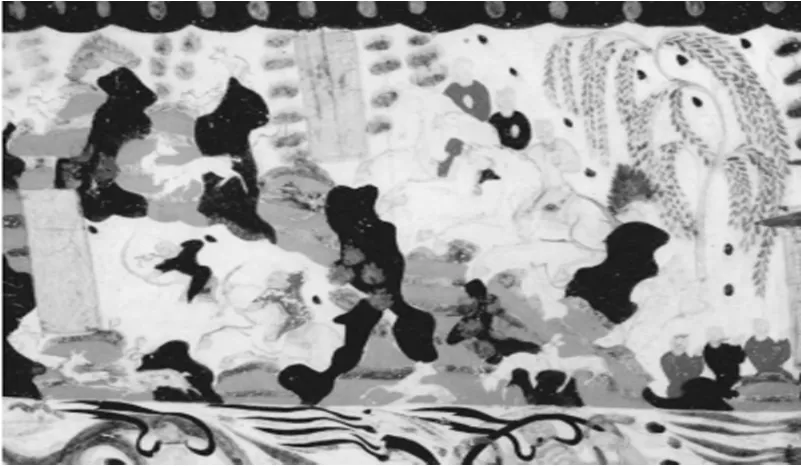
图8 射猎图
长川1号古墓的射猎图(图7)基本还原了公元6世纪高句丽大规模射猎的场景。画中勾勒出高句丽的地理自然环境“多大山深谷”,画中清晰地显示了当时射猎的团体战术,即壁画左侧和右侧的两队人马,对兽群实施了“左右夹击”,把兽群驱赶集中到图画中间,实施包夹合围,最终捕获猎物。可以看到,图画中不管是鹿群还是老虎都仓皇逃窜,而猎者纵马弯弓,瞄准了一只只猎物,并最终实现合围捕获。高句丽这样的射猎战术配合,在与敌人进行军事作战时,本文相信也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射猎图(图8)出自敦煌莫高窟第301窟,成画于北周时期,现存于敦煌莫高窟,描绘了当时大规模射猎的场景。在一片树林里,射猎者们排出几排整齐的队伍,第一排的猎者骑马搭箭,追逐着四散的猎物,第二排的猎者则携带猎犬,跟在后面,伺机进攻。这样有阵型,有层次的规模射猎,不仅仅体现了其指挥者高超的战术制定能力,也体现了猎者的基本战术素养。可以推测,类似的射猎行为,在当时已经较为常见,因为次数较少的训练配合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而这样的射猎活动,只需要把假想敌由野兽换作敌人,就是一套合格可操作的军事作战配合。
高句丽和敦煌这两幅壁画成画时间大致相同,均描绘了当时射猎的规模化场景。两地虽然相距上千公里,然而射猎所呈现的场面基本一致;虽然画面中勾勒的猎手数量不是很多,但实际狩猎过程中,不管是围捕鹿群还是猎杀猛虎,都一定是多人参与的集团射猎。因为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猎杀猛兽或是动物群体,人类依然属于较为弱势的一方,需要团体配合以及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
事实上,不论在高句丽古墓壁画群中,还是在敦煌莫高窟壁画群里,这种射猎运动的描绘,还有很多。如药水里古墓壁画射猎图、德兴里古墓藻井射猎图、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射猎图、第419窟射猎图等等。这些壁画的发现,说明了不论在西北的敦煌中原文化,还是位于东北的高句丽少数民族文化,对射猎运动都极其重视。而射猎运动盛行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射猎运动可作为军事训练的一种手段,甚至说这就是一种古代的“军事演习”也不为过。实际上,这与中原文化的“大蒐礼”一脉相承,都是通过规模化的田野射猎活动,来提高单兵的作战能力、配合能力,同时提高了指挥者的战术制定能力。耿铁华教授也指出“这就是一种作战训练和演戏,步兵、骑兵两个兵种的后备部队真刀真枪地在山林里作战,只不过对象是山林的野兽罢了”[24]。
三、小结
关于高句丽地区和敦煌地区的文化交流,目前尚未有文字性的史实资料可以佐证。但是图画性的证据,已经在敦煌莫高窟有了发现。
庄妮在《莫高窟第158窟国王举哀图中少数民族冠、帽的研究》中认为,335窟里“冠上插二羽尖状装饰,有带系于颌下,样式与乾陵《客使图》高丽使者画像如出一辙”[25]。而《北史.高句丽传》中记载高句丽人的服饰“人皆头着折风,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鸟羽[26]”。高句丽人的形象能够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敦煌壁画中,唯一的解释就是高句丽人曾前往至敦煌,所以被画师绘于壁画之上。在两地人员往来的过程里,敦煌的中原文化与东北的高句丽文化也一定进行了交流,这种交流可能就包括体育领域的交流。因此,我们可以说,高句丽体育文化是来源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这棵大树,同时与中原体育文化有着借鉴吸收的关系,是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高句丽壁画与敦煌壁画中角抵运动和射猎运动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高句丽地区和敦煌地区的角抵运动,以及以军事训练为目的的射猎运动,均来源于同一体育文化源头,这一源头很可能就是早期的中原传统文化,角抵运动是周朝“礼乐”体系的一部分,军事训练为目的的射猎运动则可能是周朝“大蒐礼”的演化。(2)角抵和射猎运动产生的初期,都被视作军事训练的手段,是我国古代政权巩固国防、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手段。(3)将敦煌为代表的中原角抵与高句丽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角抵相比较,二者并未产生显著区别,其本质依然是一种徒手搏击运动,不论是相互搏击状态还是“纠发拍张”状态,两地角抵的竞技方式和特点未产生明显不同,唯一的适应性变化是角抵手的头饰,由中原的幞头变为高句丽特有的顶髻,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高句丽的角抵运动很可能是中原体育文化传播到高句丽的结果。(4)将敦煌为代表的中原射猎运动与高句丽少数民族射猎相比较,二者均是通过射猎运动提高军队作战能力、演练军阵,二者的核心目标一致;但高句丽使用鸣镝作为射猎工具,该特征和游牧民族匈奴类似,而与农耕文明的中原射猎文化显然不同,这也说明了高句丽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其自身的民族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