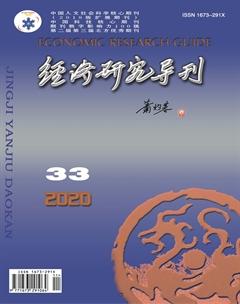“经营共同体”的形成机理、现实价值与启示
艾比江·巴吾东 马跃月
摘 要:借鉴日本学者的文献资料,从“经营共同体”的概念,形成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具体措施,资本主义经营与“经营共同体”及其经营学意义五个方面阐述藻利重隆的“经营共同体”思想,分析“经营共同体”的形成机理,提出可参考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经营共同体”;资本主义经营;二重构造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33-0008-04
德国现代社会学缔造者Fernand Tonnes提出“共同体”(Gemeinschaft)概念一百多年以来,其内容与形式在不断丰富与完善。“当前,‘共同体概念中已经融入了权力组织、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元素,它已不再是传统的单纯的地域性或情感性概念,而被赋予了更多功能性的内涵,从而使共同体理论与应用都得到了极大丰富。”[1]“‘Gemeinschaft在德文中的原意是共同生活,滕尼斯用它来表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这种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产生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2]“尽管在文献中‘共同体一词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不同的界定,但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含有‘归属意味。即除非成员都体验到一种归属感、对他人的信赖和安全感,否则共同体不会出现。”[3]共同体虽然是社会理论的概念之一,但是其内容、形式在不断扩展,“从虚拟共同体到全球共同体,形形色色新兴的所谓‘共同体大量涌现。”[4]如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学习共同体、职业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等。“共同体的内涵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不断演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维度中,不同学科对共同体的研究各有侧重,共同体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其主体、形态、范围和特征也会有很大的不同。”[5]“企业成为共同体是社会和谐劳动关系的要求。”[6]
纵观企业的发展历史,人—机协调互动始终是近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形成的主轴。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界在吸收美国管理技术及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日本式管理”“日本经营模式”并得到了管理界广泛的关注。“所谓日本经营模式,并非一套画定的观念或实践,而是一系列日本企业在长久经营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习惯性做法及其背后包含的原则。”[7]日本学者提出的“经营共同体”的思想,为日本经营模式提供着理论支撑。本文参考日本学者村田和彦教授的论著《生产合理化之经营学》,对藻利重隆“经营共同体”的思想进行诠释,分析“经营共同体”的具体内容、形成机理,明确“经营共同体”的现实价值。
一、“经营共同体”的概念
企业的劳务管理,区分为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或提高劳动者效率为目的的“人事管理”和以提高劳动力或劳动者欲望为目的的“狭义劳务管理”两类;藻利重隆以“狭义劳务管理”为课题,在探寻“经营共同体”(Betriebsgemeinschaft)的同时,分析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为构筑“经营共同体”企业采取的措施[8]。
藻利重隆从经营中生产手段的所有关系、经营中意志形成的主体、经营中劳动的特性、经营构成人员的意识及经营构成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五个方面分析并归纳了“经营共同体”的概念。
从生产手段的所有关系和劳动特性分析,经营共同体是“以协作劳动的劳动者作为整体、集体性拥有生产手段,进行集体性的自由作业”。从经营中意志形成的主体分析,经营共同体是“一方面,伴随着生产过程,即以机械化原理为指导,进一步将劳动者作为机械化对象时生产功能发挥的过程本身,全面对象化、客体化时主体的形成;另一方面,整体性赋予协作中的全体劳动者自身主体地位”的经营活动。从人员的意识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着眼点,则经营共同体是一种将经营作为“自身事物”的职场自我意识,或者在劳动者中培育整体性的“生产手段自我所有意识”,因此,是在劳动者之间形成经营者视觉(Managerial Vision)、经营者观点(Managerial Viewpoint)或经营者态度(Managerial Attitude)的经营活动;同时,是“劳动者作为一体化的经营者”,对于所属的经营具有“共同的荣誉感”,期待归属于这种经营的“人们之间能够紧密结合”,进而在经营活动中从事劳动的所有成员,克服相互间的分割,形成“统一的经营社会的构造”。
按照上述观点,经营共同体是经营活动中全体构成人员,整体性地拥有生产手段,作为经营决策主体实质性地开展自由作业,因此将经营视为“自身事物”的自我意识并具有“共同的荣誉感”,以此为结果,将经营活动中的成员进行一体化的经营活动。
二、“经营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藻利从下列一系列的事项中阐述“经营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性[8]。
1.随着“经营性生产”的高度机械化,必然产生劳动者人性的异化,使劳动者的劳动欲望减退,引发机械化效能的重大阻碍。换言之,为谋求经营性生产的效率,企业必须致力于实现经营性生产的机械化,但是,对于“为提高效率实施的机械化,相反会招致阻碍提高效率的现象”。在关注这种现象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经营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性。
按照藻利的解释,“经营性生产”是“通过协作性生产增加社会必需物品,即商品的持续性生产方式”。“经营性生产的机械化”包括“狭义机械化”和“组织化”。其中,“狭义机械化”包含:一是将经营性生产中使用的工具向机械转换;二是将使用工具的人的作业活动从生产过程中排除;三是将残存的人的作业活动机械化,从主观的手工技艺或技能向顺应机械运动规则的客观技艺的作业转变;这些狭义的机械化,形成生产手段及人的作业活动的“个别机械化”。与此对应,“组织化”则意味着作业手段及人的作业活动的“机械化组织”;所谓作业手段的“机械化组织”是指将各机械通过编程形成“机械体系”,“人的作业活动‘机械化组织”是将协作中的劳务关系向作业活动本身不具有内在约束的机械关系转变,形成能够取代作业自身内部约束的“经营性外部秩序”;更具体地说,它是通过“职位”的合理设定对“经营系统”的编程,对拥有“职位”的人的活动方式,通过制定“经营规章”“经营制度”严格确保垂直及水平“经营秩序”。
藻利认为,作业手段机械化的兴起,随即推进了人的作业活动的机械化进程,通过“个别机械化”与“机械化组织”相互促进的媒介作用,直至系统性地达成经营性生产自身的自动化过程。
2.随着经营性生产的高度机械化,必然产生劳动者人性异化的现象,就此藻利从四个方面做了阐述。第一,从所有物中异化人性,即作业手段从工具向机械的转换,伴随机械在生产中发挥着中心作用。一方面,机械已不可能是服从劳动者各自需求的所有物;另一方面,与使用工具情境不同,从劳动者分离的机械,劳动者理解为是其自身的延伸,在此不能发现自身灵魂的现象。第二,从作业活动中异化人性,即:伴随作业手段的机械化,劳动者的作业活动只是专门顺应机械及机械体系的运转规则,要求劳动者在由极其单调连续的、反复的、高度特殊化构成的部分作业中从事生产作业活动,劳动者已经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各作业间的关联性,劳动者在从事的各自作业过程中,已经不能发现自我的现象;以上两种现象,按照藻利所说,产生劳动者人性异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经营性生产的机械化。第三,从职场中异化人性,不仅从作业手段及作业活动本身异化人性,而且,在职场中从事劳动的人,丧失自我目的性,职场不是“生活的场所”或“生活的空间”,而是赚钱的场所,职场被劳动者理解为“目的空间”。第四,从劳动者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异化人性,伴随从职场中异化人性,劳动者为获得工资收入集合在一定的职场中,在此寻求人们之间跨越相互算计的友好结合关系已经变得很困难;由于层级组织及职能规定的原因,人们之间的协作关系只能依靠外部的强制来维持。
藻利认为,对于劳动者的人性异化,须从作业手段机械化必然引起“经营性生产的机械化”这一现象来把握;不仅如此,他还指出,这种现象的端绪能够从“经营性生产”本质属性之一的“协同生产”来理解;劳动者的人性异化,虽然将生产中的人理解为“被生产利用的客体”来解读,但是这种现象在机械化生产之前的简单协作劳动中早已初现端倪,即:“参加劳动的人们,各自围绕着简单协作劳动,不允许自主行动”,“即便存在程度上的差别,无论如何只服从确定了的秩序,作为协作生产的绝对要求,强加于参与其中的人们。”换言之,“人只作为生产力,或者生产要素,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对象,不是主体,而是作为客体对待。”
企业不能对劳动者人性的异化置之不理。“生产过程中,在促进机械化的发展、强化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尽可能确立劳动者‘人的本性是提高勤勉劳动欲望的可能之路”,该问题也正是藻利解答的“经营共同体”形成之路。
企业究竟能否步入形成“经营共同体”之路?藻利认为,能够从产业革命确立的近代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二重构造”得到解答。“二重构造”是指生产力构造与劳动力的所有者构造;前者是以物力为媒介的劳动力的协动组织,是向与机能性构造相关联的机械化进程迈进的构造,藻利将该构造称之为“经营的技术构造”或者“生产的技术构造”;后者是指劳动力所有者的人的结合关系,作为非机能性的构造关联,是与机械化大体没有关系而存在的,藻利将其称之为“经营的社会构造”或者“生产的社会构造”。他认为,在存在经营的社会构造中能够发现企业经营共同体形成的可能性;换言之,经营的社会构造具有将经营的技术构造对象化、客体化并向主体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对于合理形成经营技术构造指导原理的“机械化”而言,合理形成经营社会构造的指导原理正是“主体化”“人性化”,更具体地说,必须从“共同体化”来解释。
藻利指出,“‘经营的社会构造促进‘经营的技术构造的形成,成为实现效率化的必然前提”;由于伴随“共同体化”,才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欲望,才能使机械化效能的提高得以实现。因此,通过经营的社会构造共同体化的媒介作用,使得经营的技术构造实现机械化成为可能。对于经营的社会构造共同体化而言,为其提供物质基础的,正是经营的技术构造,“以促进机械化为媒介,才能够使共同体化或者人性化成为现实。”
藻利指出,必须关注伴随经营的技术构造机械化与经营的社会构造共同体化两者之间互为媒介、相互促进,才使经营得以发展这一事实,它是“在近代经营的现实构造中呈现的伦理要求”,在这种“经营本身的伦理要求”中,来探寻经营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三、“经营共同体”形成的具体措施
藻利从劳动者生活的稳定或者保障及劳动者参与经营两方面阐述了经营共同体的具体措施[8]。前者是针对伴随机械化,从“可能的恶”的生产过程中排除或解雇劳动者的一种对策,是致力于在劳动者中培育作为经营人或经营内市民“共同荣誉感”形成基础的一种措施;对于生活不安产生恐惧的劳动者而言,不能够期待“共同荣誉感”形成。对于该项措施,藻利进一步细分为两项内容:其一是以雇佣中的劳动者生活安定為意图的措施,其二是以退休后的劳动者生活安定为意图的措施。以雇佣中的劳动者生活的安定为意图的措施,包含三项具体对策,一是稳定的雇佣或有保障的雇佣对策,二是由工资、劳动时间构成的劳动条件公平化措施,三是设置卫生、福利设施等。
后者是针对伴随机械化作为“必然的恶”产生劳动者人性异化的对策,是将约束劳动间接转换为自由劳动。“劳动者参与经营”是指直接或者间接促使劳动工会参与经营;就劳动工会参与经营,需要关注三点事项:一是劳动工会参与经营的方法问题,二是劳动工会参与的对象问题,三是劳动工会参与的程度问题。这三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参与的对象规定参与的程度,引起制约参与构造的也正在于此。
四、资本主义经营与“经营共同体”
从“经营性生产”具有机械式协同生产的属性中,能够解读企业经营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性;从“经营性生产”具有二重属性中,能够解读企业经营共同体形成的可能性。据此可以认为,无论怎样的经济体制,均存在经营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8]。
在资本主义企业体制特征下,对于经营共同体的形成,我们从下述两方面对藻利的观点进行分析,第一,调整“机械化”与“共同体化”的所谓不同要求或者综合性原理的观点,第二,企业经营共同体形成的范围(或译为“界限”)的观点。针对所谓“机械化”与“共同体化”不同性质的要求,能够从调整或者综合这些要求的方法上存在的差异中解读出经济体制上的不同点,即在现今资本主义企业问题的场合下,“机械化”与“共同体化”的要求,正是通过在对利润性原理的调整或者综合中发现企业致力于形成经营共同体的体制特征。对于第二点,是在企业致力于形成经营共同体过程中,须从其目的和手段两方面刻画其范围的观点。就目的的由来而言,藻利做了如下的解释,“劳务管理是企业或经营中以劳动者为对象的对策,无论人事管理还是狭义的劳务管理(以经营的社会构造共同体化为课题)均是企业或经营的客观必要的根基……”对于企业为形成经营共同体采用的手段的来源范围而言,在最核心的措施“劳动者参与经营”本身中,藻利指出:“对于被客体化的经营者以劳动者形式存在而言,劳务管理的意图无外乎正是以间接的方法、通过主体化使经营者转化为主导地位。对于作为劳动者的经营者,完全主导意味着劳动工会成为站在雇主一边的工会。”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工会是针对经营者作为客体形式实质性地存在时,劳动者参与经营才能够成为一种手段,藻利认为“劳动者参与经营”是企业致力于形成经营共同体的界限之一。
对于保障劳动者生活安定的措施,在企业自身不存在使其成为可能的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企业培育劳动者“共同荣誉感”的基础就会欠缺,自然就会限定经营共同体的形成。
五、藻利“经营共同体”思想的经营学意义
在藻利的经营共同体观点中,一方面,能够从企业的历史存在或体制关联中内嵌着的“经营性生产”这一超历史属性或体制无关联属性中解释经营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从事经营的“企业”致力于经营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体制特质,作为赋予体制性界限的要因,正是通过企业的历史存在或与体制关联存在的事实中把握其要因的由来。
藻利的经营共同体思想的经营学意义[8],首先,以资本主义社会从事经营的企业内嵌着的经营性生产来源本身为着眼点,在解明其内容的过程中加以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从事经营的企业,如果现实中存在体制关联的事实与体制无关联的事实相融合的话,则企业完全无视引起这种体制无关联事实的必要条件是不被允许的;在藻利的经营共同体思想中,论证企业经营共同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不只是专门从超体制或体制无关联的“经营性生产”中探寻其内在的必要条件,相反是从这种超体制或体制无关联的必要条件本身内含着对企业的要求中加以分析。
像藻利主张的那样,如果在开展机械化协作生产的经营中,必然的,包含生产力构造与人力所有者构造的二重构造成立的话,此时无论在怎样的经济体制下,基于经营的经营共同体的形成成为其必要性,且存在其可能性。如果这种主张能够成立的话,对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必须致力于形成经营共同体的固有原因,至今尚未给予充分的解明。为解明这种固有的原因,我们不仅关注,无论指导经营的技术构造机械化原理本身与指导经营的社会构造共同体化原理本身在实质性地规定企业整体指导原理的内容中的关系如何,还需要重视在现实中,机械化原理与共同体化原理本身因利润性原理的调整或综合,各自(机械化原理与共同体化原理)存在因利润性原理而相互渗透的现象。因此,资本主义经营中的劳动者人性异化同样是现实中由于利润性原理渗透到机械化原理产生的结果,这意味着企业致力于形成经营共同体是为了克服这种由利润性原理渗透的机械化引起劳动者人性异化的现象。
六、现实价值
1.经营学是以经济社会中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科学。“经营的二重构造”与“经营共同体”观点是藻利重隆对经营学的理论阐述。经营的技术构造与经营的社会构造相互统一构成“经营的二重构造”,它是以持续性地提高商品生产能力的一种观点。“经营共同体”是在充分分析机械化进程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阐述其对劳动者的负面作用,是如何构建劳动者主体地位的一种思想。
2.企业与外部各利益集团的交互及内部人与机器(及技术)的良性互动是企业及其理论发展的动能。正如E.L.Trist等提出的“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人们的态度和群体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工作于其中的技术系统影响。因此,这个流派的立足点就是,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必须被结合在一起考虑,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这两个系统的和谐。”[9]“生产力是共同体进步和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是客观因素。而现实的、感性的人的活动是共同体(也即社会)发展最为直接的动力,这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因素。”[10]
“经营共同体”可视为是一个自组织、自调节、自适应的“人—机”共生体系,是企业内部共生共荣的有机体。就“经营共同体”形成的机理而言,“经营共同体”是经营的社会构造与技术构造的统一体。“经营的社会构造”促进着“经营的技术构造”的形成,是实现生产效率化的必要前提;“经营的社会构造”共同体的形成使“经营的技术构造”实现机械化成为可能;而为“经营的社会构造”共同体化提供物质基础的正是“经营的技术构造”;双向共同作用促进企业经营持续健康发展。
3.“构成现代经营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它的利润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连接二者的伦理属性。”[11]“经营共同体”正是为了克服因利润性原理在机械化与共同体化的双向渗透引起劳动者人性异化现象的一种观点。
在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中,劳动者人性异化是由于利润性原理渗透到机械化原理的结果;藻利的“勞动异化”观点,虽然不能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相提并论,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的目的、遵循的指导原则以及对劳动者剥削的认识上有相近看法。在分析他的“劳动异化”观点时,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市场体系这两个基本前提。藻利的“劳动异化”观点作为分析“经营共同体”形成的一个要件,是以“经济型企业”为着眼点、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相适应,但是,在现今无论何种经济体制的企业,从“生命型企业”入手阐述人与技术的协动关系更为妥当。
“经营共同体”的观点是日本式管理形成的基础理论之一;然而,过度强调“利润性原理”的渗透进而形成“经营共同体”的观点,会造成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忽视“企业”作为社会价值创造与价值共创的基本单元的功能,是“经济型企业”“经济人”假设的典型代表。
“经营共同体”“经营的二重构造”观点为我们理解日本式企业管理提供着理论参考;但是藻利的观点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诠释了资本主义企业形成“经营共同体”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措施,缺乏实证分析作为支撑,更缺乏定量管理方法。
4.结合本土情境,构筑管理理论具有现实紧迫性。“国外对以日本为首的东方式管理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地步,其中的‘日本式管理早已被列入公认的管理理论之中。”[12]然而,经济全球化以及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经营共同体”形成的要素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变革共同体的结构层次,从一种多元、合作、互动的角度理解共同体的新特质。”[13]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不仅引起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而且促进着人—机互动方式及企业经营方式的深刻变革。
中国式管理理论需要借鉴已有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并结合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尤其技术进步带来的对“人—机”互动方式的影响来归纳总结。“具有东方文化代表性的管理智慧则体现在和谐管理理论对‘人因素的重视当中。”“东方的整体论思维则引导管理学者与实践者在面对和解决管理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同时考察组织中‘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通过制定与其适配的和则与谐则,并构建恰当的和谐耦合机制来从整体层面上促进管理问题的解决。”[14]
参考文献:
[1] 李慧凤,蔡旭昶.“共同体”概念的演变、应用与公民社会[J].学术月刊,2010,(6):19.
[2] 张志旻,赵世奎,任之光,等.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J].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10):15.
[3] 郑葳,李芒.学习共同体及其生成[J].全球教育展望,2007,(4):58.
[4] 李荣山.共同体的命运——从赫尔德到当代的变局[J].社会学研究,2015,(1):215.
[5] 王玉明,王沛雯.多学科视域中的“共同体”范畴比较[J].社会主义研究,2015,(5):159.
[6] 孟令军.企业共同体的社会学思考[J].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6):33.
[7] 李萍.日本经营模式及其内在缺陷批判[J].日本学刊,2014,(3):122.
[8] 村田和彦.生産合理化の経営学[M].千倉書房,1993:12-29.
[9] 哈罗德·孔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EB/OL].豆丁网,2014-04-13.
[10] 陈凯.从共同体到联合体——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D].泉州:华侨大学,2017.
[11] 范作中,中岛悟史.论经营思想的多重属性——以日本企业为中心[J].日本学刊,1995,(6):93.
[12] 解冰.中国企业管理研究的着力点应放在哪[EB/OL].人民网论坛,2016-12-01.
[13] 彭宗峰.风险社会中的共同体再造:反思与出路[J].北京社会科学,2015,(3):73.
[14] 席酉民,熊畅,刘鹏.和谐管理理论及其应用述评[J].管理世界,2020,(2):197.
The Formation Mechanism,Realistic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of “Business Community”
Aibijiang Bawudong1,MA Yue-yue2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Urumqi 830012,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Xinjia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Urumqi 830000,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ations of Japanese learners,elaborate theory of management community raised by Shigetaka Mori from five aspects:the concept,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the concrete measures,capitalist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community,and its management sense.Analyz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anagement community.Offer realistic value for further application.
Key words:“management community”;capitalist management;doubl structure
收稿日期:2020-08-07
作者簡介:艾比江·巴吾东(1964-),男,新疆乌鲁木齐人,副教授,博士,从事企业管理、创新管理研究;马跃月(1964-),女,新疆乌鲁木齐人,教授,从事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