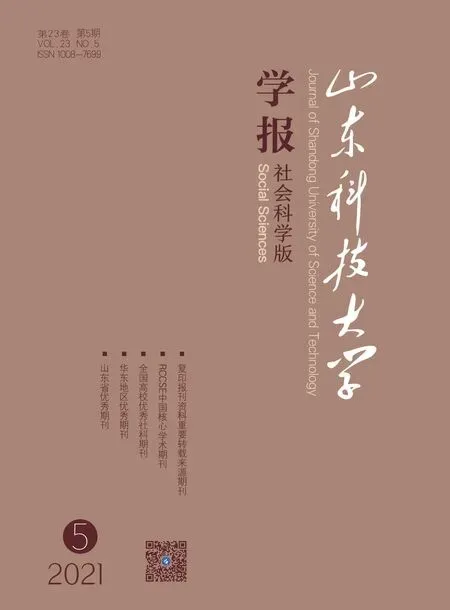风景的政治
——约翰·福尔斯“自然书写”中的文学想象与文化消费
刘 亚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1926-2005)在《哈代与巫婆》(HardyandtheHag,1977)一文中强调其生活和书写之兴趣皆在“自然”。[1]138此种“自然书写”是英国文学传统的延续。文艺复兴以来,忒奥克里托斯(Theokritos)与维吉尔(Virgil)的牧歌文学长期影响着英国文人:在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蒲柏(Alexander Pope)的诗歌以及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的散文中,都能看到对田园牧歌的赞美。[2]工业革命后,英国文学中“绿色”“古老”的“乡村”更是蕴含着英国文人的怀旧情结和民族身份认同:一方面,诗人歌颂乡村静谧、安适的环境,把工业城市描写成丑陋的怪物,通过自然风景和淳朴乡民反衬城市工业文明的弊端;另一方面,通过着力刻画传统的绿色乡村,英国文人据此确立了心目中的“英国性”(Englishness)。
然而,有学者敏锐地发现,这种田园诗般的“文学想象”背后遮掩着有诉求的意识形态神话和时髦的文化消费行为。诸多文艺作品在描绘人与自然的和谐画面时,常有意遮蔽乡村中现实的贫苦生活和主仆之间的雇佣剥削关系,并在其阅读接受过程中体现出一种文化消费的错位:一方面,描写并赞美乡村美景和乡民的淳朴,以此激发都市上层精英的阅读热情和文学想象;另一方面,在有选择的视界中令都市有产者只关注乡村美景,却忽略乡民的真实境况。这使得其对自然的欣赏成为一种经过裁剪的、精英化的艺术联想和文学消费。正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劳作的乡村几乎不曾是一幅风景。”[3]120
福尔斯的自然书写沿袭了“乡村英格兰”的文学想象传统,同时,他也在作品中批判与反讽被遮蔽的精英文化消费。为跳出这一矛盾,他回归于更古老的英格兰民间传奇,追溯了以“罗宾汉”(Robin Hood)为原型的“绿色英格兰人”(Green Englishman)及其自然精神,借以反叛近现代以“约翰牛”(John Bull)为代表的不列颠帝国形象及其资本主义精神。
一、荒野与庄园:“自然书写”与“田园文学”传统
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在其著作中把田园牧歌定义为一种源自希腊、罗马并与牧羊人生活相关的文学体裁。它所描绘的乡村生活常被视为一种对立于都市的理想生活方式。[4]随着工商业和城市的不断发展,英国的乡村田园也逐渐成为一种与前者相对应的情感依托。福尔斯对自然有着一种敏感而执着的热忱,尽管他因叙事技巧的创新而常被冠以“英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名号,但其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核更多继承自英国本土的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自然主义诗人。田园牧歌式的自然书写以及荒野、庄园等意象一以贯之地体现于其作品中。在《法国中尉的女人》(TheFrenchLieutenant’sWoman,后文简称为《法》)第七章,叙事者描绘了如下画面:
楼下传来小蹄子啪嗒啪嗒的落地声,接连不断的咩咩叫声。查尔斯站起来,向窗外望去。街上有两个穿皱褶外套的老人,正面对面地站着讲话。其中一个是牧羊人,用牧人的弯柄杖斜撑着身子。十二只母羊和一大群羊羔慌慌张张地呆在街上。古代英国留传下来的这种衣着样式到一八六七年虽并非罕见,但已不多,看起来很别致。每个村庄都还有十来个老人穿这种外套。查尔斯想,要是自己会画画就好了。的确,乡下真叫人陶醉。他转身对仆人说:“说真的,萨姆,在这儿过这样的日子,我再也不想回伦敦去了。”[5]45
这是英国南方小镇普通一早的惯常场景,包含了乡村田园文学的诸多要素:首先,牧羊人是田园文学的经典形象;其二,“楼上”“窗外”“仆人”暗示了这是一个上层人的庄园生活;第三,牧羊人的古老服饰与“斜撑着身子”的随意姿态,展示出一种历史悠久、节奏舒缓的生活方式;第四,观察者认为眼前的景象是可以“入画”的;最后,这幅“叫人陶醉”的乡村美景与观察者常居的都市生活构成鲜明对比,令其流连忘返。类似的牧歌场景和意象在福尔斯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在《巫术师》(TheMagus)中,尼古拉斯把希腊小岛设想为莎士比亚传奇剧《暴风雨》(TheTempest)中的场景。值得注意的是,莎剧中的荒岛土著卡列班(Caliban)也会被大自然的美妙声音吸引并受其感化;与之相对,米兰和那不勒斯城邦的宫廷达贵们却被各种欲望所包围,无暇顾及自然风光。荒野/城邦、低贱/高贵、自然/文明构成了一种绝妙反讽。正如福尔斯在《树》(TheTree)中所言:“离卡列班越近,也就是离自然越近。”[6]像传统文人一样,他笔下的自然书写也体现出一种情感的率真流露。当尼古拉斯与艾莉森驱车行进在绿色山谷时,遇到一对牧羊的兄妹。与小牧童的习以为常不同,面对阳光绿野的艾莉森像个孩子般狂野地奔跑,与其在伦敦涂着浓重眼影的叛逆形象有天壤之别。作为一个都市空姐,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狭小的机舱里奴隶般地工作”。[7]326于艾莉森而言,绿色的大自然不仅是一种地理空间的变换,更是一种精神空间的转换。而这样一种乡村与城市的精神空间对比,也贯穿于英国文学传统之中。
工业革命以来,许多英国文人对工业文明的“进步意义”持审慎的批判态度。由于英国工业城市主要集中于北方,在其文化中形成了“北方/城市/工业”与“南方/乡村/田园”的隐喻与象征。唐纳德·霍恩(Donald Horne)认为,在“北方”隐喻中,英国重实用主义,精于经济上的考量,资产阶级精神占主导,其罪过是“无情的贪婪”;而“南方”隐喻中,英国充满浪漫主义,秉持传统秩序和文化,贵族精神占主导,其罪过是“无情的骄傲”。[8]41-42这种“南方”与“北方”的价值冲突自19世纪延续至今。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 Gaskell)曾在小说《南方与北方》中力图调和两种文化的冲突:代表北方的男主人公桑顿逐渐接受南方带贵族气的人文文化,而代表南方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则认识到北方工业的进步意义。但小说叙述中潜移默化地植入道德考量——绿色乡村和淳朴乡民代表了一种悠久传统、有秩序有德性的生活方式。正如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所言:“我们回到简·奥斯汀的观点,即生活在乡村的人都是好的,城里的人都是坏的。”[8]79
上述观点也鲜明体现在福尔斯的生活及创作中。在《自然的本性》一文中,福尔斯回忆其到法国后了解了法国艺术、社会风俗和市井人文,并像许多同龄人一样,被加缪的存在主义迷倒。但所有这些都在“荒野”(the wild)这个“姑娘”面前黯然失色。[1]350而这位“姑娘”也反复出现在其作品中。《巫术师》中的荒野姑娘正是歌声神秘的牧羊女,因为她“属于还未使用机器前的世界”。[7]51在《法》中,这位姑娘则变成了莱姆镇的青翠山岭。于此地,查尔斯发现久居伦敦的自己在城市文明中已忘记自然的本貌。
与此同时,福尔斯对现代工业和都市生活侵袭乡村的现状感到困惑与不安。他在日记中说自己“最喜欢独自呆在乡村,就像一个人在一座岛上。城市是某种未来。它散去,与我分离,被我遗忘。”[9]220在法国旅行时,被广告牌毁容的绿色乡村令其痛心。在曼哈顿街头,他感到高耸的建筑、拥挤的人群和汽车的毒气是“对自然的完全抹杀”。[10]因此,他将这种感受写进作品。《巫术师》中的“诗人”尼古拉斯也敏感于工业文明的侵扰。当其欣赏岛上的绿树蓝天时,发现工厂破坏了景色的和谐。在岛上看到第一道铁丝网时,他就厌恶它“玷污了这里的宁静。”[7]73
在《法》中,维多利亚时代的查尔斯对工业和机器带来的冲击也深有体会。与莱姆小镇的宁静祥和不同,工业城镇给进城工人新盖的房屋狭窄潮湿,光照极差。街道臭气熏天,到处是烂泥污水。在描写埃克斯特河道旁一排乔治时代的房子时,叙事者设想当年从屋里可以俯瞰沿河景致。然而,后加盖的房子却挡住风景,破坏了自然美。在当时,建筑被视为民族记忆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保护旧建筑不仅是美学追求,更有道德考量。因此,面对莱姆镇的新会议厅,查尔斯厌恶地称其“座落的地方和造型之丑陋,堪称英伦三岛上最差的公共厕所。”[5]146这刻薄之声的背后不仅是审美批判,更有道德谴责和历史反思。像许多19世纪文人一样,在他眼中,凝聚英国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的建筑不是都市里的钢铁玻璃建筑,而是乡村庄园。在小说第二十三章,查尔斯就饱含深情地注视着温斯亚特庄园:
庄园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他才存在着的:那整洁的门房花园,那远方的园林,那一丛丛的古树——每丛古树都有一个雅号,像“卡森的讲坛”呀,“十松岭”呀,“拉米伊”呀(为庆祝那次战役的胜利而种植的),“栎榆合欢”呀,“缪斯丛”呀,等等。查尔斯对这一切都很熟悉,就象他熟悉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样;还有那酸橙树林荫道,那铁栏杆,这一切在他看来,或者凭他的本能觉得,都是来自对他的爱……[5]224
查尔斯周岁时母亲便撒手人寰,父亲对其不管不顾。因此,他自孩提时代便从庄园的每一个角落找寻情感补偿。在其眼中,这个庄园不是由无声的草木和冰冷石头构筑的建筑物,而是联结自己童年记忆和有关于爱的情感结构。因此,当未婚妻看不上老旧的庄园,想对其翻新时,查尔斯冰冷地讽刺她可以另建一座“水晶宫”。显然,时尚的未婚妻更倾心于现代化的伦敦都市生活。庄园于她只是身份象征,而非精神家园。
与笔下人物相似,福尔斯童年的乡村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让其毕生对荒野和庄园有种执着偏爱。当他因写作出名后,第一时间放弃城市生活而来到莱姆镇购置宅邸,终生居住于此。如其所言,乡村庄园是他的精神避难所。然而,如若细读文本,就会发现他在赞美乡村生活的叙事中还潜藏着另一种声音。
二、风景的政治:文学想象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悖论
在《风景与权力》(LandscapeandPower)一书中,米切尔(W. J. T. Mitchell)强调风景是一种“以文化为媒介”的自然景色。通过“自然化的习俗”与“习俗化的自然”,风景隐藏了其价值的真正基础。约翰·巴瑞尔(John Barrel)将这种隐藏称为“风景的阴暗面”(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并视其为一种“道德的、意识形态的与政治的阴暗面”。[11]5-6而伯明翰(Ann Bermingham)更进一步提出存在一种“风景意识形态”(an ideology of landscape)。她把风景视为一种有意识形态的“阶级观看”,并由此折射出一整套由经济和社会决定的价值观念。[11]8支持社会主义的福尔斯在其创作中也揭示了这种文学想象背后隐藏的观念冲突。在《法》第十九章,叙事者提及波尔蒂尼夫人的女仆米莉。她是农夫的女儿,姊妹十一人与父母一起挤在荒凉山谷中的两间潮湿草屋里。话到此时,小说笔锋一转:
现在,那两间草屋已落到了伦敦一个时髦的年轻建筑师手里,他常到那儿度周末。他很喜爱那两间草屋,因为那儿地处山野,十分偏僻,一片田园风光。这件事或许消灭了维多利亚时代这地方出现的可怕现象。但愿如此。乔治·莫兰之流(在一八六七年,伯基特·福斯特是罪魁祸首)把乡村生活大加渲染,似乎农村劳动者和他们的子孙都是那样心满意足地生活着。其实,他们的绘画同我们时代的好莱坞电影一样,都掩盖了“真实”的生活,是一种愚蠢而有害的情调。只要看一看米莉和她的十个兄弟姐妹的情况,关于“快乐的乡村少年”的神话便会不攻自破了。……就我个人而论,我最痛恨的是那种用文学和艺术建造起来的高墙。[5]183-184
叙事者以横跨两个世纪的对比,意在提醒读者,英国文化中的“乡村想象”其实是一种有选择的文化型塑。“文学和艺术建造起来的高墙”在墙前展示某种人造景观的同时,又有意遮蔽了墙后不愿告人的景象。叙事者的“痛恨”之声也呼应了安德鲁·郎利(Andrew Langley)的如下文字:
大多维多利亚时代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总是营造出一派乐观、祥和、天真无邪的田园景象。穿着工作服的农夫身强体健;收割工人在干草堆下休憩……艺术家们透过这些美妙的田园景色来表达自己的道德观。……但是广大农民的实际生活却与艺术作品中所描述的大相径庭。他们租住在窄小、阴暗、潮湿的村舍里……不论是严寒还是酷暑,他们都得起早贪黑地在户外工作。[12]
上述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那里得到更详细的阐述。他在《乡村与城市》(TheCountryandtheCity)一书中,详细梳理了英国16世纪以来的乡村田园文学作品,发现文人喜用“往昔美好的日子”“快乐的英格兰”“有机社会”“绿色田园”等词汇称呼日渐消逝的农耕社会。他们以理想化的乡村英国反衬当时快速、冰冷、隔膜的工业社会和城市生活,却极少描写辛劳的农民和破败的农舍。一方面,威廉斯认为这种田园主义怀旧反对资本主义的金钱秩序,承载了一定的人道主义情感;另一方面,他也敏锐地发觉,此类文学怀旧是一种编制出来的意识形态神话。它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之情对应于一种社会等级秩序。威廉斯认为对于这样一种叙述,我们要探究的不是“史实上的错误”(historical error),而是“历史视角”(historical perspective)问题。[3]10若变换视角,我们会发现福尔斯的作品中也暗含着另一种声音。
在《法》中,当查尔斯通过庄园窗户欣赏着小镇安静祥和的田园风光时,如若推远镜头并扩大视域,我们会发现仆人萨姆正在磨剃刀、烧开水,忙于各种仆役工作。窗外风景是他无暇消费的“奢侈品”。当主人在屋内隔着窗户欣赏牧羊人的画境并声称不想回伦敦时,萨姆却揶揄道:“要是您老是站在风口上,先生,您就真的去不成伦敦啦。”[5]45此话明褒暗讽:一层窗户把查尔斯和牧羊人分隔为两个世界。屋内的查尔斯感到暖风“搔抚着他的脖颈”,[5]45并不理解屋外牧羊人的寒冷和辛苦。因此,萨姆既在善意提醒主人注意保暖,亦在暗讽主人把牧羊人的生活美化了。
同样的,当尼古拉斯把希腊小岛上的牧羊女想象为林中仙女并倾听其神秘歌声时,却也发现那无拘无束的歌声并不欢快,而是“孤寂和痛苦的心声”。在当地赶骡人眼里,牧羊人的生活也毫无诗意:“无边的沉默偶尔被铃声打断,还要小心防狼防鹰,一种六千年不变的生活。”[7]319尼古拉斯只是叶公好龙般地把牧羊女理想化为一个审美符号,在其碰到真正的小牧羊女后,却因嫌弃她身上有虱子而不愿靠近。
威廉斯注意到,17世纪以来英国文学对乡村田园的描写慢慢滑向对乡绅生活和乡间庄园的赞美,营造了乡绅与乡民在温和家长制下的和谐,以致地主和上帝共用“Lord”这一称谓。他认为这是一种美化甚至神化的虚构:“对‘消失的乡村’的捍卫与对旧乡村秩序的捍卫相混淆了”。[3]196这种“自然的”农业经济和乡绅阶层并不天然具有一种道德优势。《法》也折射了这一复杂矛盾的关系:在温斯亚特庄园,我们看到一幅和谐画面——仆人各居其位,安心工作。有十几个老人退休后留住在庄园领取养老金,似乎这种生活是“应该的”“神圣的”“永远不可动摇的”。然而,叙事者的笔锋再次转向,讽刺了自己先前所说:
可是,老天知道——女仆米莉也知道——乡下的非正义与贫穷象谢菲尔德市和曼彻斯特市的非正义与贫穷一样丑恶。但是农村里的这种非正义与贫穷总是以隐蔽的形式进行着……农村的主人们象喜欢照料良好的土地和牲畜一样喜欢照料良好的农民。他们对雇工们相对而言的善良,只不过是追求家业兴旺过程中的副产品,但农民总可以得到一点残汤剩羹。[5]226
地主对农民的“保护”并未改变后者作为前者“财产”的身份属性。小恩小惠是为了使他们能付出更多劳力,生产更多食物,是一种“不道德事件后的道德反射”,[3]183其背后本质还是一种对农民身体和经济的控制。因此,这种乡村社会关系并非文学想象所描绘的那般完美,主要的区别就是控制力度因人而异。小说中也给出了这种对比:查尔斯的伯父醉心于打猎和收藏,较为开明,其庄园的农民和仆人待遇较好;而莫尔伯勒府邸的波尔蒂尼太太刻薄、规矩多,她每周让家仆工作一百多个小时,逼得他们逃之夭夭。
此外,对有产阶级来说,乡村旅行是对抗城市病的良方,购置乡村宅邸则成为一种昂贵的炫耀性消费。查尔斯的岳父在伦敦建立了商业帝国,却仍要模仿贵族去乡下购置庄园。在中篇小说《乌木塔》(TheEbonyTower)中,戴维在柯米奈庄园感到逃离了城市喧嚣,甚至想回国后与妻子再去威尔士的乡村体验这种感觉。英国的乡村书写构成了一种乡村文学想象,促成了中上层的文化消费;而这种文化消费又进一步强化了“乡村英国”的概念,最终形成了国家层面的“想象共同体”。诚如马丁(Martin Wiener)所言:“对旧时乡村生活的迷恋,不管是真实的或是想象的,在一战后都渗透到整个中产阶级。”[8]72
然而,在福尔斯的文本中,我们却读出了某种文化消费的悖论:一方面,所有人都相信乡村是好的,乡民是淳朴的;另一方面,都市的中上层有产者却只消费乡村风景,轻视甚至忽略乡民。当尼古拉斯形容希腊小岛的美景时,用到了“如画美”(picturesque)这个词。而在其无法入画的黑名单中,不仅有冒烟的工厂、难看的建筑,也有文学作品中赞美的淳朴乡民。在《法》中,城里游客到莱姆镇码头欣赏早春风景时,无人注意到那些补网、漆网的渔夫,后者被前者从“如画”美景中抹掉了。正如马尔科姆·安德鲁斯(Malcolm Andrews)在《寻找如画美》一书中所言,都市游客到乡下来进行时髦的“画境游”,只是想在艺术品和自然之间找到一种“想象的愉悦”,这是一种“精英阶层”的“赏景套路”。[13]而这样一种潜藏在“风景中的阶级编码”甚至可以追溯至简·奥斯丁的小说。[14]人们试图从乡村文化想象中寻找英国特性、文化历史、自然情感与和谐秩序,却仅将赞美目光聚焦于乡村宅邸和乡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真实的乡民和劳作。这种选择性想象最终会导致历史的扭曲。因此,福尔斯反对这种乡村田园文学想象的意识形态底色和文化消费的娱乐性。为此,他回溯到更久远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精神寄托。
三、约翰牛与罗宾汉:“绿色英格兰人”的精神反叛
在《巫术师》中,当尼古拉斯于1952年从希腊返回伦敦后,感到伦敦的“灰色”(greyness)令其窒息。[7]733那一年福尔斯在希腊执教,因此尼古拉斯所言正是作者内心所感。他认为真正的“英国特性”应是“绿色性”(greenness),而符合这种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的“真正英国人”在现实中难以找到。他只存在于既往历史和民间传奇中,即以绿林好汉罗宾汉和绿色骑士(Green Knight)为典型代表的“绿色英格兰人”(Green Englishman)。
“Green man”一词在今日多指“新手”之意,在20世纪的生态批评著作中还是环保主义者的代称(常被译为“绿党”)。但作为一种贴近自然的文学原型,它一直存在于西方文学传统中。巴里·奥尔森(Barry N. Olshen)曾撰文对此进行梳理总结。[15]而福尔斯笔下的“绿色英格兰人”就是英国民间传奇中深藏于林的侠盗罗宾汉。在英国文学中,这一形象常是自然和自由的代表。例如,在莎剧《皆大欢喜》中,被放逐到阿登森林的公爵就认为,自己当下的境遇像古代的罗宾汉一样。罗宾汉形象也一直萦绕在福尔斯头脑中,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及要创作一部关于罗宾汉的书。[9]323,435,563,633
在《英国人,而非不列颠人》(OnBeingEnglishButNotBritish)一文中,福尔斯专门阐述了自己对于绿色英格兰和罗宾汉精神的理解。在其看来,“绿色英格兰”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岛国(island)意识,与之相伴的是孤独意识、隐遁意识;其二是公正(justice)意识,要反抗不公与压迫。[1]79-84而在民间传说中,罗宾汉之本性在于敢与官方的一切体制禁锢与权力压迫对抗。他还一直退隐于森林,像自然之子一样脱离文明社会的各种束缚。由此,福尔斯认为罗宾汉才是“绿色英格兰”精神传统的代表,而更为人熟知的“约翰牛”只能代表工业革命以来傲慢霸道、“灰色”的不列颠帝国形象。这一原型也潜藏在其小说创作中。
首先,其小说中的诸多主人公多喜欢自然,厌恶现代文明。《巫术师》中,尼古拉斯面对希腊小岛,“平生第一次开始观察自然”,用“一种新的方式注意石头、飞鸟、花朵”。[7]53而当康奇斯站在赛德瓦雷静谧的土地上时,深深地被当地的荒凉空旷和宁静神秘所震撼。在查尔斯和莎拉那里,我们同样能找到罗宾汉的影子。前者在安德克立夫找化石时,身着臃肿的职业装束,其鼓鼓囊囊的包里装着锤头、包装材料、笔记本等工具物品。在叙事者看来,这是科学研究的必备,却也是文明的负担。当他来到“一个人影也没有”的僻静处时,叙事者“极为高兴地”记下这一时刻:
这当儿,一个完全合乎人性的时刻来到了。查尔斯警惕地环顾一下四周,当他确信四周无人时,便小心翼翼地脱去靴子、绑腿和长统袜。那是童年才会有的时刻,他试着回想荷马的诗句,说明这样的时刻古已有之。可这时一只小螃蟹从他身边爬过,捉螃蟹的念头分散了他的精神。查尔斯在水中的巨大倒影落在螃蟹警惕的、高高翘起的眼上。[5]56
在这样一个无人的荒野之地,查尔斯甩掉文明社会的包袱,以自然之躯面对自然之境。那只突然出现的小螃蟹像一个顽皮的自然精灵,把查尔斯从历史冥想中拉回到当下现实。当查尔斯的身影映照在螃蟹眼睛上时,人与自然不再是对立的,二者合而为一地融合在一起。
在《乌木塔》中,画家布里斯利栖居在隐藏于潘蓬森林的柯米奈庄园。叙事者直接称其“和罗宾汉没两样”,“不是住在庄园里,而是住在森林里。”[16]82-83布里斯利热爱自然,珍视传统,反对戴维所代表的现代抽象画,痛斥抽象画家背离了自然。作者有意将他与戴维对比:老人的创作与自然联系密切,与过去息息相关;而戴维则“包裹于书斋知识的胶囊,视艺术为某种社会机制、科学抑或争取项目资金的途径”。[16]110
其次,福尔斯小说的主人公与罗宾汉一样珍视自由。尼古拉斯在牛津求学时空谈存在主义自由,然而恰是小岛上的生活经历才令其逐步领悟了自由的真意。查尔斯出游的首选也是“岛屿、山脉和人迹罕至的绿色丛林”,“不仅仅是为了欣赏泉水,而是为了自由自在”。[5]157在波尔蒂尼夫人面前,莎拉总是很文雅(politeness),谨小慎微,吐字如金。然而一旦走向康芒岭的树林中,她就如鸟出笼般地感受到自由。当其与查尔斯在此交谈时,俨然是在“自己的会客厅”说话。当两个罗宾汉的后人相拥于旅馆时,叙事者也用了一种绿色而非暧昧的自然语言形容查尔斯的感觉:“象一个囚犯回到了绿色的田野,象一只山鹰在自由翱翔。”[5]390在《乌木塔》中,老画家的野性让其冲破各种文化藩篱的束缚,而戴维及其一代人则“天生被囚禁在笼中,只能透过栏杆,回顾过去那种属于绿色自然的自由”。[16]110在福尔斯看来,自由应该也只能在绿色的自然中获得,自由的人只能是那些生活于自然并能领略自然之美的人。通过其小说中的“绿色”人物,他表达了自己对英国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的理解。
因此,约翰·福尔斯的自然书写既是其本人热爱自然的情感表达,也是对英国田园文学传统的承继。同时,其作品也揭示了传统田园文学中隐藏在文学想象背后的意识形态隐喻和文化消费悖论,并对其持审慎的批判态度。最终,他在传统的民间形象罗宾汉身上发掘到“绿色英格兰”的精神核心——自然、传统、公正、自由,从而部分地完成了对传统自然书写的超越。如福尔斯所言,开启其小说的钥匙在“他与大自然的关系中”。[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