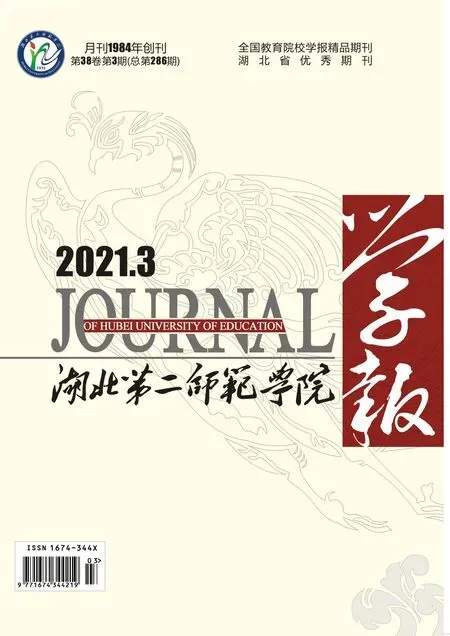浅析东汉外戚集团维系政权稳定的制度性安排
李正杰,李志明
(1.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2.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00)
外戚,意指皇帝的妻妾或母亲的同族亲属,亦称为后族。在东汉王朝统治时期,虽自光武皇帝刘秀始便深以西汉遭外戚王氏夺取刘姓权位为忧,并采取了一定限制外戚权位的政治手段[1],但终东汉一朝,大量的外戚家族成员依然通过与皇帝妻母的血缘纽带得以仕进,并在权柄极盛时实际掌控了东汉政权,甚至多次参与了帝位的废立,因此成为了东汉历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类政治力量。
此前的学人在对于东汉外戚政治的研究上更多注重于外戚专权带给东汉王朝的负面影响,将其作为一种不断腐化的政治集团,并直接将其与东汉政权的覆灭相关连[2],未能对其如何在东汉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作出系统性阐述。然而东汉外戚集团自和帝幼年继位后权位逐渐达到顶峰,开始实际控制朝政,后方在宦官集团的不断挑战下失去其近乎乾纲独断的政治地位,这一外戚政治的巅峰时期历和、殇、安、北乡侯、顺、冲、质、桓八帝经窦、邓、阎、梁四氏外戚叠相执权,达七十余年之久,且该时期的汉廷中央政府虽多次发生武力政变等事件,但整体上维系了政权的延续与安宁[3],鲜起战事且从未发生中央政治冲突扩大至内战状态的情形。由此可见外戚集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必然在长期执权中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利于稳定的政治惯例与制度性安排。本文将结合史料与前人研究对东汉外戚在不同时期维系政权稳定的举措进行探讨与思考,以求更深层次的了解东汉政治体系运作的相关模式。
一、统帅军旅:拱卫中央与征讨边疆
东汉外戚集团终东汉一朝始终握有军权,故而其维持政治稳定的主要举措之一便是为东汉政权统帅军旅,主要方式有二:宿卫禁中与统军征讨。其中以宿卫禁中为主要方式,东汉政权自草创时代便有以外戚领君主亲军并长居左右的传统,如光武帝时皇后郭圣通之弟郭况先后任为黄门侍郎、城门校尉以拱卫宫城,阴丽华之兄阴识则“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4]担负起了在君主远离中枢时保卫中央政府的职能。其弟阴兴则“兴每从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风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门。光武所幸之处,辄先入清宫,甚见亲信。”[4]亲随君主左右,在君主巡幸时负责清理所到场所,时刻注意其安危。由此可见任用外戚负责内卫事务在当时便已经成为政治惯例。而这一惯例的形成亦与东汉初年动荡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如割据一方的渔阳太守彭宠于被自己豢养的苍头子秘密刺杀,而统领汉军讨伐成家政权的来歙、岑彭亦在军中先后被刺客所杀,虽然作为隗嚣使节访汉的马援曾称赞刘秀“援顿首辞谢,因曰: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后进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帝复笑曰:卿非刺客,顾说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4]赞美了刘秀对远来之人不设过多防备的气魄,但也反映出了刺客之风横行于世的客观时代背景,因此将亲卫之权授于视为骨肉的外戚把控也就成为一种自然之举,此举亦在东汉一朝中成为定制。若马氏立为皇后后,明帝以马氏兄弟马廖为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马防、马光为黄门侍郎,俱掌亲随之事,而在明帝死后更是以遗诏使马廖典掌门禁,确保了权力的顺利交接,且其后马防亦被迁为城门校尉继续负责保卫事务。而在章帝执政后又很快从边地招入已经边疆战事的自身妻族窦固为大鸿胪并在几年后使其替代了马防的宫禁职责,且很快将窦后兄弟窦宪任为侍中、虎贲中郎将,直接控制禁中军队,而章帝去世、和帝即位后又遗诏以窦笃为虎贲中郎将,和帝立邓绥为后后便升任邓氏之亲邓骘为虎贲中郎将,安帝亲政废邓氏权后,又将皇后阎姬兄弟阎显、阎景、阎耀、阎晏皆任命为卿校共同掌控禁兵大权,此后梁、窦、何诸氏均依此例叠相参预禁兵事务。足见惟有至亲外戚方能得到信任执掌禁兵,即便是外戚中之疏属也会被解除禁中兵权(常见情况下为妻族取代母族,例如前文所提及的章帝年间以作为妻族更为亲近的窦氏取代作为母族较疏远的后族马氏掌管禁兵)。而与东汉皇权荣辱一体的外戚也多在宿卫事务上尽忠职守,使得东汉一朝在最后一位辅政外戚何进主动调外兵入京却意外遇难前始终未有任何内廷之外的政治势力能够得以武装干涉中央政权,大大提升了东汉政权整体的稳定性。虽然其间宦官亦参预内廷军务与外戚发生多次交锋,但双方集团参与政治的合法性同为刘汉政治力量的延伸,即使二者叠相诛夷也未动摇汉廷政权本身的稳定性,也从未扩大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与内战。而在东汉末年何氏外戚被消灭后东汉中央政权旋即陷入了军阀的叠相争夺之中,最终导致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扫地与东汉政府的整体瓦解,更是进一步突显了外戚宿卫中央的重要性。
统军征讨则是外戚掌管军权、维系东汉政权稳定的另一种方式。在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之初,作为其妻族外戚的真定郭氏、南阳阴氏便多次参与其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郭竟作为骑将从征伐,阴兴“建武二年,为黄门侍郎,守期门仆射,典将武骑,从征伐,平定郡国。”[4]不难发现,在光武时期负责统军征伐的外戚将领虽有之,且均立有军功,但均为跟随大军出伐之偏将,本身俱无独领方面之功,甚至阴兴亦自称“臣未有先登陷阵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诚为盈溢。”[4]可见一方面其征讨之功于开国勋臣中甚为微小,另一方面亦证明此时的外戚集团并无插手前线统帅事务的政治诉求。而在汉章帝建初二年金城陇西羌人反叛时,时为章帝母族的马防作为主将领兵“拜防行车骑将军事,以长水校尉耿恭副,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积射士三万人击之。”[4]主导了此次征讨。而马防在此次作战中更是采用了恩威并施的战略,不仅在军事交锋上取得了胜利,更是通过恫吓与劝降的方式以较小的损失取得了叛军降附的结果,东汉外戚领兵方面之先河由此遂开。其后和帝朝外戚窦宪更是“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4]其通过统领东汉政权治下的多民族军队成功多次大破北匈奴所部,最终北单于失踪、北匈奴政权也近乎消亡,不再能对东汉构成威胁。堪称东汉外戚的武功顶峰。窦宪之后安帝外戚邓骘亦于永初元年统帅中央军队讨伐凉州叛羌“于是诏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车驾幸平乐观饯送。”[4],然而却损失惨重、大败而归“骘西屯汉阳,使征西校尉任尚、从事中郎司马钧与羌战,大败。时以转输疲弊,百姓苦役。冬,徵骘班师。”[4],邓骘的战败而归虽然依旧在邓后的政治操作下被作为功绩得以升任大将军并加以举朝慰劳“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将迎拜骘为大将军。军到河南,使大鸿胪亲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4],然而此举颠倒黑白必然不甚光彩,此即外戚统兵形势又一大变。此后虽亦有外戚统兵出战为国平定内忧外患的情况,如安帝元初二年邓遵统南匈奴部众平西羌之乱“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及左鹿蠡王须沉万骑,击零昌于灵州,斩首八百馀级,封须沉为破虏侯,金印紫绶,赐金帛各有差。”[4],灵帝中平四年何苗统兵镇压荥阳民变“荥阳贼数千人群起,攻烧郡县,杀中牟县令,诏使进弟河南尹苗出击之。苗攻破群贼,平定而还。”[4]等。但从此便无如窦宪、邓骘等中央辅政外戚自领兵出战的事例,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多数辅政外戚久居中央,虽多为元勋将门出身,但自身并无甚多军旅经验,在自掌大军的情况下稍有差池便可能损兵折将,对政权的安全与自身的政治声誉都无疑是巨大的损害。故而此后中央辅政外戚便不再强行此举。其二,即使中央辅政外戚出征如窦宪一般大获成功,也很难避免如窦宪一般由于长期出征在外、久疏中枢军事以至于虽然自身在边时身握精兵良将但依然在回朝时为政敌领禁兵所制的尴尬局面,故而委任其他亲属以出征兵事而自握宿卫中央之权便成为了其后辅政外戚的最优选择。
二、参预朝政:劝谏进言、辅佐嗣君与树立道德典范
东汉外戚作为皇帝近亲属多直接被委以重任参预朝政,其具体方式有以下几种。
其一,劝谏进言,东汉外戚集团往往以侍中、黄门侍郎等内职官身份直接参与内朝政治[5],故而其谏议往往可以直接上达天听以直接影响到皇帝或者执政皇太后的决断,发挥极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如章帝时马廖对皇太后上疏“臣案前世诏令,以百姓不足,起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躬服厚缯,斥去华饰,素简所安,发自圣性。此诚上合天心,下顺民望,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犹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终。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于行仁心乎,况于行令乎!愿置章坐侧,以当瞽人夜诵之音。”[4]试图通过阐释统治者的行为对于风尚的引领的作用,极言抑制奢靡之风对于民生的重要性,而后太后也采纳了这一提议。而外戚马严则在日食之时借天相弹劾不称职的地方官员“臣伏见方今刺史太守专州典郡,不务奉事尽心为国,而司察偏阿,取与自己,同则举为尤异,异则中以刑法,不即垂头塞耳,採求财赂。今益州刺史朱酺、杨州刺史倪说、凉州刺史尹业等,每行考事,辄有物故,又选举不实,曾无贬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4]最终使得三名擅作威福、祸于地方的刺史高官在一夕之间皆被皇帝罢去。外戚梁商辅顺帝时面对宦官张逵、石光等矛头指向自身的未遂政变且在顺帝公开表示“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的支持宣言下,依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表示“春秋之义,功在元帅,罪止首恶,故赏不僭溢,刑不淫滥,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窃闻考中常侍张逵等,辞语多所牵及。大狱一起,无辜者众,死囚久繫,纤微成大,非所以顺迎和气,平政成化也。宜早讫竟,以止逮捕之烦。”极力阻止了顺帝扩大诛连范围,避免了冲突的扩大化与政局的动荡。而在宦官权力甚嚣尘上的党锢时代,作皇后之父的外戚窦武更是直接上言为党人辩护,要求释放党人、抑制宦官,其言辞甚至颇为尖锐“而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餮,外典州郡,内干心膂。宜以次贬黜,案罪纠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宝爱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应可待。閒者有嘉禾、芝草、黄龙之见。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4]其奏疏之末不仅有直接抨击皇帝之言,而且随即请病自还所任官爵印绶,而恒帝旋即应允了此事,释放了大量狱中的党人。由上述例子可见外戚因其与皇室为亲的特殊身份往往可以对君主提出部分敏感而直接的谏言,使得君主得以在政局过于紧张的时代依然具备一种得以了解部分不同意见的渠道,在客观上起到了使统治者之言路不至于过于闭塞的作用。
其二,辅佐嗣君。外戚作为皇室家族的延伸,由于其方便接近君主家庭且与嗣君利害一致的性质往往被直接选为继承人的辅佐者,这一惯例始自光武帝刘秀妻族阴兴——“十九年,拜卫尉,亦辅导皇太子。明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受顾命于云台广室。”[4],自此辅政外戚往往在皇帝病危之时肩负起了嗣君的教导与重大的政治职能。章帝之时外戚马廖“朝廷大议,辄以询访”[4],马防“数言政事,多见採用”[4],此时的外戚马氏尚在行顾问之权。而后东汉政权通常立幼君为帝,心智尚不成熟,便由太后摄政,而太后又不得不任用其男性亲族以控制朝政,开始了外戚总领幼主朝政的时代,若外戚窦宪之“内干机密,出宣诰命”[4]已经近乎无所不统,在旧史家的叙事中这无疑是对皇权的篡取甚至于背叛,但出于政权整体的考虑,成年的外戚职官的实际执政能力,显然是优于幼年不知世的君主与久居深宫的太后的。且由于东汉的政治惯例,母族的摄政往往在皇帝成年后便很难再得到朝中士大夫与内廷宦官的支持,其原所控制的内朝之职也将被新帝妻族取代,以至遭到亲政新帝的政治清算,无力完成实际上的篡夺,而新帝之妻族荣辱俱系于新帝一身安危,自然会倾力帮助新帝稳定朝局,两方也往往将在这时在政治上成为进退与共的联盟。同时君主的政治能力的养成便是在此阶段,东汉一朝并无成年后无力控制中央政府的君主,亦足见历代外戚集团的教护之能。
其三,树立道德典范。东汉政权的外戚集团多会在辅佐朝政期间中运用多种减少自身直接获利的政治手段近乎公开地强调、宣扬自身对崇高道德标准的坚持。例如控制宾客来往则有阴兴“虽好施接宾,然门无侠客”[4]与马严“明德皇后既立,严乃闭门自守,犹复虑致讥嫌,遂更徙北地,断绝宾客”[4],表达绝无蓄勇犯上之意。如辞让官爵则有阴兴先以“臣未有先登陷阵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诚为盈溢。臣蒙陛下、贵人恩泽至厚,富贵已极,不可复加,至诚不愿”[4]拒绝关内侯之爵,后以“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4]拒绝大司马之位,着力表现自足之态。如轻财好施则有窦固“赀累巨亿,而性谦俭,爱人好施,士以此称之”[4],家产丰厚但有所捐纳亦受到称赞。退职奉母则有邓骘兄弟“及服阕,诏喻骘还辅朝政,更授前封。骘等叩头固让,乃止,于是并奉朝请,位次在三公下,特进、侯上”[4],显示出忠孝大于仕进的朴素价值观。试分析之,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避免给其他政治集团借故发难的话柄,另一方面东汉王朝的士人阶层多出自地方豪族大家,往往掌握大量土地与人口资源,一旦肆意妄为便极易对国家治理体系造成相当的干扰。而同为豪族的外戚集团树立的道德楷模形象在这一时代得到士人阶级的交口称赞,充分说明了外戚集团所倡导的尚忠孝、退名利的道德准绳已经被士人阶级认可,对其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三、举荐贤才
东汉外戚举荐贤能的先决条件就是其特殊政治地位往往可以招徕大批宾客置于门下,此情形在光武帝建武初年便已经形成,如郭况“以后弟贵重,宾客辐凑。况恭谦下士,颇得声誉。”[4]外戚借帝胄声威对士人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结合东汉以察举为主的推举式选官制度,外戚集团理所当然对东汉的职官人事任用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便是外戚推举、提拔官员的原则,光武帝时阴识“所用掾史皆简贤者,如虞廷、傅宽、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4]展现了其重视贤能的倾向,但所擢用者仅限自身掾史属吏范畴,而其弟阴兴则更进一步“与同郡张宗、上谷鲜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犹称所长而达之;友人张汜、杜禽与兴厚善,以为华而少实,但私之以财,终不为言”“兴素与从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兴疾病,帝亲临,问以政事及群臣能不。兴顿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见议郎席广、谒者阴嵩,并经行明深,踰于公卿。兴没后,帝思其言,遂擢广为光禄勳;嵩为中郎将,监羽林十馀年,以谨敕见幸。”[4]主动推荐与自己不相好却有才华之人而放弃推荐能给自己带来直接政治利益但并无甚能力的友人,显示出不偏私好的立场,这些显然是有利于东汉政府的长期稳定的。此时阴氏举任的官员而后虽最高可至公卿校尉,却无一人位至中央宰铺,亦无一人任地方大员,影响还比较有限。到了章帝朝,辅政外戚马防“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4]其能影响的官员任职范围大大提升,但明显更偏向于地方镇守官员。和帝朝的窦宪则“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4]在掌握地方镇守官的基础上亦发掘出了一批长于文学的幕僚官员。到了安帝朝时,外戚邓骘在政权蒙受自然灾变之际积极向中央推举了多名政务官员使得这场危机得以消解“人士荒飢,死者相望,盗贼群起,四夷侵畔。骘等崇节俭,罢力役,推进天下贤士何熙、祋讽、羊浸、李郃、陶敦等列于朝廷,辟杨震、朱宠、陈禅置之幕府,故天下复安”[4]可见其所举官员在极短的时间便可以融入朝中体系并开始铺助中央政府的议程,影响力远超出幕府范畴。自后辅政外戚的征辟,往往可以使人直升中央政府要职,若梁商“辟汉阳巨览、上党陈龟为掾属,李固、周举为从事中郎,于是京师翕然,称为良辅,帝委重焉”[4]使有才能的士人有了直至君主身侧的进身通路。当然也必须看到,东汉外戚在选举问题上明显偏向自身亲信与同郡士人,但这是东汉选举制度过于强调举主权力造成的通病,客观上外戚对于士人任官的选举标准多以才能、名望为本,保证了在东汉政权存在的绝大多数时间不至于沦为纯粹的任人唯亲,维护了东汉重视才干的风气。
四、余论
综上所述,东汉的外戚集团在军事上一方面久掌宿卫,保证了东汉中央政府的稳定,另一方面亦曾率部赴边疆,捍卫了整个国家的安全。在政事上对君主进言直谏,保证了在非常时刻的言路畅通,向统治阶级倡导道德自律,使得轻利、忠义的朴素价值观深入人心,且在幼君嗣位时能肩负起过渡统治者的职能,避免了政局的动荡。在选举上亦能任用贤能,给有才学的士人以进仕之路。可以说,在东汉的政治体系中,外戚集团对维系政权稳定发挥了其他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外戚集团不会因时局而变,他们对自己群体政治惯例的破坏,如梁冀结党营私丶滥杀无辜、横征暴敛、侵吞土地,终使皇帝联合宦官将其铲除,开始了宦官专权时代;如何进引外兵入都,参与中央政府政治斗争,最终在自己身死后使得军阀轮流夺权,对地方的统治全然失控,开始了军阀割据时代。最终变质的外戚集团也成为了东汉王朝政治体系崩溃的原因之一,而这一同兴同衰的局面无疑更证明了外戚对于东汉政治稳定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