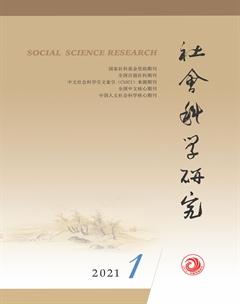后《民法典》时代的中国民法学:问题与方法
〔摘要〕 《民法典》划定了民法教义学的问题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教义学的想象力,但它将促使中国民法学进一步体系化和细密化。《民法典》解释论可推动通说的形成,且可确保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和安定性。民法学的中国元素并不影响法教义学的体系建构,而是本土民法学的重要部分。民法学研究应关注“活法”,尤其是典型案例和交易习惯,并提炼社会事实,将抽象的法规范的适用情形予以类型化。民法教义学特别是其内在体系的形成仰赖其他社会科学,但在形成之后,自足性成为其可欲的目标,往往使其排除其他社会科学。民法教义学不可能也不应拒斥其他社会科学,民法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和多学科的协同研究值得提倡。
〔关键词〕 概念法学;法律历史社会学;法教义学;社科法学;习惯(法)
〔中图分类号〕D9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1-0010-11
〔作者简介〕谢鸿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私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博士,北京 100009。
一、导言
民法学以发现社会运行原理和人类行为规律为己任,近代民法学以及其前身,无一不以此为鹄的。果如此,民法学研究的社会事实和社会行为就具有普适性和无限可重复性,民法学也将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超越地域,“民法学”是唯一的,不存在“德国民法学”“中国民法学”等国别民法学;二是超越时间,可以毫无窒碍地解释因时代变迁出现的新法律问题。但事实并非这般:一方面,各国民法学的主题、内容甚至表达形式都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固有民法学也很难面对时代变迁而岿然不动。
中国民法学的变迁也很能说明民法学本身处于不断的流变中,绝非一成不变。1949年后,中国民法学基本因袭了苏联民法学,但其主题、内容、材料等也有较为突出的中国特色;1978年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民法学逐渐回归正统潘德克顿法学①,但又广泛吸收了英美制度的精华,加之它直面国家和社会转型中的重大民法问题,其中国特色更为突出。
不容否认的是,民法学之所以出现这些差异,主要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围绕本国成文民法典展开,而任何民法典都不可能不体现国别特征和时代色彩。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民法典》的颁行对中国民法学将产生何种影响?民法学应如何回应这种影响?同时,本文也试图从一个民法学研究者的角度,反思和分析民法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前者主要分析中国民法学主题的特殊性,后者主要关注民法学如何运用教义学方法与社科法学方法。本人学植未深,研究这样一个关乎民法学根本发展趋向的主题,倍感绠短汲深,野人献芹,唯望抛砖引玉,就教于前辈时贤。
二、后《民法典》时代中国民法学的问题
(一)后《民法典》时代民法学的问题转型
在《民法典》出台前,我国民法学界盛行立法论,即针对某个制度或规则,以民法理论和比较法为基础,参酌司法裁判和社会现实,提出法律“立改废”的具体建议。其成果的集大成者,是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民法典的学者建议稿。2000年梁慧星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出版后②,起草法律文本学者建议稿蔚然成风,甚至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这样卷帙浩繁的作品,民法学界都贡献了三部。毋庸置疑,这种“立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既是中国民法学无法逾越的必由之路,也是民事立法不可或缺的智力资源,为“科学立法”奠定了基础。《民法典》可谓这种立法论的最大成果。
《民法典》有机整合了现行九部民事单行法,除《民法总则》基本维持原状外,其他八部单行法都做了较大或很大的实质性修改。作为社会领域的基本法,《民法典》通常具有超级稳定性,在很长时期内不可能被改动。这意味着,中国民法学的研究主题必须从立法论转化为解释论。在2011年,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时,就有学者意识到部门法学应向法律体系建成后的解释论研究范式转化。③在《民法典》颁行后,可以预见的是,解释论将进一步取代立法论,成为民法学当仁不让的核心研究范式,解释论也将围绕《民法典》条文确定其主题。
在相应的成文法颁行后,法教义学对法律的立场可概括为:其一,确信法律本身的权威和正当性。若实证法不具有这些属性,则不存在研究的价值。实际上,法教义学被称为具有神学意味的Rechtsdogmatik,因为它探究的恰好是作为国家意志、人民意志的法律。其二,承认“徒法不足自行”。内容再详尽的法律也不可能比民法学理论涉及面更广、内容更细密、主题更繁丰,法律规范的文意、适用条件和情形等,唯有通过解释才能精准实现立法者的意志。
《民法典》编纂追求简明、通俗,虽裨益法律传播和理解,但法律的精确性多少会因此有所流失,故以它为中心建构教义学,以实现民事司法的各种可欲目標,就更为必要。可见,《民法典》的颁行也意味着奠定了中国民法学的体系、结构、内容和问题阈。
与范式民法典相比,我国《民法典》在决定教义学主题方面有其特色:一是它明确了法典的内在体系。这体现为两方面:其第1条确定了立法宗旨;其第3条到第9条规定的七项民法基本原则,将传统民法典作为公理性内蕴的基本原则外化。④这种立法技术为民法学内在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实证法基础。二是其外在体系上尽可能采用“总-分”结构。首先,整体上采用总则编和六个分则编的安排;其次,各编内部也采用了“总-分”结构,完全契合目前中国民法教义学的结构。三是《民法典》未设债权总则编,但将合同编与侵权责任编独立成编。这对中国民法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必须在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中融入债法总则的理论内容;其二,侵权责任编的理论建构任务相对减轻。范式民法典有关侵权责任的规范较少,法教义学必须通过大量类型化研究充实法律规范的文义,甚至进行法律续造工作。而在《民法典》的体例编排下,这种理论工作要轻松很多。
《民法典》并非禁绝了立法论的研究路径。一方面,《民法典》并非尽善尽美,法律漏洞和体系违反等立法瑕疵在所难免,为立法论留下了空间;另一方面,只要最高人民法院还需针对《民法典》作出司法解释,立法论的余地则依然很大,需要围绕司法解释来讨论应规定哪些内容和如何规定,毕竟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造法”的情形并不鲜见。
(二)后《民法典》时代民法学的问题类型与层次
围绕《民法典》建构的中国民法学,或应包括如下几个层层递进的问题类型。
第一层次:民法内在体系诸要素的内涵及其优序。
尽管《民法典》的内在体系已经通过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外显,然而它们都以最抽象的理念和价值作为表达载体。概念越抽象,其内涵和外延就越不确定,如“自愿”“公平”“诚信”等原则,其抽象程度和内涵几乎接近法律的最高价值——正义。公序良俗原则虽诉诸社会底限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准则,但也难以寻求到公认的一般标准;即使它以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为基础,但克减一方基本权利的合同约定是否绝对无效,依然无法一劳永逸地认定,而必须随着社会观念的变迁不断调适。因此,精确厘定民法内在体系的内涵,界定直接适用基本原则且不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的情形并将其类型化,依然是中国民法学的重要任务。
《民法典》内在体系的诸价值之间往往存在冲突,且均为立法者极为珍惜和致力实现的目标,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固定的排序来解决冲突,如自愿原则优于公平原则等。对个案确实需要适用民法基本原则时,也往往难以直接决定适用某个原则,而通常是各原则相互“碰撞”和权衡的结果。未来民法学的发展方向之一,或是借鉴法律论证理论⑤和论题学⑥,尝试提出民事领域适用法律基本原则时应斟酌的各种要素及其一般权重。
与基本原则适用较为类似的是拉伦茨所称的“界定功能型概念”(Functionsbestimmte Begriffge),如法律行为、危险责任、人格权等。和其他民法概念相比,它们更为抽象,蕴含了立法者赋予的丰富价值,如法律行为中的自治和自决,危险责任中的损害公正分摊,人格权中的人格独立、尊严和平等。确定这类概念的内容“必须建立在有决定性的法律原则的基础上。”⑦此外,立法者为扩张立法的体系效益,使法律规则能最大限度适用于社会事实,往往会采用弹性较大的术语,如《民法典》第36条、第83条第2款、第411条、第527条、第1095条、第1125条、第1183条、第1185条、第1207条、第1232条使用的“严重”,虽为普通构成要件的内容,但“严重”如何判断,不通过类型化亦难精确界定。
民法学对内在体系梳理具有两个最重要的意义:一是在解释法律规则时,确保解释结论可纳入立法者预先设定的价值轨道,从而使法律原则之间、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之间以及法律规则之间保持体系内在的融贯性。二是为法律续造提供理论支援,同时对续造的内容进行正当性限制,使其不偏离立法者的规范预期和公众的实践理性。
第二层次:法律规则的适用。
《民法典》规则可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分类,如以是否能单独作为请求权基础为依据分为完全规则和不完全规则等。后者无法单独适用(如定义性规则等),甚至几乎无法适用(如宣示性规则),但大多数规则均采用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模式,可以作为请求权的规范基础。法教义学尤其是实用教义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社会生活中的典型事实纳入法律规则的精密网络和系统,使实用教义学和法律适用高度一致。⑧因此,民法教义学的规则分析包括构成要件(if)和法律效果(then)两部分内容。构成要件是对社会事实的高度提炼,它直接决定社会事实能否被纳入某个规则的适用范围;法律效果则是对纳入规范的社会事实进行法律评价的结果,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
《民法典》一些条文体现了动态体系的立法思想,其目的是在明确但僵化的规则和灵活但抽象的原则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⑨如其第1026条规定: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时,若行为人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应承担民事责任。对行为人是否尽到“合理核实义务”,应考虑内容来源的可信度、对明显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是否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内容的时限性、核实能力和核实成本等因素。对动态体系的功能和适用空间,学界见解不一。反对者认为其“鱼和熊掌”兼得的理想不仅无法实现,反而有损法律适用平等性和安定性⑩;赞成者认为其协调了法律的灵活性和原则性,可将其用于对民法诸多制度、规则和定义的分析。B11动态体系分析要求研究者参酌立法者的原意、构成要件的权重、某一要素的强度是否可弥补其他要件的缺失、可否改变“全有全无”的法律效果等,运用得当并不会产生不良效果,反而会克服法律规则僵化之弊。
第三层次:法律规则的体系效应。
和民事单行法相比,《民法典》最为突出的功能体现为体系效益。《民法典》的体系性意味着《民法典》规定的原則与原则之间、原则与规则之间以及规则与规则之间都存在各种复杂的法律意义脉络和关联,甚至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体系效益要求司法者将个案置于法律规则的网络中,并探求法律规则的适用。在以请求权规范基础为主的研究范式中,研究者不应单独研究某个法律规范,而必须结合其他相关规范进行整体研究(如将债权让与、应收账款质押和保理规则作为一个整体),并充分考虑各规范之间全部或部分的竞合、排斥、互补、并用等关系后,才能得出妥当的研究结论。恰好在这里,民法学体现了它的专业性特征。
就《民法典》体系研究而言,一个特殊问题是《民法典》未设债法总则,然而,这些规范是不可或缺的。它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见于其第468条规定:合同编通则的有关规定可适用于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除非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但这种立法技术难以处理债法总则和合同编的逻辑关系,如对多数人之债,《民法典》第514条到第524条不区分债的发生原因,以各种债为规范对象。这就使债和合同纠缠不清,体系安排明显失当。目前,学界已开始关注实质债总规范的法律适用问题B12,相信未来中国民法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是《民法典》实质债总规则和各种具体之债的体系关联问题。
第四层次:民法和其他法域的体系关联。
民法和其他法律的体系关联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
一是《民法典》和商事单行法的关系。《民法典》与这些法律的适用关系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按照《立法法》第92条,《民法典》作为新法,应优于《公司法》适用;《公司法》作为特别法,又应优于《民法典》适用。这可概括为“新的一般法”和“旧的特别法”的冲突。如《民法典》有关营利法人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责以及清算义务人的规定,都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存在较大差异。此外,民商关系是否以及如何实质区隔,也将是未来民法教义学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
二是《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民法和民事程序法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如基于《民法典》第234条的物权确认请求权,可否提出确认集体土地所有权诉讼?错误登记中的真实权利人,能否对抗登记权利人的借款债权人?担保物权的非诉实现程序如何处理当事人对债权金额的争议?
三是《民法典》和公法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管制国家”的兴起使民法学研究不可能不考虑国家通过公法对民事关系基于各种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的考量而实施的管制,在中国尤其如此。如《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涉及大量“违反法律规定”的内容,它们对侵权责任成立要件的影响如何,如是否影响“过错”要件的认定,都值得深入思考。
(三)后《民法典》时代中国民法学的“中国问题”与“时代问题”
1.中国问题
在任何一个移植外国法的国家和地区,即使忽视法律可否移植这一聚讼盈庭的难题,其民法学也面临建构本土民法学与全面照搬国外民法学的艰难抉择。毕竟再优秀的外国民法学,也总有部分让移植国“水土不服”的内容,而且亦步亦趋他国民法学,多少有损移植国的文化自尊心B13,毕竟民法学(至少其部分内容)并非像数学、物理学那样,是超越时空的、必须服膺的真理。
无疑,中国民法学应以中国问题为重心和依归B14,但这并不否认中国自清末以降继受的德国民法学在中国民法学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是最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承认民法学研究的是社会组成及其运行、社会行为的一般规律,就必须承认潘德克顿学派民法学的很多内容都已是“民法自然法”,尤其有关法律行为的内容。它们是人类共同的民法学财富,具有普适性,当然也是中国民法学的重要内容。然而,任何国家的民法学者都可能发现或创设一些新理论,如德国学者创设缔约过失责任、积极侵害债权等理论。即使在最具有普遍性的交易领域,中国民法学者也并非对德国民法学照单全收,而是对传统民法学有所调整,这些内容可称为“中国元素”,如在不动产物权变动方面,区分农村和城市土地的物權变动模式,强调多元化的侵权损害分配方式和机制等。B15这些要素中,不以特定的中国土壤为前提的部分,本身是对传统民法学的自我修正,有可能登堂入室成为世界民法学的一部分。
民法领域的中国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市场领域内的国家管制问题。这主要涉及《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相较于《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民法典》更尊重契约自由。如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领域,《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许可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时,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这历来被认为是将“无效合同的效力有效化”。《民法典》第793条则进一步删除了“竣工”要件,无论工程是否竣工,只要验收合格,承包人都有请求“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的权利。又如其第760条继受了《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4条,许可当事人在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时,按照合同约定确定租赁物的归属。在法律对法律行为否定性评价最强的无效情形,赋予当事人某些重要约定以法律效力,这对契约自由的捍卫程度可谓无以复加。然而,公法和私法不应相互排除、势同水火,而应彼此补强、共同配合,协力实现全部法律体系内在价值。但是,在研判具体规范时,公法和私法适用时的价值优序还需结合法益权衡、交易安全、善意保护、社会变迁等因素综合权衡,同时避免《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1条、第42条杂糅强制性规范和公序良俗之弊,明确区分违反强行法与悖离公序良俗的不同规范功能。
二是土地权利问题。土地公有制是《民法典》最为显著的中国特色之一,它也决定了土地权利类型和权能的私法配置。《民法典》为实现发展农业、富裕农民、稳定农村的多重目标,通过对“三权分置”的法律安排,增设了土地经营权,并切断了它与农民身份和农村社会治理的关系,使土地权利的流通更为顺畅。而土地经营权到底是物权还是债权、物债区分的核心差异、不同种类的土地经营权的法律适用应否趋同、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的方式及其实现等都是中国特色的民法问题。
三是家事法和继承法领域的固有法问题。人法在各国都具有浓厚的固有法特征,凸显的是强烈的民族文化观念。除对《民法典》“立改废”的规则进行解释论作业外,对遗产管理人等新增制度的具体建构也值得研究;《民法典》未纳入的非婚同居、彩礼、婚约等问题,也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2.时代问题
民法既然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法,研究者就必须敏锐感知、体察社会诸领域的细微变迁,然后评判它对民法理念的影响以及对制度和规则的新需求,最后评估民法应否作出相应的变革以及这种变革的影响。民法学对时代精神(Zeitgeist)的研究似乎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宏观纵论社会变迁与民法的关系。民法学术史上,这类作品首推维亚克尔脍炙人口的《近代私法史》,它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交织的、复杂而恢弘的背景中分析欧陆私法制度和观念变迁B16;其《工业社会和私法秩序》更是以工业社会为背景,揭示潘德克顿学派与工业革命的勾连、古典私法立法时期的社会模式等问题,揭示了民法与社会的互动、互嵌关系。B17二是微观剖析社会变迁对民法制度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经典首推萨维尼煌煌八卷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罗马法改造成适应时代需要的近代民法。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妻荣的 《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它是作者“资本主义发展中私法的变迁”研究的一部分,是民法学结合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的典范,“是日本民法学中水平最高的经典论文”“即使在欧美各国也相当罕见”。B18
《民法典》彰显了信息社会的时代特征。B19囿于信息社会科技、社会和交易日新月异的变化,《民法典》作为基本法,若在理论未成熟时对这些新问题仓促立法,通过法典固定规则,不仅无助于鼓励社会创新,反而会扼杀生机,故它采取了面向长久未来、预留规范空间的立法技术。然而,毋庸置疑,当前技术的发展已使传统民法规则不敷适用,如人工智能等,学界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窘境B20,且展开了充分讨论。如有关人工智能对民商法影响的宏观讨论B21,对人工智能产物的主体人格分析B22,对智能汽车侵权责任的承担规则的讨论B23,尤其是对目前已经深入社会诸多交易领域的算法规制,学者讨论更为深入。B24对传统合同规则在区块链合同的适用B25,也是未来的一个研究重点。中国学者历来关注社会新技术对法律的影响,这一领域或可涌现出世界领先的民法学成果。
三、后《民法典》时代中国民法学的方法
(一)后《民法典》时期的中国民法学与法教义学
民法教义学是民法学最为核心的方法,迄今未遭遇任何强劲挑战,在中国也如此。其原因在于它对法律和法学的理论预设和法学方法,对研究者最有吸引力。
1.民法教义学的两个基本假定
民法教义学暗含了法律自足性的假定,这是法律安身立命的根本。B26它最大的功能是至少在形式上使法律保持中立,远离各种社会力量,使执法者、司法者免受个体情感、价值、偏好的纠缠,充分实现立法意图。为此,法学家必须以现行法的解释为中心建构法学体系,并运用各种解释技术将法律规范的内容更为具体化,以便法律顺利执行、一体适用。
民法教义学假定法学和数学类似,可以在确定社会构成、运行和人类互动行为的公理(即法律基本原则)后,通过公理演绎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出细致入微的规则。这些规则群的基础都是公理,规则和公理共同构成一个倒立金字塔。这种法学观念可被称为“法律公理体系之梦”。B27“法教义学”之名表明它与神学相若,都意味着权威和真理,不过它是以客观社会事实为基础,且以理性发现公理而已。
2.民法教义学的三个核心方法
从潘德克顿学派伊始,民法教义学主要运用如下三种方法来获得知识或建立公理体系。
(1)归纳法
所有学科一定是以抽象性的知识为前提的,不可能是就事论事、讨论具体情境的“决疑学”。民法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获得超越具体实例和事件的知识,即未来可普遍用于该种行为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则。若民法学无法抽象出一般规则,而只分析具体的当事人之间的特定行为或事件,它就不可能具有普遍性,也就无法建构体系;民法典也不可能成功编纂。在美国“法律与社会科学”传统中,针对具体案例所做的研究,如调查消费者对有争议商标的混淆程度,就被认为更接近于事实,而不是法律或法學的内容。B28
早在潘德克顿学派形成时期,形成法学概念就需经分析、集中和建构(Konstruktion)三个阶段。前两者层次相对较低,“建构”的层次最高:“分析”是将法律规则和社会关系的联合体分为普遍的和特殊的两种,“集中”是对法律进行简化,“建构”作为最高的法学技术,是将法条沉淀为法律概念。B29耶林就借用了康德哲学中的“结合(Aggregat)”概念,认为研究者必须把材料通过各种理性化技术建构为一个脉络体系,否则法学就将成为一个机械的规则集合体,而无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也就无法得到保障。B30
(2)演绎法
在公理体系建构之后,法学发展的方向是将为数不多的公理适用于具体领域中的社会事实,基于公理演绎出具体规则,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这恰好对应于民法学总论-分论的理论结构和层次。事实上,英美法学的发展路径亦相同。庞德就认为,美国古典法学的基本观念是,案件裁决是纯粹理性的、演绎的过程,可通过形式的、机械的决策方法解决;其路径是首先承认一些不证自明的原则,然后为具体案例寻找唯一的、正确的答案。B31可见,经由演绎方法发展法学和通过司法三段论涵摄社会事实,其思路大致相同。
归纳法和演绎法对法教义学最重要的意义体现为扩张、衍生法学知识,使法学具有源源不断的自我生产能力。概念法学的集大成者普赫塔指出,“科学不仅是单纯的接受,它也具有生产能力。法学本身就是法律渊源之一,法律渊源除了习惯法与成文法,还有科学法。”B32耶林认同普赫塔关于法学具有生产能力的见解,认为概念有再生能力,从一个概念可以衍生出其他概念:“概念具有再生性,它们配对并孕育新概念”。B33化学家在已知元素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新的化合物,法学家也可以既有概念为基础,创造新概念与新混合物,故法学可称为“建构法学”。B34
(3)区分法
法教义学主要在两个层次上使用区分法:一是在研究社会事实时,剔除与法律无关的事实和细节(如当事人身份)等,在完成甄别后,相关社会事实通过法学表达为各构成要件。二是按照特定的标准对不同的行为、事件、权利等做出区分,如财产权以物权和债权为基本类型、行为分为表意行为和非表意行为等,这种区分在民法教义学中比比皆是。区分意味着法学体系可以通过不同层级的抽象,不断对被区分的概念进行归并,建构层层递进的概念,直到无法抽象为止,比如“人”“法律行为”和“物”等。以不同抽象层级的概念为基础,可以建构层次清晰、结构对称的民法学体系,体系也进一步区分为总体系、大体系和小体系,形成体系金字塔。这种方法同样也是美国法学的基础。霍维茨指出,19世纪美国法学是以“分类心智(categorical mind)”和“分类思想(categorical thinking)”为基础的。B35事实上,所有的社会科学甚至人类生活都必须对事物进行区分,以便确定事物的秩序。
(二)后《民法典》时代的中国民法学与社科法学
1.社科法学的由来
在1908年的Muller v. OregonB36案中,美国法院第一次采用了统计学和医学等学科的成果,确认限制妇女最长工作时间的州成文法有效。该案的事实是:1903年,俄勒冈州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工厂、洗衣店雇用的女性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0小时。1905年,俄勒冈高等法院判决一名洗衣店老板因违反该法令应受惩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妇女承担抚育下一代的社会责任,其角色具有特殊性,故州议会对妇女特殊保护的立法并不违宪。本案的律师布兰代斯(Brandeis)提交了长时间工作对妇女存在不良影响的哲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领域的证明材料,并得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可。在1970-198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很多裁决均采用了社科研究成果B37,美国法学家也逐渐运用交叉学科方法研究法律现象。这主要体现为美国法学中的各种“法律与……”(lawands),如法律与哲学、法律与历史、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文学、法律与音乐等。
“社科法学”在中国被用于指称使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来研究法学的方法。它强调法学研究应结合定性与定量、事实与理论、经验研究与规范分析。B38当然,用它来笼统指称已相当成熟的法社会学、法经济学并不妥当,可能混淆社科法学的不同研究进路和分化功能。B39
2.社科法学的理论预设
社科法学的理论预设包括:
一是法律调整的是社会行为,而社会行为必然具有意义(Sinn),是人的理性、情感、偏见等主观世界的产物,而并非单纯的身体动作。德国理论传统中的“精神科学”(狄尔泰)、“两种科学”(斯诺)、“理解社会学”(韦伯等)的出发点都在于此。对行为的意义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且均可为法学和法律提供智力支持,如法律可借鉴经济学对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制定激励或遏制人实施某种行为的规则,充分实现立法者追求的法律规范的社会效果。可以说,没有一个社会领域是任何学科的禁脔,可以排除不同学科不同侧面的研究。在美国,一些社会心理学家、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关注法律决策过程,尤其陪审团的决策。B40
二是法律是社会的一部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法律和社会相互嵌入,根本不可分割,故法律绝非独立的、封闭的系统。更重要的是,法律自身绝无可能为其提供正当性源泉,而必须借助法律以外的正当性源泉,如神启、功利(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等)、哲学(自由意志)、伦理等:“法律是一个空容器,需要依靠其他学科来填补其实质性知识。”B41如法律调整医疗,但法律人不是医生;法律规范商业行为,但法律人不是商人;法律规定精神病人免责,但法律人并不是精神病专家……舍弃其他学科的洞见,法律难以获得正当性。
三是法律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法学家很早就攀附自然科学以获得“科学”资格,然而并未如愿。在工业革命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及其成果确定性的崇拜和迷恋,使法学本身是不是一门“科学”都成为反复被讨论的问题。这表明,立法和司法都很难精准地把握人类行为的规律,并作出妥当的安排和裁决。通过发挥社会科学在法律中的作用,正确立法和妥当司法(尤其是疑难案件)的可能性将得以提升。另一方面,社科法学乐观地相信,社会科学家已经了解了人类的决策过程,甚至可以通过模型来预测看似非理性的、随机的行为。B42这种信念源于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独断性权威。对法律人而言,援用社会科学作为论据来支持其决定,可以隐藏这些决定背后真正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基础。
3.社科法学的方法论
社科法学涉及法学和众多社会科学的交叉,不同社科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并不相同,但社科法学的共同方法论或可概括为语境论。B43法教义学是一种典型的文本(text)研究,通过文本不断衍生新内容,但实际上新内容都暗含于已有内容,不过是对已有内容进行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而已。语境论强调法律与其社会土壤的亲和关系,关注法律文本的语境或脉络(context)。早在潘德克顿学派形成时期,德国学者就区分了两种法律史:内史(innere Geschichte)是指典章制度的历史,研究法律文本;外史(aeussere Geschichte)是指法律与经济、社会、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的互动历史。“它不是按照编年史来阐述法律与习惯的来龙去脉,而是要阐释法律的历史变迁。” B44 在其他法学领域,只要考虑法律如何演变和如何适用,法学就不可能不考虑社科法学的思路,从而为这些基础法律问题提供答案。B45
“法律和……”研究不仅为立法、司法提供了智力支持,使裁决结果更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而且其诸多分析都可能让法律人产生“知识上的震惊”。如对“法律与情感”的研究表明,在传统观念中,法律是中立、公正和冷静的,尽可能排斥了法律人的情感,尤其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的情感。然而,立法者可能控制情感,如通过操纵羞耻、悔恨等情绪以确保行为人遵守法律,实现法律对社会的控制;通过婚姻文化可以加强对同性戀的谴责,强化异性婚姻观念。B46
(三)后《民法典》时代的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互动
前文从一般理论层面讨论了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互动的必然性,这里以民法学为例再予以说明。两者在民法学中必然互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法是社会基本法,很难想象民法学家不关注社会问题,不了解布帛菽粟和人们的日常行为。如在日本,“民法与社会”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并涌现出我妻荣、星野英一等学者的杰出作品。B47下文以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为例进一步具体说明。
除立法者基于各种公共政策做了不同的规定之外,法律上的损失应是全部赔偿。依据《民法典》第584条第1款,违约损害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依据其第1184条,侵害财产的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这些规定确立了赔偿标准和计算方法,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损害赔偿数额往往很难精确确定,尤其是在没有相关的市场和交易存在,以及其他需要予以斟酌的特殊情况时,司法实践往往诉诸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但评估机构的评估方法和计算结果也难称准确。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则更难以确定。在美国,陪审团确定的惩罚性赔偿额往往会引发争议,对其他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也同样如此。如人们愿意支付多少钱来保护两千只鸟,或者因疏忽行为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被告应赔偿多少。B48对人身损害赔偿,采用一次性支付还是定期金支付方式,理论上也存在争议。B49在这些情形,法学不借助其他学科基本无法准确量化损害赔偿数额。
社会科学的成果通常被视为和自然科学一样,是客观的、中立的、有效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法学应将其视为事实还是法律?从理论上说,社会科学更类似于“法律”(规律),而不是事实,因为事实总是特殊的、不断变化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学就必须对社会科学的成果亦步亦趋,相反,它可以结合自身的内在体系、法益类型、公共政策等予以灵活运用。这里以无行为能力人的年龄设置为例进行说明。在《民法总则》起草过程中,各界对降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年龄门槛达成了共识,但对《民法通则》规定的十周岁降低到六周岁、七周岁还是八周岁,众说纷纭。B50美国对未成年人的行为能力也存在争议。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开始研究青少年心智能力。结果表明,11岁或12岁的青少年具有一定的决策能力,14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具有与成年人相同的认知决策能力,能够理解相关信息,权衡风险和收益,并为其决策提供与成年人相同的合理推理,甚至可以在听取医疗问题的描述后,做出医疗选择。一些社会科学家由此认为,青少年应获得知情同意权。美国心理学协会提交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庭之友”摘要文件甚至认为,应该允许青少年同意堕胎。然而,法律不仅要考虑未成年人实际的心智能力,还需要综合权衡其情感、欲望、未来的身心健康等因素,以保护其不受成年人的伤害。B51可见,立法者完全可以在斟酌各种因素后,设定行为能力年龄的门槛。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民法学必然以民法学固有的理论争议和实践问题为导向,以解释论为中心建构本土民法学。社科民法学在短期将继续无人问津或门可罗雀,甚至被目为异端,然而,它带给学界的不只是知识上的“震惊”或对学科的自我省察,还包括推动民法学的想象力、拓展民法学的主题、增强民法学的深度和广度等好处。因此,多元化的民法学既值得期待,也值得鼓励。
① 孙宪忠:《中国民法继受潘德克顿法学:引进、衰落和复兴》,《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② 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③ 陈甦:《体系前研究到体系后研究的范式转型》,《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
④ 方新军:《内在体系外显与民法典体系融贯性的实现——对〈民法总则〉基本原则规定的评论》,《中外法学》2017年第3期。
⑤ 理论上的尝试,如李勰:《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以Alexy的原则理论为视角》,《人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1期。
⑥〔德〕特奥多尔·菲韦格:《论题学与法学——论法学的基础研究》, 舒国滢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
⑦〔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譯,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05页。
⑧〔德〕罗尔夫·施蒂尔纳:《德国民法学及方法论——对中国法学的一剂良药?》,黎立译,方小敏主编:《中德法学论坛》第1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⑨〔奥〕瓦尔特·维尔伯格:《私法领域内动态体系的发展》,李昊译,《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4期。
⑩ 解亘、班天可:《被误解和被高估的动态体系论》,《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
B11 比较典型的作品,如李昊:《危险责任的动态体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尚连杰:《缔约过程中说明义务的动态体系论》,《法学研究》 2016年第3期。
B12 于飞:《中国民法典实质债法总则的确立与解释论展开》,《法学》2020年第9期。
B13 谢鸿飞:《一个法学家眼里的世界、人类与法》,《中外法学》2000年第3期。
B14 王利明:《构建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5年第1期。
B15 王轶:《论中国民事立法中的“中国元素”》,《法学杂志》2011年第4期。
B16〔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上下)——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B17 Franz Wieacker,Industriegesellschaft und Privatrechtsordnung,Scriptor Verlag Kronberg/Ts.,1974.
B18〔日〕星野英一:《我妻荣先生其人与其业绩》,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地位》,王书江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B19 谢鸿飞:《〈民法典〉制度革新的三个维度:世界、中国和时代》,《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4期。
B20 王利明:《人工智能时代对民法学的新挑战》,《东方法学》2018年第3期。
B21 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
B22 石冠彬:《人工智能民事主体资格论:不同路径的价值抉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12期。
B23 许中缘:《论智能汽车侵权责任立法——以工具性人格为中心》,《法学》2019年第4期。
B24 张凌寒:《算法权力的兴起、异化及法律规制》,《法商研究》2019年第4期; 陈景辉:《算法的法律性质:言论、商业秘密还是正当程序?》,《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2期。
B25 夏庆锋:《从传统合同到智能合同:由事后法院裁判到事前自动履行的转变》,《法学家》2020年第2期。
B26 曹险峰、张龙:《法学教学中法教义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贯彻》,《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B27 舒国滢:《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兼谈“论题学法学”的思考方式》,《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B28 John Monahan and Laurens Walker,“Social Authority: Obtaining, Evaluating, And Establishing Social Science In Law,”134 U. Pa. L. Rev. 491(1986).
B29 吴从周:《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探索一部民法方法论的演变史》,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84页以下。
B30 G.F.Puchta,Cursus der Institutionen,Bd.I,Die Geschichte des Rechts bey dem roemischen Volk,3 Aufl. Leipzig,1850,s.101.
B31 Roscoe Pound, “Mechanical Jurisprudence,” 8 Colum. L. Rev. 607 (1908).
B32 G.F.Puchta,Vorlesungen ueber das heutige roemische Recht,3 Aufl. Bd.I,Leipzig,1852,s.39.
B33 Jhering,Der Geist des r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elung,Teil 1,Leipzig,1852,s.29.
B34 R.Jhering,Der Geist des r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elung,Teil 2(2),s.361.
B35 Morton J.Horwitz,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1870-1960:The Crisis of Legal Orthodox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1-17.
B36 208 U.S. 412 (1908).
B37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都使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做出判决。如在Paris Adult Theatre v. Slaton案〔413 U.S. 49 (1973)〕中,首席大法官伯格(Warren Burger)运用行为研究理论,认为各州惩治传播淫秽作品的立法并不涉及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因而也不违宪。在Florida v. Royer案〔460 U.S. 491, 519 (1983)〕中,伯格和奥康纳法官引用社会学调查,认为通过“毒品运送者档案”进行合理搜查的行为并不违法。
B38 侯猛:《社科法学的研究格局:从分立走向整合》,《法学》2017年第2期。
B39 谢海定:《法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考察》,《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
B40 Felice J. Levine, “‘His And ‘Her Story: The Life and Future of the Law and Society Movement,” 18 Fla. St. U.L. Rev. 69(1990).
B41 J.AlExander Tanford,“The Limits of a Scientific Jurisprudence: The Supreme Court and Psychology,” 66 Ind. L.J. 152(1990).
B42 J. Alexander Tanford,“The Limits of a Scientific Jurisprudence: The Supreme Court and Psychology,” 66 Ind. L.J. 137(1990).
B43 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B44 Dozenten Taranowsky,Leibniz und die sogenannte aeussere Rechtsgeschichte,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uer Rechtsgeschichte( ZRG 40),1906,s.192.
B45 张泰苏:《自足的社科法学与不自足的教义学》,《北大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
B46 Susan A. Bandes ed.,The Passions of Law,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B47 章程:《日台民法学坛过眼录》,《北航法律评论》 2015年第1期。
B48 Neil Vidmar, “Juries Dont Make Legal Decisions! And Other Problems: A Critique of Hastie et al. on Punitive Damages,” 23 Law & Hum. Behav. 705, 705 (1999).
B49 Cass R. Sunstein,“The Future of Law and Economics: Looking Forward: Behavioral Analysis of Law,” 64 U. Chi. L. Rev. 1194(1997).
B50 就此争议,笔者印象深刻的是:2016年11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总则(草案)》,笔者参加的分组讨论会议上,一位代表依据教育部有关小学生识字量的要求来说明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建议将十周岁的门槛下调为八周岁。
B51 Richard E. Redding,“Reconstructing Science Through Law,” 23 S. Ill. U. L. J. 585(1999).
B52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Xin He, Lungang Wang and Yang Su,“Above the Roof, Beneath the Law: Perceived Justice behind Disruptive Tactics of Migrant Wage Claimants in China,”47 Law & Society Rev.703(2013).
B53 徐國栋:《民法哲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
B54 参见简资修:《经济推理与法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张永健:《物权法之经济分析:所有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B55 参见陈小君等:《田野、实证与法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体系构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小君等:《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法律制度研究:村庄经验与域外视野》,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
B56 吴汉东、易军、高飞:《民法学方法论——从学术论文撰写看中国民法之发展》,陈小君、张红编:《私法研究》第1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
B57 管兵:《农村集体产权的脱嵌治理与双重嵌入——以珠三角地区40年的经验为例》,《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6期。
B58 郭台辉、周浥莽:《历史社会学能化解学科之争吗?——基于西方学术史的结构主题模型分析》,《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3期。
B59 David Nelken,“Social Science in the Law: Theoretical Issues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Can Law Learn From Social Science?” 35 Isr. L. Rev. 205(2001).
B60 Jeremy A. Blumenthal,“Law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2 S. Cal. Interdis. L.J. 9(2002).
B61 德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法经济学作品,如〔德〕舍费尔、奥特:《民法的经济分析》,江清云、杜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B62 钱一栋:《规则至上与后果主义的价值理由及其局限——从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看当代中国司法哲学》,《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B63 缪剑文:《缪剑文先生的信》,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徐国栋:《在知识、意见与无知之间的法学论文——对缪剑文先生批评的答复》,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1卷。
B64 J.M. Balkin,“Interdisciplinarity as Colonization,” 53 Wash & Lee L. Rev. 949(1996).中国也有学者从这一角度分析刑法学科中的权力话语。参见孙运梁:《“权力-学科”规训下刑事法学科的产生、嬗变及其整合——以“权力-学科-知识”理论考察刑法知识形态的尝试》,陳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B65 日本刑法和民法学者的有益尝试值得借鉴,如〔日〕佐伯仁志、道垣内弘人:《刑法与民法的对话》,于改之、张小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责任编辑:周中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