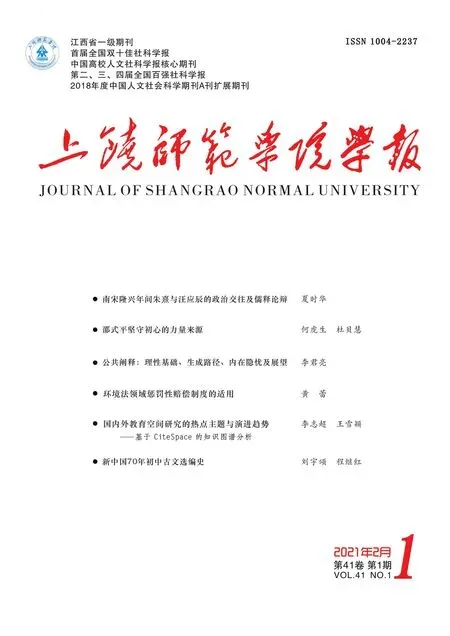论朱熹《家礼》中“家”的政治伦理学内涵
陈力士
(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上饶334001)
关于朱熹《家礼》,学界研究多聚焦于“礼”,从礼学思想、宗族文化、礼教价值等角度开展研究;而较少关注“家”,据笔者考察,目前学界还没有就《家礼》中“家”展开系统研究的论文。因此,本论文将从政治伦理学角度切入,就朱熹《家礼》中的“家”展开研究,探讨其伦理、宗教、政治内涵。
一、《家礼》中“家”的伦理内涵
《家礼》为施之于“家”之“礼”,“家”为“礼”的承载空间,是一个“守名实”的伦理空间。且看《家礼》对“家”的描摹。
(一) “家”的成员与空间
《家礼》描摹的“家”,其成员论及五代。且看《家礼·通礼》的两则材料:
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为四龛,每龛内置一桌。大宗及继高祖之小宗,则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1]876
但于皇高祖考、皇高祖妣,自称“孝元孙”;于皇曾祖考、皇曾祖妣,自称“孝曾孙”;于皇祖考、皇祖妣,自称“孝孙”;于皇考、皇妣,自称“孝子”[1]879。
从宗子往上溯,己辈(宗子)、父、祖、曾祖、高祖,家庭成员论到五代。从高祖往下论,己辈(高祖)、子、孙、曾孙、元孙(宗子),家庭成员也论到五代。若以宗子上溯下论,死生相承,则有高祖、曾祖、祖、父、己辈(宗子)、子、孙、曾孙、元孙,家庭成员可论及九代。就一代人而论,家庭成员,除宗子外,有其妻(妾)、兄(嫂)、弟(弟媳)、姊、妹。九代相承,构成了累世同居①关于“同居”,时亮这么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同居’,与今天社会上对这个词的理解差别很大,指的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兄弟子孙们不但居住在一起,而且没有经过民间或官方的分家手续,在法律上仍然维持着一个‘户’,其中大的同居家族可以达到上下数代,人口达到数千人”(时亮:《<朱子家训 朱子家礼>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23页)。邢铁指出,古代的“同居”之家,是介于家庭与家族的特殊家庭结构,“家庭只含有直系血缘关系,家族则含有旁系血缘关系;介于两者之间的还有一种以直系血缘关系为主,稍稍扩展到旁系的家庭结构模式,即同一个祖父或曾祖父的所有的子孙都不分家的大家庭,社会学上称作‘联合家庭’,我国古代称作‘同居共财’‘累世同居’”(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41页)。之家。
《家礼》所描摹的“家”,为(同一高祖之后代)累世同居、生活的场所,它包括了“仓廪厩库庖厨舍业田园”[1]880等空间。“家”的重要活动空间有祠堂、宫室、墓所。
祠堂为存放先祖神主(牌位)的地方,是“家”最重要的活动空间。祠堂可三间可一间,《家礼·通礼》写道:
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间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1]875
祠堂是宗子带领家众正至、朔望参拜先祖的地方,是家族成员离家、归家须瞻拜的地方,也是生者与死者“对话”的地方。家庭成员“出入必告”:
主人、主妇近出,则入大门瞻礼,而行归亦如之。经宿而归,则焚香再拜。远出经旬以上,则再拜焚香……而行归亦如之……经月而归,则开中门,立于阶下,再拜,升自阼阶,焚香告毕,再拜降,复位再拜。余人亦然,但不开中门。[1]876-877
宫室,包括堂、房、室,是家族成员居住、活动的地方,是“家”的主体空间。宫室包括了祠堂,《家礼·通礼》开篇即说:“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1]875。《家礼》提及的厅事、中堂、书院、庭、中庭、私室、寝处、房、庖厨、浴室、厕等,皆是“宫室”的组成部分。
墓所、幽宅,是家族逝者埋葬之地,是“家”的延伸空间。孝子重视墓所,《家礼·丧礼》写道:“三月而葬,前期择地之可葬者”[1]914,“然孝子之心,虑患深远,恐浅则为人所抇,深则湿润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择地也”“维五患者不得不谨”[1]915,“所谓五患者,沟,渠,道路,避村落,远井窖”[1]916。每年三月上旬择日,宗子率众子弟墓祭,瞻扫封茔,献祭参拜,感慕先人。
(二) “家”的空间伦理
《家礼》中的“家”,是以宗子为家长,众多家族成员聚居之地。日常、冠、婚、丧、祭活动,宗子处尊位;家庭成员的空间位置,如东西、左右、前后、内外等,有着相应的规定。
其一,东西与夫妇有别。《家礼》用“东西”一组方位词,规定“家”中夫妇、男女在婚、丧、葬、祭活动中应处空间位置,如:
凡升降,惟主人由阼阶,主妇及余人虽尊长亦由西阶。[1]877
(女方)父坐东序,西向;母坐西序,东向。[1]898
妇从者布婿席于东方,婿从者布妇席于西方。[1]899
主人、诸丈夫立于圹东,西向;主妇、诸妇女立于圹西,东向。[1]920
主人立于门东,西向,众丈夫在其后。主妇立于门西,东向,众妇女在其后。[1]939
一般说来,东,如(上列五则材料)阼阶(东阶)、东序、室东、圹东、门东,为宗子、男性家庭成员所处位置;西,如(上列五则材料)西阶、西序、室西、圹西、门西等,为主妇、女性家庭成员所处位置。男东女西、夫妇有别,是《家礼》中“家”显在的空间伦理。
其二,左右前后与尊卑长幼。《家礼》用“左右”“前后”两组方位词,规定了在婚、丧、葬、祭活动中,“家”中夫妇、男女们应处空间位置。
丈夫处左,西上;妇人处右,东上。[1]884
共拜家长毕,长兄立于门之左,长姊立于门之右,皆南向。诸弟妹以次拜讫,各就列。丈夫西上,妇人东上,共受卑幼拜。[1]884
凡屋之制,不问何北向,……左为东、右为西。[1]876
“左右”通“东西”,“男东女西”和“男左女右”一样,也表夫妇有别。
瞻拜、祭祀活动中,夫、妇应遵守男左女右的空间秩序,族中男性间、女性间如何序立呢? 这就关涉到“左右”和“前后”的空间秩序。看两则材料:
若丧主非宗子,则宗子主妇分立两阶之下,丧主在宗子之右,丧主妇在宗子妇之左,长则居前,少则居后,余亦如虞祭之仪。[1]926
主人北面于阼阶下;主妇北面于西阶下。主人有母,则特位于主妇之前。主人有诸父兄,则特位于主人之右少前,重行西上。有诸母、姑、嫂、姊,则特位于主妇之左少前,重行东上。诸弟在主人之右少退。子孙、外执事者在主人之后,重行西上。主人弟之妻及诸妹在主妇之左少退。子孙妇女、内执事者在主妇之后,重行东上。[1]877
瞻拜、祭祀活动,男性以左(东)为尊(正)。宗子居左(阼阶),丧主和诸父、兄、弟、子、孙,位于宗子之右。宗子因嫡出、主家,居正为尊;丧主、诸父、兄、弟因庶出,居旁为卑。瞻拜、祭祀活动,女性以右(西)为尊。主妇居右(西阶)表尊正,丧主妇以及诸母、姑、嫂、姊、妹、孙妇、孙女,位于主妇之左,为卑。瞻拜、祭祀活动,辈高、年长者在前,辈低、年幼者居后。丧主、宗子诸父兄辈高、年长而身卑于宗子,因而位于宗子之右少前。宗子诸弟,因年幼、身卑于宗子,而位于宗子之右少退。诸母、嫂因其夫,姑、姊因自身,年长而身卑于宗子,而位于主妇之左少前,弟妻、诸妹因年幼身卑,位于主妇之后。
空间位置“左右”关涉尊卑,“前后”关涉的长幼。左右前后与尊卑长幼,构成《家礼》中“家”又一显在的空间伦理。
其三,内外与亲疏有别。《家礼》中,“家”分内外,有两层含义:第一,指物理空间的,家宅之内外;第二,侧重于心理空间的,指家族之内外。家分内外、亲疏有别,也是《家礼》显在的空间伦理。
第一,从物理空间上看,《家礼》通过禁避,将家宅分割成内外,规定了“家”中男女活动空间,圈限了女性,确保了“家”之血统的纯正性。《家礼·司马氏居家杂仪》这么描摹:
凡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铃下苍头,但主通内外之言,传致内外之物,毋得辄升堂室,入庖厨。[1]883-884
中门成了家宅内外的界限,连送嫁,“诸母姑嫂姊送至中门之内”[1]898-899。
第二,从心理空间上看,《家礼》依血统区别对待内外亲属。男儿纳内室,承己家血统,女儿嫁外郎,承他姓血统。宗亲(诸儿及其妇、后代)聚居“家”内,为同宗内亲;婚亲(诸已婚女及其夫、后代)别居他家,为异性外亲。如:
别设帷以障内外。异性丈夫坐于帷外之东,北向西上;妇人坐于帷外之西,北向东上。[1]904
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及女子已婚嫁者,皆不被发、徒跣。[1]902-903
在丧礼中,宗亲居帷内、姻亲居帷外;已婚女儿无须“被发、徒跣”,不用像儿子那样,为亲生父母承重孝。亲生儿女区别对待——男内女外、男亲女疏。“家”分内外,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区分,更是心理空间的区分。
综上所述,《家礼》中所描摹的“家”,其伦理内涵为:“家”为家族之家,是家族成员(同一高祖父所有子孙)居住的宫室,是家族成员在日常、冠、婚、丧、祭中,遵守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嫡尊庶卑、亲疏有别等伦理规定,按东西、左右、前后、内外等空间秩序列次,落实“名分”的伦理空间。
二、《家礼》中“家”的宗教内涵
《家礼》为施之于家族之“礼”,“家”是施行宗子法、教育家族成员的空间,是一个“崇爱敬”的宗教空间。下面从宗法、教育两个方面,看《家礼》对“家”的描摹。
(一) “家”之宗子法
《家礼》所呈显的“家”,是讲宗子法的宗族之家。有宗法,家才传而不散,宋人张载说:“若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2]。《家礼》中的宗子法,是确立世嫡宗子的家主地位、赋予宗子统宗聚族的伦理规定。何为“宗子”? 《家礼·通礼》写道:
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1]875-876
支子不祭。故今专以世嫡宗子夫妇,为主人、主妇。[1]878
主人,谓之宗子,主此堂之祭者。[1]876
“宗”强调了父系的血脉传承,宗子为守祠堂、主祭祀的嫡长子。“家”之宗法如何施行的,宗子如何统宗、聚族的呢?
其一,宗子统宗。宗子为一“家”之家长,在家众中地位最为尊高:
(祠堂瞻拜)凡升降,惟主人由阼阶,主妇及余人虽尊长亦由西阶。[1]877
(冠者见于尊长)若非宗子之子,则先见宗子,及诸尊于父者于堂,乃就私室见于父母及余亲。[1]892
(婿往见妇之父母)妇父非宗子,即先见宗子夫妇[1]901
“家”中尊长的地位低于宗子,就宗中小辈而言,其亲生父母的地位也低于宗子。
宗子带领家众四时祭祖,除了三月在墓所祭祀,其余皆在祠堂中进行,由宗子主祭。正至、朔望,宗子聚家众于祠堂参拜先祖。家庭成员有“事”,则通过宗子祭、告祠堂祖先。非宗子,则不敢于祠堂祭祖:
非嫡长子,则不敢祭其父。[1]876
非宗子之子,则宗子告于祠堂。[1]898非宗子之女,则宗子告于祠堂。[1]899
这里的“事”指家庭成员封官、贬降、追赠、冠婚以及宗子嫡长子满月等大事,由宗子拜祭、祝执版跪读。“家”之宗法,赋予宗子家长身份与主祭特权。宗子通过祠堂、祭祀权,统领同一高祖父所有子孙后代。
其二,宗子聚族。作为家长的宗子,掌控了家中的经济权和管理权。《家礼》这么写道:
初立祠堂,则计见田,每龛取其二十之一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后凡正位祔者,皆放此,宗子主之,以给祭用。[1]876
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授之以事。而责其成功。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费,禁止奢华,常须稍存赢余,一备不虞。[1]880-881
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1]881
宗子主祭田之给用,管理家中日常之开支,为不虞之备而存赢余,牢牢掌控“家”中的经济大权;宗子“御群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授之以事”,族中大小事须咨禀于宗子,牢牢掌握了“家”中管理权。“家”之宗法,赋予宗子经济权和管理权,使宗子成为聚族而居之“家”的主事人。
概而言之,《家礼》中“家”之宗子法,赋予嫡长子宗子身份,使其主家、主祭,掌控家中的经济权、管理权;宗子统宗聚族,“号令出于一人,家政始可得而洽矣”[1]881。
(二) “家”之教育
“家”对于居住其中的家族成员而言,是一个教育空间。《家礼》以礼教治家,在“家”这一教育空间中,将“名实之守”化为“爱敬之实”。下面从“家”之教育的在场熏陶、现实观照两个层面进行论说。
其一,家风——“家”之教育的在场熏陶。家族成员居身于“家”这一“宗教”空间,通过在场熏陶,家族成员养成重孝敬祖、重德善教的家风。
重孝敬祖的家风。《家礼》之“家”,父母在世,早晚侍奉;父母逝世,治丧、墓葬、守孝、奉神主入祠堂;四时祭先祖,正至、朔望拜先祖,有事告先祖。《家礼》言,“夫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1]881,不忘出身,感恩父母,由孝顺父母推及到崇敬祖先。崇孝敬祖的家风,通过上一代的力行、言传、身教,使下一代明其义、付于行。《家礼》充分发挥了“家”这一“宗教”空间的场效应。
重德善教的家风。“家”之嫁男娶女,放眼将来,重德性,看家教,不盲目攀富贵。《昏礼·议昏》引用司马光的话:
司马公曰:“凡议昏姻,当先察其婿与妇之性
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贵。婿苟贤矣,今虽
贫贱,安知异时不富贵乎?苟为不孝,今虽富盛,安知异时不贫贱乎?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
慕其一时之富贵而娶之,彼挟其富贵,鲜有不轻
其夫而傲其舅姑;养成骄妒之性,异日为患,庸有
极乎?借使因妇财以致富,依妇势以取贵,苟有
丈夫之志气者,能无愧乎? ……”[1]895-896
《家礼》重视家族儿童教育,引入了一套系统的家教法。《通礼·司马氏居家杂仪》这么写道:
凡子始生,若为之求乳母,必择良家妇人稍温谨者。子能食,饲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万福、安置。稍有知,则教之以恭敬尊长;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六岁,教之数。与方名。男子始习书字;女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自七岁以下,谓之孺子,早寝晏起,食无时。八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以让。男子诵《尚书》,女子不出中门。九岁,男子诵《春秋》及诸史,始为之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戎》之类,略晓大意。十岁,男子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诵《诗》《礼》《传》,为之讲解,使知仁义礼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读《孟》《荀》《杨子》,博观群书。凡所读书,必择其精要者而读之;其异端非圣贤之书传,宜禁之,勿使妄观,以惑乱其志。观书皆通,始可学文辞。女子则教以婉娩,听从,及女工之大者。未冠笄者,质明而起,总角、面贵面,以见尊长。佐长者供养,祭祀则佐执酒食。若既冠笄,
则皆责以成人之礼,不得复言童幼矣。[1]885-886《家礼》重家法,善家教,从出生到成人,从言行教化到知识教育,环环相扣、面面俱到。
其二,家德——“家”之教育的现实观照。家族成员居身于“家”这一教育空间,通过现实观照,家族成员体悟并践行孝顺与仁义等家德。
“家”之孝顺。“家”之孝,主要通过子、妇日常侍奉父母、姑舅的言行举止来体现。孝,在行为上主要体现为早晚请安、按时备食、病时不离。孝,在态度上体现为恭谨、不违命、不违志,《通礼·司马氏居家杂仪》这么描摹:
(侍于父母、姑舅之所)容貌必恭,执事必谨。言语应对,必下气怡声;出入起居,必谨扶卫之。不敢涕唾、喧呼于父母、姑舅之侧。父母、姑舅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1]882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记而佩之,时省而速行之,事毕则返命焉。[1]882
凡子事父母,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1]883
顺,主要体现为顺从、柔谏、曲就于父母,《通礼·司马氏居家杂仪》这么描摹:
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则和色柔声,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许,然后改之。若不许,苟于事无大害者,亦当曲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己志,虽所执皆是,尤为不顺之子,况未必是乎?[1]882
凡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1]883
“家”之仁义。从对待子妇、仆人的行为上,可现实观照到“家”之仁义。《通礼·司马氏居家杂仪》写道:
凡子妇未敬未孝,不可遂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后怒之;若不可怒,然后笞之,屡笞而终不改,子放妇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礼也。[1]883
凡女仆年满,不愿留者,从之。勤奋少过者,资而嫁之。其两面二舌,饰虚造谗,离间骨肉者,逐之。屡为盗窃者,逐之。放荡不谨者,逐之。有离叛之志者,逐之。[1]887
凡男仆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禄;能干家事,次之。其专务欺诈,背公徇私,屡焉盗窃,弄权犯上者,逐之。[1]887“家”行仁德,仁厚地处理妇之过,面对子妇之不敬不孝,再三教育而不改才休出,对外不明言妇所犯之礼;对待下人持仁慈的态度,女仆年满随其志愿决定去留,仆人屡犯盗窃才驱逐出家。“家”施义行,是非、奖罚分明;凡下人若有造谗、放荡、离叛、欺诈、徇私、盗窃、弄权等行为,驱逐出家;女仆“勤奋少过者,资而嫁之”,男仆“忠信可任者,重其禄;能干家事,次之”。
综上所述,《家礼》中所描摹的“家”,其宗教内涵为:“家”为宗族之家,是同宗聚居、立嫡长子为宗子统宗聚族、传承有序的伦理空间,是传扬重孝敬祖、重德善教的风气,养成孝顺、仁义行为的教育空间。
三、《家礼》中“家”的政治内涵
朱熹立足实情,将“家国一体”“化孝为忠”“修齐治平”等儒家政治观植入《家礼》中,实现了“家”的伦理政治化、宗教政治化。“家”具有政治内涵。
(一) “家”的伦理政治化
朱熹用“理一分殊”阐释“家国一体”,在“家”中植入“修身齐家治国”的儒家政治观念。
今人观念中,“国”“家”首先是两个描摹空间的概念,“国”的空间大于“家”,“国乃政治共同体,家则为血缘团体”[3]。在传统观念中,“家”专指家室、家人、家族;“国”常指古代国家,“国家”与“朝廷”“天下”①关于“国家”“天下”的概念,笔者采用梁治平《“家国”的谱系:家国的终结》一文的界定:“国家为朝廷,系于一家一姓,原本是家国体制中应有之义”“古人所谓天下,在大部分情况下即指王朝统治下的国家,维其仍非清末时贤所欲建立的现代国家”(详见:《文汇报》2015年5月8日第11版)。有时是同义的。儒家经典中,常将“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如:
正家而天下定矣。[4]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5]
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6]
以上材料,认为治国的基本在于治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观,“家”“国”关联紧密,“国”是扩大化的“家”。这些看法皆内嵌“家国一体”(“天下一家”)的儒家政治观。
从先秦到汉唐,“家国一体”靠的是圣人的教化和劝善。而到了宋代的理学,“形而下的道德劝善,开始具有形而上的理论支撑”[7]。张载用“气化论”将“小家”统协为“大家”(“天下一家”),他在《西铭》中说: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8]
张载的“气化论”认为:人都是由天地之气孕育而成的,都是天地的孩子,民为吾同胞,物与吾同构。从血缘看,“家”为家族团体,是“小家”。从“气化论”角度讲,所有人都是同胞,“家”为“大家”“天下为一家”。天下(国)如一家,君王、大臣依次是“家”之宗子、家相,要用“兼爱”的态度,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天下无血缘关系的长、幼、弱者,因为他们都是“大家”中“我”的兄弟。朱熹用程颐的“理一分殊”注解张载的《西铭》,用哲学阐释“家国一体”(“天下一家”)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哉! 《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盖以乾为父,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9]
“一”为“宇宙之本体”,天地万物其理一也。“一”在不同事物之间的表现是不同的,这就是“分殊”。从统一性讲,“天下”之所以是“一家”(“家国一体”),是因为天下各家皆一理也。从多样性讲,天下各家“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朱熹认为“天下一家”(“家国一体”)是有差异性的同构,唯有圣人才能“合其异而反其同”,以“德”(“不梏于为我之私”)将天下合为一家,实现“家国一体”。
朱熹撰著《家礼》,基于“理一分殊”的理解,通过“家”日修之礼,落实圣人之“德”,将天下各家统协为一家,完成了由“家”到“国”的伦理空间的扩张。在《家礼·序》中,朱熹这么说:
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者,其本也;冠婚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终始,虽其行之又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亦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尤可以复见,而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1]873《家礼》的编撰的目的,就是通过“修身齐家”来“崇化导民”,进而实现治国。天下各家皆落实“礼”之“本文”,“修身齐家治国”落到了实处,“家”扩张为“国家”。从撰著意图上,《家礼》是有目的将“家”之伦理政治化,落实儒家“家国一体”的政治观。
(二) “家”的宗教政治化
如果说,朱熹的“理一分殊”给“家”空间伦理政治化以哲理阐释,解决了儒家“家国一体”的理论性问题,那么,朱熹《家礼》植入儒家“化孝为忠”的观念,将“礼”庶民化,则给“家”宗教政治化以合理性阐释,解决了“家国一体”的现实性问题。
首先,朱熹《家礼》植入了儒家“化孝为忠”的观念,给予“家”宗教政治化以合理性阐释。《家礼·序》中说:“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尤可以复见,而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1]873谨“终追远之心”在《家礼》中呈显为“重孝”,“家”之“孝”是与治“国”相关联。
《家礼》一再强调“孝顺”,要求事父母应恭谨,不违命,不违志。《家礼》特别强调女性的“孝顺”,新娘出嫁前,长辈一再强调的妇德就是“孝顺”,《昏礼·迎亲》这样写道:
(对新娘)父起命之,曰:“敬之,戒之,夙夜无违尔舅姑之命。”母送至西阶上,为之整冠敛帔,命之曰:“免之,敬之,夙夜无违尔闺门之礼。”诸母姑嫂姊送至中门之内,为之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曰:“谨听尔父母之命,夙夜无愆。”[1]898-899“敬”“无违”“谨听”“无愆”等词,强调了妇侍舅姑不仅应落实到日常行为,更应体现为内心的认可,乃至于盲目的顺从。
儒家重“孝”。孔子强调“孝”的政治功用,他说: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10]
《孝经·广扬名》指出“孝”是可移用于“忠”的:
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
悌,故顺可移于长;君家理,故治可移于官。[11]
朱熹深明儒家的“移孝以忠”,他在《孝经刊误》中说:
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12]
“孝”用于事父母,“忠”用于事国君。“孝”何以能移于“忠”? 是因为“孝”“忠”皆是下对上的敬事、听命、顺从。同属上下级、同样的尊卑观念、敬顺心理,是可以迁移的,于“家”呈显为“孝”,于“国”则体现为“忠”。
《家礼》为何重孝顺? 徐公喜如是说:“(《家礼》)重‘孝’旨在移孝作忠,朱子强化伦理纲常中的‘父为子纲’旨在‘借正父子之伦,以严君臣之分’”[13];梁治平如是说:“以孝道为治道,是假定家与国通,礼与法合,齐家与治国并非二事”[14]。《家礼》重孝顺,旨在“化孝为忠”,将“家”之宗教政治化,落实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观。
其次,朱熹《家礼》将“礼”庶民化,解决“家”宗教政治化的现实问题。先来看几则材料:
古礼繁缛,后人于礼日益疏略,然居今欲行古礼,亦恐情文不相称,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令有节文、制数、等威足矣。[15]
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者,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能举其要,而用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熹之愚盖两病焉,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1]873
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1]875
通过以上三则材料可知,有感于古礼的繁缛、俗礼的实用,朱熹“观古今之书”,参详古今之礼,删简、俗化了礼节,使礼能适用于“贫窭者”。朱熹编撰《家礼》,将“家”之礼庶民化了。
《家礼》的庶民化,立足于现实,由“家”及“国”,解决了“家”之宗教政治化的现实性问题。据学者考究,庶民化了的《家礼》“很快便在社会上广泛传布,以至宋元以降,成为一般家庭和宗族公认的治家和行为准则”[16],“明初国家制礼,《家礼》成为修订士民礼文的参考;永乐年间,朝廷更版《家礼》于天下,确定其士庶社会家礼范本的地位”[17]。“家”之礼的庶民化,立足于现实,适应时代,有益于“治国平天下”。
综上所述,《家礼》中所描摹的“家”,其政治内涵为:“家”为国家之家,是一个与“国”同构的政治单元,是个内嵌儒家“天下一家”观念、具有“崇化导民”功用的伦理政治空间,也是个内嵌儒家“化孝为忠”观念、具有“治国平天下”功用的宗教政治空间。
四、结语
“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不同时代的“家”具有不同的内涵。《家礼》所描摹的“家”是家族之家、宗族之家、国家之家。朱熹将“家”设置为联结个人与天下(国家)最重要的纽带,“家”不仅仅是个人居住的空间,也是个人修身、事亲的宫室,还是宗主主事的族居之地,又是君主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政治单元。“家”具有伦理、宗教、政治三重内涵,具备“修齐治平”的功用。
《家礼》广为流传,朱熹所描摹的“家”,成为封建时代(南宋以后)庶民阶层之“家”的基本类型。今人称之为封建礼教之“家”。到了清代,封建礼教之“家”因过分过度讲伦理、死守“名分”,而忽略了“爱敬”,最终走向了“礼教吃人”之路。
现代意义上的“家”指家庭,多指由父母、子女构成的三、五口之家。现代家庭尊重个性,强调人权,“家”不再是联结“个人”与“国家”最重要的纽带,学校、社会分担了“家”的教育与政治功用,“家”的政治伦理地位被弱化。然而,《家礼》所描摹的“家”,其个人与集体融洽的相处方式、崇德善教的家风、死生仪式所蕴含的生命教育是现代家庭所缺乏的。对抗不断滋长的个人主义,避免个体走向虚妄,更好地培养个人的集体观念、家国情怀、责任意识,《家礼》中的“家”值得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