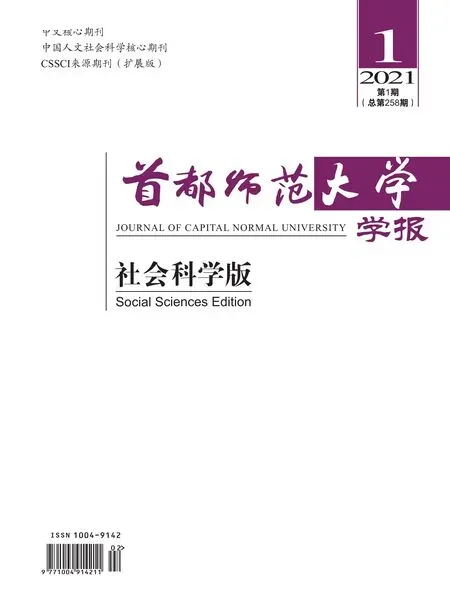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抗日战争
唐剑明
中国抗日战争是20世纪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中日两国出版的任何历史教科书都无法回避的话题。尤其是日本作为抗日战争的侵略一方,对这场战争持有何种态度,便能够反映出日本对侵略行为的态度。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国民教育阶段的基本作用是建立学生正确看待历史的观念。在这一基础之上,才能接着讨论学习上的方法论。日本所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均对抗日战争有所记述,根据不同的立场,措辞有所不同。但是,在对历史本身的叙述上基本都能够做到陈述事实。近年来,随着右翼势力的膨胀,教科书当中有关日军暴行的内容被淡化或从略,一些有右翼背景的历史教科书开始在对事实的叙述上动起了歪脑筋,对一些概念进行断章取义,这是我们必须足够重视和警惕的。
历史教育是国民教育当中的重要环节,它体现着国家的意志,从中折射出现实中这个国家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和认同,并且能够体现出这个国家在培养怎样的未来公民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根据日本的国情,历史教科书均由私有制性质的出版社出版发行,目前正在使用的历史教科书种类繁多。历史教科书均根据文部科学省颁布的初中或高中《学习指导要领》的精神进行编撰。由于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容量远远大于《学习指导要领》,且《学习指导要领》只是以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作为基本立场,提供教材编纂的基本框架,并没有明确规定教材具体内容的价值取向。因此,只要根据其框架安排内容即可。初中方面,目前正在使用的有8个出版社所出版的8种历史教科书。初中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社是东京书籍、帝国书院、教育出版、日本文教、育鹏社、清水书院、学习社、自由社这8家。这8种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在2017年分别是51%、17.9%、14.1%、9.4%、6.3%、0.8%、0.5%、0.05%。其中,在所有的出版社中,育鹏社可视作之前曝光过问题教科书的扶桑社的正统继承者。①2007年,因为教科书编委会的内部纠纷,扶桑社将教科书出版事业全部移交给了子公司育鹏社。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是2008年通过文部省教科书审查合格的历史教科书,与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相同,同为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下推出的历史教科书。需要注意的是,在2009年4月10日举行的文部科学大臣记者见面会上,时任文部科学大臣盐谷立以符合出版程序为由,表态支持上述两种右翼历史教科书。这能够体现出当时日本官方对右翼势力在历史教育领域影响力的态度。②文部科学省:《大臣会见概要(4月10日)》,https://warp.ndl.go.jp/info:ndljp/pid/11373293/www.mext.go.jp/b_menu/daijin/detail/1262899.htm,2009年4月10日。
一、非右翼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抗日战争叙述
日本初中《学习指导要领》当中并没有点明抗日战争的概念,只是进行了如下表述:“通过经济的世界性混乱和社会问题的发生,阐述从昭和初期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为止的我国的政治、外交的动向,以及同中国等亚洲各国的关系,欧美各国的动向,战时国民的生活等,让学生理解从军部的崛起到战争发生的经过和大战灾殃祸及全人类。”③文部科学省:《学习指导要领》(初中),第24页,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new-cs/youryou/chu/__icsFiles/afieldfile/2010/12/16/121504.pdf,2019年3月。显然,同中国的关系在同“亚洲各国的关系”之中也是十分特别的存在。而“从昭和初期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为止”的时间设定则同后面的“战争”以及“大战”对应起来。自然地,“战争”和“大战”并非可以互换的概念,在这里的“战争”显然是包括“大战”当中的太平洋战场的。从《学习指导要领》当中的表述不难看出,对抗日战争的直接记述是不存在的,抗日战争的内容被安排到了“同中国的关系”和“战争”的模糊范畴当中。这样就给予了教科书充分大的叙述空间进行发挥。
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是所有初中历史教科书当中学校采用率最高的一种,因而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有关抗日战争的内容全部安排在了第六章“两次世界大战和日本”④坂上康俊等:《新编新社会历史》,东京书籍2017年版,第195页。的第二节“世界恐慌和日本的中国侵略”⑤坂上康俊等:《新编新社会历史》,东京书籍2017年版,第212页。当中。从章节的安排上来看,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将两次世界大战看作一体的。这样的观点在其他历史教科书当中也有类似的表达,这种观点的好处是能够将两次世界大战的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从宏观的角度更好地理解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但是问题也是存在的,这样以宏观的视角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审视,会使一些历史事件无法得到精确的界定。比如,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在这一问题上,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作出的处理结果同日本主流社会的观点是一致的。教科书跟随欧美国家的基本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是从1939年9月1日德军闪击波兰开始,并不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节点算起。尽管如此,第二节的标题“世界恐慌和日本的中国侵略”依然坦承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第二节的第四目名为“满洲事变⑥即九一八事变。和军部的崛起”。正文内容当中提及“中国越来越加强了从日本手中夺回权益的行动,因此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炸毁了位于奉天郊外柳条湖的南满铁道的线路,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军事行动(满洲事变)”。⑦坂上康俊等:《新编新社会历史》,东京书籍2017年版,第218页。该表述承认了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是关东军,但是“中国越来越加强了从日本手中夺回权益的行动”这一表述显然是在推卸一部分责任,并没有正视中国人民的正当诉求。对“满洲事变”的注释,倒是很好地将日本的真实野心展现出来。注释称:“日本以‘满蒙’为日本的生命线,加强了对满洲的控制。”①坂上康俊等:《新编新社会历史》,东京书籍2017年版,第218页。因此,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已经暗示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所谓“中国越来越加强了从日本手中夺回权益的行动”不过是日本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进行的辩护。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既有军事方面的目的,也接纳了许多来自日本的移民”。②坂上康俊等:《新编新社会历史》,东京书籍2017年版,第218页。
日本由于侵略行为而使得自己在国际社会上遭遇空前的孤立。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在这里的表述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于同年(1936年,笔者注)以对抗共产主义势力的进入为由,同德国签订日德防共协定,接近了法西斯各国。”③坂上康俊等:《新编新社会历史》,东京书籍2017年版,第218页。在这里,至少可以明确的是,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对于法西斯概念的理解是较为广义的,并非停留在狭义的仅仅指代意大利法西斯的那个法西斯概念。在这一点上,第二节第二目当中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标题分别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即很好地印证了这一判断。然而问题在于,意大利和德国均被定义为法西斯,那么日本该如何被定义?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普遍共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均把法西斯作为战争对象。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策源地之一的日本,当然应当被视作法西斯国家的一员。而从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来看,“(日本)接近了法西斯各国”这样的表述显然是将“日本”和“法西斯各国”作为两个对立关系的概念来对待。日本是在“接近”法西斯各国,因而日本同法西斯各国是不同的。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并不愿意承认日本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似乎在努力地从特殊性的叙述入手来强调自己同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距离。当然,这种距离感的基本面是主体性的要求所决定的,课程标准也好,历史教科书也好,只是通过这种距离感来制造概念之间的对立感,最终造成一种特殊性的错觉。暗示个性,必然地会减弱对共性的认知。在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的表述当中,日本已经不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了。
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五目“日中战争④即抗日战争。和战时体制”⑤坂上康俊等:《新编新社会历史》,东京书籍2017年版,第220页。,是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最后涉及抗日战争内容的部分。从该目的标题上来看,“日中战争”是“战时体制”的原因,两者之间是因果关系。教科书对战时体制的描述是:“随着日中战争的长期化,在日本,政府遵从军部的要求在增加军费的同时将国家调整为战时体制。”⑥坂上康俊等:《新编新社会历史》,东京书籍2017年版,第220-221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场艰巨的、长期的战争。第五目第一部分的标题名为“日中战争的开始和长期化”,对应了第五目标题中战时体制的原因。在陈述抗日战争开始的地方,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还特意提及了将中国“满洲”置于控制之下的日本,“又入侵了中国北部(华北,笔者注)”。⑦坂上康俊等:《新编新社会历史》,东京书籍2017年版,第220页。这一表述同“满洲事变”相接,大致讲清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背景。只是,同中国所主张的14年抗战不同,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将抗日战争的开始时间节点定为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件”⑧即卢沟桥事变。。教科书的表述是:“以卢沟桥事件为契机,日中战争开始了。”⑨坂上康俊等:《新编新社会历史》,东京书籍2017年版,第220页。在日语的语境当中,“事变”往往伴随着军事冲突,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战行为事实上即可认为战争爆发。因此“满洲事变”和“日中战争”的表述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因为前者亦可被认为是战争行为的开始,从而被后者所包纳。在日本学术界,“十五年战争”是近现代史研究方面比较主流的提法。内容上包括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乃至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所有战争历史。显然地,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试图以卢沟桥事变为抗战全面爆发的开端,而将九一八事变之后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部分视为中日两国矛盾积累的量变期。可见,教科书的编者在战争定义这一问题上,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存在认知偏差。通过对战争时间长度的重新定义,给学生留下了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之间的时间不是战争状态的印象,一定程度上开脱了侵略战争的罪责。
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在采用率上不及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在日本全国初中的采用率为17.9%,位居所有初中历史教科书的第二位。若是将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与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相加,可以得到近乎70%的数字。因此,这两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在学校教育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能够体现广泛的教育现状。
作为老牌的历史教科书出版社,帝国书院同东京书籍一样秉持着折中的态度,立场基本中立。在教科书叙述的行文上面,可以看出帝国书院版教科书的编写者们更加在意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这一点也体现在标题的设计上面。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同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一样,将“日中战争”的开始时间定为1937年7月。在这一点上,帝国书院和东京书籍的历史教科书编写者们还是严格地遵照了一直以来的历史观念,将全面战争的爆发定为中日之间“战争”的开端。有关抗日战争的所有内容,在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当中都被安排在了第三章“军国主义和日本的走向”中。从标题来看,“军国主义”的提法是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不同于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的地方,帝国书院似乎在中立立场上面更加倾向于东京审判史观的立场,对二战以后国际上的基本认识抱持了尊重的态度。但是,这个标题本身也体现了主体性,包括第四章的标题“在亚洲和太平洋扩大的战线”也是体现了这样的倾向。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内容被安置在了第四章“在亚洲和太平洋扩大的战线”之下。这同课程标准的要求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也同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有了区别。由于对主体性的强调,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更注重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框架下面阐述日本以及日本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联系。在这两个内容当中,日本本身的重要程度是高于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的。
九一八事变的相关内容被放置在第三章的第三节“强化的军部和衰弱的政党”之下,第二节的标题名为“欧美各国选择的道路”,其中的第四部分是“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在这部分内容当中意大利和德国被认定为法西斯主义,教科书当中的表述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推行的独裁体制被称为法西斯主义”。②黑田日出男等:《社会科中学生的历史》,帝国书院2017年版,第217页。后面又说,“以法西斯主义为本的各国同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本的各国之间的对立变得愈加激烈”。③黑田日出男等:《社会科中学生的历史》,帝国书院2017年版,第217页。这一观点契合了西方国家关于二战观念的建构。但问题是,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如何定位战时日本。教科书当中对日本的提法是“军国主义”,这当然也没错。在对军国主义的解说当中,教科书的表述是这样的:“军国主义是一种重视发动战争和提高军事实力的思想。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领域将战争和军队放置在优先位置。”④黑田日出男等:《社会科中学生的历史》,帝国书院2017年版,第218页。这一表述虽然在含义上把军国主义的特征进行了明确的说明,但是并未提及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反倒是,在“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部分当中,对法西斯主义的注释称“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最优先的军国主义性质的独裁政治的体制称为法西斯主义”⑤黑田日出男等:《社会科中学生的历史》,帝国书院2017年版,第217页。,在这当中有军国主义的含义。但是,在这两个概念的注释当中,并没有能够将军国主义放入法西斯主义的余地。反倒是,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具有军国主义特点的“独裁政治的体制”。这样一来,基本的判断就是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同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一样,并没有将战时日本明确确定为法西斯主义。但是至少同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一样,帝国书院版将日本和法西斯主义建立起了一定的关系。从效果上来看,相较于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在国家外交层面上表述“日本接近法西斯各国”,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在概念阐释上的表达更为清晰,也体现出了一种拘谨。
军国主义的基本认识确立了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对于日本的主体性叙述。在第三章第三节“强化的军部和衰弱的政党”当中,“满洲事变和‘满洲国’的建国”被放置在第一目当中。教科书中有这样的表述:“这(满洲事变)是在没有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由军部中的一部分人发起的行动。在不景气当中失去了人们信赖的内阁没有压制军部的力量,提出了总辞职。”这一表述同小节标题保持了一致,并且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另外一部分原因,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则将其归结为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以后,有了从列强手中夺回权益的意愿,并且开始建设与南满铁道并行的线路。①黑田日出男等:《社会科中学生的历史》,帝国书院2017年版,第218页。在九一八事变的问题上,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的态度是坦诚的,叙述也符合基本事实。在九一八事变后建立伪满洲国的问题上,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给出了带上引号的“满洲国”表述②黑田日出男等:《社会科中学生的历史》,帝国书院2017年版,第218页。,同我国的表述保持了最大程度的一致。并且,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也承认了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控制,称“‘满洲国’的实权握在日本手中,产业也被日本控制。并且,在不景气之中日本还从农村向‘满洲国’进行移民活动”。③黑田日出男等:《社会科中学生的历史》,帝国书院2017年版,第218-219页。这样,即承认了侵略中国的事实。
但是,在措辞问题上,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在叙述九一八事变的经过时并没有提及“侵略”二字,并且在对军国主义的注释当中也没有出现“侵略”二字。相较对法西斯主义的注释当中有“侵略”二字,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为什么在提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前提下并没有提及“侵略”?这一点就值得深思了。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压力所留下的痕迹,压力显然是来自于上方的。教科书叙述话语的展开被牢牢地掌握着,甚至教科书为第三节设置的学习课题也是“满洲事变以后,政党政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④黑田日出男等:《社会科中学生的历史》,帝国书院2017年版,第218页。其重点完全落在了日本国内政治斗争上面了。
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在叙述“日中战争”爆发的背景时称:“并未止步‘满洲’,而是也向中国北部(华北,笔者注)派遣了军队。”⑤黑田日出男等:《社会科中学生的历史》,帝国书院2017年版,第220页。在表述当中并没有说明任何缘由。事实上,不作任何辩解的叙述亦是对侵略事实的承认。同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一样,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也将“卢沟桥事件”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在涉及南京大屠杀的部分中,教科书的表述为:“日军也从中国南部(指长三角,笔者注)发动入侵⑥日语表述为“侵攻”。,占领了上海和当时作为首都的南京。在南京,不仅仅有士兵,还有许多平民遭到杀害(南京事件)。”⑦黑田日出男等:《社会科中学生的历史》,帝国书院2017年版,第220页。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并没有像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那样,将“南京大虐杀”⑧即日语所表达的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安排在版面上。这也是因为受到了来自上方的压力。但是,在“入侵”这一用词上更好地表现出了日军的军事行动是侵略性质的。在日语当中,“侵攻”的表现形式如果用在体育比赛上,即意味进入对方半场等场域性的活动;然而用在国际关系的领域就等同于“侵略”的表现形式了。上文提到,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在章节编排上体现出了强烈的日本主体性色彩。位于第三章第四节“突入战争的日本”之下的“日中战争”一目,已经将日本观点下对战争爆发的理解解释清楚了。同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有所不同的是,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第三章第四节之下的一个目来进行处理,其用意在于通过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叙述来更有力地说明战争进入长期化的理由。在这一目的叙述当中,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采用了三段式的叙述手法,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军无法完全占领中国—中国迁都并获得国际援助”。从逻辑上来看,这样的三段式叙述手法有助于学生理清事理,更好地掌握内容。用词上面,教科书在表述国共内战的时候称:“日本加紧入侵的时候,中国方面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铆足了全力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继续打着内战。”⑨黑田日出男等:《社会科中学生的历史》,帝国书院2017年版,第220页。在这句话当中再次出现了“入侵”的表述。但是,这一“入侵”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七七事变以前,也就是说,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承认了在“日中战争”之前就已经有日本发动的侵略行为,包括在第三章第三节当中提及的“占领‘满洲’全部”①黑田日出男等:《社会科中学生的历史》,帝国书院2017年版,第218页。的内容,从侧面支持了14年抗战的新观点。在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容的最后部分,有着这样的表述:“这场战争,从满洲事变开始计算的话,就是一场横跨15年的战争。被日军占领过的中国和东南亚的人们欢天喜地地迎来了解放。另一方面,深刻体悟战败的日本人的心境,由其立场及年龄、职业和地位、性别而各异,但这是一场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伤痕的战争。”②黑田日出男等:《社会科中学生的历史》,帝国书院2017年版,第233页。总的来说,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同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一样,在右翼势力压制之下不得不在一些敏感的地方作出不得已的修改。然而在大的方面,依然能够坚持和平宪法的原则,对战争认识的态度也是较为端正的。虽然囿于主体性③“主体性”一词在日本中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当中经常出现,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而阐发的自主学习和生存的能力,二是作为日本国民的立场所体现出来的以日本为出发点思考问题的素养。详见唐剑明:《日本历史学习指导要领中的全球意识和日本主体》,《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1期。的局限,仍不失为日本编撰水平较高、观点立场基本正确的历史教科书。
二、右翼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抗日战争叙述
最近,日本右翼教科书的采用率逐步上升,尺度也越来越大。以育鹏社和自由社出版的两种初中历史教科书为代表,其内容体现了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真实态度。育鹏社版和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同属于日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④日文是: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旗下。该会所引发的最有名事件即是扶桑社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事件⑤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了翌年度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审核通过名单。在合格的8家出版商中,也包括了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纂、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在内。由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是以挑战现有的教学内容为宗旨,在审议过程中,该教科书就已经引起国内外媒体的高度重视。所以,当文部科学省宣布该书通过之后,更是风波不断。尤其是中国及韩国政府还以例举不满事由的方式,要求修改教科书内容。。
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将有关抗日战争的所有内容均放置在第五章“两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的第二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为止的日本和世界”之下。由于所有的目都是按照从1开始的数字进行排列,不因章节关系重新计算,所以涉及抗日战争的内容分别是第70目“中国的排日运动和满洲事变”、第71目“日中战争(支那事变)”。从以上各目的标题来看,育鹏社教科书在叙事角度上保持了与《学习指导要领》所要求的主体性相一致的姿态,以日本作为主视角来进行叙述。但是,同东京书籍版和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均有所不同的是,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在各目标题用语的设计上显示出了其对侵略战争的不正确认识。第70目的标题“中国的排日运动和满洲事变”,其构建的逻辑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将九一八事变的责任推卸给了中国的排日运动,而绝口不提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第71目“日中战争(支那事变)”,在通用的“日中战争”表述后面特地加上括号中的“支那事变”表述。所谓“支那事变”是1937年9月2日日本内阁经过会议议定的名称,可以被视为军国主义的产物。而“支那”一词,不论历史上是否带有贬义色彩,在如今的年代若是依然使用的话,则是对中国的极大不尊重。
需要注意的是,育鹏社历史教科书对九一八事变的描述较东京书籍版和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都要更加详细,总共使用了两个版面。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方面,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着重阐述了来自于中国国内的因素。育鹏社历史教科书阐述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所引发的列强的不安,以及日本在其中左右为难的处境,并认为:“(炸死张作霖)是一部分军人独断的结果。政府并没有严惩凶手,所以这也是日后容许军队擅作主张的原因。”⑥伊藤隆等:《新编新日本的历史》,育鹏社2017年版,第226页。这样的表述,事实上是想将以后由于日本方面原因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责任往军部身上推卸一部分。关于战争责任这一问题,日本国内主流舆论似乎已经达成默契,即所有的责任都要推到军部身上,政治家的责任是不能够随便追究的,天皇更是不可问责的。在叙述九一八事变爆发的背景时,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提到了“以寻求收回日本在华权益为目的的排日运动被加强了。对于排日运动的计划,日本国内对日军确保满洲权益的期待提高了”。①伊藤隆等:《新编新日本的历史》,育鹏社2017年版,第227页。如此的表述显然是在将事变的责任推向中国。同帝国书院版历史教科书不同的是,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在伪满洲国的表述上没有像上述两种历史教科书那样以引号的形式表现。同东京书籍出版社一样,这是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延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的错误观念。伪满洲国从来就没有被中国任何一个政府所承认,东京书籍版和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执意将引号去掉,是在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并在国际上取得广泛共识的战后秩序。
第71目“日中战争(支那事变)”,其主要内容“日中战争”为该目的第三部分,第一和第二部分分别是“满洲国的发展”和“二二六事件”,在这里教科书将这两部分内容作为抗日战争的背景进行了描述。在“满洲国的发展”之下,有“以西安事件②即西安事变。为契机,形成了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合力对抗日本的态势,两者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③伊藤隆等:《新编新日本的历史》,育鹏社2017年版,第228页。的表述。显然,这一表述同“满洲国的发展”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作为叙述建立国共联合抗日的政治基础的话语。在该部分占据大量篇幅的,是同国共合作抗日并无直接关系的“满洲国”的发展。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在行文当中对“满洲国”在日本控制之下的“盛况”进行了日本视角的正面叙述,称:“在实际上处于日本控制之下的满洲国,政治和经济的建设顺利进行,日企进入而重工业得到了发展,许多日本农民作为开拓者进入满洲开荒。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增加的从中国本土和朝鲜居民的流入,在满洲事变之后也在持续增加。”④伊藤隆等:《新编新日本的历史》,育鹏社2017年版,第228页。这一段充满了“自豪感”的表述首先对“满洲”和中国进行了割裂,东北三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是陆地相连,不存在日本这样“本土-离岛”的关系。此外,东北三省亦不应当被视作有别于中国其他地方的特殊地带。“满洲国”在当今近现代史观当中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合法的国家,育鹏社也不应当以“尊重史实”为借口在历史叙述中进行不当的表述。
在描述卢沟桥事变的时候,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提到了“日本政府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但另一方面决定增加兵力”⑤伊藤隆等:《新编新日本的历史》,育鹏社2017年版,第229页。,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表述不知道想要传递给读者怎样的信息。因为在前文当中就已经暗示了政府对军部掌控不力,想要说明日后的军事行动是军部自作主张的妄动。然而,在这里又说决定增加兵力是日本政府的主张,这样前后矛盾的表述不得不令人怀疑教科书编撰者的能力。或者,之前有关政府无力掌控军部的说法已经过时,政府和军部在1937年7月这一时间节点早已达成高度的一致。但是,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并没有在这一点上提供足够的说明。课文中也提到了日军于12月占领了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但是在正文当中并没有出现南京大屠杀或者“南京事件”的表述,仅仅在注释部分出现了“此时,由于日军而使中国军民造成许多死伤(南京事件)。关于此事件牺牲者的实际数量,存在着种种见解,直到今天争论依然持续着”⑥伊藤隆等:《新编新日本的历史》,育鹏社2017年版,第229页。这一轻描淡写的叙述,倒是符合右翼教科书一贯的做法。
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是所有日本历史教科书当中观点立场最为保守的一种。在涉及抗日战争的问题上,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的表述同它一直以来的立场保持了一致。同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一样,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将内容编为若干个目,不拘于章节编排的束缚,按照顺序进行排列。同抗日战争有关的目分别是第75目“中国的排日运动和协调外交的挫折”、第76目“满洲事变和满洲国建国”、第77目“日中战争(支那事变)”、第78目“围绕中国的日美关系的恶化”。这些内容均被安排在第五章“近代的日本与世界II”的第二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之下。从目的标题来看,自由社历史教科书非常强调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因素当中有关中国的因素,试图将引起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并且,以抗日战争长期化影响到美日关系为论点,将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建立了一定的联系。
同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有所不同的是,在阐述中国的“排日运动”时,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除了提示蒋介石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之后,中国废除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的呼声越来越高以外,还特别提到了“这些虽然是针对列强控制的中国人的民族反抗,但是受到了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带有过激的性格”。①杉原诚四郎等:《新版中学社会·新历史教科书》,自由社2017年版,第228页。在这里,凸显了日本右翼的另外一种性格。如果说强调日本的主体性,在语言上把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美化只是在历史问题上进行篡改的话,那么在历史问题上加入鲜明的意识形态偏见,则体现了日本右翼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场。日本右翼在历史上曾经受到了美国占领军当局的镇压,右翼文人和学者也遭到了“公职追放”的处分。但是,随着战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扩大影响,美国占领军当局将日本右翼放出铁笼,专门对付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日本右翼同美国当局之间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显然是受到了当时作为保护伞的美国占领军高层的影响。尽管当前的日本右翼不再受到像当时那样的全方位管控,但是其性格当中已经留下了反共的痕迹。包括其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多少受到了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
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中还说:“基于政党内阁规则担任了两期外务大臣的币原喜重郎同英美协调而遵守条约,支持中国的恢复关税主权的要求,也对中国的民族感情抱有同情,推进国际协调外交。但是中国的排日运动并没有停止。”②杉原诚四郎等:《新版中学社会·新历史教科书》,自由社2017年版,第228-229页。这是典型的推卸责任的说辞,故意将侵华战争的原因和结果进行了颠倒。后面又称:“在日本,以军部为中心,将币原外交批判为软弱外交的声浪逐渐加强。”③杉原诚四郎等:《新版中学社会·新历史教科书》,自由社2017年版,第229页。此表述恰好说明了当时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野心,也从侧面提供了一个自我矛盾的论据。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有一个地方相较于其他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都要好,那就是为了给日本的侵略行为做辩解,会提供较其他历史教科书更多的材料和叙述。在第75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当中,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花费了一定的篇幅专门讨论“围绕满洲的状况”,其本意是为九一八事变的叙述进行铺垫,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辩解。其中的表述为:“1928年(昭和三年),日本以保护在山东省的侨民为由派遣军队(山东出兵)。关东军炸死了满洲的军阀张作霖,强化了对满洲的控制。相对应地,中国人的排日运动也更加激烈,妨碍列车运行和恐怖活动频发,威胁到了日本侨民的安全。更有甚者,北方有苏联的威胁,南方有国民党的势力逼近。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的一部分军官开始计划军事占领满洲并驱逐排日势力,守护日本权益。”④杉原诚四郎等:《新版中学社会·新历史教科书》,自由社2017年版,第229页。以上表述将排日作为出兵的理由,其实是一种强盗逻辑。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和平宪法依然有效的当今日本,居然还有人抱着军国主义的这种强盗逻辑,将日本发动侵略的责任推给被侵略的一方。
在叙述九一八事变的部分,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同育鹏社版以及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一样,并没有在“满洲国”的表述上使用引号。这三种历史教科书都将“满洲国”作为了历史上的合法国家。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在政治上没有经过成熟的考虑,而是偏执于所谓“历史事实”,而育鹏社版和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的处理方式则反映出这两种教科书编撰者一直以来的政治观点,其是基于政治层面上的考虑。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对九一八事变过程的描述是:“1931年(昭和六年)9月,关东军在奉天(现沈阳)郊外的柳条湖炸毁了满铁的线路,并嫁祸给中方,随即占领了满铁沿线的城市。政府和军部中央虽然秉持不扩大方针,但是关东军扩大了军事行动的范围,占领了全满洲的主要地区。”⑤杉原诚四郎等:《新版中学社会·新历史教科书》,自由社2017年版,第230页。所谓的“政府和军部中央秉持不扩大方针”,把军部首脑也视作同政府一样并不想扩大事态,想要继续推卸责任。该目第二部分“李顿调查团”当中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另一方面,(调查团)不承认日本主持下的满洲国建国,规劝日本从满洲的占领地撤军以及满洲的国际管理。已经承认了满洲国的日本政府于1933年(昭和八年)拒绝了这一规劝,退出了国际联盟。”⑥杉原诚四郎等:《新版中学社会·新历史教科书》,自由社2017年版,第231页。从这一表述当中可以看到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是:其他列强觊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想要通过调查团来对日方施压,而日方的所为只是为了保障自身权益。然而,这一表述的潜台词是,日本想要单独占领中国东北。这是有长远计划的战略目标,因此日本不惜为此退出国联。这也从侧面动摇了由于中国排日而日本不得不出兵的论证基础。
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对“日中战争”的阐述同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相似,在第77目的标题上也使用了括号中填入“支那事变”的表述,但是并不像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那样给“支那事变”添加注释。在该目当中,有一半的内容是阐述抗日战争爆发的直接背景。其中,第一部分内容的标题是“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战略”,这是同其他版本的教科书都不同的表述形式,其中声称:“共产国际创立了保卫社会主义苏联,在欧美和日本的殖民地和附庸国展开活动的世界革命战略。在作为活动据点的中国,日本终于成为了目标。”①杉原诚四郎等:《新版中学社会·新历史教科书》,自由社2017年版,第232页。这一段表述放置在第77目当中,从结构上来看,将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战略同中国的抗日战争扯到一起,根本无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事实。其放置在第二部分“西安事件”之前的用意无非是想说明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唆使而挑动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充满了阴谋论的色彩。以上两部分组成了对抗日战争背景的叙述,较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的叙述更有一层反共的内容。
在涉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部分,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对卢沟桥事变的叙述大致同其他版本的历史教科书相似。但是,在关键的南京大屠杀问题上,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的表述只有“日军以为只要攻克南京即可令蒋介石投降,遂于12月占领了南京”。②杉原诚四郎等:《新版中学社会·新历史教科书》,自由社2017年版,第233页。有关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所进行的大屠杀的事实,在教科书的任何地方均没有被提及。相反地,在叙述八一三淞沪抗战的部分,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却在“中国军队的精锐部队”上增加了这样一条注释:“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国的军事指导和武器援助而变身为一支劲旅,但是日本却轻视了这支部队。中国为了回报德国,给德国提供了稀有金属钨,支援了希特勒的军备扩张。”③杉原诚四郎等:《新版中学社会·新历史教科书》,自由社2017年版,第233页。如此反咬一口,无非就是想要减轻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将抗日战争长期化作为美日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在叙述时说道:“蒋介石得到了美英法苏的支援,继续进行战争。”④杉原诚四郎等:《新版中学社会·新历史教科书》,自由社2017年版,第234页。并且,在上面还说:“日本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多次策动和平工作。”⑤杉原诚四郎等:《新版中学社会·新历史教科书》,自由社2017年版,第234页。两段放在一起看,倒有一种日本爱好和平、中国执意战争的味道了。殊不知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原因就在于这场抗日战争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而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提出的所谓“和平工作”,其本质就是诱降活动。如此厚颜无耻的表述居然出现在历史教科书当中,实在是令人大开眼界。右翼历史教科书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史观,顽固地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是合理的,对战争罪行采取一律回避的态度。这样的史观本质上是在“日本主体”的意识基础上走向了极端化。尽管在中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当中多次提及要培养“主体性”,但是用既有成见来胡乱解构史实的做法是令人不齿的。
三、结论
历史教科书体现的是一个国家主流的历史认识。尽管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均是由各家出版社自行聘请专家编写,但毕竟编写的依据是《学习指导要领》,而要领则是由文部科学省颁布的。也就是说,国家的手中依然握有指导历史教育的指挥棒,日本的历史教育并不能超然于国家意志的影响。所有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症结依然在于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政治生活当中的影响,尤其是有关抗日战争的问题,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是日本右翼势力最愿意借题发挥、博人眼球的地方。因此,在应对这样的问题时,必须十分地慎重。
首先,从日本方面来看,二战以后很快形成的冷战格局使日本迅速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绑定,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最前线,对自身的侵略历史并没有足够的反思和清算。尤其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以来,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得以恢复,面对尚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时,在各方面或多或少地流露出轻慢的态度。历史问题对于一部分日本人而言关乎民族自信问题,所以他们对历史问题特别敏感,并且经常通过历史问题来针对现实问题。中日关系在建交以来起起伏伏螺旋上升,但是日本右翼对历史教育的影响力在冷战结束以后却是在持续增加的。其次,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成为妨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因素。在确认了这一点的基础上需要明确的是,历史教科书问题本质上依然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虽然教育领域并不直接对现实中的国际政治产生影响,但是却能够直接影响到一代国民的意识形态底色。因此,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抗日战争叙述是我们有必要去追踪研究的。
我们必须不断地重申我国对抗日战争的基本认识和立场,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我国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定性,也是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捍卫,是在维护战后的和平秩序。这不仅仅涉及历史问题,还涉及现实政治问题,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各种不友好势力进行角力的有力武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①习近平:《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cpc.people.com.cn/n/2015/0903/c64094-27543286.html,2015年9月3日。
随着近期日本右翼势力的频繁活动,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观点也通过文部科学省发布的通知被追加到了《学习指导要领》当中,历史学科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历史和现实并不遥远,尤其在二战后日本的政治传统当中,现实中的政治态度有时会通过在历史问题上制造麻烦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因此,现实政治问题会以另一个面目在历史教学的课堂当中出现,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通过历史教学的课堂传递给国家的下一代。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希望同日本保持长期友好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基本共识之上。在这一点上,日本历史教科书当中有关抗日战争部分的内容叙述,并没有完全在共识的框架下,这是很可惜的。一些右翼教科书甚至想要破坏建立共识的基础,这是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而在这一问题上持续对日方保持压力,增强我方在日本舆论界的影响力,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