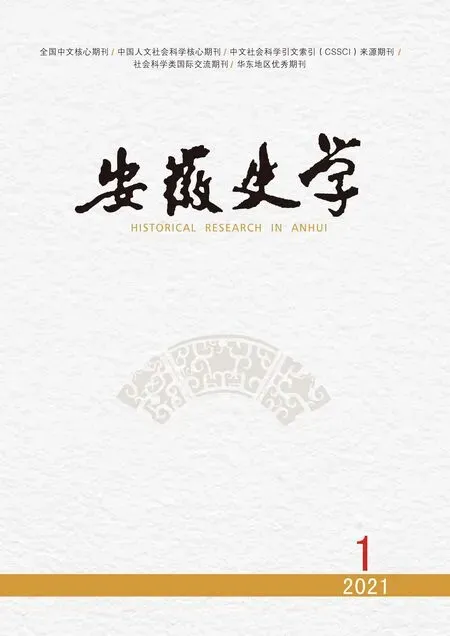清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水利经费筹措方式研究
田 宓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在水利设施的兴建与维护中,经费筹措是一个关键性问题。以往关于水利经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河流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湖堤垸、江浙水利设施、宁绍海塘、安徽长江江堤、温州滨海平原水利工程等得到关注。(1)参见张建民:《清代两湖堤垸水利经营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熊元斌:《论清代江浙地区水利经费筹措与劳动力动用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刘丹、陈君静:《试论清代宁绍地区海塘修筑的经费来源与筹措方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房利:《清代安徽长江江堤建设经费来源问题考察》,《中国农史》2015年第3期,等。黄河流域的研究集中于河工银收支的贪腐现象、河工银征收制度的结构性问题。(2)参见倪玉平:《清代嘉道财政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3—156页;潘威:《清代前期黄河额征河银空间形态特征的初步研究——以乾隆五十七年的山东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4期。检视前人成果,可以发现研究者或关注水利经费来源的多元性,指出水利经费筹措主要有官方、民间两种渠道,并剖析双方力量消长及其原因;或就某一专项水利经费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展开具体论述,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研究都增进了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水利经费筹措方式实际运作和历史特点的理解。
归化城土默特位于内蒙古西部土默特平原(即黄河前套平原)。其地北依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南临黄河,水草丰茂,亦农亦牧。元朝覆亡之后,蒙古贵族率领部众退居北方草原。此后,土默特平原诸部争锋,互为雄长。15世纪以来,土默特蒙古开始在这里驻牧。入清以后,土默特蒙古归附清廷,清廷编制蒙旗,对其进行治理。雍正以后,又开始设“厅”(民国时期改厅为县),对出口外谋生的民人实施管理,形成旗厅并立、蒙汉分治的局面。关于归化城土默特的水利经费问题,较少有学者研究(3)主要有燕红忠、丰若非:《试析清代河套地区农田水利发展过程中的资本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穆俊:《清至民国土默特地区水事纠纷与社会研究(1644—1937)》,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230—231页。,本文主要利用土默特档案、新发现的民间契约以及地方志、民国期刊等资料,探讨归化城土默特水利经费筹措方式的历史演变。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自清代至民国,归化城土默特的水利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并日益复杂的连续历史进程。在这个连续历史进程中分析水利经费的筹措问题,可以动态地呈现地方社会从游牧到农耕、从传统到近代的社会转型。其二,归化城土默特旗厅(县)并立、蒙汉分治的社会结构,使当地的水利发展留下了独特的历史轨迹,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社会水利事业演进复杂性、多样性的认识。
一、民间集股与水利经费的筹措
入清以后,归化城土默特农业垦殖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水利事业也逐步发展。在水利设施的兴修与维护过程中,经费筹措是蒙汉民众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清代大部分时间里,归化城土默特的水利经费多由民间社会自行筹措。直至清末,当地水利事业仍是“半皆民间自由办理,任便使用,官厅多不过问”。(4)《总论》,《绥远建设季刊》1929年第1期。
个人集股出资是水利经费的主要筹措方式。民人在租种蒙古人土地之后,为发展农业生产,往往修建水利设施。乾隆四十七年,归化城厅巧尔报村发生了一件水案,巧尔报村色令多尔济等状告本村张成宗等串通哈力不岱村郭老六等挖渠毁坏草厂、破坏官道。此案案卷中保留了被告张成宗等人的供词:“讯据张成宗、辛有、郭照进、岳金山、石宗同供,小的们先人自康熙年间租下巧尔气召罗树喇嘛名下沿河荒草地亩,陆续开成熟地。到雍正三年上与地主商议明白,开渠引水费用工本有一百多两银子。召里立下文契,不许旁人拦阻。”(5)《详送色令多尔济张成宗等完结销案册》,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二十五日,土默特档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下同,不一一注明),档号:80/5/77。张成宗等强调了修建渠道得到了“地主”巧尔气召罗树喇嘛的许可,并且花费了工本一百多两银子。从中可知,这条渠道是由张成宗等个人集股出资修建。
随着农耕定居化的发展,原本不擅农耕的蒙古人,也越来越多地从事农业生产,并且主动筑坝开渠。光绪十八年,萨拉齐厅二十家子村发生了一起水案,此案由善友板申村甲会张犁虎子越界填塞二十家村渠口引起。该案案卷记载了官府断案的情况:“据此卑职伊精额奉委束装抵萨,会同卑职周桂敷查明卷宗,讯得此案因渠争控缠讼有年,蒙古七十五等从前筑坝开渠曾经花费财力,情难为该民人等平白堵塞,实属不合,除申斥外,断令张木兆气等帮给七十五自垫渠费钱一百三十吊,以作从前花费,嗣后再不准与二十家子村民开渠滋事,致起讼端,两造允服,情愿遵断息讼”。(6)《张犁虎子填塞渠口案讯结书册》,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土默特档案,档号:80/5/330。此案官府断案的依据正是蒙古七十五、民人侯良等修建了水利设施,耗费了财力,因此断令被告张木兆气(即张犁虎子)等补给蒙古七十五渠费钱一百三十吊。
由合村民众共同修建水利设施的情况也比较常见。乾隆四十八年萨拉齐厅的一个村子发生土地纠纷,纠纷在蒙妇伍把什和民人杨天沼之间产生。本案虽然是一件关于土地纷争的案件,却在无意中留下了水利设施兴修的记录。该案案卷中蒙汉坝头的供词称:“讯据民人坝头要照、刘德子、蒙古坝头色旺等同供,小的们村里三十八、九年、四十四年三次修筑坝堰,每分(原字如此——引者注)地三十亩,共摊花费钱八千八百有零,现有账目可凭。伍把什地内应摊钱文俱系杨天沼出的是实。”(7)《详报审断蒙妇伍把什控杨姓一案情形(附书册)》,乾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土默特档案,档号:80/5/66。不难发现,这个村子的水利设施,由民人坝头和蒙古坝头组织全村集资修成,按每份地三十亩摊钱,共摊钱八千八百多文,并且留下账目。
清末朝廷在内蒙古地方推行蒙地放垦,倡导发展水利。土默特地区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村落兴修水利设施。光绪三十一年,萨拉齐厅参将村发生一起水案,此案由参将村贾荣娃、挠狮子阻挠合村在张庆和地内开渠引起。本案案卷中记载了原告民人张庆和的供词,“据张庆和供,向在萨属参将村居住种地度日。小的先人置到赵佐领苏目下地一段三十余亩。地里还有小的祖坟,耕种数十年之久,并无异说。到光绪三十一年春上,村众蒙汉公议在小的地里开渠浇地,渠口相挨蒙古得胜户口地。兴工开掘,突有案下西河沿岸村人贾荣娃,佐出蒙古挠狮子拦阻填渠,小的合(应为“和”——引者注)蒙古得胜们当就控蒙樊案下,勘讯贾荣娃们合约不符,且渠身并未占贾荣娃们的地,断给小的们印谕,准予开渠浇地,以兴利水(应为“水利”——引者注),不准贾荣娃们阻挠。各具甘结完案。”(8)《详张庆和控贾荣娃违断填渠案已会审明确请销案批示》,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土默特档案,档号:80/5/496。这条材料中没有直接提到水渠修建的经费筹措情况,不过,既然是由“村众蒙汉公议”,其经费理应由全村共同筹集。
自民元鼎革至1920年代,土默特地区的水利经费仍是主要依赖民间自发筹措。(9)民国《绥远通志稿》卷40(上)《水利》,第5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9、800、594、796页。1920年代以后,绥远当局制定章程,鼓励民间自筹经费开挖渠道。在《绥远建设厅奖励兴办水利简章》第七条中就规定:“凡有合于左列各规定之一者,由县局长查明出力人员,择优请奖。(一)各县局联合或各村联合创办水利组合开渠,著有成效者。(一)创办水利公司开渠凿井以营业为性质,而定价低廉办理完善者。(一)创兴水利或堤防水害,纯由人民出资出丁,不借公款补助者。(一)凡在一村提倡凿井十眼以上者”。(10)《绥远建设厅奖励兴办水利简章》,《西北新农月刊》1933年第2期。在这一政策导向下,不少民间人士独立修浚渠道。然而,民间社会出资修建,常因经费不济,陷入难以为续的境地。归绥县的复兴渠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复兴渠,原名义和渠,引大黑河水而建。1925年,赵登桂等人集资开凿,投资经费四千元,开渠十余里,但因款项不继而被迫停止。1929年,张世昌继续集股修建,同年又由复兴渠水利社接续工程。到1930年,渠道已经可以灌溉田亩。但此后大黑河水泛滥,冲决渠口,不得不再次停工,“厥后屡修屡圮。需款已属不资,而工程迄未完成,截至二十三年,已需款五万余元,多数股东于成渠无日,不愿再予投,故至二十四年春,复行停工矣。”(11)民国《绥远通志稿》卷40(上)《水利》,第5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9、800、594、796页。
二、官方拨款与水利经费的供给
地方政府在包括水利经费筹措等水利事务中开始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与1920年代的大旱灾有关。民国《绥远通志稿》记载:“自十五年后,连年旱灾,盖藏悉尽。老弱饿殍,少壮流亡,为绥地空前未有之惨象。事后痛定思痛,农民旧习为之一变,渐知注意水利,或欲利用河流,或欲疏导山泉。开渠之风,自十八九年以来,于以大盛。公家既广为劝谕,以导其机,复优为贷款,以促其成”。(12)民国《绥远通志稿》卷40(上)《水利》,第5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9、800、594、796页。也就是说,1926年以后归化城土默特连年亢旱,这成为地方政府在水利事务中承担更多职能的重要契机。
(一)斗捐、报荒地款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的地方官员偶有参与兴修水利设施的行为。萨拉齐厅治是萨拉齐,位于大青山南麓,正对水涧沟,常受山洪侵害,因此需要修坝防洪。道光八年《萨拉齐修筑土坝碑记》记载:“迩年来雨水浩大,冲堤直下,居民颇受其害,郡之人每议筑土坝于郡外而不果举。幸逢我神君寿老公祖念切民瘼,思患预防,督率乡总等,动众兴工,以完堤防,以谨壅塞。凡我商民无不欣然乐从,富者捐缗,贫者效力,经数月而工告竣。”(13)《萨拉齐修筑土坝碑记》,《萨拉齐县志》卷15《艺文》,《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八,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760页。“神君寿老公祖”即萨拉齐通判寿麟,他于道光七年至道光十四年,在萨拉齐厅任职。(14)《重修官坝碑记》《重修水涧沟石坝记》《重修萨县保安石坝碑记》,《萨拉齐县志》卷15《艺文》,第767、769、770页。在其任内,因督率修坝而得到百姓称赞。不过,从碑文内容可知,官员只有督率之功,官府并未投入经费。
光绪年间,托克托厅的官员参与兴修顺水坝。民国《绥远通志稿》记载:“托克托县顺水坝,清光绪十三年通判恩承用斗捐款修筑一次。三十年孙多煌禀请从赈款项下拨银二万两。三十一年魏鋆时开工,大家修治。”(15)民国《绥远通志稿》卷40(上)《水利》,第5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9、800、594、796页。从中可知,托克托县顺水坝在光绪十三年用斗捐修建。这里所说的斗捐,是在通判恩承任内,由河口镇乡耆公盛长铺长岳恒瑞、晋义恒铺长刘登龙牵头倡办,“因托河顺水坝失修,恐出危险,倡办二文斗厘,由籴粜米粮者,每斗各抽一文,集款预备随时补修,以防水患。”这笔款项后来交由官厅接收。民国以后,划为省款。(16)民国《绥远通志稿》卷31《税捐》,第4册,第557—558页。
1920年代,归化城土默特旱魃肆虐,地方社会出现了“以地集款,开渠灌溉”的提议。1932年,托克托县县长荣任民、新章营等村村民向绥远建设厅呈请报垦荒地五十顷,以每亩现洋四角的时价,招徕民户承领,可得款项二千元,用于修建水渠。这一提议得到绥远建设厅批准,“兹由厅长察以情形,拟将此渠定名民康渠,所有工程应需之款即将新章营村报荒三十顷、拐沟营报荒二十顷定为官产,责成该县政府招垦发给财政厅官产部照。此项收入拨作修渠之费,一俟渠成,再按渠费摊还”。(17)《呈请修挖托县民康渠拟具办法文附图暨办法》,《绥远建设季刊》1932年第11期。民康渠的例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地方政府为了兴修水利如何多方开辟财源。
(二)工赈贷款
为救济遭遇旱灾的灾民,地方政府开始将灾荒赈款用于水利兴修。赈款主要由中央政府筹拨、各界募捐和税捐附加款构成。(18)民国《绥远通志稿》卷66《赈务》,第9册,第72,53、71,136,136页。其中税捐附加款是赈款的经常性来源。附加赈款自1927年起征,主要来自货捐局货捐、禁烟善后局罚款、警察厅戏妓捐、粮食出口捐,其中禁烟善后局所得最多。1928年,又增加了平绥铁路客货运费附加款。这些款项“按月解会备用,每年约三万余元”。(19)民国《绥远通志稿》卷66《赈务》,第9册,第72,53、71,136,136页。
赈款用于兴修水利的主要形式是“以工代赈”。工赈分为路工和渠工。渠工即召集灾民,开挖渠道,拨款赈济。在时人看来,修挖渠道是工赈的首选方式,“绥远两年以来,人民历受刀兵水旱风霜之灾,无衣无食者数逾一百五十余万名口,其惨酷情状匪言可喻,政府筹拨赈款,各慈善团又复尽量拯救,无如灾区太广,普救匪易,是于急赈之外,必须工赈兼施,而工赈进行,应以修渠为先要”。(20)《绥远工赈拟修各县渠道计划书·引言》,《绥远省政府年刊》1931年。
1929年,由赈务会积极倡导各县贷款兴办水利,以工代赈,“至是复经赈务会贷给水利用款,专事修浚渠道,灌溉田地。”(21)民国《绥远通志稿》卷66《赈务》,第9册,第72,53、71,136,136页。为了管理水利贷款事务,绥远当局还于1929年八月设立了“保管水利建设基金委员会”,并颁布了管理办法。1930年议决的《绥远省修正保管水利建设基金委员会贷款办法》规定,修挖新旧干支渠道、浚河凿井、购用水车都可以贷款。贷款可贷于团体或私人,私人贷款仅限于凿井。贷款两年内还清,展期不得超过四年。年息六厘,每展限一年,加息一厘。(22)《绥远省修正保管水利建设基金委员会贷款办法》,《绥远政府年刊》1931年。次年,又制定了《补订绥远省赈务会工赈水利建设贷款办法》,与前一办法相比,这一办法免除了工赈水利款项的利息,并规定水利款项于工程竣工后,由其征收水租项下分年摊还。(23)《补订绥远省赈务会工赈水利建设贷款办法》,《绥远政府年刊》1931年。
在这一情况下,各县纷纷贷款修渠。其贷款金额如下,萨拉齐县兴农、富农两渠六千元,托克托县民阜渠六千元、民利渠二万八千零九十三元,包头民福、公济两渠一万二千元,和林格尔县盘山渠、小沙梁渠八千元,归绥民丰渠六万两千元。(24)民国《绥远通志稿》卷66《赈务》,第9册,第72,53、71,136,136页。但是贷款款项往往不敷使用,因此仍然需要地方集股。托克托县民利渠,“计先修干渠和九道支渠。需时一年半,费款三万七千元。内水利贷款二万七千五百元,由赈务会支领。地方集股一千六百七十元,又提用各区领回之赈粮值价七千八百元。”(25)民国《绥远通志稿》卷40(下)《水利》,第5册,第791、792,793页。托克托县民阜渠,“此渠亦为水利贷款所修。由地方人士提倡,向省赈会领得六千元。民国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开工。六月八日因款用尽停工。嗣由沿渠农户暂为借垫。”(26)民国《绥远通志稿》卷40(下)《水利》,第5册,第791、792,793页。
按照前述《绥远省修正保管水利建设基金委员会贷款办法》规定,水利贷款只能用于水利,但各县不乏将贷款挪作他用的情况。(27)《绥远省修正保管水利建设基金委员会贷款办法》,《绥远政府年刊》1931年。在武川县,“武川领到八千元,二十年春季修城借用,虽经各区按地均摊,统归财务局起收,现在已逾一年,分文未还。本局早拟利用此项工赈款开挖塔布河渠道,业蒙照准,刻下款项无着,致工程停顿。查各县将此项工赈款,挪作别用,在所难免。”(28)《如何催索工赈款以便建设案》,《绥远建设季刊·议案》1933年第13期。尽管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赈款贷款兴修水利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查各县工赈修渠大半完成,惟和林小沙梁渠,萨县之兴农、富农渠,包头民福渠、公济渠,或因借款纠葛,迄未竣工,或因他故,半途中辍,应由各建设局长回县后,切实晓谕,协助妥办,督促早日完工,勿任前功废弃。”(29)《建设厅第三科韩科长提请继续举办河渠调查以资振兴水利案》,《绥远建设季刊》1933年第13期。
民国时期绥远水利以工代赈中影响最大的是“民生渠”。绥远“民生渠”与陕西“泾惠渠”并称为西北两大水利工程,时人记载“陕西泾惠渠与绥远民生渠的开凿,不但是陕绥二省的巨大水利工程,而且也是我们几年来稀有的水利建设。开发西北,久经国人视线所集,而泾惠渠与民生渠的开筑,实足为树立开发西北之先声”。(30)赵镜元:《泾惠渠与民生渠》,《新中华》1933年第1卷第11期。民生渠的修建,其直接导因就是绥远地区的旱灾。1927年,萨拉齐、托克托二县旱情严重,在地方人士的呼吁声中,1928年,都统李培基、建设厅厅长冯曦主持修建民生渠。民生渠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招集流亡,赈济灾民。其赈款构成如下:“除由平绥路附加赈款,及本省烟亩罚款附加赈款,并承阎总司令筹发急赈,综共集资二十余万元,而以四分之一用于工赈,兴工一载,耗资六七万元,顾工程浩大,经费困难,颇难为继,复由绥省府及建设厅与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商妥,于民国十八年订立合同,双方集资,所有未完工程,继续开挖。是年七月,即由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接办,担任开渠工作。经营三载,于二十一年冬始大部告成,综计兴工五六年,用费八十余万元。”(31)绥远省民生渠水利工会编:《绥远省民生渠水利工会第一届报告书》1934年,第1页。从中可知,民生渠的赈款,在平绥路附加赈款、绥远省烟亩罚款附加赈款、阎锡山急赈款之外,还有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赈济款。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全称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成立于1921年,是由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近代中国最大的国际慈善社会团体。(32)参见薛毅:《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华洋义赈会在全国各地都展开赈灾活动。绥远地区罹遭大旱之后,华洋义赈会也参与赈济。可见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一些新出现的社会团体在绥远地区的水利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水租与水利经费的维持
水利设施修成之后,其日常的维护管理同样需要经费的支持。清代水利经费的维持,主要依赖水租。不过,这方面的资料鲜少留存。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收集到三份珍贵的契约,契约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土默特水利设施日常维护的情况。三份契约契文如下:
其一:
大清咸丰八年三月十九日
立合同各执一张
知见人 段典有+ 杨喜+ 张永隆+
其二:
咸丰九年正月十九日
合同约据,各执一张
知见人 段典有+ 杨喜+ 张永隆+
约存威俊村蒙古手
其三:
立合同公议信约人渠头粟官、李狗毛、许老八,蒙古以力克太、那木架什、泥尔降、白银降等公议引水灌地事。民人、蒙古公议无论某村浇地一亩,粟官抽辛金钱七文,李狗毛抽钱五文,许老八抽钱三文,巡渠负苦,粟官等承应,如渠路有蒙古、民人拦阻,二村蒙古以力克太、那木架什等承当,目下渠路花费俱系粟官垫给,灌地之后,向走户起钱,系粟官一人,不准众人讨要。恐口无凭,立合同约为证用。
咸丰十年九月十五日
约见吕祥+、黄元+、李九子+(33)以上三份契约均为笔者在田野调查时收集的民间契约。
从以上三份契约来看,渠头更换较为频繁,咸丰八年约载渠头赵仕贵和咸丰九年约载渠头甘永贵之间间隔的时间是9个月,咸丰九年约载渠头甘永贵与咸丰十年约载渠头粟官、李狗毛、许老八之间间隔的时间是21个月。也就是说,每隔一两年,渠头就更换一次。渠头的人数不断增多,咸丰八年约载和咸丰九年约载都是一位渠头,咸丰十年约载则是三位渠头。渠头的薪资不断增加。咸丰八年约载渠头的薪资是每亩五文摊钱,咸丰九年约载是每亩十文摊钱。咸丰十年约载是三位渠头,每亩共计摊钱十五文。这似乎反映出三村的水利事务日益繁杂的实际情形。而渠道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所需经费都是由蒙古和众浇地户按亩摊钱承担。
1920年代以后,在水利设施维护经费方面,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出资修建的渠道,都是从水租款项下支出各项费用。1929年,《各县各渠水利公社章程》颁布,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本社经费及渠费由本社于灌域内地亩,计顷征收水费,以支付之,其目别如左:一、本社经费。甲,公费,即本社暨董事会办公应需之款;乙,薪工。除经理、副经理、董事会董事,均义务职外,其余司账、书记、渠头、渠夫等均支给薪水或工食;二、修渠费。丙,经常修渠费,即每年岁修应需之款;丁,特别修渠费,即临时发生紧急渠工应需之款。第十五条,本社水费之征收,每顷应征十元至十五元”。(34)《各县各渠水利公社章程》,《绥远概况》上册第5编《水利》,绥远省政府1933年编印,第69页。可见水利社日常运行的费用和修渠的经常费、特别费均从水租款项下支出。(35)本文关于这一内容的分析,参考了穆俊博士对绥远地区水利公社经费的收入与支出情况的研究。参见穆俊:《清至民国土默特地区水事纠纷与社会研究(1644—1937)》,第230—231页。
民国时期水利经费情况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水租”逐渐被纳入到地方政府的公共事业经费之中。毕克齐镇水磨沟沟水是土默特右翼二甲二三苏木蒙古的户口水分。(36)即土默特蒙古人的户口地随带水分。参见田宓:《水权的生成——以归化城土默特大青山沟水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2期。民国《绥远通志稿》追记,乾隆年间,由园行、大行、蒙行组成三合社,管理水利事务。道光二十六年,因发生水利纠纷,又组成五行办事社。因诉讼费用繁巨,遂以三天水分的水租予以抵补。款项还清之后,这三天水分并未取消,而是作为办公经费保留了下来。(37)《绥远通志稿》卷40(下)《水利》,第5册,第835—836页。1931年毕克齐镇成立了水利社,并制定了《归绥县毕克齐镇水利改善管理办法》,其中第八条规定,“每渠各农户共缴纳每年水租一次洋十二元,以六成作为该镇兴学经费,以四成作为该镇蒙民分工所办公之用,每年由该公社直接分别收交公家,对于款项,概不收管,惟每年所收水租,暨拨交数目,年终由该公社分报绥远建设厅土默特总管理署,以资查考。”(38)《就汉民加入水利社一案仰会同总管遵办的指令(附毕镇水利改善管理办法)》,1931年7月10日,土默特档案,档号:79/1/547。此后围绕毕克镇水租的征收,各方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直到1936年才告平息。(39)关于这一纷争的详细经过,参见穆俊:《清至民国土默特地区水事纠纷与社会研究(1644—1937)》,第234—254页。但是六成水租作为兴学费用的规定一直没有改变。1936年收取水租款项四柱清折中,“旧管”有1925年六成学费洋一百六十九元二角,“新收”有1926年六成学费洋一百七十二元八角,“开除”则有修盖校舍的各项支出。(40)《核销毕镇水利公社25年收支各款并报租水各户姓名的呈文》,1937年6月5日,土默特档案,档号:79/1/236。
此外,土默特旗还一直有将水租收归旗有的呼声。不过,水租正式收归旗有是在日伪时期。伪蒙疆政权曾制定《土默特旗境内各甲佐水利整理计划书》,其中第二条“各甲佐水利现况调查”中说:“本管境内有大青山水磨沟等六道沟水,人民利用此项清水及夏秋山洪浇灌地亩,在过去由各该管参佐领及领催蒙民等自行租典,于客民永远承业者,所在多有,现亦仍之”。第四条“起征水租办法”规定,“在现时特殊情形之下,水利为蒙旗固有之权益,而各渠所经之地段,亦为本旗固有之土地,无论水租或渠租,均有起征之必要,以恢复旧有之水权”。(41)《发水利整理计划书的训令》,1942年9月9日,土默特档案,档号:79/1/258。由此可见,此次整理重在改变以往蒙民自相租典的情况,水租或渠租改为蒙旗起征。1946年5月22日,土默特旗左翼首、二甲自治督导处向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呈请将水租收归公有,“查本旗境内所属山川河流暨开挖之渠路土地,向为本旗固有之权。……兹为划一旗权计,拟将此项收入收回公有,不得私相收受,由旗征收,以裕公帑。伏查此项收入曾在伪政权时,按水利团体征过,有案可稽。”(42)《呈请实施征收水租并祈颁发章则》,1946年5月22日,土默特档案,档号:79/1/264。从中可知,土默特旗当局延续了日伪时期水租收归旗有的政策,欲以水租充实公帑。
结 语
从入清以后水利事业初兴,到民国年间取得较大发展,归化城土默特水利经费的筹措方式经历了诸多变化。通过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其一,清代土默特社会水利设施的兴修,其经费筹措主要是由民间社会自行完成。官员偶有参与其中,倡行其事,但地方衙门经费并不用于地方公共事务建设。清末斗捐等附加性税收和赈款开始用于水利事务,不过均无定章准则。(43)彭雨新:《县地方财政》,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民国时期绥远当局以1920年代的旱灾为契机,在地方水利事务中承担了更多的职能,为振兴水利,设立专门机构,订立相关章程,并通过报荒地款和工赈贷款等方式筹措水利经费。这与此前水利事务主要依赖民间力量的传统做法明显不同,体现了近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地方财政的生成。
其二,地方水利设施在兴办之际,需要筹措资金,在建成之后,其后续的维护和管理同样需要经费支持。在归化城土默特,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经费主要出自受益人交纳的水租。民国时期,随着近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地方财政的逐步建立,水利事业作为一项公共服务被正式纳入到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水租也有逐渐进入地方财政系统之中的动向。
其三,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在入清以后,逐渐形成了旗厅并立、蒙汉分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不过,在地方公共事业建设中,蒙汉民众往往不自限于这一行政管理上的区隔,彼此之间相互协作,同襄共举。就地方水利事务而言,入清之后,汉人移民首倡其事。随着地方社会由牧转农,蒙古人也加入到水利事业的营修中来。(44)清廷在归化城土默特设置蒙旗之后,给蒙古人划拨户口地作为当兵养赡之资。很多汉人出口谋生需向蒙古人租地租水。因此蒙古人在归化城土默特的水利秩序中具有优先地位,对此笔者已经另文讨论。民国时期,绥远当局在地方水利事务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正是在地方政府和蒙汉民众的共同推动下,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