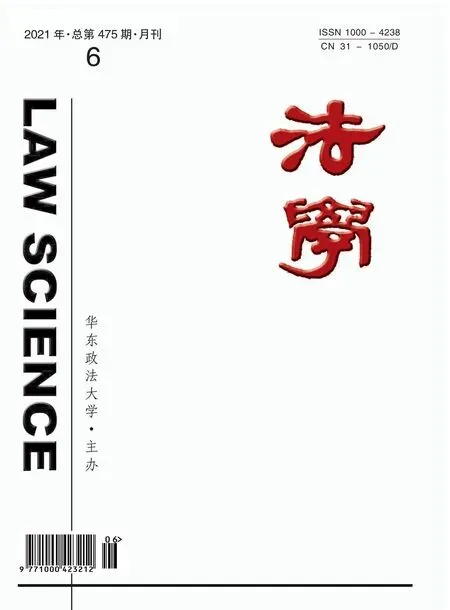民法典中缔约信赖保护的规范路径
●李潇洋
在民法体系中,缔约信赖保护处于合同自由、诚实信用、信赖保护与合同拘束力的十字路口。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在缔约前的“最后一分钟”中断磋商,相对人的缔约信赖原则上不受法律保护。虽然当事人有中断磋商的自由,但如果其一方面作出缔约允诺、促成或要求相对人的支出,另一方面又中断磋商、漠视支出的浪费,其行为并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从相对人的视角看,其缔约信赖完全由当事人引起并以此为基础作出了信赖投资,中断磋商的行为使缔约信赖完全落空,因而产生信赖保护的需求。与此同时,当事人作出的缔约允诺经由意思表示解释可能构成预约、获得合同拘束力,但这取决于预约合同制度的整体设计。
此种原则间的相互交错集中反映在缔约信赖保护的路径选择问题上,其内部以构成解释与利益权衡为核心,外部则以制度间的体系协调为重点。随着我国《民法典》的正式施行,以《民法典》第500条第3项诚信磋商原则为基础构建缔约信赖保护的完整方案,为自由、诚信与信赖的利益权衡提供规范工具与理论支撑;在体系上协调《民法典》第500条第3项与第495条预约合同制度的规范关系,明晰前合同诚信与合同拘束力的制度边界,是我国民法学的重要任务。
一、缔约信赖保护的缔约过失路径:诚实信用原则的解释边界
通过缔约过失路径保护缔约信赖是我国民法学说与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按照对缔约过失的通常认识,该路径在构成机理上侧重对中断磋商的行为评价,而不关注相对人的信赖状态是否值得保护。我国相关学说常使用“恶意中断磋商”这一表述并将其作为《民法典》第500条第3项“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之一。其中“恶意”的意义与违背诚信原则具有同一性,而非如《民法典》第500条第1项仅限于磋商意图的虚假性或诈害他人的主观目的。〔1〕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页;张家勇:《论前合同责任的归责标准》,载《法学家》2014年第1期,第103-104页。我国《民法典》起草机关就此未使用“恶意”的表述,参与立法人士指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期间基于信赖为合同成立做了前期准备,则对方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损害当事人信赖利益的应当予以赔偿。诚信原则要求的是互相协助、照顾、保护、通知等义务。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中),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959页。因此,解释论的任务在于探寻中断磋商行为与违反诚实信用的“连接因素”。
(一)前合同义务违反及其解释困境
缔约过失路径在责任构成上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诚实信用原则设定了何种具体的前合同义务,以及当事人的何种行为构成了义务违反。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会有引发缔约信赖和中断磋商前后两个行为,如果其在引发缔约信赖时主观上确实存在这种意愿,前行为便难以被认定为义务违反;如果基于合同自由原则认为不存在缔约义务,后行为同样不构成义务违反。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尽管有法院判决中断磋商的一方当事人应依《民法典》第500条第3项〔2〕在我国《民法典》施行前,法院的裁判依据为原《合同法》第42条第3项,该项与《民法典》第500条第3项一致。对相对人承担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但对义务违反的解释各不相同。例如在参加用人单位面试后,应聘人接到人事部门要求提供入职手续的通知而辞去现职,随后用人单位又声称因招聘计划临时变化无法订立劳动合同。法院认为用人单位隐瞒岗位招录可能被取消的情况是对“附随义务”的违反,亦即义务违反出现在引发信赖的前行为,但对于事实上是否存在隐瞒行为及其时点则未予关注。〔3〕在该案中,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既认定了被告的“附随义务”,又认定了原告合理信赖的基础事实。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常民终字第2176号民事判决书。在类似情形中,法院则直接认为在引发信赖后中断磋商的后行为本身就是违背诚信。〔4〕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2)徐民五初字第252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6民初10952号民事判决书。在法律服务合同磋商中,律师按照当事人要求参加合同所涉上市项目的有关活动后,当事人又中断磋商,法院认为被告未履行诚信通知义务以及不能证明其中断磋商有正当理由,但对被告应负何种通知义务未予说明。按照上述逻辑,违背诚信的评价对象既可能是中断磋商的后行为,也可能发生在前后行为之间的某一时点。〔5〕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终3588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在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中鲜明地表达其立场,认为缔约过失责任包括“在一定前提下不得无故中断磋商的继续协商义务”。〔6〕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10392号民事判决书。需要注意的是,法院在一些案例中仅以原告未证明被告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为由否定缔约过失的构成,但对于证明对象与标准并未说明。〔7〕参见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11民终352号民事判决书。
我国民法理论尽管承认中断磋商作为《民法典》第500条第3项的一种类型,但对司法实践中“连接因素”的难题尚未形成教义学的理论支撑。有学者以示例说明引起信赖支出而又使其落空属于“恶意终止磋商”。〔8〕同前注〔1〕,韩世远书,第163-164页。也有学者回溯至德国法,直接以理由正当性作为诚实信用的判断依据。〔9〕参见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甚至也有观点将中断磋商与《民法典》第500条第1项规定的恶意进行磋商等同视之,但后者仅指磋商意图的虚假性,这与中断磋商的一般情形大不相同。〔10〕参见尚连杰:《信赖利益赔偿以履行利益为限吗——从一般命题到局部经验》,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1期,第123-124页。这些学说观点都回避了前合同义务的认定。不过也有观点明确提出中断磋商违反了“不得滥用谈判自由的义务”〔11〕王利明教授认为:“足以使一方当事人合法地相信对方当事人会与其订立合同,并为此支付了一定的费用,那么中断谈判就是有过错的。”参见王利明:《债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4页。或“继续磋商义务”〔12〕参见周江洪:《缔约过程中的磋商义务及其责任》,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11-12页。,但两者不属于传统民法理论中前合同义务的内容,需要进一步的证成。
相似的解释困境也出现在德国法中。德国通说认为,磋商中一方当事人若引发相对人对缔约结果或特定缔约条件的合理信赖,而后又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中断磋商,该方应赔偿相对人因此产生的信赖利益损失,这被称为“无正当理由中断磋商”的损害赔偿。〔13〕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8-99页。尽管德国学说与判例同样倾向于将缔约信赖保护构建在缔约过失的基础之上,但义务违反的认定在教义学上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14〕针对这一问题,在德国有法典评注直接区分违反诚信和无正当理由中断磋商两种不同情况,但两者都属于缔约过失的范畴(《德国民法典》第311条),对于后者“信赖构成”(Vertrauenstatbestand)是核心。Vgl. BeckOGK/Herresthal, 2019, § 311 Rn. 365 あ.也有评注区分了保护义务违反与无正当理由中断磋商,对于后者义务违反的类型同样未予明确说明。Vgl. MüKoBGB/Emmerich,2019, § 311 Rn. 176 あ.德国司法实践早期曾要求缔约过失的成立以引发信赖的前行为具有过错为必要。〔15〕Vgl. BGH WM 1962, 936; BGH WM 1974, 508.由于这一要件过于严格,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后续又放弃了这一做法,引发信赖后无正当理由中断磋商这一事实本身即可能产生损害赔偿责任。〔16〕Vgl. BGH ZIP 1989, 514 (517).德国法院只否定了责任成立以前行为过错为必要的传统立场,至于是否有其他义务违反,还是其试图发展无过错责任,法院始终摇摆不定,学界的解读也大不相同。〔17〕Vgl. Krawitz, Schutz vorvertraglicher Investitionen, 1. Aufl., 2015, S. 50.
就中断磋商与诚实信用原则的连接因素,民法理论上有以下可能的方案,它们均是建立在诚实信用原则解释论的基础之上,这也为正确认识诚实信用原则在前合同阶段的意义提供了启发。
(二)“告知义务说”:与磋商程序相关的前合同告知义务
前合同告知义务除了关于合同目的或条款等实体内容外,也可能仅涉及磋商程序本身。所谓磋商程序的告知义务,是指如果当事人已有中断磋商的意图或者发现了可能导致磋商失败的风险,就不应再给相对人一定会缔约的印象;如果的确给相对人留下了这种印象,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其必须在磋商中将缔约意愿或能力的变化以及随时出现的外部障碍及时告知相对人。告知义务的履行必须达到足以使相对人认识到缔约风险或障碍的程度。〔18〕Vgl. Grunewald, Das Scheitern von Vertragsverhandlungen ohne triftigen Grund, JZ 1984, S. 711.在前述法律服务合同磋商案中,我国法院所称的“通知义务”即倾向于采此种解释方案,但其论证上的不足之处在于法院并未在事实上查明何时发生了缔约意愿、能力的改变或出现了外部障碍。该说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同样备受青睐,其一方面非常灵活,法院可以通过外部事实认定中断磋商的一方在某一中间时点的“不作为”构成义务违反;另一方面,程序性的告知义务不涉及中断磋商的行为评价,与合同自由原则兼容性强,避免触及适用“无正当理由中断磋商”所面临的教义学争议。
不过,告知义务说的局限性也较为突出。其一在于证明困难,缔约意愿是一个纯粹主观要素,在实践中原告通常无法证明被告引发信赖是否符合其内心真意,更难以证明被告在哪一具体时点改变其意愿。某一外在条件的变化是否真正构成缔约障碍也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很难由客观表象予以间接证明。其二在于保护范围不周延,从被告引起信赖到改变意愿一定具有时间差,因为不可能做到在引发信赖的同时又警示无法缔约的风险,即使被告在改变意愿时立即通知原告,原告在时间差内的信赖投资仍有保护的合理性。此外,法院通常仅能从外在环境是否变化及变化具体时点推知被告意愿的改变,这种推知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更令人诟病的是,法院试图通过寻找某一中间点以从实质上达成原被告分担损失的效果,这使事实判断本身掺杂了价值判断。〔19〕同前注〔17〕,Krawitz书,第43页以下。其三在于理论上仍有难以解释的问题,特别是中断磋商损害赔偿为何以无正当理由为必要。如果按照告知义务说的逻辑,义务违反仅在于磋商中的疏于告知,与之后的中断磋商行为无关,因而无必要关注中断磋商的原因。退一步说,即使被告没有引发原告的缔约信赖,当其丧失缔约意愿时也应及时告知原告退出磋商,否则将构成《民法典》第500条第1项所包含的“恶意继续磋商”。如果按照告知义务说的解释,中断磋商基本可以被恶意继续磋商所吸收,似无单独存在的必要。
综上,尽管告知义务的解释方案无须对中断磋商行为作出直接评价,客观上缓和了诚实信用与合同自由的潜在冲突,但仍无法完整构建中断磋商损害赔偿的教义学基础,也难以满足缔约信赖保护的现实需求。在告知义务之外仍有引发责任的其他因素。
(三)“行为矛盾说”:出尔反尔的行为规制及其否定
尽管表述上有所差异,但在我国已有学说与案例将中断磋商认定为义务违反,并承认前合同关系就是继续磋商或缔约义务的基础。前合同磋商固然是一种“特别结合关系”,但仅凭此尚不足以达到要求一方当事人放弃合同自由、通过缔约保护相对人的程度。否则,相对人可以动辄通过扩大信赖投资或拖延磋商进程达到锁定当事人继续磋商的目的。因此,前合同诚信原则或信赖关系本身无法证成以促成缔约或继续磋商为内容的义务,理论上必须在前合同关系外寻找更加坚实的义务解释基础。
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矛盾禁令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在我国民法理论中,行为矛盾禁令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其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进程中有很大的发展潜力。〔20〕王泽鉴教授特别指出“矛盾行为”作为子类型在诚实信用原则具体化过程中的作用。参见周江洪、陆青、章程主编:《民法判例百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在德国民法理论中,行为矛盾禁令的意义是在满足特定信赖构成时,行为人被禁止从事与其前行为矛盾的后行为。换言之,“出尔反尔”损害合理信赖被认定为一种违反诚信原则的具体情形并受到效力上的否定评价。〔21〕Vgl. Canaris, 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eutschen Privatrecht, 1. Aufl., 1971, S. 287 f.; MüKoBGB/Schubert, 2019, § 242 Rn.314 あ.在形式上,当事人中断磋商的后行为与引发信赖的前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成为中断磋商与诚信原则新的连接点。受行为矛盾禁令的启发,对于中断磋商的义务违反形成了两种较具代表性的解释方案,即所谓“不作为义务说”与“协作义务说”,两者都是对“继续磋商义务”的弱化和再解释,仅在程度和表述上略有区别。
不作为义务说认为,当事人在磋商中虽然不存在积极的缔约义务或磋商义务,但在其引发相对人缔约信赖时产生了一种无正当理由不中断磋商的消极义务或不作为义务。〔22〕Vgl. Lutter, Der Letter of Intent: Zur rechtlichen Bedeutung von Absichtserklärungen, 1. Aufl., 1998, S. 65 あ.协作义务说则认为应更积极地表述义务内容,不作为的概念既无法包含磋商中积极的协作与保护义务,也难以与告知义务相兼容。〔23〕Vgl. Küpper, Das Scheitern von Vertragsverhandlungen als Fallgruppe der culpa in contrahendo, 1. Aufl., 1988, S. 219.协作义务说基于行为矛盾禁令解释与限定传统意义上的继续磋商义务,其理论构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中断磋商是完全契合于行为矛盾禁令的范例。禁令的作用不在于评价引发信赖的前行为,而是禁止与前行为矛盾的后行为。第二,当事人在引发相对人的缔约信赖后,便产生了更高程度的前合同义务,即朝着与其引发信赖相一致的方向推进磋商的协作义务。第三,磋商是一种产生拘束力的渐进过程,只有在义务设定上坚持程序导向而非结果导向才符合磋商的性质;因而,协作义务在效力上限于消极信赖的范围,当事人不能主张具有结果性质的缔约或履行利益损害赔偿。〔24〕同上注,第216页以下。
这种观点通过“出尔反尔”这一事实将中断磋商与诚信原则相连接,使中断磋商本身成为法律评价的对象,在论证上较为完整。但该说并未发展为通说,主要原因在于欠缺实质论证。较具代表性的批评意见指出,协作义务说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行为矛盾禁令所遵循的是形式论证,即前后两行为在形式上的矛盾性,而不对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实质判断。这一形式结构在实际运用中很可能会产生论证上的缺陷,即在发现矛盾的过程中将须被证成的结论直接作为前提。在法律意义上,如果认为中断磋商与引发信赖是一对前后矛盾,至少需要证明这种信赖是值得法律保护的,然而这本身就是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信赖是否值得保护需要根据信赖保护的原理进行实质论证。〔25〕Vgl. Singer, Das Verbot widersprüchlichen Verhaltens, 1. Aufl., 1992, S. 280.
(四)诚实信用的解释范围与边界
前述关于前合同义务违反的理论尝试均有一定的说服力和适用范围,但在理论构成上也有各自的缺陷。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在于,各学说之间不仅对于磋商过程中的责任构成行为存在不同的认定,对于诚信原则的理解更是相去甚远。尽管理论上泛称当事人间有通知、协作与保护等前合同义务,但对于谋求更佳交易条件的当事人而言,对相对人的协作义务、保护义务边界的判断是极为困难的。
行为矛盾说的贡献在于从诚实信用的理论范畴中寻获了确定义务内容的客观方法,而非陷入特别结合关系的泛泛而谈。但该说在形式逻辑论证之外未能进一步探讨实质论证的标准。法律中的“前后矛盾”是规范评价,除了生活意义上的“出尔反尔”,前后矛盾是否形成了值得法律保护的信赖状态才是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关键,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需仰赖信赖保护的一般原理。
二、缔约信赖保护的信赖责任路径:信赖保护原则的自成体系
如前所述,诚实信用原则于责任证成上的困难主要是其在磋商阶段的不确定性以及论证过程的“形式化”。反对观点就此指出,缔约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及其保护范围、程度与具体路径,在本质上都是信赖保护原则的贯彻而非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因而形成了回归信赖保护一般原理的“信赖保护说”。尽管我国《民法典》并未为独立的“信赖责任”预留规范空间,但理论中仍不乏信赖责任独立于缔约过失的主张。如有学者认为对于缔约过程中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应以缔约过失责任与缔约信赖责任为基干进行新的体系构造。〔26〕参见朱广新:《合同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页。也有评注观点认为“区分缔约过失责任与信赖责任是非常可取的缔约责任体系构建,具有科学性”,似将《民法典》第500条理解为缔约过失与独立的信赖责任的集合。〔27〕参见朱广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通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89页。此种信赖责任路径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解决缔约过失路径的解释困境需要回归该学说的理论渊源。
(一)信赖责任理论的体系构建
信赖责任路径在理论渊源上主要受到了卡纳里斯信赖责任理论的影响,此前理论上多将权利外观作为适用信赖保护原理的基础,〔28〕此即“狭义”的信赖保护说,如叶金强教授认为:“表见事实的存在,是适用信赖原理的基础,不存在表见事实的情况下,信赖者对表见事实之外的外在事实发生信赖的,将会被直接排除在相应的信赖保护范围之外。”参见叶金强:《信赖原理的私法结构》,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12页。而卡纳里斯将德国私法体系中具有信赖保护功能的具体制度进行体系化整合,不仅扩充了信赖保护的适用范围,也强化了信赖责任外在体系上的“自成一体”。在内在体系中,信赖责任包括“权利外观责任”“强法律伦理必要性的信赖责任”以及“表示责任”等子类型,但以权利外观责任最为典型。〔29〕信赖保护原理于“使用他人名义的行为”情形的具体运用,参见余佳楠:《平台在自营业务中的法律地位——以信赖保护为中心》,载《法学》2020年第10期,第38页。这些责任类型客观上涉及不同的信赖状态,其保护的正当性、规范基础和程度也有所不同。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缔约信赖居于何种位置,信赖保护原理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支撑缔约信赖的保护,以及如何区分和协调信赖保护与诚实信用的体系关系仍需要厘清。
缔约信赖是一种对非现实存在的、未来某种法律状态的信赖,其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应当完全排除权利外观责任的适用,而其余几种责任类型均有适用的可能。
“强法律伦理必要性的信赖责任”是诚实信用原则嵌入信赖责任体系的产物,是两者的交汇点,其主要内容就是前文提到的“行为矛盾禁令”。行为矛盾造成的信赖责任构建在如下基础之上:当事人通过其先行行为以可归责的方式形成了相对人的某种特定信赖状态,当此种状态在随后的发展中难以逆转且当事人无法及时向相对人披露真实的法律状态时,当事人必须为自己引起的信赖状态所拘束。在行为矛盾禁令的判断中有两项标准是决定性的,其一在于相对人已经采取了特别重大的措施以适应或准备其信赖的法律状态,其二在于引发信赖的当事人通过相对人的行为获得了利益且其现在仍能保有该项利益。〔30〕同前注〔21〕,Canaris书,第530页以下。此处之所以强调实际保有利益,原因在于该种责任类型在性质上属于“履行责任”,即与信赖内容一致的积极履行义务,而非消极的信赖利益损害赔偿。此外,行为矛盾禁令的适用以先行行为的可归责性为前提,但卡纳里斯对此设定了极为严格的要求,仅限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唯有如此才存在强烈的、为法律伦理所不容的状态。换言之,其在强化禁令实际履行效力的同时,也相应地将禁令的适用范围从客观诚实信用限缩至主观上的故意与重大过失。〔31〕同上注,第543页以下。缔约过失路径之所以陷入解释困境,原因正在于多数情况下无法证明先行行为的过错,而此处的行为矛盾禁令如果以先行行为的重大过失为最低标准,则其对于缔约信赖保护的意义极为有限。在信赖责任理论形成时,行为矛盾禁令仍然是德国民法理论中有待进一步发掘的领域,而其后来的发展已远超卡纳里斯的预期。
“表示责任”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基于强风险归责的表示责任”与“基于保护义务违反的表示责任”,前者以因错误撤销意思表示时表意人的损害赔偿为典型,后者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缔约过失责任。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不要求过错归责,对于主张信赖保护的一方更为有利。而将两者在归责原则上区别对待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前一种情况中存在相当强的、更值得保护的信赖状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意人的内心真意完全无法为相对人所辨识,如果相对人可以从客观上认识到错误的存在,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即直接被排除。〔32〕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22条第2款。其二,对信赖产生有支配性的情况完全来自于表意人的影响或控制领域,与相对人无关,不存在适用与有过失规则的可能。相反,对于保护义务违反的表示责任,相对人的信赖状态相当弱,需要以过错作为额外的正当性基础;此外,责任成立也不要求导致效力瑕疵的事由完全归于表意人的领域内,此时与有过失规则与损害赔偿相兼容,相对人的过错不排除表意人的损害赔偿。此时,通过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各自法律义务的范围,并结合与有过失规则,可以实现法律效果的灵活性,促进个案正义的实现。〔33〕同前注〔21〕,Canaris书,第535页以下。卡纳里斯认为在中断磋商的情形中可以首先考虑保护义务违反,但在通常情况下因证明困难,应当转而适用“基于强风险归责的表示责任”。〔34〕同上注,第544页。
综上所述,“基于强风险归责的表示责任”与“基于保护义务违反的表示责任”这一区分是在德国法基础上的极为精致的教义学分析,深刻揭示了《德国民法典》第122条规定的错误意思表示撤销损害赔偿与缔约过失在内在机理上的差异,这与《德国民法典》所采的“意思说”,亦即对内部错误可撤销性的宽容态度一以贯之,体现了意思表示理论与信赖责任理论的体系互动。〔35〕意思表示错误的模式选择与消极利益损害赔偿归责原则、撤销权期限以及起算点在体系上是联动的,如果意思表示错误模式倾向于保护表意人(即德国法的选择),在后者就要侧重于相对人信赖的保护、限制表意人的利益。此种体系关系,参见薛军:《论意思表示错误的撤销权存续期间——以中国民法典编纂为背景的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8页。这不仅是我国学说中缔约过失双重归责论的主要来源,〔36〕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5页;同前注〔1〕,韩世远书,第169-170页。也是我国学说中信赖责任独立论的主要依据。〔37〕参见朱广新:《信赖保护原则及其在民法中的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275页。但我国《民法典》并未对“基于强风险归责的表示责任”留有任何解释空间,无论第500条第3项的缔约过失责任一般条款,还是第157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的损害赔偿均坚持过失归责原则。如果对《民法典》第147条的重大误解制度按照“信赖说”进行解释、严格限制甚至排除内部错误的撤销权,坚持过失原则也不会产生信赖保护不足的疑虑。〔38〕对于重大误解制度“信赖说”的解释方案,参见韩世远:《重大误解解释论纲》,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3期,第679-682页;龙俊:《论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构造》,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第128-130页。因此,信赖责任独立性在我国《民法典》的规范框架内是难以实现的。
(二)缔约信赖保护的路径探寻:信赖责任体系内的类推适用
本着上述信赖责任理论的基本立场,缔约信赖保护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引发信赖的因素完全来自于表意人的影响和控制领域,同时其真实意愿无法在客观上为相对人所识别;诚实信用原则则被限缩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引发的缔约信赖。主张信赖保护说的学者往往更倾向于信赖责任体系内的类推而非适用体系外的诚实信用一般条款。
最具代表性的是拉伦茨,其主张将《德国民法典》第122条的信赖责任类推适用于缔约信赖保护,这与卡纳里斯主张的适用“基于强风险归责的表示责任”完全一致。在拉伦茨看来,中断磋商损害赔偿是一种无涉义务违反的、纯粹的信赖责任。如果当事人通过磋商中的行为引起或强化了相对人对于以特定条件缔约这一未来状态的信赖,且达到了可以合理地不加怀疑的程度,相对人即被引入了一种特别风险状态,此时的事实及法律状态与因错误撤销意思表示的情况极为相似,应采无过错归责原则。〔39〕Vgl. Larenz, Bemerkungen zur Haftung für culpa in contrahendo, FS-Ballerstedt, 1978, S. 417 f.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偶有判决采此思路。〔40〕Vgl. BGH WM 1969, 595 (596); MüKoBGB/Emmerich, 2019, § 311 Rn. 182.然而,这一类推方案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原因在于其忽略了合同表象存在与否这一关键前提,两者欠缺类推的基础。〔41〕梅迪库斯在缔约过失中又区分了“没有有效合同的表象而致害”与“表象上构成订约,合同不生效力”两种不同的信赖构成,前者涉及中断磋商,后者则是缔约过失的最初形态之一。同前注〔13〕,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98页。
卡纳里斯对此引入了更具争议的类推方案,其虽然指出中断磋商损害赔偿与《德国民法典》第1298条婚约解除损害赔偿规定背后的法理是一致的,但未明确是否类推适用该法条。其理由在于婚约也是一种引起信赖的缔约允诺;当事人对其既不能请求实际履行、也不能主张违约金,无法以意思自治的方式实现履约保障;且正当原因是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这些情况均与中断磋商基本一致。〔42〕同前注〔21〕,Canaris书,第544页。这一类比方案的问题在于婚约在性质上已构成预约,仅因其特殊的人身属性和法律特别规定而不具有履行力,这与中断磋商的事实状况及法律评价均不相同。总之,德国法中通过信赖责任体系内的类推适用解释中断磋商损害赔偿的尝试并不成功,其虽然避免了义务认定与归责问题,但缺乏对应的请求权基础。我国民法理论中信赖责任独立的观点同样面临欠缺请求权基础的困境,学者多在立法论而非解释论的层次上讨论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
(三)缔约信赖保护的美国法方案:一般化的信赖责任及其缺陷
面对缔约信赖保护的问题,英美法系同样未形成统一的制度方案。有美国法院回归衡平法中的“允诺禁反言”准则并将其形塑为一般性的信赖责任制度,此种方案被英国法明确否定,〔43〕See James J. Edelman, Liability in Unjust Enrichment Where a Contract Fails to Materialize, in Andrew Burrows, Edwin Peel(eds.), Contract Formation and Par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78-179.但为澳大利亚、新西兰所继受。〔44〕澳大利亚标志性案例,参见Waltons Stores (Interstate) Ltd v. Maher (1988) 164 CLR 387;新西兰标志性案例,参见Wilson Parking New Zealand Limited v. Fanshawe, 136 Limited [2014] NZCA 407.
美国法保护缔约信赖的标志性案例是“霍夫曼诉红色猫头鹰案”〔45〕See Hoあman v. Red Owl Stores, Inc., 133 N. W. 2d 267 (Wis. 1965).,该案显著扩张了衡平法的适用范围,在美国合同法理论中意义重大。该案不仅是美国法学院的经典教学案例,我国民法学者也大多将其作为“恶意中断磋商”的典型示例。〔46〕同前注〔1〕,韩世远书,第164页;同前注〔37〕,朱广新书,第276页;同前注〔1〕,黄薇主编书,第959页。
“允诺禁反言”在概念上非常简明,是指如果一方作出了允诺,即被禁止对其进行否认。该准则的规范目的在于作为一种法律上的障碍,防止允诺人“出尔反尔”损害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允诺禁反言”是一种合同拘束力欠缺时的替代性履行机制,在原理上与德国法中的行为矛盾禁令基本一致。
该案涉及加盟合同的磋商,原告希望开办一家被告公司的加盟商店,被告允诺原告将来一定能够以某一数额的加盟费用缔约,并以积累经验为由屡次要求原告作出了大量的缔约准备和投资。原告倾其所有地配合被告的各项要求,包括出售了原先长期经营、获利颇丰的产业,但最终被告却临时提价并要求改变出资性质从而导致磋商失败。美国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依据“允诺禁反言”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的信赖利益损失。运用“允诺禁反言”保护缔约信赖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三项突破,因而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第一,其在性质上突破了“矛盾规则”,成为积极的请求权基础。矛盾规则由英国上诉法院提出,“允诺禁反言”只能作为“盾”而不是“矛”,即只能作为一项拒绝履行的抗辩,而不能作为一项要求他人积极履行的诉由。根据丹宁勋爵的解释,英国法的这种制度安排主要是为了维护对价原则在普通法中的核心地位。〔47〕See Combe v. Combe [1951] 2 KB 215, 219.在美国法中,“允诺禁反言”则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其请求权基础的地位最终也为《美国合同法第二次重述》第90条第1款所确认。〔48〕《美国合同法第二次重述》第90条第1款规定:“如果允诺人应当合理预见其允诺足以引起受允诺人或第三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且其允诺现实引起了此种作为或不作为,若只有通过履行允诺才能避免不公平,则该允诺有拘束力。因违反允诺而产生的救济应限定在公平要求的范围内。”第二,其突破了“允诺禁反言”的既有功能和适用范围,“允诺禁反言”的原有功能在于调和对价原则的严苛,避免因允诺无拘束力而导致信赖相对人在极端情况下的重大不利,是一种非常例外的利益调整工具。〔49〕在英美法中,“允诺”这一概念有特殊的规范意义,拘束力的产生以“允诺+对价”(合同)为原则,以“允诺禁反言”为例外。See Mindy Chen-Wishart, Contract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08.此处的“允诺”要求内容具体、明确且完整,其与合同的区别仅在于欠缺对价。而该案认为磋商中关于具体缔约条件或缔约结果的“允诺”即足矣。第三,“允诺禁反言”的原有效果在于使允诺产生拘束力,然而该案提供了新的救济方式,即消极利益损害赔偿。尽管学界普遍肯定该案保护缔约信赖的象征意义,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其混淆了积极信赖保护与消极信赖保护的关系,是对“允诺禁反言”的误用,其后也未被裁判完全承继。〔50〕See E. Allan Farnsworth, Precontractual Liability and Preliminary Agreements: Fair Dealing and Failed Negotiations, 87 Columbia Law Review 217, 237-238 (1987).美国学者试图重新为该案判决寻找规范基础,最主要的观点是缔约允诺已经构成预约,〔51〕See Alan Schwartz, Robert E. Scott, Precontractual Liability and Preliminary Agreements, 120 Harvard Law Review 661, 673-674 (2007).此外也有观点主张不实陈述的侵权责任〔52〕See Charles Fried, Contract as Promise: A Theory of Contractual Oblig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4.或诉诸于磋商阶段的诚实信用〔53〕See Charles L. Knapp, Enforcing the Contract to Bargain, 44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673, 686-690 (1969).。
“允诺禁反言”作为一般性的信赖保护制度也引起了我国民法学者的关注,但宽泛的“信赖”以及规范指向不明的“允诺”在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极易产生概念上的误导。我国《民法典草案(一审稿)》在第281条规定了“构成合同条款的允诺”,其目的原在于处理前合同陈述是否构成合同内容这一问题,而正因“允诺”这一宽泛的概念使缔约信赖保护、前合同陈述的解释、合同形式对合同内容的确定力、依附于合同的独立保证甚至是传统民法中的单方允诺等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学说中的支持观点即以该条在价值上体现“允诺禁反言”、保护受允诺人的缔约信赖为由,但实际上两者是不相关的法律问题。〔54〕对该条的支持观点,参见刘承韪:《民法典合同编的立法建议》,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3期,第32-33页。该条在我国民法学界引发了激烈争议,最终被立法机关删除。德国民法理论中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德国学者斯托尔受“允诺禁反言”的启发提出缔约“允诺”就是传统民法中的单方允诺,但是受允诺人不因此取得积极的履行请求权,仅能将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作为强制缔约的“弱替代”。〔55〕Vgl. Stoll, Vertrauensschutz bei einseitigen Leistungsversprechen, FS-Flume, 1978, S. 754 あ.这种观点不仅与单方允诺的既有规范定位有所冲突,而且其完全不考虑具体的信赖构成,一概赋予缔约允诺以拘束力,这并不符合信赖保护的原理。〔56〕同前注〔23〕,Küpper书,第213页以下。
(四)信赖责任路径的解释功能与局限
相较于缔约过失路径,信赖责任路径通过引入风险等因素对缔约信赖的可保护性进行了实质权衡,更加贴合磋商背景,也更进一步地触及了中断磋商的核心议题。但信赖责任路径也存在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信赖保护原则不具有直接的裁判效力,该说始终难以为中断磋商损害赔偿找到合适的请求权基础。第二,在信赖保护的范围和程度上,该说也难以区分积极信赖与消极信赖,尤其是缔约信赖的保护为何仅能以损害赔偿作为履行的“弱替代”。第三,由于各类型的信赖构成建立在不同具体制度的基础上,如果过于强调信赖保护的自成一体,必然会冲击民法体系中既有概念与规则间的界限,造成混淆和误解。最重要的是,信赖责任路径刻意地割裂了诚实信用与信赖保护的内在关联,在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解与适用上侧重于主观方面的限定,这并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客观化发展趋势。
三、缔约信赖保护的预约合同路径:拘束力原则的柔化
《民法典》第495条系我国立法首次明确预约合同制度,该制度与缔约过失在缔约信赖保护中的体系关系理应得到理论研究的重视。对于预约合同的法律效果,民法学界观点纷呈,莫衷一是,整体上呈现为以订立本约为效果、承认预约完整拘束力的“缔约说”,以诚信磋商为效果、柔化预约拘束力的“磋商说”,以及依预约内容确定性区分缔约或磋商效果的“内容决定说”。这三种学说为预约合同制度设定了不同的功能,也形成了与缔约过失完全不同的体系关系:若采“缔约说”,预约合同与缔约过失分属履行利益与信赖利益的实现方式;若采后两种学说,则会形成法定诚信磋商义务与约定诚信磋商义务的并存,由于预约合同同样以非要式为原则,当事人在磋商阶段引起相对人缔约信赖的言行很容易构成明示或默示的预约,进而形成缔约过失与预约违约责任的竞合。
《民法典》第495条对预约合同的具体构成、法律效果与功能定位采模糊立场,为学说争议保留了空间。该条第1款在构成上仅规定了“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并列举了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等形式,并未对预约内容的确定性作出要求;第2款则规定预约不履行的法律效果是“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否包括实际履行(即“订立本约”),损害赔偿的范围是履行利益还是信赖利益,该条均未予明确。在方法论上,此种立法上的开放性奠定了进一步法律续造的基础。在域外法中,德国法与美国法中的预约制度分别对应我国民法理论中的“缔约说”与“磋商说”,两者在规范目的及体系上均有重大区别,对两者的比较分析为我国预约合同制度的路径选择提供了启发。
(一)“缔约说”的德国法实践:预约作为订立本约的工具
在德国法中罕有学者依预约路径处理缔约信赖保护问题,原因在于德国法对预约制度的功能有特别的认识。预约的主要功能在于当现实中存在事实障碍或法律障碍导致不能立即缔约时,通过预约提前产生合同的拘束力。〔57〕Vgl. MüKoBGB/Busche, 2019, vor § 145 Rn. 60.预约的唯一效果在于订立本约,法院得直接根据有效的预约拟制当事人订立本约的意思表示。这要求预约在内容上已经具有高度的确定性、不能留有不合意,法院已经可以在不需要当事人继续磋商的情况下直接从预约中提取本约。与合同成立的判断一致,预约的存在与否也是规范判断,亦即意思表示的解释问题。
在预约成立与否的规范判断中,首先要求当事人应具有受拘束的意思。在当事人作出将来一定缔约的表示时,其受预约拘束的意思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方面表示当前不能订立本约,即无“受本约拘束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将来一定缔约的意思,即“受预约拘束的意思”。如果认为此时当事人欠缺受预约拘束的意思,那么其引起相对人缔约信赖的表示反而因与真实意愿不一致而构成前合同义务的故意违反。对相对人而言,其已经基于缔约信赖作出进一步的支出或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准备,也不能认为其欠缺未来缔约的意思。因此,“受预约拘束的意思”这一要件并非缔约允诺构成预约的障碍。
最为关键的是,德国法对预约有高标准的确定性要求,要求本约的内容已经由预约确定或可得确定。〔58〕Vgl. Staudinger/Bork, 2020, vor § 145 Rn. 56 あ.这意味着一方面合同必要之点已经磋商完成,另一方面当事人也应就磋商中任何一方提出的待决事项达成合意,不能存在公开的不合意。理由在于,如果在磋商尚存争议时就认定当事人就已磋商完成的事项达成了预约,然后再由法院对其他内容进行补充,将明显违背当事人的意思、过度干预合同自由。根据疑义规则,在磋商整体完成前对于个别事项的合意不具有拘束力,亦同此理。〔59〕《德国民法典》第154条第1款确立了“疑义规则”:“当事人未就契约之各点达成合意,即使仅一方当事人表示就该点应达成协议,有疑义时,应认为契约不成立。对于各点所作之说明,纵经记载,当事人仍不受其拘束。”按照这种思路,预约与本约的差别不在于内容的确定程度,而是受拘束的意思指向现在还是将来。缔约允诺构成预约的情形只可能在于,双方已经完全可以达成本约、不存在不合意,但一方允诺现在不缔约而在将来某一时间点缔约。当该方不履行预约时,对方可以诉请实际履行,法院直接根据预约内容拟制本约的意思表示,本约即可成立、生效。综上,德国法中预约制度的功能单一,仅为确定和拟制本约,既无法巩固部分磋商成果,也不能使缔约允诺本身具有合同拘束力。德国学者普遍承认,预约的效果是合意基础上的“强制缔约义务”,而非诚实信用基础上的“强制磋商义务”,其正当性完全来自于合同自由与拘束力原则。〔60〕Vgl. Busche, Privatautonomie und Kontrahierungszwang, 1. Aufl., 1999, S. 113; Palandt/Ellenberger, 2020, vor § 145 Rn. 19;Staudinger/Bork, 2020, vor § 145 Rn. 51.
(二)“磋商说”的美国法实践:预约作为缔约信赖保护工具
英美普通法中的预约并非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或制度,当事人在前合同磋商中形成的各种形式上的约定或安排,无论其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均属于预约的范畴。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意向书或信心保证函,内容上是磋商当事人向相对人允诺其严肃的缔约意愿,减少相对人对于推进磋商所需信赖投资的疑虑。另外,还有备忘录或所谓“同意的约定”(Agreement to agree),即双方载明已经磋商完成的合同条款,巩固既有的磋商成果。〔61〕See John Cartwright, Formation and Variation of Contracts, Sweet & Maxwell, 2014, p. 29-30.
传统普通法对预约效力的立场与德国法相似,采拘束力的“全有”或“全无”路径:要么具有完全拘束力、实现履行利益;要么完全无拘束力,相对人无法获得包括信赖利益在内的任何损害赔偿。如果预约在内容上足够完整、确定,足以从中提取出本约的权利义务内容,法院即可推断出当事人受拘束的意思,预约本身包括其中载明的条款均具有与本约一致的合同拘束力,相对人可以主张履行利益。如果不能达到上述确定性要求,那么意向书、信心保证函仅产生道德层面上的义务,并没有法律拘束力。对于备忘录或“同意的约定”,只要其中载明仍有条款留待后续磋商,即彻底排除其拘束力。唯一的例外在于如果当事人明确表示其将支付相对人某些准备工作的费用,或在未缔约时偿还相对人某些成本,则将其视为单独的、与本约无关的费用承担约定,在相关费用的范围内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62〕同上注,第29-30页。
20世纪80年代,美国法院在既有的“全有”或“全无”路径之间开辟出一条中间路径,即不符合确定性要求的预约也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但相对人既不能主张实际履行,也不能主张履行利益。其拘束力仅体现在预约中的“缺省规则”,即预约的当事人共同承诺诚信参与磋商,努力协作达成最终合同,这为当事人主张信赖利益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63〕同前注〔51〕,Alan Schwartz、Robert E. Scott文,第674-676页。美国法原则上不承认诚实信用原则在磋商阶段的适用,因而这一司法拟制的诚信磋商或协作约定有其特别的意义。此后,美国学者通常会讨论预约制度中缔约信赖的保护问题。由于当事人引发相对人缔约信赖必定需要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作出将来缔约的意思表示(即英美法中所称的“允诺”),而这一意思表示又为相对人所接受并引发了信赖投资,学者多宽泛地认定此时双方已达成预约,并将预约作为缔约信赖保护的主要工具。
(三)我国法中缔约信赖保护与预约制度关系的厘清
从上述比较法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预约合同的制度设计中,预约的规范功能、范围界定、效力与责任内容是基本的逻辑主线。如果按照“缔约说”,在规范目的上仅将预约作为一种实现本约的拘束工具,便必然要求其内容达到本约的确定程度,并以明确的将来缔约意思与本约相区分;在范围上亦排除仅表达缔约意愿或巩固既有磋商成果、仍有内容留待后续磋商的意向书;预约的效力体现为强制缔约义务,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就是实际履行,当事人得根据预约内容、无需继续磋商而直接请求订立本约。如果按照“磋商说”,将预约定位为一种灵活的磋商与信赖保护工具,可以巩固和确认已有的磋商成果,其构成门槛即显著降低,包括缔约允诺在内的各种意向书均属于预约的范围;与此对应,其法律效果仅限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如果采兼容两者的“内容决定说”,预约的范围虽与“磋商说”一致,但法律效果会依预约内容的确定程度予以区分,仅在达成完全合意时才能主张实际履行或履行利益损害赔偿。实际上,“内容决定说”内部存在两种构成及法律效果迥异的法律机制,在法律适用上必须采取明确的二元区分。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预约—实际履行”与“预约—诚信磋商”的裁判路径即分别是“缔约说”与“磋商说”的体现,其中“预约—诚信磋商”被认为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主导性裁判思路。〔64〕参见耿利航:《预约合同效力和违约救济的实证考察与应然路径》,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29-36页。尽管我国民法学说采用了多元的概念表述,但实质上均可被归入上述三种类型之中。〔65〕“缔约说”常被表述为“实际履行说”“强制缔约说”“应当缔约说”。“磋商说”常被表述为“诚信磋商说”“必须磋商说”。
预约制度规范功能、范围、构成与效力的体系关联集中体现在“意向书”的性质认定中。《民法典》第495条第1款对修订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2条作出了实质性修正,将意向书与备忘录排除出预约的范围。〔66〕根据法释〔2020〕17号,法释〔2012〕8号第2条被删除。意向书在性质上之所以与预约不同,原因在于意向书仅派生出当事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继续磋商的义务,预约合同则设定了当事人订立本约的义务。恶意违反意向书规定、造成对方损害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违反预约则产生违约责任。〔67〕参见王利明:《预约合同若干问题研究——我国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述评》,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1期,第56-57页。意向书要构成预约,除了实体性条款具体、确定外,当事人还必须有受拘束的意思。如果双方明确约定了未来合同的内容且未来据此签约,则应当承认该约定的效力,在一方违反约定时法院可以强制当事人缔约。〔68〕参见许德风:《意向书的法律效力问题》,载《法学》2007年第10期,第88-89页。因此,按照“缔约说”的基本观点,缔约过失制度保护意向书引发的缔约信赖,而预约制度旨在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两者的规范基础不同、功能有别。如果按照“磋商说”的观点,预约的效力仅在于诚信磋商义务,那么预约和意向书在性质上就没有差别。因此,仅有“缔约说”可以逻辑一贯地解释《民法典》第495条第1款对意向书的排除,是一种更符合立法条文的解释方案。
“磋商说”在实质论证上也存有不足之处。其论据之一在于对当事人的保护更充分,“因为如果一方当事人不诚实磋商,另一方可依据缔约过失责任要求赔偿,不会使磋商义务流于形式”。〔69〕同前注〔27〕,朱广新、谢鸿飞主编书,第236-237页。该论据将缔约过失责任等同于预约违约责任,与《民法典》第495条对预约的合同定性并不相符。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同样与预约的拘束力无关,对意向书的违反也可能构成缔约过失责任。“磋商说”无法解释预约产生的“诚信磋商义务”与缔约过失基础上的“无正当理由中断磋商”的实质区别,时常将两者混同。例如在一则公报案例中,法院认为预约违约责任要以当事人对中断磋商有无正当理由为前提,如果当事人已公平、诚信地继续磋商,只是基于自身利益无法就未决条款达成合意就不属于违约。〔70〕参见“戴雪飞诉华新公司商品房订购协议定金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8期,第33页。这种观点与合同的基本逻辑是矛盾的,合同拘束力的产生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与当事人违约时是否有正当理由无关,追求自身利益更不能成为当事人摆脱违约责任的正当理由;中断磋商有无正当理由仅是缔约过失责任的考虑因素。
“磋商说”的论据之二在于“缔约说”虽然在法律适用上更为清晰,但过于僵化。而“信赖说”更为弹性化,其“结合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的具体阶段和当事人的利益需求加以判断,从而使预约制度更大程度地发挥功能、反映和满足磋商阶段当事人的不同利益需求”。〔71〕陆青:《〈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评析》,载《法学家》2013年第3期,第127页。该文正确认识了预约的体系关系,即预约构成和效果上向本约规则靠拢,预约规则的适用空间即应受到严格限制。这一论据的不足在于,民法规范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或裁判标准,并非所有制度都要讲究“弹性”,是否保持“弹性”应以制度背后的规范目的为基础。预约制度的内在逻辑是合同拘束力原则,其构成和效果也要严格遵循“刚性”拘束力原则的内在要求,不能脱离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则“另起炉灶”,形成一种所谓效力柔化的“拘束力”。〔72〕不同观点,参见汤文平:《论预约在法教义学体系中的地位——以类型序列之建构为基础》,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4期,第983-986页。将双方当事人的信赖状态、利益衡量引入预约拘束力的判断并相应地降低合同拘束力的一般标准和效力,在理论上将导致法律行为效力体系的紊乱。这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完全符合拘束力条件的预约合同因法院采纳不同的学说见解和裁判路径而在效果上仅得到“弹性化”的处理。这种不确定性明显违背了拘束力原则的确定性要求。
从体系论看,“磋商说”在对“拘束力”存有特别认识的同时,又在法定诚信原则之外形成了“约定诚信磋商义务”的解释思路,但这种思路与前述“无正当理由中断磋商”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没有本质差别;对“正当理由”的认定,根据信赖构成的强弱有所区分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解释问题,无法证成本质差别。美国法上之所以产生“磋商说”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缔约信赖保护的规则供给不足,普通法明确拒绝前合同诚信原则,而衡平法中的“允诺禁反言”又被认为是积极信赖保护的工具。在我国《民法典》第500条第3项明确承认前合同诚信原则时,根据不同的磋商背景、考虑当事人信赖状态的可保护性以及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冲突本来就是诚信原则具体化的应有之义。
从方法论视角审视,兼顾不同的磋商背景与信赖构成,在《民法典》第500条第3项内寻求针对缔约信赖保护、统一的诚信原则解释方案更符合民法体系的思路。仅因事实上信赖构成的强弱有别就放弃对法定诚信磋商义务的解释,通过打破既有的拘束力原则再平行地设置一种“约定诚信磋商义务”,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复杂,还使预约合同制度丧失了其原本的规范逻辑、无限延伸为一个“无所本”的庞杂集合,造成了理论体系和司法实践的紊乱。因此,通过柔化拘束力原则使预约合同制度成为消极信赖保护的工具,这一路径既不合理,也不符合《民法典》的体系化要求。所以,《民法典》第495条在解释上应恢复其基于拘束力原则的制度“刚性”,而保护缔约信赖的“弹性”功能应由《民法典》第500条第3项承担,教义学的任务正在于此。
四、缔约信赖保护的规范证成
上述三种规范路径及其理论建构虽各有局限,但从不同面向解构了缔约信赖保护,为建构完善的教义学方案指明了方向。
缔约过失路径将观察视角置于中断磋商的当事人,难点在于确定义务违反的行为,因为在明确存在前合同义务违反时,基本上都能满足以客观注意程度为标准的过失要件,而寻找义务违反的行为就需要对前合同诚信原则予以具体化。如果此时再将诚信原则解释为当事人的某种主观过错或可谴责因素就会陷入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因为过错的认定又需要以义务违反为前提;反之,如果将前合同诚信原则宽泛地解释为保护义务,此时其更像一种法律伦理意义上的形式符号,难以为义务履行提供实质的指引。如果在预约合同功能上采纳“缔约说”,其无法成为缔约信赖的保护路径;即使采纳“磋商说”,诚信磋商义务的认定仍受制于在特定磋商背景中对诚信原则的具体化。因此,前合同诚信原则的具体化是缔约信赖保护的核心问题。
信赖责任路径过于强调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将违反诚信原则等同于主观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但其回答了为什么缔约信赖是一种值得法律特别保护的信赖的问题。由于表意人的真实意愿在客观上难以识别,再将其作为缔约过失构成要件的意义非常有限。但信赖责任路径存在难以克服的体系障碍,其内部存在积极信赖与消极信赖的界分难题,外部则造成了信赖责任与缔约过失的分离。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缔约信赖保护的规范证成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在目的论上,何种情况下的缔约信赖是值得保护的。其二,在解释论上,诚实信用原则是否足以包容缔约信赖保护的目的。
(一)目的论证成:缔约信赖可保护性的基础与范围
关于缔约信赖的保护条件与范围,信赖责任说引入了风险来源、支配与负担等判断因素,信赖构成与风险论证被极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于磋商失败的风险,合同自由原则背后的分配方式是非常清晰的,双方当事人以各自的成本对磋商失败承担风险。双方均应有明确预期,为了吸引对方订立合同、进行履约准备所付出的信赖投资都将由其自担风险,不能要求对方赔偿。这一自己风险原则的合理性在于“原则上即应由交易者不断评估交易的可能利益而决定投入缔约的成本与缔约的步调,在交易者之间没有达成程序共识的情形,轻易以法律要求一方承担交涉中断的所有缔约成本,会使交易者轻易投入缔约成本或履约的准备,而造成资源的浪费”。〔73〕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13页。
缔约信赖保护是自己风险原则的例外,要探求这一例外责任的正当性首先需要关注风险的具体内容是一般磋商支出还是信赖投资。一般磋商支出是指同一类型磋商通常支出的必要成本,一般包括行政、人力以及标的信息的提供与证明成本。之所以强调同一类型,原因在于不同合同类型受合同性质、目的及交易习惯的影响而对磋商行为有特别要求,例如在买卖合同磋商中提供样品、在招投标过程中提交标书、在房屋装修合同磋商中提出具体的设计方案。信赖投资则是指相对人在必要成本之外又负担了其他与磋商目的并不直接相关的非必要成本,且这些成本只有在合同成立后才有其意义,通常是相对人为履约准备或当事人便利所作的支出。一般磋商支出是参与磋商的固有风险,无关磋商的深入程度、结果的评估以及双方的信赖;信赖投资则并非磋商必要,由相对人根据信赖程度予以决定。两者与缔约信赖的结合程度不同,在责任构成上即有显著差异。
其次,缔约信赖保护所处理的是由外部引发的信赖投资,而非相对人自招风险。换言之,相对人之所以愿意付出比一般磋商更高的成本是基于缔约信赖,而不是为了在不确定状态下提高磋商成功的可能性。相对人的缔约信赖应由当事人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所引起,此外还应具有磋商深入程度的客观基础。〔74〕See John Cartwright, Martijn W. Hesselink (eds.), Precontractual Liability in European Privat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94-195.在当事人对于是否缔约未作明确表示或双方在磋商中尚未就合同必要之点达成一致时,相对人作出信赖投资仍属于自甘风险,不属于受保护的信赖。
最后,仅当磋商当事人之间的风险分配极端失衡时才会引发缔约信赖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一方当事人通过引发缔约信赖将相对人引入特别风险,其目的在于将相对人留在磋商关系中或消除相对人对进一步投资的疑虑。引发信赖与否取决于该当事人的主观意愿,不能立即缔约的原因也往往受其影响。第二,即使在特别风险状态中,具体的风险范围也由该当事人掌握,这体现在其积极地要求相对人为特定行为,或者基于其特殊的合同目的或需求可以合理地推导出相对人的提前准备与配合行为,如履行期限的急迫以及标的的特殊性质,或者其鼓励或同意相对人基于信赖的自发准备行为。在德国法中曾出现不动产买卖双方已约定对价但尚未完成合同成立所必需的法定公证手续,出卖人在同意买受人提前改建和装修不动产后又临时提价的案例,此种同意即明显扩大了买受人的风险范围。〔75〕Vgl. BGH NJW 1996, 1884.第三,从风险引发到实现取决于当事人的内部意思,但客观上其真实内容及前后变化难以为相对人及时探知。
总之,磋商当事人的风险对比呈现失衡状态,风险的来源、范围、支配与实现全部由一方当事人控制,但其对此不承担任何风险。此时很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当事人可以藉此要挟相对人接受有失公平的交易条件。正是基于风险论证,相对人的缔约信赖保护不仅符合规范目的,也有法伦理上的必要性。
风险论证也得到法律经济分析的支撑,有美国学者主张对于中断磋商,合同法应追求稳妥的中间责任规则,才能实现最有效率的磋商投资并保障当事人的磋商自由。无责任规则将产生所谓“套牢问题”(hold-up problem),导致当事人在磋商中怯于投资;严格责任规则则会诱发过度投资,造成资源的浪费,这两种极端规则都将扭曲当事人的缔约决定。中间责任规则的内容之一,就是由磋商中“出尔反尔”的当事人对相对人的信赖成本负责。此种规则不仅不会冷却当事人磋商的热忱,反而会通过引导有效率的投资,提升当事人参与磋商的意愿和效率,同时确保当事人缔约的动因不被扭曲。〔76〕See Lucian Arye Bebchuk, Omri Ben-Shahar, Precontractual Reliance, 30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23, 456-457 (2001).
(二)解释论证成:诚实信用原则对缔约信赖保护的包容力
近年来,我国民法理论对诚信原则的研究更为深入,认为诚实信用是一种客观行为标准,而非限于对主观“恶意”的道德谴责。〔77〕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立法机关曾认为缔约过失的归责原则是“故意”或“恶意”。同前注〔37〕,朱广新书,第272-273页。尽管诚实信用有其概念上的不确定性,但仍有一定的可把握的价值取向,其要求当事人相互体谅、以正直的方式行使权利与自由,不能仅以实现自己利益作为唯一的考量依据。〔78〕参见易军:《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脉络》,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64-65页。也有观点认为,诚信原则的文义和公平正义共同构成该原则的两大支柱。参见李夏旭:《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的适用及限度》,载《法学》2021年第2期,第59页。客观诚信说是诚信原则包容信赖保护的基础。
诚信原则对信赖保护的包容并非法律适用上的“修辞”,而是基于两者作用机理的“融贯”。在民法基本原则的体系中,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都体现了民法对社会公共道德的维护,相较于公序良俗仅消极地设定民事主体不得逾越的道德底线,诚实信用则强制民事主体积极地实现特定道德要求。与此对应,相较于公序良俗的普适性,诚实信用通常仅作用于法律上有特殊联系的民事主体之间。〔79〕参见王轶:《论民法诸项基本原则及其关系》,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97页。正是民事主体间的“特别关联”为诚信原则积极的道德要求与更高的行为标准提供了正当性基础。〔80〕于飞教授认为:“只有在有一定法律上关联的当事人之间,要求其依诚信标准为行为才有正当性。如果当事人之间并无任何‘特别关联’,这种较高的注意义务就无从建立。”参见于飞:《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区分》,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153页。而此种“特别关联”同样是信赖产生的基础,或者信赖关系本身就足以构成一种“特别关联”。有学者就此指出,正是基于信赖关系才能要求当事人遵守诚信原则。〔81〕参见王利明:《论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界分》,载《江汉论坛》2019年第3期,第131页。“特别关联”与信赖关系是一体两面,以前合同关系为例,民法理论上既认为基于当事人的信赖产生“特别结合关系”,也将前合同关系本身界定为一种信赖关系,并在此种“特别关联”的基础上发展出前合同诚信原则与前合同义务。此外,“特别关联”的意义同样体现在行为标准的认定中,当事人之间的信赖构成随“特别关联”的法律性质和紧密程度而强弱有别,注意义务的标准亦随之调整,信赖程度越高,注意义务标准就越高,因而诚信原则在适用时总是呈现个案衡量的特点。
在域外法中,诚信原则对信赖保护的包容性不断增强。20世纪后期的《欧洲合同法原则》虽在总则第1:201条规定了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原则,但并未作出明确定义,仅规定其具有效力上的强制性。而近年来由学者编纂的《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于第I-1:103条第1款明确将诚信原则定义为“一种诚实、透明以及考虑相对人利益的行为标准”。更重要的发展在于,该条第2款特别将损害合理信赖的前后行为矛盾作为违反诚信的具体类型。〔82〕参见欧洲民法典研究组、欧盟现行私法研究组编著:《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和示范规则》,高圣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2-63页。该款的规范功能在于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免于当事人矛盾行为的损害,违反诚信的构成以信赖合理性的判断为前提,从而搭建起信赖保护原理进入诚信原则强制性效力的桥梁。其不仅将德国法中的“行为矛盾禁令”成文化,而且也赋予其一般性的信赖保护功能,矛盾行为所引发的信赖保护需求已为诚信原则完全包容。
“行为矛盾禁令”在德国法中的现实发展也远超卡纳里斯的预期,其主张的“仅有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才能适用禁令”已被目前的通说所否定。按照主流见解,是否适用禁令无涉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仅以相对人的信赖状态是否值得保护为依据,而在此判断中,实质利益衡量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行为人已经引起相对人实际的信赖投资时特别有保护的必要。〔83〕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Dirk, 2019, § 242 Rn. 289 あ.; Palandt/Grüneberg, 2020, § 242 Rn. 55 あ.; MüKoBGB/Schubert,2019, § 242 Rn. 317.可见,通过融入信赖可保护性的实质利益衡量,禁令形式结构上的缺陷已被克服。行为矛盾禁令以信赖可保护性的判断为核心,这并不妨碍其作为诚信原则的组成部分,其法律效果也藉由诚信原则得以实现。不过,行为矛盾禁令在目前的德国法理论中仍被视为积极信赖保护的工具,在效果上与缔约过失的消极信赖保护平行,但两者内部的价值判断是融贯的,仅是诚信原则的不同具体类型而已。
荷兰法中的诚信原则客观化更为彻底,《荷兰民法典》直接用“合理与衡平”取代诚实信用的表述,司法实践以此为基础发展出著名的“三阶段”理论以保护缔约信赖。这一理论曾引起我国学界的关注,有学者称其颇有参考价值,理由是“于不同的磋商阶段,不同支出的合理性也会发生变化,信赖的强度、信赖的对象均会有所不同”。〔84〕参见叶金强:《论中断磋商的赔偿责任》,载《法学》2010年第3期,第102页。该理论根据法律效果的差别将磋商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当事人得完全自由地中断磋商而不负任何责任;第二阶段,即当事人仍然可以中断磋商,但必须赔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损失;第三阶段,即当事人有继续磋商义务,否则产生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三阶段”的理论意义仅在于提供了一个基于信赖保护原理的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其本身既未明确三个阶段的分界点,也未反映荷兰法的全貌,因为仅凭磋商深入程度或阶段的表象不能实质衡量信赖的可保护性。在司法实践中,荷兰法院为这一框架补充了更为实质的要素,具体包括缔约信赖的诱因、客观上的合理基础以及外部环境风险。〔85〕See Pieter De Tavernier, Jeroen van der Weide, Exploring the CESL: The Dutch Perspective, 18 Contratto e impresa/Europa 572,585-586 (2013).在司法适用中,“三阶段”理论仅发挥消极信赖保护的功能,第三阶段几乎从未被适用,而第一阶段仅是对合同自由的重述,所以该理论的实质不过是适用诚信原则进行缔约信赖的消极保护。
纵观全文,我国《民法典》第500条第3项应在构成上区分主客观两个层次,客观上前合同诚信原则设定了积极的行为义务;主观上仍坚持过失归责原则,根据一般注意标准判断义务人在特定磋商背景下是否可以预见相对人的保护需求,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机会保护相对人利益。客观义务违反与主观可归责性是责任构成的不同层次,应当分别予以判断,而诚信原则主要作用于客观构成。若当事人在引发信赖时无缔约意愿或疏于告知既有的缔约障碍,以及当事人在引发信赖后未能将主观意愿或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告知相对人,此时无需考虑信赖状态即可认定告知义务的违反。若相对人无法证明上述义务违反,即需要结合信赖状态的实质利益衡量对保护义务进行更加精准的认定。如果相对人的信赖状态值得法律保护,双方间形成了比一般磋商更为密切的信赖关系,保护义务的标准也就更高。按照此种解释方案,前合同诚信原则的发展融入了更多信赖保护的因素,当信赖合理而值得保护时,诚实信用原则也调整因信赖状态而扭曲的风险分配,这与其客观化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五、结语
缔约过失是兼具体系包容性与价值宣示性的统合规范,其具体案型针对的法律问题不同,背后的理论脉络与价值判断也有所差异。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磋商阶段形成特别结合关系,负有告知、协作与保护等前合同义务,但在具体利益衡量中这一原则性论述仍欠缺可操作性,应通过教义学的发展探求更为实质的规范内涵与要素。具体到本文研究的缔约信赖保护,在规范基础、构成及适用范围等方面都体现了诚实信用与信赖保护的交织与渗透。信赖保护对诚信原则进行了价值与标准的填充,弥补了诚信原则在前合同阶段不确定性的不足;诚信原则使缔约信赖保护回归缔约过失的规范路径,为积极信赖与消极信赖的保护划分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在缔约过失制度通过解释论的发展足以包容信赖保护的规范目的时,预约合同制度即应回归其本质,不应为迎合信赖保护需求而一味地保持构成上的模糊与效力上的弹性。将缔约过失作为缔约信赖保护的统一路径符合体系协调性与法律确定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