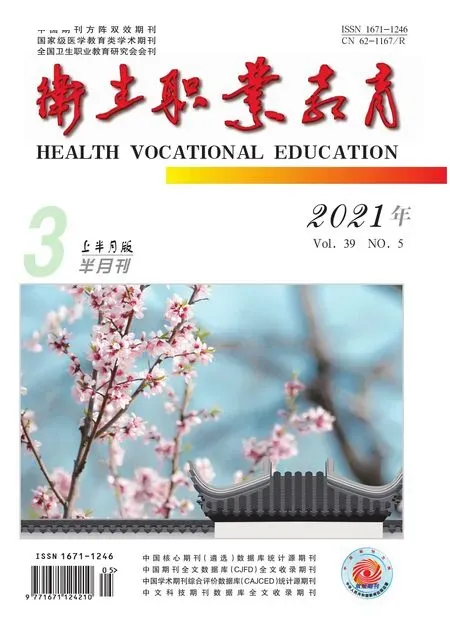实现我国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以疫情防控新常态为视角
夏恩强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认识疫情防控新常态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全球新发疫病的流行趋势和危害来看,“风险社会”已然成为解释现代社会性质的新名词之一,特别是新发疫病引起的公共卫生风险成为危害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控制不当则会引发地域性甚至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外Frontiers in Immunology期刊发表的文章显示,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2009年以后,几乎每隔1年便会暴发一起地域性甚至全球性(新发)传染病流行大事件,其中最恐怖的新发传染病是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波及全球,共造成约284 000人死亡;影响较小的是2017年暴发于马达加斯加的瘟疫,但也感染了2 147例,造成209人死亡。在我国,21世纪前20年新兴传染病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危害了人民健康和国家发展,而且不容易控制,如2003年的SARS、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3年的甲型H7N9流感和2019年的新冠肺炎等。
二是从诱发新发疫病的风险因子和加速风险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来看,当下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是关键。在过去的60年中,人类传染病病毒60%来自动物宿主,包括SARS、埃博拉等病毒。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野生动物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之中,随着人类不断“尝鲜”,它们携带的原始病毒开始在人类社会传播蔓延,最终造成新发疫病的流行。由于这些病毒长期“隐匿”在宿主体内,人类社会缺乏对其专门的研究,难以掌握病毒结构和变异原理,成为患者救治和疫苗研发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另外,城市空间的加速开发极大地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城市治安等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平常,但当新发疫病大流行时则会被无限放大。例如,人口的密集流动增加了疫病传染的几率,加速了疫情的扩散,特别是在节假日期间;医护物资和医院床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不到保障,同样会加速风险演化为危机。同时,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而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不排除会出现疫情“风险倒灌”情况,必须做好内防扩散、外防输入,防止外部环境变迁造成风险的进一步演化。
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根据传染病的流行规律和当下外部环境的变迁,新发疫病或许会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并在局部地区间歇流行。因此,一定要做好应对新发疫病的准备,坚持以健康为中心的治理理念、预防与应急结合的治理目标,善于应用科学技术手段优化卫生健康治理、创新治理范式、提升治理绩效,这就是疫情防控的新常态。
1 新常态下我国卫生健康治理的特色表征
1.1 坚持以健康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当前,公共卫生治理的重心在食品安全、医疗卫生和新发疫病等风险防控上,治理理念正从以往的“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坚持把防范化解健康风险放在首位,推动健康治理关口前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从广泛的健康影响因素入手……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1]。实质上,以健康为中心的公共卫生治理理念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回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正是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制度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要意识到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战胜疫情的重要保障。对于卫生健康治理来说,重大或新发疫病的流行是人民健康的“最大敌人”,甚至还会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因为疫情是涉及公共利益最深、受灾领域最广的一类突发事件,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国家和社会在应对重大疫情时极有可能处于疲乏和瘫痪状态,伴随而来的将是各种矛盾的激增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因此,立足我国疫情防控新常态,必须加强党对“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领导,全面统筹推进国家卫生健康工作部署,将全民健康提上国家重大议事日程。
1.2 明确预防与应急结合的治理目标
从治理目标来说,立足疫情防控新常态,卫生健康治理需要明确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与应急结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的治理目标。要实现这一治理目标,就需要建立健全重大疫情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应急管理能力。韩自强认为应急管理能力是国家常态化治理能力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2],重大疫情应急管理体系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实现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双管齐下”、相互促进。在常态化管理中,建立防范、化解新发疫病风险的有效机制,做好早期监测预警,力争止于未发;重视医防结合,健全疾控人才培养体系,开展重大疾病科研攻关等。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则需要搭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平台,汇聚群体的智慧与力量,保障治理主体之间信息互通、交流融洽,建立重大疫情应急演练长效机制,加快整个国家的应急响应速度等;建立公共卫生危机学习机制,将应急管理从“发生了什么”向“为什么发生”转变,将应急管理中有效的政策措施转化为常态化制度举措;建立地方行政领导应急管理学习制度,提升对突发事件的领导和应对能力,保证应急预案的可行性等。
1.3 创新卫生健康治理范式
卫生健康治理技术与治理工具的创新,如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电子医保卡、电子病历、AI医生、5G远程手术等,改变了以往落后的卫生健康治理模式,实现了从传统治理向智慧治理范式的转变。当下,针对新发疫病的科研攻关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是疫情防控的“利剑”。2003年SARS暴发,受限于科研水平、互联网技术和产品化能力等,广大医务人员和救援组织有劲使不上。经过近20年的基础研究和科研攻关,我国医疗研究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掌握的关键技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清华大学科研团队研发的生物芯片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又快又准地检验新冠病毒分子,研发的一体化自助式核酸检测卡盒不仅大幅度缩短了检测时间,同时提高了检测效率。另外,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拓宽了社会参与应急救援的渠道,实现了疫情大数据的及时更新和群体智慧的交融汇聚,不仅为政府应急救援争取了时间、提供了信息,还能有效监督各地疫情防控工作。在常态化治理中,大数据采集与分析有助于政府精准识别卫生健康服务的“真空”,对症下药,避免资源浪费,降低治理成本,优化服务决策;通过建立标准化的数据端口和技术系统,整合并共享人口、环境、食药、医疗、生物等卫生健康数据资源,创新卫生健康服务流程,形成以数据赋能为驱动的政府主导、部门负责、最终社会受益的智慧化、协同化的卫生健康治理体系。
2 新常态下实现我国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在科学认识疫情防控新常态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卫生健康治理的特色表征,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秉承以健康为中心的治理理念,落实党对“健康中国”建设的领导,完善卫生健康治理的顶层设计;如何建立健全现代化的重大疫情应急管理体系,如针对目前疾控人才流失与短缺现状,思考建立适应现代化疫情防控与应急管理模式的人才培养机制、转变重医轻防的落后观念、落实医防结合等;如何推进卫生健康智慧治理,树立数据治理思维,共享治理数据资源,以数据赋能提升卫生健康治理绩效等。由于本文篇幅有限不能面面俱到地论述,所以仅对以上我国卫生健康治理的关键领域提出从宏观到微观的建议,希望在以后应对新发疫病时,我们能够做到有备无患。
2.1 加强我国卫生健康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
第一,完善卫生健康治理的领导机制与制度体系。坚持以健康为中心的卫生工作方针,必须加强党对“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领导,整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与国务院医疗改革领导小组的职能,改变碎片化的卫生健康治理模式,并在地方党委和政府成立相关领导小组,督促落实党对“健康中国”建设的领导工作[3]。另外,科学研究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大部制”,坚持权力与责任对等、权力与资源匹配原则,建议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健康服务与保障委员会”或“国家健康服务与保障部”[3],整合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的公共卫生服务、医疗保障与救助、食药监管等领域的行政管理职能,健全现代化卫生健康治理制度。另外,针对传染病防控与救治,我们还要建立应急医疗物资分级保障、综合管理和统筹调配制度,创新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鼓励职业医生任全职或兼职社区家庭医生,加强对服务对象的健康检查和跟进管理,支持非公医疗机构发展,保障基层医疗资源充分,提升基层疾病防控与首诊水平。
第二,完善卫生健康智慧治理的顶层设计。决策者要树立数据治理思维,出台地方卫生健康智慧治理规划,建立卫生行政、医保部门、疾控中心、医疗机构之间统一规范的智慧技术执行标准框架。加快建立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制度,以国务院颁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为指导,出台“促进医疗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卫生部门数据开放与共享实施办法”和“居民健康大数据管理规范”等,坚持卫生健康数据共享原则。如建立疾控中心与医院的数据交换机制,保障信息共享通畅。利用电子病历等医院信息系统,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筛查新发疫病等,一经发现立刻上报当地疾控中心,避免因人工统计产生的漏报、错报。重视卫生行政部门的数据开放,公共卫生元数据开放有利于其他组织进行分析和再利用,进而发现潜在的流行病风险,帮助政府做好应对突发疫情的决策准备与应急部署。例如谷歌团队曾在2008年利用美国卫生部开放的关于季节性流感的大数据,成功预测出甲型H1N1大流行事件。
2.2 建立健全现代化重大疫情应急管理体系
第一,加强公共卫生法制建设。深刻意识到公共卫生安全不仅关系到“健康中国”建设,也影响到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加快公共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保证全民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用法。对我国现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加以完善,将生物安全上升至国家安全的高度,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建立权责明确、程序规范、执行有力、公开透明的卫生应急处置和疫情防控执法机制。
第二,提高新发疫病风险防控能力。通过国家立法和技术监管加强食品安全管理、野生动物保护,强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定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和销售网络规范,依法深入开展爱国卫生和动物保护运动,加强生物检测及对新发或潜在疫病病原体的普查和监测工作。建立卫生、农林、海关等跨部门数据共享体系和疫情智能监测分析报告系统,避免因动力不足和压力较大导致人工分析、报告造成的错判与漏报。考虑在相关职能部门下设传染病监测机构,直接对政府负责,由地方行政领导任命主要负责人,负责协调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合作。优化卫生健康治理的产学研协作,加强疾控中心与互联网科技企业、医学院校等的合作,积极开展国际与社会关于传染病防治的前沿合作,形成群策群力的卫生健康治理格局。
第三,积极发挥疾控体系的专业作用。对疾控中心实行“一类公益事业单位保障,二类公益事业单位管理”制度,提高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赋予疾控中心一定的政府行政职能,确保疫病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保证权威信息及时发布。另外,建立疾控中心、医院之间人员弹性流动制度,实行临床(传染病)医师由医院与疾控中心“双聘制”,确保信息及时共享,支持和推动县级以上医院设置“公共卫生科”,监督和强化医院的公共卫生工作。建议在北京、广州、武汉等人口密集且跨省份流动性强、国际化程度高、有潜在风险的城市设立疾控中心与医院合作的防治结合的公共卫生中心。
第四,建立重大疫情应急科研攻关体系。首先,科学技术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的锐利武器,是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的科技投入力度,建立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卫生等跨领域、跨学科的新发疫病风险防控实验室、重大疾病科研攻关基地等。创新科研机构的管理方式,对重点科研机构实行直接管理、上报措施,避免其他行政部门的介入和干涉。其次,尊重科研人员,保证其处理突发事件的决策权、话语权,优化特殊时期的政府决策。最后,开发专门针对传统中药研究的科研平台,中药在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表现亮眼,进一步改革现行中药评审和审批机制,解决中药研发和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建立中西医融合的应急救治体系,提升重大疫情救治能力。
第五,打造新型卫生健康治理人才梯队。治理的关键在人才,加快建设适应现代疾病防控和应急管理体系的人才梯队,制定相关人才培养、使用的配套机制尤为重要。(1)强化院校公共卫生教育。优选一批适合的高校率先成立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以本科生为起点进行人才培养,强化中医药学科建设,提升传染病与免疫学科的实力;设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一级学科,重视应急防疫人才培养和多学科交叉发展,融合预防医学、生物安全、应急管理和计算机等学科优势开展循证研究。(2)建立疾控体系与医疗体系之间的“桥接”制度。完善疾控中心和医学院联合培养人才制度,制定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联合培养计划,重视疾病预防教育;建立医院和疾控中心的人才流动机制,保证疾控中心高素质人才储备量,便于特殊时期指导医院疫情防控工作[4]。(3)完善基层卫生人才培养、使用机制。组织基层行政领导和卫生人员定期前往高校、疾控中心和重点医院开展系统性培训,制定考核制度;完善基层卫生职业资格审查、卫生人员上岗培训制度,吸纳兼具疾病预防与应急知识的人才常驻基层,进而提升基层卫生健康治理水平,实现城乡医疗资源公平、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