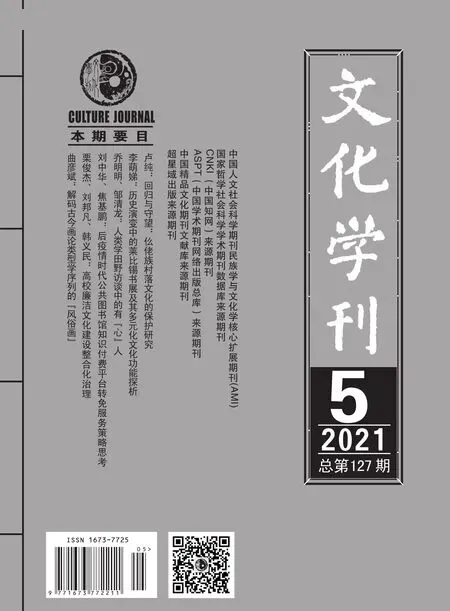文明起源中“巫”的作用
郭 冰
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在学术界向来以文明起源中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精神层面的研究则较少被学者所关注。当下学术界一致认为探索文明起源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系统性工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种研究手段都需要投入其中,因而,民族学、宗教学、人类行为学乃至哲学在探究人类文明起源中的作用显得越发重要,因为在“科学解释产生之前的史前社会,某些人神关系的自圆其说的、震慑人心的阐释往往能决定个人、族群、部落的价值取向,进而又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发展”[1]。这种“人神关系的自圆其说的、震慑人心的阐释”就是古代“巫”的一种职能,或者可以看作“巫”的特质之一。古时的“巫”,是精神的直接把持者、施行者和人神关系的联系者,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有时难以直接把握和呈现(这种意识形态也具有物质载体,即祭祀遗迹、祭祀用品、巫像、行巫工具及巫术场景等),因此,对“巫”的研究需要通过民族学或宗教学并结合其物质反映。“巫”在史前社会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政治导向作用,对“巫”作用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中难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解决的问题。
一、“巫”与原始宗教
对于宗教,恩格斯的定义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复杂的人格化[2]。”而童恩正认为,信仰是指人类的宇宙观和价值观,责任是指由信仰决定的戒律和教条,而行为是指体现信仰的仪式活动[3]。原始宗教作为宗教的最初形态,直接源于人类在史前社会对于远强大于自己的自然力的应对和诉求。面对无法理解的强大生存压力,人类诉求于异己力量来寻求安慰和自我满足,以获得对个人焦虑和恐惧的排解。因此,泛灵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应运而生。
宗教除了上述的宗教信仰系统外,还包括宗教仪式系统,而宗教仪式系统的施行则直接推动了“巫”这一角色的诞生。卜辞和金文中的“巫”字,为两个“工”字垂直相叠,对此,张光直先生认为这是巫者所用的道具之形态,作“矩”讲,“既可以用来画方,也可以用来画圆,用这工具的人,便是知天知地的人。“巫”便是知天知地又是能通天通地的专家”[4]。涂白奎先生从古文字研究的角度阐释甲文“巫”字作两“I”相交,“I”即“工”,而“工”与“玉”同义,因此,“巫”与“工”“玉”二字的原始意义是相近或相同的,“巫”从字源上便具有与“玉”相同的“事鬼神示”之意[5]。无论是矩说还是玉说,他们都认为“巫”能通天通地、联系人神。巫要联通鬼神,可以请神附身,代其说话,也可以上下升降去寻找鬼神,而要通灵,必须借助一定的刺激方法(如击鼓、舞蹈、服用药物等)来进入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如此看来,“巫”这一概念,既包含人格化的行使巫术的通灵者,也包括物化的、进行巫活动的工具和行为方式,其与原始宗教一样,都萌生于人类初期心里寄托的需要。
二、早期的“巫”
在早期,世俗政权中出现了最高的权威,而原始时期的“巫”却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与权贵相结合,更加成为协助权贵巩固世俗政权的神职人员,甚至王与“巫”也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为一体。这一时期的王者既为政治领袖,亦为群“巫”之长。在商代,从统治者到下面的官,都成为“巫”在世俗世界的代言人。而且,各种“巫”用的工具、手段都能被我们识别出来。众多的卜骨,无疑就是巫师进行仪式的工具或生成物,而其上的记录也有相当部分体现了商“巫”的地位。张光直先生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总结出了山、树、鸟、动物、酒与药物等巫师通神的工具和手段,其中商代青铜器中酒器数量和种类之多表示酒在祭祀时是服用的,而且是重要的;动物作为商“巫”通天的手段,他认为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人与动物之间的转型,二是人与动物之间的亲昵伙伴关系。在夏商时期,“巫”强烈影响着社会发展方向和人们的生活。那么在夏商之前,在塞维斯的“部落”“酋邦”这一段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巫”又发挥着怎样的影响力,贡献了多大的力量,这就需要从民族学的资料来分析巫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
三、从民族学看“巫”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
“巫”从产生就将自己与超自然的力量联系在一起,这种力量在原始社会是至上的、不可挑战的。那么,与强大的超自然力量联系的“巫”便成为人们行为的合理解释者,“巫”在其部族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担当了一个强有力的影响者的角色。
巫者自身对于巫术中谬误的认识是否清醒,并不妨碍他们要用敏锐于常人的头脑来开展巫术活动,也不妨碍他们通过巫师仪式获得其所希望产生的结果的决心,即使会有那么一些“不走运者”,因族人短期内期望的结果没有出现而遭受惩罚。“在尼罗河上游的拉图卡人,每逢庄家干枯而酋长的一切求雨努力都已被证明无效时,人们便在夜里对他群起而攻之,抢走他的所有财产,把他赶走,还常常杀死他。”[6]151-152
但是,对巫师的惩罚只是其个体的失败,继而会有其他个体接替下去,发生的只是巫师个体的更替,而非巫师这一社会角色。相反,巫师在其社会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他们需要知道得更多,担负更多的责任,精通一切并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并在未知世界的鼓励下去寻找答案。那些受他们庇佑保护的人们,“期待着他们为了人的利益不仅要了解而且要控制自然界的伟大进程。”[6]109此外,处于其职的巫师个体,由于要避免自己神圣性的丧失而遭受惩罚,就比他人有着更为强烈的探索追求真理、认识自然规律的动力,巫师在人类社会起源中扮演着掌握天文知识者、地理知识者、具有一定数理知识者、具有一定医药知识者、重要建筑工程的设计者、古代文化的传承者等角色[7]。由此看来,巫师在其职业与信仰或个人主观动机的推动下,不免以多获取多学科知识为己任,加之善于思考的头脑,在客观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绝有可能的。
这样,巫者能力的提升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更有利于其对于世俗领导权的获得,而往往会使得酋长与巫师逐步结为一体。酋长如果没能与巫师相结合,那么他就不会获得实质性的统治权。苏丹的努尔人的“豹皮酋长”在处理类似杀人之类的纠纷事件时,是没有政治权力的,他只能通过劝说和“恤牛”仪式来使双方的争端得以平息,但是却无权强迫双方接受他的调解,强行解决争端[8]。相反,酋长如与巫师相结合,就会将自己的决策镀上一层神秘的力量,其执行力度和威慑力度将是豹皮酋长的力量无法比拟的。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对纠纷进行是非裁决的“神判”,通常会让受指控者经受危险或痛苦的检验来确定其有罪还是无罪。“神判”并非毫无意义或毫无根据的一种随即的判决,其与人类心理密切联系,也往往是抓住了人们的心理弱点进行突破。当然,因为判决是神的旨意,所以绝对不会有错判、误判的情况,在这里人们很容易借助神的力量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
如此,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巫”在拥有神权的同时又取得了世俗的领导权,在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同时又通过神判来控制社会运转。因此,“巫”就成为从原始社会过渡到早期文明社会的重要动力之一。
四、考古学上“巫”的反映
在众多的考古材料中,有不少与“巫”有关的遗迹,如祭坛、巫像、巫术工具以及其他的祭祀场景、巫俗等。目前的考古发掘材料中有很多关于祭坛和祭祀场所的遗迹,如红山文化因为它的“坛、庙、冢”而成为一个宗教巫术色彩浓厚的考古学文化。东山嘴遗址挖掘出一组南北长、东西窄的石砌建筑基址,其中部有一个10米见方的方形基址,内竖成组立石,南部为一直径2.5米的圆台址,而且附近还有小型孕妇陶塑像,双龙首玉璜和绿松石鸮形饰件等。牛河梁遗址发现有分主、侧室的“女神庙”,其内有接近真人大小的主神和小型的众神。积石冢呈圆形,四周竖立着大量的无底的筒形彩陶器,很可能是红山人在巫的带领下在祭坛上举行祭祀女神的集体仪式,积石冢可能是巫师的墓葬。良渚文化的瑶山祭坛平面呈边长20米、总面积约400平方米的方形,由里外三部分组成。最里面一部分是一座红土台,呈方形,系生土。第二部分是红土台周围的围沟,填灰色斑土,土质疏松。第三部分是在灰土围沟的西、北、南三面,是由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土台,台面上为人工铺筑的砾石。如此,祭坛由多种颜色的土构成,更增添了其巫术的神秘色彩。濮阳西水坡的M45南部呈圆弧形,北部呈方形,墓主为男性,两侧用蚌壳精心摆成一龙一虎,龙居右侧,虎居左侧。另外还发现了其他的蚌壳摆塑的龙形、虎形等图像。对于M45,有人认为墓穴南部边缘呈圆弧形,北部边缘为方形,符合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学说。将这三组龙虎蚌图综合起来看,因为龙、虎、鹿后来都发展成具有通天性的动物,所以这里出土的文物具有巫祭性质应当是正确的,而且处于龙虎之间的墓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大巫师。
关于巫本人和人物神的相关考古材料亦有发现。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了全身像的玉人,有站姿和坐姿两种。玉人方脸、大耳,头戴扁冠。两臂弯曲,十指张开置于胸前。双脚明显刻出五趾,背部有一对穿孔,可供传挂之用。这些玉人具有很强的写实性,仪表不凡,神态严肃,应是巫觋类的人物。至于玉人的姿态与手势,或许正是神灵祭祀礼仪中巫师的特定动作。在反山墓地M12中出土的一件大玉琮上,在四个直槽内上下各有一个神像纹,全琮共八个。每个神像纹的形象基本相同,倒梯形脸,大眼宽鼻,阔嘴,头戴呈向四周辐射状的羽冠,耸肩叉腰,身下骑着一头神兽。神情严肃、气势威严的神人兽面纹正是良渚人们所敬畏的巫神的写照。
关于与“巫”有关的器具,玉器当属首位。玉石由最初的美石的装饰意义随着巫教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神物意义,并且又以其繁荣推动了巫教文化的发展。凌家滩出土了许多种类繁多、内涵丰富的玉礼器,不但是财富、权力的标志,而且是统治者祭祀天地、沟通神灵的法物。出土的玉龙、玉鹰、长方形玉版、玉龟、玉人和刻画的神秘纹饰等,表现出宗教信仰在凌家滩社会中煊赫的地位和作用。良渚文化的玉琮、三叉形器、锥形器、玉钺、玉璧等,都是独立供放或手持使用的巫祭时的道具。动物骨、牙、甲器,是另一类与巫祭联系密切的器具。经过灼烧的动物肩胛骨或龟甲骨在殷商时期成为重要的占卜吉凶的工具,而在仰韶晚期的淅川下王岗遗址到龙山时期的诸遗址中,也发现了相当数量带有烧痕的卜骨。当因骨质不同而导致的在灼烧过程中产生的爆裂痕迹的差异等此类当时无法合理解释的现象被诉诸神的时候,卜骨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巫所借用的施行巫术的器具了。另外,一些特殊的陶制礼器也带有一定的巫祭意味。在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与良渚玉器上立鸟图像十分相似的立鸟陶器,器表呈红褐色,整体自上而下分为三部分,下部是一中空的圆柱体,中部是一中空的两侧各有一个鸡尾形装饰的圆锥体,上部为一只立鸟。对此,吴耀利认为,这件器物不是一件纯陶塑艺术品,应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用途,暂将它称为“立鸟神器”,推测为当时人们在举行祭祀之类的仪式上摆放的一件“神器”[9]。大汶口文化出土的大量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尊,器大、壁厚、尖底、直唇,有学者认为其非寻常用器,拥有者地位特殊,且主要用于盛放酒浆,用于郊野、坛台祭祀。或直接安放于土筑坛台上预挖的浅坑中,热酒自然蒸发,上闻于天;或抱起倾于地下,施祭厚土。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祭祀场景等情况的考古反映。马家窑文化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在其内壁上绘有三组舞蹈纹,每组有舞蹈者五人,手拉着手,面向一致地踏歌而舞。这应是祭祀时的一种舞蹈场景。对于大汶口文化中广泛存在的拔除侧门齿、枕骨人工变形、口含石球致齿弓变形等特殊的习俗中有些因素是受到巫俗影响的,这不应被忽视。
综上看来,巫与文明起源之间是存在着重要联系的,这在民族学及考古学上均有较多反映。同时,巫在早期历史社会中的显赫地位并非一蹴而就的,它历经史前社会的漫长,在史前社会逐步发展,伴随人类文明进程的脚步,在早期文明起源时期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