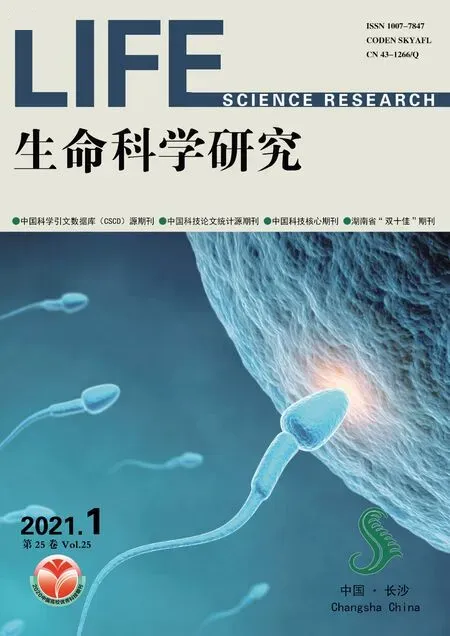动物捕食性天敌摄食分析方法的研究进展
颜亨梅,钟文涛
(1.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中国湖南长沙410081;2.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国家农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湖南长沙410007)
食性分析是生态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几十年来一直受到生物学家的关注。各物种围绕着生存繁衍不断展开竞争,导致了地球上物种的多样性,而捕食关系反映了竞争的过程,是影响竞争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捕食者往往从其生活的环境中随机获取猎物,但捕食的选择同时受到猎物防御和逃避策略、营养品质(如食用尸体与消耗植物)、内毒素、捕食者和猎物的时空分布等诸多因素影响[1]。因此,对捕食者的食性进行分析是研究动物能量和营养需求、采食策略、生境利用及生态系统中种间关系的核心内容[2~4]。
如何获得某个捕食者准确的食物谱和捕食量一直是食性分析研究领域的难点。对于大型捕食者(如狮子)来说,它们只需要每隔几天捕杀1~2头猎物即可满足营养需求,研究人员较容易对其捕食能力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而对于小型的捕食者(如甲虫、蜘蛛)来说,它们往往隐藏在植被下或在夜间捕食,其捕食行为较难进行观察和分析,如果以强行清除植被或强光照射等方式对其捕食过程进行观察,势必对其捕食造成干扰,导致实验结果出现偏差。同时,小型捕食者往往数量更多、食性更杂,而且可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的研究和实践中,人们需要对天敌的控害作用进行客观评价,评价内容可从其“吃什么”和“吃多少”两个方面综合分析。“吃什么”是明确天敌的捕杀范围和捕食喜好,“吃多少”则是要明确该天敌对目标害虫的控制能力。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既要明确天敌的食物谱,也要对其捕食量进行估算,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利用捕食性天敌防治害虫的目的。例如:“生物防治”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动物捕食性天敌摄食分析的基础研究之上。
蜘蛛作为农业生态系统中一类重要的捕食性天敌,其种类之多、种群发生量之大仅次于昆虫。另外,蜘蛛在狩猎方式、栖息地偏好和活跃时期等方面有着各种各样的组合,从而使该类天敌在生物防治方面具有较高的效率。因此,作为广食性的捕食者,蜘蛛的捕食作用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食物网的能量流动。对蜘蛛这一类捕食性天敌采取有效实验手段分析它们的摄食范围和摄食量,对有目的地实施相应的“保蛛治虫”措施具有重要实际指导意义。下面综述几种捕食性天敌摄食分析方法研究的类型及其进展。
1 基于形态学鉴别的食性分析研究方法
食性分析的传统研究方法多基于形态学鉴别,如直接观察法、胃内容物法和粪便分析法。直接观察法通过实地对动物的捕食行为进行记录,从而获取该动物食谱组成的直接证据。但是,使用该研究方法进行食性分析效率低、偏差大,且对于体型小的杂食性动物或夜间捕食的动物很难获得准确的食物谱[5]。胃内容物法是通过检查捕食者胃内未消化完全的食物残渣对其食性进行分析[6]。粪便分析法则是通过检查捕食者粪样中残留的种壳、种皮、骨骼、毛发、指爪、鳞片和羽毛等对其食性进行分析[7]。两种分析法都直接反映了捕食者实际摄食情况。由于粪便样本采集时容易受到环境杂质的污染,相比之下,胃内容物法的分析结果能更真实地反映捕食者采食的食物种类与数量,偏差相对较小[8]。但是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要求实验人员具备非常丰富的物种分类经验,通过显微镜对胃内或粪便中较大的食物残渣碎片进行鉴定。同时,由于消化完全的或呈液化状态的食物几乎无法辨别,因此获得的实验数据非常有限,效率较低。
对蜘蛛来说,上述传统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蜘蛛进食通常采用体外消化和体内消化相结合的方式。游猎型蜘蛛捕食时首先用螯肢的螯爪刺穿猎物体壁,随后注入毒液使之麻痹;结网型蜘蛛捕食时先用后足从纺器上拉出丝捆缚猎物,再注入毒液,然后运到隐蔽处取食。取食时先吸食猎物的体液,并注入消化液,将猎物的器官组织初步消化后,再吸入蜘蛛头胸部消化道前端的吸胃内,暂时贮存在吸胃内的是无形态的猎物组织液,最后在腹部肠道内完成对猎物的体内消化与营养素吸收。这种特殊的进食方式,使蜘蛛的摄食分析无法采用传统形态学分类方法进行研究[9]。然而,分子生物学新技术及其实验手段(诸如二代测序和数字PCR等)给蜘蛛摄食分析方法和技术的突破带来了福音。
2 基于分子生物学实验的食性分析研究方法
随着研究技术的不断进步,更多前沿的实验技术引入食性分析研究,食性分析也经历了从传统的宏观观察向更为精准的微观检测演变的过程[10]。近几十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基因组公共资源数据库信息的不断扩充和完善,使基于DNA水平鉴定的生物分类学呈现出勃勃生机,对传统生物分类学起到很好的补充和校正作用[11~12]。研究人员对某一捕食者进行食性分析,不再依托对胃或粪便中食物碎片进行形态学分类,只需提取其中的核酸成分,通过扩增、克隆、测序等技术手段即可确定其捕食猎物的种类[13~14],减少了人为误差的同时极大提高了准确性。
Höss等[15]于1992年在Nature上首次发表了使用DNA扩增技术分析意大利北部濒危棕熊粪便中食物残留的研究报告,认为从粪便中提取的DNA可用于分析动物的捕食行为。Deagle等[16]通过对澳大利亚海狗粪便中猎物线粒体的16S序列进行焦磷酸测序,识别出其猎物谱中包含了54种硬骨鱼、4种软骨鱼和4种头足类动物,其中Emmelichthysnitidus和Trachurusdeclivis在海狗的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些研究人员将分子生物学和传统形态学相结合进行食性研究,对胃内容物或粪便中的食物残渣进行形态学辨认可大致得出捕食数量,而DNA检测技术则可对形态学无法鉴定出来的物种提供补充数据,这种联合分析方法显著提高了样本的利用率,并增加了可从样本中获得的信息量[17]。除了大型哺乳动物食性分析的研究,小型节肢动物的食性分析也因DNA检测技术的发展得以实现。Sint等[18]使用单重PCR法对喂食不同形态食物后的蜘蛛和步甲体内的残留物进行了比较,发现与咀嚼习性的捕食者相比,吸食习性的蜘蛛体内猎物检测率更高。Staudacher等[14]对步甲的胃内容物进行了多重PCR检测,发现在种植禾本科作物的农田中,步甲的主要食物为蚜虫,占整个DNA检出率的51%。Hamback等[19]采用DNA条形码技术对波罗的海海岸周边的蜘蛛摄食进行了筛查,发现膜翅目和鳞翅目的昆虫为其主要捕食对象。
在食性研究方面,多个目标基因片段可供选择。早期鉴定工作多利用核DNA序列,包括随机扩增 DNA 的 SCAR 标记[20]、ITS-1[21]和酯酶基因[22];近年研究中,线粒体基因组被广泛应用,因其具有拷贝数多、无内含子、重组现象少等特点,所以在物种鉴定方面比核基因组更具优势。线粒体基因组由核糖体基因和蛋白质基因组成,人们可根据所需鉴定的水平(属或种)选择不同的目的基因片段。线粒体中蛋白质基因组较核糖体基因组更不易保存,在设计物种特异性引物时,多选择长度合适、进化速率较快的细胞色素氧化酶Ⅰ亚基(cytochrome oxidase subunitⅠ,COI)或线粒体细胞色素 b(mitochondrial cytochrome b,Cytb)基因[23]。而核糖体中12S和16S基因进化速率较慢,同时大量插入和缺失的现象造成不同物种间核糖体大小不同,因此常用于设计群特异性引物[24~25]。
加拿大动物学家Hebert博士于2003年首次提出了DNA条形码(DNA barcoding)的概念[26],认为线粒体COI基因中一段长度约为650 bp的基因片段兼具种间变异性和种内保守性,通过设计通用引物对不同物种的COI基因进行扩增测序,并建立可供比对的数据库,即可以实现对不同物种快速、准确的识别。随着基因测序的技术手段不断升级,越来越多可用于条形码查询及序列比对的公共数据库已经建立,旨在促进全球标准DNA条形码的研究,如Bold(http://www.barcodinglife.org/)、GenBank(http://www.ncbi.nlm.nih.gov)、EMBL(http://www.ebi.ac.uk/embl)和DDBJ(http://www.ddbj.nig.ac.jp)。
现有文献报道证实,利用COI序列进行物种鉴别的分辨率可高达95%,其种内和种间的差异也在节肢动物、鸟类、鱼类中被观察到并广泛应用[27~28]。Murugan 等[29]利用 DNA 条形码技术对印度的10种蚊子进行了分类鉴定,鉴定结果分别为库蚊属、按蚊属和伊蚊属,获得的种内与种间差异分别为1.30%和3.83%。Decru等[27]比较了刚果盆地东北部的821个鱼类样本COI水平的差异,结果发现26.1%的样本依据以往的形态学分类方法可能存在错误,并强调运用DNA条形码将有助于建立刚果盆地鱼类可靠的分类目录。Maralit等[30]利用DNA条形码技术对菲律宾市场上的渔类产品(金枪鱼、罗非鱼、沙丁鱼、鳕鱼、海鲂、虾等)进行了鉴定,发现金枪鱼与标签声称的原料不符合,同时发现一种标签名称为银鳕鱼排的产品里含有有害人类身体健康的鱼类成分,强调了DNA条形码技术在渔类产品掺假监测方面能实现无靶标鉴别的优势。DNA条形码技术在食性分析方面也有应用的报道。Sheppard等[31]用两段COI基因作标记,研究了蚜虫-蜘蛛-步甲模型中的初级捕食和次级捕食现象,发现步甲体内可检出8 h前被蜘蛛捕食的蚜虫成分,并且步甲捕食蜘蛛4 h后仍可检出已被蜘蛛消化4 h的蚜虫DNA,说明基于COI基因的PCR技术极其灵敏,可用于次级捕食的研究。Greenstone等[32]研究了瓢虫和刺益猎蝽捕食马铃薯甲虫后猎物COI基因的半衰期,由于两种天敌在取食方式和消化生理学上存在差异,其对同一猎物消化的半衰期分别为7 h和50.9 h。此外,Weber等[33]使用qPCR技术对瓢虫幼虫取食甲虫卵后,不同进食量、经历时间和样品处理方式对捕食者体内猎物DNA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取食卵量和取食后经历的时长对最终能检测到的目标DNA量有显著影响,另外将捕食者立即储存在预先冷却至-20℃的70%乙醇中,可检测出的靶序列含量最高。
当然,其他技术如温度梯度凝胶电泳[34]、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35]、稳定同位素分析[36~37]等在食性分析上也均有应用的报道。但是,要分析某一捕食者的猎物谱,需要对它在某一生境下的整个食谱的宽度进行鉴定。上述基于分子生物学实验的食性分析方法,适用于狭食性捕食者的食性研究[38~39],或针对某几种特定猎物的捕食进行定性定量研究,对广食性捕食者来说,要用上述方法窥得其猎物谱的全貌仍很难实现。
3 基于二代测序和数字PCR的食性分析研究方法
3.1 二代测序技术
在四十多年前,Sanger团队[40]首次完成了对噬菌体φX174完整基因组图谱的绘制工作,建立了DNA双脱氧末端终止法测序技术,标志着第一代核酸测序技术的诞生。Sanger测序技术可靠性高,序列读长较长,但其基于电泳分离技术的原理,使得测序速度与通量均受到限制,如ABI3730测序仪每次最多处理48个样本[41~42],同时检测海量样本时,所需的时间成本及经济成本都将是天文数字。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DNA二代测序技术应运而生。二代测序又称为高通量测序(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HTS),能同时对上百万条DNA进行序列测定[43~44]。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逐步商品化,以罗氏公司的454测序平台、ABI公司的Solid测序平台以及Illumina公司的Solexa测序平台为代表的三大测序平台出现,使人们能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大量基因组数据。二代测序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空间,如:全基因组从头测序[45]及重测序[46]、转录组测序、差异基因表达分析[47]、发现新基因[48]并完善基因组注释[49]、DNA 甲基化[50~51]和组蛋白修饰[52]鉴定等。
此外,将二代测序技术应用于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分析上也有着极大的前景[11,53]。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Metabarcoding技术,其将DNA条形码的分类理念和高通量测序手段相结合,是食性分析研究较为理想的工具。二代测序的原理是使用一组或几组PCR通用引物,对来自生物体或环境中的具有分类学信息的基因同时进行扩增,扩增子的集合通过高通量基因测序仪得到大量物种分类的DNA信息[54~55],经过数据库比对,最终同时得到样品中存在的多个物种鉴定数据。Shehzad等[56]利用Metabarcoding法从不同栖息地的38份豹猫粪便中鉴定出18种豹猫的捕食类群,包括8种哺乳动物、8种鸟类、1种两栖动物和1种鱼类。Meredith等[44]则利用该方法对巴尼加特(Barnegat)湾的水母食性进行了调查,发现其猎物谱可分为23个不同的分类群,包括先前没有记录为猎物物种的多种软体生物。此外,王先锋等[57]通过二代测序技术对海州湾平岛海域牡蛎捕食真核生物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主要食物为链形植物门、绿藻门、囊泡虫门、子囊菌门等。总的来讲,二代测序技术高效率、低成本的特点在分析捕食者食物谱上的应用是其他实验技术无法媲美的,但是该技术对蜘蛛食谱与食量的分析尚未见报道。
3.2 数字PCR技术
数字PCR的概念于1999年由Vogelstein等[58]首次提出,其原理是将一个PCR反应体系有限稀释到不同的反应单元中,实现每个反应单元理论上要么包含一条DNA模板链,要么没有DNA模板链,经过PCR扩增,对每个反应单元中的荧光强度进行直接计数或用泊松分布公式计算[59],即可知道原始样本中DNA的拷贝数。最初的数字PCR实验是在96孔板或384孔板中进行的,操作较为繁琐,因此应用范围有限。2007年,第一台商品化的数字PCR仪正式投入市场,使其实验操作变得更简单、可操作性更强[60],从而推动了该技术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基于分液方式的不同,数字PCR分为微流体系统(Fluidigm公司的Bio-MarkTM基因分析系统)、微孔芯片系统(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司的QuantStudio系统)和微滴系统(Bio-Rad公司的QX100/QX200微滴式dPCR系统、RainDance公司的RainDropTMdPCR系统)[61],其中以微滴数字PCR(droplet digital PCR,ddPCR)应用最为广泛。
相对于实时荧光定量PCR,数字PCR有以下优势[62~66]:1)不需要对照标准样品和标准曲线即能实现绝对定量分析;2)不受扩增效率的影响,对PCR反应抑制物有很强的耐受性;3)数据具有更好的精密度和灵敏性,可对样品中痕量DNA进行精确定量。基于以上特点,数字PCR被广泛应用于癌症早期筛查[67~69]、疾病诊断[70~71]、产前诊断[72~73]、转基因成分分析[74~75]以及食品安全[76~78]等众多领域,然而在动物食性分析方面,数字PCR的应用报道较少。
由于蜘蛛直接吮吸猎物体液的特殊摄食方式,在其消化道内无法采用传统的食性分析方法来检查猎物残骸。2016—2018年颜亨梅、钟文涛等尝试使用DNA条形码结合数字PCR技术对蜘蛛的摄食进行精确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该联合分析方法可以直接探明野外蜘蛛的摄食实况[79],突破了在蜘蛛中进行食谱和食量分析的难题。在该研究中,数字PCR测得的VIC和FAM阳性液滴数为初始样本中DNA的拷贝数,通过比较人工干预条件下和自然条件下猎物与蜘蛛拷贝数的差异,结合捕食实验中各处理组的平均捕食量,按照下列公式即可对自然条件下蜘蛛的捕食量做出精细的定量测算。

式中:N——自然条件下蜘蛛对某一猎物的总捕食量;PFAM1——人工干预条件下测得的猎物阳性微滴数;PVIC1——人工干预条件下测得的蜘蛛阳性微滴数;PFAM2——自然条件下测得的猎物阳性微滴数;PVIC2——自然条件下测得的蜘蛛阳性微滴数;Na——人工干预条件下蜘蛛的捕食量;n——人工干预条件下用于检测的蜘蛛头数;N′——自然条件下单头蜘蛛对某一猎物的平均捕食量;n′——自然条件下用于检测的蜘蛛头数。
4 总结与展望
物理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研究人员更精准地分析捕食性天敌的食谱与食量提供了多种方式。颜亨梅和钟文涛所建立的蜘蛛食量检测数学模型,为客观评价蜘蛛控虫作用提供了实用的新方法,可使人们直观了解蜘蛛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对害虫的控制效能。该成果不仅在生产实践中对制定“保蛛治虫”的措施,进一步发挥该捕食性天敌对害虫的控制作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在理论上丰富了动物学和植物保护学相关内容,为发展蜘蛛学做了开创性工作。
尽管数字PCR在痕量分析和精确定量等研究领域大放异彩[80~82],但该方法也存在一定不足:1)仪器昂贵且运行成本较高,单样成本约为RT-PCR方法的30~50倍;2)通量小,不同的数字PCR平台每次可同时处理8~12个样本,而RT-PCR每次最多可处理384个样本;3)速度较慢,数字PCR一次全过程分析约需要8 h,RT-PCR仅需要1.5 h。虽有诸如上述缺点,数字PCR技术仍然获得生命科学研究者的热捧[83~85]。
基于现阶段工作的研究结果,作者认为在以下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出现,对食性分析的研究可以实现更高效、更精准的检测。二代测序技术能对某一天敌的猎物谱做全面筛查,检测结果中的reads值能够反映食谱中各类昆虫的大致比例,再使用数字PCR技术对食谱中的主要猎物进行精确定量分析,在理论上能实现对某一捕食性天敌在某一生境下的捕食范围及捕食量的精确检测,具有极大的实际应用价值。将两种技术相结合用于食性分析的设想,存在实现的可能性,但尚无文献报道,期盼有兴趣的学者作为后续研究的方向,为捕食性天敌摄食的分析、检测创建更多快速、精确、高效和简便的新方法与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