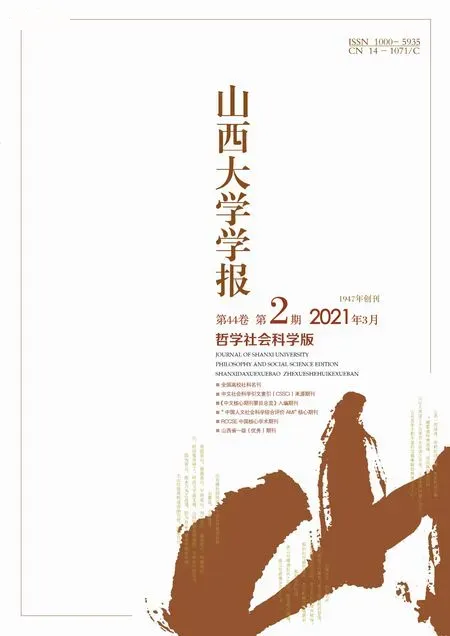近代欧洲文献中的“京广大运河”
——中西交流史中的京广水陆交通线
李夏菲,王永平
(1.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2.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一、康德、赫尔德笔下的“京广大运河”和京广水路
在《自然地理学》(VorlesungenüberphysischeGeographie)中,康德(Immanuel Kant)曾对中国有过一段论述,其中他谈道,在中国,几乎每省都有运河纵穿而过,从这些运河中,又引出小一些的运河流向城市,以及更小的流向乡村。所有运河上,都架设有桥梁,这些桥梁带有数个砖石拱圈,最中间的部分很高,可供有桅杆的船只通过。自广州至北京的大运河,其长度举世无双。[1]687
《自然地理学》的书稿源于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讲授的同名课程讲义。这门课程自1757年起年年开设,一直持续到1797年。[2]139在上面这段引文中,最引人注意的恐怕要数康德关于“京广大运河”地描述了。令人费解是,中国并没有一条“京广大运河”,“长度举世无双”的是京杭大运河。
无独有偶,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IdeenzurPhilosophiederGeschichtederMenschheit)第三卷(1787)中,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曾描述过这么一条自广州至北京的水路:
许多旅行者一致认为,除去欧洲,或者还有古埃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道路和河流,桥梁和水道,乃至假山能多过中国。这些与长城一样,全都是通过艰苦努力由人类的双手建造出来的。人们可以坐船从广州直抵北京近郊,如此,人们用公路、运河和河流把这个被群山峻岭和荒漠分割开的帝国艰辛地连接起来:村庄和城市坐落在河流之畔,各省之间的内部贸易往来繁忙而充满生机。[3]431
赫尔德虽然并未直接提到“京广大运河”,但非常明确的是,北京至广州的直线距离已近2000公里,其间并不存在一条可以坐船直达的水路。
那么,康德和赫尔德书中的“京广大运河”和京广水路,会是两位思想家的笔误吗?
二、欧洲文献对京广水陆交通线的介绍
康德与赫尔德都是18世纪重要的德国思想家,他们两人都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的认识完全基于当时欧洲对中国的介绍。
18世纪时,正值欧洲人认识中国、接受中国的一个高峰。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自16世纪末,陆续有欧洲传教士、使团、冒险家和商人从欧洲去往中国。特别是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向欧洲发回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其内容广泛地涉及中国的山川水文、风俗文化、社会政治、经济贸易、文学哲学等诸多方面,同时还将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译介到欧洲。在介绍和评价中国时,耶稣会士常常不吝赞美之词,在当时的欧洲塑造出一个优越、理想的中国形象。他们对中国的介绍,连同贩往欧洲的大量中国茶叶、瓷器、漆器、丝绸、香料等等一道,在17世纪下半叶18世纪上半叶,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一时间,在欧洲各国王室中间,中国风的器具、家具、装潢、园林和建筑形成了一股风尚。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中国塔、奥地利美泉宫的中国厅、德国卡尔斯鲁厄小雉宫的中国茶室等等都是这一风尚的留存。也在这一时期,欧洲的思想界同样形成了论述中国的潮流。当时欧洲知名的思想家,如培根(Francis Bacon)、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伏尔泰(Voltaire)、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孟德斯鸠(Montesquieu)、魁奈(Francois Quesnay)、亚当·斯密(Adam Smith)、康德、赫尔德、福修斯父子(Gerhard Johannes Vossius, Issac Vossius)、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等等,都曾参与其中。就当时欧洲人认识中国的总体情况而言,正如赫尔德所说:“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欧洲的一些国家。”[4]577康德和赫尔德笔下的“京广大运河”和京广水路的问题,也要放在这一时期欧洲对中国的介绍中去考察。
查阅当时欧洲对中国的介绍,可以找到大量介绍广州至北京路线的文献材料。根据这些文献对这条路线的不同描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京广大运河”
这类文献认为北京与广州之间由一条“京广大运河”直接沟通。
在1750年出版的《一般水陆旅游史》(AllgemeineHistoriederReisenzuWasserundzuLande)第六卷第一章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
大运河,三百里长,从广州直达北京,纵穿中国,其间有大量舟船,开凿于一百六十四年前。河上有较大桥梁三百三十一座,纪念王公和其他伟人的塔和牌坊一千一百五十九座,著名的书店二百七十二间,纪念祖先和有功勋之人的祠堂七百零九座,墓碑七百八十八个,其形制非常引人注意;王公宫舍三十二座,高官府邸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座。[5]6:9
《一般水陆旅游史》是18世纪德语世界中规模最大的游记集,全书共21卷,由约翰·约阿希姆·施瓦伯(Johann Joachim Schwabe)在1747至1774年间编译出版。其中收集的游记很多来源于《新航海旅行总集》(ANewGeneralCollectionofVoyagesandTravels,1745—1747)和《一般旅行史》(Histoiregénéraledesvoyages, 1746—1791)两部英语、法语游记集。可以说,是当时欧洲多语种游记的一个大汇编。康德在《人类学讲义》(VorlesungenüberAnthropologie)中,就曾经参考过《一般水陆旅游史》的第六卷。[6]1379
除《一般水陆旅游史》外,在1778年的《航行探险记新大全集》(ANewandCompleteCollectionofVoyagesandTravels)中也可见到“京广大运河”的说法,其中记录的一些数据与《一般水陆旅游史》相近,只在开凿时间上相差较大:
大运河长达三百里格,自广州通至北京,纵穿整个帝国。它开凿于约四百年前,其中处处挤满船只,载着商品从一地去往另一地。这条闻名于世的运河上方有桥梁三百座,纪念伟人的塔和牌坊一千一百五十九座,书店两百七十二间,超过七百座大殿,三十二座皇帝的行宫,一万三千六百座权贵的美舍。运河两岸有无数精美的中式园林,其间点缀着纳凉的亭榭,怡人的小径和最清新不过的树林。皇亲大员们在这里消夏,园中栽植的可口水果更为他们增添雅兴。[7]586
1782年出版的《最重要的历史科学手册》(HandbuchvornehmstenhistorischenWissenschaften)在介绍中国时也提到一条连接北京和广州的大运河:
在中国为数众多的湖泊、河流和运河当中,最重要的是湖广省的洞庭湖、江南省的洪泽湖、江西省的鄱阳湖;两条大河:江,即蓝色的河与黄河,即黄色的河;以及运粮运河,或称御河,连接北京和广州。[8]195
在1825年版的《报刊和会话百科词典》(Zeitungs-und Conversations-Lexikon)第二卷中,“皇家运河”词条下也有说明:“长300里的中国运河,从广州延伸至北京。”[9]399
(二)被山脉隔断的“京广大运河”
在第二类介绍京广路线的欧洲文献中,虽也能看到“京广大运河”的说法,但较之上一类,这类文献介绍得更为全面细致,提到这条“京广大运河”中间有一段陆路连接。
1696年,曾亲至中国传教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在巴黎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mémoiresurl’étatprésentdelaChine)。李明1687年来到中国传教,至1691年回到法国,前后在中国生活三年余。他的这部书出版后反响很大,是欧洲介绍中国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赫尔德在论述中国时也曾参考过它,并认为它对中国的“评价十分公允”。[3]433《中国近事报道》是一部书信集,全书由14封李明写给当时的法国政界显贵和教会高层的书信组成,介绍了中国的风土人情、政治宗教和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情况。在第四封写给克莱西伯爵的信中,李明向他仔细描述了中国的气候、土地、运河和河流。其中,他写道:“南方省份的运河之一被称为大运河,因为它贯穿整个王国,起自王国南方的广州,通往位于最北部的北京城。”[10]108至此处为止,李明的叙述与第一类文献并无大的差别。然而他又续写道:“途中只有一天的路程不得不走旱路以通过江西边境的梅岭山。”[10]108从李明的描述可以看出,所谓的“京广大运河”实际上并不是一条连贯的水路。李明执意将这条中间被山脉隔断的水路称作运河,或许是出于误解,或许是有意地夸大这项工程。
这一类介绍还可见于《当代历史或万国现状》(Modern History Or the Present State of All Nations)第一卷(1724)、1786年出版的《中国志》(De la Chine, ou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cet empire, rédigée d’après les Mémoires de la mission de Pékin)、第五版《新现代地理学系统》(A New System of Modern Geography: or, 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and Commercial Grammar,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Several Nations of the World, 1792)和第三版《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四卷(1797)。
在《当代历史或万国现状》中,托马斯·萨尔蒙(Thomas Salmon)对中国的运河和大运河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从内容上看,他的这段描述极有可能是参考李明在《中国近事报道》[10]107-109中的介绍完成的:
中国的每个省都有一条大的运河穿过,它承担着驰道的作用。这些运河的边缘铺着粗糙的大理石制成的方石板,纤夫就在石板上拉船。从大的运河中分流出许多小一些的运河,这些小一些的运河又会分出像小溪一样的支流,它们通常流向某个村庄或是小城。在这些运河上,处处都架有三孔、五孔或七孔桥。桥梁最中间的拱圈必须达到一定高度,以供桥下船只不用拆下桅杆就可以从中通过。这些桥全部都是由大理石或是其他石头建造的,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些数不清的,点缀着桥梁的漂亮运河提供更好的景色了,在它们的两岸,坐落着大量城市和村庄,而在河上,又有无数船舶在富饶的山谷间往来穿梭。在欧洲,我们完全没有可以与之相比拟的。
这些运河中的一条,被称为大运河,它起自中国最南部的广州,直通北方的都城北京。其长1200里,但在江西被一座山隔断,人们必须走一段不多日路程的陆路。[11]14
1786年,法国神父格鲁贤(Jean-Baptiste Gabriel Alexandre Grosier)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志》,此书最初是作为《中国通史》(HistoiregénéraledelaChine)的补遗卷面世的:18世纪初,耶稣会在华传教士冯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用六年时间将满文版朱熹《通鉴纲目》译为法语,在补充了一些其他材料后,形成了一部大部头的《中国通史》。冯秉正1737年即将书稿寄回法国,[12]611但此书一直到四十年后,才由格鲁贤整理成十二卷本,于1777年至1783年间陆续问世。1786年,格鲁贤又补充出版了《中国通史》的第十三卷,即为《中国志》。这一卷出版后大获成功,随后在1786、1787、1818—1820三次单独出版,又在1788、1789年分别被翻译为英语和德语。书中,格鲁贤在介绍中国的运河时写道:
在让湖泊和河流的有利位置发挥最大作用的方面,中国人展现出的聪明才智值得钦佩。著名的大运河是他们为方便贸易完成的主要工程之一。这条运河从广州一直延伸到北京,它沟通了所有南方和北方的省份。这项工程被称作御河,长六百里格。在这条运河上航行,除了需要在梅岭山行10或12里格陆路以外,其余全程都是无间断的。[13]358-359
格鲁贤在《中国志》里对大运河做的介绍,后来还几乎一字不差地被收入威廉·古思睿(William Guthrie)的《新现代地理学系统》第五版中:
古代中国人足以被称作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他们的运河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便利性和长度。主要的运河两侧砌有凿好的石块,这些运河非常深,可以承载大型船只,有时长度超过1000英里。其中最著名的运河从广州一直延伸到北京,它沟通了所有南方和北方的省份。这项工程被称作御河,长六百里格。在这条运河上航行,除了需要在梅岭山行10或12里格陆路以外,其余全程都是无间断的。[14]689
此外,在第三版《大英百科全书》的“中国”词条下,也可以看到这类对运河的介绍:“中国人付出了极辛勤的劳动,通过改善内河航运,使他们的湖泊河流转化为贸易优势。在这方面,他们的一个主要成就是极负盛名的连接广州和北京的运河,它沟通了南北诸省。这条运河长度超过600里格,但它在一处地方被山脉隔断,乘客必须在此处走陆路10到12里格。”[15]66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直至1875—1889年间出版的第九版,《大英百科全书》对中国大运河的介绍才改“京广”为“京杭”:“作为水上快速路而言,重要性排在长江之后的是运河,即在欧洲广为人知的大运河。这条宏伟的人工河起自浙江杭州府,通向直隶的天津,在此处它与北河相连,因此可以说它延伸至北京附近的通州。”[16]631
(三)京广水陆交通线
第三类文献不称“京广大运河”,而将大运河作为京广路线的一部分,有材料提及运河的终点在杭州。这些文献中较为典型的有《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physiquedel’empiredelaChineetdelaTartarieChinoise)和《北京、马尼拉和毛里求斯游记:1784—1801》(VoyagesàPéking,Manilleetl’?ledeFrancefaitsdansl’intervalledesannées1784 à 1801)。
《中华帝国全志》是18世纪欧洲介绍中国的文献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全书共四卷,于1735在巴黎出版。这部大部头介绍中国的著作出版后仅四年,即被译成英文,1747至1756年间又有了德语版,1774至1777年间俄语版也在圣彼得堡出版。这部书的翻译和出版情况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欧洲各国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志书的编者——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虽然从未到过中国,却与同会来华的传教士保持着长期的联系。他将这些传教士们发回的报道做统一的编辑和整理,最终形成《中华帝国全志》这部大百科式的中国介绍。在书的第二卷,有一段对大运河的描述,其中涉及京广路线:
没有什么可以与长达三百英里的大运河运粮河(Yun leang),或称御河相比拟。……
运河从北直隶省(Pe tche li)流经山东省(Chan tong),随后流入江南省(Kiang nan),并在此地汇入一条湍急的大河,中国人称其为黄河(Hoang ho),即黄色的河。沿此河航行两日,便达另一条河流,随即新的一段运河从此接续,直通淮安(Hoai ngan)。运河继续流经许多城市和地区,通向扬州(Yang tcheou),这是整个帝国最有名的港口之一。随后,在距南京一日路程之处,汇入长江(Yang tse kiang)。经长江可继续航行至江西省(Kiang si)的鄱阳湖(Po yang),纵穿此湖,即入赣江(Kan kiang)。此江将江西省几分为二。随后,须行陆路一日至南雄(Nan hiang),此为入广东省(Quang tong)的首座城市。在此处再登船,可经一条河流直通广州(Canton)。如此,或经江河,或经运河,可从帝国首都抵达中国最边缘的城市,十分便利地完成长达六百里的旅行。[17]186-187
这段材料虽然并没有明确说明大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但它开头谈到大运河长“三百英里”,末尾处说北京至广州全程“六百里”,可见材料的原作者并不认为大运河直接连通北京和广州,而只是京广线路中重要的一段。
对于京广路线和大运河之间的关系,法国汉学家小德金(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在其1808年出版的《北京、马尼拉和毛里求斯游记:1784—1801》中表述地更为清晰明确。小德金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德金(Joseph de Guignes)之子,他1784年来到中国,至1801年返回法国,先后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其间曾担任法国驻广州领事。这部游记记录了他在中国生活的种种见闻。在谈到中国的河流和运河时,他写道:
中国有无数河流和运河。中国人尽其所能地扩充它们,不仅是为了灌溉土地,也是为了方便国内交通。除非是在某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一切贸易都由水路进行,一切旅行都经水路完成。人们可以从广东一直走水路到北京,只除了中间的一天。
通向北京的御河非常长……在穿过山东省和江南省的一部分后,在杨家园(Yang-kia-yn)与黄河交汇;后从清江浦(Tsin-kiang-pou)流经淮安府(Quay-ngan-fou)、扬州府(Yang-tcheou-fou),在瓜州(Koua-tcheou)汇入长江;过长江后,再经镇江府(Tsin-kiang-fou),至杭州府(Hang-tcheou-fou),在此处结束它超过300小时的流程。[18]29-30,32
小德金在指出京广水陆交通线的同时,对大运河流经的主要省份、城市、起点和终点都做了比较清楚的介绍。这在同时期的材料中并不多见。
对上述三类文献进行梳理后,可以明确下列几点:
第一,在欧洲介绍中国的文献中,“京广大运河”的提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比较流行的。1697年出版的《中国近事报道》中已可见到这种说法,在18世纪的各类有关中国的欧洲文献里,这种说法更是多次出现。进入19世纪后,“京广大运河”较少出现在欧洲文献中,但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大英百科全书》仍保留着“京广大运河”的表述。
第二,三类文献的作者中,既有曾亲至中国,在中国生活过的传教士和使节,如李明和小德金等;也有不曾到过中国的百科作家和翻译家,如《一般水陆旅游史》的编者施瓦伯,《当代历史或万国现状》的作者萨尔蒙,第三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者科林·麦克法奎尔(Colin MacFarguhar)等。对于后一类作者而言,他们在介绍中国时使用的往往是前者的报道。这就使不少文献的介绍在内容上,甚至是在数据上都是非常相似的,如文中提到的《航行探险记新大全集》与《一般水陆旅游史》《中国近事报道》与《当代历史或万国现状》《中国志》与《新现代地理学系统》。但另一方面,相比《中国近事报道》《中国志》等专门介绍中国的书籍而言,《一般水陆旅游史》《当代历史或万国现状》《新现代地理学系统》等一般性的历史、地理著作受众更广,在“京广大运河”的说法在欧洲的传播中,它们发挥的影响不容忽视。
第三,“京广大运河”的说法显然是有误的。这种说法大量出现在欧洲文献中,且在所谓“运河”的长度、构成等细节上不尽相同,这使其具体形成实难确考。但能够明确的是,这一说法不是出于京杭大运河在流传中的语音讹误,而是来自一条绝大部分由水路构成的京广水陆交通线。根据《中华帝国全志》的记述,这条线路约沿京杭大运河南下至长江,过长江后,经江西入粤至广州。
三、17、18世纪中西交流中的京广水陆交通线及其历史源流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前两类欧洲文献在提到“京广大运河”时,几乎均称运河起自广州、通向北京,即一个自地方向京城、自南向北的方向,与中文的习惯正相反(京杭、京广),却与当时西方人进入中国的行进路线相吻合。这种由南而北的“广京”说法,暗示了17、18世纪欧洲文献中“京广大运河”的由来:这种说法不是欧洲人从中国的文献里翻译来的,而是他们自己的表述,它源于来华欧洲人的亲身经验。
17、18世纪间的中西交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它是由欧洲单方面推动和主导的。这一时期,欧洲对中国抱有极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宗教和贸易两个方面。大量传教士、商人和通商使团自欧洲来到中国。据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两个世纪间仅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就已超过四百人。[12]1-11另据包乐史和庄国土的研究,仅在顺治、康熙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五次派遣使团往中国,以期能与中国建立商贸关系。[19]31-32
然而,对于这一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使团和旅行者而言,进入中国的途径并不丰富。清朝初建时,承袭明制,实施海禁。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仅仅只能通过澳门这一已由葡萄牙人占据了一个多世纪的城市自由地进入中国”。[20]1-301而对于那时能够取道澳门进入中国内陆的欧洲人来说,广州是他们的第一站。这样的情况直至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后才有所改变。这一年,清政府解禁开海,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来华的欧洲人在获准后,可经广州、泉州、宁波、松江四口岸进入中国内地。然而,到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又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此后直至《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是中国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口岸,也是外国人经海路进入中国的唯一入口。总体来看,在17、18两个世纪里,广州始终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在1684年以前和1757年以后,经海路来华的外国人只能通过广州进入中国内地。
下面这幅绘于约1750年,题为“中国大城市广州一览”的西班牙图画(见图1),充分反映出18世纪中叶广州繁忙的海外贸易和交流景象。

图1 “中国大城市广州一览”[21]135
在当时,对于大多数进入广州的外国商旅而言,这个繁荣的港口城市已经是他们远航的目的地。但对许多在广州登岸的欧洲来华传教士和使节来说,这里只是他们另一段旅途的起点,而终点则在遥远的中国首都——北京。仅在《一般水陆旅游史》第五卷中,就摘录有五篇欧洲人自广州往北京的游记:荷兰旅行家约翰·纽霍夫(Joan Nieuhof)及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1655年自广州往北京,[5]5:236-274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93年自北京往广州,[5]5:469-477意大利旅行家杰梅里(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 Careri)1695年自广州至北京,[5]5:478-511教皇使节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1720年自广州至北京,[5]5:545-555和法国传教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1722年自广州往北京[5]5:536-546的游记。除此之外,1793年,由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领的英国使团返英时,也曾自北京往广州出海,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22]394-478和使团成员约翰·巴罗(John Barrow)对此都曾有过记述。[23]428-487
自广州去往北京的路自然不止一条。上述游记的作者在广州和北京之间往来时,选择的路线均取道梅岭过江西,大部分以水路为主,但在整体上不完全相同。其中,纽霍夫及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自广州入京的行进路线与《中华帝国全志》中对京广路线的描述完全一致。但相较《中华帝国全志》,纽霍夫的记录则更要细致得多,从其中可以看到这一条被许多欧洲人错认为“京广大运河”的京广水陆交通线的具体构成。
(一)纽霍夫游记和提维诺地图中的京广水陆交通线
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使团前往中国,以期获得在中国南海通商的许可。使团由彼得·德·侯耶尔(Peter de Goyer)和雅克布·德·凯泽尔(Jacob de Keyser)率领,1655年抵达广州,次年初自广州往北京觐见顺治帝,请求被拒绝后,使团又自北京返回广州,于1657年离开中国。在往返于北京和广州之间的两年时间里,纽霍夫随使团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他将沿途的所见所闻和在北京的经历都详细地记录下来,与他绘制的150幅关于中国城市、山川、建筑和动植物的图画一道整理成书,以《荷使初访中国记》(HetGezandtschapderNeêrlandtscheOost-IndischeCompagnie,aandengrootenTartarischenCham,dentegenwoordigenKeizervanChina)为题,1665年由他的兄弟亨德里克·纽霍夫(Hendrik Nieuhof)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该书面世后大获成功,短短十年之间,就有了四个荷兰语版(1665,1666,1669,1670),一个法语版(1665),三个德语版(1666, 1669,1675),一个拉丁语版(1668)和两个英语版(1669,1673)。在书中,他用一百余页的篇幅详细描述了使团自广州入京时的具体经过,记录了他们行经的城市和村落,沿途所见,乃至每段路途耗费的时间。这是西方文献对这一条京广之间的交通线最为详尽的记述。
总结纽霍夫的记录,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团的行程大体如下:1656年3月17日一行人自广州启程,先沿北江航行,经三水、清远、英德、韶州,4月4日至赣粤边境的南雄。在此处,他们改行陆路,整装4日后,于4月9日早9时离开南雄,过梅岭,当日傍晚即至江西省南安。自南安起,一行人续行水路,船行章水(赣江上游)上,经南康,4月15日至赣州,在此地船入赣江,经万安、泰和、吉安、吉水、峡江、新淦、丰城,4月23日至南昌,随后经鄱阳湖边的吴城,再穿鄱阳湖,4月28日至长江南岸的湖口。自湖口起,沿长江向东航行至彭泽,过江南省安庆、铜陵、芜湖、当涂,5月4日至南京,在南京修整和游览十四日后,使团于5月18日再度启程,过仪征,进入运河,5月24日至扬州,经高邮、宝应、淮安,在清江浦转入黄河,航行过山东桃源后再入运河,经宿迁、迦口、济宁、东昌,6月20日抵达临清。自临清起,驶入卫河(卫运河),经武城、直隶故城、吴桥、东光、长芦(沧州)、兴济、靖海,7月4日抵天津,后经河西务、漷县,7月16日至张家湾,使团在这里换行陆路,次日抵达通州,随后进入北京。[24]66-175
根据纽霍夫的记录,荷兰使团先后经过北江、赣江、鄱阳湖、长江、大运河、黄河、卫(运)河等多条河流、运河河段以及湖泊,其间在赣粤边境换陆路通过梅岭时,的确只花费了一日时间。
1663年,法国作家、地图绘制家麦基齐德克·提维诺(MelchisédechThévenot)出版了《奇旅报道》(RelationsdeDiversVoyagesCurieux),书中收录有一幅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其中中国的部分根据纽霍夫的行程绘出。[25]8
相较欧洲同时期的中国地图,提维诺的地图在比例和准确性上胜出不少。可以看到,这份地图详细地标出了京广路线沿线的中国各城镇,在赣粤边境绘有梅岭,江西省境内绘有鄱阳湖,直观地显示出这一路线的走向和构成。
(二)京广水陆交通线的历史源流
纽霍夫记录的这一条京广水陆交通线由多条水道相接而成,整条路线设施完备,行船中遇逆水或者无风时,沿岸皆有纤夫拉船,可以说是一条非常成熟的交通线。那么,这条路线在中文史料中有所记载吗?
在《明代海外贸易史》中,李金明曾谈到明代时规定的京广贡道:“由广州运送贡品到北京的路线是:自怀远驿出发,乘船到佛山,溯北江而上,经韶关到南雄,然后越过梅岭,进入江西南安,由水路辗转以抵北京附近运河终点”,而南雄至南安一段,“因限隔梅岭,舟楫不通,需用民力借运”。[26]16可以看到,纽霍夫记录的京广路线在大体上与明时广州至北京的贡道是相符的。清朝前期推行朝贡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到北京的目的是想与清朝建立开放的贸易关系,但在清廷看来,他们一行人则是荷兰派往大清朝贡的贡使。清代对各国朝贡路线有明确规定,而早期时又基本沿用了明制,纽霍夫一行走的应就是这一条明代沿袭下来的贡道。然而,由于“我国旧史志往往忽视记载交通路线”,[27]2明清时京广贡道的具体路线史料中少有详述。加之国内文献对大运河的关注历来也多集中在华北和江南一带,对于依靠京杭大运河实现的京广水陆交通的详细记载和研究很少。在这个意义上,纽霍夫的记录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他对途中行经的各河道情况、水流、河上船只等等描述细致翔实,具有较高的中西交通史价值。
参考纽霍夫的记录,这一条贡道主要为水路,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由大运河沟通的京杭水路,二是长江的湖口至南京一段,三是由梅岭连接的赣粤水路。三段水路中,长江是天然水道,京杭水路自元代京杭大运河重修后一直是漕运要道,而赣粤水路的形成则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发展历程,与海外贸易的繁荣息息相关。
赣粤水路主要依靠梅岭的一段陆路连接广东的北江和江西的赣江、鄱阳湖而成。梅岭在广东南雄和江西南安之间,是北江和赣江的分水岭。713年(唐玄宗先天二年),为便利海外商品自广东经江西向内陆运输,张九龄请旨在梅岭开凿驿道。驿道修成后,梅岭的通行状况一改旧日“人苦峻极,行径寅缘”,“载则曾不容轨”,“运则负之以背”的状况。[28]608这条驿道随后成为赣粤之间的重要商道。
然而,梅岭驿道的开辟,与赣粤间水路的形成并不同步。据《宋史·蒙正传》载,宋太祖乾德年间(963—968),“岭南陆运香药入京,诏蒙正往规划。蒙正请自广、韶江泝流至南雄;由大庾岭步运至南安军,凡三铺,铺给卒三十人;复由水路输送”。[29]9101“大庾岭”即梅岭。由此处记载可知,宋太祖年间,自广东运香药至开封,依然惯走陆路。梅岭驿道修成二百年五十余后,赣粤间的水路输送仍远未形成常例。而蒙正规划的新香药运输路径起自广州,经韶关至南雄均走水路,南雄至江西南安军之间走陆路过梅岭,此后续走水路。这一条路线与后来的赣粤水路已十分一致。
《宋史·凌策传》又载,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岭南输香药,以陲置卒万人,分铺二百,负担抵京师,且以烦役为患。诏策规制之,策请陆运至南安,汎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转送之费”。[29]10128从此处记载来看,蒙正在宋太祖时规划的新香药运输路径并未得到长期沿袭。宋太宗年间,从广东运送香药时,竟然又考虑全走陆路,以至于要“置卒万人”,分两百站以人力负担至开封,可谓劳民伤财。而观凌策提出的办法——先从广东陆运香药至江西南安,再走水路北上,将所需役卒人数从万人减至八百,的确“大省转送之费”。然而,蒙正规划的赣粤水路运输只需陆运三站,每站三十人,共只需九十人,凌策在进入江西境内后才转水路的运输方法相比之下仍要不便许多。
从《宋史》的这两处记载看,赣粤水路的开通应与海外贸易密切相关。宋太祖、太宗年间两次在赣粤一线尝试水路运输,都是为了将海外来的香药自广东沿海一带转运至内地。再往前看,张九龄开凿梅岭驿道也是为了便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28]608赣粤水路的最终形成,无疑大大方便了广东和江西之间,乃至海外与中国内地之间的货物输送。
明代后,赣粤水路不仅成为官方规定的朝贡线路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繁忙的交通和商贸要道。万历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曾在广州往南京的路上途经梅岭。在过梅岭时,利玛窦注意到,“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不断经这一条通道“输往内地”,梅岭上往来行人如织,热闹非凡,“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则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像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30]276
作为朝贡路线,由赣粤水路、长江、京杭水路共同构成的京广水陆交通线优缺点都非常明显。这一条交通线的主要缺陷在于耗时长、不可预料的因素多。纽霍夫在游记中曾提到,荷兰使团一行由广州向南雄航行时,要逆北江而上,全程都需人力在岸边拉船,行船既慢又艰难。[24]79这样需要靠人力拖船而行的航段在整条交通线上还有很多。到了秋冬,北方的河道又会因枯水期或结冰上冻而无法通航。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在访问结束后,于10月7日自北京启程,往广州出海返英。使团副使斯当东记述,使团在通州登船时,“白河水位确实已经很低,并且还在继续下降,再等几天恐怕就不能走大船了”。[22]399在运河上航行,遇到漕运繁忙时,水面船只拥挤,不易通过,有时需要等待很长时间。英使团成员约翰·巴罗曾在游记中记道,使团的行程必须要在杭州“耽误两天,因为行李要经一个拥塞的河道运达”。[23]448
由于这些因素,由京广水陆交通线往来北京和广州之间,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用纽霍夫和耶稣会士白晋的行程作一对比,可以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纽霍夫及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一行人1656年3月17日自广州动身,7月17日抵达北京,全程耗时四个月。而白晋在1693年受康熙帝指派出使法国时,走的是北京与广州之间的陆路。他于1693年7月8日启程,8月21日即抵达广州,全程只用了一月余。[5]469-477
京广水陆交通线最大的优点则在于行程舒适,运力大。这条交通线基本由水路组成,在运送贡品、货物等方面有巨大的优势。纽霍夫曾提到,荷兰使团携带了大量送给顺治帝的礼物,在广州启程时,组成了一支50艘船的船队,[24]60在梅岭换行陆路时,则需要四百五十人搬运。[24]76这样的规模,假如走陆路从广州至北京,可想而知是极为不便的。而这也从侧面说明,在当时,京广之间的水陆交通各段水道的运力整体上是较为可观的。
(三)京广水陆交通线上的得与失
京广水陆交通线的形成与中国的海外贸易是不可分割的。在17、18世纪时,它又成为欧洲人进入中国政治中心的一条重要通道,在中西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一条通道也见证了中国曾经在历史中的故步自封。1655年,来到中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携带大量礼品,向清政府提出开放贸易的请求,但在清政府眼中,这却是“僻在西陲”,“声教不及”的番邦“赴阙来朝”。[31]803近一个半世纪后,马戛尔尼率领的英使团带着“各种各样、最近发明的昂贵仪器”[23]67访问中国,希望能够引起当时中国人的兴趣。然而“无论乾隆本人,还是他身边的人,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奇心”,“没有一个人关注水压、光学原理、透视法、幻灯、戏箱”。[23]67这样的自大和封闭使中国在17、18两个世纪间在科学和技术的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
17、18世纪间的京广水陆交通线是欧洲人通向中国的一条要道,但它却没能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条通道。今天,这一历史仍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应以史为鉴,始终敞开胸怀与世界交流。
四、小结
总的来说,康德、赫尔德笔下的“京广大运河”、京广水路不是笔误。这种说法在17、18世纪欧洲介绍中国的文献当中非常流行。它源于一条确实存在的京广水陆交通线。这条线路的形成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过程。对于清初来华的传教士、使节和旅行者来说,这是一条往来于中国的首都北京和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之间,进而往来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欧洲之间的重要通路。在17、18世纪的中西交流中,这条通路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这条路上,诞生过不少重要的游记。游记的作者把往来于这条路线上的见闻和经历记录下来,带回欧洲,向欧洲介绍了中国,对欧洲人认识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