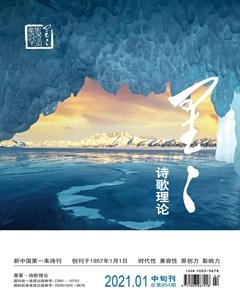把诗歌还给人民
唐政,当代诗人,评论家。现居重庆。曾在大学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后辞职经商。有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报》《星星》《草堂》《作家》《青年文学》《诗潮》等刊物。
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這既是诗歌发展的规律,也是时代对诗歌的基本要求。《诗经》《离骚》、汉赋、唐诗宋词,都是以不同的文学形态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但我们不能据此简单地说,每个时代的诗歌都一定要自成体系和另辟新格。因为诗歌除了时代的要求,它还必须要完成其自主化的进程,这显得更艰难和漫长。每首诗歌在其自主化进程中,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脉络,这是艺术的传承。当然,诗歌也必定要响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艺术才能不断地获得新的生命和能量。
新诗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更多形式上的嬗变,这也是诗歌得以异彩纷呈的根源。但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无论经历了怎样的革命,它依然会处在不断地变新求异之中。文学发展没有终极,它总是在相对接近极致时又峰回路转。比如从诗到词,从古体到白话,其实都是应了时代的具体要求。甚至就唐诗本身,盛唐、中唐、晚唐都呈现出了不同的诗歌气象。
从古体诗到白话诗,这不止是一场形式上的革命,也是诗歌内容向大众和现实的复归。随着人们的生活内容和说话方式的改变,文学的语言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文言到文白夹杂再到白话,诗歌语言的自主化进程是合乎了内在逻辑变化的。但从郭沫若、胡适等人的白话诗始,当代自由体诗歌在推陈出新的问题上,“推陈”明显没跟上“出新”的步伐。也就是说诗歌中“歌”的元素渐渐减少直至消失,诗歌变成了“诗”,“诗”成了一种分行体文字。同时,传统诗歌的众多美学原则也跟着逐渐消失,比如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格律美等,更别说意境、空灵、传神了。每一个美学原则的确立、盛行和结束,都是时间和空间相对应的结果。
西渡在《新诗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诗人》中谈到:“中国自陆游以降便没有真正的大诗人了。”意思是不仅是新诗,自宋代以后的旧体诗,也都没有产生过大诗人。但像郭沫若、艾青、穆旦、海子、顾城等,都是有可能成为大诗人的,但为什么后来又都没能成为大诗人呢?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归根结底是诗人个体的原因,他们的思想还没达到那个高度,他们的境界没有实现最后突破,诗歌表现的形式也还缺乏足够的建设性。
进入21世纪后,强大的互联网优势和相对开放的话语系统,彻底改变了诗歌传播的方式、途径和速度,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诗歌创作和阅读的习惯。大量的写作者抛弃了格式化的稿子、冰冷的邮局,热衷于建立自主性的写作平台并自由发布,使诗歌写作由最初的集体回到个体,诗歌发布则由个体回到集体,诗歌交流也从被动变为主动,从纯粹的阅读到复杂的阅读干预(跟贴和回贴)。但人们的审美心态和标准尚未完全适应互联网形式,这从某种意义上说,造成了诗歌的审美困惑。
二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全球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所以,这个时代的诗歌总体表现上是迸发的、激进的,充满了幻想和乌托邦似的理想主义,和以往的保守主义不同。同时,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互相撕裂,诗歌创作和审美都出现了反向共振,直接导致诗歌美与非美的价值混淆,艺术和非艺术的观念混淆,诗歌总体风格摇摆不定。尤其是亲身经历过“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洗礼的诗人们,往往用华丽的外表掩饰内心的虚弱,诗歌形式上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一切艺术终了的阶段必有一个艺术的衰微期,艺术腐朽、枯萎,受着陈规惯例的束缚,毫无生气。相反,他的手段却从来没有这样熟练,所有的方法都十全十美,精致至极,甚至大众皆知,谁都能利用。诗歌语言已经发展完全,最平庸的作家也知道如何造句,如何换韵,如何处理一个结局,这时使艺术低落的乃是思想感情的薄弱”。人心的浮躁和偏执,不可能让诗歌得以冷静地沉淀。因此,诗歌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华和21世纪初的相对沉寂都是与时代的变化一脉相承的。
时间到了近十年,风云变幻的时代主题从多元化逐渐统一到发展这个大主题上来。人心思定,诗歌也在某种意义上开始追求诗学和美学的平衡之美。大量90后和00后的诗歌创作者一方面充分享受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艺术领域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巨大便利,他们的创作体现在更多地追求实现自我的价值和意义,而非众生。因此,这个时代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大量小众化的作品。表面上看,百花齐放,而实际上是对西方诗歌的一次自以为是的重构或者解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元素,尤其是从其他陌生领域引入的跨界元素,如物理、化学、生物、高等数学、绘画等为新时代的诗歌注入了更多的陌生化成分,也使诗歌创作有了更多的可能。题材的广阔性和视野的开放性,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歌意象驳杂而碎片化,同时也带来了碎片化的美感。
但诗歌的创新从来都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90和00后,他们似乎没有任何艺术的禁忌和束缚,在形式上更具侵略性,在思想上更是得到了自由的铺展。所有的文学艺术都在试图与当下生活形成某种呼应或者同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和思考,又是对这个重大历史进程的反思与回顾。而文学艺术的却是对这个结局和答案的哲学思考与艺术化再现。
90后和00后们的诗歌创作在整体风格上更加风轻云淡和举重若轻,在自我认知领域却纵横捭阖、汪洋恣肆,而鲜少触及重大的历史题材和对当下更深层次的精神挖掘,在人性的纵深层面欠缺思考。他们的诗歌,虽有题材的拓展,但过于边缘化。有表现形式的创新,但又过多地受制于当代西方诗歌的束缚;有意境和诗思上的探索,但又停留在非诗层面。他们广泛而深入地利用了互联网的传播优势,但因此又丧失了对传统诗歌美学原则的坚守和对诗美的基本判断。当然,90后和00后的诗歌有他们固有的话语权优势,这是与其他时代诗人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没有语法规则的显著束缚,亦没有思想的牢笼,结构大开大合,用语进退有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群体的诗人大多拥有很高的学历,他们的外语识读能力大大强于之前,所以,他们可以自由而充分地阅读西方诗歌。他们比前辈更直接和更完整地受到了西方诗歌的影响,这也决定了他们自由主义的写作立场,表现出了更具潜能的观念开拓和精神空间的铺展。
三
如果从朦胧诗时代开始统筹考量,我们不得不说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是缓慢的,甚至可以说相对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的出现,今天的诗歌艺术形式总体上是退化的。
从《诗经》开始到唐代诗歌,这一时期,可以说诗歌大体上还是人民的。无论是从民间采诗还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诗歌风格的发轫和互动,诗歌基本上没有离开民众诉求和他们的审美习惯。而唐诗以后,诗歌就慢慢地变成了一种精英文化,包括宋词元曲。而从古体到白话,看似与普通大众近了,但其实质仍是一种小众娱乐,因为当时军阀割据,写诗和读诗依然是所谓的主流精英文化阶层的审美趣味。
那么当下诗歌究竟应该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才能把诗歌还给人民,才能讓诗歌真正成为普通大众的精神食粮?这也许是一个太大的话题,但处于时代漩涡中的诗人却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首先是写什么?这是指诗歌的内容。其实也是个伪命题,因为诗歌什么都可以写,没有内容的禁区。但是作为文艺工作者,他有义务承担更多的精神教化和美育的责任,他有义务关心和关注人民和大众也关心和关注的话题,他要自觉地选择一些有健康的精神指向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的命题,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更高尚和更可为的阅读境界。所以我们谈写什么,实质上是谈诗人的自觉性和写作态度的问题。在当下时代,大众所关心的生活品质、幸福指数、社会保障、国家前途、精准扶贫、民族复兴,诗人没有理由不去关心。当然,你也可以一意孤行地继续写你的花花草草,谁也不会否定你。我们在这里谈的是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层面是人民大众需要诗歌,另一个层面是诗人如何创作他们需要的诗歌。而那种根本不屑于为普通大众创作的诗人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如何才能把普通大众喜爱和关心的题材诗意地再现出来,从而更接近大众的审美愉悦和需求,是当今诗人们应该反思的问题。诗学和哲学的终极问题就是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关注,但这并不等于说,对生命本体的关注就一定是形而上的,相反,不回避现实和最基本的生存状态,更是时代诗人的使命。
其次是怎么写?这是诗歌表现形式的范畴,同样也是一个伪命题。文无定法,诗无达诂,怎么写都可以,这是诗人创作的权利和创作的自由。从朦胧诗开始,当代诗歌便经历了各种形式的探索和尝试,朦胧的,唯美的,口语的,哲理的,玄幻的,我们不能以任何理由去评判这些形式本身的优劣。正如,我们不能说古体诗就落伍了,自由诗就先进了。诗歌的发展固然有其自主化进程的必然规律,但也有创作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我们只能说,好的诗歌是贴近大众审美需求而不是远离审美需求的。那些所谓诗歌是小众的艺术,所谓诗歌是越让人读不懂越好,所谓诗歌是高雅的殿堂艺术,必然远离普通百姓需求等等说法,都是违背了诗歌艺术本质的。《诗经》就是存留在民间的、由人民口口相传的经典;唐诗也是,人人会吟,人人会唱,方能传诵至今。而怎么写虽是诗人的自由选择,但也必须考虑到与人民的互动。包含情感的互动,命运的互动,以及表现形式的互动。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领会各种诗歌技巧的奥妙,我们应当自觉地照顾到一些非专业读者的审美能力,这是艺术工作者的基本义务。但不能因此降低了自己艺术的标准,这其实是给诗人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现在很多诗人所谓的“诗话”,是脱离了语言和语法规范的陌生化语言。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并不是说我们的语言要高得让大众都看不懂。我们希望听到的是那种亲密的、私人的声音,而不是简单的形容词和动词的组合,也不是讲台上的发言,更不是那些试图通过钢琴和其他乐器发出来的声音。我们需要听到诗人的声音至少是真实的声音,听得懂的声音。女诗人余秀华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典型的诗歌个案,快速地崛起并成为大众认可度比较高的诗人,就与她贴近生活、现实、生命本真状态的写作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为什么写?这就涉及到诗歌的功利目的了,也是许多诗人羞于触及的话题。他们认为诗歌的功利和目的性越强,诗歌的审美价值就会越弱,非诗的因素就会增多。事实并非如此,诗歌创作,如果连为什么写都不知道,那你写出来的作品就一定是空洞,没有目的,甚至都没有审美对象的。这其实是认识上的问题,为什么写是不是非诗的因素?为人民大众而写是不是功利目的?诗人自我情绪的释放又是不是一种功利目的?
四
当下,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诗歌?相信大部分的诗人和理论工作者都没有勇气来立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应是诗人和诗歌理论家,而应该是读者,只有读者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当今诗歌除了圈内的人在读,圈外还有几人在读诗歌?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够胆去问普通大众,问他们喜欢什么样的诗?我估计这将会是一个令整个中国诗坛都无比尴尬的答案。如果我们还因为诗歌是小众的高雅的艺术而沾沾自喜,而忽略了人民大众的阅读感受,这才是诗歌走向非诗的必然。而普通大众真正需要的诗歌又往往是我们所谓的诗人们不屑于去创作的。普通大众认可的诗歌,反倒成了圈子内的异类产物。我不知道这究竟是诗人的悲哀还是普通大众的悲哀?其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们的需要,是主动的主观的,而不是被动的,不是你写什么我就要什么,有什么我就读什么,读者也有选择的权利。精神食粮也是要合符市场规律的,按需生产,才是艺术生产的良性思维。
无论是主流媒体上的诗歌,还是互联网上自由传播的诗歌,或者是所谓民间诗刊上民间高手的大作,拿去给普通大众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一首诗歌只在圈内被认可,或者只被少数几个精英分子认可,自以为是,自得其乐,而不能广泛传播,普惠众生,这样的诗歌又有什么意思呢?越高雅的艺术越接近人心和人的本质,比如歌剧、交响乐、绘画,虽然欣赏者不一定能够专业地欣赏到每个音符每个乐章每个节奏的意义,但他们却能感受到美和愉悦,接受精神的洗礼,并充分享受声音和画面带来的快乐。这才是艺术的真谛和价值所在。
诗歌越写越复杂,越写越像是在搞语言实验。所有的技巧到最后都是对艺术本质的伤害。这如同语言一样,语法越简单的就越容易传播,也越先进。文学艺术应等同此理,它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日趋简单化而不是越来越复杂。修饰的力量和价值永远都只能是修饰,而不是根本。唐诗中写民间疾苦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写战争带来的伤痛有“城春草木深”,写边塞的苍茫有“一片孤城万仞山”,都是简单到极致又深刻到骨髓的诗句。而我们当下的诗歌弯弯绕,碎碎念,清风徐来,波澜不惊。但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自我陶醉于某一个词,某一个句子,某一个意象,某一个片断,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我们当下对于诗歌的审美也是狭隘的,仅限于诗歌小圈子里,为什么我们天天都在讴歌爱情和友情,天天都在关心人类的疾苦和命运,但人类却不关心我们的诗歌呢?我们写的爱情和友情难道不是他们所要?我们感受到的幸福和痛苦难道不是他们感同身受的?
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绝不能把这一切归罪于这个物质化的时代,人心浮躁,行色苍茫,人们不关心诗歌,他们没有更高的精神需求。人们不关心诗歌,并不是人们不需要诗歌,诗意地生活是每个人的生活目标。人们不关心诗歌,是因为诗歌根本不关心他们,或者说没有真正地关心到他们。唐朝是一个国富民弱的时代,宋代相反,国弱民富,但那个时代为什么就能达到诗词的顶峰?当下的诗歌创作缺乏贴近现实,贴近民生,贴近普通大众的精神追求,故步自封,自以为是,站在所谓的精神高点或元点去俯瞰众生的“疾苦”,其实那只是诗人自身的疾苦或者臆想的众生疾苦。
把诗歌还给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把诗歌还给诗歌本身。这些年,流行音乐、大众电影、电视剧、各种曲艺几乎都在以各种方式想尽办法还给人民。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才是真的人民的艺术。诗歌,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属于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