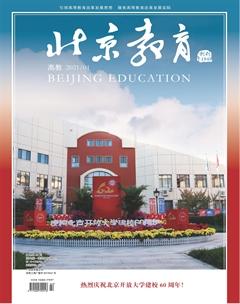从祛魅到赋权:寻找高等教育的公平世界
施晓光
摘 要:高等教育公平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值得不断思考和研究。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了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与外延、价值属性和形式内容;然后,又从经济发展、制度安排和文化观念三个维度分析了影响高等教育公平的主客观因素;最后,从理念重塑和行动策略选择两个方面提出保障高等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思路。
关键词:教育公平;概念;价值;困境和对策
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值得不断思考和研究。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中学考察时曾经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正义。” [1] 2018年11月,英国负责举办了有30个国家、100多个组织机构参加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机会日”大会。其目的旨在敦促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加快解决全世界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2]这表明:虽然世界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和普及阶段转变,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也得到了进入高等学府学习的机会,传统意义上的入学机会“不公平”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因为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入学机会”上的公平,同时更加关注过程和结果上的公平。人们开始对优质高等教育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诉求,不仅希望进入大学,而且还希望得到优质的高等教育过程,更希望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时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和平等的机会。这就不禁令人产生疑问:究竟什么是公平?高等教育领域是否存在一个真正的公平世界?是否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原因何在?又应该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一问题,从而让高等教育公平在最大限度上成为可能?基于此,本文首先从解释概念内涵出发对高等教育公平进行理论祛魅;然后,再从经济发展、制度安排和文化观念三个维度分析产生不公平的原因;最后,通过赋权的角度从观念世界和行动策略两个方面提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发展的对策建议。
高等教育公平的基本内涵
概念的理解和解释是揭示现象意义、认识事物本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理论祛魅和寻找意义的过程。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世界祛魅”的过程源于人类对“世界意义”的寻觅,这个过程的每一种发展都预示了对人类生存的某种信念的确认。[3]因此,本文首先拟从概念上解析什么是“公平”,进而推演出“高等教育公平”的基本内涵。
1.一个超级复杂的概念
公平(Fairness)是一个超级复杂的概念。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历史性、歧义性和难以量化等特征方面。首先,公平是一个历史概念。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明确指出:“公平即正义”。[4]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思想,将“正义视为平等的同义语”[5]。其次,公平是一个发展性概念。从内涵外延到价值属性,从形式到内容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不断与时俱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不再失败:教育平等十大举措》(2007年)的报告中对“公平”做出了一个权威性的解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平等”(Equality),即任何个人和社会环境,如区域、城乡、性别、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种族出身等因素都不应成为实现发展潜力的障碍;二是“包容”(Inclusiveness),即所有人的基本最低标准和权力应该得到保障。[6]再次,公平是一个多歧义概念。对其理解和解释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譬如:社会学家胡森和科尔曼认为公平重点在于机会和权利在多大程度上的获得;伦理学家罗杰斯则强调公平是对自由和正义的追求;经济学家海特曼则认为公平的内核是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由于出身生长环境、家庭经济地位以及教育水平不同,往往会造成人们对公平的认知、感知和理解上的巨大差异性。最后,公平是一个难量化概念。有学者认为给“公平下个定义要比识别不公平现象困难得多”,因为对“公平”与“不公平”的判断与个体主观感受有着直接的关联性。[7]美国学者斯塔西·亚当斯发明一个公平关系的方程式,即个人:结果/投入=他人:结果/投入。当公式比值相等时,人们就会产生公平感。[8]然而,这种想法只在理论上有意义。在现实中,个人的投入与结果并不一定成正比。因此说,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公平。公平是相对的,而不公平才是绝对的。
2.现实世界中的理想诉求
根据上述对公平概念的释义,我们可以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予以如下几个方面的识读:
第一,高等教育公平是指稀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不同人群中实现均衡、公正以及合理的分配,具体体现在入学机会和权利均等;接受教育过程待遇上一视同仁;毕业求职和职业发展无差别性竞争等,即实现高等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三方面资源均衡、公正及合理分配。[9]从这个定义上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公平实际上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是一种价值理性意义上的追求。在现实社会中,绝对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公平并不存在,也是不真实的,但从高等教育公平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双重属性特点上看,将之视为期冀的美好愿景和价值理性追求是极其必要,也是可能的。一方面,從内在价值上看,高等教育公平是一种被赋予自然属性的客观存在,即包括一个人或一群人所拥有通常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的基本权利。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教育反歧视公约》第4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1)款之规定,强调“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面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性别、语言、宗教,也不因经济、文化或社会差异或身体残疾而被拒绝接受高等教育”。[10]再如:《俄罗斯联邦教育法》也明确规定:“国家教育政策保障每个公民获得教育权利,……俄罗斯公民有权在竞试的基础上免费接受首次的高等教育。”[11]另一方面,从外在价值上看,高等教育公平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调整社会制度的一种国家治理策略,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和手段。换言之,高等教育公平被国家和社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性赋予了某种责任和使命。进入21世纪,接受高等教育不论是对于国家和社会,还是对家庭和个人都显得越来越重要,作用不可替代。人们对高等教育公平的诉求不仅仅满足于理论上的阐述和法律上的规定,更希望高等教育公平在实践层面得到践行,并被人们主观感受和体验。因此,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其所制定的高等教育政策能否有利于实现公平和公正,并被人们满意和称道是鉴别政府“有为”和“无为”的试金石,是衡量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优劣的重要指标和参照。
第二,高等教育公平是一种社会理想和个人家庭理想的集中反映,可以体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和文明发展程度。缺乏理想目标的社会一定是混乱无序的社会。不追求“公平”的国家不是文明和民主的国家。一方面,之于国家和社会,促进和实现高等教育公平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发展目标,是建立民主、平等和公正国家和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条件。另一方面,之于个人和家庭,“上大学,上好大学”不单纯是个人的梦想,同时也寄托着家族的希望。尤其是对生活在社会底层和出身卑微的人而言,接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文凭社会”某些岗位所需的学历学位,或许就是其实现“鲤鱼跳龙门”式的社会身份转换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第三,理论上,高等教育公平是由一系列极具实践指导意义的行动准则构成,包括“平等赋权”“效率效能”“民主自由”“补偿弱势”“程序公平”和“非歧视性”等理念和原则。这些理念和原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得以践行,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公平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然而,高等教育公平的这些理念和原则的形成和确立不是自然发生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被剥削阶级和弱势群体不断斗争获得的权利成就。历史上高等教育一直被视为是少数贵族的特权,是满足有产阶层闲暇好奇的奢饰品。直到20世纪中期之后,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的到来,这一状况才得到改变。如今,接受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优越特权,而是所有人拥有的平等权利。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概念也正在发生改变:“第三级教育”(Tertiary Education)和“中学后教育”(Post Secondary Education)作为高等教育的同义语,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这种改变不仅仅是“术语”上的变化,而是宣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阶段。事实上,高等教育内涵与外延上的这种变化进一步反映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理解和诉求。
第四,高等教育公平不能等同于教育的平均主义,即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一样的教育。英国学者安迪·格林在《教育、平等和社会凝聚力:一种基于比较的分析》中指出:“高等教育公平不过是一种有条件的虚幻存在,是极其不真实的。……由于高等教育公平理想和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两者之间共同实现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12]教育经济学将高等教育定义为“高投入低产出”的准公共产品,是具有竞争性的稀缺资源。如果这种有限的资源给予了一部分人,这就将意味着另外一些人的机会被剥夺。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的高等教育公平是“不真实”(Non-reality)和“不存在”(Non-existence)的。尽管“谁能上大学”“上什么样的大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高等教育起点是否“公平”“公正”的“风向标”或“晴雨表”,但是高等教育公平并非是指个体之间能够享受到无差别性,而是指某个群体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过程和结果方面的权利和地位上的平等。因为毕竟优质高等教育属于非公共性的稀缺资源,始终充满竞争性。
影响高等教育公平的因素
前世界银行高级专家萨米尔(Jamil Salmi)受 “鲁米拉”(Lumina)基金会之托撰写的《全世界—全球高等教育公平政策》报告发现:全球很多国家对于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只做了表面文章。该报告批评道:“很多国家除了发表一些官方的关于公平的声明,试图反映其一般的接纳性共同原则之外,在很多情况下,当这些原则需要被转化成实际政策和干预措施时,很多国家对公平议程不过耍耍 ‘嘴上功夫(Lip Service)”。[13]由此可见,各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发展程度和水平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高等教育公平的诉求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原因何在?这里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
1.发展不平衡的制约
第一,社会贫富差距是造成高等教育不公平的主要根源之一。经济是基础,没有经济发展,国家就不可能大量投资高等教育,就不能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也就不能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旺盛的需求。因此,发展经济、脱贫致富是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关键所在。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发达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也是最发达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普及化程度也相对较高。例如: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大学数量和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也是最多的。然而,经济发展只是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换言之,高等教育公平并非完全是与国家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保持一致的。虽然美国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同时美国也是社会严重“不平等”的国家。有数据表明:美国在西方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为严重。最富有的10%家庭占有美国全部家庭净资产的近75%。[14]虽然美国高等教育很发达,一流大学数量也很多,但昂贵的学费也令许多低收入家庭子女难以支付。
第二,区域发展不均衡是制约高等教育公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中国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生产形态同时存在。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或者南部与北部)之间发展存在巨大差距。一般来说,经济發展水平高的地区,其高等教育水平也比较高,其所生产出的劳动力就具有竞争力。这种差别不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表现在高等教育领域。以我国高等教育分布情况来看,大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高于西部和内地高等教育。
第三,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高等教育公平。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76个国家(主要是低收入国家)进行调查发现:在25岁至29岁的最贫困人群中,只有1%的人完成了至少四年的高等教育,而最富裕人群中这一比例为20%。[15] OECD的《2018年教育概览》报告指出:社会经济地位、性别、移民背景、居住地理位置是造成教育不公平的四个重要方面,其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教育公平和社会产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出生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家庭的孩子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低,且往往他们的父母本身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16]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父辈之间阶层、收入差异的程度与子辈享有教育机会的程度基本成正比关系。最显著的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致使农村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明显偏低。另外,在一些重点大学中,来自贫困家庭的子女数量急剧减少,“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
2.制度安排的缺陷
“制度安排”可以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能对人们行为产生规范影响的规则”[17]。既然规则是人制定的,那么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既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从理论上讲,好的制度安排应该保护或者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应该体现“规则公平”和“无歧视性”两大基本原则。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建立体现这两个“原则”的制度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制度安排人的稳定天性是利己的,即人是一个“经济人”。[18]有学者指出:“自私性设计是一切制度安排的基础”,即一切制度设计都是按照“人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来安排。[19]
第一,不好的制度产生的一个恶果是寻租行为,又称“权力腐败”。所谓寻租行为是指政府部门或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获得自身好处的行为。在高等教育领域,由于优质资源稀缺,各种权力和腐败也渗透到院校。其中利用关系进入大学就符合腐败的定义。[20]在许多国家,这种以幕后操纵为基础的入学徇私舞弊行为十分普遍,有时这些行为被认为是对社会资本的合法利用。例如:在欧美,那些有“能量”的家长同样会对大学招生机构施加巨大的压力,千方百计给大学校长“打招呼”“递条子”,甚至以巨额捐款作为交换条件。[21]在我国,尤其是在研究生教育中,一些人利用手中权力和影响力,不遵守学校纪律,投机钻营,名不副实,挂羊头卖狗肉,把专业学习和攻读学位看作是“镀金”和积攒“资本”的过程。这就是“翟某某事件”和“官员攻读博士现象”产生的原因。
第二,政府决策失误或政策偏差是另一种不合理制度安排的表现,也是造成高等教育不公平的原因之一。政策失误或政策偏差并非决策者有意识地实施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有时,或许出发点和主观意愿是好的,但由于决策者政策水平限制,客观上导致“不好”的制度安排产生。例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招生分省定额制度对于人口多而高校数量少的省份学生就明显不公平。再如:我国确立重点大学制度以及“综合定额 +专项补助”式的高等教育拨款制度等都明显有利于央属院校少数名校。
第三,制度安排上阶段性的“权宜之计”。高等教育公平的前提是以充分资源为保障的。当资源不充分,或者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某些有利于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不得不被搁置或者暂时性放弃。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公平领域,“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性。“公平优先”抑或“效率优先”是每个国家和政府都必须要面对和考虑的问题。如果政府认为公平较为重要,并不顾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意味着追求所谓的高等教育公平,其后果就可能造成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上的延迟和标准质量的降低;如果政府认为效率比公平重要,严格按照市场逻辑,用效率的标准计算高等教育的成本,进而导致对公平问题的忽视。正因为如此,一些高等教育资源不充足的国家和社会,只能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但事实上,这样的政策只能是在资源不充足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
3.文化观念的滞后
文化观念滞后是指人们对高等教育认识落后于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从而导致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产生。
第一,教育政策决策者和管理者头脑中落后甚至错误的观念。主要表现为他们否认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为公平是不真实的,而不公平却是现实的存在且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基本的高等教育公平概念。当公平与效率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效率优先”而放弃“公平和正义”。或许,一些官员有时会把高等教育公平挂在口头,但在其思想意识中始终认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工作可有可无。有时,高等教育公平口号震天响,却不见他们制定任何具体的政策目标和任何可行项目,采取任何行动策略。即使有一些项目和行动,往往只会做表面文章,多半属于面子工程或形象工程。
第二,家庭和个人头脑中的落后和错误观念。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态度问题上。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那里的人们认为女性的主要社会责任是结婚生子,繁衍后代。例如:在我国农村,一些人男尊女卑思想严重,仍然抱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迂腐观念,不鼓励和支持女性上大学,希望她们尽早工作,结婚生子。当家庭无法同时资助子女上学的时候,家庭通常都是选择放弃女童接受教育的机会,这就导致很多女童在小学或中学阶段就被迫辍学,更不用说上大学。全球范围内,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属于弱势群体。一些家庭的女性因为得不到家庭的支持而过早地离开学校。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远远低于男性的原因。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性别平等与赋权成为世界范围有关社会包容与平等的核心议题,这种轻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落后文化才有所改变,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在逐渐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反映的仅是高等教育增量公平。
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理念与行动
高等教育公平既是理论性的,也是实践性的问题。保证和实现高等教育公平须从理念世界构建和现实行动策略两个方面寻找路径。
1.理念世界重构:强化三种意识
理念是行动的支配力量,具有先导作用。高等教育公平是一种自成一体的权利理念,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公平观念。这种观念往往与残酷的不平等的现实社会产生尖锐的矛盾,具有不可通约性的特征。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性和不可通约性的存在,很多人对待高等教育公平重要性程度的认识不够、意识不强。因此,培养良好的高等教育公平意识,强化正确的高等教育公平观念,是保证和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关键所在。
第一,坚持数量公平发展意识。发展是硬道理,是保证高等教育公平实现的前提。数量公平发展就是不断扩大高等教育供给,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从历史上看,世界各国高等教育都经历了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转变。在精英阶段,高等教育被视为少数富人的特权,大多数穷人子女无法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进入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为高等教育扩张提供了物质保障,使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成为可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成为所有人(不论出身、种族、社会阶层、年龄和性别)的权利。尤其是在“文凭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学位不再被視为一种“装饰品”,成为职业发展的“必需品”,是进入人力资本市场的基本需要。[22]因此,一个国家和社会要想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扩大高等教育有效供给,不断满足国家和个人对接受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
第二,坚持质量公平发展意识。有学者指出,在一定教育水平上实现数量平等之后,应考虑质量不平等问题。[23]从某种意义上说,质量公平是真正的公平,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完成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过渡之后,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再是难事,但是由于高校之间办学水平差距较大,所有人都希望有机会进入名校学习。如何提高整个系统办学水平,促进质量发展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之后,各国政府和社会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那么,什么是高等教育公平的质量标准呢?简单说,质量公平发展可以视为个性化差异发展的同义语,是高等教育公平最高水平的体现。个性化差异发展目的就要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使之在自身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得到公平的获得感,但是高等教育公平不是平均主义的高等教育,不意味着,也不可能供给每个人完全一样的教育产品。公平的获得感应该是建立在个体能力基础上的,需要每个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进行平衡。
第三,坚持责任共同分担意识。公平理论认为:“社会公正的中心问题是责任及责任认定问题。……如果找不到责任主体,那么也就不存在社会不公平。”[24] 高等教育公平是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和大学)的共同责任。首先,国家和政府是高等教育公平的第一责任主体。高等教育公平关乎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政府和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不仅需要在舆论上,而且还需要在行动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政府和国家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具体责任可以体现在: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为适龄青年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产品,最大限度地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制定有利于缩小地区、城乡之间差别,倾向弱势群体的特殊高等教育政策等。其次,高校是高等教育公平的主要实践者,可以视为确保高等教育公平的直接责任部门。高等教育公平的核心是包容性,或者说是全纳性的。这种包容性和全纳性深深植根于公正和平等机会的民主原则,并体现在高校的招生、培养和就业等各个环节之中。高校能否做到公平、公正、民主和透明,对待所有家庭出身、种族、社会阶层的学生一视同仁,是能否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再次,是社会和家庭的责任。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认为,高等教育是“高投入,低产出”的领域,需要大量经费投入作保障。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充,政府越来越成为有限责任和有限能力部门。政府不需要,也不可能保证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同样的高等教育。最后,高等教育不是公共产品,充其量只能算上准公共产品,具有排他性、竞争性和一定的公益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政府和学校责任外,社会企业、家庭个人和所有利益相关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才符合“成本分担”理论上所说的“谁投入,谁受益”原则。
2.行动策略选择:强化政策引导作用
政策是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结合点,是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原则。[25]因此,最有效的行动策略就是合理地制定和执行好教育政策,利用教育政策的引导、激励、协调等作用,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发展。怎样才能制定和执行好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这里主要从政策价值取向、政策项目设置和政策落实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政策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在政策制定和实施全过程中,高等教育资源向谁倾斜,向哪里倾斜与政治家和决策者们价值判断直接关联。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的理性分成两类:一种是“价值理性”,又称“实质理性”,只注重行为主体本身内在价值及价值意义,而对其能否兑现和成败得失不予考虑。另外一种是“工具理性”,又称“技术理性”,通常是把目标、手段和与之相伴的后果一起合理性地加以考虑和估量。[26]根据这样的分类,在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上,出现两种教育政策价值选择:一种是“公平优先论”,强调给“每个人公平的教育机会”,实现高等教育公平是制定政策时予以优先考虑的选项;另一种是“效率优先论”,认为虽然教育公平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但是在社会不公平现象被消除之前,教育公平不过是过于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因此,这种观点的典型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从理论上,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合理和也是理性的。因此,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公平似乎只是停留在文件文本上的“虚而不实”的口号,而只关注效率成为唯一的一种选择。
第二,教育政策的制定。高等教育公平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必须落实到行动。其中,最有效的行动就是制定相应的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制定高等教育公平政策是世界各国的常规做法:美国为了保证少数弱势群体,尤其是黑人的入学问题,专门出台了《平权法案》,即《肯定行动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Act);印度政府为保证有关表列种姓(SCs)、表列部落(STs)和其他落后阶级 (OBCs)的受教育权专门制定了教育“保留政策”(Reserve Policy);加拿大政府为保证最大的弱势群体—原住民的高等教育公平,专门制定了《原住民高等教育培训策略与行动计划》,提出要设置6,500万加元专项拨款用以提升原住民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我国为了保证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公平,专门出台一系列教育政策,诸如高考加分、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等;还有为了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出台的“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等。
第三,教育政策执行。这对实现高等教育公平至关重要。不论教育政策制定得多好,如果不能落实和实施,或者落实和实施得不好,那么这样的教育政策不仅是“纸上谈兵”,更是束之高阁的无用之物。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政策执行偏差。所谓政策执行偏差是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效果偏离实际目标,执行与目标之间出现差距,甚至偏离原目标,并产生不良社会结果的政策现象。在实践中,一旦政策执行出现偏差,其危害非常大。它会使一些好的政策流于形式,成为空头支票,无法产生预期效果。造成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除了一些教育政策自身存在不完善的原因之外,制度安排缺陷,如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督机制不健全是造成政策執行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另外,政策执行者素质和工作态度可能是造成执行偏差的原因。因此,在保证高等教育公平方面,国家制定相应政策和必要的项目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确保这些政策和项目在执行过程不出现偏差。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课题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01.
[2][13][15] Jamil Salmi(2018)All around the world: Higher education equity policies across the globe.Lumina [EB/OL].[2020-12-18].https://worldaccesshe.com/wp-content/uploads/2019/02/All-around-the-world-Higher-education-equity-policies-across-the-globe-FINAL-COPY-2.pdf.
[3]冯刚.马克斯·韦伯:文明与精神[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2.
[4]张法琨.古希腊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65-70.
[5]Georgios Anagnostopoulos · Gerasimos Santas(2018)Democracy, Justice, and Equality in Ancient Greec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springer[EB/OL].[2020-11-28].http://library.lol/main/ 6F4E E4043843 D7F8B74C1 342F58E897B.
[6]Simon Field et al.(2007). No more failures:ten steps to equity in education. Paris: OECD Publishing[EB/OL]. [2020-11-28]. http:/ /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45179151.pdf.
[7]Neil J.Dorans and Linda L.Cook,2016.Fairness in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Measurement,Routledge[EB/OL].[2020-11-28]. http://library.lol/main /A2ADEE313ECF3E956C 7374 BA890A66C9.
[8]周智杰.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特征及其政策保障[J].教师教育学报,2019,6(2):84-91.
[9]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91-217.
[10]UNESCO(1998)higher Education in the 21century:Vision and Action[EB/OL].http://old.moe.gov.cn// publicfiles/ business/htmlfiles/moe /moe_ 236/200409/712.html.
[11]赵伟.俄罗斯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障碍与解决政策[J].现代教育论丛,2019(5):89-96.
[12]GREEN A, PRESTON J, JANMAAT J G.Education, Equality and Social Cohesion:A Comparative Analysis [EB/OL]. [2020-11-28]. http://library.lol/main/4C23CAE4C926735E3A15EA08AC73CFAD.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N]. 人民日报,2020-03-14(6).
[16]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8:OECD Indicators [EB/OL]. [2020-11-28].https://www.oecd-ilibrary.org/ education /education- at-a-glance-2018.
[17]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2-33.
[18]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59.
[19]朱启才.权力、制度与经济增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69.
[20]OSIPIAN A. Corrup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Does it Differ across the Nations and Why?. December 2008Research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3(4) DOI: 10.2304/rcie.[EB/OL].[2008-03-04].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8618433.
[21]秦春華.世界顶尖大学招生如何防止腐败[N].中国青年报,2015-12-21(10).
[22]Bathmaker A M , Ingram N , Abrahams J , et al.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Mobility[M].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6.Higher Education,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Mobility:The Degree,Generation,Palgrave[EB/OL].[2020-11-28].http://library.lol/main/ 5B2AF70A7B35020AB16 DAA5835FF1BAC.
[23]LUCAS S R.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ducation transitions,track mobility,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1,10(6):1642-1690.
[24]Folger,R. & Cropanzano,R.Fairness Theory:Justice as Accountability.In J.Greenberg&R.Cropanzano(Eds.). Advances inOrganizationalJustice,StanfordUniversity Press[EB/OL]. [2020-11-28].https://www.scirp.org/reference/ ReferencesPapers. aspx?ReferenceID=1640071.
[25]吴遵民.关于建立我国科学的基础教育决策机制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2(12):35.
[26]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
说明:由于参考文献第[5][6][7][10][22][24]国外网站已无法下载,如有需要可以联系作者(shixiaoguang@pku.edu.cn).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