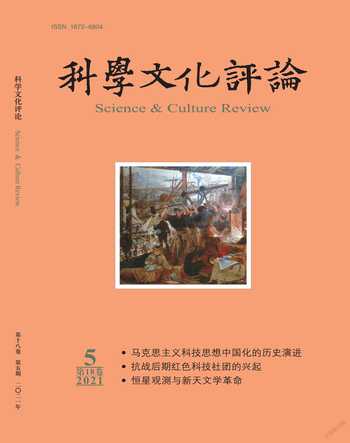全面抗战前国防化学知识的引入以《化学战争通论》的译介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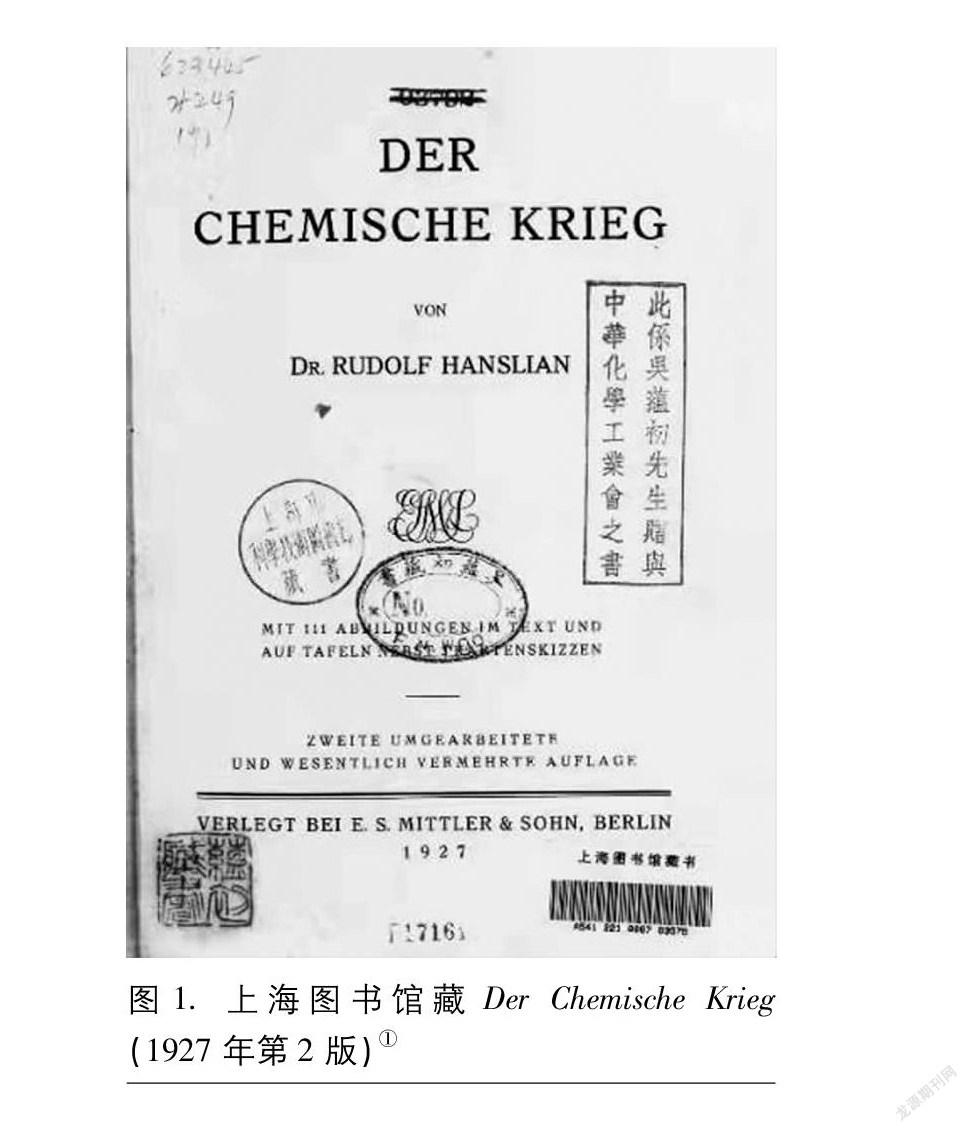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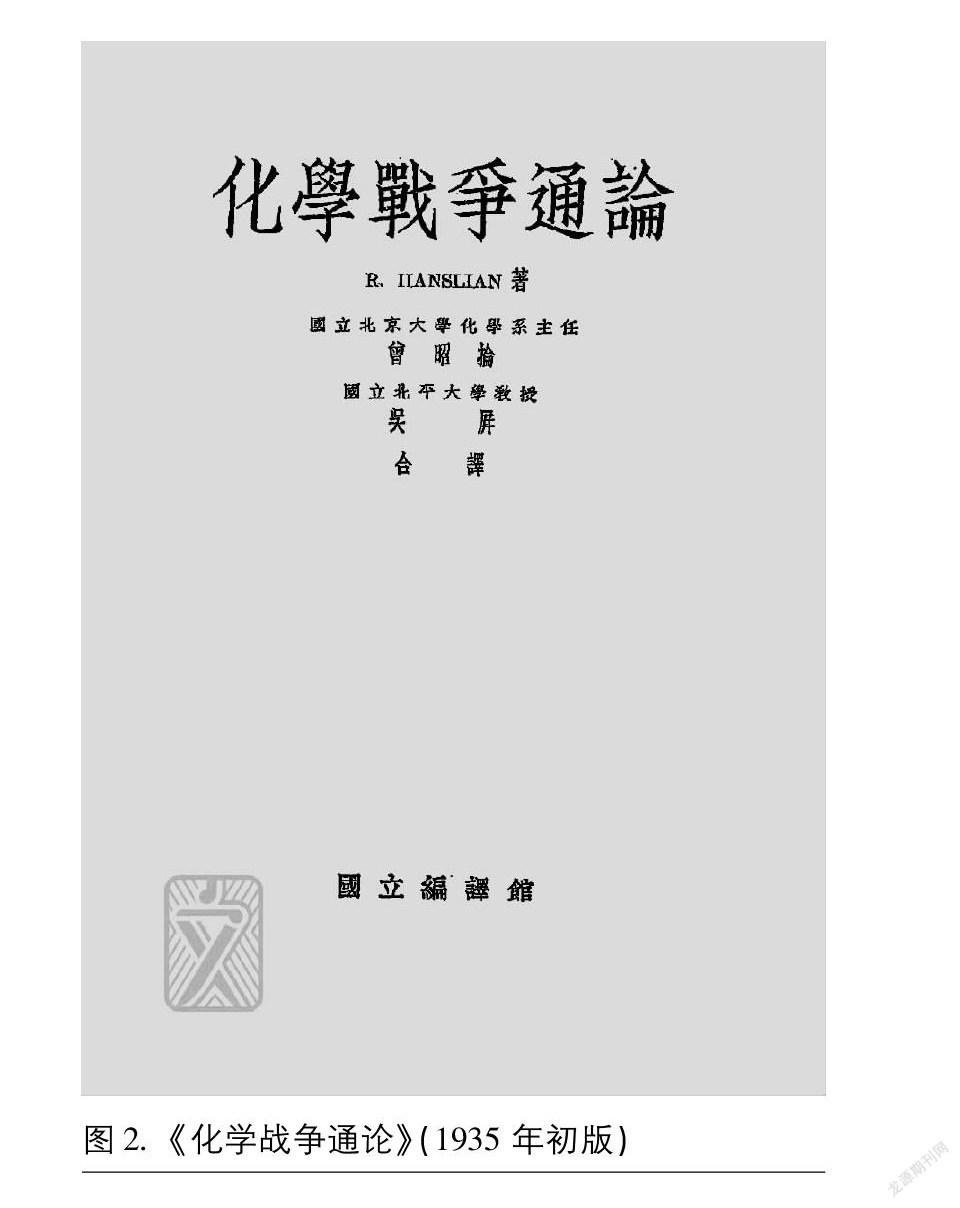
摘 要 《化学战争通论》由曾昭抡、吴屏合译,是全面抗战前国立编译馆编译的唯一一部军事学和国防化学理论著作。底本为1927年出版的德国著名化学家、军事科学家韩斯联的名著Der Chemische Krieg第2版。《化学战争通论》的编译工作由官方主导,科学工作者主持并參与,反映了当时在国防化学方面,中国政学两界“以德为师”的价值取向。该书忠实原著,语言流畅,译名规范,注解清晰,出版后对国内国防化学书籍产生深远的影响。该书的翻译出版是全面抗战前国防化学知识在中国引入的一个典型案例,体现了政治与科学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国防化学 化学战争通论 国立编译馆 科学传播
中图分类号 N092∶O6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1-04-07
作者简介:朱昊,1994年生,四川江油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Email: zhuhao@ihns.ac.cn。
① 民国时期与“国防化学”类似的称呼还有军用化学、军事化学、化学武器学、毒气化学等,其内涵在全面抗战前大致相同,主要指化学中涉及毒气、炸药和烟雾相关的部分。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过多讨论。可参考1936年6月29日《中央日报》所刊童志言《进展中的国防化学》一文对于“国防化学”的定义:“广义的国防化学,不仅指炸药毒气,并且把制造炸药毒气的原料,和一切与军事有关系的化学工业,都包括在内。至于狭义的国防化学,仅指炸药毒气而言。”
自19世纪以来,化学在西方国防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防化学”这一化学学科的重要分支也逐渐发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防化学①知识开始传入中国。至20世纪20年代,国内学界和军界在着手编写本土化的国防化学教材的同时,开始在官方支持下编译国外经典的国防化学著作。1935年,曾昭抡和吴屏的译著《化学战争通论》由国立编译馆出版。这本译著是国立编译馆在全面抗战前编译的73部学术著作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部国防化学和军事学理论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这一官方渠道,国防化学知识开始正式被引入中国当时国内国防化学著作的引入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由“官方主导,学界主持并参与”,如本文中曾昭抡、吴屏合译的《化学战争通论》是由教育部主导,后文中提到的《化学兵器学要览》(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司编,1931)、《化学战争》(吴沆,1933)等著作是由军政部主导。二是由科学工作者主导,如《军事化学》(胡逵、胡远编译,1930)及《最新化学战》(李昌明,1933),等等。。《化学战争通论》在全面抗战前中国引入的国防化学著作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目前学界关于《化学战争通论》尚无专门的探讨,有些论著虽然涉及该书,但基本是简要论述,对该书缺乏系统而坚实的实证研究。本文从部分原始文献入手,对《化学战争通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探清其翻译背景、底本和翻译情况,以及其影响和局限等问题,从侧面呈现全面抗战前国防化学知识在中国的引入情况。
一 《化学战争通论》的翻译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场上超越以往传统兵器的新型化学武器,如毒气弹、烟幕弹等,开始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化学武器“为现代战术开一新纪元”([1],页148),“利用化学药品制成毒气烟雾及纵火信号照明等药剂,于欧战中显示其特殊效能,颇引起军事家之注意”[2]。一战后,关于战场上化学武器的报道和介绍陆续见诸于国内报端,极大地引起国人的危机感。
“现代战争,十九为科学的战争,尤以化学战为最。”([3],引言)“化学国防,实国防上极重要之问题。”[4]随着化学武器在国内开始受到关注,国防化学知识也逐渐传入中国。1915年开始,《东方杂志》《进步》等国内刊物陆续开始介绍一战时各国使用的化学武器。1919年,作为民国时期国内最重要的科学刊物之一,《科学》杂志刊载了第一篇化学战争相关的学术文章《毒气战术》。此后,《工业杂志》《同德医学》《学艺》和《军事杂志》等国内刊物开始陆续系统介绍毒气、毒气战等国防化学相关知识。与此同时,毒气的防御也开始成为这一时期国内刊物上的重要话题。
20世纪20年代,国内报刊对于化学武器夸张的报道甚嚣尘上,对其形容是“暴戾恣睢,至德而极。淫巧杀人,惨无人道”[5],某些骇人听闻的报道引起民众对化学武器的极大恐慌。到20世纪30年代初,报道的化学毒气有“四千余种之多”,某些毒气仅需少量就能令“尸横遍野”[6]。同时,随着国内科学界对毒气、毒烟等化学武器的认识逐渐深入,对于化学武器的态度也逐渐回归理性,一方面认识到化学战的危害通过科学的防御是可以完全消除的,另一方面认识到毒气等化学武器的致死致残率远不如传统兵器高——军用毒气“有法防御,非若枪炮之必致人于死也”([7],页8),“除极少数之例外外,气体致病者(Gaskranken)之疗愈,均系完全的及永久的;残废之现象,完全无之”([8],页9)。国内对于毒气等化学武器持续夸大的宣传“将影响后方秩序,而致阻碍前线之抗敌情绪”[9],因此引导国内民众对其理性认识就显得尤为必要。
20世纪20年代,国内学界对于国防化学的认识尚停留在介绍国外相关成果的阶段,专门性的研究十分稀少——系统性的专著仅有1921年《欧战中之军用化学》和1929年《新兵器化学:毒瓦斯及烟》。20世纪30年代初,虽有《军事化学》《化学兵器学要览》《最新化学战》《化学战争》几部国防化学相关专著,以及《沪大科学·军事化学专号》等期刊问世。但书中要么材料过时,要么大谈理论,对于国内相关领域实践或指导性不强。1934年8月张郁岚著《化学武器教程》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刊行,内容质量虽然有所提高,但由于是内部刊物,国内相关研究者和大众很难接触到。
抗日战争爆发成为国防化学知识在国内传播的重要推动。在“1·28”淞沪抗战激战方殷之际,“举国上下,积极注意国防化学”,政府希望为国家安全“自科学研究方面树立安全可靠根基,以为实施国防之预备”([10],页10—12)。1932年,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以下简称“讨论会”)在南京召开。“大会决议案”中,第一项即为“国防化学方面决议案”。其中“关于教育及宣传者”中包括“请国立编译馆编译关于国防化学书籍以广宣传案”,且附有说明:“各国国防化学之研究,日新月异,关于此类之出版物,亦日渐增多。亟宜早事翻译,以资广播。同时亦当自行编制各种专籍及小册,借广宣传”,并“请教育部转令国立编译馆从事编译”([10],页98)。讨论会召开之后,国防化学作为化学讨论会重要主题,受到了普遍重视。“鉴于国防情形之迫切,暨军事教育方面之需要,爰约国内对此问题夙有特殊研究之专家担任编译”,国立编译馆开始编译国防化学书籍中“近今允称标准著作之外籍”([8],弁言)。讨论会后,国防化学著作在国内开始大量出版。曾昭抡、吴屏的译著《化学战争通论》是其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
二 《化学战争通论》的作者与底本
《化学战争通论》的底本书名为《化学战》(Der Chemische Krieg),该书用德语写成,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化学战的标准书”([8],页Ⅷ—Ⅸ)。《化学战争通论》“译者序”后附有“原文第二版序”,落款为“柏林,1927年春。韩斯联”,同时该著作中收录有大量1924—1927年间的化学武器最新成果,因此笔者判断该译著的底本为1927年的第2版《化学战》(图1,初版于1925年在柏林出版)。
底本作者韩斯联(Rudolf Hanslian,1883—1954)现译名为“汉斯利安”。,出生于德国,先后在埃尔朗根(Erlangen)大学和莱比锡(Leipzig)大学学习化学,并在恩斯特·贝克曼(Ernst Beckmann)恩斯特·贝克曼(Ernst Beckmann,1853—1923),德国著名化学家。他于1878年获得莱比锡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890年被利奥波迪纳和萨克森科学院录取,1892年成为埃尔朗根大学全职教授,并担任国家食品研究所所长,1897年他回到莱比锡大学任应用化学实验室教授兼主任。1912年,前往柏林担任新成立的凯撒·威廉化学研究所首位主任,并當选为普鲁士科学院正式会员。他的名字广泛出现在化学领域,如有机化学中的Beckmann重排,Beckmann温度计等。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于1910年获得博士学位。韩斯联于1912年在哈勒(Halle)大学生理学院任埃米尔·阿布德哈尔登(Emil Abderhalden)埃米尔·阿布德哈尔登(Emil Abderhalden,1877—1950),瑞士生理化学家,蛋白质生物化学的创立者。他于1902年获巴尔塞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8年起先后任柏林兽医大学生理学教授,哈勒(Halle)大学教授。1932—1950年任利奥波迪纳科学院(Leopoldina)第20任院长。1945年二战结束后回到祖国瑞士,任苏黎世大学生理化学教授。教授的助教。一战时韩斯联先后担任近卫军团药剂官和药剂监,即第22预备军团之毒瓦斯专员。1919年任政府药剂师及军医训练所附设之化学检验室主任。自德国国防部成立后,任国防军军团卫生材料第一厂化学检验室主任。一战后不久韩斯联任德国气体技术代表,并被选为“国际防御化学战保护平民专家委员会”(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expert Pour la Protection des Populations Civiles Contre la Guerre Chimique)会员。在布鲁塞尔和罗马的国际会议上,任德国政府代表,并担任红十字会民众气体防护国际专门委员会之顾问([8],页Ⅷ—Ⅸ)。
韩斯联“对于军队的及民众的气体防护之著作,极为丰富,为世界上最有名之化学战专家,其最著名之著作,即‘化学战即Der Chemische Krieg。一书,此书系根据其丰富的战场经验而成”([8],页Ⅷ—Ⅸ)。此外,他还担任《气体防护与防空》(Gas-und Luftschutz)杂志主笔,并为火药及爆炸物杂志之气体防护部专门顾问。1932年德国红十字会会长特颁给韩斯联该会名誉奖章,“以酬谢其为红十字会组织及建设气体卫生与气体防护之功绩”([8],页Ⅷ—Ⅸ)。
《化学战》于1925年在德国出版后,于1927、1937、1948年数次再版,同时被翻译成英语[11]、日语[12]等多种语言译介至国外,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化学战》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国化学武器与防护装备的发展;第二部分韩斯联主要对一战后各国化学武器和防护装备的发展作了介绍;第三部分对化学战争中烟和雾产生的原理、化学物质和辅助工具作了介绍。该书在广度和深度上较国内以往相关著作都更为丰富——从作者自身的丰富战场经验出发,以化学战争的国际视野,按照一战前和一战后的时间顺序对主要参战国在军用化学物质、化学武器、攻击技术、防护装备、防护战术等方面进行了说明和比较,同时对各种武器、装备的优劣都进行说明,为国内的化学战争的准备提供了众多参考。
尤为重要的是,在第二章中,韩斯联讨论了当时人们热议的两个尖锐的问题——“化学武器自道德上及国际公法上的立场之理论的评价”和“化学武器在将来战争中之预料的地位”。这两个问题,一个面对“过去”,需要对这一全新的战争兵器作一公允评价;另一个问题面向“未来”,需要回答化学武器将何去何从,未来在战场上将如何发展。
作为一名化学武器的研究者和支持者,韩斯联在化学武器是否人道这一问题上,认为“一种兵器是否合乎人道,并不能以盲从的言论判断,而仅能以事实证明” ([8],页336)。更明确地说,“应以该种兵器所产生的痛苦,致伤后的影响,及受伤人中死亡及永久残废的成分为标准而评价也”([8],页336)。通过对各国军队因毒气和传统兵器伤亡人数和比例的对比,他认为化学武器在战争中造成的伤亡率都远低于传统兵器,同时可以较快地让敌方丧失战斗力,因此是一种相对人道的武器。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国内在化学武器人道与否这一问题上多持肯定态度,如“除毒气及他种化学战品外,天下未有再合人道之战具”[13]。一方面,国内逐渐认识到化学武器造成的伤亡率远不如传统兵器高。另一方面,以枪炮炸弹为代表的传统兵器“不中则已,中者重则死亡,轻则毁肢断体,不可救药,吾人毫无节制之余地”[14],化学武器“出奇致胜,减少损伤,无乖人道,较为优越耳”[15]。韩斯联的观点与当时国内的主流观点相呼应,成为《化学战争通论》在国内编译与出版的有力推动。韩斯联结合《凡尔赛和约》《华盛顿协定》《日内瓦公约》等一战前后涉及化学武器国际条约的签订过程,在探讨了各国的态度以及实际做法后,认为战争中化学武器的应用是大势所趋,“对于化学军用物质的应用之反对,自科学上及历史上之眼光观之,终久不能保持也”([8],页351)。
对于化学武器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他认为,化学武器是新的事物,各国对于化學武器的研究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就目前各国对于化学武器的使用情况而言,化学武器尚不能成为“主要的及基本的兵器”。他批判了报纸上夸大的不实言论,认为实际效果上看“气体炸弹”的威力远不如普通的爆裂弹巨大。同时,在战场上“气体之伤害及致死之功效,可以气体防护法抵制之”,因此就实际情况而言,“为一种效力极弱及偶尔有效的兵器”([8],页470—471),在海军中,化学武器更是只能“视作一种次要的兵器”([8],页482)。
同时,韩斯联“极力劝告民众注意化学战之危险,但同时警告民众对于化学战毋庸作夸大之宣传”([8],页Ⅸ)。他重申了“全民武装”(Volk in Waffen)的观点——“在将来人民及军队为不能分开之意念。整个国家之道德的力量,如军纪,爱国心,及胜利的志愿,不顾一切技术上之成就,将仍为成功之首要条件”([8],页484)。最后,韩斯联写下这样一段话:
战争之原则,迄今尚不以气体兵器之引用而变更,惟其实行的可能性,则因之而扩大。进一步言之,成功的基础,仍在能以突然的于适当时机,在有关紧要的地点,以优势的兵力对付敌人。第二原则,仍为无积极的动作者不能得到成功;消极抵抗,从不能致胜。对于成功之不易条件,仍为优越的指挥,军队的攻击精神及其对兵器使用之训练,与在可能范围内以最大的速度移动军队及物料;其他一切之战法,均不过是项定律之变形而已。([8],页485)
这一论断对于指导国内化学战争的防御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为消除国内弥漫的对于化学武器的恐慌情绪,稳固民心,号召国内民众科学备战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
韩斯联的这部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末已受到中国军界的关注。1929年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军官团编译的《新兵器化学:毒瓦斯及烟》一书附录中,列有23种“化学武器之参考书目”,最后一种即为《化学战》。1932年出版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专刊》中,“军政部兵工署理化研究所”条目中特别介绍了该所在国防化学方面收藏的39种“特别图书”,该著作也位列其中。20世纪30年代国内出版的国防化学著作在撰写时几乎都参考了此书,如1932年吴屏著《国难中民众对于化学战应有之认识》、1933年吴沆著《化学战争》、1933年孙豫寿著《化学战争概论》、1939年沈星五著《化学战争》等,由此可见该著作在当时国内的学术地位举足轻重。当时国内国立山东大学[16]、国立武汉大学[17]、国立四川大学[18]等高校均将其作为国防化学相关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
与同时期国内其他国防化学著作相比,《化学战》有以下三个特点,特点之一是内容详尽,论述科学。该著作是当时国内内容最详尽的国防化学著作,正文篇幅长达381页,同时还附有记载欧洲战场上各种化学武器、装备实物以及化学武器运用实际效果的图片78幅。“书中关于化学战争之历史,其所用之材料与此项物质之物理化学及其生理上之性质,叙述甚详。”([19],页47)以芥子气为例,芥子气(Mustard Gas)化学名称为2,2-二氯二乙硫醚(Dichlorodiethyl Sulfide),属糜烂性毒剂代表,由于其具有挥发性且持久性强,对人体伤害巨大,因此在当时被称作是“毒气之王”[20]。一战后国内外各类国防化学著作中都对这一毒气作了大量介绍。以当时国内三部代表性的国防化学著作中对于芥子气的介绍作一简要比较——孙豫寿《化学战争概论》中对于芥子气的介绍相对较为简略,主要停留在定性介绍上。吴沆《化学战争》中对于芥子气的介绍较为丰富,已经开始涉及定量研究,主要侧重于芥子气的生产工艺与身体表面的毒气防护,着重介绍了美国研制的不同溶剂的防毒药膏对芥子气防御效果的研究,但这一防御方法为韩斯联所诟病韩斯联认为,各交战国对于芥子气的防御问题“均未能得一完满的解决”,而防毒膏“经证明之结果,乃系一种可怀疑的防护工具”,最好的防御方法还是避免接触。([8],页434)。Der Chemische Krieg中对于芥子气的介绍最系统、丰富,在第一章中,韩斯联几乎搜罗了当时各国对于芥子气及其防御的最新研究成果,并附以图表加以说明。在第二章中,他介绍了美国最新研究的针对前线士兵衣物的“防护浸渍法”,但也指出“战场经验尚属缺乏”,然后介绍了当时三种相对有效的去毒方法——高压水蒸气去毒法、硫化蓖麻油-碳酸氢钠混合液去毒法和“沐浴车”去毒法。同时,对于平民的毒气防御工作韩斯联也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
该书特点之二是应用性广,实操性强,和国内之前的著作相比,《化学战》“于化学武器之战术上之应用,尤予以特别注意”([19],页47)。韩斯联多次参与战场上和民众的气体防御工作,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因此在书中记载了多国对于战场毒气攻击和防御的经验,并提供了大量的参数和图表,同时引经据典,结合众多战场报告,对欧洲战场上许多实际案例从科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例如在毒气防御方面,韩斯联重点介绍了对于毒气的各种防御装备和方法。他将个人防护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认为“妥当的防护,只有用个人的防护设备,方能保障之”([8],页234)。《化学战》图文并茂,收录了各国在化学战争中所使用的气体攻击与防御装备。以“个人防护法”中“防护面具或过滤式气体防护器具”为例,韩斯联首先介绍了防护面具的防护原理和分类,然后分别讨论了德、法、英、俄、美以及其他交战国所使用的防护面具,对其样式、类型、构造、适用条件和当时各国的产量都作了详细研究,还研究了不同类型防护面具之间的关系和异同,为国内的毒气防御研究工作提供了有用的参考。因此,该著作堪称是一部从战场中提炼出的“化学战争宝典”。
该著作的特点之三是多方引证,学术价值高。《化学战》在当时被曾昭抡和吴屏认为是“世界上化学战的标准书”([8],页Ⅸ)。该书不同于之前国内出版的国防化学著作,以往国内相关著作往往是作者通过对国外译著的学习或个人经验整理编写而成,主观性较强。即使附有参考文献,其不足之处一是参考文献数量较少,二是书中的观点、例证等均未注明出处,倘若作者对其翻译或理解出现讹误,或是书中某些材料过时,国内读者都无从查证,从而不利于国内科学工作者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
韩斯联写作《化学战》时参考了当时大量的国防化学相关资料,在该书最后“参考材料表册”中列出的参考文献多达251种,按照时间先后排序,时间跨度从1914至1926年。该书严格按照学术著作的格式撰写,引证充分,“一切讨论均以真实为贵”([8],页Ⅵ),书末还附有长达45页的英文索引。在书中凡是提到前文中论述的观点或事物时,均注明在前文中出现的页码。“书中所引之事实,曾经复行极端慎重的搜查参考材料以证实之,并曾追究其来源而载明之,用此法首可对第一次说出相关之思想,及首先将其材料公之于大众者,予以相当之应得的名誉(Ehrenpflieht),但同时亦可使追踪或有之错误,有其可能性。”([8],页Ⅵ)
此外,韩斯联在书中大量引用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的观点,哈伯是犹太裔德国化学家,1918年因合成氨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在一战期间他因开发部署氯气及其他毒气的化学武器而出名,被称作“化学武器之父”。因此,该书不仅有着较高的学术性,同时也为当时国内有志于从事国防化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大量学术参考。
三 《化学战争通论》的译者与译本
《化学战争通论》(图2)的译者之一是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曾昭抡,字隽奇,号书伟,1899年生,湖南湘乡人。先后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化工和化学专业,1926年获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先后任广州兵工试验厂技师,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后又兼任化学系主任[21]。他曾在中央大学主持国防化学课程,该课程是“中国现代高校首次开设的相对完善的国防化学课程”([22],页81)。因其长期从事毒气化学相关研究,1927年任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毒气化学专业筹备员。1931年他受聘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化学战争通论》出版前,著译有《炸药制备实验法》《有机物质分类反应及鉴定实验》(与侯家骕合译)等。曾昭抡还长期担任国立编译馆的学术著作审校人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為出版高质量的化学译著出力颇多”([21],页150—15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昭抡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22]。
该书另一位译者是国立北平大学教授吴屏。吴屏,字伯藩,1903年生,湖北广济人。先后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福郎夫克大学与基耳大学,专攻酿造化学和油脂工业,获理学博士学位,并担任过启耳大学农学院与卫生学院助教,以及启耳市卫生局化学师。1929年吴屏回国后先后担任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23],北京大学讲师[24]。他于1932年前后赴北平大学任教在1930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大学校况简表》和1932年《国立北平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一年度)》关于农化系教职员的记载中均未找到吴屏任教的记载。,时任国立北平大学农业化学系教授[25]。著有《国难中民众对于化学战应有之认识》《液体燃料与西北之关系》《中国液体燃料之代替问题》等。此外,他受陕西省政府之邀,任该省顾问,代为设计陕西化学试验所和陕西酒精厂并兼任厂长,成绩卓著[26]。1937年2月23日吴屏受李宗仁之邀,由广州前往桂林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广东三水不幸溺水身亡[24]。
此外,该书的出版得到国立编译馆陈可忠、北平大学医学院徐益甫据1932、1934、1936年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编辑《国立北平大学一览》记载:徐佐夏,字益甫,山东广饶人,先后毕业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德国柏林大学,曾任山东省立医专教员。1932年起任国立北平大学农业生物系讲师,1936年任农业生物学系与医学院合聘教授。等人的支持与帮助。军政部兵工署理化研究所所长吴钦烈据《国防部公报》(1946年第1卷第5期,第45页)载,吴钦烈,字景直,浙江诸暨人。191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科学习,之后从事无烟火药与苦味酸的生产制造工作。1918年一战结束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化学并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吴钦烈在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化学工程科主持工作,之后多次赴欧考察。1929年军政部兵工署成立后先后任兵工研究委员会专门委员,理化研究所所长,技术司司长。1937年任理化学兵工厂厂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兵工厂内迁,1938年任兵工二十三厂厂长兼任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抗战结束后任国防部第六厅副厅长。和军政部兵工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张郁岚校阅了该书。吴、张二人均有留德背景,长期从事国防化学领域相关研究[27],他们的校阅有助于保障该书翻译质量。该著作较国内其他著作有以下特点:
一是忠实原著,语言流畅。《化学战争通论》是国立编译馆在全面抗战前编译的73部学术专著中唯一一部国防化学理论书籍,同时也是其中唯一的军事学书籍([19],页37—54)。曾昭抡、吴屏在翻译该著作时忠实于原著,基本按照原文的章节进行翻译。全书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为“世界大战前之化学武器”,分为“气体攻击”和“气体防护”两部分。第二章为“大战后之化学武器”,除了对一战后各国化学武器的发展作了介绍外,还讨论了对于化学武器的评价和对其在未来战争中地位的预测。第三章为“烟及雾之产生”,主要论述了战争中各种烟雾的产生、应用和辅助技术。曾昭抡、吴屏在翻译该著作时,基本采用白话文的语言风格,只有虚词和句式仍保留了一定的文言色彩。译本对于专有名词的翻译,采用在译文后面标注原文的方式呈现,使读者一目了然。
二是译名规范,注解清晰。1932年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之后,教育部于同年11月颁布了《化学命名原则》,并于次年6月出版[28]。受此影响,曾昭抡、吴屏在翻译该书时尤其注意对专有名词的翻译。“为免误会起见,在本书中不惮烦琐,常在译名后注以原文以参对照。所注之原文,如系军事上名词,多即用原书中之德文字。如系化学上名词,则多改注英文字,以目前国内读化学者,对于英文名词,较对德文名词熟习也。”([8],页Ⅲ—Ⅳ)《化学战争通论》较同时期其他相关著作中对于军用化学物质的命名更加科学,更加接近现代化学规范的命名方式。一方面,曾昭抡、吴屏对之前相关著作中命名不规范的一些军用化学物质名称进行了修订。绝大部分军用化学物质都属于有机物,结构相对复杂。旧的命名方式往往不能很好地体现其结构特点,对于同分异构体有时还会出现歧义。另一方面,曾昭抡、吴屏对一些之前采用俗名表示的物质名称进行规范命名,基本按照《化学命名原则》中的命名规范。如第一章“气体攻击所用之军用化学物质”中所提到的Cl3CNO2这一物质为例,以往著作中将其称为“氯化卑格林”[29]或“氯苦味质”([30],页45)。曾昭抡、吴屏在翻译时特地在该物质后面特别注明——“译者按,在西文书籍中,寻常多称此物为Chloropicrin,但在本书译文中,则即用硝基三氯甲烷一名,取其一目而知其结构也”([8],页68)。
四 《化学战争通论》的影响与局限
《化学战争通论》与国立编译馆之前出版的《炸药制备实验法》(曾昭抡著)、《毒气制备实验法》(Dr. Hugo Stoltzenberg著,张郁岚译)底本为Darstellungsvorschriften für Ultragifte。、《烟幕发火剂及爆炸实验》(韩组康著)同属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之后,国立编译馆首批确定编译出版的国防化学著作。《化学战争通论》与另外三部相比,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理论性最强。同时由于涉及大量的专有名词和术语——既涵盖化学方面,也包括军事方面,因此该著作编译难度也最大。编译工作历时三年,《化学战争通论》于1935年7月由国立编译馆正式出版。《化学战争通论》出版后不到一年,于1936年5月再版。这四部国防化学专著中,另外三部相继在1934年出版,均侧重于实验操作。《化学战争通论》最后出版,是其中唯一一部国防化学方面的理论专著,凸显其重要的学术价值。1933年国立北京大学便将其列为化学系选修课军事化学课程的两种参考书之一,当时该著作尚未正式出版,因此特别注明了“在印刷中”[31]。
该著作的翻译出版,对于学界开展国防化学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对于国外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让国内科学工作者可以直接阅读国外经典著作,进而快速开展研究和教学工作,省去了语言转换这一繁琐的步骤,有利于国防化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进而促进国内国防化学学科的发展。同时,该著作的翻译出版也有助于国民政府的国防化学建设,国防化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可以在军队中普及国防化学知识,让化学战争的“欧洲经验”迅速传递到国内政界和军界,进而完成对于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化学战争的安排和部署。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更多的科学工作者从事国防化学研究,服务于国防建设。
不可否认的是,该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其一是书中内容虽然详尽,但由于战争催生新的国防化学相关研究成果突飞猛进,该书在国外和国内出版时间已相隔八年,书中部分材料已经过时。其二是书中虽然介绍了多国在化学战争中使用的武器、装备以及采用的战术,但许多战场实际经验却不适宜中国,所提供的“大都限于欧战的经验与事实”[32]。“以我们的特殊环境,以及未来抗敌战斗的特殊情形为对象的化学战争论著,还很稀少。”[32]国内的国防化学著作迫切地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一步本土化,因此,如上文中所述,在《化学战争通论》问世之后,国内涌现了一大批更适合中国实际情形的国防化学著作,该书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五 结语
《化学战争通论》是民国时期国内引入的最重要的国防化学著作之一,也是全面抗战前国防化学知识在国内引入的一个缩影。以该著作为代表,当時国内国防化学著作大量出版,是国防化学知识引入与传播的一个主要渠道。该著作的出版是当时国际和国内政治环境,国内政界与学界共同参与配合,以及高水平译者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全面抗战爆发的20余年间,国内诞生了众多国防化学著作。《化学战争通论》因其底本重要的学术价值,译本高质量的翻译而在当时国内独树一帜。底本作者韩斯联在书中介绍了大量自身对化学武器的深入研究,以及丰富的欧洲战场经验,他对于战争中支持使用化学武器的观点,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但在当时却于国内对于化学武器的主流看法相吻合。他在该书中的诸如号召“全民武装”、理性看待化学武器、战争的成败决定因素是人而非先进的武器等观点,恰好与当时国内官方对民众的战时宣传不谋而合,同时响应了国内科学界对于化学武器的认识寻求理性的呼声。这或许也是国立编译馆选择首先编译该著作的原因之一。《化学战争通论》的出版工作是经由当时中国官方渠道进行的一项科学传播活动——国立编译馆及其隶属的教育部主导,国内相关科学工作者主持并参与,同时也反映了曾昭抡、吴屏在国防化学传入中国这一工作中起到关键作用。他们结合自身的学术经历,在工作中付出巨大的努力,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完成了《化学战争通论》的翻译工作。该著作内容详实、系统论述、翻译流畅,在当时国内国防化学著作中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对之后相关著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化学战争通论》编译的三年正处于民国时期“德国影响中国的十年”([33],页3),德国是当时世界上的军事强国,中国在军事方面与德国积极寻求合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各军事机关聘用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并以德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方法训练军队。当时许多人将德国视为“中国发展某些特定方面的模式或良师益友”([33],中文版序言),但国内习德文者相对较少。国立编译馆首批编译的四部国防化学专著中,《化学战争通论》与《毒气制备实验法》的底本均来自德国。同时,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著作内容——即大量以德国为中心的化学战争经验的介绍,以及译者和校阅成员的学术、职业背景中以俞大维、杨继曾为代表的留德科技精英,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纷纷加入军政部兵工署,对中国军事科技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中就包括《化学战争通论》的两位校阅者——吴钦烈与张郁岚。此外,吴屏、徐佐夏也具有德国留学背景。,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当时中国政界和学界在军事方面“以德为师”的价值取向。
从更深的层次看,《化学战争通论》的翻译出版体现了政治与科学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国际和国内政治环境是国立编译馆主导该书翻译出版的重要动力,国立编译馆的官方权威地位无疑对该书出版后相关著作产生重要影响也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该书的出版又促进了国防化学知识在国民政府政界和社会的传播和普及,并为国民政府国防化学建设做出贡献,起到了反哺政治的作用。这种良性的互动反映出在“倭寇猖獗,国祸日亟”([3],序一)的背景下全面抗战前国防化学知识在中国的引入与政治的密切关联,背后倾注着国内学界和政界为引入和传播国防化学知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付出的努力,值得后人回味。
致谢 本文在导师郭金海研究员指导下完成,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宝贵的修订建议,在此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1]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军官团. 新兵器化学: 毒瓦斯及烟[M]. 南京: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军官团, 1929.
[2] 张郁岚. 化学武器教程[M].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内部刊行, 1934. 1.
[3] 吴屏. 国难中民众对于化学战应有之认识[M]. 北京: 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 1932.
[4] 靳宗岳. 近代化学国防之重要[J]. 复兴月刊, 1933, 1(12): 1—20.
[5] 徐名材. 毒气战术[J]. 科学, 1919, 4(9): 818—827.
[6] 世界将来两大战争[N]. 中央日报, 1929-6-9: 7.
[7] 吳沆. 化学战争[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8] R. Hanslian. 化学战争通论[M]. 曾昭抡, 吴屏译. 上海: 国立编译馆, 1935.
[9] 景瑚. 毒气威力之估价[J]. 国立浙江大学日刊, 1937,(232): 932.
[10] 国立编译馆. 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专刊[M]. 上海: 国立编译馆, 1932.
[11] Rudolf Hanslian. Chemical Warfare: extracts[M]. Washington, D.C.: Army War College, 1934.
[12] ルードルフ·ハンズリアン. 化学战. 第六陆军技术研究所[R]. 东京: 第六陆军技术研究所高等官集会所, 1943.
[13] 郭庆禄. 化学国防概论(续)[J]. 同泽半月刊, 1931, 4(11, 12): 53—57.
[14] 靳宗岳. 近代化学国防之重要[J]. 复兴月刊, 1933, 1(12): 1—20.
[15] 赫尔登演讲、吴沆译述. 毒气战之人道观[J]. 兵工杂志, 1932, 4(7): 147—154.
[16] 国立山东大学出版课. 国立山东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四年度)[M]. 青岛: 国立山东大学, 1935. 136.
[17] 国立武汉大学. 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年度)[M]. 武汉: 国立武汉大学, 1936. 109—110.
[18] 国立四川大学. 国立四川大学一览[M]. 成都: 国立四川大学, 1936. 109.
[19] 国立编译馆. 国立编译馆一览[M]. 南京: 国立编译馆, 1937.
[20] 吉良济. 毒气之王——芥子气[J]. 科学的中国, 1936, 7(11): 389—392.
[21] 李新, 孙思白, 朱信泉, 等.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八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4802—4807.
[22] 戴美政. 曾昭抡评传[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23] 国立武汉大学. 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十九年度)[M]. 武汉: 国立武汉大学, 1931. 229.
[24] 吴启中、曾昭抡. 工业化学家吴屏堕机陨命[J]. 时事月报, 1937, 16(4): 23—24.
[25] 国立北平大学. 国立北平大学教职员录[M]. 北京: 国立北平大学, 1934. 12.
[26] 雨. 吴伯藩之生平[N]. 北洋画报, 1937-3-16: 1.
[27] 麦劲生. 留德科技精英、兵工署和南京政府的军事现代化[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3(2): 100—107.
[28] 国立编译馆. 化学命名原则[M]. 上海: 国立编译馆, 1933.
[29] 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司. 化学兵器学要览[M]. 南京: 军医公报社, 1931.
[30] 孙豫寿. 化学战争概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31] 国立北京大学. 国立北京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年度)[M]. 北京: 国立北京大学, 1933. 126.
[32] 葛春霖. 化学战争与中国国防[M]. 上海: 新知书店, 1937. 著者自序.
[33] 柯伟林著, 陈谦平、陈红民等译. 德国与中华民国[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The Introduction of Defense Chemistry Knowledge before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ith the case of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Der Chemische Krieg
ZHU Hao
Abstract:The General Theory of Chemical War, co-translated by Zeng Zhaolun and Wu Ping, is the only theoretical work on military science and defense chemistry compiled by the Nation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Center before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The base is the second edition of Der Chemische Krieg, a famous German chemist and military scientist Rudolf Hanslians famous work, published in 1927. The compilation of The General Theory of Chemical War was led by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scientists, which reflecte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aking Germany as the teacher” in the field of defense chemistry in China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that time.The book is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work, fluent in language, standard in translation and clear in annotation, and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domestic defense chemistry books after publication.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is a typical case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chemistry knowledge in China before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which reflects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science.
Keywords:The defense of chemical, General Theory of Chemical Warfare, Nation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Center, science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