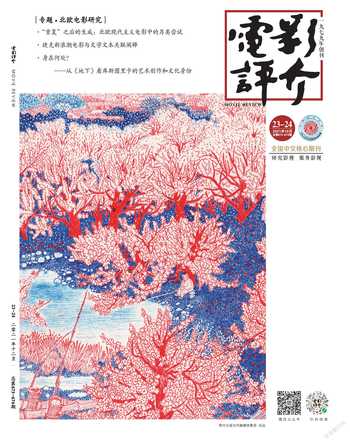日本庶民现实主义电影历史进展研究
日本电影发展史上庶民电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描写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山本喜久男在对20世纪30年代的日美欧电影进行比较时指出,这一时期日本正在完成着以小市民影片为中心的日本电影的特征——“庶民电影”。[1]日本庶民电影往往反映日本中下层人民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情感矛盾;电影结构松散,节奏缓慢,接近日常生活的流动性体验,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在考察日本庶民现实主义电影的时候,可以把小津安二郎、山田洋次、是枝裕和放在一个脉络之中。从时间上看,三位导演的年龄彼此相差30岁左右,他们创作的时代轨迹几乎贯穿20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日本社会,他们的影片反映了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家庭的发展历程,从战后初期日本传统家庭制度的瓦解,到经济高速发展后期小家庭的合理化,再到泡沫经济破灭后偶和家庭的出现。他们的代表性影片都将目光投射到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通过描写日本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家庭功能的变化或受损,产生的诸多问题与深远影响,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同时也表现出对于重建人们之间的情感纽带,修复家庭功能等问题的思考。
一、小津安二郎家庭片中的现实主义
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影评人路易斯·贾内梯认为:“日本电影最多的类型是庶民剧,也是小津惟一做的类型,”“这类电影处理日常家居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点点滴滴宛如自我否定的苦药,最终总将生活指向遗憾。”[2]在无声电影时代,当小津安二郎还是青年的时候,他已经走上了描写小市民生活的现实主义道路。[3]小津通过对正在瓦解的日本传统家庭的描写,表现了对转型家庭中出现问题的思考,也流露了依恋传统家庭形态的保守主义倾向。
(一)小津安二郎影片中的转型家庭
日本从明治维新后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个体小家庭逐渐脱离家制度而独立。尤其是经过战后民主改革,家庭制度趋于崩溃,个体家庭获得了法律上的独立地位。[4]战后家庭改革的动向具有两方面的性质,一是重新构建合理的家庭关系,二是以利己主义为前提的私人家庭关系的构成。由于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发展的需要,重构的小家庭造成传统家庭制度中家长和子女生活的隔离,同时以资本主义利己主义的个人契约为基础构成的家庭关系造成传统家制度中家长和子女精神的疏离。小津安二郎经由日本古典审美趣味所要表达的乃是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日渐兴盛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之流弊的深深隐忧。[5]
小津的早期作品大多通过喜剧的形式表现日本现实社会中的悲剧问题,这集中反映在其“但”字系列作品中。1932年执导的《我出生了,但……》隐含了日本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比如父子关系、等级制度、维护个人尊严的理想与屈从等级制度的无奈等等,被评价为是确立了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6]。之后,小津在电影中集中反映了传统家制度的崩溃以及父权的消逝。拍摄于战前的《户田家兄妹》(1941年)描写了在一家之主的父亲户田进太郎病逝后,家族的凝聚力随着父亲的猝死而逐渐瓦解的故事。如果说小津在这时对于父权瓦解的描述还是隐晦的、有条件的,即父亲的亡故是导致家族瓦解的背景,那么在战后拍摄的《东京物语》(1953年)中则更加凸显地、无条件地描写了父权的消逝以及随着孩子的成长,亲子关系的疏离导致家族制度的崩溃。
对于亲子关系,小津持有悲观态度,小津是带着一种极度的自尊和一种非常克制的悲观情绪在做电影。[7]小津想要通过子女的成长独立来描述日渐显露的亲人之间的嫌恶感。无论是《户田家兄妹》还是《东京物语》,都描述了成家立业、构成新家庭之后的子女與父母之间的疏离与嫌隙,而只有尚未形成独立家庭的子女才保有传统的孝道。例如,《户田家兄妹》中的次子昌次郎和小女儿节子,《东京物语》中的小女儿京子。在《东京物语》中小津甚至通过身为他人、成为遗孀的儿媳纪子对公婆的体贴照顾来探求解决传统家制度崩溃后带来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等问题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关怀。同时,小津通过小女儿京子道出了拯救家庭危机、亲子危机的前提,即需要所有家庭成员的自觉和努力。
(二)小津安二郎影片基于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
日本当代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史学家佐藤忠男指出:“作为小市民电影的大师,小津在日本电影中创造了自己的写实主义,但也喜欢轻松和无厘头的喜剧。战后,小津继续精心描绘因为战争丧失的旧日本的人情和日常生活礼仪,始终如一地成为最好的保守派。”[8]无论是《户田家兄妹》中的昌次郎,还是《东京物语》中的京子,都是小津为了体现传统家制度中的人情和日常生活礼仪而设定的角色。《户田家兄妹》中赴中国天津工作的次子昌次郎在父亲周年忌日时回到日本,发现母亲和妹妹因为哥哥姐姐的嫌弃无法同住,只能住在废弃的老宅里,于是在严正批评了哥哥姐姐们的行为之后,说服母亲和妹妹和自己一起远赴天津定居。《东京物语》中儿媳纪子向公司请了一天假,带公婆周吉夫妇游览东京。招待他们到自己的公寓后,向隔壁房间借来酒款待他们。从热海回来后没了住处的周吉老伴儿富子再次来访时,纪子发自内心地高兴,在床上给富子揉肩膀,第二天早上还关怀备至地给她零花钱。小津通过儿媳纪子,描述的是与周吉夫妇子女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来自他人的关怀和诚意。这可以说是小津在思考战后家庭形态变化过程中所拥有的新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不局限于血缘关系的发自内心的爱和关怀的力量,是维系逐渐崩溃的家庭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小津通过电影唤起潜藏在人们心中的切实的不安和愿望。
不同于《东京物语》与《户田家兄妹》的故事背景设定为东京,小津将《晚春》(1949年)、《麦秋》(1951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离开东京的北镰仓,描述了不同于高速工业化的大都市的人情冷漠,在历史文化小城中流淌着的脉脉温情。《晚春》中小津通过描写女儿纪子过分依恋父亲不愿出嫁,想要树立牢固而又温柔的父性权威,这种父性权威其实是传统家庭即将崩溃而给小津带来深深的危机感的一种过激反应。[9]同时,小津通过父亲周吉和姑姑真纱的对话反映出父辈不得不接受由于时代发展,子女表现出与传统背离的无奈。在《麦秋》中小津同样表现出对战后的现代与传统、女性自由的焦虑。纪子宁愿嫁给丧偶带着三岁女儿的哥哥的同事,也不愿嫁给上司介绍的身世良好、具有留洋背景的中年未婚男子。小津借纪子反映出对传统事物的依恋以及对现代事物的抵触,正如纪子所说:“以前乱纷纷地都忘了他,经这么一提,才发现最可靠的是他啊。”小津安二郎终其一生执着于描写家庭关系,亲情关系和寂寥的晚年故事。在小津的电影里,体现了对于日本传统文明,特别是即将过往的传统文化观念的一种深刻眷恋。[10]
二、山田洋次家庭片中的现实主义
佐藤忠男认为继承肯定性地描写庶民人情的传统并予以集大成的是山田洋次。[11]家庭片是山田洋次的代表作系列之一,无论是早期拍摄的家族三部曲《家族》(1970年)、《故乡》(1972年)、《同胞》(1975年),还是近年来拍摄的《家族之苦》(2016-2018年)系列电影,山田洋次的影片所表现的已不再是小津安二郎影片中那种封闭家庭内部的亲子、夫妻之情,而是社会变化给家庭带来的撞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家庭内部关系的感情波澜。[12]山田洋次习惯用一种带有幽默诙谐的方式表现人们之间的温情,呈现出憧憬理想家庭形态的理想主义倾向。
(一)山田洋次影片中的理想家庭
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完成了近代向现代的转变。同时,这也意味着现代家庭的完成和大众化。山田洋次70年代拍摄的家族三部曲描绘了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后,年轻一代为了理想或迫于生计不得不离开原住地,迁移到新的地方进行打拼,追逐梦想的故事。《家族》描写了为了帮助丈夫精一实现成为奶农的梦想,妻子民子说服爷爷源藏带着两个孩子举家从故乡长崎县移居到北海道开拓牧场的故事。虽然小女儿和爷爷在途中和到达北海道之后相继离世,但村民的热情和关心让精一一家重新燃起了生活下去的希望。两年后,山田洋次的《故乡》用不同的场景和视角,再次关注了同样的问题,描写了在濑户内海的仓桥岛上,靠用船搬运石头为生、过着简单生活的精一夫妇,因为旧运石船出现问题,为了追寻更光明的前景和新天地,不得不离开深爱的故乡的故事。《同胞》则以岩手县松尾村实际发生的故事为原型,描写了为了实现东京剧团在乡下的音乐剧公演而奋斗的村里青年团的活动。《家族》《故乡》《同胞》虽然故事内容不同,但都折射出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出现的必然趋势即城乡流动的社会问题。不同于小津安二郎对于传统的依恋,山田洋次在不同于固化为既有秩序的战后家庭的意义上,积极探索新的“家庭”关系。
自2016年至2018年山田洋次连续推出了《家族之苦》系列,都描写了三代同堂的温馨家庭,但也折射出了当代日本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第一部讲述了退休后的平田周造在即将迎来金婚之际,遭遇一向温顺的妻子的离婚请求,最后意识到妻子多年来为自己的付出与不易,获得了妻子的谅解的故事。影片反映了近年来日本社会的“熟年离婚”现象。第二部讲述了周造与高中老同学畅饮后带丸田回家留宿,第二天一早发现丸田在家中去世,一家人为孤寡无依的丸田温情送葬的故事。影片折射了日本無缘社会现象及老人孤独死的问题。第三部讲述了整日操劳的家庭主妇史枝因为家中失窃遭到丈夫幸之助的抱怨与不理解,愤而离家出走,幸之助在大家的批评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史枝和好如初的故事。影片反映了现代日本社会中依然保持传统分工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女性劳动被漠视的问题。三部影片虽然都集中反映了日本社会的某些问题,但最后都在温情中得到了化解,勾勒出其乐融融的理想家庭形态。
2013年山田洋次拍摄的《东京家族》翻拍自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但表现了与小津不一样的山田风格。如果说《东京物语》表现的是传统家制度崩溃后新建小家庭的分崩离析与亲子关系的疏离,那么《东京家族》呈现的则是即使在小家庭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家人聚在一起时还是充满温情。比如,滋子在厨房帮大嫂文子准备晚饭的情景,昌次和侄子们以及外甥女的融洽关系。而对于忙于个人事务,无暇顾及父母的子女,山田也给出了合理的理由。比如,身为医生的长子是因为患者突发紧急病情,在女儿女婿家时因为雨天不便外出,所以儿女们都无法陪同父母游玩。山田想要表现的除了家人之间的亲情之外,还有温馨的邻里之情。周吉夫妇到东京当天,邻居小雪便打来电话询问是否平安到达。富子丧事之后,只留下周吉一人在乡下,小雪一早便来周吉家里拿换洗的脏衣服,并带周吉家的小狗去散步。通过这样的设定,治愈了人们心中对于独处乡下的周吉未来生活的隐忧。
(二)山田洋次影片基于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
山田洋次的电影总想挖掘隐藏于人内心的善意,从而让人们理解那些不近人情的不得已。70年代拍摄的《家族》《故乡》《同胞》,虽然反映了家庭内部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但并没有停留至此,电影呈现的是只要有奋斗的方向,亲情的疏离也能在欢笑一堂中消融的理想景致。近年来拍摄的《家族之苦》虽然反映了在看似幸福和睦的家庭中也会出现各种让人啼笑皆非的矛盾与问题,但最后总能在家人的努力下圆满解决。即使是翻拍自小津安二郎《东京物语》的《东京家族》,也没有让人感到压抑和克制,而是感受到亲人之间、邻里之间的温情。山田认为艺术家存在的价值是“痛苦的时候会说些搞笑的话让人们开心。”[13]山田说:“对于创作者来说,对自己生活的社会现实的认识有多深刻、多准确,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表面上人们笑着开玩笑,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很多痛苦的事情,而这些痛苦究竟是怎样的,必须彻底理解。要努力正确认识那种痛苦、讨厌和残忍的心情。”[14]也就是说山田想要表现的“现实”并不是充斥在表象的残酷现实,而是被忽视了的隐藏在人们内心的观众想要邂逅的温情“现实”。
《家族》中当6月的晚春来临,牧场从寒冷的雪景变成了美丽的新绿,影片在一种快乐的心情中结束。关于这个结局,有人批评说大团圆的结尾是太无视现实的过于乐观的态度。对此,山田却说:“当雪变成了一片绿色,在一个暖洋洋的好天气里,人们发自内心的高兴,有人开了个有趣的玩笑,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觉得应该也有这样的瞬间,正因为有了它,人们才能活下去。倒不如说完全没有这种情景的生活才是不现实的。”[15]因此,在面对日本的家庭人伦方面,山田更愿意展示温情的一面,即便是因为社会的变化而带来了一些矛盾危机,最终都能有一个较为平和的解决方式。[16]
三、是枝裕和家庭片中的现实主义
是枝裕和被称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他的很多影片都不同程度地关注传统家庭的发展变化,关注儿童的现实生活,关注无缘社会问题等等,使得他相关影片的社会批判性思考及人文情怀显得特别有深度[17],成为本世纪以来日本庶民现实主义电影最为杰出的代表。是枝裕和的影片将自我和社会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偶合的、非常态的家族折射出深刻的社会问题。
(一)是枝裕和影片中的非常态家庭
与山田洋次《家族之苦》中近乎完整的家庭人员关系不同,是枝裕和的家庭关系总是带有缺憾的,甚至是病态的。与小津安二郎想要唤醒人们“血浓于水”的亲情观不同,是枝裕和在作品中以“比血浓的东西”来发现和提示家人的关系。超越“血缘”,由共同度过的时间和新的决断构成的“家庭”,描绘出处于现代社会诸多深刻问题中的家庭可能存在的方式。是枝裕和电影有三个反复呈现的主题:底层关注与人文关怀、父权的缺失与找寻、家庭的解构与重组。[18]《无人知晓》和《小偷家族》中通过病态的家族形态,表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直面的真实现状,即男人抛弃女人,女人抛弃孩子,老无所依,幼无所养的社会现状。《海街日记》和《比海更深》中呈现的是父权缺失的不完整的家庭形态以及不经意间找寻到一直存在的父爱。《海街日记》中三姐妹在参加完父亲的葬礼后返回途中收到同父异母的铃送来的父亲一直珍藏的她们小时候的照片,以及当看到父亲常带铃去的地方与她们生活的镰仓景致非常相似时,才感知父亲从未忘记她们,从而化解了对父亲的怨恨。《比海更深》中良多在变卖去世父亲留下的砚台时从典当铺老板那里得知父亲生前一直以自己为傲,这份从未发现的父爱让他重拾对梦想、对生活的希望。正如《比海更深》的片尾曲所诠释的那样,父爱从未缺失,只是我们未能发现:“就算当我自己都无法相信自己的时候,你是唯一一个相信我的人。”《步履不停》和《如父如子》中呈现了解构与重组后的家庭形态。是枝裕和坦言《步履不停》这部家庭情节剧让他“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终于萌生了一丝自信。”[19]换句话说,是枝裕和在思考原生家庭的解构与重组过程中确立了属于自己的叙事风格,之后拍摄的《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小偷家族》等家庭题材影片自成体系并深入人心。
(二)是枝裕和影片基于激进主义的现实主义
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个人精神危机以及引发的家庭危机,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这种危机既具有日本现代社会的独特性,也有着全球现代社会的普遍性。[20]随着养老、教育甚至日常的饮食、陪护等家庭功能不断被“外部化”,导致家庭功能的弱化甚至丧失。[21]是枝裕和通过描写病态的、非常规的、社会底层的家庭情况,试图以家庭单元来反映社会结构运转的失衡,深刻披露当个人精神危机导致家庭功能弱化甚至丧失之后,社会又不能很好地发挥补充家庭功能的作用时,导致的家庭解体与社会不安。
是枝裕和通过《无人知晓》中缺失父母的家庭,《如父如子》中抱错孩子的家庭,《小偷家族》中各有问题的社会边缘人物临时重组的家庭,表现出对日本现代社会和家庭中存在问题进行的深入冷峻的思考,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意味和社会反思色彩。虽然是枝裕和在影片中并未明显表述对社会怀有的不满以及对现存社会制度抱有的否定态度,但通过影片构筑的孤儿家族、小偷家族尝试探索家庭的新型变体,这种新型变体反映了对传统伦理僭越的现代城市“陌生人伦理”的诞生,这种尝试也表现了是枝急切希望社会现状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愿望。
结语
综上可知,从20世纪30年代确立了庶民现实主义的小津安二郎,到被称为“日本国民导演”的山田洋次,再到被称为“小津安二郎接班人”的是枝裕和,家庭生活题材一直是他们主要关注的对象,也是推动日本电影在世界影坛获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法宝。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体现了明显的“日本式”风格,这种风格起初不被外国人理解,但同时小津也被冠以“最具日本特色”的导演。山田洋次的电影由于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发达之后,无论是影片场景还是人物设定都具有现代化氛围,因此更容易与国际接轨。是枝裕和的电影反映了泡沫经济破灭之后,人们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诸多问题,影片将现代社會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老龄化问题、儿童问题等统统表现出来,这些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于世界其他国家,因此,是枝裕和电影的庶民现实主义更具普适性,这也是其在世界各大电影奖项中备受青睐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日]山本喜久男.日美欧比较电影史 外国电影对日本电影的影响[M].郭二民,等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624.
[2][美]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M].焦雄屏,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354.
[3][日]岩崎昶.日本电影史[M].钟理,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256.
[4]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2.
[5]卢迎伏.秩序与风度:论《东京物语》中小津安二郎的现代性隐忧[ J ].文艺争鸣,2016(12):123-129.
[6][日]佐藤忠男.日本电影史·上[M].应雄,主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398.
[7][10]郭小橹.一种影像:关于小津,关于侯孝贤[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9(3):33-38.
[8][日]佐藤忠男.日本映画の巨匠たち①[M].東京:学陽書房,1996:303.
[9]豆耀君.论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家庭伦理观[ J ].电影评介,2011(4):7-9.
[11][日]佐藤忠男.日本电影史·下[M].应雄,主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25.
[12]俞虹.平民视角育出了常青摇钱树——记维护电影大众路线的日本导演山田洋次[ J ].当代电影,1996(6):8.
[13][日]香川智之.山田洋次の映画づくりから学ぶ(上)[ J ].文学と教育,1996(172):52-55.
[14][日]香川智之.山田洋次の映画づくりから学ぶ(下)[ J ].文学と教育,1996(174):44-49.
[15][日]山田洋次.映画をつくる[M].東京:大月書店,1978:90-92.
[16]张容.山田洋次影像中的家族情结[ J ].大众文艺,2018(2):158-159.
[17]任萍.是枝裕和电影新现实主义特征及美学创新[ J ].未来传播,2021,28(5):113-119.
[18]金俊建,严红彦.“作者电影”理论视域下的是枝裕和电影主题分析[ J ].视听,2021(2):104-105.
[19][日]是枝裕和.再次从这里开始[M].匡匡,译.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9:349.
[20]李秀萍.日本治愈系电影类型特征初探[ J ].电影文学,2019(16):24-26.
[21]李素杰.是枝裕和家庭电影中的社会批判[ J ].电影文学,2020(21):7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