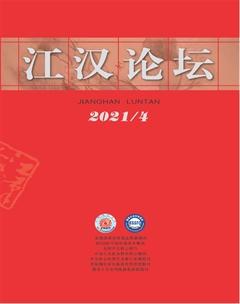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的政策体系设计



摘要:国家兴衰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完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又必须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集中体现为党和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能力,而国家发展战略要通过科学有效的政策体系方能实现,因此要加强各级决策者的战略谋划和政策体系设计能力。政策体系由若干政策或政策单元有机构成,包括链式政策体系与复式政策体系两种类型,在典型的链式政策体系设计中,设计的关键是决策者能基于事物的发展变化对关键时间节点作出正确判断与选择,并适时推出相应的政策或政策单元。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谋划能力与政策体系设计能力,充分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具备高超的国家治理能力。
关键词:国家治理能力;政策体系;税费改革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4-0028-09
一、為何要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理解公共政策设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小罗伯特·E·卢卡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秘密和机制曾深表感叹:“不同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大得令人无法相信……一旦人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①。确实,发现并解释国家兴衰的内在奥秘一直是中外许多杰出思想家的执着追求。在对国家兴衰探秘解谜的人类思想之旅中,主要形成了科学技术、发展环境、国家制度三种解释视角。基于科学技术视角的思想家倾向于从国家的科技实力与科技创新能力去寻找答案,保罗·肯尼迪的“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蒸汽动力及其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大大增强了一些国家的力量”之观点,表明他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②;基于发展环境视角的思想家侧重于从国家所处国际发展环境及应对能力去寻求答案,以“挑战—应战”模式去解释文明起源、成长、衰落、解体的阿诺德·汤因比堪称发展环境论的主要开创者③,而以“中心—边缘”框架去解释不发达现象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④和以多斯·桑托斯、费尔南多·卡多佐为代表的依附学派则是发展环境论的集大成者⑤;基于国家制度视角的思想家把目光聚焦于国家制度体系并试图从中寻找解决谜团的锁匙,比如道格拉斯·诺斯等从经济制度创新的角度(产权制度)解释了西方世界为什么兴起⑥,德隆·阿西莫格鲁等则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两个维度,基于对制度包容性或攫取性的判断与分析来说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⑦。
在上述三种解释视角中,基于制度视角形成的学术流派更为复杂多元,其研究方法更为科学严谨,研究解释更为深入充分,学术影响也更为深远持久,乃至于制度变量似乎已然成为可以解释和说明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不过,制度视角却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制度是问题的终极原因和答案,那么是否意味着,拥有相同或近似制度的国家,都会有大体相似的国家兴衰历程与命运?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同样采取资本主义制度的英国和美国,前者是江河日下,而后者却后来居上,而曾经同样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和中国,前者已成历史遗迹,后者却正蒸蒸日上。显然,对于这个深层的重大理论问题,制度学派未能加以深究并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毫无疑问,制度是重要的,制度问题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国家制度是国家最根本的“基础设施”。然而,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国家制度优势能否转化成治理效能,却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相辅相成。缺乏有效的治理能力和制度执行力,再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也难以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且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事实表明,无论是在理论探索上还是在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间内在关系,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以及对于国家兴衰奥秘的认识达到的理论高度,超越了以往任何制度学派和国外一切政党。至少中国案例充分说明,提高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方面因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才是实现国家兴盛的终极决定因素。要解释国家长盛不衰的内在奥秘,既要立足于国家制度体系,又要立足于国家治理能力;要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完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又必须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⑧。显而易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最集中体现。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要“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⑨
国家战略能力由战略设计能力和战略实施能力构成。众所周知,国家发展战略只是初步构想和设定了国家在某一较长时期的战略发展方向、战略目标以及相关制度框架。要最终实现国家的战略构想和战略设计意图,离不开国家的战略实施能力。国家发展战略构想和战略设计意图需要通过政策体系去贯彻落实,只有通过政策体系的科学设计、逐步完善与有效实施,方能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因此,政策体系设计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主要表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应该更加强调和突出决策者的战略谋划和政策体系设计能力,各级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要站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建设和提升各级党委和政府谋划和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科学设计与实施政策体系的政策能力。
二、公共政策研究存在何种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
令人遗憾的是,以往的公共政策研究,无论是政策过程研究、政策能力研究还是政策链研究,都没能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去审视政策体系的科学设计,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
第一,政策过程研究的理论缺陷。过程分析法是一种常见的发现事物发展规律的方法。作为公共政策分析与研究中历史最久、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研究者与政策分析师都倾向于以时间为轴,依据公共政策从创议到终结的整个线性流程去建构理论分析框架,把完整的政策过程依序划分为前后相继的若干阶段或环节,并沿着政策过程中的问题或聚焦于某个政策环节进行研究。政策过程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哈罗德·D·拉斯韦尔⑩、加里·D·布鲁尔{11}、查尔斯·琼斯{12}和詹姆斯·E·安德森{13}等人,他们的基本观点大同小异,比如拉斯韦尔将政策过程划分为情报、提议、规定、合法化、应用、终止、评估七个阶段,布鲁尔将其老师拉斯韦尔的七个阶段修正为创始、预评、选择、执行、评估、终止六个阶段,等等。
可以看出,政策过程研究止步于把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解析为不同时序上的若干政策环节或阶段,既没能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宽广视野与理论高度去追踪和审视某一政策连续实施、不断加码或者修正完善的多样态过程的原因、机制、动力与方式,也没能集中关注政策内容本身的时序特征与发展变化。另外,又恰恰因为缺乏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谋划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视野,现有政策过程研究只注重单项政策安排的过程建构与政策分析,既缺乏对政策体系的过程建构及政策形态的深度分析,又没能从政策体系的高度来审视单项政策。总之,鉴于上述两个缺陷,基于传统政策过程框架的政策分析,由于脱离了政策体系框架,所以无法从政策体系的视角去逐一审视政策过程的每一环节以及政策体系中的单项政策,因而也就无法更为有效地进行政策修正与完善,不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第二,政策能力研究的理论缺陷。提升政府的政策能力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一个并不精确的学术概念,对于什么是政策能力学界并无共识性的严格定义。比如,鲍静基于改进政策制定系统的学术思想,提出了提高政策问题诊断能力、改进政策议程安排、创新政策方案等提升公共危机中政策制定能力的合理政策建议{14},由此可见她认为政策制定能力是政策能力的核心要素;李玲玲则基于政策过程的视角,认为“公共政策过程各个阶段的能力的综合就是政策能力的全部内容,政策能力是公共政策的规制、引导、调控和分配能力的综合”{15};钱正荣认为,政策能力是通过资源配置作出符合公共目的的明智的集体选择的能力{16};盖伊·皮特斯则把政府在程序意义上将公众意愿转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和实质意义上的决策质量合称为政府作出决策的能力,并将其等同于政府的政策能力{17};迈克尔·豪利特则更为极端,他宽泛地把政府在政策相关知识的习得及应用、政策框架的搭建、政策定性及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政策管理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对利益相关者的协调等诸多方面的能力统统纳入政策能力的范畴{18}。
戴维·L·韦默等指出:“政策研究应该关注反映社会问题的变量和那些能够被公共政策改变的变量之间的关系。”{19} 而从上述定义可以明显看出,中外学者对政策能力的理解、界定和研究,无不立足于公共政策本身的层面与范围,都没能跳出公共政策本身的框框与束缚,没能基于公共政策最不应该忽视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政策背景,没能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没能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谋划、设计与实施视角,去理解和审视政府的每项公共政策、每个政策体系及其政策能力,因而自然难免导致具体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要么在政策定位与方向上发生偏差,要么在政策理解上不够深刻与精准到位,从而影响到政策质量与治理效能。盖伊·皮特斯、迈克尔·豪利特等人虽然概括了第三波政策设计研究中形成的五种模式(路径依赖模式、政策复制扩散模式、事实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制定模式、行动者中心的设计模式、严重棘手问题的直接应对模式){20},并详细论述了混合政策工具的使用问题,但也只是停留在政策工具(或政策混合)层次,而没能站在政策体系的更高层次去关注公共政策问题,并理解政策体系中的政策与政策体系的设计{21}。
第三,政策链研究的理论缺陷。在本文中,笔者把政策链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现状的观测点与述评对象之一,是因为作为一种以特殊组合方式存在的政策形态,政策链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理应享有一定的研究地位。然而与其应有地位不相称的是,国内政策链研究既不充分,也乏善可陈。
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公共政策研究中最早涉及政策链问题的是宁骚教授。他指出:“政策链,是指国家、政府和一定类型的政治体制中的执政党为解决同一政策问题而先后制定的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在形态和功能上具有差别性的一系列政策。同一系列的政策相互衔接、相互补充,但其中一二项政策在形态上更具完整性,在内容和功能上更具全面性与系统性,起着统摄全系列的政策的作用,从而使得同一系列的政策环环相扣,如同一个链条。”{22} 客观而论,这一定义还算到位。不过美中不足,他没有结合具体政策案例进行实证研究。
而从中国知网刊出的论文情况看来,在整个公共政策领域,竟然没有一篇专门从学理上对这种特殊政策形态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论文。以“政策链”为题名进行检索,也只能检索到其他学科领域涉及政策链问题的屈指可数的几篇实证研究论文。而从對推动公共政策发展的理论贡献和学术价值来看,即使是这样几篇略微涉及政策链的其他领域的论文,对政策链问题也只是点到即止,而没有对这种特殊政策形态进行理论分析与总结,就更别说是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谋划实施角度去进行研究了。比如在《“负成本”低碳转型及其政策链构建》一文中,作者通篇都在论述如何基于负成本来选择实现低碳转型的政策工具,丝毫没有对政策链进行学理分析的任何意图与内容{23};又如在《面向中国汽车产业的政策链研究》一文中,作者虽然把政策链界定为“由多项相互影响、互为关联的政策组成,涉及政府、企业、消费者多个行为主体,宏观、中观和微观多个层面的错综复杂的系统”,并将它粗略划分为横向政策链与纵向政策链两种类型,但作为一种以特殊方式组合而成的政策形态,政策链的要素结构是什么以及要素间有何内在关系等,作者却并未进行学理分析{24}。更重要的是,上述两篇论文恰恰由于没有基于国家发展战略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分析相关政策链,因此对于分别涉及的低碳经济转型问题和汽车产业问题,在给予政策建议时也就大大束缚了作者的政策视野,而没能分别从国家生态战略与国家产业战略高度,在政策体系层面上提供更具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的政策建议。
总之,通过对公共政策研究三个理论观测点的扫描与梳理,可以看出:现有公共政策研究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即未能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从谋划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政策体系的层面上去全面审视、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每项公共政策和政策体系的制定与实施。而为了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共政策学界需要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在政策体系的层面上更加精准深入地进行公共政策研究。
三、如何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谋划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设计政策体系
阿马蒂亚·森曾经指出,经济学有两个根源:其中一个,即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中有关伦理观念的联系,为经济学规定了不能逃避的任务;另外一个,即经济学与工程学方法的联系,人类的目标在这里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宜手段。{25}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学科的目标是为一国乃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工程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那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谋划与实施则是为这一经济社会工程提供政策施工方案。政策工程学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目标治理方法。社会工程和经济工程等在结构上具有复杂性与系统性,在目标设定上具有层次性和整体性。M·克兰兹伯格指出:“技术都是配‘套而来的,但这个‘套有大有小。”{26} 如果将政策看作实现社会、经济工程和进行国家治理的技术,那么政策也具有配“套”而来的特点,各种政策或政策单元组合匹配、相互衔接。这就要求实现目标的政策方案具有体系性、整体性和连贯性,要求决策者站在政策体系的层面去谋划政策方案,因为仅凭单项政策往往难竟全功。
说明:a为由不同时间节点同一政策A构成的持续政策链;b为由不同时间节点不同政策A、B、C、D构成的依序链式政策体系;c为由不同时间节点同一政策单元ABC构成的持续链式政策体系;d为由不同时间节点不同政策单元ABC、DEF、GHI、JKL构成的依序链式政策体系;e为由同一时间节点不同政策A、B、C、D组成的复式政策体系。
政策体系由若干政策(如图1a、图1b、图1e)或若干政策单元(如图1c、图1d)组成,但并非它们的简单叠加和随意拼凑,而应是政策或政策单元之间的有机组合。政策单元由若干政策构成,它们也并非各项政策的简单叠加。政策、政策单元与政策体系是处于三种不同层次的政策形态,它们共同组成政策结构体系。在政策体系内,各项政策与政策单元既自成一体、各有分工,又相互衔接、整体协同,它们的目标是协同实现政策体系的总体治理目标,而各单项政策目标则共同服务于政策单元目标,这样又形成了由政策目标、政策单元目标和政策体系目标三个不同层次构成的政策目标体系。
政策体系会呈现多种形态。在时间形态上,组成政策体系的各项政策既可以同期存在(如图1e),又可具有明显的时间序列特征,并依序先后呈现(如图1a、图1b、图1c、图1d)。从政策组合方式上区分,既包括链式政策体系(如图1a、图1b、图1c、图1d),又包括复式政策体系(如图1e)。
在政策制定尤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谋划制定中,至为重要的是执政党与各级决策者能对问题性质进行精准研判,并对相关发展战略和政略及时作出科学调整。比如,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分别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等重大国情以及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的“两个趋向”等问题,及时作出了精准研判、科学论断与政策体系的战略性调整。链式政策体系就是一种基于对根本问题的性质和事物发展变化情况的科学研判、精准把握而对战略政略相应作出重大调整的政策体系设计模式。
链式政策体系是指决策者为了实现某一治理目标,在不同时间节点依序安排的一系列政策(如图1a、图1b)或政策单元(如图1c、图1d)组成的政策链条,它具有明显的逻辑性、系统性、步骤性、阶段性、层次性、调适性和时间上的纵贯性。组成政策链的要素一是时间节点,二是与时间节点匹配的政策或政策单元。政策链这一概念始创于列宁。在1921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把新经济政策看作“历史事迹发展的链条”,而把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或指导下发展商业看作这个链条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列宁要求,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必须注意研究整个链条“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联,它们之间的区别”。{27} 由此看来,链式政策体系设计成功的关键是决策者对不同时间节点作出正确判断与选择,并及时推出相应的政策或政策单元。而要对时间节点作出正确判断与选择,就需要决策者基于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和实际演化过程,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敏锐洞察、及时发现事物的量变和质变、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转换,把握时机,因势利导,及时精准研判和界定政策问题,确立相应的行动目标和任务,出台相关的政策或政策单元。因此,最终看来,时机的判断与把握是链式政策体系能否实现治理目标的关键。所以,在链式政策体系中,各政策与政策单元之间虽然具有一定互补性,但更多情况下呈现的是一种依序进行、步步深入、层层推进的政策衔接关系。
链式政策体系要能一以贯之,实现政策初心与治理总体目标,需要执政党执政理念、政策理念与政策伦理的持续稳定的指引、匡正和助推。只有通过决策者对执政理念、政策理念和政策伦理的长期贯彻坚持,才能时时校正政策偏差,始终沿着最初设定的战略方向和治理总体目标努力下去。
复式政策体系是指决策者为了实现某一治理目标在同一时间节点沿不同方向一次性推出且互相支撑匹配的若干政策组成的政策体系。与链式政策体系显著的线性关系特征不同,复式政策体系的各项政策之间是一种同步关系,具有明显的横向匹配性与协同性(如图1e)。
从决策模式来看,虽然一些决策者可能在政策设计之初就已(粗略地或精细地)通盘、系统谋划好了不同时间节点与不同发展阶段的因应之策,但更多情况下,因为受制于有限的信息基础,决策者无法提前预设或预判问题并进行通盘谋划,而只能根据问题解决进展和目标实现情况,随着事物情况的变化选择后续的政策组合方式,不断调整和修正政策。因此,链式政策体系设计者更多情况下使用渐进决策模式。反之,复式政策体系则采用一次决策成型模式,它對决策者提出了更高的前瞻能力要求,同时也更加仰赖全面精准的信息基础,因而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政策体系。
因此,在国家治理与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各级决策者需要基于不同的政策情境,选择最为合适的政策体系形态。但不管选择哪种政策体系,以及决策模式如何,都要求政策体系具有较高的体系性与完备性。
四、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中的政策体系设计
农村税费改革特指由党中央主动发起并于2000年开始正式启动的一场以根治农村乱收费、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实现城乡税制统一为主要内容的调整国家和农民分配关系的重大制度变革。这场改革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思路由农业养育工业与城乡二元管理向工业反哺农业与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转变,又实际“推动了农村政权组织、财政体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等一系列的深刻改变”{28}。
毫无疑问,这场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战略能力。对于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经指出:“现在回过头来看,农村税费改革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改革的第一位的目标,把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作为基本出发点;始终坚持加强对农村税费改革的领导,中央把握改革的大方向、大原则,依靠地方和基层,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始终坚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兼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和对改革的承受能力,确保农村税费改革顺利平稳地推进。”{29}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现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也曾总结出了税费改革的四条成功经验:一是把保障农民各项权益放在突出位置;二是必须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整体合力;三是把搞好顶层设计和鼓励地方先行先试结合起来;四是把减轻农民负担和各项配套改革结合起来。{30} 显然,上述分析从实践经验层面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然而,对于关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学者而言,如何从国家治理能力与政策设计角度来解释这场触及多方重大利益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奥秘,以及在政策实践中应该如何进行政策体系设计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才是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在此,笔者尝试从政策体系设计角度作出新的解释。
自1980年代末,农村乱收费问题日趋严重,既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又成为影响党的执政基础与社会稳定的重要现实问题。显然,农村乱收费问题决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问题。虽然早在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曾发布《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在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再度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并进行过数次专项治理,但因为专项治理存在缺乏制度配套与制度延伸的重大缺陷{31},乱收费的机制和动力没能消除,所以成效甚微。为了从根源上彻底消除农民承担不合理税负的制度性缺陷,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逐步改革税费制度,加快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立法”这一农村税费改革战略蓝图。{32} 同时,国务院成立由财政部、农业部和中农办三个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2004年调增为七人小组,并设立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开始着手研究和制定新的改革方案,为减轻农民负担由治乱减负向税费改革作准备。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两点:一是税制问题;二是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方面的问题。{33} 因此,为了寻求治本之策,党中央、国务院即于2000年开始税费改革试点,并正式拉开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序幕。
改革先后经历了正税清费、减免取消农业税、配套改革三个阶段。改革虽然涉及各方利益,但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改革之所以成功,根本上在于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国家发展战略高度,通盘谋划,精准施策。如果从公共政策设计的理论高度来总结改革的成功经验,那么从中可以获得的一条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要基于国家战略的谋劃与实施高度,科学设计政策体系。由于此次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因此作为改革举措的政策体系属于典型的链式政策体系类型。
具体而言,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体系的三个阶段及其政策单元和辅助政策如图2所示:
第一阶段:减轻、规范、稳定的正税清费阶段。A:三项取消——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和各种专门面向农民的集资摊派及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B:两项调整——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C:一项改革——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第二阶段:减征、免征农业税到彻底取消农业税阶段。D:降低农业税税率;E:试点免征农业税;F:彻底取消农业税。
第三阶段:为从制度上巩固税费改革成果而稳妥推进的配套改革阶段。G: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进行乡镇机构改革;H:以落实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重点,进行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I:以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为重点,进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辅助政策K:2001、2002、2003、2006、2012年,中办、国办多次专门发布关于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在2004、2005年,中办、国办都发布了上一年度《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的情况通报》,因此也可纳入同一辅助性政策K的范畴。
如前所述,科学设计链式政策体系的关键在于,在政策过程中,决策者能够基于事物情况的发展变化,对时间节点及其根本问题作出精准研判,从而适时推出最合理的政策单元,并通过若干阶段性政策单元目标的实现,最终实现政策体系的总体战略目标。
非常明显的是,在此次改革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从一开始就对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早在2000年3月2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就初步规定并要求试点实施在2006年才开始大规模攻坚实施的配套改革阶段的政策单元。2001年2月27日,温家宝更是明确指出:“这次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配套改革能否到位。乡镇政府机构、乡镇财政体制、农村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仅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延伸和扩展,而且是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必须坚持同步实施,整体推进。”{34} 由此可见,党中央、国务院在税费改革甫行之初,就已全盘谋划、顶层设计、深谋远虑、成竹在胸。
此外,在改革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还基于对税费改革情况的整体把握和所处阶段的清醒认识,全力推进改革目标向前迈进,及时作出政策调整并精准推出主干性的政策单元,因而又具有明显的渐进决策特征。如在2000年、2001年、2002年的国务院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并无减免农业税的相关内容,而在2003年3月27日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中,已首次出现适用于特殊情况和特殊地域的“农业税减免制度”的提法;在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了中央确立的“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政策目标与步骤{35};在2004年7月2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做好2004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正式提出“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在2005年7月1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更是发展为“2005年要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因此,以2003和2004年为重要分界点,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与政策单元发生了根本性的阶段性变化。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党中央、国务院在农村税费改革战略实施过程中于2003年开始着手调整并逐渐调高政策体系的总体目标呢?那是因为自2001年开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首次下降至15%以下,而农业各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总体上呈现逐渐下降趋势。(见表1)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基本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对工农、城乡关系进行重新调整的时机和条件已基本成熟”{36}。2004年9月19日,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37}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为中央开始大幅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改善工农城乡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因此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党中央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对事物情况变化及其发展规律有了全面精准把握,在前4年“按照‘减轻、规范、稳定的目标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已基本到位”和“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效”的前提下{38},把握时机,精准施策,在2004年这一时间节点正确适时地把农村税费改革推向下一个目标更高的阶段。
而当全国已有27个省区市决定全部免征农业税,另外4个省区中的多数市县也免除了农业税,全国行将从2006年1月1日始正式取消农业税时,温家宝又指出:从2006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将进入新的阶段,重点是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推进综合改革的阶段,是农村税费改革更重要、更艰难的阶段。”{39} 这充分说明,在税费改革前两阶段即将大功告成之际,党中央、国务院就因势利导,马不停蹄,立即开始部署和全面实施早已试点过的配套性综合改革,将政策过程推向下一个阶段。
在改革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运用了多种政策途径,一方面自始至终坚持采用政策试点不断推广的实施手段,另一方面还以图1a中的持续政策链方式,长期坚持制定和实施减轻农民负担、制止乱收费的辅助性政策K。
可以看出,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综合采取了图1a、图1c、图1d这三种政策模式,坚持顶层设计与渐进决策相结合,为实现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治理总体目标,建构并形成了一个结构完整、功能协调、相互补充、组织严密的政策体系。
前已述及,在链式政策体系尤其是改革性政策体系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要确保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为实现政策初心与目标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做到始终坚定不移,离不开执政党执政理念和决策者政策理念的引导、匡正、推动和保障。惟其如此,才能时时校正政策偏差,确保各阶段的政策单元朝著既定方向和总体治理目标深入贯彻下去。政治伦理、执政理念内在于政策伦理之中。R·M·克朗指出:“价值规定着政治进程和管理过程,并且是资源分配指导原则的核心”{40}。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切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是“谁,以及什么最为重要”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必须在其他一切具体问题之前首先搞清楚。回顾长达12年的农村税费改革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疾苦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摆在谋划国家发展战略和作出决策时最重要、最优先的位置。正因为如此,才能在涉及多方利益的漫长改革过程中,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而2019年9月1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把农民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作为制定党的农村政策的依据”,这更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最生动写照,也是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和水平的根本。
总之,在税费改革中党中央对关键时间节点的精准把握,对多种政策手段与政策模式的系统运用,以及始终坚定不移地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政策理念,正是其国家战略谋划能力与政策体系设计能力的充分体现。而2018年1月,党中央基于“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这一科学判断,适时提出了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41},又一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超的国家战略谋划能力和政策体系设计能力。
五、结语
O·C·麦克斯怀特指出:“在公共行政中,真正鼓舞人心的事是,使政府权威变成人类目标的推动者”{42}。人类的发展离不开各国一项项国家发展战略的科学制定与有效实施,需要强大的国家战略谋划与实施能力作保障。没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战略谋划实施能力,无论是国家的繁荣富强还是人类的文明进步,都只能是痴人说梦。而现有公共政策研究正是由于没能跳出公共政策本身的框框,导致无论是在政策过程研究还是政策能力研究中,都局囿并痴迷于单项政策的政策能力与政策过程,而没能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更高层面,去思考和探索更为宏大和复杂多变的政策体系的制定能力与政策过程,去研究国家是如何通过政策体系的科学设计与有效实施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因而也就没能很好地解释与回答如何才能使政府权威变成人类目标的更好推动者这一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制度保障,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依托。为了提升作为国家治理能力集中体现的国家战略谋划与实施能力,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者在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始终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站在国家战略谋划与实施的高度,从政策体系的层面来科学谋划每一项公共政策和每一套政策体系。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事例充分证明,中国的繁荣昌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因为别的,而恰恰是由于我们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党领导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各项部署中,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43},因而在具体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能够始终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从政策体系层面来谋划与实施每一项公共政策,从而不断提升党和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而近期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则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战略谋划和实施能力为核心的高超的国家治理能力以及政策体系设计能力,正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保障和内在奥秘。
注释:
① [美]小罗伯特·E·卢卡斯:《为什么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经济增长演讲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1页。
②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上),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
③ 参见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④ 参见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⑤ 参见 [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⑥ 参见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
⑦ 参见 [美]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技出版社2015年版。
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⑨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17页。
⑩ Harold D. Lasswell, The Decision Process: Seven Categories of Functional Analysis,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Press, 1956.
{11} Garry D. Brewer, The Policy Sciences Emerge: To Nurture and Structure a Discipline, Policy Sciences, 1974, 5(3), pp.239-244.
{12} Charles Jon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3rd ed.,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1984.
{13} James E. Anderson, Public Policy Making: An Introduc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4.
{14} 鮑静:《危机中的政策困境与化解:政策能力的提升》,《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5} 李玲玲:《转型期中国政府政策能力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16} 钱正荣:《政策能力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17} B. Guy Peters, The Policy Capacity of Government, Canadian Centr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Research Paper, No.18, June, 1996.
{18} Michael Howlett, Governance Modes, Policy Regimes, and Operational Plans, Policy Sciences, 2009, 42(1), pp.73-89; Michael Howlett,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as a Policy Tool: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The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9, 3(2), pp.23-37.
{19} [美]戴维·L·韦默、[加]艾丹·R·瓦伊宁:《公共政策分析: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20}{21} B. Guy Peters, Giliberto Capano, Michael Howlett et al. (eds.), Designing for Policy Effectiveness: Defining and Understanding a Concep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8-12, pp.19-23.
{22} 宁骚主编:《公共政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23} 秦艳:《“负成本”低碳转型及其政策链构建》,《生态经济》2012年第5期。
{24} 宋丹妮:《面向中国汽车产业的政策链研究》,《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21期。
{25}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页。
{26} [美]M·克兰兹伯格:《技术与历史:克兰兹伯格定律》,载邱仁宗主编:《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200页。
{2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7—578页。
{28} 郑有贵:《目标与路径: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与实践6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29}{33}{37}{38}{39}{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19、916—917、311、918、922—923、277页。
{30} 韩俊等:《中国农村改革(2002—2012):促进“三农”發展的制度创新》,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108页。
{31} 臧雷振:《国家治理: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2—98页。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3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6页。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33页。
{36} 宋洪远主编:《中国“三农”重要政策执行情况及实施机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40} [美]R·M·克朗:《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页。
{4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6、8页。
{42} [美]O·C·麦克斯怀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中文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页。
作者简介:欧阳景根,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006。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