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昂贵的一句话:这次不一样
郭荆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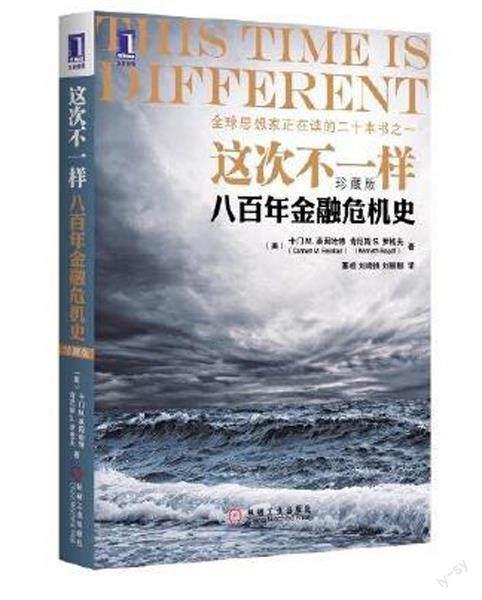
卡门 M· 莱因哈特 肯尼斯 S· 罗格夫/著
泡沫的基础都是solid truth
霍华德·马克斯在他的名著《投资最重要的事》当中讲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观察:每一次金融市场的泡沫,事实上都能找到其背后坚实的基本面,也就是说泡沫的基础都是solid truth。我们可以回想起很多这样的例子:
郁金香美丽而稀有(17世纪,荷兰);
漂亮50都是美国最大最好的公司,有着光明的前景(1968年,美国);
明治维新以来东京地价从未下跌(1990年,日本);互联网将改变世界(1999年,美国);
房地产能够抵御通货膨胀,而且可以永久持有,还可以在银行抵押融资获得现金(2006年,美国)。
越大的泡沫,就有越多的人参与,这也就意味着越多的人有共识,而共识的基础自然更有可能是solid truth,所以霍华德·马克斯会说,非凡表现来自于正确的、非共识性的预测。
那么金融危机开始之前,人们相信“这次不一样”的基础又是什么呢?《这次不一样》的作者概括道:坚实的基本面、结构改革、技术创新、良好的政策。
当这样的信念——相信金融危机已经被消灭的信念滋长,结合如下5项前兆的时候,金融危机也就不远了。
这5项前兆是:资产价格显著上升;实体经济活动减缓;大额经常项目赤字;持续的债务累积;持续性资本流入和金融自由化。一个国家的国内/国际债务、产出和通货膨胀,是判断金融危机即将到来与否的主要指标。
换言之,金融危机是资产价格显著上升带来的乐观情绪和资本流入,使市场参与者忽视了经济体内在的、正在积累的问题,导致现金流无法覆盖越来越高的融资成本,金融市场最终出现突然的大幅调整和崩溃。
最值得警惕的是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在一片光明的前景当中,不断累积债务。
莱因哈特与罗格夫特别指出“债务不耐综合症”的存在。“债务不耐”是指部分国家制度结构和政府体系存在固有的问题,使得政府在面临支出无法被税收覆盖的时候,一次又一次求助外债,最终形成的综合症状。也可以说,“债务不耐”就是想要靠借债来降低税务和支出矛盾压力。政府债务的基础是对政府的信心,因此债务规模扩大、利率上升、信心丧失构成螺旋形恶化的形态,导致政府偿还意愿降低,并最终导致政府违约。
历史数据表明,当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债与GNP的比率超过35%时,发生债务违约的风险就将显著增加。然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无法拒绝新周期的财政政策的诱惑,因为他们会错误地把经济周期和外部环境有利的冲击当做经济结构永久性的变化,以无节制的政府支出和借贷来刺激经济沿着周期的方向无限伸展,最终以悲剧收场。
正如茨威格所说,“命运赠予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
对政府“维护声誉”的错误信仰
除了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的盲目乐观,政府违约导致金融危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对政府会偿还债务的信仰,也就是说投资者相信政府会维护“声誉”。
对金融史和财政史的研究,以及对早期中央银行历史的研究都可以显示,在农业时代,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动力来自于一国在异常的歉收时期可以获得食物,而随着17世纪、18世纪英国国债市场的建立和国债投资者的壮大,英国获得了更为强大的应对突然增加的支出的能力,在与法国漫长的争霸战争中,英王和政府总是能够从国债投资者那里筹集远高于法国农业税收的一次性的收入,这也成为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最终击败法国,建立日不落帝国的重要支柱。
可以说,最初,国债市场的意义在于应对突然增加的一笔支出,为了这样的不时之需,就必须在不时之需出现之前时刻做个好学生。在当代,各国应对战争的准备在弱化,而更加可能需要国际借贷来应对经济衰退和进行高效率的基础设施建设,常规的追求更高效率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外国投资者,经过两百年的发展,政府债务已经变成了常备选项。
我们总是假设,政府很关心自身作为国际借款人的声誉,然而如果政府对国际债券融资市场的需求从应对不时之需变成了常规需求,时刻保持“好孩子”的形象,似乎也就没有英法争夺霸主地位那个时代那么迫切了。
在经济逐渐全球化的时代,除战争时期以外的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的变化都是可控的,尤其是在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经济体的各个参与方都在明确、可信地致力于逐步增加出口以最终完全偿还债务的时候。也就是说,只要看起来想還债,投资者就不用你真的还了。这就是信用和声誉的魅力。
真正的矛盾在于良好的声誉也只能保证债务展期,但不能支撑债务人(政府)越借越多,否则利率上升终究会超过经济增长率,跨过明斯基时刻。
庞氏骗局不能成为国际贷款的基础,因为庞氏骗局终将崩溃。在实际操作当中流行的观点是,能够还清债务的国家也能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贷款,因此现在借给他们是安全的,即使他们面临流动性不足。在国际债务市场上,流动性不足应当等同于偿付能力不足来看待,流动性不足是短期融资有压力,而偿付能力不足则是不愿或不足以偿还,这二者对于政府借贷人来说,其实没有区别。
在这种对“维护声誉”的错误信仰中,政府违约总是会突然地带来金融危机。
观察金融危机的历史,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就是曾经出现违约的政府,总还是能继续借到钱,似乎资本市场对国债违约(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违约)之后的政府,都有着远超借贷企业的容忍度。这与破产企业难以东山再起,欺诈资本市场的企业家遭受长久的唾弃,以及信用记录不良的个人无法获得金融资源相比,显示出诡异的异常。
從政府债务的角度来说,国家会破产,而且会持续不断地破产,这是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带给我们的重要结论:全球各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外债连续违约阶段。然而他们还是借得到钱。他们发现,正如我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在拉美、在欧洲和北美、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上不断观察到的现象,主权债务的偿付几乎完全依赖于各国的还款意愿,而非还款能力,也就是说国家破产和企业破产是两回事,国家破产就是不想还了。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在国际资本市场关闭后,金融危机发生国的国内公共债务将持续增加这一事实,这种异常就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了,既然许多政府的措施都是外面借不到钱就朝国内借,那么为什么当新兴市场国家的居民同样频繁地被“欺骗”时,还会选择将其资金存放于银行或以本币形式持有呢?
既然通货膨胀与债务违约关系密切,特别是在长久的历史中,外债违约和恶性通货膨胀几乎是一回事——也即减少货币的贵金属含量,我们把目光转向通货膨胀时也可以发现,政府有时会使通货膨胀率超过最大化铸币税的通货膨胀率,单纯从基础货币创造铸币税的角度看是不完全的,通货膨胀在面对可能的危机时,是替代债务违约的一种选择。但是在恶性通货膨胀发生时,为什么居民会持有贬值预期中的本币资产呢?
全球通货膨胀有时会发生,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有45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20%,而有时又不发生,比如在21世纪初只有两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20%。来去不定的通货膨胀给国债投资者带来了更大的困扰。
有句话叫做“悲观者正确,乐观者赚钱”,阴晴不定的通货膨胀和无法预知的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增长,似乎更加让理性的投资者无法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难道真的只有相信那些“坚实的事实”吗?
也许我们现在经历的,正是金融史上数得着的让人迷惑的时刻,可以数一数,2018年以来,有什么是让人信服的坚实的事实呢?是新颖的工具可以让美联储既不压垮市场又能循序渐进地退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额刺激,还是低利率对应高PE,还是标普500指数33倍的CAPE可以维持呢?
又或者,是通货膨胀不会发生在老龄化的中国和欧美,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所以让我们尽情的发行国债吧。
当下无可避免,未来早已注定,是这样吗?
现在的美国乃至西方经济和金融市场,真的在美联储的呵护下强健如新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