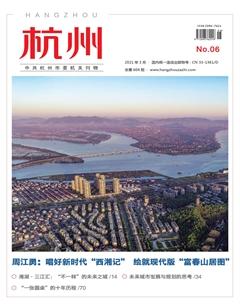未来城市发展与规划的思考
张京祥



什么是未来城市?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未来”是相对于过去、现在的时间概念,“城市”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缩影,深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因而“未来城市”可以理解为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技术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下,面向未来提出的针对性、预测性、理想性的城市发展模式。
从“理想国”到当代实践:未来城市的缘起与发展
回顾历史,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从“周王城”“管子营城”到近现代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古今中外人类对“未来理想城市”的探索从未停止。可以说,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对“未来城市”、理想城市持续追求的历史。具体而言,可将“未来城市”的探索演进历程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19世纪末及以前:理想与艺术导向的空想化阶段。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从城市形态、社会、人性等方面讨论了如何建立理想的国家(城市),对西方“未来城市”的探索影响深远。“希波丹姆斯模式”,《建筑十书》中的“理想城市”,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模型等,均继承了柏拉图等人对理性、秩序的强调。16世纪初以“乌托邦”为代表,西方还出现了将城市建设与社会改良相联系的理想化探索。中国古代对“未来城市”的探求则表现为“周王城”的秩序化范式、“管子营城”的因地制宜范式两类。总之,在农业社会,未来城市的构想多体现在空间形态方面,但受制于制度、经济等条件,这些方案大多呈现出“空想化”的特征而难以施行。
19世纪末-20世纪:化解城市病导向的技术应对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所引致的严峻城市病,人们开始针对具体的城市问题来探讨理想的城市模型,由此出现了“技术理性”导向、“人本主义”导向下的两类探索。技术理性导向源于20世纪初的未来派,他们对科学技术的作用极度乐观,以意大利诗人马里奈蒂的《未来主义宣言》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未来城市”探索开始萌芽、发展,无论是“工业城市”“广亩城市”“光辉城市”,还是“立体城市”“海上城市”“穿梭城市”等等,都表达出人们对通过高技术来解决城市问题的极度憧憬。虽然在这一时期也有“田园城市”“邻里单元”“拼贴城市”等人本主义思想的解决方案,但总体上这段时期西方对未来城市的探索实践是在高技术、现实功利主义驱动下进行的。
20世纪末以来:可持续理念导向的多元探索阶段。20世纪末以来,城市在日益成为人类主要居所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城市病和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成为未来城市探索的核心理念。尤其伴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一代技术革命,人们更加热衷于对未来城市的探索,生态城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云端城市等概念不断涌现,相应的研究和规划实践也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人们从生态、技术、宜居等方面提出了多样化的“未来城市”解决方案,并努力在实践中落实为具体的政策、工程措施和评价指标。但这些方案大多是对城市发展某一方面要素的特别强调,尤其是在实践中常常受技术与资本的主导而偏离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导致难以破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系统性难题。
从技术至上到以人为本:未来城市的内涵重构
纵观“未来城市”发展演进的总體历程,“技术”与“人本”两条主线始终在其中相互交织,前者强调技术的工具理性推动,后者则更多将城市与社会联系起来,体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在认识论层面,如今“未来城市”正在由技术导向逐步回归人本导向,这不仅体现在百余年来无数人文主义大家对高技术指向的纠偏,也体现在一些技术型概念向人本的回归,例如国际上关于智慧城市的讨论正在向技术与人本结合的综合导向演变。然而在实践层面,许多地方普遍陷入了“未来城市”的建设误区,有必要正本清源:一方面,当前很多未来城市实践的高技术指向性仍然十分明显,据统计我国已有上百座在建的智慧城市、生态城市,但这些智慧城市的项目大多是对政府职能和工作流程的技术改造,停留在表层工具手段的信息化,而许多“生态城市”要么成为了标榜“生态”概念的伪生态城市,要么陷入了高技术堆叠的运维危机;另一方面,“未来城市”还成为了资本、技术用于产品营销、攫取利润的时髦概念,近年来一些国际国内的信息科技企业、房地产企业直接攀附“未来城市”之名,而实际上只是单纯地提供某种技术或住房产品——这些所谓的“未来城市”,越发成为了一场由“前沿科技”堆砌起来的技术盛宴和资本盛宴,由此牵引出的规划建设风潮必将是片面的、应景式的,极易将人们引入错误的方向、实践的歧途。
那么如何准确认识“未来城市”?不可否认,突破性的技术变革将对城市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而资本更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动能,但未来城市的涵义远不止于此。我们有必要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未来城市的内涵和基本的发展方向,不能再被技术、资本所挟持,而兴奋地误将动力当成方向、将手段当成目的。回归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实现自然、文化与科技的和谐交融,才应该是贯穿于城市发展脉络之中的真理,才应当成为未来城市的核心内涵并以此引领正确的探索实践方向。
正如近期加拿大多伦多湖滨地区“未来城市”规划中提到的那样,“当我们询问市民对未来城市的畅想时,我们没有听到对飞行器和飞天汽车的渴望,没有听到对摩天大楼的憧憬,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个朴实、人本的愿望:可步行的街道、可负担的高品质居所、人与人的交往远多于人与手机的互动……(未来城市)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可以称之为‘家园的地方”。城市有兴衰,技术的发展更是瞬息万变,唯有自然可以永续,唯有文化可以永恒,唯有可以安放心灵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家园。因此,我们探索“未来城市”的价值不在于追求精准地预知未来,不在于痴迷、追赶各种前沿技术,而核心是以人为本,服务于人类对理想、品质、幸福生活的追求,在于尊重生态规律、城市发展规律,不忘营造美好人居环境的初心和使命。
从超越现在到永续魅力:未来城市的演进方向
“未来城市”如何演化和发展?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如今世界各地对未来城市的探索实践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解决现实的城市病、城市问题,尽管这个依然是我们所关注的,但是对一些新区,当它们还没有城市问题的时候,我们更要将复杂的城市场景当作一个触发未来技术、产业与业态发展的巨大实验室和孵化器,去孕育未来,把握未来,从而有效地增强国家与城市的竞争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于“未来城市”的理解应该是分层级的,存在着认知的升维。这里可以借用“马斯洛需求”金字塔来描绘未来城市演化升级的总体方向,或者称之未来城市演进的“马斯洛模型”:技术的进步和超前只是处于最基础层次的未来城市概念,它让未来城市的活动和景观表征得以某种形式的“超越现在”;位于其上层次的未来城市则是“适应未来”的城市,城市的经济、社会与空间具有应对种种不确定性的能力与弹性,比如常说的“韧性城市”概念;再其上的层次是“迭代更新”的未来城市,这些城市具有持续保持创新活力、社会活力从而不断实现自我完善的能力;而最高层次的则是具有“永续魅力”的未来城市,这样的城市是依托文化、自然与科技的完美结合而迸发出对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持续吸引力,从而实现城市的永续、健康发展。
作者系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