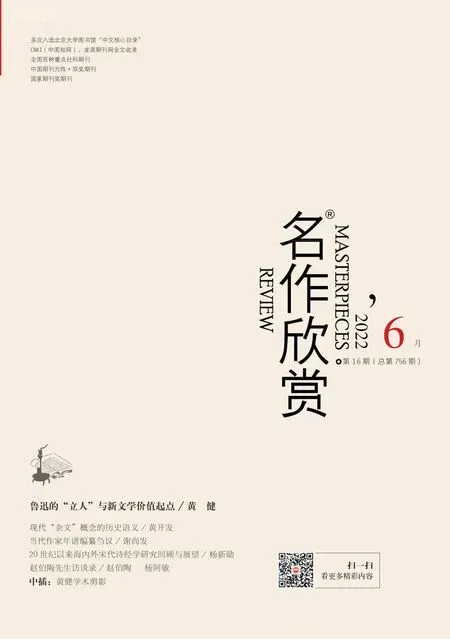“诗圣”的平民情怀
——杜甫《登高》诗与节日民俗
安徽 吴怀东
众所周知,《登高》是代表杜甫近体诗创作最高成就的诗作,明代学者胡应麟就赞美说:“全诗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微有说者,是杜诗,非唐诗耳。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诗擞·内编》)其实,宋代学者最为推崇的唐人七律诗并非如此,严羽就认为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沧浪诗话·诗评》),由此还产生了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模仿崔颢《黄鹤楼》并与争胜的传说(《唐才子传》卷一“崔颢”条)。后代学者进一步研究,竟然发现崔颢《黄鹤楼》实模仿了沈佺期《龙池篇》。从《龙池篇》到《黄鹤楼》再到《登金陵凤凰台》,三首诗的关联恰恰显示出唐人七律创作具有相对公认的标准,而严羽对崔颢《黄鹤楼》的推崇,表明他对唐人标准的认可。周勋初先生注意到胡应麟和严羽诗歌选择标准中内涵的观念差异及其时代性背景:“严羽与明人虽然都推崇盛唐诗歌,但实质上却有很大的不同。严羽推重的唐诗,是指那些保留着很多汉魏古诗的写作手法而呈现出浑朴气象的篇什;明人推重的近体诗是指那些技巧全然成熟而表现为精工的作品。因此,这两种学说之间虽似一系相承,然而随着时代和创作潮流的演变,内涵已有不同。这是探讨我国诗歌发展史时应当注意的地方。到了清代,明人的意见更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大家的看法差不多已趋一致,论诗注重格律,强调的是诗体之正。”可补充的是杜甫此诗之所以被明清学者推崇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仅有诗歌艺术层面的考虑(如“四联皆对”),也还有诗歌思想内容层面的选择。因为自从《新唐书·杜甫传》以来,杜甫与儒家思想的关联(“诗圣”)、杜诗对“时事”的反映(“诗史”)成为宋人推崇杜甫的主要依据,而以书写个人悲惨遭遇、抒发个人悲哀之情的《登高》诗并未表现出前述社会性内容,因此,胡应麟对《登高》的推崇从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明代诗论家与宋代诗论家价值观念的重大差异。然而,尽管明清学者推崇《登高》,古今学者中却并非没有异词,比较集中的意见集中于末两句“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明代学者许学夷云:“第七句即杜体亦不免为累句。”(《诗源辩体》卷十五)清初学者黄生云:“结联宜略放松,始成调法,今更板对两句,通体为之不灵。”(《杜诗说》卷九)沈德潜云:“结句意尽语竭。”(《杜诗偶评》卷四)纪昀赞同其说:“归愚谓‘落句词意并竭’,其言良是。”(《瀛奎律髓刊误》)这些意见,看起来是批评诗句语言问题,如用语臃肿——既说“艰难苦恨”,又说“潦倒”,用语相复,对仗板滞——律诗尾联宜用散句,方才诗意婉转,而根本上还是批评诗句内容“意尽语竭”,即结句没有蓄余之意,缺少象外之旨,“此诗最后二句,没有结束上文,表达新的意旨”,“结句终究给人一种气力不足之感”。其实,按照律诗章法,此诗开头写景、中间叙事抒情,“前景后情,自是杜诗常格”(黄生:《杜诗说》卷九),“前四句景,后四句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七)。如杜甫名篇《春望》即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写景,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即转入叙事“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最后“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是触景抒情、感时叙事的当下反应,因此,《登高》最后一联两句正是杜甫当时处境与感受的真实写照。如胡应麟所云:“此篇结句似微弱者,第前六句既极飞扬震动,复作峭快,恐未合张弛之宜,或转入别调,反更为全首之累。只如此软冷收之,而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似未为不称也。”(《诗擞·内编》)胡应麟的辨析还只是着眼于这个细节本身的叙事抒情效果,其实,这个细节的出现乃至整首诗的内容、感情都与特定的节日风俗即重阳节有关,而这种关联也细微而深刻地折射出杜甫人格思想的重要特点。
“节日是社会文化所设置的时间单位,以历日和季节等组成的历年作为循环的基础。……节日是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之间的日子,节日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历日,就在于这期间包含着特定的风俗、习惯。节日的组成要素可以划分为下列三项:(l)特定的日期;(2)祭祀或纪念的对象,包括相关的神话、传说、俗信、禁忌等观念性因素;(3)人们相沿成习的仪式性的、社交性的以及娱乐性的活动。当这三项要素有机地结合的时候,一定的历日就成其为节日。”重阳节是中国特有的重要民俗活动,其来源颇不可考,《荆楚岁时记》记载“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世以来未改”,同时又引《续齐谐记》中东汉人桓景随费长房学仙避难事,并云:“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宫人贾佩兰,九月九日配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盖相传自古,莫知其由。”可见九月九日之节俗,在西汉之前已出现,其活动内容包括登高、配茱萸、饮菊花酒、食糕等,目的是避难、求长生。到了魏晋南北朝,重阳节登高饮酒渐渐成士人的风雅聚会,如西晋周处《风土记》载:“以重阳相会,登高饮菊花酒,谓之登高会。”在这种聚会中,因佩茱萸,故又称“茱萸会”。佩茱萸乃是因其气味有“辟恶气,御初寒”(周处:《风土记》)的功用,而饮菊酒则有“令人长寿”(《荆楚岁时记》)之效。陶渊明《九日闲居》诗明确说:“酒能祛百律,菊解制颓龄。”其诗歌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之采菊,并不如宋代以来学者所理解的仅仅强调菊花的气节象征意义,其实更强调了“菊解制颓龄”的实际药用效果。唐代“大大地发展了由魏晋人起始的亲近自然乃至回归大自然之倾向,而使其祈求避灾免祸的原初主题削弱到最低限度”,“形成重九之初的种种实际考虑,对于唐人来说,已经变得相当遥远,相当无所谓了——他们并不真的希求通过登高来避灾免祸,说到底,只是乐此一游罢了”。唐代诗人对此节日的描述甚多,如李白《九日龙山饮》名篇:“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于秋高气爽之际登高望远,饮酒赏花,畅游赋诗,确实是一种现实的生活享受。值得注意的是节日活动都是亲朋好友相聚一起进行,求长生的重阳节当然更重视亲人的相聚,如盛唐诗人王维的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景龙文馆记》记载“景龙三年九月九日,中宗临渭亭登高赋诗,学士皆属和”,“九月九日中宗幸慈恩寺,登浮图,群臣献菊花酒称寿,昭容赋诗”,可见唐代九月九日活动之盛况。
根据徐国能先生的考察,现存杜集中以“九日”为主题的诗歌有10 题14 首,是唐代诗人中最多的。杜甫入蜀前有《九日曲江》《九日寄岑参》《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九日蓝田崔氏庄》,盘桓蜀中有《九日登梓州城》《九日奉寄严大夫》《九日》,离蜀到云安后作《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到夔州后则先后创作了《九日诸人集于林》《九日五首》以及《登高》。这些诗显示,杜甫在九月九日节日活动内容与同时代人并无差异——欢聚、登高、赏花、饮酒等。
杜甫于代宗永泰元年(765),正月三日辞幕府,居草堂,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九月,至云安县(重庆云阳),因病,遂留居云安,馆于严明府之水阁。代宗大历元年(766),春晚,移居夔州,初寓山中客堂;秋日,移寓西阁,作《九日诸人集于林》。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公颇蒙资助。大历二年(767),春,自西阁移居赤甲;三月,迁居瀼西草屋;秋,因获稻暂住东屯。是年秋,杜甫复动东游荆湘之意。一般认为,杜甫于大历二年(767)九月九日创作了《登高》这首名作,时杜甫因暂住东屯。次年,即大历三年(768),正月中旬,杜甫即携家带口乘舟去夔出峡。
杜甫在夔州创作的九日诗也反映了杜甫当时生活处境与心理状态的变化,以及出峡的原因。大历元年作《九日诸人集于林》:“九日明朝是,相要旧俗非。老翁难早出,贤客幸知归。旧采黄花剩,新梳白发微。漫看年少乐,忍泪已沾衣。”在这个节日里,还有朋友欢聚,杜甫由此联想到自己岁暮年老,情不自禁,黯然伤怀。相对于大历元年《九日诸人集于林》所展示的节日朋友相聚,大历二年的《九日五首》以及《登高》,则表明杜甫是孤独度过重阳节,心情更加悲伤。现杜集中有诗题《九日五首》而实存诗4 首,宋人编辑杜集以来,《登高》诗就被编排在《九日五首》之后,因此,一种观点就认为《登高》是《九日五首》之第五首,而从内容上看,《登高》与《九日五首》其他四首诗确实密切相关,清代学者卢元昌说:“五章为一时之作,随兴所至,体各不同。首思弟妹,次思君,三思故友,四思故国,末(按,指《登高》)总结。”(《杜诗阐》卷二十七)
此诗题作“登高”,正是重阳节最基本的活动。登高所见与所感者何?“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正是夔州所见实景。这里山高峡深,秋风浩荡,诗歌描绘了江边空旷寂寥的景致,历来赞美此诗者都认为这四句写景生动传神地刻画了秋江的无边萧瑟。其实,写景之佳是含蓄地象征着诗人之遭遇和感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一联备受后代诗论家赞美,不仅对仗精工,而且内涵丰富,充分揭示了杜甫处境之艰难。如宋代学者罗大经之分析:“盖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鹤林玉露》)“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在这个本应登高欢会、游目骋怀、把酒畅饮的美好节日里,却是忧时伤世、离乡背井、穷困潦倒的诗人一人登台,既无菊花可赏,且因多病,亦不能饮酒取乐,诗人才感到格外的孤独、凄凉:“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导致诗人“艰难苦恨繁霜鬓”,并在此基础之上增加当下遭遇的书写——在节日里不得不“潦倒新停浊酒杯”的痛苦,写尽了诗人的艰难,可见结尾一联两句用词与语意并不重复,表达效果确如胡应麟所云:“如此软冷收之,而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这首九日诗所表达的深沉艰难感、衰暮感和孤独感,正是导致杜甫最后离开夔州的重要原因。还乡是杜甫所愿,实际上杜甫出峡后并未如愿,在荆州、公安等地稍作停留后依然是一路漂泊,到了湖湘,但至少他不再像在夔州那么孤独,所到各处还有频繁的交接应酬。
《登高》之所以被明清以来学者认为是“古今七言律第一”,是因为人们都注意到其艺术的精致完美,尤其是这首诗真正做到了移情入境、情景交融:秋风浩荡,秋色萧瑟,秋意寂寥,不仅是诗人身处的自然环境,而且也象征着诗人的悲剧命运。在古代从宋玉《九辩》开始的刻画秋景、表现秋意的各文体作品中,这首诗无疑最为简约,也最为出色,最为动人。读者既感动于夔州秋景之萧瑟苍凉,更感动于杜甫的悲剧命运。一般认为,杜甫的情感反应符合唐前流行的“物感”模式。《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也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者也。”陆机《文赋》提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和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观点“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都强调外在自然对诗人心理的感发作用;而钟嵘《诗品序》不仅强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而且还强调“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对诗人创作的激发作用。就《登高》情景结合之艺术境界生成的角度看,节日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要素,正是钟嵘所谓“离群托诗以怨”:杜甫触景生情,感情反应如此强烈,关键是他正经历的这个祈求健康、欢会畅饮的九月九日——特定的节日文化刺激了诗人的心理感觉。应该承认,既往的研究对这个因素关注不够。节日不仅是一个包含特定活动内容乃至仪式的时间点,更包含特定的情感体验,正是激发诗人诗情的触媒。有些古代学者认为《登高》最后两句“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结句似微弱者”,认为没有表现出杜甫惯有的抗拒悲剧命运的弘毅精神,这实出于对杜甫模式化的理解,也不了解特定的节日文化及其情感内涵。这首诗与节日的密切关联,也显示出“诗圣”杜甫思想人格的重要特点:他关注日常生活,重视世俗节日,具有炽热的平民情怀,正因如此,这首诗也才能引发读者大众的强烈共鸣和感同身受。
①《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评论》1985 年第5 期。
②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275 页。
③何满子语,见袁行霈主编,赵为民、程郁缀编辑:《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年版,第865 页。
④徐国能曾讨论杜甫及唐代“九日”诗(《论杜甫“九日”诗》,载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学术年刊》第21 期,2000 年)、赵睿才《杜甫节令诗文化精神探骊》(载《杜甫研究学刊》2002 年第1 期)都对杜甫“九日”诗(包括《登高》)的民俗背景有所论列,但没有讨论九日民俗对《登高》这篇文学经典生成的内在驱动作用。
⑤高丙中:《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202 页。
⑥黄新亚:《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234 页。
⑦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66—67 页。
⑧此二次活动存诗甚多,《登慈恩寺》应制的诗人共有二十七人(其中上官昭容与崔湜为同一首,疑是误钞);“渭亭登高”为分字之作,有二十二篇;另有一次《闰重九》亦有多人应制作诗,可见当时重九受到的重视程度,民间与朝廷都有热烈的节日活动。见徐国能《论杜甫“九日”诗》所论。
⑨这五首诗是否是一时之作,自宋代编辑杜集以来就存在争论,吴若本于《九日五首》题下注:“阙一首。”而赵次公以“风急天高”一首足之,云未尝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