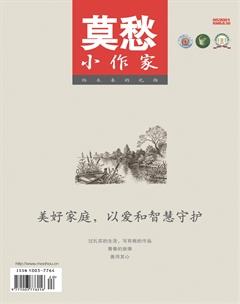善用其心
如果没有创新,没有融入个人情感和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只是千篇一律的复制,即使这种复制再精巧,也将使手工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采访札记
1
蒯良荣做壶超过五十年,有一批忠诚的客户。他们称蒯良荣为“窑火的魔术师”,认为他的壶艺风格和工艺开一代新风,堪称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山西的一位同行与蒯良荣有过接触,对他在制壶工艺上的追求给予四个字的评价:前无古人。一位熟悉蒯良荣的朋友对我说:目前在国内,他是第一,也是唯一。
去拜访蒯良荣。推开工作室的门,热气扑面,电炉丝与砂石在高温烧烤之下交织出一股工业的味道。这是一间干净、现代、小规模的电窑车间。蒯良荣转身迎来,扬着笑脸,眼睛明亮清澈。
我开门见山,“怎么证明您的壶好呢?”
这个很简单。取两把壶,一把是蒯氏的高温壶,一把是别人的壶,泡两壶同样的茶,实验证明,蒯氏高温壶泡茶更香。别家的壶,泡茶放一星期,茶叶发白。蒯氏茶壶同样的茶放一星期,茶叶没有变白的迹象。
蒯良荣的紫砂壶除了上述的宜茶、实用之外,造型上也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从橱柜里捧出一把蒯氏的“线圆合菱”筋囊壶,上下左右细细端详,舒展的线条里有类似于时大彬“瓜棱壶”的瓜棱纹,但在壶纽上蒯良荣做了创新,他改变了壶盖桥式壶纽的跨度,通过提升桥纽的高度让壶型显得高挑、清丽。这就是于传统中见新意。
老蒯举起泡茶的小西施壶,说看起来普通,但与其他的西施壶不同,“从壶纽、壶盖、把手、壶嘴、壶肚子一直到壶底,这条流畅自然的曲线,弧度优美。”西施壶以小巧取胜,特别是盖纽,小巧挺拔才更秀气。
一把好壶就是一个小小的宇宙。整把壶饱满的线条如同流淌的音符,清新甜润的小调在山涧、密林中低吟浅唱。曾在一本画册上见过顾景舟、王寅春、蒯良荣等人的西施壶,各有巧妙不同。顾景舟的西施壶华美高贵,王寅春的丰裕雍容,而蒯良荣的西施壶带给我的则是惊艳。
这把小壶稍稍离远一点看,壶形起伏的波澜不仅是音符,还是刻刀,雕塑出的人物其轮廓形同一位明媚俏丽的江南女子,蓬松如云的发鬏堕于脸侧,是壶把手;樱桃小口轻启,是壶嘴;而圆润饱满的壶身,是俊俏饱满的脸颊。论到紫砂壶的器型,西施壶是免不了的话题。善默者最是能语。一把简单至极的小壶,让人从中窥得紫砂工艺诸多沉默的语言。
蒯良荣的创新,不是大动干戈,改天换地,而是于传统中四两拨千斤,而是于不动声色中画龙点睛一两笔,风景迥然不同,峰回路转一两处,轻舟却早过了万重山。这是艺人求新求变的能力,也是艺术创新创造的另一层境界。
另外,老蒯的火工还具有独创性。他的紫砂壶最高烧到了1305℃,这在紫砂界是个很难达到的温度。眼前这把西施小壶烧到了1305℃,高温窑变令壶身落满明暗交织的光斑,如散落在夜空的星星,在无尽浩渺之间闪烁。那光不起眼,甚至微弱,但每个光斑却又是那样倔强,似穿透千年冰土,奔腾而来,固执地亮着、绽放着火与土激烈缠绵后的光华,无数个这样的光斑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壶身的光怪陆离、五彩斑斓。
2
客户根据蒯良荣的制作工艺,总结出“蒯氏制壶三法”:一是泥料是自己找的矿料,自己炼的泥。二是独特的拿捏制壶的技法。三是高火产生窑变。
有人见过他找矿石,说比找黄金还认真。天气晴好,骑辆自行车,车两边各挂一只农民装化肥的编织袋,踏遍当地各个山头。
好东西总是藏在人迹罕至处。有一次,在山上找石头时,蒯良荣一脚踩空,掉进一丈多深的坑道,这是当年探矿留下的废弃宕口。三四个小时过去了,他才恢复知觉。这件事蒯良荣悄没声气地谁也没告诉。他凡事不喜张扬,从来听不到他高声涨气地说话。蒯良荣的岳丈去世得早,岳母常年生病,吃药看病生活用度等费用一直都是蒯良荣在默默接济,兄弟姐妹间他从不为此多说一句,让老岳母心情舒畅地活到了100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境况,不叫苦、不喊累、不抱怨,在老蒯看来,是一种体面。
蒯良荣所有的劲都用在心里。完全沉浸在创作状态中的艺人,思绪连绵不断,从心到手之间贯穿着一股行云流水般的气,指尖上捏的不是泥巴,是自己心里的精气神。
“捧着一团不知来历的泥,稀里糊涂地开始所谓的创作,是做不出好壶来的。”他说。丁山、蜀山、黄龙山、青龙山、大潮山、北宕宕等等,这些山头蒯良荣都有所涉足。偶尔发现一星半点合意的泥块便如获至宝,捧回家中分门别类贴上标签,腐熟极致后,粉碎,磨浆,反复筛滤,摔打成泥。
他的独生女儿也是一位有经验的壶手,但蒯良荣始终不把自己的泥料给女儿做壶。他说,不仅是舍不得泥料,手上得要有相当功力才驾驭得了这好料。不是有好料就能做出好壶的,对壶的理解、认知、手工造型的能力,以及做壶人的耐力和性情都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不辜负那把好泥。“做壶,看起来是拍泥、捏泥、塑形,更是做人,考验的是人的精气神。”
3
但蒯良荣是有争议的。最大的争议就是,他将紫砂壶烧到了1305℃。
“你在紫砂泥中,会添加耐火材料吗?”这是大家对蒯良荣的质疑,正常的紫砂燒不到这个温度,如果能烧到他所说的1300℃以上,那就是加了耐火材料。这是人们从经验中得出的结论。
“怎么可能添加耐火材料,连陶土都没有添加的,没有作何添加剂,泥料都是我上山找的石头,自己炼的超高温紫砂泥。”
有专家说:除了极个别的泥料,比如大红袍,绝大多数的紫砂泥料烧不到高温区间的,一般都是1150℃——1200℃之间,所以根本谈不上破坏双气孔,因为就烧不到1300℃。大红袍现在只是用来讲故事的,基本没真的,所以现在紫砂说什么烧到1300多度基本都是讲故事。
宜兴当地一位紫砂行业的管理者说:烧这么高就不是紫砂了,再说根本不可能烧成的,紫砂烧塌了,壶坯的表层都要烧破皮的,起泡泡了。
怎么可能在同样一件事上,一个人处于舆论的两个极端呢?夸赞他的是客户,质疑他的是专家。谁说了算?
他坦然,“质疑一直都有的。我说得清窑烧的原理,心里没数不敢烧这么高的温度,烧爆、烧塌、烧炸裂开的,这事我都经历过的。”蒯良荣从墙角拖出一只竹筐,罩在筐上灰尘扑扑的布一掀开,里面是一堆壶,七歪八扭。老蒯说,“做实验烧坏的。”他拿起一把仿鼓,指着壶上凸起的小包包说,“火高了,爆浆。”再拎起一把井栏壶,“把手歪了,吃不住火温。”将近一年多的时间,老蒯一把没毛病的壶都拿不出来。一下班,就坐在泥凳上,一坐就是通宵。有一次,一窑的壶都烧坏了,60把壶全烧爆掉了。心疼,伤心动肺。
就在这一次次的理性探索中,完成了壶的独家高温烧制:“通常,一把壶起码要烧两次,而我的壶起码要烧到六次,每一次递进20度。通常一把壶烧三天就拿出来卖钱了,我一把壶前前后后加起来要烧到两个月,让火和土充分纠缠,从里到外产生窑变,而不仅仅是在壶的表层产生色彩的变化,我的窑变,壶里壶外是一致的。”
“你完全可以开个发布会,或者专家论证会,向外界公布一下你窑烧的过程,这样会平复一下争议的吧?”
蒯良荣笑笑,不置可否。
至今还有人记得,当年老蒯成年累月拿不出一把好壶的困窘。窑上的工人对老蒯的行为也很不解,正是紫砂行情看涨的年头,许多人恨不得今天做的壶明天就变成钱,有些手艺人卖几把壶的钱就能在市里买套商品房。蒯良荣精通各款壶型,对泥料在行,如果规规矩矩做壶,钱早就挣足了。爱人洪华平打趣老蒯,“人家做壶的都发达了,你手艺好,但做一把坏一把,图个什么呢?”
是的,图什么呢?图个心安。蒯良荣十五六岁时,跟着大人们炼泥,与紫砂打了近60年的交道,他技艺全面,集采砂、炼泥、配泥、制坯、窑烧等技能于一身。他知道砂的脾性,了解采砂的艰难。他懂泥,“紫砂给艺人的创作空间很大,火给紫砂能带来的变化远远不止这些。别人理解也好,质疑也好,影响不了我什么,我想走自己的路。”蒯良荣淡淡地说。
蒯良荣说过两句话让我一直难忘。一句是,他要做自己心目中的好壶。还有一句是,要做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好壶。做好壶,做老百姓买得起的好壶,凭的是良知和本事,凭的是心性和胸襟。
他捧出一把合菱壶。我举起壶盖,从侧面滑到壶上,任意一面都能与壶体盖上,纹丝不差。光给合菱壶整口就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整口这样的活,许多制壶的人懒得动手,都是让助手和徒弟做,要不就是付5元钱,窑上有工人顺带着整口。蒯良荣做了几十年的壶,这样的活都还是他自己来。其中光是整壶盖就费了他两个多小时,先是用大钢挫,继而用小钢挫,再用捖石刮摩,用竹针找平,整一个壶盖蒯良荣用上了30多件工具。“做一把好壶,没有一道工序可以轻慢。你松劲的那个地方,就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用多少心,就成多大的事。”
蒯良荣性格中的宁静、与世无争,化成他作品的线条挺拔,骨相清丽。人到无求品自高,他没有刻意求奇求怪,壶里注入的是他對人生的感悟。生活没有给过他奇迹,他所能拥有的便是在苦难、庸常和寂寥中的坚守。人有嘴,壶也有嘴。壶尽管不语,但再能说会道的嘴,也不敢轻视一把真正的好壶。
韩丽晴:《莫愁》杂志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作品多部。散文集《意思》获第七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
编辑 沈不言 7865596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