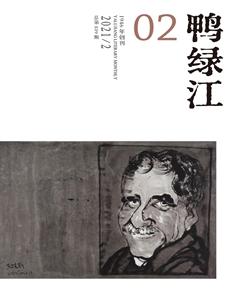“知识信仰”与“20世纪80年代爱情故事” (评论)
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贾平凹不无欣慰地提到:1978年,时年27岁的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总算摸出点门道了”,“稿子的采用率逐渐在提高”。①事实的确如此,尽管从1971年贾平凹就开始尝试向报社投稿,并且在此后六七年间他陆续有各类作品在一些报刊发表,但他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并有了寻找属于自己创作道路的自觉意识却是在1978年——我之所以重提这一点,并非意在回顾他文学跋涉的早期历程,而是要提请大家注意:贾平凹文学创作真正意义上的发端与“新时期文学”乃至“新时期”政治、思想和文化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较为明显的同辐共振关系。贾平凹这样回顾当时的自己:“我一面读中外名著,一面读社会的大书。我开始否定了我那些声嘶力竭的诗作,否定了我一向自鸣得意的编故事的才能……我要在创作中寻找我自己的路,提出的口号是:打出潼关去!” ②——自我否定想必是有些痛苦的,然而,这对一位有巨大的文学野心并在未来也走得足够长远的重量级作家而言,又是极为必要和极其重要的。就此而言,发表于《鸭绿江》1979年第11期的短篇小说《丈夫》,似乎可以视为在经历了明确的自我否定过程之后,贾平凹试图调动自己的生活和知识积累并将其转化为去寻找“自己的路”的作品,也是他逐步形成自己精神内质和艺术风格从而实现自我蜕变的一次创作实践。
时隔三十多年再去重读贾平凹这篇“少作”,很容易发现其中存在的诸如矛盾冲突的二元对立倾向、情节设置的人为安排痕迹、价值判断后显现出的单一化道德立场、情感与文辞表达的质直浅切等问题,尤其较之今日贾平凹的醇厚、沉稳、朴拙而老辣,其间差距自不可以道里计。但是,作为青年贾平凹自觉尝试探索个人化文学路径的产物之一,《丈夫》那饱满丰富的细节刻画、隐忍克制的叙事节奏推进、“编故事”色彩的淡化与“留白”与“诗意”等传统美学意味的凸显……这些已初步显示出他在当时文坛的独特性并让他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辨识度;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作为“新时期文学”发生期的作品之一,与其所产生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脉络之间天然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层纠葛。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与其所置身时代背景之间存在着格外紧密、深切的互动关联,这已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基本共识。可以说,当时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是对各类现实问题的直接呼应与想象性应对,也因此無可避免地被深深镂刻上时代的印迹,即便是那些看似在讲述个人爱恨情仇的作品,也无不被涂抹上强烈的历史与时代寓言色彩——《丈夫》自然亦不例外。①这篇小说看似沿袭了在中国源远流长且影响深远的“才子落难、佳人相救”及“薄情郎背义负心始乱终弃”的旧有故事模式,但假如深入其叙事腠理并将“故事讲述的时代”与“讲述故事的时代”相互关联,我们会发现,这篇看似意蕴单薄的短篇小说其实携带了许多启示我们深度体察和解析20世纪80年代社会、思想及文化逻辑的信息符码,比如男女主人公对待爱情和婚姻各自态度背后显现出的“知识信仰”与阶层/权力差序格局,比如男主人公遭遇到的爱情挫折及其“始乱终弃”行为折射出的社会分化与个体选择遭遇的伦理困境,比如青年人坚韧决绝的个人奋斗与主体性建构的破灭……凡此种种无不向我们昭示,《丈夫》所讲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爱情故事”,故事深层的复杂意蕴其实更值得注意,也有待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检视和发掘。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洋溢着浓郁的知识崇拜氛围的时代,弗朗西斯·培根那句“知识就是力量”的断言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深入人心并逐步凝聚为时代的共同信条。这既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至上”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性复归,更是国人对“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反智主义思想及其灾难性后果进行深刻反思和激烈批判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思想共识。毋庸置疑,这种对知识和文化的崇仰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与历史意义。在当时,知识不仅被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推动力量,更被“拨乱反正”后的国家政权作为建构其新的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柱石之一,基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才会相应地被确立为新时期的基本国策,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的现实与精神走向。②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之中,举国上下很快建构起了一种指向明确、内涵清晰的知识信仰。经由国家政权有意识地询唤、引领、灌输与民众的价值认同与主动参与,原本依托人类理性能力产生从而具有客观、中立特质的“知识”由此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从而具有了甚为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自不待言,这自然也会发挥其作为意识形态既有的文化功能和实际效用,知识信仰迅速弥散、辐射于当时中国的现实及精神空间的各个层面与角落,并自然而然地参与到民众的价值理形与精神图景构造之中,进而有力地影响和制约着他们对自我人生道路乃至爱情、婚姻关系的抉择。
从《丈夫》讲述的人物爱情与婚姻故事之中,我们足以见其一斑。
小说的男主人公“丈夫”,是一名出身农民家庭而通过个人努力终于进入城市并成为一家大型工厂技术员的“凤凰男”,同时也赢得了一位“高干女儿”的爱情,“相好了三年”。小说尽管没有对此正面描述,但可以想象,这名农民之子之所以能够获得“高干女儿”的青睐并跨越巨大的阶层鸿沟实现爱情逆袭,他真正能够依恃的除了“人物又齐整”之类非决定性因素之外,最有力的支持性资源恐怕就是他“技术员”的身份及其作为“知识”现实化身的象征性资本。与“高干女儿”建立在这种相对脆弱的根基之上的爱情遭遇失败之后,小说女主人公、工厂女工“她”主动走进他的生活世界,两人也很快建立了婚恋关系。但耐人寻味的是,与高干女儿一样,“她”对“丈夫”之所以倾心相爱,其最为核心的动力源泉其实同样是来自他作为“技术员”(知识表征者)的身份。尤其是小说对二人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描述,更为醒目地彰显出了在那个时代“知识者”对于知识匮乏者而言所具有的神秘魅力:
他们结婚了。他似乎没有对她表现出多大的亲热,只是钻研技术。但她高兴,全部挑起了家务担子:做饭,洗衣,买菜,拉煤,甚至月月定期把一定的钱寄给他乡下的父母。每天晚上,忙完了一天家务,她就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看他在灯下一本一本看那些厚书,觉得自己是世上十分幸福的人。
透过小说设置的“灯下看书”这一颇具仪式感的家庭生活场景,我们会发现,“文化浅”的妻子或许始终都未曾也根本无从走进那名有能力“一本一本看那些厚书”的“技术员”丈夫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她仅仅是在外部对丈夫隔空凝望,已足以让她感觉充实和幸福,当然,将自己凄冷、孤独、畸形的婚姻家庭生活状况与那些“双双对对,领着孩子看电影呀,逛公园呀”的“别人”的生活相互参照,尤其是面对自己“三四个月不回家”的丈夫与“帮女的做饭呀,洗衣呀,陪着老婆看电影,一把扇子整夜给她扇风”的“别人的丈夫”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之时,“她”不可避免地也会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而感觉到失落与哀怨,但在“她”心目中,与那些实用却庸常的“丈夫”们相比,自己正潜心于钻研科研项目并作为知识化身的丈夫,无疑更为高大伟岸也更令她骄傲,因此,当女伴们将她的丈夫与“隔壁老张”之类的丈夫相比时,她才会“觉得是受了侮辱”,并有足够的底气起身而去并在心里说她们这些人“庸俗!”——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来自“知识信仰”所提供的强大精神支撑。
但是,接下来要需追问的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精神资源的“知识信仰”,是否真的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是否强大到足以挑战、撼动或者颠覆社会阶层分化以及权力结构固化的社会现实?知识水平的提高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攀升,究竟能否为那些始终自强不息坚持奋斗甚至为此付出惨烈代价的青年人提供足够坚实的价值和精神根基,并借此完成自我的主体性建构?知识的累积、提升与良知、德性的丧失是否又存在必然性的内在联系?其实,这些问题在《丈夫》的情节架构和叙事脉络中都已显现端倪,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知识信仰”的有效祛魅和“知识神话”的自我拆解。
首先,小说的叙述告诉我们,“技术员”在被“高干女儿”无情抛弃和爱情理想由此破灭之后,他对阶层分化的社会结构和自我的命运出身发出了尖锐的质疑和冷峻的拷问:
“为什么农民的儿子就不能娶高干的女儿?我为什么就是农民的儿子?”
她觉得可笑,却拿宽心话劝他:
“阶级社会嘛,什么人没有呢?”
“高干,为什么就能成了高干?以前还不是和咱一样吗?”
“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与身为车间女工无知无识的“她”对阶层分化和权力结构的无奈认可与心平气和地接受不同,作为“知识者”的丈夫并没有就此消弭心中由爱情失败所激发的愤慨、不公甚至反而由此引燃了他强烈的报复心理,事实上,他后来之所以会冷酷无情地抛弃结发妻子,并试图再次挑战和掠取那些“高干女儿”的爱情,这恰恰是其最为强烈的原生精神动力。但问题在于,即便这个“农民的儿子”的确“经过奋斗,终于干出名堂来了”,他就必然能够成功获得一个“高干女儿”的爱情和一切吗?退一步来说,即便他真的“挑战成功”,他也仅仅是凭借自己的知识者和工程师身份征服了作为个体形态的一位“高干女儿”,但并不能对那些“高干女儿”依然会鄙视、冷落甚至根本无视千千万万“农民的儿子”的冰冷现实有任何改变,更不会对社会处处存在的阶层分化和无比强大的权力结构有丝毫撼动,他所谓的“为普通的工人、农民争这口气”,充其量是一种主观臆造因而极度虚妄的“精神胜利”而已!
其次,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就个人努力的现实目标而言,“丈夫”确实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他为此主动放弃了一个正常人应该享有的夫妻家庭生活,在“科研项目”攻关的最后阶段,甚至“三四个月内没时间回来了”;为了不“影响他的事业”,他几乎用尽各种手段驱使妻子连续三次刮掉腹中的胎儿……以自身尤其是其妻子的巨大牺牲为代价,他主持的项目终于获得了成功,他成为庆功会的绝对主角,并获得物质奖励,同时还被提拔为工程师。但是,他获得的这些利益、荣耀以及现实身份地位的迅速提升,并不能为他提供安妥自己灵魂和身心的确定价值体系和坚实精神根基。他依然是阶层社会中一个躁动不息的孤立因子,一个人生观和理想信念错位的虚无主义者,一个因社会位置不确定和信仰崩塌造就的人格不健全者。他野心勃勃、情绪偏激、心胸狭隘,胸中激荡着强烈的攫取心和征服欲,因而在具备了一定的现实资本之后便开始着手对权贵阶层的个体实施报复性掠夺和占有,然而他并不具备对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及其深层成因进行理性反思和彻底抗争的意识和能力,反而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完全信服并主动投身其中,这其实在客观上延续甚至强化了阶层分化和权力通吃的不合理现实格局。这也让他“为普通的工人、农民争这口气”的正义宣言显示出了本质的苍白无力及其内在的悖谬,他对“高干女儿”爱情的挑战究其实仅仅是一种“跪着的造反”,这让他看似勇敢、决绝甚至有些惨烈的抗争留下的只是一个空洞、苍凉而无望的姿势,能够自由掌控自我精神、意志及命运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建构更是无从谈起。
最后,《丈夫》对作为被欺骗和伤害者的妻子人生悲剧的正面描述,为她涂抹上了浓重的悲情甚至苦情色彩,对“丈夫”形象的刻画也显示出了作者鲜明的道德批判立场。这其实体现了青年贾平凹在文学创作和思想价值理念方面的一些局限。实际上,这种将“知识者”与“薄情郎”一体化的人物设置,与早先的占据主导性的反智主义思想倾向分享的是同一套话语逻辑,只不过将“知识越多越反动”置换为“知识越多越没良心”而已。但是,这种叙事伦理背后的意味才尤为值得注意:“知识者”与“良知缺失”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其實,这也是小说对“知识信仰”最有力的质疑和拆解力量之一。黄平曾经借用福柯的理论,将路遥《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指认为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利益主体“经济人”①,在某种意义上,《丈夫》的男主人公身上具有同样明显的利益主体“经济人”气质。对知识的汲取和对科研的全身心投入让他终于获取了更多的现实与象征资本,但知识对他而言只是实现自身欲望和野心的手段,“工具理性”彻底压倒了“价值理性”,对丛林法则的信奉驱使他精于利害算计并为了实现个人目标变得不择手段,不惜成为一个冷酷、绝情、虚伪、残忍的道德败坏者。艰苦卓绝的努力付出使他成为一个“知识主体”,却并未能够让他同时成长为一个“德性主体”——或许,这也是此类出身于社会底层而在阶层固化的世界试图通过个体努力实现命运转折的青年人必然要面对的人生难题,也是他们不得不付出的惨痛代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行其道的当前现实也提醒着我们: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不解决,这种“知识主体”和“德性主体”相互分裂的现象恐怕依然会存在下去。
整体而言,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多重要的命题在这样一个短篇小说中尚未能恐怕也不可能得以充分展开,但其讲述的20世纪80年代爱情故事却敏锐地触及很多当时客观存在甚至延续至今的社会、思想及文化症候,这或许也是我们隔着三十多年的巨大时空界限依然对其进行重读的实际意义所在。
【本栏责任编辑】 洪 波
作者简介:
刘新锁,山东滨州人,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研究。山东省作协签约评论家,在《文艺争鸣》《读书》《江苏社会科学》《山东社会科学》《扬子江评论》等期刊发表论述3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等多项,研究成果曾获得山东省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济南市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