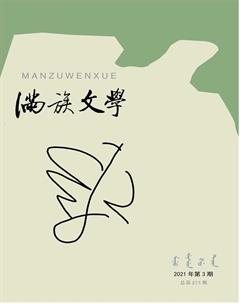白天不懂夜的黑
虹晓
背着行李,整整一个晚上,都在坐火车。我想我是一个慎重的丫头,不会随随便便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朋友丽影,就在那座城里。在电话里,她说:“这个地方有山有海,天空蓝得像水晶,更重要的是,”她顿了一顿,“如果你至今还一事无成,这里就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我还有什么话说,连夜整理了行囊,顺着两根油光锃亮的铁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地方。
最先见识的是这个城市的早点铺,丽影带着我,一根油条、一碗豆浆,外带两个叉烧包。除了这个味道怪怪的叉烧包外,这里和老家的早点铺没什么不同。客人带着清晨的寒气走进来,吃得肚儿溜圆地走出去,整个城市就打着饱嗝心满意足地醒来了。而我却脑袋昏昏沉沉地只想睡觉,在丽影的宿舍里,我放下两天来和我形影不离的行李,轻快地爬上了丽影的铺位,就迫不及待地闭上了眼睛。一躺下来,我就觉得我又上了火车,上上下下地颠簸,我甚至听到了火车在铁轨上走累了“咔咔”的咳嗽声。
火车终于停了,我从铺上下来,已经到了中午。丽影带着我跑,说是要让我真正长些见识,等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居然在一个农贸菜市场里边。她领着我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看过去,我的眼睛都直了,都是些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它们从浅蓝色的海洋里爬出来,如今栖居在一只只大小不一的白铁盆里,个个都懒洋洋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也难怪它们,要是我从一个天高海阔的地方来到这个几尺宽的破铁盆里,我也会寻死觅活地横竖想不通。丽影已经挑好了要买的东西,那是一条刚烈的黄鱼,据说一离开海水马上就自绝于人世,外带几条乐不思蜀的海鲶鱼,因为在破铁盆里都欢实地如鱼得水,另外还有好多兢兢业业的蚬子,蒙着头闭着眼一刻不停地在吐沙。不管它们怎样个性迥异,等摆上餐桌的时候,就彻底面目全非了。黄鱼软塌塌地缩在汤汁里,一点气节都没有,海鲶鱼就像一截呆木头,而蚬子彻底休闲起来,在躺椅上敞开白肚皮,懒洋洋地晒太阳。我津津有味地把小刺小壳堆满整个小碟,然后就想这个城市就像个魔法师,一只手摊开是一样东西,这只手向空中一扬,再摊开时,又变成另一样东西。
在火车把我送到这个城市之前,通过那条细长的电话线,丽影已经兴高采烈地向我描述过魔法师了。这天下午,我推门走进“伊人”美发厅,果然看见了丽影说到的魔法师,不是一个,而是一排,都穿着灰色的紧身小马甲,忙着在客人的黑头发上变戏法。丽影拍着一张角落里的空椅子,大声说:“青青,上来,待会儿让他们给你弄弄,你这个小土妞。”我坐在黑皮椅子上,认真打量对面的镜子,半身长的镜子中央有个胖乎乎的“假小子”。丽影低下头来,用我熟悉的小细嗓低声对我说:“他是娄东,是这家发廊最棒的造型师,还是咱们老乡呢!他会帮你收拾得好看一點。”一个穿着灰马甲的小伙子,就笑眯眯地出现在镜子里了。他用耳语一般的声音对我说:“青青,坐好了。”我的头发上就像拂过一阵细风,接着他用叹气一般的声音对我说:“女人的头发,要轻拿轻放,轻轻的。”
我顶着一个被娄东称为“酷毙”的发型,到过这个城市的海边、沙滩、栈道、商场,最后停在了一个叫做千里香的饭店前,丽影对我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就从这里开始吧。”然后,我就套上了一条盘龙绣凤的红旗袍,在雅间里端茶倒水了。这个雅间有个好听的名字“暗香”,暗是没窗见不到天日的幽暗,香是酒醉人去楼空后的浊香。这暗香厅是饭店三楼最把边、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套间,对过就是烹炒油炸大厨房。领班徐姐倒是个爽快人,她第一次见我,就语重心长地说:“这饭店啊,就像个水果摊,只有好看的水果才能放在前边招客。”于是我就像一个蔫巴苹果,一路滚到了千里香最偏僻的暗香厅里。
一天中的大部分时候,在千里香饭店,我端着各种形状的盘子,脚不点地地走着,像一片浮云游来荡去。有时,这片浮云会悄悄停在厨房的门口,只要有人吆喝“青青”,或者抱怨菜怎么上得这么慢的时候,它就得仓皇地荡开。就这样飘飘荡荡了几个月,我终于看出点门道。这些来自遥远大海的鱼类,不论是两只眼睛都长在一边的,还是嘴巴小小偏在一旁的;不论是长着规规矩矩的鳞片的,还是别具一格滑溜溜赤身裸体的,被人类放入笼屉清蒸、放入铁锅红烧之后,都驯顺地裸露出蒜瓣一样的细皮嫩肉。而它们那些长长短短、背着壳类的小兄弟们,人生道路就会有不同的分野,它们中的一部分在走上蒸锅之前,壳里增添了蒜蓉、粉丝等新装备,需要负重前行才能走完最后的人生之路。而另外一些的归宿就比较惨烈了,它们需要奋不顾身跳入滚烫的油锅,和葱丝、姜丝、辣椒丝纠缠着热舞一番,然后在灼痛中打开自己的心扉,当砰砰的声音接二连三地响起的时候,无色透明的料酒就适时地淋在它们敞开的肚皮上,就像人类在入土为安的前夕要撒一些泥土一样,这是死亡前的最后一个仪式。然后是铁铲、盘子,最后是我,接过它们生命最后的余温,小跑着送到客人的桌子上。如果运气好,我有时候也能看到幽蓝的小火,怎样暴跳如雷一般“腾”地窜到锅底,炎炎的火冲到一丈多高,在火的盛怒里隐隐传来痛苦的哀叹与呻吟,当火慢慢息了,外焦里嫩的松鼠鱼已经翘着尾巴,等着酸甜可口的调味汁“黄袍加身”了。当然,有时候厨房是安静着的,刀子滑动着优美的弧线,游走在冰冷的身体之上,然后停顿、用力,让过骨头,再用力,适可而止,当刀子提起的片刻,一片透着光的薄肉片,在空气中匀速无声地落入白的磁盘。然后这些片好的鱼,蜷曲着,被细心摆好,直到优雅的孔雀在白瓷盘里旋转、定格、开屏,一种花团锦簇的死。从生到死的距离,有时候仅仅是一双手,可我经常看不到那双握着刀柄、端着炒锅、不断变出戏法的手,我是说每次我刚刚站在厨房边上,厨房的老季就开始跟我说话了:“不忙啦,今天客人多不多。”老季是“千里香”的大厨,手艺最好。我一边应付着,一边就忘了看他那双能变出戏法的手。老季说这里人说话“海蛎子”味儿太重,他就爱听我说话,亲切。老季的口音是南腔,我的是北调,事实上大部分时候,我们俩各说各的,谁也听不懂谁的。
谁也听不懂谁的,还有我和丽影。丽影说她是一定要上对花轿嫁对郎的,这是个技术活。然后我的眼前就飞动起了剪子,像两只鸟,上上下下,在头发上飞,那是娄东。再或者就是一把跳舞的刀,在案板上one two three,恰恰,one two three,恰恰,那又是老季。不用我说,丽影马上就看到那把剪子和刀,她像个果敢的女战士一样摇着头,说这是两回事。不等我同意,我已经被丽影神神秘秘的声音带着跑了起来了,很快我看到了一座三层别墅,奶黄色的外墙,尖尖的屋顶,有一面墙那么大的落地窗,风从窗外吹过来的时候,天蓝丝绒配着金黄流苏的帘子波澜不惊。记不清多少次了,我跟着丽影在这座声音搭建的房子里跑进跑出,我用想象的触手紧握纯银的把手,推开黑檀的原木门,纯天然大理石的壁炉里燃着的是真正的白橡树,木材在火焰中“哔哔啵啵”地裂开,那是白色钢琴在睡梦中轻轻吐出的音符。丽影不说,我也知道这就是她想要上的花轿了。很多时候,我支楞着耳朵还想听丽影说说那个“郎”。然而每到这个时候,丽影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运动员一样,除了那个终点线之外再也看不到别的了。丽影一心想撞到的那条线,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不确定的形状,像金子一样灿灿地闪着光,有时候它有着复杂的轮廓:罗马柱、拱廊,茵茵的绿草坪。有时候它简单到就是一个叫蔡姐的女人。蔡姐是丽影在美发厅的老主顾,她就是丽影嘴里那个真正上对花轿的女人。
在“伊人”美发厅里,蔡姐的花轿是让丽影和娄东抬着的。丽影和娄东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一个还在帮蔡姐扇扇子,另一个已经把红枣银耳粥端上来了。蔡姐周到,从来不顾此失彼,她刚对右边的娄东说她要办一个最贵的剪烫套餐,又会对左边的丽影说,她已经决定考虑丽影推荐的营养护理了。丽影笑着去端水果,娄东就会用唱歌一般的声音说:“先洗头,蔡姐。”等蔡姐头发包着格子毛巾高高顶起的时候,丽影会小跑过去,把蔡姐小心翼翼地扶在贵宾椅上。然后丽影退开,娄东开始大显身手了。娄东湿哒哒的声音会变出很多只小蜜蜂,绕着蔡姐高高低低地飞,在红热的灯罩子下,蔡姐像一朵不再萎顿的花,慢慢有了摇曳的姿态。
有时候,蔡姐的老公会来,这个叫做郝建的男人,一进门,发廊里的人就迎过去了,最先过去的总是丽影,她手里端着柠檬水,一迭声地赶着叫“大哥”。郝建接过柠檬水,先去老婆那里打个招呼,这个时候多半蔡姐头上还顶着个罩子。郝建就会站在发廊的吧台附近,点上一支烟,抱着胳膊,静静地站着。店长过来的时候,郝建就会跟店长聊两句,问问今天生意怎么样。说话中间,为了弹烟灰,郝建会绕过几张椅子,专门去找垃圾箱。不用郝建去第二次,丽影就把一个玻璃烟灰缸放在离郝建最近的茶几上了。不到几支烟的工夫,蔡姐头上的罩子该拿下来了。然后,郝建抱着胳膊,看老婆最后洗完头,吹完头发,就先出去发动车子了。蔡姐跟在后面,照了又照镜子,临出门前,还要专门去拉拉丽影的手,再和娄东说说感谢话。
丽影推门进来的时候,我还在包间里收拾。孔雀的屏有一半被拉扯地分了家,蓝莓山药歪歪扭扭塌陷下来,西红柿萎靡不振,瘫在牛腩汤汁里像个病人似的,手打的鱼丸只剩下一个了,孤零零地在葱花汤里打着旋子。刚才花团锦簇的一大桌人、一大桌菜,现在转眼人走茶凉,狼藉一片。丽影带着一团热气进来,在我把桌子彻底收拾干净之前,她已经热热闹闹讲了半个钟头了。我一边往泔水桶里倒这些五味俱全的垃圾,一边往脑子倒丽影嘴巴里蹦出的那些五颜六色的词,金卡、银卡,提成,人脉,跳槽,投资,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往泔水桶里倒的是这些我不明所以的词汇,而往脑子里倒的则是七荤八素的剩菜。最后,丽影终于用我能听懂的话告诉我,她晚上要请蔡姐吃饭,让娄东作陪,就订在暗香雅间。
暗香雅间就像一个过惯夜生活的美人,白天灰头土脸的毫无神采,可是一到夜晚,华灯初上,它就顾盼生辉,楚楚动人起来了。楚楚动人的还有蔡姐,她是客人里最后到的。她来的时候,我已经按照丽影的吩咐,在白盖子茶壶里泡好了金骏眉,丽影也已经把菜单从头到尾翻了两遍,娄东作为一个陪客,早早地把他好看的微笑摆在脸上了。蔡姐进来的时候,他们俩就像又回到了伊人发廊,一个过去帮蔡姐把包和衣服挂在衣架上,另外一个帮蔡姐挪开椅子,等着蔡姐舒舒服服地坐进去。“你就是青青啊,”蔡姐朝我微笑,“我听丽影经常提起你。”我本来也想把这句话再重复一遍,只要把青青换成蔡姐就可以了,可是我只听到自己闷声闷气地说:“蔡姐好。”我递上菜单,蔡姐什么都没看,就在菜单的最后一页,随意挑了两个小凉菜。等我挨个往上端菜的时候,就听到丽影早先说过的那些个五颜六色的东西,什么金卡、银卡,提成,人脉,跳槽,投资啊,又都统统跳上了饭桌。蔡姐不说话,微笑地听着。我把她带的红酒倒在长脖子的醒酒器里。等我送汤上去的时候,紫红的酒已经苏醒过来,在三个透亮的高脚杯里漾漾地伸着懒腰,我听见他们说,为缘分干杯。灯光下,蔡姐精雕细琢的脸,眼睛是两个酒杯,周到地盛着笑。丽影的妆好像有点花,包间里有空调,可她的额头始终是汗津津的。娄东就像杯里的酒,有点不安有点懒散,少了一点小心翼翼多了一点什么。是什么呢,我还没来得及看出所以然,就听到有人在走廊上喊“青青”。
等我再回到包间里的时候,我发现那多了点东西,应当跟酒有关了。蔡姐脸已经红了,嗓门也亮了,平时精心藏在小提包里的谨慎,现在大喇喇地扔在菜盘中间。我听她在讲她的私人影院,巴黎之旅。丽影更小了,缩在座位上,一直笑着的脸有点僵。娄东的座位离蔡姐近了一些,他不说也不笑,只是喝了太多的酒,满脸通红。我挨个给他们递温热的小毛巾。最后一块小毛巾掉在地上,我弯下腰来,突然看见蔡姐的脚压在娄东的脚上。我站起身来,头有点晕,灯光下一切正常,蔡姐还是边笑边说,两颊都已经红了,眼角的细纹按捺不住地三五成群地跳了出来。丽影很费力很用心在听,她的脸倒是白的。娄东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贪杯的人,除了一杯杯地喝酒以外,好像再想不起别的事了,我走了出去。
我推门出去找丽影,那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这三个月让城市从夏天缓慢地走到秋天。海滩上的外地游客越来越少了,海风从海滩一路跑来,绕过这个城市的高樓大厦,把叶子从树上叫下来,然后一齐拉着手欢天喜地朝前跑去。我还清楚记得我第一天来到这个城市,怎么拉着手和丽影一路小跑,那时天还是燠热的,海风吹乱了人们的头发。我的头发在这个城市里慢慢长长了。那天徐姐突然像第一次看我一样,拉扯着我的头发说:“哎呦,看看才来几天,假小子就变样了,会浪了啊。”我把自己拽到镜子前,看到镜子里的小姑娘尖尖的下巴,眉眼舒朗,头发已经过肩,前边一小撮刘海上边停着小小的卡通蝴蝶。我看到镜子里的姑娘皱着眉头,噘着嘴巴,我知道这是因为她讨厌那个“浪”字。在遥远的西北故乡,“浪”有不正经的意思,是说一个女人作风有问题。可这个城市嘴里的“浪”,就有好看、会打扮的意思,是人们在相互打趣或者赞赏时候说的。我不知道漂亮的徐姐是拿我开心,还是真心夸我变好看了。我只知道,这三个月以来,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已经被调整到一个更大更漂亮的雅间里,我不知道这跟徐姐说的“浪”有没有关系。在千里香饭店,我也有了新的朋友。跟着这些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们,我跑遍了这个城市所有卖衣服的地方,在那些光彩夺目的专卖店里,我们装作老练地摸着衣服质地,评价最新的款式,有的小姐妹甚至胆子更大一些,干脆穿上在镜子前左看右看,当然最后一律是不买,因为各种各样不合适的理由,其实所有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价签后边的价格。但我们还年轻,总有一天这些高不可及的价格,也会在我们慢慢鼓起来的口袋前低下头来。丽影不用等了,她现在就轻巧地能让这些藏在价签后边的数字乖乖地低下头来。她穿着精美的衣服,跨着名牌的包包,微笑着站在微信的相片里。看来,这三个月已经让丽影接近那条让她艳羡已久的终点线。仅仅三个月,我想我没什么可以担心的,这个城市就像一个魔法师,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
我没有奇迹,唯一值得说一下的就是我的钱包了,它看着我在这个城市里天天早出晚归,也懂事地慢慢鼓起来给我撑撑腰。当属于我的钱第一次超过四位数的时候,我觉得我应当对我的朋友表示一下感谢了。我迫不及待要找到丽影,我推开伊人发廊的门,可丽影不在那里,或者说,丽影已经很久都不在那里。我给丽影在微信中留了言,我没有说我到过伊人发廊,我只是说我发了奖金,要请她和娄东吃饭。到了晚上,丽影给我回复了,大致意思是说,人太少出去玩没意思,不如把我那些新认识的小姐妹们都叫上,她来买单。我想,丽影是个深思熟虑的人,她做事肯定有她的道理。只是,在小姐妹之外,我又约了老季,我想就娄东一个男的,总归有点孤单。
当夜色下定决心要把整个城市严丝合缝包起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块厚厚的黑金丝绒帘子。那些依然不熄灭的灯光,是缀在帘子上的廉价的亮片。爵色KTV是这些亮片中最闪耀的一个,当周围的灯光渐次暗下去的时候,它孤单地站在那里,勉力支撑着这个城市最后的声色。我第一次来这个城市的KTV,就被门顶上快节奏的闪烁的灯光弄得心烦意乱。更别说大门的入口也让我难受,那是一个金发的美人大张着嘴在唱歌,而我们就要从那两片鲜红欲滴的嘴唇中间走进去。我听到小姐妹里有人说:“够劲,爵色绝色。”我听到好多人在笑,一个从陕西来的小姐妹,捅捅我的胳膊问我,他们为什么笑。我有点头晕,什么都没说。那天晚上真正堪称绝色的,既不是门口那个可怕的金发美人,也不是我们路过走廊时,从我们身边经过的一排身份可疑、妖艳无比的女人。而是丽影。她推开门的一刻,我们都不约而同喊了一声。我看到娄东和老季同时亮起来的眼睛。一字肩,V字领,宽腿裤,是黑麻料的,宽腰带、宽发带,手提包,是白色的。丽影夹在黑白两色的强烈对比中,明艳照人。我站起身来迎过去,这三个月来,她杳如黄鹤,等她从天边降落到凡间的时候,竟然是这样遥远神秘。丽影没有架子,即使她穿成像时尚杂志封面女郎,即使她提着三万多GUCCI重工刺绣的手提包,也是和以前一样热情周到。热情周到的还有娄东,他就像个圆规,绕来绕去地忙活,只围绕丽影一个圆心。他提议要和丽影唱个《相思风雨中》,所有人都在起哄,丽影笑着站起来,在拿起麦克之前,用手拽住了我。她要拖住我一起唱,娄东眼里有失望。老季说两个人的歌,三个人唱有点挤。我趁机回到座位上。娄东转过头来看着丽影唱,丽影看着屏幕唱,我们其他人跟着伴奏低着声音哼着唱。娄东从台子上下来的时候,脚步有点趔趄,老季过去迎住他,手里带着酒。丽影站在台子上说,她知道娄东有个拿手绝招,就是唱女声。大家纷纷鼓掌。有人尖着嗓子说:“最流行,李玉刚嘛。”然后那些小姐妹就边跺脚边喊“李玉刚、李玉刚。”娄东站起来,老季低着头,只是喝酒。我有点不舒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周围吵得太厉害。娄东说:“丽影和我是老乡,就和家人一样。她要听,我就唱。”姐妹们鼓掌鼓得更用力了,连老季都从酒杯里抬起头来,拿出两只手,拍在了一起。前奏一响,娄东伸出兰花指,一声挤着嗓子的假女音,像啤酒瓶刚打开的气泡,咕嘟咕嘟冒出来,“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大家哄笑起来,我看见娄东嘟着嘴巴,夸张地向着丽影抛媚眼。丽影站在台子下面,没心没肺地笑着,连老季也像看呆了一样。“此生只为丽影去,道他君王情也痴。”我看不下去了,站起身来出去透口气。包房内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曲子停下来的时候,干杯声又响了起来。我听见娄东尖着嗓子喊:“喝,喝,人在江湖走,谁能不喝酒。”过了一会儿,老季的声音:“慢点喝,兄弟。”突然门被撞开,娄东捂住嘴跑了出来,我跟过去,想要扶住他,他推开我,径直跑到卫生间。我定一定神,耳边响起的却是丽影的声音,那是我刚来这个城市的夜晚,丽影跟我挤在床上说的悄悄话,她说:“娄东,这个人呢,好是好,可惜,”她停了半天,说,“可惜也是小地方来的,在这个城里除了手艺什么都没有。”
从卫生间出来,那个脸色白净、衣服整洁、说起话来轻声轻气的娄东不见了。出来的是一个领口松垮,袖口污脏,眼神迷离的城市浪子。我架着这个不知道是山寨还是原版的娄东,从那个金发女人张开的大嘴里走了出来,在近旁广场的长椅上坐下。秋天的夜晚,月亮在远处,一两片枯黄的叶片,蜷缩着,抱着头在地上打哆嗦。不时打哆嗦的还有娄东,他一边打哆嗦一边不停地说着脏话,就像一个人冷了不停地跺脚一样。我从没见过娄东像今天这样失态,但也许,我压根就不了解他,就像我压根就不了解丽影一样。这个城市才了解他们,就像那个张着性感大嘴的金发女人一样,把人们吞进去再吐出去,对他们样样心知肚明。夜已经深了,金发女人不知疲倦地盯着眼前的街道和偶尔飞掠过去的汽车。我猜,她一定看过这个城市太多的秘密,可她依然能大张着嘴守口如瓶。
有一辆越野车慢慢减速,犹犹豫豫地停在了金发女人的刘海下面。那辆车停了一会儿,仿佛受不了这个大红嘴唇的撩拨似的,慢慢移到了金发女人侧面阴影里。很快,车门打开,是个男人,抱着胳膊,在那里抽烟,抽完后又不忘把烟蒂送到附近的垃圾箱里。金发女人仿佛要说话,只不过她这一次只吐出了一个字,一个小跑出来的黑白相间的女人,她上了那辆车,那个男人也回到了车上。车没有马上开动,而是又停了一会儿,才倒退着经过那张守口如瓶的大嘴,然后摆正方向扬尘而去。我和娄东把眼光收回来,我听见娄东低声说:“进去吧,太冷了,这里。”
天一天比一天冷了,可老季自从上次唱完歌后,对我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老季说:“青青,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可我知道,老季说的这个头,早就开始过了,在江南遥远的乡下,那里有一个女人和孩子。老季说:“现在离婚不是个事,只要我们俩情投意合就行。”我就想要是离婚都不是个事,那生活里基本也没什么事了。老季说:“你不是喜欢做菜吗?我教你,然后咱俩开个夫妻店。”我想老季看着也不像传说中的渣男,怎么动不动就约人开夫妻店呢。老季热了一段时间,看我总冷着一张脸,就说:“要不然我请你吃顿饭,再请你看场电影,以后我就不提这事了。”我没想到厨师老季在这么多天想入非非之后,还能这么优雅地把车刹住,用美食和电影完成一个告别仪式。我说行,但吃饭买单的人应当是我,感谢老季这么多天以来诲人不倦地教我做菜。我这么说其实是有点抬举老季,老季除了在我站在厨房门口张望时没有赶走我以外,其实也没正经教过我什么东西。老季想也没想就说行,说那就请我看电影。我们俩凑了个都休息的时间,就出来了。老季自己是厨子,所以他点起菜来,话特别多,几乎是把菜单上每个菜的做法给我报了一遍。我想,这也不怪老季,说到自己专业的时候谁不想着多说两三句的。菜上来了,老季就开始用嘴巴给这几个菜添油加醋,我闭紧嘴巴吃菜,顺便也把耳朵閉上。我想自己真是个幸运的女人,不用天天站在老季的夫妻店里听他没完没了地报菜单。终于等到看电影,我和老季坐在黑暗里,听着屏幕上的人说话,我想幸福有时候特别简单,仅仅是需要一个人闭上他的嘴巴。在黑暗里,我把自己全部扔到剧情里,不记得身边还有一个叫做老季的人。问题是老季不愿意自己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他把嘴巴闭上,却把胳膊贴在我的胳膊上,我让开了,过一会儿,他好像无意似的,把他那只天天握着刀的手压在我的手上,我抽出手来,心里想,千里香我是不能再呆下去了。
又是丽影,她用好听的嗓音在微信里给我留言说,“不想待着,就换地方呗,这个城市机会有的是。”这个城市的确很大,我走了整整一大圈,才把快走残了的双脚落在一家小小的烧烤店里。这家烧烤店比不上千里香,门面不大,但进去敞亮,坐落在一家高档小区的旁边。小小是它的名字,在一座座如性感尤物的高档别墅旁边,它含蓄内敛,温润如玉,是典型的小家碧玉。一块块蓝底白花的小素帘子,像模像样地隔开小小的雅间。我穿着小花围裙,微笑着站在生卒不详的羊的残腿前,用小本子记下啤酒、花生米、拍黄瓜。老范是这里的常客,一个星期总有一两次,他腋下夹着手包,微胖的身躯挤过小小开了一半的门,撩开花布帘子,在小小的雅间里坐坐。老范不用看菜单,甚至不用说话,说话的是我。“十根羊肉大串,五串板筋,两串骨肉相连,一串羊腰子,一盘拍黄瓜,两瓶啤酒。”还没等我说:“对吧?”或者“您要不要再添些什么?”老范把手一挥,我就下去报菜单了。老范来的这个点,正是店里客人慢慢离开的时候,一般是在晚上十一点左右。菜上来了,老范先给自己倒一小杯啤酒,满满喝一大口,眉头一皱,哈出一口气,然后再用筷子夹两片黄瓜,放下筷子,再喝一口酒,然后是羊肉串,然后再喝一口酒,然后是板筋和骨肉相连。腰子是要放到最后吃的。老范一板一眼,有条不紊地进餐,雷打不动。这个程序中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老范有话要说。一般到了这个时候,老范的酒已经两瓶喝完了,他会特意再要两瓶,一瓶留给自己,一瓶塞给小李。小李是我的搭档,十一点后,一般是我们俩和厨子大刘在应付最后一批客人。小李拿着酒,只好坐下陪老范。当别桌客人都走干净的时候,老范也会让我坐下来。我和小李不能催老范,只能耐心等老范把他的老三篇重头再捋一遍。老范的话就三个重点,第一个苦出身,第二个挣了钱,第三个离了婚,最后瞎活。听起来有点像三句半。老范一走,我们就可以关门大吉了,但有时我们也会议论两句。我和小李的那一句是老范孤孤单单,挺可怜的。大刘偏过头来插另外一句:“有钱人的世界咱们不懂。”或者“老范泡妞的时候多着呢。”
这个城市有海,冷和热都是不慌不忙的。等到新年的前一周,人们已经把最厚的衣服穿起来了。烧烤店晚上的生意越来越火爆了,到凌晨的时候,都有人吆喝着大嗓门划拳斗酒。老范来了,喝完酒,吃完肉串,也不叫嚷着让我们陪他了,老范是个识趣的人,知道我们忙,结了账,一声不吭地往外走。临出门前,突然叫住我,问我新年怎么过,还没等我回答,老范说他倒有个好去处。看我犹豫,老范又说,他也会请小李和大刘。我心里想着丽影,她是我在这个城市最好的朋友,这个城市的第一个新年我希望能和她在一起。老范看我不太积极,就说没事没事,到时候再说。到了新年夜这天,店里已经忙得脚不点地了,我抽出空来给丽影发了微信,想约她吃饭逛街。丽影说她已经约好一个很重要的朋友,让我等她改天聚。跟在对话框下面的,是丽影发来的好多照片。照片里的丽影,穿着各种泳装,斜倚着、站着、坐着,每一张都嘟着嘴,好像在朝镜头外的什么人在笑。远处是阳光下的海。丽影说那是巴厘岛,她刚从那里回来。我脑子里想着这个有着古怪名字的远方岛屿,脚已经开始在各个小雅间里穿梭了。
新年的头一天,是从中午开始的。我睁开眼睛,天灰蒙蒙地阴着,没有太阳。小李在微信里约我说晚上和老范一起坐坐。我没什么地方好去,就答应了他。一过五点,我们就坐在一家高级酒店的西餐厅里了。大刘没有来,小小烧烤店又要开始忙了,他是主心骨。老范把一个绿色丝绸绒面的大菜单递给我,说:“女士优先。”这里的菜单,沉甸甸的,就像一位穿着燕尾服的老先生,低调奢华,沉稳周全,相比,我们小小烧烤店的菜单,轻飘飘的,就像一个无家无业,在外孤身漂泊的小姑娘。我把老先生请到餐桌上,端正坐好,郑重其事地打开。我象征性地翻了翻菜单,然后把它还给老范,说:“您来选吧,我随便。”老范把脸凑过来,纠正我,“别您您的,又不是在烧烤店,以后就叫我哥。”“还有,”他笑眯眯地说,“哥告诉你,女人不能说随便呦。”我低下头,觉得老范撸串时候都没这么油腻。牛排上来的时候,老范提议举杯:“一是为新年,二是为缘分,三是为新添个妹妹。”最后,老范把这三句半补充完整:“开心。”可我有点不开心,我觉得我更愿意听老范以前的三句半。我看出来,小李和我一个心思,因为他不断揪起话头,想让老范说说那些在小小烧烤店每周两次说起的话。可老范好像被这些外国菜震慑住了,除了摆弄自己的刀叉,礼貌性地叫我们多吃菜以外,他的话没有了。桌子上,只有刀叉拿起来放下的声音,耳边不知是什么外国曲子,一遍遍说“LOVE”。
老范说要带我们找个有感觉的地方坐坐。小李欢呼,我没法反对。老范带着我们走进一家酒吧,那里灯火通明。我从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酒,整整一面墙,高脚玻璃杯倒吊着,一溜儿挂在宽条木头板上,木头板被四条粗铁链吊着,挂在吧台的正上方。酒柜上的灯是金色的,灼灼的,一溜儿排开,每个倒吊的大玻璃杯,此刻啜饮了全部光的精髓,创造出了虚假的灯火辉煌。我们坐的卡座,离灯有点远,甚至有点暗。可老范说刚刚好。酒吧里的人还不太多,在台子上,有个女人坐在高脚椅上,两手抱着麦克,唱着一支外国歌,远远地,在散台的另一头,更暗的地方,走进来一个女人,黑头发,黑的羊毛长裙,看不清面孔,她好像要把自己隐没在黑暗中,她挑的是一张更暗的桌子。没有理由的,我觉得我认识她。随后我笑我自己,这个城市的漂亮女人总是大同小异。
老范为我点了一杯叫做莫吉托的鸡尾酒,看着胖乎乎的老范费力地把嘴巴瘪下去,两边撑开,再嘟起来。我咬了咬嘴唇。老范说:“洋名真他妈的拗口。”我才悄无声息把笑声放出来。我发现,小李笑得有点勉强,好像有什么心事。果然,等那首歌一唱完,小李就抱歉地说,他不得不回去了,老板刚来微信,店里太忙了,需要人手。我也站了起来,小李奇怪地看着我說:“你有病啊,又没叫你去,还想干活啊!”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老范变得很高兴,他大着嗓门说:“对,对,你不用去。”我站着不动,说回去我还有点事。老范说:“你是总理,日理万机啊。”我还是站着不动,小李有点急了,他说:“要不然我跟老板说说,你回去,我在这里跟范哥喝两杯。”老范一抬手,对小李说:“走,走,你快走,我们青青才不回去干活呢。”我只好坐下来,心想,再坐一会儿,等那个女人再唱一首歌,我就回去。
台上的女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注意到她穿的也是一条黑裙,一字肩,只是裙尾好像被撕碎了一样,一条一条的。我不由得想起另外一条黑裙。这次她唱的是一首老歌,《白天不懂夜的黑》。那是我高中时,循环过无数遍的歌。那时我迷恋一个男孩,他没有正眼看过我,最后他去了北京,上名牌大学,而我来到海滨,端盘子,从始至终我们都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有时候人们以为远离了过去,但其实过去根本不会走远,它长年累月、屏声静气地藏在我们身体里,一首歌就能把它召唤出来。“青青,青青,”老范在轻声唤我,我从过去抬起头来,看到一双亮得异常的眼睛。我偏了偏头,想把这不舒服的亮避开来。“喜欢这里吗?”我点点头。女歌手转过身去,把黑瀑布一样的长长头发、浓浓感伤,留给台下的我们:“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月亮的盈缺。”我突然发现手被攥住了,原来是老范,老范大着舌头说:“青青,跟哥好,哥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再也不用给人端茶倒水了。”顿时,有好多苍蝇从我身上爬过,我一边往出拽自己的手,一边急急地说:“你放开你放开。”老范压低嗓音:“你再喊,就把人喊过来了。等我把话说完。”看我声音低了下来,老范说,他每周两次去烧烤店,不是为了那些油腻腻的烤串,就是为了看看我。不用费力,我就回想起老范在小小烧烤店里,皱着眉头,哈着气,一口啤酒一口肉。那时他的眼里根本没有我,心里也一样没有。老范在撒谎。老范看我不说话,以为我被他说动了,就腾出一只手想过来搂我。我趁机把手拽出来,抓起包往外走。老范还在叫我。走出几步远,我听到老范在我背后扔下一句话:“臭跑堂的,还不识抬举。”晚上吃的牛排,五成熟,现在从胃里翻上来,那首歌只剩下最后一句“不懂我伤悲,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里边还亮如白昼,出口这边已经豁然暗了下来,这个城市的夜晚已经毫无悬念地过来了。白天确实没法懂夜的黑。我抬脚要钻进夜色里,突然觉得有人在拽我,我心里一紧,回头一看居然是丽影。披肩发,黑裙子,一件淡紫色的斗篷大衣松松地披在外边。原来我没有看错,这个城市也会带着促狭的心情,让人们在各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巧遇。
“看着像你,怎么走这么快,那个男人是谁?”
我一时千头万绪,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只好问:“你怎么来这了?”
“哦,我在等人。跟一个朋友约好了。”
也许是光线,我觉着丽影的脸突然白得怕人,不知怎的,我想起马戏团的小丑也有一张像这样白得过分的脸。我听到丽影笑着在打招呼,可我觉得她的笑比哭难看多了。我回过头去,看到了蔡姐。我说蔡姐好,可蔡姐眼里我就像空气,她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倒是她身后有两个粗壮的男人,好奇地打量着我。我听到蔡姐笑着跟丽影说:“怎么不玩了,这么早就回去?”外边的寒意争先恐后要从门外涌进来,我感受到了它们的心意,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丽影突然拉起我的手,夸张地说:“我和青青过来玩,她有事,我们就先走了。”临了,丽影说祝蔡姐今晚开心。我们还没有推开门,门就被挡住了。一个男人说,蔡姐想请我们今晚玩一玩,丽影要挣扎着出去,那个人只是抬了抬胳膊,我和丽影就掉转了方向,又回到了酒吧。吧台上方,酒杯倒悬着,不怀好意地露出一排排金灿灿的假牙。后边每个小方格里,都躺着一瓶酒,坏脾气的,好像要随时跳起来,把自己倒进一个人的嘴巴。我看见,我原来的座位上,在老范旁边,坐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老范攥着她的手。
丽影一直攥着我的手,蔡姐挑了最里边最暗的一张卡座,让我们坐下。她对侍应生说,她的好妹妹喜欢好东西,所以她要好好给妹妹点杯酒。蔡姐眼里没有我,她只对丽影说话。她说妹妹是来这里等人的吧,可惜这个人是来不了了。妹妹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我脑子里电光石火般出现了一个抱着胳膊抽烟的男人。丽影没有说话,她仿佛被定住了一样,只会两眼呆呆地看着蔡姐。
蔡姐拿起丽影的包看了看,有点不相信地说:“他还挺舍得呀。巴宝莉的最新款。”又探过身来,摸了摸丽影那件斗篷,“巴黎春天的皮草。”红酒上来了,只有一杯,蔡姐把它放在丽影前边,然后突然说起了巴厘岛。丽影好像有点缓过来,嗫嚅着说:“蔡姐,您好像误会了。”蔡姐现在也把她当成空气了,蔡姐点起一支烟,看着远处。“妹妹,蔡姐对你怎么样啊?”丽影不说话。蔡姐只是看着远处,慢慢地说:“我自问是个厚道人,尽量照顾你們,知道你们小地方来的不容易。”我知道蔡姐嘴里的那个你们,有一个是娄东。可娄东现在在哪里呢?他能像个超人一样从天而降,把我和丽影救出这个该死的地方吗?我知道他不能,就是他现在在这里,估计也只能像我一样,像一团空气一样傻傻地坐在这里。
“可你呢?你是怎么对姐姐的?”不用看,我也知道蔡姐是咬着牙把这句话说出来的。丽影想抬头说什么,蔡姐身后那个男人突然横过来,挡在丽影前面,我听到“啪”的一声。我说你们怎么可以打人,我想过去帮丽影,可我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了,另外一个男人把我按在座位上。端盘子的侍应生又过来了,他怕出事,蔡姐往菜单上放了一沓子钱,说换个浪漫点的曲子。丽影捂着脸,满脸都是泪,我想挣扎着报警,可我动不了。曲子换了,还是女声,一首外国歌。巴黎巴黎隔一会儿就出现在声音里。她每唱三个巴黎,我就听到“啪”的一声,我想喊,可我的嘴巴也被捂住了。我的眼里都是泪,泪眼朦胧中,我看到远处台子上,那个唱歌的女人,手里端着一杯酒,像只美人鱼一样,摇头晃脑,没心没肝地在唱巴黎巴黎。在这个曲子唱完最后一个巴黎的时候,蔡姐终于站起身来,让那个男人住手,然后蔡姐优雅地拿起那杯红酒,整个一杯泼在丽影的脸上。
这天晚上,雪花洋洋洒洒从天而降,就像女人手中的香粉,终于扑在这个城市的脸上了。新年的第一天就下了雪,随后整整一个月,天都阴着脸,满怀心事,始终不肯放晴。在回家过年之前,我想再去看看娄东。于是我推开了伊人发廊的门,发廊里异常安静,人们都看着我不说话,我想蔡姐一定来过了,一定热情周到地跟每一个人都打过招呼了。娄东看见我,眼睛里满满都是话,但他什么都没有说。我坐下来,突然耳边又响起了巴黎巴黎,我问这是个什么曲子,怎么就像鬼魂附体似的,走到哪里它都会跟着来。娄东告诉我这个女人在唱“我有两个爱人,故乡和巴黎”。然后他用叹气一样的声音,在我耳边轻声说:“女人的头发,要轻拿轻放,轻轻的。”“唰”的一下子,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再过几个小时,农历的新年就要来了。天始终是阴阴的。放好行李,坐在火车上,我的对面是丽影。火车压低了嗓音,匆匆跑过了一座桥。这座桥,是这个城市的门户,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经过这座桥时,火车是怎样昂首奋蹄、兴奋不已。透过窗户,看着这个城市慢慢后退的灯火,仿佛再一次听到火车进城时快活的嘶鸣。当城市最后一盏灯火无声熄灭时,坚硬的雪,如期而至。
【责任编辑】大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