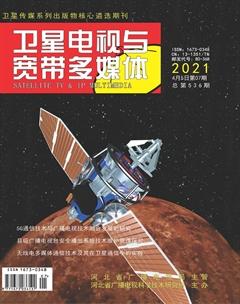分析罗伯特·布列松的导演手法与艺术风格
李圆

中图分类号:G2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07..084
“布列松之于法国电影,正如莫扎特之于奥地利音乐,陀斯妥耶夫斯基之于俄国文学。”——让-吕克·戈达尔
1. 背景
要想理解一個导演的电影作品,将他置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语境是十分有必要的。罗伯特·布列松是一位长寿的导演,在他1901-1999年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中,他几乎是见证了电影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尽管并不是与每一个阶段的轨迹都相交,但受到时代浪潮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罗伯特.布列松的导演生涯应该是从1943年执导的《罪恶天使》正式开始的,于是我试图梳理出时间线,将布列松导演的电影放于时代框架中去找寻其受到的影响。
二战期间,布列松被关入德国集中营,在那里认识了勃里克柏杰主教,他的电影从此刻开始就展现出了天主教思想。由于他做过战俘的人生经历,他对人生与宗教的思考在他的电影中可见一斑。精神救赎是天主教的核心,于是在《罪恶天使》《乡村牧师日记》中都充斥着包容、宽恕、哲学思辨的意味。
新浪潮反对传统电影,强调电影是一种个人的艺术创作,要求电影从传统艺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受到新浪潮的影响,布列松在这个时段的电影《死囚越狱》《扒手》已形成了一种属于自己的风格,布列松电影的简约之力逐渐凸显。
60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不仅注重个性化,还倾向于精神探索。我个人认为布列松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比如《驴子巴特萨》,全片以一头驴子为主角,通过人们在这头驴子面前的失调不安与强烈情感来表述电影的中心思想。同时段的《穆谢特》,现实主义的意味更加浓烈,通过少女穆谢特的遭遇,来表现人们对待与己无关的挣扎灵魂的时候的冷漠,以及这个社会贫瘠的关切。
70年代出现了一批新美国电影,其中讽刺电影和异类电影大多都是揭示关于人和环境的现实真相,在这个时段,布列松导演了《可能是魔鬼》。同时,也有一批关于身份认知的电影涌现,布列松的《梦想者四夜》也在进行发问。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总是在无休止的彷徨与幻想中,爱的异化和意志的普遍沦丧让人活在幻象中。在80年代全球电影创作与反抗中,布列松的《钱》应运而生,这部影片通过道德的传染性,来表达布列松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2. 导演手法
2.1 声音造型
在布列松的电影中,人物对白非常少,在表现人物形象和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的时候,他更愿意用画外音和内心独白。在《乡村牧师日记》中,布列松采用大量内心独白用来表现年轻牧师复杂迷茫的内心世界。用一本日记,用一个人的声音在银幕上刻画牧师细腻隐秘且孤独的内心活动,同时,大量的内心独白也深刻揭示了年轻牧师内心情感与现实关系的纠葛,当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时,他也有过挣扎,但是最后他选择坚持自己的信仰。试想,这种复杂的内心活动如果通过单纯的人物对话来表现会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但是用牧师内心独白来朗读他写下的字句时,观众们就会置身于牧师的世界里,分享他的孤独、迷茫、释然和坚持。
同样,布列松对音乐的使用也是少之又少,他觉得音乐的加入必定会转移观众的注意力,一个成熟的导演不需要音乐去弥补画面上的不足。比如《穆谢特》里基本没有什么音乐,只在片尾出现圣歌,这段圣歌在影片中被穆谢特哼唱过两次,一次是学校音乐课上被严厉的老师强行摁在钢琴前逼唱,另一次哼唱是安抚性侵自己的人。所以当穆谢特严肃冷静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后这首歌再次响起就充满了特殊的含义,像解脱像释怀又像是对神性的回归。
但是布列松十分重视音响。他并不是简单的收集环境声动作声或者是背景声,他的一片嘈杂一片宁静都精确到位而且富有含义。比如死囚越狱里面最后方丹深夜逃走 整个监狱应该是特别安静,但是布列松加大了有轨电车的声响,而且根本没有出现有轨电车的画面。我觉得布列松是在用一个无源音响来帮助方丹逃狱。也许这个声音是客观存在的,也或许这个声音是布列松臆想出来强加给监狱看守或所有观众的,但归根结底目的就是掩盖住方丹逃狱的动静让一切合理化。同时音响在这里也变成了一个起象征和隐喻作用的写意符号自由,外界的声音此时正是方丹内心最需要的声音,声响越大他内心对自由的渴望就越强烈。类似这样的音响处理方法在他的电影里有很多,他会结合画面加入特定环境下的特殊音响,让他们不再只是单纯的环境声,他电影中的音响往往会冲破电影画框的限制,直接冲击着观众的内心。
2.2 模特理论
布列松把自己影片中的人物扮演者称为模特儿,以区别通常所说的演员。在他看来“演员”是剧院的产物,而电影需要的是“模特”。“模特只是一张脸而已,要彻底抹掉他们自己的愿望。以是代像。把他们纳入你的规划之中,他们任你摆布。”所以我们在布列松的电影里看到的人物永远都是克制到极致,甚至有些许的僵硬呆板。“模特儿”没有强烈的情感外化,也没有刻意的表演痕迹,如《可能是魔鬼》中游走在巴黎街头的青年如同一具行尸走肉,映射着战后核威胁笼罩下惶恐不可终日的精神状态。布列松提供他的身份,他所面临的困境,甚至是他的思想,但又始终克制着人物的情态和动作,以“外在的机械化”表现内在的精神的流动。
2.3 简约的画面与剪辑
简约是出发点,单纯是终点。布列松曾说道:“许多情况下,事物之理本来没那么复杂,只是人们太容易被事物纷乱繁复的外表迷惑而无法看透其本质,才经常陷入盲人摸象式的无休止论争之中而难以自拔。更多情况下,理无须论,只须或只能在切身实践中去用心发现和感悟,然后再应用到实践中去。”在布列松的著作《电影书写札记》中也不断的在表明他追求简约的态度:“我因觉得太简单而扔掉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和最应挖掘的东西。蔑视简单的东西是愚蠢的。创造不靠增添,而靠削减。展示一切必沦为滥调。”
当其形式纯粹,艺术才强而有力。布列松追求“精炼纯化的艺术”,反对电影是综合艺术这一说法。布列松的镜头专注度非常高,他只给你他认为最必要的,剩下的需要观众自己去填充。布列松曾引用帕斯卡尔的一段话说“一座城市,一片田园,远看是城市和田园,走近之后看到的却是房屋、树木、瓦当、树叶、草地、蚂蚁、蚂蚁的腿以至无穷。”布列松習惯将眼前的事物拆解成碎片,然后按照自己的审美观有意舍弃某些碎片,有选择地表现某些碎片。不难发现,在他的电影中,常有特写镜头,他说“模特,浑身是脸”。通常情况下,人的脸是最有表现力的,但有时身体的其他部位可能比面部更有表现力。
3. 艺术风格
3.1 真实与非戏剧性
布列松说“到达心中的真实已不再真实,我们的眼睛太爱思考太过聪明。两种真实:摄影机原样记录的原始真实;我们看到的被我们的记忆和错误的估计歪曲的所谓真实。”提到真实,一定就会涉及主观和客观的问题。布列松提出“视像”这一说法:将你的毫不相干和最不相及的画面联结起来的难以察觉的关系,这就是视像。布列松主张摒弃画面的概念,用视像取代。主观视像与客观描述之间存在着极其微妙的辩证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同一事物两个无法分割的面。他更喜欢传达自己的主观视像,强调感觉、印象、直觉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强调电影艺术从感觉出发,并非完全否定描述,而是以此为出发点,以超越原始现实,追求隐藏在现实表象之中的真实。
他的影片没有什么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一切都很平实,布列松也不设置悬念或惊奇效果,甚至在行动开始之前就透露出失败的必然结局。布列松用这种非戏剧性的手段,将观众的注意力从外部的事件冲突转移至人物内心受到的冲击和震撼。“压平我的影像如熨过一般而不减弱他们。”“所有这些效果你可得自一个影像或声音的重复。”所以在《穆谢特》中,布列松运用规律性的重复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意境,许多画面都出现了两次甚至以上,包括穆谢特向女孩们投掷土块、男孩们对穆谢特的羞辱、家中不断哭闹的婴儿等等,重复的手法包含一种超越个体的沉重感,重复的背后实则暗含着灵魂不断变幻的历程。
3.2 超验美学风格
字面意义上理解,超验即超越一般的感官经验,既不同于先天形成的能力与认知,又不同于后天实践中形成的经验,超验描述着超越先验与经验的某种神圣或理念自身。最完美的超验艺术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在电影创作中,超验风格常倾向于显影一种自我牺牲的叙事母题,透露出对信仰合理性的怀疑与评判。
死亡始终是布列松处理人物命运的注脚,母题的反复重现是克制的、深沉的而非宣泄的,这保持了观众对银幕的距离感,反思艺术表现的社会泛文本。似乎在他的世界里,生命的消殒连通了悲凉的现实和诗意的栖息,因此具备对社会现状的最优解。比如电影《钱》,布列松同样以辛辣的笔法讽刺资本主义世界金钱至上的处世准则,在这套腐朽准则的运行下道德的崩溃、人性的毁灭和死亡的发生变得异乎寻常地容易;而冲破资产阶级规则、打开新世界的秘钥在哪里,他却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他总会在影片的结尾处,作为对外部世界的重新审视,暗示万物的同一性。在《乡村牧师日记》中是那个十字架的阴影,《死囚越狱》中则是那条黑暗街道的长镜头,方丹和若斯特在街上渐行渐远,而《扒手》则是米歇尔入狱时的面孔,《圣女贞德的审判》则是燃烧的刑柱。
很多时候,布列松想表达的内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的一句话相契合:“学会承担,将自己犯过的罪别人犯过的罪一并承担过来,自知所有的罪过都该由你负责。”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布列松:《电影书写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