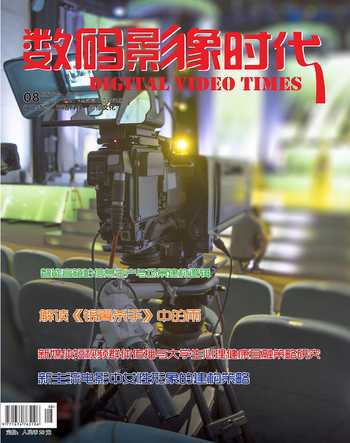Z世代在虚拟情境中的自我呈现
田王佳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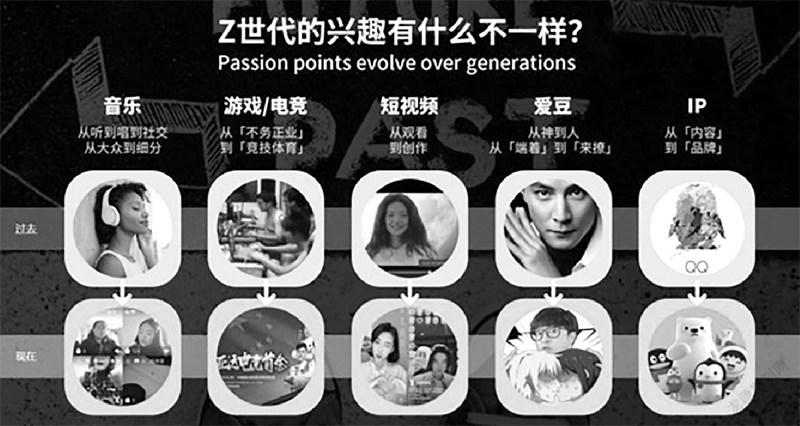

编者按: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社交阵地从线下转移到线上,长期沉浸在线上虚拟情境中的Z世代也在不同平台展现出不同的自我呈现特征。此篇文章通过对15名Z世代用户进行深度访谈发现,Z世代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很大程度上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并作为宁芙式的拟生命体存在,且自身成为了不自察的异化者与数字劳工。
研究背景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70.4%,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6亿。
随着网络的发展,自我呈现的情景也从线下的面对面交流变成了线上交流,自我呈现的概念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有了新的解读。网络不但创造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生活场景的表演舞台,更对个体在网络环境中的形象呈现、行为模式、互动方式等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在网络环境中改变了获得自我认知、建构身份的方式,“自我呈现”的内容更加丰富、策略更加多样、内涵更为深刻,所获得的结果与人们的动机、目标更为接近。网络不仅仅是为“自我呈现与建构”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也显现了“自我呈现与建构”的真正的内在含义。
在正兴盛的互联网平台中,微信、微博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虚拟情景。自2011年1月面世以来,微信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移动运营商的联系方式,用户量直线上升;微博作为另一种大众社交媒体,同样有着很高的用户活跃度;与此同时,带有社交属性的电子游戏也获得了许多年轻用户。因此本文将虚拟情境拆分为三种有代表性的媒体平台:微信、微博与电子游戏,横向对比不同具体情境中自我呈现的异同点,综合分析伴随互联网成长的Z世代在虚拟情境中自我呈现的特点。
研究发现
本文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与15位在三种虚拟情境中均拥有深度体验的Z世代进行了交流,并对访谈结果进行了编码整理,得出了以下结论。
社交需求与拟剧理论的典型呈现
“Life is like a big stage, each person has his own role to play.”
早在16世纪后半叶,莎翁便将人类的悲欢离合置于剧院舞台这一小方天地,人类的个人行为、社会行为、与他人的互动等一系列的真实都被一幕幕戏剧所展现。到了20世纪,戏剧的基本思想也被许多社会学家应用到社会研究领域,其中,戈夫曼在1959年撰写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书中戈夫曼认为社会中的人就像是舞台上表演的演员,利用各种道具——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等,在观众面前努力地去展现自己的形象,进行表演,由此在人们心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在当下互联网的语境下,先进的媒体技术为在线选择性自我展示提供了越来越宽广的平台,千禧一代随着互联网一起成长,热衷并精通于在虚拟情境下进行表达。在虚拟情境的自我呈现中,表达被强化,流露被弱化,这使得95后大学生对于自己的形象更加具有控制力,而在不同虚拟情境之下,他们呈现出了稍显不同的自我形象。
通过访谈结果可以得出,对基于强关系的社交平台微信,Z世代更愿意把它视作个人前台去进行展示,精心选择图片或文字进行表达,目的是社交、塑造自我形象、寻求他人认同等等,并且会进行实时的审查。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使用时,在很大程度上期待着他人的回应,这一方面体现了人的社会性,“没有人能够独自生活,人们不只在需求和照应方面是相互依存的,而且在他们的最高官能即人类心智(human mind)方面也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人类社会,人类心智便毫无用武之地。”“同伴对于思想者(thinker)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表达着他们期望自己所呈现出的形象能够为人认可,就如康德所说的,“我们从每一个他者那里寻求赞同,因为我们被一个所有人都共有(common)的理据所鼓舞。”康德把“共享判断”的这一理据(ground)称为“共同感觉”(commonsense),而且康德认为这种共同感觉并非一种私人化的感触,而是“一种公共感觉”(public sense)。为此,他们会小心翼翼地选择呈现内容,注重表达的连贯性(expressive coherence),并且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而微博则被他们视作更偏向于后台的区域,他们在微博上的表达更加自由,个人情绪体现比较极端,面对公众事件又显得平和,舆论参与的欲望逐渐下降,从表演者变化为观众,并且他们之中大多数希望微博能够继续维持一个“后台”的定位,让他们暂时从舞台上退下来,稍作休息。
作为消费社会产物的社交平台自我呈现
在访谈之外,很容易发现Z世代群体的泛娱乐化倾向较普遍,文化对于他们而言不再是文化本身,反而成为一种娱乐,一种快消品,例如名人逝世时微信朋友圈常见的爆款哀悼类推文,微博对于断章取义或杜撰的历史故事的众多转发,游戏《王者荣耀》对于历史名人的消费都随处可见,95后大学生对此也早已习惯,更是参与其中,对于文化内涵一知半解,却乐于跟紧“潮流”,附庸风雅一番以凸显品味。在阿伦特生前出版的著作中,对判断最充分的说明,可以在收录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文化的危机:这一危机的社会及政治意义”一文中找到。在“文化的危机”一文中,阿伦特的分析基础是对物(文化对象)、价值(交换价值)、消费品这三者所作的区分。文化品(cultural goods)的固有尊严源自它們是“物”,它们是“世界的永恒不灭的附属物”,“文化品的优异性,是由其抵御生命进程的能力衡量的”。这样的文化对象被18—19世纪“好社会”(good society)中的文化市侩主义(cultural philistinism)贬损为“价值”,因为受过教育的欧洲中产阶层将其作为交换价值,用来换取社会地位的提升。随之兴起的大众社会又带来了新的发展:作为交换价值的文化遭到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对某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即娱乐的关注。所谓“大众人”(mass man),就是按照“他的消费能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判断的无能甚至辨别的无能”,还有“与世界严重且毁灭性的疏离”而被定义的。娱乐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消费品”,连同其他一切在一个劳动社会(laboring society)中被生产和消费的东西,都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过程”必需的组成部分,只要满足了它所服务的目的,它就立即被消费掉。阿伦特相信,劳动社会的消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对文化的威胁要小于“好社会”中的市侩主义,因为消费主义要的就是娱乐,对文化并不做什么,因此不会像市侩主义那样对文化造成侵害。另一方面,通过一种无所不包的功能化过程(functionalization),文化最终也被纳入到消费社会对娱乐的需求中。
故而,尽管大学生们在各类平台上分享着有关文化的内容,将自己呈现为文化人,把自己塑造为文化艺术的信徒,他们也很难证明自己追逐的是文化,而不是阿多诺所说的“文化工业”。当平台上的诸位把文化当作追逐热点的工具,作为展现自己的途径,“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我们所追逐和热爱的“文化”似乎只是工业,而此行为同时损伤了文化本身。
作为宁芙式的拟生命体存在的社交平台展现
除了传统的拟剧论提出的表演形式,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一种新型品味表演形式——文本表演,其实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利用数据进行的表演,一种“宁芙式存在”。大学生在社交账号上分享听过的音乐、读过的书,又或者在游戏中穿上一套炫酷的装备,以显示独特的品味,鲜明的自我,而最终,这些都是由数据构成的表演。正如南京大学哲学系蓝江教授在《电子游戏世代的存在哲学》一文中,以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经写过谈影像的著作《宁芙》拿来作喻,“宁芙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尤其在面对今天的电子游戏世代时,宁芙成了我们打开理解电子游戏的存在哲学的一把关键钥匙。宁芙没有魂魄,它们只有躯体,它们用独特的魅惑来吸引人的进入,一旦有人与它们结合,原先那个没有魂魄的身体便有了灵魄,在它们的世界里可以自由地驰骋。“电子游戏中,我们不是将自己的意志直接上传到游戏世界的角色中,而是它生成了一个不同的生命状态,一个既不同于NPC,也不同于我们的意志直接体现的状态,我们可以将这种生命理解为‘拟生命’”,除了文中提到的电子游戏,社交账号又未尝不是一种拟生命,它们原先是无生命无灵魂的,当被账号背后的人注入各种个性化的数据,才变得鲜活起来,成为一个个鲜明的个体,并且,当他们在利用各种数据进行表演时,他们本身完整的自我也被打碎成了零散的数据。社交平台上所呈现的那个“自我”,对于使用者而言,便是宁芙式的存在。该平台上的“自我”,有“我”的形象,过着“我”的生活,但是只要我不登上那个平台,不对其进行操作,那这个“我”就像是没有灵魂进入的宁芙,不管在现实世界还是数据世界,都不能够自由驰骋。
不自察的异化者与数字劳工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沉迷于微信、微博和游戏的大学生们正被自我异化为数字劳工和一种审美层面的景观。他们认为一切选择都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是我选择在各个平台上去创建一个“我”,而我对于“我”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然被这些平台或是数据运作逻辑牢牢困住。他们会在朋友圈更新自己的动态,展现出或乐观或超脱的形象;在微博上追逐着热点,不时刷新热搜榜生怕自己被热点和潮流所抛弃;他们玩着游戏,每天去签到完成任务,不敢中断一天,为了晋级付出自己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是的,可能到这一步你也会说这是我自己选择这样去做的。但是让我们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思考一下,你确定你是自己选择这样做的吗?游戏设计出种种环节与机制,你但凡不听它的规定,平台上的“你”就会输给别人一些。微博上的“你”不发一些带有热点的内容,浏览量就大大低于别人。朋友圈的“你”不精心打造自己,“你”寥寥无几的赞仿佛就在嘲笑你和“你”——现在你还认为自己苦心孤诣做出的选择是自己的选择吗?是的,我们大部分都是被这些平台的商业逻辑和运作逻辑所裹挟,才做出了所谓的“选择”,而事实上从我们选择进入这些平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根本就没得选择。
而这些我们为这些平台所做的事情,我们每一次追逐的热点,一次次的点击,一次次的操作,不仅在顺从他的商业逻辑与产品逻辑,更大程度上,我们自己变成了平台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工,我们用自己的时间为他们创造热度,使平台了解我们的喜好,把我们统称为“大数据”,并用此盈利,而我们还相信着,我是上帝一般的用户。我们用普罗米修斯式的奉献度与投入度实现着自我异化。
“从这一刻起,游戏者走入了一个别人(非游戏者)的世界并被这个世界所囚禁”,“这种过度追求虚拟的自我实现等也使人们对游戏目的追求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功能。”从此可见网络游戏对Z世代群体的异化,或许我们应该时时谨记迈克尔海姆的忠告:“虚拟世界可以威胁人为经验的完整性……我们需要学会时不时地抑制虚拟实在。无限多样的世界呼唤心智健全,呼唤与现实的联系,呼唤形而上学的基础。”
结语
本研究发现,Z世代在不同虚拟情境中自我呈现的特点有所区别。他们把微信作为前台,表演精致的自我,并严格地自我审查,而在微博中却从时常从表演者化为观众,并且一定程度上希望微博维持一个“后台”的定位。除了拟剧论提出的表演形式,互联网也催生出了一种利用数据进行的表演,一种“宁芙式存在”,而数据的积累与存储的区隔影响了他们的表演“场地”与“道具”。
除此之外,Z世代在社交平台上的自我呈现带着消费社会的特征,同时也是消费主义的一种产物,文化于他们而言似乎成为一种用于塑造形象的快消品。同时,当人们沉浸于虚拟世界中不亦乐乎时,已然成为了平台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工,成为异化的人,这是值得我们警惕与反思的。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在京发布[EB/OL].https://www.isc.org.cn/zxzx/xhdt/listinfo-40203.html,2021-7.
[2]马忠君.虚拟社群中虚拟自我的建构与呈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06):139-141.
[3]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藍江.在美杜莎与宁芙之间——论阿甘本的图像理论[J].文艺理论研究,2015,35(06): 61-68.
[5]Boyd D.Material Virtualities: Approaching Online Textual Embodiment[M].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03.
[6]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7]伊曼努尔·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廖宏建.网络游戏对人的异化——兼论游戏的本质[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359-362,420.
[9]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10]童慧.微信的自我呈现与人际传播[J].重庆社会科学,2014(01):102-110.
[11]董晨宇,丁依然.当戈夫曼遇到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与表演[J].新闻与写作,2018(01):5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