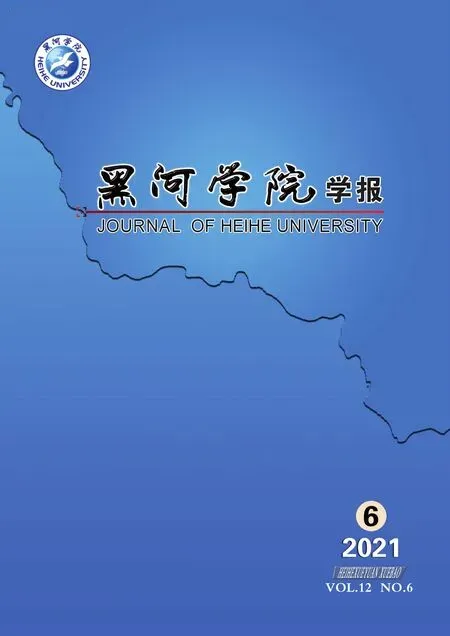唐《李纲墓志》考释
赵静静
(西华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一、李纲墓志全文
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
大唐故安康郡太守李府君墓志铭并序①出土时地不详,据云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出自赵文成等编: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724。。
太宗之爱季曰司徒霍王元轨,王之五子曰南阳郡公,讳纲,字友正。在童儿之岁,有成人之姿,太宗器焉,特拜赞善。奇表日角,庆流天池,禀东平之风,袭河间之训。太妃之薨,执丧泣血,时议比于柴参。差其贵贱,鲁愚之不及也。明矣服阙,以旧官兼金州别驾,无贵骄色,有清白名,转襄、滑二州别驾。即彼三州,政其一贯。坐陈蕃之榻,佩王祥之刀,谋臧于身,行彰有后,厥德孔懋,惟善乃愆。戾发亢龙,舋萌砂鹿。高宗厌代,后氏弄权。窃大象以罔天,执严刑以虐国,竟归汉相,旋绝赵王。朝拜五侯,痛海内之凌主;林凋一叶,知天下之皆秋。垂拱初,配流梧州。公窜南闽,王从西蜀,道路咸怨,士庶同嗟,炎州非养德之乡,瘴海是谪居之地。在奔波际,晤得丧门。所造必安,虽远无愠,谦以自牧,本重衣冠,信以与人,何必蛮貊。闻新室铸升,听非刘而王,自料覆巢,岂全遗卵!乃信轻帆、乘偏舟,跣足投林,髡首入洞。均其嗜欲,必顺于土风;揣其进退,无违于游处。是以宅薮者,分排楯以护之;居岛者,积储峙以安之。练气以存真,保和以含道。思返魂于旧里,乃积骨于异乡,莫知其年,但纪其坎。洎国人诛吕,代邸兴龙。日月重光,存正昭洗,赠金州刺史。嗣子志悌,茹荼疚心,衔痛沥血,南驰万里,傍讯数州,神谓其居,是谕其志,启藤公之室,归皇孙之灵,哀哉!以开元三载,自远而界乎临汝郡。宅兆未臧,权殡于彼。夫人巨鹿魏氏,故太师徵之孙,豫州刺史叔瑜之次女也。生此德门,嫔于贵邸,候鸡鸣以盥嗽,肃奉天人;诵螽斯以谦和,克事君子,衣不曳地,饭才脱粟,娫姒允和,舅姑推美。王门仰其正,妇道由是闻。南阳窜流之时,夫人配入宫掖,势应永误,方指及泉之期;释不苟存,岂复下山之望!幼探释教,精信无生,冀百灯以剜身,持一香以焚顶。俨示凝,寂怛化,葬宫人茔,莫知其所,哀哉!卫巫莫测,越觋徒占。生也长辞,竟乖同穴之礼;死而有作,应藏异室之冤。之魄何从,招魂自古。以天宝三载五月四日,迁厝于京兆少陵原之阳,招夫人以合祔,礼也。孝孙幼成等,考龟蓍,审阡陌,启杜原之穴,窆皇孙之櫬。不有志也,曷以明孝孙之心乎;不抒父亡,曷以明亡父之德乎。式刊贞石,以表幽邃。铭曰:
圣嗣三代兮化洽四方,宗社几坠兮公亦亡父。南子北兮行路伤,幽囚亟放兮罹百殃。殄莽屠禄兮归我唐,冤魂旅榇还旧乡。列植松槚兮苍苍,信既远兮言亦章。嘉声不陨兮德实良,厥有后兮犹子臧。龙剑分兮何时同,马鬣开兮庶事无。生人之恨斯为丰,已焉已焉,徒趍公子之下风。
正议大夫行中书舍人侍皇太子及诸王文章集贤院学士吕向撰
二、唐宗室霍王房世系及其相关问题
霍王李元轨在《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记,乃高祖李渊和张美人所生。两《唐书》均载,“霍王元轨,②《新唐书》载“高宗厌代,后氏弄权。”诸王有匡复之志,起兵征讨,霍王李元轨及其长子李绪也参与其中。兵败后,“杀霍王元轨、江都郡王绪及殿中监裴承光。”据《新唐书》的说法,兵败后李元轨和李绪直接被杀害。但《旧唐书》却有不同的记载“(垂拱)四年,(霍王李元轨)坐与越王贞连谋起兵,事觉,徙居黔州,仍令载以槛车,行至陈仓而死。”因此,兵败后李绪被杀,而李元轨被流放黔州,流放途中而死。志文载“公窜南闽,王从西蜀,道路咸怨,士庶同嗟,炎州非养德之乡,瘴海是谪居之地。在奔波际,晤得丧门”公指南阳郡公李纲,王指霍王李元轨,可知二人被流放至不同地方,李元轨被流放至西蜀,西蜀即黔州之地。此事记载与《旧唐书》相吻合,可知李元轨兵败后未被杀害,而是被流放,途经陈仓而死,可证《旧唐书》记载不误。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艺,高祖甚奇之”[1]2429。“(贞观)十年,改封霍王”[1]2430。李纲即为霍王之子,唐高祖李渊之孙,可谓出身显赫。
1.唐宗室霍王房世系
李纲是唐代皇室成员之一,《旧唐书》《新唐书》甚少有相关之记载,①《旧唐书》《新唐书》均有《李纲传》,所记李纲字文纪,观州蓚人也,乃隋及唐初人,非本篇墓志所载之李纲。通过两《唐书》对霍王李元轨的记载,可从中窥略其子李纲的行迹。《旧唐书》简略记载了霍王“有子七人。长子绪,最有才艺。”[1]2431除了霍王长子李绪,并未提及其他子嗣,因而无法了解李纲的相关信息。而通过《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可知霍王李元轨有“六子”,这六子分别为:江都郡王李绪、安定郡王李纯、胙国公李绰、南阳公李纲、南昌郡公李绚、山阳郡公李绎。而从《新唐书》宗室世系表的排列顺序来看,李纲为第四子,第五子为李绚,而且《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载“绚,以霍王元轨第五子继”[2]2059,第五子李绚过继给了彭王李元则。根据墓志所述:“王之五子曰南阳郡公,讳纲字友正”,霍王的第五子乃李纲是也。该墓志为玄宗时吕向所撰,距离李纲所处时代不远,且李纲为宗室之子,关于其家室的记载必详尽准确,由此可证《新唐书》霍王房世系记载有误,李绚非霍王第五子,李纲乃霍王第五子。而两《唐书》中关于霍王子嗣为六子或七子的记载,经查其他史料,并未发现其他史料佐证,暂且存疑,故通过此方墓志足可校补《新唐书》宗室世系表的缺误。
2.嗣霍王的身份
李绪作为霍王李元轨的嫡子,本应承袭嗣霍王,但因“重拱中,坐与裴承光交通被杀。”[1]2431直到神龙初才与其父李元轨同时追复爵位,李晖作为李绪的后人被封嗣霍王。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李晖为李志顺之孙,李绪的曾孙。然史料对嗣霍王李晖的记载较为混乱,主要集中在嗣霍王李晖是李绪子或孙的问题上。《新唐书》载“神龙初,并复官爵,以绪孙晖嗣王”[2]3554,《旧唐书》载“神龙初,与元轨并追复爵位,仍封绪孙晖为嗣霍王”[2]2431,《册府元龟·复爵》记“封绪孙晖为霍王嗣”[3]3331。两《唐书》《册府元龟·复爵》均以李晖作为李绪之孙载入史册。而以同书《册府元龟·承袭》却载“封绪男晖为嗣霍王”[3]3209,同时《唐会要》中“(封)故霍王元轨长子江都王绪男晖为嗣霍王”[4],以李晖为李绪的之子。
由上述史料可知《册府元龟·复爵》和《册府元龟·承袭》前后记载互异,李晖在史料记载中有两种不同的身份:一是两《唐书》和《册府元龟·复爵》均记载嗣霍王李晖为李绪的孙子。二是《唐会要》《册府元龟·承袭》记载李晖为李绪的儿子。查《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可知,安定郡王李纯的继子李志直、胙国公李绰的继子李志廉、南阳郡公李纲之子李志悌、南昌郡公李绚之子李志谦、李志暕,李绪的子侄都为“志”字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李绪下的嗣王李志顺也是“志”字辈,嗣王李志顺概为李绪之子,李晖在辈分上非“志”字辈,作为嗣霍王的李晖只能为李绪之孙。而《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显示李晖为江都王李绪的曾孙,此处概为排序之误,应上移一栏,见表1。

表1 校补后之霍王房世系

表1(续)
3.李元轨、李纲父子的婚姻
“李唐皇室望出陇西,其不仅门第清贵,亦权位无双,故为诸多士族之理想婚姻对象。对皇室而言,联姻士族不仅可获社会势力对政权的大力支持,也可消解潜在的政治威胁和敌对情绪。”[5]皇帝经常通过赐婚皇室成员、下嫁公主等政治行为与臣子进行连姻。李元轨作为皇室成员之一,与大臣魏徵之女的婚姻亦不排除是出于政治考虑而联结的姻亲。
“太宗尝问群臣曰:“朕子弟孰贤?”魏征曰:“臣愚不尽知其能,唯吴王数与臣言,未尝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为前代孰比?”对曰:“经学文雅,汉河间、东平也。至孝行,曾、闵不能过。”魏徵“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1]2547,魏徵称李元轨为吴王,李元轨在(武德)八年(625),徙封吴王。”“(贞观)十年(636),改封霍王”[1]2429。可知李元轨被封吴王的时间是武德八年(625)至贞观十年(636)间。他称赞李元轨有汉代皇室河间、东平二王之遗风。根据墓志记载李纲“禀东平之风,袭河间之训。太妃之薨,执丧泣血,时议比于柴参”。李纲以孝事母,且深袭其父间、平之风。根据史书和墓志对李元轨父子的书写,彰显了李氏良好的家风门风。正因李元轨与魏徵常有交往,了解李元轨堪为所托。在李元轨为吴王时得到太宗亲自赐婚,“诏纳征女为妃。”[2]3553太宗和魏徵作为双方的尊长,拥有着决定婚姻关系的权力,主导着这场婚姻,亦是为了笼络臣下,平衡政治的一种手段。
南阳郡公李纲“夫人巨鹿魏氏,故太师徵之孙,豫州刺史叔瑜之次女也。”魏徵之子有四:即魏叔玉、魏叔琬、魏叔璘、魏叔瑜。魏叔瑜即魏徵第四子也。而霍王元轨的夫人是魏徵之女,即魏叔瑜的姐姐或妹妹。根据此篇墓志,李纲所娶的是叔瑜的次女,魏徵的孙女。那么,李纲和夫人魏氏为同一辈分的表兄妹或表姐弟,可能是奉双方家长之命而成婚的。李氏和魏氏两代联姻并非出于偶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所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6]李元轨和夫人魏氏、李纲和夫人魏氏的婚姻概为政治、家世平衡后的产物。
三、李纲的仕宦问题
志文记载李纲“在童儿之岁有成人之姿,太宗器焉,特拜赞善。”李纲在幼年时深得唐太宗的喜爱,被授予赞善一官。《唐六典》载“皇朝贞观初,改太子中舍人为中允,位右庶子下,而中舍人复置。龙朔二年(662)改曰太子左赞善大夫,咸亨元年(670)复为太子中允,而左赞善大夫仍置。”[7]664唐太宗时将太子中舍人改为中允,在高宗龙朔二年(662)太子中允改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可知赞善大夫一职为唐高宗时所设,而墓志记载唐太宗时就授予李纲赞善一官,令人不解。笔者认为,唐太宗授予李纲的应为太子中允一职。其根据如下,太子中允和左右赞善大夫都为太子府属官,皆为五品官。太子中允设于大唐贞观初,“改太子中舍人为中允,置二员。……中允掌侍从礼仪,驳正启奏,并监药及通判坊局事”[8]826。左右赞善大夫设于龙朔二年(662),“置左赞善大夫,替中允;置右赞善大夫,替中舍人。咸亨元年(670),中允、舍人复旧,而赞善大夫别自为官,左右各五人,皆掌侍从翊赞,比谏议大夫。”[8]826中允掌“侍从礼仪,驳正启奏”,与赞善大夫“侍从翊赞,比谏议大夫”的职司相比,二者职责大都相同。导从和驳正之责主要由左庶子执掌,“中允为之贰”[1]1909,作为副长官的中允,只有协从之任。因此,在玄宗时期,中允或已成为一个闲置的空职,并无实际作用。太子中允和赞善的执掌、官品无太大差别,对处于玄宗时期的吕向来说,太宗时太子中允一官的侍从和驳正劝谏之责已为赞善所替代,因此,撰者吕向就将太宗时中允写作赞善。但李纲在童儿时就被太宗赐予中允一官,但考虑到李纲的年龄,孩童之年是无法担任此官职的,因此,太宗恩赐给李纲的太子中允一官只是个虚衔,“用来寄俸禄(类似宋代的寄禄官)、序品阶、定大朝会的班秩等等”[9],太子中允用来给幼童时的李纲分发俸禄,而且“唐人做官必须有官资”[9],太宗授予李纲官职,不仅为其创造优渥的物质条件,还为李纲进入仕途铺平了道路,显示了太宗对皇室成员的恩典和优待。
李纲的仕宦经历相对较为简单,“以旧官兼金州别驾,无贵骄色,有清白名,转襄、滑二州别驾,即彼三州政其一贯。”李纲的旧官除了赞善外,未提及其他的任官经历,旧官或指太宗朝曾任的太子中允一官。以旧官去出任金州别驾,可知李纲未执行太子中允的职责,实际职务是在金州担任别驾,更证旧官为虚衔。李纲以旧官兼金州别驾,因吏治清白,后转襄州、滑州别驾,可知李纲的仕宦生涯主要是三任别驾。唐代对别驾时有废置,李纲生活的时代是在太宗至武后垂拱时期,现将这一时期有关别驾废置的史料排列如下:“《武德令》,上州别驾正五品上。二十三年为长史,前上元年,复置别驾,定入从四品也。”[1]1794“上元二年(675),诸州复置别驾,以诸王子为之。永隆元年省,永淳元年复置。”[2]1317“垂拱初,又置别驾员”[7]743。
由上可知别驾的设置时间主要是武德元年(618)至贞观二十三年(649),上元二年(675)至永隆元年(680),永淳元年(682)至垂拱初(685)三个时期。志文未提及李纲任别驾的时间和年龄,若李纲任金州别驾在武德元年(618)至贞观二十三年(649)这一时期内,此后转任襄、滑二州别驾,考虑到李纲的年龄,在太宗时就转任三州别驾不太可能实现。且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高宗即位,改别驾皆为长史”[2]1317,贞观二十三年(649)至上元元年(674)已经废除别驾,若李纲已在太宗朝转任三州别驾,其后定会迁转其他官职。但墓志中并未提及李纲的其他官职,可见,李纲并未在武德元年(618)至贞观二十三年(649)间担任金州别驾。
金州是唐代的上州,《新唐书》载“金州汉阴郡,上。本西城郡,天宝元年(742)曰安康郡,至德二载更名。”[2]1033襄、滑二州在唐代是望州。因李纲“有清白名”,从上州到望州任别驾,官职实际上是升迁了。《旧唐书》载:“内外官从见任改为别官者,其年考从日申校,百司量其闲剧,诸州据其上下。进考之人,皆有定限,苟无其功,不要充数。功过于限,亦听量进”[1]1824。唐代“凡居官必四考”[2]1173,官吏凡四年一考,官吏的升迁也有一定的年限。李纲中清白科后,先后迁转襄州、滑州别驾。迁升需要年限,永淳元年(682)已处于高宗统治末年,而武后垂拱初李纲就被流放。在永淳元年(682)至垂拱初这三年时间内无法实现三州之间的迁转。
别驾自废除后,高宗在位期间一直未予恢复,但上元二年(675)复置别驾,与当时 的权力斗争有关。“上元元年,高宗号天皇,皇后亦号天后,天下之人谓之‘二圣’”[2]81,高宗和武后共同摄政,武则天的“天后”称号是进一步争夺权力的敲门砖。此后发生了“上元年间向高宗逼宫的事件,导致太子李弘之死。这是自麟德元年(664)上官仪事件以来,在改变政权现状上又一次严重的政治斗争,其结果是高宗进一步被架空,忠于李唐体制的势力受挫。”[10]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武后的势力越发强大。以皇族任别驾很可能是武后的授意,“前上元年,①唐代有两个上元年号,一为高宗,一为肃宗。《新唐书》有“上元二年,诸州复置别驾”的记载,因此,前上元指高宗上元年间。复置别驾,多以皇族为之。”[8]911别驾职责“以贰牧之事”[8]911,协助州的长官州牧处理州内事务。“大抵上佐品位颇崇,虽有‘通判列曹’‘纲纪众务’之名,但无具体职务。”[11]武则天为大肆揽权采取了“虚尊其位”的手段。将别驾由原来的正五品上,升为从四品。提高别驾的官品,任用李纲这样的皇族子弟担任别驾,表面上彰显皇室身份及对皇室成员的优待,实际上是为了扩张权力而将皇室成员调离政治中心。因此,李纲任别驾的时间应在上元二年(675)至永隆元年(680)这一时期。
李纲死后赠金州刺史,而志文却称李纲为“大唐故安康郡太守李府君”。唐于“武德元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8]888,可知志文中的太守即刺史。唐代安康郡本为西城郡,由玄宗天宝元年改名而来,均属金州,二者异名同地。李纲夫妇于天宝三年(744)进行合葬,吕向撰写志文应在此时,天宝元年(742)金州治所已改为安康郡,故称李纲为安康郡太守。
四、李纲夫妇的安葬事宜
垂拱年间,武则天得政,将王室宗臣“外示尊宠,而内实图之。”[2]3551霍王李元轨被尊为司徒,毫无实权,逐渐被调离政权之外。后越王李元嘉以“太后必尽诛诸王”而起事,兵败自杀。霍王坐尝与越王通谋,举家流徙,李元轨、第五子李纲及夫人魏氏均因此事变而丧命。直到神龙革命后,霍王一房冤雪得昭,诏“韩王元嘉、霍王元轨等自垂拱以来皆遭非命,是日追复官爵,令备礼改葬,有胤嗣者即令承袭,无胤嗣者听取亲为后。”[1]137这才对离乱中死去的宗室霍王一房备礼改葬。魏氏作为李纲的夫人,霍王李元轨的儿媳,也得以备礼改葬。志文记叙“窜流之时,夫人配入宫掖,……怛化葬宫人,茔莫知其所”。李纲窜流南闽时,夫人魏氏没入宫掖,茔不知其所。《旧唐书》载:“凡宫人有疾病,则供其医药,死亡则供其衣服,各视其品命。仍于随近寺观,为之修福”[1]1871。近年出土的大量唐代宫人墓志,①唐代宫人墓志约151方,见陈丽萍.《亡宫八品柳志铭并序》发微[J].北大史学,2014。这些宫人或有官品、或陪葬陵寝,均有品秩。李纲夫人魏氏表明既为宫人,但死后不知茔之所在,可知魏氏自没入宫掖直至死亡,始终是一个没有品秩的宫人,因此,死后不知茔之所在。
作为死生之大事的丧礼体现着传承孝道、团结内部宗族的重要理念,“气感而应,鬼福祸人。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12],古人认为父母子孙同心共气,以“孝”相连,子孙通过“考龟蓍,审阡陌”的方式择墓选地,表现出对丧葬事宜的极大敬重。唐代颇为盛行招魂作为中国丧礼中的一种特殊丧葬仪式,在《大唐开元礼》载有招魂的具体做法,“复于正寝。复者三人,皆常服。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东,当屋履危,北面西上,左执领,右执腰,招以左,每招长声呼某复’,三呼而止,以衣投于前,承之以箧,升自阼阶,入以覆尸。”[13]此外,招魂葬的方式在民间颇为常见,在张籍的诗亦有所表现,“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14]。对于战死他乡的普通兵士,或囿于财力,或失其葬所,故亲人只能通过招魂葬来使死者有归。这样的情况常见于唐代墓志中,在《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蜀王府长史索府君墓志铭并序》中,妻子王氏早先亡故,权厝于饶州,因“岁月淹久,寻觅不得”[15],故采取招魂来合葬。鉴于李纲在流放途中死去,夫人魏氏失茔地所在,故“以天宝三载五月四日,迁厝于京兆少陵原之阳。招夫人以合祔,礼也。”李氏子孙由于不知茔之所在,为追求同穴之义,使魂有所安,故对李纲夫妇进行招魂合葬,符合儒家“死则同穴”的教义。
《大唐故安康郡太守李府君墓志铭并序》这篇墓志为了解志主皇族成员李纲的生平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此篇墓志对唐宗室霍王房的世系作校补,墓志所记李纲为霍王李元轨五子曰南阳郡公,李纲之子李志悌、孙李幼成,可补校《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之阙误。另外,高宗上元年间将别驾正五品上升为从四品,并任用李纲这样的皇族子弟担任别驾,表面上彰显皇室身份及优待皇室成员,实际上是武后为扩张权力而将皇室成员调离政治中心的谋略。从李纲的三任别驾的仕宦经历可窥略武后政治手腕的高明,并了解高宗武后时期皇室成员的情况。此外,李纲和夫人魏氏的表亲婚和招魂合葬等,有助于了解唐人婚姻和丧葬习俗。因而对《李纲墓志》的考释,为研究唐代的婚姻、仕宦、丧葬习俗等问题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