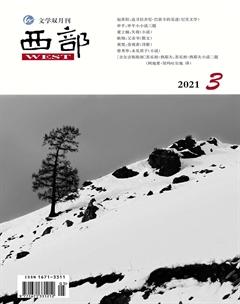蜀地散篇
干海兵
来世不再做棵女贞树
经历一冬,这两棵长得高大粗壮的树,叶子落光了,一丝不挂地站在茶店乡李家湾村的一个山坳里。三月的阳光和煦,四野寂静,我仿佛听见了两棵树生机流淌的声音,它们袒露在早春空气中的器官,高亢而微微颤动。
这两棵树,一棵是黄连木,一棵是油患子。
我想说的并不是它们,而是被它们拦在身后的女贞树——这是一株葱茏得有点发闷的树,叶片残破,身躯佝偻,那蓬严实而呆滞的绿荫不知道绿了多少个冬天,上面积满灰尘鸟屎,枝杈间没有掩严的部分,漏出惊慌的闪电般的白光。在这荒山野岭,方圆数里不见人户,可女贞树的脚下却躺着几块残碑,上面蛇痕蛛影,字迹隐约,看了让人背心发瘆。看这棵树上新钉的牌,树龄已经三百多岁了,和旁边的黄连木、油患子一样。
当年青青葱葱地把它栽在这里的主人,恐怕已经轮回了几回,但这棵树还在坚持。秋天它不落叶,冬天它不落叶,仿佛穿着厚厚的衣服,生怕不怀好意的黄连木和油患子窥伺到它的秘密。《本草纲目》中对女贞树的命名有所释义:“此木凌冬青翠,有贞守之操,故以贞女状之。”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也专门点到“欃檀木兰,豫章女贞”。看得出来,女贞树的秘密不仅与女人有关,更与中国传统男人关心的贞操有关。在民间,关于女贞树的演绎就更多了,比较经典的一个是:古代有个叫贞子的姑娘嫁给了一个农夫,两人虽家境贫寒但感情甚笃。哪知婚后三月丈夫便被抓去充军,一去三年,音信全无。贞子整日思念丈夫,以泪洗面,茶饭不思。一天,前线带来消息,说她的丈夫不幸战死,贞子终于倒下,临死前叮嘱亲人在她的坟头栽一棵小树,并交代说,如果此树四季常青,便是她对丈夫的情意永世不变。那棵树便是女贞的始祖。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来看,那棵女贞估计不是幽居于茶店镇李家湾村的这棵,幸好是这样,不然这棵树下残损的碑文,我又得好好去考证。
一棵女贞树活到三百多年,便会有些巫气,尤其是一年四季不动声色地绿着,那些朝云暮霞、潮涨水落、星移斗转都与它无关,这得活得多累啊。我的家乡,地处川康边地的荥经,那儿的女贞树似乎有巫气,怨气还很重。每年清明过后,斑鸠应约而来,一大群一大群地在树杈间腾挪跳跃,嘀嘀咕咕个不停。到了七八月,女贞树果子熟了,哪怕再瘦骨嶙峋的树杈都举着一串串殷红的小炸弹,似随时准备往过路的人头上扔。仅仅几天,那棵女贞守护的小路就会血迹斑斑。关于这种树,记得我故去的老外婆曾经讲过一个龙门阵,昔年吾乡有家穷得叮当响的邻居,在独子七岁大时,便替他娶回了一户更穷人家的女儿做童养媳,那小女子命苦,才九岁多就大人一样栽秧打草、养鸡放牛,而且又吃不饱,顿顿是玉米糊糊。小女子打起了野果的主意,什么沙棘子、刺泡、地果子、桑泡等等。有年夏天,她家茅草房外的女贞树结果结得早,而且颗粒饱满如小葡萄粒一般,小女子一口气摘了一筲箕,连吃了好几顿,最终拉肚子夭折。这个龙门阵在今天仍让我有所疑惑,一是女贞果味道偏苦她如何吃得下,二是我了解的女贞果的药效,几乎都是益大于弊,如何单她吃了就丢了命?直到最近,我才从相关药书上看出了端倪,《本草经疏》记载:“女贞子,气味俱阴,正入肾补精之要品,肾得补,则五脏自安,精神自足,百病去而身肥健矣。”《本草述》中说:“女贞实,益血……并以淫精于上下,不独髯须为然也,即广嗣方中。”原来,女贞的功效大多是针对男人的。
一棵被赋予性别色彩和伦理标记的树,难怪要活得很累。它长在路旁,先生们会津津乐道地讲起绿叶后面的故事,它结出果子,医生们会赶紧采下来给男人养精固血。只有中国早期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刘索拉,在一部叫《女贞汤》的长篇小说中替它说过话:“这药(女贞汤)可灭妇人虎豹之心,斩其尖牙利爪,散其眼中凶光,抽其丹田壮气,造出个淑女佳人来。”我知道因这深沉的寓意,女贞树的果子才充盈着殷红的、一触即淌的血。
过松州
那个黑红脸膛的汉子,跟着阿訇陪我们在寺内走了一圈,偶尔插话,脸上也是喜气洋洋的。从他厚重鼻音的普通话里,我听出了宁夏西海固的味道,也想起了那满坡的胡麻和土豆。与松潘的回族人相比,他的鼻子仿佛更钩一点,眼瞳更褐一点,脸膛上堆积着黄河故道上的阳光。
最先进入松潘的回族人,估计经过了几代人的接力,才穿过河西走廊,从瓜州、肃州、甘州、凉州、兰州,最后到达了大山深处的松州。回族人来来去去,在古城留下了两座著名的清真寺,一座历史早一些的,叫城关清真寺,一座稍晚一些的,叫真北寺。那个黑红脸膛的汉子就在我们参观的真北寺功修并兼管着寺庙的重建。参观完后,他送我们出来。站在一棵把天空挑得又高又蓝的大树下,他说我们面前的那条马路,是从成都通往兰州去的,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从成都来或者从兰州来,这条流动着盐巴、茶叶、果蔬,甚至冷兵器和炮火的小路,会在松潘打上一个结。这些结和西去的草原雪山有关,也和南下的河谷隘口有关。唐太宗时期,松赞干布信心满满地遣使长安求亲,没想到使者走到松州便被州官扣下。藏王一怒之下兵出雪域,二十万人与唐王朝决一死战。仗,松赞干布最终是打输了的,求亲最终居然也是成了的,松州的古城墙见证了这段坚硬而柔软的历史:不会说藏语的文成公主和不会说汉语的松赞干布之前连面也没有见过,但他们的爱情故事一千多年后被人镌刻在松州古城的城门口,常常使南来北往的人驻足沉思。公元789年,又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发生在松州,成都女校书薛涛被宠主韦皋发配到川西北边关,这个素来锦衣玉食的交际花夹杂在贩夫走卒中,沿岷江河谷饥一顿饱一顿地挣扎了半个多月,当她泪眼迷离地看见古城门口“松州”两个字时,她的《十离诗》成了,现代松州城内与爱情有关的景点也成了。
松潘就像是岷江留在历史记忆中的深邃漩涡,它汇集、沉淀,兼容并蓄。在松潘的几天里,我们这些成都来的小文人,几乎夸张地对遇见的每个人提出各种各样所能见到和所能想到的关于民族文化的疑问,而他们对答中的从容和平淡,常常让我们有感于自身的浅薄。在松潘,我和多年前写诗赞颂过的藏族美女Z同行半日。她气质温润冲和,有汉儒气韵,谁也不会想到她家族三代在松潘、黑水、马尔康的带血的跌宕传奇。与Z一样,松潘市井、山野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一段与这片山水血脉相融的故事。为我们开车的师傅,平头阔腮、肚大体肥,黑黝黝的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让人误以为是草原来的财大气粗的藏民,其实他是纵横川主寺几十年的汉族袍哥后代。每一段血脉的延续都有精彩的故事;为我们一行充当着导游角色的两个女孩,一个是羌族,一个是藏族。羌族妹妹的成都话比成都人还地道,但她在松潘一下汽车,舌头便在松潘藏羌汉和土话间任意转换,如鱼得水。藏族妹妹卓玛在车上向我们谈起,她在成都的房子里如何种花种草。但在一次观赏松潘马术队表演时,卓玛脱口说出她是红原安多藏族,十多岁就在辽阔无边的草原策马驰骋——這个美女,经历过什么样的雪山草地,经历过什么样的起承转合,她才从奔放不羁的马背上下来,贤淑安静地坐到我们身边。
面对古城墙上长着箭痕和青苔的砖块,除了安适地坐在街口阳光下清理虫草的阿妈和木门前闭目抽着叶子烟的老汉,谁还能看见时光背后的道路?现今的国道213线车水马龙,一辆辆旅游车从松州城外呼啸而过,那些挎着照相机的游客,足不着地小半天便将松赞干布、薛涛走了一千年的路走完。松潘的野性和坚硬,在大染缸一样的迷蒙历史中变得舒缓而安详,这里的天空依然高远纯净、朝霞如火、落日熔金。不同族群的村寨鸡犬相闻、炊烟彼此缭绕。
又见向峨
中峰寺很小,只有一间简陋的大殿和一排低矮的厢房。庙子里好像也没有和尚,只有几个整天忙忙碌碌的居士婆婆。
庙子虽小,仿佛却是有些来历的。据向峨乡文化站的同志介绍,这古刹大殿中的两根长两丈粗五尺的大柱子,是马桑树做的,颇有典故。蜀地马桑难以成材,歪歪倒倒长个一二十年,也不比粗藤子好多少。这家伙生命力极强,田间地头,崖畔谷旁,只要有手掌大的泥土地,便会妖妖娆娆地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用马桑树做大殿柱子,这的确是要有点想象力才行,其一这马桑为灌木,好多长到手臂大就已经垂垂老矣,其二马桑枝干含水较多,容易变形,山地农民用它来做锄头把子都嫌不成器。想来想去,能让马桑“登堂入室”的只有传说了。在西南地区,马桑树被古代先民意化为太阳神树扶桑,主要象征便是通天,传说上古时期的马桑可以齐达天庭,有不少寻道求仙的凡人因此走了捷径。另一个传说是,后羿射日,借助了马桑树曾经高大的枝干,惹恼了天帝,以致马桑树遭到天谴成为永不成材的杂树。
中峰寺的大柱子是不是马桑,已经不必再由林木学家去考证了,只要它屹立在那儿,庙子就不会倒,古蜀神话就会一代又一代地流传,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最令人惊讶的是,5·12汶川大地震,这个距震中不足百里的老旧建筑居然未伤筋骨,梁还是梁,柱还是柱。
离开中峰寺,带着一脑袋的疑问,驱车前往十几里外的向峨乡观景台。仲夏,盆地的湿热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而减退,在茂林修竹间穿行,干净清爽的水泥山道蜿蜒而不逼仄,三两户农家白墙灰瓦,鸡鸣犬吠,一片生机。到了观景台,只见山下云蒸霞蔚,那隐隐约约的绿波是阶梯一样铺向平原的龙门山余脉,植被太好,村庄农舍都成了绿的漂浮物,斑斑斓斓,煞是好看。听向峨乡陪同的同志介绍,5·12地震之后,灾后重建的几个居民点集中选址,按照城市化标准建设,以往散居在山林河口间的农民们按村社集聚,既有效整合了土地资源,也避免了地质灾害的侵扰。在观景台下方,是向峨乡上万亩的猕猴桃种植基地,时近六月,叶碧连天,有小风吹过,满山满野在太阳下荡漾着粼粼波光。
因为一场千年不遇的大地震,隐于深山的向峨乡终于为人所知。记得彼时,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滚动播出的救灾新闻中,向峨乡在屏幕上跳跃的数字令人揪心,满目疮痍的画面让人抓狂。2008年5月14日,我和诗人胡马驱车百里,载着几箱应急的药物奔赴向峨乡,刚穿出都江堰城区,便因前方道路垮塌被执勤的交警拦住,药物就近放到了帐篷区。一年之后,我应朋友之邀去都江堰看灾后重建,看完聚源、二王庙后,朋友提议到向峨走一走,这次终于上到了半山腰,看到了大工地一般的乡场。站在集中埋葬地震遇难者墓地的十字路口,汽车、三轮车、电瓶车往来穿梭,肩挑背扛的向峨人忙忙碌碌地建设着新家园,脸上终于有了点喜色。
其实,从地理和交通条件来看,向峨算得上是都江堰极具发展潜力的乡镇,山清水秀,空气优良,适合开发新型农业和打造新农村旅游。据乡政府的同志介绍,最近两年,有上海和成都的房地产开发商相中了大山中的几个地块,主题公园和避暑山庄的建设已在火热进行中。向峨乡莲花湖附近的一个大型高端地产,定位为都市后花园,理念前卫,规划完善,其销售价格已远超都江堰市区。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就像几千年前种下马桑树,搭上登天梯一样,勤劳智慧的向峨人懂得运用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发展经济、重造美好生活。
又见向峨。在休闲的步伐中细细品味它的每一段传说,欣赏它日新月异的变化,体味它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的确和前两次的向峨之行感受大不相同。在向峨乡采风快结束的下午,热情的东道主邀请我们到茶山小坐。山风徐来,暑热尽去,一根根在茶水中飞翔的通灵之叶似翅膀,扇动着文人骚客的遐思。此情此景,让我忍不住对同行的都江堰文友说,这么有故事的向峨乡,我下次还会再来的。
富乐游仙
绵阳城东北有座不太高的山,终年草木葳蕤,远观如胖乎乎的多肉植物。听游仙区的诗友介绍,该山名富乐山,号称“绵州第一山”。就这么个放在我老家的大山中最多算婴幼儿高的土丘居然是“第一山”,简直令我吃惊不小。绵阳坝子虽多,境内的山不可小觑,我去过的北川、平武,重峦叠嶂、雄奇浩莽,记得早年参加过一个到白马王朗的文学采风活动,有位文友在连续的爬山中竟然虚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莫非这小小的富乐山上有神仙?据葛洪的《神仙传》載,蜀中八仙之一的李意期修真之处便是富乐山。当然,另一个与李意期有仙道交集的名流更确立了富乐山“绵州老大”的地位,这人便是入蜀即反客为主的刘备。汉建安十六年,刘备怀揣张松偷献的地图,在本家、益州牧刘璋为其举办的百日接风酒会上,登上东山(富乐山)不算高的高台,雄顾蜀中盛景,竟失态地惊呼:“富哉!今日之乐乎!”
富乐山因刘备而得名,游仙区在富乐山下,游仙人在山前山后发掘出不少蜀汉标记的文化遗迹:汉皇园、蒋琬墓、姜维营。周末假期,悠闲的市民信步个把小时,便能在历史与现实中完成穿越。想想一千八百多年前,刘皇叔虽初具龙形,目力却断不可能达到百里千里,其视野中的富乐之地估计就是今天的游仙、涪城一带。涪城自不必说,已经连续几年位居四川县级地区经济三甲,而富乐山下的游仙,GDP增速更是雄踞绵阳十四个区县第一。既富且乐,便是神仙过的日子。记得几年前到绵阳参加迎春诗会,越王楼华灯高照,小广场里且歌且舞、百姓熙来攘往。我以为是诗会主办方有意组织的,一问,方知天天都是这样。“仓廪实而知礼仪”,游仙区近年来着力打造的惠民富民工程中,和谐文化元素的巧妙嵌入几乎无处不在,乡村博物馆、道德墙、玫瑰山庄、千亩兰园……游仙的市民不仅口袋富足了,精神层面的追求也上了台阶。
公元725年,大诗人李白动了出川游历的心思,第一站到达的便是游仙。在李意期羽化的富乐山一带,谪仙呼朋唤友把酒问青天,留下了人生中的美好回忆。后来,绵州人民将他与入川也曾逗留此地的杜甫合祠纪念,修建了李杜祠。富乐山下文风盛,杨雄、司马相如、李商隐、高适、陆游等都曾先后在此吟诗作赋,遗下风雅诗句。中国浪漫主义文人的仙道情结,给予了富乐山缥缈悠长的历史想象力,唐代诗人薛曜的《登绵州富乐山别李道士策》是写给蜀中著名词人、也是道人的李荣的,他在诗中写道:“珠阙昆山远,银宫涨海悬。送君从此路,城郭几千年。云雾含丹景,桑麻覆细田。笙歌未尽曲,风驭独泠然。”诗中对岁月、尘世的洞明通透,颇有仙道之玄。据我妄测,此诗中的几个关键词一千多年来还隐现在游仙的风貌中:珠阙、银宫、笙歌;云雾、丹景、桑麻。游仙区位处涪江中游冲击坝子,天府富庶之地的铺介地带,阡陌纵横、河港交叉。每到晨昏,涪江云雾伴着炊烟在良田沃野中缥缥缈缈,一片祥和安泰的气象。地杰再加人灵,游仙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城市面貌的富华和堂皇,早在唐代,越王楼、子云亭等展示城市不俗财力的“地标建筑”便在游仙出现,而充盈着游仙人开放逸乐精神场景的兴会雅集更是绵延至今。
由于地处川陕要津,游仙人总是最先感受到中原文明对封闭大盆地的儒化。在当代游仙十大景点中,人文类竟然占了七个,儒雅的民风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取向,给游仙带来了勃勃生机。也不知道我当地的诗友闲时是否常常信步登上富乐山,是否也像先贤陆游一样写过“游东山”的诗句。陆游的诗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登山正可小天下,跨海何用寻蓬莱。
青天肯为陆子见,妍日似趣梅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