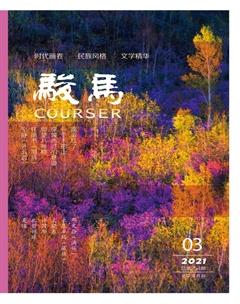雅漠营子是条船
海东升
1
哈斯巴根出事了。
刘方明的右脚背一麻。
手机从左手换到右手,大声地问:“哪个哈斯巴根?”
因为在雅漠营子,重名的人很多。在这里,叫巴图,巴特尔的多。叫“柱”的多,铁柱,巴柱,双柱,占柱,落柱。叫“剩儿”的多,为了区别开他们,人们往往以年龄来划分。老剩儿,大剩儿,小剩儿。叫小明的也多,人们也在说到他们的时候,前面加上定语,前街的小明,中街的小明,后街的小明。
刘方明来到这里一年多,在人名上下了很大一番功夫。
后街的哈斯巴根。
刘方明再次确定后,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一条船,这是雅漠营子的地形,一百二十户人家,停车场一般分为前中后三个区域。每个区域的每一户人家,刘方明都有编号。
坐标后移,停留在后街的东北角。天眼俯瞰,115号哈斯巴根。
刘方明的脑袋里像被针扎了一下。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刘方明最担心的就是他。今年刚刚脱贫的哈斯巴根,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要是倒下,返贫就是分分钟的事。
2
连着好几年,辽西春旱。
周围几个靠山地吃饭的屯子,人们愁得眼眉都打了结儿,动一动,绞得要掉毛。
而靠洼地过日子的雅漠营子,人们乐得眼角的鱼尾纹都绽开了线,每个汗毛眼里都汪着一圈笑。
过去的历史上,雨水都是多,泡得雅漠营子的老老小小,苦水一抖搂,溻湿一片地,而如今风水轮流转,也该让苦巴巴的洼子人抖一把威风了!
还没开年的时候,营子里仙得乎的瞎五就曾掐算过,说今年六龙治水,龙多四靠,非旱即涝。而去年冬天也没下过几场透亮雪,开春也仅挤过几滴泪,那不是明摆着旱吗?
这话还真打瞎五说的来了,人们眼瞅着别的村子的小苗出得屁嘣似的,稀稀楞楞,而雅漠营子的地里,小苗眨眼之时就罩了垄,又吹气似的一哄而起,嘎巴嘎巴抽节,噼里啪啦扬花,好一派丰收景象。
可谁知这死瞎五也掐捏不准,就在高粱睁眼,苞米白皮的节骨眼儿上,上界的六条龙却一下子搅翻了天,三天一大下,两天一小下。雅漠营子的人们乐了个大半截,提溜着的一颗心又和庄稼棵子一起,咕唧一下子坠到泥水里。人们又和往年一样,瞅准老天爷喘气的空当儿,急三火四地从地里往家“抢”苞米。
这天上午,是个难得的晴天,哈斯巴根赶着毛驴车,拉着一车苞米上了道。这驴蛋子牲口巴道,见着前面有车,四蹄撒欢地撵,哈斯巴根嘴里不住地喊着“吁”,可驴蛋子听都没听,仍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奔。道上坑坑洼洼,苞米在车上颠得哗啦啦响,哈斯巴根耳朵细,拿眼往后一溜,见几穗大苞米从车箱斗子里晃晃当当地往下栽歪,他忙连喊了几声“吁”,这毛驴子也不知是跑累了,还是心静了,竟顺从地停了下来。哈斯巴根屁股一出溜,两脚落到地上,回过身两手忙乎,把几个栽歪出来的苞米往箱斗子里插。
说来也该着,就差三两穗就完事了,可这驴蛋子真不是东西,连个瘪屁都没放,四腿一使劲,呼地启车就走。哈斯巴根哪有防备,紧贴车轱辘的右脚还没来得及抽出,车轱辘便“呼”地一下碾了過去,哈斯巴根疼得“啊呀”一声,咕咚一下坐到地上,眼泪都差点造出来了。他定神看了看,右脚面子没出血,却疼得钻心。哈斯巴根咬了咬牙,左脚着地,一使劲站了起来,右脚一着地,却软绵绵地不听使唤,他心想完了,脑子一蒙,咕咚又坐在地上。缓了缓,他往前瞅了眼毛驴车,车还慢悠悠地往前出溜,他连喊几声,毛驴顿了顿,蔫叽叽地停了下来。
哈斯巴根是条汉子,左脚一使劲,又站了起来,啪嗒啪嗒往前蹦,汗珠子啪啪往下落,他撵上毛驴车,手拄着车辕,往后一靠,一屁股坐到车沿子上,脸白得像一页纸。
车到院子里,瘫巴媳妇拄着拐,出得屋来,一看车上的哈斯巴根,眼直了:“他阿爸,你这是咋啦?”
哈斯巴根左脚着地,从车上下来,右脚仍是那样疼,他低头一看,脚面子肿得像个馒头,他停脚瞅一眼女人:“没事,车轧了一下。”
女人一拐一拐地凑到跟前:“他阿爸,这得让人看看,严重了可咋整?”
哈斯巴根说没事,仍是蹦到车边,一只脚着地往下扔苞米。女人一看,眼泪都下来了,一拐一拐地挪到街上,招呼来左邻右舍,人们找来营子里的红伤大夫一瞧,都叹了口气,哈斯巴根的脚背骨折了。
天黑了,哈斯巴根家却还没动烟火,送走驻村第一书记刘方明,三口人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也没言语。
停了半晌,哈斯巴根的儿子开口了:“阿爸,明个我不上学了,在家收苞米。”
哈斯巴根吧嗒一口旱烟,冲着儿子一瞪眼珠子:“你敢!”
儿子吓得一激灵,女人直了直身子,忙打圆场:“孩子也是替你着想……”
“替我着想,就该有出息。”哈斯巴根把烟屁股一扔,说:“念了一溜十三遭,到初三了想下来,要那样,我还供你干啥?”
儿子吭吭叽叽地说:“可地里的苞米?”
哈斯巴根又一瞪眼珠子:“扔了能咋地,过两天我就能下地。”女人心疼地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逞哪份子能,打发儿子去问问家族兄弟,看看能不能帮忙。”哈斯巴根点了点头,儿子忙不迭地出去了。
哈斯巴根拧开身边的收音机,里边的一个女人正在播着天气预报,哈斯巴根两口子越听越心里蹿火:今明两天,辽西地区还要有一场中雨。哈斯巴根听完,啪地关了收音机,边打嗨声,边拿纸卷烟。
烟刚点着,门吱扭一响,儿子垂头丧气地打外边进来,哈斯巴根两口子一下子明白了八九分,儿子哭唧唧地说:“都说没工夫,等收完自己的再给咱收。”
哈斯巴根把叶子烟一扔,脑袋差点沁到裤裆里。女人想了想,说:“求求辣椒书记吧,这孩子实诚。”哈斯巴根头都没抬,闷声闷气地说:“这年头人情薄,家族都不中,他,一个外地来的,咱就更别指望。”女人说:“你这人咋这么死性呢?人家刘方明自打去年来咱们营子当第一书记,可没少替大家伙办事,对咱家更是多看几眼,去年咱们营子种辣椒,人家刘方明跑前跑后的,咱们家日子有了起色,这辣椒可帮了大忙。我觉得求他,肯定好使。”哈斯巴根打个嗨声,说:“就因为第一书记没少帮咱们,营子里的困难户也不是咱们一家,更不好张口……”
3
驻村第一书记刘方明打哈斯巴根家回来,就觉得该帮帮哈斯巴根。这哈斯巴根是营子里的精准扶贫户,过去家里日子紧巴,三十好几才娶上个瘫巴媳妇,而哈斯巴根的要求亦不很高,说只要能将就个犊就中。这个女人也没让哈斯巴根失望,连着给他生了一女一男,且个个脑袋灵通,丫头上了高中,小子进了初三,个个名拔头筹,哈斯巴根虽说屋里地里一个人紧忙活,心里却也有个盼望,可如今这根顶梁柱一趴下,这十几亩地的苞米不眼睁睁地扔吗?
刘方明边想边走,自己是海军部队里的优秀艇长,转业到县里招商局,没少把沿海驻地的企业往县里招。前年,一个四川的战友把一家辣酱企业介绍给刘方明,带动了三个乡的老百姓致富。去年,县里派驻驻村第一书记,刘方明选了雅漠营子,因为这里的贫困户最多。在这众多的贫困户中,属哈斯巴根家最穷,人,也最倔。他家里地是不少,别的人家除了种苞米,还种花生。可哈斯巴根就是图省事,二三十亩地,全种苞米。这几年,天气旱,收成不好,苞米的价格也低得可怜,费劲巴力种了一年地,去掉种子,化肥,人工的钱,基本没有盈余。幸亏了刘方明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哈斯巴根也跟着种辣椒,要不,脱贫,哪有哈斯巴根的份儿。如今哈斯巴根摊上事,哪有不帮的道理。
回到村部,屋子里有孩子和女人的声音。刘方明很是纳闷儿。走到大门口,一个小女孩从门里跑出来,“爸爸”,女孩一边跑,一边喊,刘方明仔细一看,是自己的闺女诗雨。他赶紧弯下腰,抱起孩子,问:“你和谁来的?”
“我和妈妈。”刚拐进走廊,村妇联主任和另一个年轻女人从刘方明的办公室走出来。妇联主任快人快语,说:“刘书记,你看谁来了?”
刘方明仔细打量着那个年轻女人,他发觉,女人的眼角,又多了细纹。年轻女人被刘方明看得有些不好意思,笑着说:“不认识了,咋地?”刘方明经她这么一说,也不好意思起来。妇联主任是个精明人,在这种场合,最好的方式,就是撤退。她一边往外走,一边说:“弟妹,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多住几天,好好陪陪刘书记。我走了,缺啥少啥,尽管吱声。”
送走妇联主任,刘方明说:“你们娘俩儿咋来了?”
女人说:“我们不来,你也不回啊!”刘方明感到确实有些亏待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就说:“等我忙过秋收,就回去。”女人说,“不用等,这几天好好陪陪我们娘俩儿,就行了。”刘方明说:“可能让你失望。”女人的眼睛一圆,“还有事?”
“有。明天还得找人帮哈斯巴根家收苞米。”
“那后天呢?”女儿问。刘方明说:“后天,后天好像没事。”女儿一下子跳上椅子。“太好了,爸爸可以和我们玩喽。”刘方明说:“我领着你们娘俩儿,去看看西大洼,再爬爬骆驼山。不过,现在你们俩儿,自己在村部一左一右,溜达溜达,熟悉熟悉环境。”听刘方明话题一转移,娘俩儿几乎异口同声:“你还有事?”
刘方明说:“我去找哈斯乌拉合计合计明天的事。”
4
村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哈斯乌拉,也是一个立正人,和刘方明一样,都是三十出头,去年新上来的搭档。
听刘方明一说,便爽快地说:“刘书记,你放心,营子里的党团员干部划拉划拉也二十几个,紧忙紧赶,一天也差不多,你找前街的,我找后街的,明个天一放亮,在营子头集合。”
5
第二天,天一放亮,人们在营子头的大柳树下集合。刘方明一查,少了刘成,这小子在城里打工,这几天回来紧着收秋。刘方明呼哧呼哧跑到刘成家,刘成开着三轮车刚要出门,刘方明一边喘气一边着急地说:“兄弟,就差你啦。”
刘成不好意思地说:“刘书记,我不想去了……”
刘方明一愣:“咋,你可是答应了的?”刘成为难地说:“我得紧赶,人家催我回呢。”刘方明见他仍不给面儿,说:“党员说话就该算话,你听哥的,今个忙完哈斯巴根的,大伙明个帮你。”
刘成有点不信:“哥的话当真?”
刘方明说:“哥办事秃噜过扣?”
刘成说:“哥办事,碾唾沫成钉”。
“那你还跟我划弧?”
刘成说:“我不是探哥的口信吗?”
刘方明一拍刘成的肩膀:“你小子,心眼够多的,快走,大伙可都等你呢。”
哈斯巴根的苞米地在西大洼子,水排不出去,地头子汪着水,車进不去。刘方明让十几辆车都站在地头的大壕上,人拎着丝袋子,光着脚丫,进地里掰苞米。
地里闷热,苞米叶子刮到湿漉漉的脸上胳膊上,肉蜇得生疼,脚往前一动,泥从脚丫瓣里咕唧往上一钻,喷一脚面子,蚊子叮在脸上,啪地一拍,粘乎乎的一堆血。
刘方明和哈斯乌拉边咕唧咕唧地往地头背,边合计:“这西大洼子,非治治不可,上冬前,得把排水沟整上。”哈斯乌拉点点头:“排水站的家伙,也该修修了,把它们都待坏了。”
“还有人,一盘散沙咋行呢?咱们得搞个合作社,遇到事情,集体力量大。”刘方明想了想,郑重地说。
“就是。”哈斯乌拉说:“人心散,是咱们还没让他们拧成一股绳。其实,都上外面打工,也不是人人都能挣到钱,咱们这地方好好设计设计,也能守家在地挣大钱。去年咱们搞辣椒,也有人不信,可一见厚厚的票子,今年不就好干了吗?去年五百亩,今年就是一千亩,还不吸引人?”
刘方明说:“吸引人是不假,可咱们不能靠一条腿走路,这河滩地,我的老家也有。在咱们小时候那就是大甸子,河套里有鱼,苇塘里有鸟,有虾,我觉得种苞米就是整瞎了。前几天在乡上开会,乡长说一个在咱们这长大的人,在沈阳混大了,想回乡开养殖场,挖鱼塘,搞农家乐,当时我还没寻思到,今个在这一看,比哪都适合。一会儿我就给乡长打电话,把这个事应下来。”
哈斯乌拉心里没底,问刘方明:“不是我担心,你整辣椒我服,可这整农家乐,谁来呀?”
刘方明走到地头,把肩上的袋子放下来,说:“咱有咱的优势啊!你看咱们蒙古贞,条件也不比别的地方差,各有各的优势。人家山南有宝力根寺,人家新民镇还整个佛山寺,咱们没有海棠山的名气,可你忘了,咱们这有西骆驼山,还有靴底山呢,薛平贵征西在这歇脚,靴子底扔这了,你忘了前些时候,你爷爷给咱们讲的这些故事了?”
“可咱们这没名呀,人家能来吗?”
刘方明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咱们得找名人啊,把咱们省市县的大筆杆子请来,让这些名人在报刊上一宣传,还怕没人来?我都观察好了,这两年城里人都爱爬山,这隔三差五的就有人来爬靴底山、骆驼山,你忘了,咱们这骆驼山,虽说没有乌兰山高,可也七百多米呢!也是咱蒙古贞第二高峰呢!”
“哎,你还别说,经你这么一说,这戏有看头。”哈斯乌拉抹一把脑袋上的汗,边说边笑。“这是一招好棋,往这一摆,一棋定周边。你刘书记鬼道啊!”
刘方明听哈斯乌拉这么一肯定,底气更足了,“我寻思好了,这河滩上边,都种上葡萄树,那边的山坡地,咱们也别让它们撂荒,整上它五百亩朝阳大枣。到时候,让城里人有山爬,有鱼吃,喝羊汤,吃手把肉,吃地道的蒙古馅饼,钓钓鱼,摸摸虾,摘点有机葡萄,尝尝滚甜的大枣。来时候高兴,回去也不跑空,一个传俩,俩传三儿,还愁没有人来?”哈斯乌拉说:“是啊!到时候让哈斯巴根他们这样的脱贫户都入股,咱们的扶贫就不愁了。”
“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一件事。”刘方明说。“脱贫是目的,但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说过,雅漠营子就是一条船,要想让它跑得快,走得远,就要给它动力,我们要有常规动力,还要有核动力。我在核潜艇上干过,知道它的优势。像哈斯巴根家里的,营子里还有几个,我的一个沈阳战友,把满绣做大了,我想把他的分厂整到咱营子,让那些待着没事的妇女,在家就有钱赚。已经说好了,后天就来定盘子。”
听着刘方明和哈斯乌拉的想法,刘成几个都说:“你别说,经你们这一说,我们心里都有扑奔了,那还上外面去扯啥?守家在地的就把钱挣了,收完秋,我们就不出去了,你们该张罗的就紧着张罗,现在这事儿,你不张罗,就该让别的村整去了。”
刘方明说:“我这就给乡长打电话,把咱们的想法跟上边说说,把沈阳那个钱匣子留下。”
6
一拨一拨的大车小辆驶进哈斯巴根的院子,哈斯巴根的院子里堆起了苞米山。下午五点多钟,最后一车苞米也拐进了院子。
阴了大半晌的天边,太阳从云缝里钻了出来,天边一片火红。哈斯巴根家的院子红了,雅漠营子也红了。在这满天的霞光里,哈斯巴根一家子笑了,院子里的二十几个人都笑了。
刘方明的脑海里,雅漠营子这条小船,正动力满满,续航远行……
责任编辑 乌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