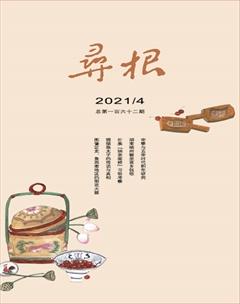尘土淹沉客,诗书梦寐身
叶隽
在现代留德学人中,颇不乏研究一些冷门绝学的学者,譬如陈寅恪、季羡林、徐梵澄都是走的研究梵文的路子,这是追究东方文化之根源;还有则是奔着西学渊源去的,譬如陈康(1902-1992,又名忠寰)。如今我们对西方古典学研究日益重视,像陈康这样的先行者应予以足够关注。
在学术史上,陈康为人所熟知的,是他那句常被转述的豪语:“要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这确实是让国人心神振奋的表述,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回到具体的语境中去,此语出自1942年时陈康为所翻译注释的《巴曼尼得斯篇》所撰的序文,他说:“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他应贺麟之邀请,参与了中国哲学会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的工作,该会由贺麟担任主席,翻译出版了一批颇为经典的西方哲学名著,包括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斯宾诺莎的《致知学》、鲁一士的《近代哲学之精神》等。贺麟与陈康都有留德背景,不过陈康一居十余年,而贺麟只有一年的光阴,但贺麟作为德国哲学专家,深知古希腊哲学的学术意义,他对陈康的工作也评价甚高,认为其是“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文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他的品格也很得认同,同为留德好友的朱偰称其为“谦谦君子之行,有邹鲁遗风”。
陈康在国外著述多署名陈忠寰,理解他在西方学术世界的浸润与学养形成,须以此为线索进行。靳希平这样描述他的学养形成:“他到德国跟尼古拉哈特曼读希腊哲学读得非常精通。当时在德国有一些崇拜希腊文学和希腊哲学的小圈子,包括现在大家知道的Gardiner应该也属于那个圈子。他们每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有一个教员和助教的小聚会,前两个小时大家不许说别的语言,只许说希腊语,两个小时之后才恢复说德语。他是在那个环境里熏陶出来的,他的希腊文化的学养跟我们今天喜欢希腊的人根本不可比。”(《作为西学根基的古希腊哲学——靳希平教授访谈录》,载朱青生、庄泽伟主编:《反思与对谈》,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这种后学追述,难免带上缅怀前贤甚至敬意言表的态度,但基本描述还是可信的,即正如洪谦之于维也纳学派那样,那代人确实能浸入式地落实到其时日耳曼学术的圈子里,所学确非一般。这里提及的是和德国学者的交往,譬如导师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1882-1950),還有此处未提及的其他老师,如斯坦策尔(Julius Stenzel,1883-1935)、施特鲁克斯(Johannes Stroux,1886-1954)等人。其博士口试考官除哈特曼、施特鲁克斯,还有施普朗格(Eduard Spranger, 1882-1963)。另一块不应忽略的是留德学人之间的友谊,蒋复璁在回忆录中提到:“我们及其他几位同学在德国的留学生之中形成一个圈子,大家都成了知交好友。如陈康(1911- ),研究希腊哲学,专攻柏拉图,能读希腊文,现居美国;张樑任,德文很好,钻研经济,得到Reel Politik的博士学位;朱偰(生于1907年)是朱希祖(1879-1944)的儿子,文笔极佳,写了不少文章,为才子型的人物……张贵永(1908-1965),研究德国史,他的博士论文《俾斯麦后的德国外交》十分有名。我们几个人常常见面,后来有几个返德进修的前期留学生,如学物理的叶挺生、姚玉泰两人,与我们的关系亦不错。那时我们还办了一个同学会,约定放假时一起出去玩,并决定这天不许说中文,一起练习德文。这段生活非常愉快。”(蒋复璁等口述、黄克武编撰:《蒋复璁口述回忆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这里关于陈康的生卒年明显是记错了,而且陈康的学术背景也更复杂,他早年求学东南大学,1929年先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哲学;1931年才转往柏林大学,其间转往哈勒大学随斯坦策尔进行研究,1935年才转回柏林大学,接受哈特曼指导。这一点也得到陈康自述的印证,他在论文中明确提及是受到斯坦策尔的激励而研究此问题的,“他将这项研究看作一项有历史合法性的任务”。
留德期间的朋友之交是大乐事,诸人均有记录,甚至有诗,譬如滕固这首诗中就提及陈康:
宗岱欣赏诵佳句,君培覃思作清吐。
从吾史余敦旧睦,慰堂巧啭遏云谱。
湘南学子檀文辞,雅典贤人缅往古。
惟有不才无赖固,猖狂磊落殊粗卤。
亦复风流檀词赋,我侪知己六七人,
多君周旋作盟主。
这里说的“盟主”自然是朱偰,而冯至有时也会做东;所谓“雅典贤人”,指的当然是研究古希腊哲学的陈康。
徐梵澄则更有直接写给陈康的诗:
牙签玉轴爨缥青,东壁昼梦花冥冥。
忽惊故人来在门,倒屣急豁双眸醒。
柏林忆昔初相见,谈艺论文有深眷。
握手今看两鬓霜,一十四年如掣电。
当时豪彦争低昂,各抱奇器夸门墙。
唯君端简尚玄默,独与古哲参翱翔。
自从不醉莱茵酒,世事浮云幻苍狗。
我归洞庭南岳峰,爱与山僧话空有。
君留太学恣潜研,关西清节同吞毡。
升堂睹奥已无两,急纾国难归来翩。
滇池定波明古绿,迤山翠黛螺新束。
南国春风蔚众芳,玄言析理森寒玉。
食羊则瘦蔬岂肥,广文冷骨颤秋衣。
不于市井逐乾没,乐道知复忘朝饥。
见君神旺作豪语,大业恢张仗伊吕。
中兴佳气郁眉黄,莫向蜗庐论凡楚。
这里的“古哲”注释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自然说的是陈康研究的专门对象。如此酬唱相和,让我们遥想当年情景,那代留德学人的文采风流、求知之乐、向学之诚,真是让人艳羡。在纳粹统治之下,战火纷飞之际,虽然难免有马革报国之情,却能在异邦继续沉浸在古典文化的世界里,这不能不让我们感慨知识世界的巨大精神力量和“道终不灭”的信念。徐梵澄研习梵文,以追溯东方文化之源;而陈康研治古希腊文,以探索西方文明之根。两者正可谓“东海西海”,也展现出那代中国知识精英求知于世界(此处首先是德国,德国学术)、探索文明根源的向学之诚,以及恢宏豁达的问道气度。
虽然诗中说的是14年,未必那么准确,但确实有10余年的光景了。最初陈康于1930年转学德国,在柏林追随异邦导师穷究西方古典之学(古希腊哲学),那时真是意气风发啊!朱偰、滕固、冯至等,都是一时英杰,我们或者也可以说,老天爷其实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只可惜时势动荡,让他们“千古文章未尽才”!在冯至居处花园里的那张合影正好说明了他们的“风云际会”。
陈康在德国期间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和翻译观,譬如他说:“凡遇着文辞和义理不能兼顾的时候,我们自订的原则是: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诚然是历史上已经验证了的名言,然而我们还要补充以下两句话,即:文胜其质,行远愈耻。汉、魏、六朝的著作前人已目之为文章之衰:这可以为我们这两句话作佐证。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绝对避免矫情动俗的伎俩;凡变通言词于义无碍的时候,则我们即放弃‘不雅‘不辞的直译。”[陈康:《序》(1942年),载柏拉图著:《巴曼尼得斯篇》,陈康译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从这段论述来看,陈康有着自己的翻译观,是知学之士,绝不是那种泛泛而谈、蜻蜓点水的“学术混子”可比。陈康形成了良好的学养,无论是对翻译问题,还是对研究对象都有独到的自家见地,这点也表现在陈康对希腊哲学、学术、思维方式的整体认知上,譬如他追索希腊人科学知识之所以能形成,并迥异于其他民族,其根本原因在于好奇心:“希腊人见到日月的起伏、盈、亏,宇宙的形成,二至的更迭,数值,琥珀的吸引力,虹的现象等等不能了解,发生惊愕。其实这些現象无一非其他民族直接或间接所可见到的,而且初见时,他们也皆不能了解的。希腊人和他们的差别在此:希腊人不将这些现象轻轻放过。由于惊愕,他们发觉自身的无知,欲避免无知乃进而研究。初步问题的解决又引导出较高深的问题来,再继续研究。问题唤起研究,研究获得解答,解答引致问题。更迭前进,科学于以产生,于以发展。”(陈康:《希腊时代科学的曙光》,汪子嵩、王太庆编:《陈康:论古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陈康一生著述有限,但其见地却非同凡俗,我们从其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思考的深度就可以“窥一斑见全貌”了。当然,后人也有进一步的思考:“陈康先生提出要让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外国人以不懂中文为憾。这不是仅凭专业性、技术性的工作所能达到的……这种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文字功底,用中文写作很难逾越文字的障碍,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典范。”( 《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史论关系的三种模式》,载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这一方面确实是做研究的甘苦之言,但另一方面也略乏学术自信,中国学术若能锱铢积累、遵循规律、执着求道,未必不可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东西之学,更不必说立一家之言了。
陈康为台湾联经版的《陈康哲学论文集》作序,称:“这本小册子里的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必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不作广泛空洞的断语,更避免玄虚致使人不能捉摸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惊愚。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表现出一个学者的良好学术伦理意识,这样锱铢积累起来的学问,有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陈康其实也是很有学术见地、判断力和勇气的,譬如他就直言不讳地说:“玄学是价值很低的学科,也许我们称它为一种Intellektuale Romantik格外合适些。然而这只限于名实相符的玄学,至于那些无问题根据的玄思玄想,即使很精巧,也不过是Gedankenspiel罢了。”(陈康:《哲学自身的问题》,汪子嵩、王太庆编:《陈康:论古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此处两个德文概念均未译成中文,可能是觉得用原文更清楚,翻译起来有难度。Intellektuale Romantik或为“知性浪漫”,而Gedankenspiel则是“思想游戏”之意。
纵观陈康一生,颇为典型有着那个时代的岁月痕迹。早期求学,颇有坚韧不拔、四海寻真知的执着;日后留学海外,也可谓是“十年磨一剑”,当1940年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已年近不惑,论文题目《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属于相当有分量的专题,是可以在德国和西方的学术史脉络中寻到定位的;自1943年归国后,旋即任教于大学,短短五年间,历经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等,其贡献主要在于译注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1948年到台湾,在台大哲学系任教;1958年后留居美国,也是在多所大学辗转,包括普林斯顿大学、艾默瑞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等,在此期间只出版一部英文专著《智慧——亚里士多德寻求的科学》。他的一生路向选择与导师方东美关系匪浅。这段生命史,包括其传记,都值得后来者书写整理。需要承认的是,陈康虽然著述很少,却都颇有学术分量,哈佛大学教授哈桑甚至誉之为“当今亚里士多德学的世界第一权威”,此言未见原出处,似乎值得考证,但也当非空穴来风。其案间箴语为:“生则日勤,死则永息”(Work diligently day while alive eternally after death),也可见其致力于学术与哲学的勤奋和执着!
陈康虽毕生研治西方古典学,但却自有其思想立场:“自从‘五四以来,念外国书的人日多,才华超迈绝伦,不甘略受拘束的人士喜欢将糖酒油盐酱醋倾注于一锅,用烹调‘大杂烩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大成的思想体系。”(江日新:《作者自序》,《陈康哲学论文集》,关子尹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言下之意,自己的治学显然是更立足于学问的专精方面,而非简单的“求全责备”甚至“良莠不分”。
总体而言,陈康作为一代学人,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史意义,也具有那代学人特有的学术特点,关于他在学术上的成绩,也希望有专业的学人出来做出公允的评价,或可避免人言人殊的尴尬状况。至少,就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的交汇点而言,陈康有其标本意义,他代表了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那代学人建设西方古典学的努力,虽然成果不丰,但价值不灭。而作为留德学人的陈康,更有其特殊的学科史、学术史、教育史个案价值,这在与徐梵澄、冯至、朱偰等人的比较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所谓“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其源当出自陆九渊,后来贺麟又加以发覆,但大致说来,东方与西方的相互认知,乃是构成人类文明与世界精神的核心要义所在,所以像陈康这样追索对方思想源流的学术工作者,其胸襟与思想,必然非一介陋儒可比。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