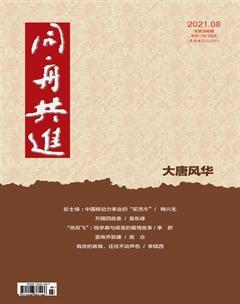科技之光:赡思与《河防通议》
王小帅
在中国历代王朝里,若论从前朝中收获最少的王朝,肯定有明朝。虽说历代王朝开国,大多都建立在战后的烂摊子上,但明朝立国后的社会状况,依然让人不禁慨叹。元末的战乱,其剧烈程度比起之前的乱世来,破坏力堪称空前,特别是元王朝的最后十年,从北方草原到南方各省,几乎都在打仗。
旷日持久的战事造成了严重的经济、人口损失。在明朝统一战争里,大军所过之处,无不是一片废墟。昔日的经济重镇扬州竟只剩下18户人家;山东、河南等省份更“多是无人之地”。明军北伐占领开封后,一路向河北行进,所经过的那些昔日繁华的城镇,竟都是“居民鲜少”。比如河北真定府,户口只剩下1/3。济南府和兖州府等地“近城之地多荒芜”“目无烟火”。
由于人口损失太大,许多元代的州县到了明代时,不得不重新裁撤合并。昔日的中原重镇开封,明初时就从“上府”降到了“下府”。洪武十年(1377)这一年,光是河南、四川两省就有60个县合并,12个州“降”成县。大明王朝三个世纪的历史,就是在元王朝留下的这一片废墟上开始的。
不过,在废墟之外,元王朝还是留了一样“好东西”——科学,它让开国时内外交困的明王朝长期受益匪浅。
在元代长达97年的历史中,方方面面都有些混乱,唯独科学的发展却是井井有条:中外科技交流在元代进入空前繁荣期,无论是天文、数学还是机械制造,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特别是元王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在位时期,这位有着“鲁班天子”雅号的皇帝,不但自己设计发明了“自鸣钟”“自动龙舟”等物件,更提拔了张墉、李国凤、杨瑀等科学家,科技图书的印刷也一时火热。虽然这一切并未能挽救元王朝的衰亡,但后来却成了明朝的宝物。
其中,对明朝乃至明清历史意义格外重大的,是一系列科技图书典籍,尤其是元代学者赡思所著的《河防通议》。
【无心做官】
《河防通议》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这得先说说他的作者:赡思。
赡思,元代色目人,1277年出生在河北真定的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祖父鲁坤曾做过真定路的监榷课税使,从此全家定居在真定。元代时迁居内地的色目人家族,很多都渐渐“多敦诗书而说礼乐”,成了儒家文化的虔诚学习者。赡思的父亲就是如此,他们家族也因此成为了真定有名的书香门第。
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下,赡思从小展现出不凡的天赋,自幼博闻强记,又师从元王朝的学问家王思廉(元好问的弟子),不但成了一名精通儒家典籍的学者,更對天文、地理、水利等学科都有极深的造诣。所以“其年虽少,已为乡邦所敬重”,年纪轻轻就名气在外。
以赡思的家庭条件,只要他想做官,基本不是难事。但赡思的父亲一辈子淡泊功名,且乐善好施,所以,赡思成年后的生活也一度陷入贫困,甚至“擅粥或不继”。得悉赡思名声的朝廷高官屡次向他伸出橄榄枝,但受父亲的影响,即便条件拮据,他也不为所动。
在60岁以前的日子,赡思主要忙于“考订经传”,比如《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西国图经》《镇阳风土记》《五经思问》等作品,都是完成于这一时期。
赡思不愿为官,除了受家风的影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生活的年代恰恰是元王朝吏治开始走向腐朽的时候。元王朝期间,科举时办时停,贵族阶层几乎垄断了一切高官要职。各地的吏治也败坏不堪,以《元史》的话来形容,就是“江淮行省至重,而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至于地方的州县,那更是“州县三四员,字不辨王张”。如此低素质的吏治,当然也就百弊丛生,就连负责督查各地吏治的“宣抚使”,也是“类皆脂韦贪浊”。这样的权力场,对于正直的赡思来说,自然是不相容的。
所以,在人生的大部分岁月里,尽管朝廷多次“征召”,赡思都婉言谢绝,直到60岁时才出仕。他以花甲之躯就任陕西监察御史,刚上任就给朝廷上书,提出10条意见,句句戳中朝廷时弊,甚至有同僚惊呼“御史言及此,天下之福也”。之后,他又陆续在陕西、云南、湖北、浙江等地担任过地方官,做过不少“平反冤狱”“打击豪强”之类的事,直到73岁那年因病退休,次年病故于家。
除了为官清廉、刚正敢言、为民发声之外,赡思的另一个重要成就,便是完成了重量级著作——《河防通议》。
其实,严格说来,《河防通议》并不算是赡思的“原创”。年轻时,赡思曾师从真定水力学家张祥,从此有了编订一部水利著作的想法。金朝年间,水力学家沈立就完成过一本《河防通议》,南宋年间的周俊也著有一本《河事集》。赡思的这本《河防通议》就是结合前人的成就,将其“削去冗长”后重新编订,最终在他53岁那年,即1321年四月,完成了“修订版”的《河防通议》。
赡思为什么要在“河防”上投入大量心血?因为彼时的黄河已成为朝廷的大患。自从两宋年间,黄河“夺淮入海”后,曾经富饶的江淮平原就变成了水灾频繁的黄泛区。黄河的水患从金朝年间开始频发,元王朝一统天下后,黄河水灾更是进入了多发期。从1272年至1366年的94年里,平均每两年多就会发生一次黄河水灾。有时候,黄河一年中决口的次数竟达数十次之多;严重时,一次决口的危害长达六七年,以至于“方数千里,民被其害”。
比如1344年,黄河在白茅口(今山东曹县境内)决口,波及济宁、汶上、嘉祥、楚丘、沛县、定陶、曹州、巨野、郓城等近20个州县,以至于“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这样的灾情在元朝的历史上并不是某年的特例,而是每次决口都会发生的情状。
而且对于元王朝来说,黄河的水患还关乎着王朝的兴衰。元王朝定都于元大都,元大都需要的粮草赋税,都需要通过京杭大运河向北运输。一旦黄河决口成灾,必然要威胁京杭大运河的安全,这条朝廷的主动脉就将处于“断血”的威胁之下。
对于黄河灾害的破坏力与威胁,元王朝历代也高度重视,从开国开始至赡思生活的元朝中后期,历代统治者都不惜血本加固黄河两岸的堤坝。每次发生决口灾害,更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至于“塞河之役,无岁无之”。但巨大的投入换来的依然是频繁的灾害,身在民间的赡思对这样的灾害更是感同身受。
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学者,赡思虽然无心于仕途,但无时无刻不在牵挂人民的安危。与那些“不通文墨”的官员不同,作为通才,赡思看到了“治水”的重要症结——缺少专业化操作。于是,他耗尽多年精力,用心编纂完成《河防通议》。
【治水利器】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以“治水”为主题的巨著不算少,赡思的《河防通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治水经验的“整合版”。而它之所以首屈一指,就是因为它的“专业化”。
虽然身为儒生,但对天文、地理、算学都造诣精深的赡思,非常反感空洞无物的学问,所以下笔写书时格外实在。《河防通议》对前人的水利著作去粗取精,剔除空洞之处,没有一句空话、套话,重点阐述治水的基本学问,语言简单生动,方法行之有效。
比如书中罗列的各种治水装备,对于当时的治水实践来说就有着启示意义。其时的水利书籍里,虽然也有记载这些专用装备,但都把重点放在装备的效用和形态上,至于这些装备该如何打造、如何操作、如何检验质量,就只是寥寥几句带过。
赡思则不同。比如《河防通议》里记载的宋、元、明时代的“挖掘机”——“铁龙爪扬泥车”就是典型。这款发明于北宋年间的扬泥车,可以用船驾驶,携带“铁龙爪”挖掘淤泥,是宋、元年间疏通发掘河道的利器。但因为当时的各类书籍对它的记载过于简略,以至于后世往往“制造不得法”。元初,科学家郭守敬将扬泥车改造,重新设计它的宽、高比例,也因此,扬泥车曾在元初的一系列治水工程里发挥大用。但好景不长,随着郭守敬去世,铁龙爪扬泥车的制造出现了质量低劣等问题。直到赡思在《河防通议》里,重新细致地还原了铁龙爪扬泥车的生产标准和正确图样,这件治水利器才得以重新派上用场。
“黄河运石船”也是黄河治水时的刚需装备,特别是每当黄河发生决口灾害时,堵塞决口的办法就是用黄河运石船运来大批石料,然后投往激流里。因此,对黄河运石船的质量要求自然极高,倘若质量不过关,必然会被汹涌的河水冲到散架。而在《河防通议》里,赡思也对黄河运石船的制造做了极其细致的规定,从船的用料到宽、高比例,从所需板木的数量到检验的标准,都有清晰的要求。只要谨遵赡思所写的要求,大批质量过硬的黄河运石船就能顺利生产出来。
除了写及治水装备,《河防通议》还呈现出赡思的治水理念。赡思对治水的观察渗透到每一个细节里。在书中,赡思专门提出了“辩土脉”的理念,将治河时会遇到的土质,划分成19种类型;每一种土质的特性和适用范围,他也做了归纳总结。比如,倘若遇到“带沙黑”的“河底死土”,那这样的地面就会出现“活动走流,难以成功”的问题,根本不适合进行水利施工。
就连水流的运动规律,赡思也做了精确的分类。在赡思看来,即使是河流里汹涌的大浪,也同样有规律可循。水灾里经常发生的河浪,他也分了18类之多,每一类的成因与冲击力都各不相同。只有掌握了这些河浪的运行规律,才有可能遏制恐怖的洪灾。
这种透彻研究的理念渗透在整部《河防通议》中。《河防通议》分为上、下两卷,一共有“六门六十八目”,包括了“河议”“制度”“功程”“料例”“输运”“算法”等学问,几乎涵盖治水工作的方方面面,既有对治河工程的全盘规划性管理,也有对每个细节的操作指引,比如在“料例”一栏,他就对治河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基本用料做了严格规定,杜绝偷工减料的口子。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元代首屈一指的数学家,赡思还在“算法”一栏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一环节,赡思列出了25道应用题,每一道都涉及治河施工过程里的常见问题。他先是提出问题,然后再以当时领先世界的“天元术”将问题一一解开。可以说,这25道题也代表了当时中国数学的最高成就。
如此一本奇书,虽然以赡思自己谦虚的说法,是对前人著作“省其门,析其类,使粗有条贯,以便观览而资实用”,但是放在中国水利史上,它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把治水变成了一个系统化工程,对每个看似繁琐的步骤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任何一个官员,哪怕对治水一窍不通,只要读过《河防通议》,就可以现学现用。
这部书问世后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当时就被“推行之”。元顺帝年间著名的“贾鲁治河”工程就是凭着《河防通议》顺利完成的。虽然当时赡思已经去世,但元朝从治水管理到工程用料乃至器械打造,都实现了升级,克服了这次颇具挑战性的治水行动。
1368年,赡思去世17年后,已能驾驭黄河的元朝谢幕,《河防通议》也在下一个王朝里焕发出全新的价值。
【永久的贡献】
明朝在废墟上开国,问题多如牛毛,但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依然在一个“水”字上。
比起多年来文恬武嬉的元王朝来,初立国的明王朝采取了强力的经济发展措施。全国大力推广垦荒屯田,自耕农的农作物种植内容也由朝廷严格規划。果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全国推广。以明太祖朱元璋诏书里的话说:“务欲使民丰衣足食。”要实现这个目标,“水”依然是关键,各地大片的荒田需要充足的水源来灌溉;广袤的国土更是需要水路来连接。与北元残余势力的战争还在继续,北方军队的粮食物资也要靠水路运输……可以说,水利的成功与否,关乎着新生明王朝的国运。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规模巨大的水利建设随之铺开,包括《河防通议》在内的一系列科学书籍都派上了用场。明初,每当有治水工程时,朝廷都会将《河防通议》交给经办官员,《永乐大典》也将此书辑录进去。明太祖在位的30年里,依据《河防通议》的指引,明王朝完成了“塘堰40987处,浚河4162处,修建陂渠堤岸5048处”,农业产量也随之飙升,洪武二十七年(1394)的税粮收入达到了3200万石,是宋、元时代最高值的两倍多。
元朝时期的京杭大运河由于设计失误,导致明初时长期阻塞,永乐帝朱棣要迁都北京,就要打通漕运。凭着《河防通议》等图书的技术指导,明朝廷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完成了会通河、清江浦等工程的开凿,断流数十年的京杭大运河终于重新开通。从此,明朝顺风顺水,“用东南之财富,会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
也许,在忠心为民的赡思心里,后面发生的一切都是他没有料到的,但相信他已无憾——兵威王朝的兴衰都是一时,而科技文明的贡献却是永久。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