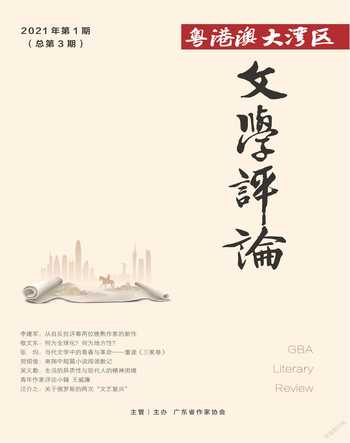南翔中短篇小说阅读散记
贺绍俊
摘要: 南翔是一位比较典型的学者型作家,他将学院气质、民间情怀和南方立场完美结合为一体,构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小说叙述, 其特征是关注社会人生的命运沉浮,在社会政治如何影响和干预了人生命运和人性变异的方面着力,以文学形象表达他对社会问题的见解。南翔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用力最多,中短篇小说也最能体现南翔的独创性。
关键词:学者型;民间情怀;中短篇小说
南翔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写作。八十年代被称为当代文学的新时期,这是一个强调理想和激情的年代,文学担当着匡正社会的思想责任。这一时代特征也典型地体现在南翔的身上,因此他是一位充满理想也具有社会担当的作家,他的写作生涯至今已有四十年了,这四十年社会发生着巨大变化,南翔的人生也经历了种种变迁,但无论如何变化,南翔始终没有放弃身上的理想和社会担当,这就构成了他在文学上的一贯性。在南翔的人生经历中,九十年代末由江西迁到深圳应该是他的文学创作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因为深圳的思想文化氛围更有助于他发展自己在思想上的优势, 从而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我记得《女人的葵花》这本小说集就是收录了他到深圳后写的九篇中短篇小说,当时我读到这本小说集后,还专门写了一段话:“南翔的小说很好看,也很耐读;他可以在不同的时空里展开想象,而最终又都凝聚于思想性和文学性,这得益于他的学院气质、民间情怀和南方立场三者的完美结合。”现在看来,我这一段话还是抓住了南翔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一我说他的小说很好看,是因为南翔注重小说的故事性,他很会讲故事,也善于讲故事。但他并不满足于讲故事,或者说讲故事并不是他写小说的目的。他的目的落在思想性和文学性这两点上。他的小说叙述其实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努力去挖掘故事里面包含的思想性。而且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也不是浅陋的、公共化的思想,而是有着一定学术积累的思想。毫无疑问,他的这一突出特点与他身处深圳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深圳的开放和包容更加激活了南翔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成为深圳大学的一名教师,浸润于校园丰厚的学术氛围之中。从这个角度说,南翔属于比较典型的学者型作家。所谓学者型作家,不仅在于其小说的思想主题具有明显的学术基础, 而且还在于作家的小说叙述会受到学术思维的影响,并在小说写作中会有较明确的理性意识和明确的写作目标。在我看来,南翔所设定的是一种社会政治的目标,他关注社会人生的命运沉浮,他的小说往往在社会政治如何影响和干预了人生命运和人性变异的方面着力,以文学形象表达他对社会问题的见解。南翔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用力最多,中短篇小说也最能体现南翔的独创性。我一直踊跃着阅读南翔的中短篇小说,在这方面也有不少阅读体会。
有意思的是,南翔四十年来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学前沿,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的中短篇小说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佳作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我们又很难把南翔归入某一个潮流和类型之中。且以《女人的葵花》中的小说为例,其中有两篇小说《我的秘书生涯》和《辞官记》都是写官场的,但南翔并没有像一般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那样热衷于揭露官场的复杂性和险恶性。《我的秘书生涯》通过一个优秀秘书如何败在了一个熟稔权力与人情交易秘诀的女人的故事,揭示了官场规则与潜规则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辞官记》的故事核心则是一个博士竟被一段少年时期饥饿的悲惨记忆阻碍了他的仕途,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官本位意识在当代社会是如何发酵变异的。显然,无论是在主题的确定上,还是在叙述的诉求上,南翔的这两篇写官场的小说都迥异于我们从大量官场小说中获取的共同性。事实上, 南翔对当代文学的现状和趋势非常了解,他不是那种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完全书写自我的封闭型作家。他也善于吸收新的讯息,他的小说世界是开放性的,比如他最近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曾把自己的创作归纳为三个维度:“文革”/ 历史、环保 / 生态、底层 / 弱势。这三个维度的确是南翔在创作中重点关注的内容,其实这些内容也是我们社会以及文学界十分关注的内容,比如底层、生态等,也曾经一度成为创作的热点。这也许说明一个问题,南翔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作家,始终对社会热点充满了敏锐的感知,也必然会在他的小说中体现出来。但他在文学创作中又对同质化和流行化保持警惕,因此即使选取了同一类题材, 他也非常注意与这类题材中所呈现的共同倾向保持距离和差异。比如底层基本上是南翔小说的出发点,他在小说中多半讲述的是底层小人物的故事,但我注意到批评家们在评述底层小说时几乎很少提到南翔的这些写底层小人物的小说,我想这完全是因为南翔的小说并没有采取当时流行的底层小说的叙述套路,也没有刻意强调底层的主题诉求。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性的首要问题,自然也越来越受到作家们的关注。南翔作为一名思想敏锐的作家,也加强了小说中关于生态的分量。比如《哭泣的白鹳》《来自伊尼的告白》《消失的养蜂人》等小说就属于具有明确生态意识的小说,小说涉及物种衰减、环境恶化等突出的生态问题,但这几篇小说又与那些刻意标记為生态小说的小说不一样,那些刻意标记为生态小说的小说往往有一种过度宣传生态的毛病,而忽略了生态问题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复杂性。南翔这几篇小说都是将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搁置在一起来写,写出了生态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消失的养蜂人》从构思上说就很特别,是以养蜂的生物学知识来结构小说的。虽然有些地方也看出南翔试图在反思生态问题的思想层面用力,但他并没有在生态话题上过多地展开,而是任由情节的复杂内涵弥散开去。在小说的结尾,养蜂人阿强突然消失,作者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无解的谜。这个谜提示人们,还有一个“生态”在困扰着人们,这就是不良的社会生态。阿强虽然能成功地把中蜂和意蜂混在一起养,但是他无法克服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当他发现很可能会卷入矛盾中时,他的一切努力都可能会报废,所以他不得不悄悄离开。当然南翔在这篇小说中并没有揭露这个社会生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使得阿强悄悄离开,他实际上是在小说结尾设置了一个谜。他希望读者能依据自己的经验去解答这个谜,我们的社会生态在很多方面都出了问题,其中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有可能会让处于弱势位置的养蜂人阿强难以承受。
也许应该从学术思想的一贯性来理解南翔的小说创作。南翔的小说写作首先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这种写作是建立在一贯的思想立场和认知背景上的。他的思想立场和认知背景概要地说,可以归结为具有民间色彩的自由主义思想。我以为,南翔是在以小说这一载体不断地表达他从自由主义思想出发对历史和现实所作出的评判与臧否。因此,南翔所说的三个维度并不是三条互不关联的平行线,而是相互交错、相互补充从而统一于自由主义思想上的一个完整的艺术王国。南翔似乎也将这一写作姿态视为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应有责任。他有一篇小说《表弟》仿佛就是在表白自己的这一心境。《表弟》的社会容量非常密集,读者能够从这篇作品中看到作者对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政治风云变幻的历史把握,作者也揭示和批判了当下社会权力与资本结合的现状。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南翔让“我”做了一个扳手腕的梦, 表弟输了以后要再来一次,禄禄却抢白说,你们一家,既有运动员,又有裁判员,还讲我不公平?在小说中,禄禄可以说是权势寻租的形象,“我”则应该是知识分子形象。禄禄固然是一个值得批判的对象,但南翔也不放过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我”,或许从这里可以感觉到南翔的一种难得的自我警策,他显然不满于一些知识分子自视清高而对社会所作的不负责任的批评,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可能摆脱物欲世界的纠缠,你必须把自己摆进去,才能真正担当起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
作为一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南翔对于中国百年来的历史进程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他的历史观是清晰的,他对历史和现实的价值判断保持着一致性。他曾接连写过一批反思历史的小说,这些小说结集为《前尘:民国遗事》《1975 年秋天的那片枫叶》《抄家》,这些小说虽然讲述的是民国、“文革”历史时段的故事,但叙述的锋芒分明剑指现实。正如他在《抄家》一书的后记中所说:“对于历史,尤其是发生不远且迄今或深或浅,仍在影响我们的思维与生活的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评价、看法乃至思想交锋,亦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不同学科、不同方法的研究与呈现。但硬要找出一些恬淡、温馨与优容,来辩说与粉饰一场大灾难,实非我能接受。”因此南翔写历史不是单纯地为了忆旧,而是抱着匡正现实的明确目的。同样的,南翔书写现实时也不是呈现一个平面化的现实图景,而是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现象时,都会从历史演进和延续的角度去进行评判。因此他的所有书写现实的小说,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感。
且以《老桂家的鱼》为例。这是一个发生在深莞一带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既不是充满现代感的高楼大厦,也不是透着珠光宝气的酒吧咖啡厅,也不是风情万种的沙滩浴场。它是西枝江边的一处尚未开发的荒芜处,这里零零落落住着一些靠打鱼为生的人。也许说他们住在这里并不准确,因为他们没有房子,一条船就是他们的家。如小说的主人公老桂,当年曾是农村最先觉悟者,他摆脱即将崩溃的集体所有制,到水上跑运输,却赶不上社会的突变,竟然再也回不了陆地,只能在一条船上赖以为生。有一个细节读来让人心酸。老桂在他一家生活的船上钉了一张铭牌,上面写着的“大岭山”是他曾经居住的地方,可见他魂牵梦绕般地希望回到家乡,回到陆地上。小说截取了老桂在船上的最后一段经历。虽然拖着衰弱的病体,却仍不得不出去打鱼。回来后一病不起, 最终“死在破败的大船上”。南翔在深圳发现了这样一个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像老桂这样生活在船上的渔民,“在这个城市里,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社保,也没有医保。或许可以说,他们的生活,随着潮汐变化而变化。”南翔意识到,西枝江上的那些破败的船不得不说同样是深圳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是现代化带来的问题。为了表现这一现实批判性,南翔在小说中专门设计了一个电视台记者去采访破败渔船的情节,记者们采访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老桂们的生活困顿,而是因为旁边的高档住宅里的居民们投诉,这些破败的渔船“严重影响市容和干扰居民生活”。终于政府出面要求这些渔民“限期搬迁”,这些渔民彻底清除后,西枝江边确实发生了变化:“堤边新修了绿道,新植了绿柳, 江面愈发空阔了。”单独看这几句描写,是一种诗情画意的味道,但在我们读到前面关于老桂一家的艰辛故事以及老桂的死之后,再读到这几句诗情画意的描写,便会产生巨大的反差。
南翔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批判上,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简单地把老桂家看成是现代化的代价而问责于现代化,而是从历史层面去探究老桂悲剧的成因。老桂当年也是一名回乡青年,还当过民兵营长。也就是说,他们在上一个时代是可以正常生活甚至很体面地生活的。老桂既不懒惰也不愚笨,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反而越来越陷入窘困呢?这让我想起了过去我们反复接受的教育: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治国之本,自然一个阶级的欢笑就是另一个阶级的痛苦。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观完全从今天的社会里消失, 因此即使今天社会经济大大发展了,但依然会存在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问题。《老桂家的鱼》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我们不能再犯历史曾犯过的导致阶级固化的错误,现代化在解决“破败的船”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船上的“老桂”们从破败中摆脱出来。
南翔的《绿皮车》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完全将历史与现实打通了,从情感上说,既有岁月的缅怀,也有对现实中的温情与善良的礼赞。而从理智上说,南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兴衰,强调了任何事物的进步都有得有失,因此在历史进步的喜悦中也要警惕我们是否丢失了有价值的东西,整篇小说充满着历史辩证法。绿皮车是代表计划经济时代的十分典型的“物”,绿皮车行进在祖国的大地上,曾是当年诗人们最爱歌吟的意象,但到了今天,动车,高铁,和谐号,这一系列的高科技和加速度,足以把绿皮车挤出列车的轨道。但南翔的这篇小说并不是为即将被淘汰的绿皮车唱挽歌,而是在提醒人们,在欢呼高速度的“和谐号”取代绿皮车时,不要忘记始终陪伴着绿皮车的老工人们,以及由绿皮车营造出的特定的生活方式。《绿皮车》里的老工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铁路钱,《绿皮车》具有一种绵绵的怀旧情愫,我以为《绿皮车》最出彩的地方,就是通过这种怀旧情愫,缅怀了在绿皮车这一特殊空间所营造出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哪怕今天社会发展速度再快、经济再繁荣、物质再丰富,但是南翔强调,我们不应该随便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在绿皮车里,人们享受着慢节奏的生活,在慢节奏里人性得以充分展开,人们也自得其乐。但出于经济考虑,我们只想到列车的提速,就把这种慢節奏的生活环境毁掉了,而那些习惯了这种生活环境的人就会无所着落,他们哪怕得到的物质再丰富,可能也不会感到幸福的。
《打镰刀》是南翔 2020 年发表的一篇小说,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关闭在屋子里,得到了这篇小说的电子版,小说洋溢着明快的调子,一扫因疫情积压在心上的阴霾,将我从封闭的空间带到了艳阳高照的广袤田园。最后我想着重说说我读这篇小说的体会。
南翔是一位胸怀很博大的作家,他的小说哪怕书写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或者讲述一件很平常的物事,总是要透过人物或物事放眼悠远的时间和广袤的空间。他着眼于现实生活, 却对现实中的变化具有特别的敏感,他从现实的细微变化中打探到历史与文明演化的脉搏跳动。这一回,他注意到了乡镇铁铺店里悬挂在屋檐下的锄头和镰刀。这不过是农民最常用的农具,应该是每一户农家必备的物事。但似乎现在它们遭到了冷落,在这个铁铺店里被挂在屋檐下,没有人来光顾。关注锄头和镰刀的除了南翔还有一位美术学院的教授刘寥廓,他慷慨地将这些锄头和镰刀买了下来。但他买下来并不是要用其作为农业生产工具,而是觉得它们挂在屋檐下极其具有“艺术范儿”,他要把这些农具用在他的装置艺术中。这些作为农业生产工具的铁器给了他艺术灵感,他决定要打一万把镰刀,用这一万把镰刀创作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南翔便是沿着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入点扩展开来,讲述了一个打镰刀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他把现实中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凸显了出来,让我们感到了那些悬挂在乡村屋檐下的锄头和镰刀的分量。
我们得承认,中国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与世界性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同步进行的,它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乡村的变化之大也是令我们过去难以想象的。这一切也反映在文学上,我们的乡土叙述完全不是半个多世纪前占据主流的或者田园牧歌式或者荷锄挥镰式或者鸡犬之声式的叙述,因为如今的乡土叙述已经不可能再面对一个封闭自足的乡村风景了,乡村与城市交织在一起,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触角已经伸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在乡土小说中读到的是进城的农民工,或者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乡村的这些变化已经成了乡村的常态,因此《打镰刀》中所写的乡村同样也是这样一种情景,如鹰嘴山这个小村子的年轻男女几乎都出去打工了。但南翔要说的还不止是这些,他在大家都很熟知的这些变化之外,发现了还有一种变化,这就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由此南翔便带大家一起认识了小说中的两位重要人物:两个老铁匠,一个是张铁匠,一个是魏老伯,他们曾是打铁的老搭档,他们手艺好,打出的铁器远近闻名。但是他们打铁的火炉早就封炉熄火了,魏老伯也去照看儿子的果园了。也许这就是铁匠的结局吧,他们的手艺也就从此衰落,失去了传承。南翔从镰刀看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文化问题: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是一种文明的衰落。是呵,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高科技的工业化流程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最标准的包括镰刀等各种铁器,生炉打铁的小作坊在这种现代化强势的倾轧下甚至连苟延残喘的机会都没有了。其实何止铁匠,整个农业文明逐渐走向衰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打镰刀》以一个小场景的故事触碰的是这样一个关乎大文化的坚硬问题。
我很欣赏南翔面对这一文化问题所采取的姿态。农业文明衰落的现象其实是当下文学一个比较热门的书写题材。我也读到过不少写农业文明衰落的作品,作家们面对这一现象时似乎更偏向于做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为衰落的文明唱挽歌,却往往无视在一种文明衰落的同时还会有一种新的文明在冉冉升起。而无论是旧文明的衰落还是新文明的升起,都不应该忘记最根本的一点:人类是文明的创造者。因此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首先必须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才能保证你对文化的认知不会出现偏差。南翔就是一位严肃的人道主义者,即使面对社会变迁、文明兴衰这些关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重大问题时,他也秉持着一位作家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打镰刀》中,正是人道主义精神给一个涉及文明衰落的沉重故事带来了亮丽的色彩。张铁匠和魏老伯是文明衰落的直接承受者,也许他们会有一种失落感和被遗弃感, 但南翔并沒有刻意去渲染他们的失落感,相反而是真实客观地写他们能够坦然接受现实,同时,南翔又以非常体恤的心情去小心地叩问他们的内心感受。如写到两位老人重新开炉生火时的兴奋劲,“炉火是一个引信,同时点燃了两个老手艺人遥远又切近的记忆,伴随着叮叮当当的锤打声,两人默契的动作便是昨日的对接和延展,一点点生疏也无,一点点遗忘也无, 一点点迟疑也无。全都是熟门熟路,是认真的手艺,也是认真的把玩。那种熟练与利落,像飞瀑一样流畅,完全举重若轻,根本觉察不出这是两个古稀之年的配合。炉火不时映现在两个人的脸上,雕刻出两尊铜像,却富于色彩和线条的变化”。这是充满敬仰的抒情文字,也渗透出一丝对于逝去文明的惋惜。当然,当张铁匠看到一万把精心打造的新镰刀在展览中被全部做成锈迹斑斑的旧镰刀时,他心情特别难受,南翔此时也只能无奈地让刘教授耸耸肩地暗想等以后再慢慢来解释吧。南翔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他对张铁匠和魏老伯的定位和描述上,而且尤其体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中。南翔将农业文明衰落的现象与农村年轻男人找对象难的现实串在一起来写,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思。当然,这两件事情本来就有关联,乡村的凋败自然就导致了大量乡村女性逃离乡村, 但南翔并非要探究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他要写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困顿现实中,爱情也会要寻找到宣泄的渠道。于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在彬彬的召集下,一群年轻男女都来帮张铁匠打铁,打镰刀的现场成了村子里一个少有的热闹现场。在挥汗出力的同时, 青年男女们的青春荷尔蒙得到尽情的释放。连张铁匠都说:“你们男男女女在一起,这么些日子好好相处,都给我擦出几点火花来。真能结成几个对子,那就比我赚几块辛苦钱更开心。” 而年轻人则调侃道:“两个老倌子也作兴是老树发芽,枯木逢春咯!”小说就是在收获爱情的惊喜气氛中结束的,彬彬终于捅穿了观念习俗的阻隔,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倩倩谈婚论嫁了;而藿香则大胆地追到了与刘教授的爱情。一个乡村大龄胖妞能与离婚的城里教授牵手则是一份令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尽管这一惊喜在前面的叙述中铺垫得不是很充分,但我完全可以理解南翔的用意: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无论文化如何沉浮,爱情却是永恒的。打镰刀打出了爱情火花,也就会让我们能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去面对农业文明的衰落,也许打铁今后真的只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但我们的爱情仍然会在新的土壤上绽放得更加鲜艳。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