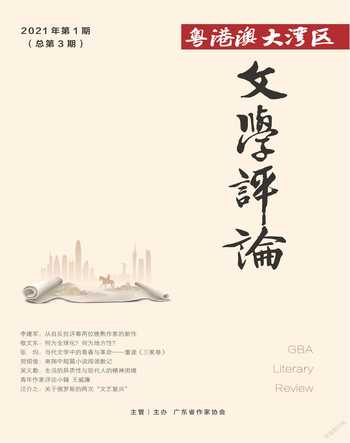生活的异质性与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吴义勤
摘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常生活作为新的审美对象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叙事的重要维度。本文以浙江青年女作家黄咏梅、祁媛、杨怡芬、柳营等的写作为例,从典型文本出发分析这种审美转向的特征。文章认为她们的写作致力于日常生活异质性因素和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发现,悲中有喜,笑中有泪,风格多样,表达了对于时代生活、个体生命以及普遍人性的深刻思考,拓展了当代文学人性表达的边界。
关键词: 黄咏梅;祁媛;杨怡芬;柳营; 日常生活审美化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常生活作为新的审美对象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叙事的重要维度。几位浙江青年女作家黄咏梅、祁媛、杨怡芬、柳营等的写作堪称这种审美转向的成功实践者。她们的写作均致力于建构日常生活的审美性, 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异质性因素并进行各具特色的叙事转化,并通过营构不同的人物和故事, 表达对于时代生活、个体生命以及普遍人性的思考和希冀。
一、“生活在别处”与分裂的主体
黄咏梅等在她们的小说中塑造了大量世俗意义上的现代主体,但这些主体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世俗生活及周围人的疏离感和个体的分裂感、孤独感,存在着反生活逻辑和世俗伦理的自我分裂和乖蹇行为,呈现出一种远离世俗、“在别处”的状态。
祁媛的中篇小说《除夕》讲述了一个在除夕之夜滞留城市的异乡人的生活状态。在这样一个传统阖家团圆的时刻反方向地与故乡、亲人以及家庭分离,使得人物自然地与日常生活拉开了距离,具有了重新审视故乡、亲情乃至生活本身的合适位置与视角。人物的这种反向的生活状态的形成,既有父亲去世这种直接的、客观的自然推力,也有个体内在的主动性的、期望中的与家乡和家庭的主动隔离。“想到今年是自己三十多年来第一次独自过春节,她心里就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多少年了,这是她第一次置身春节返乡大潮之外,终于熬出来了,她感到一种解脱,觉得身轻如燕。”这种与故乡及亲人主动疏离的状态,恰是主人公一种总体性的生活特征和自觉的精神选择。如果说与故乡及亲人(主要是父亲)的关系可能存在代际上或性别上的隔阂,但在个人生活的内部尤其是情感层面,同样体现出这种疏离特征,即与男性关系的游离感和不确定性。父亲、初恋男孩、丈夫、经理约翰、邻居小海都曾在她不同的生命阶段占有相当的分量,但她与他们的关系都显出一种若即若离的轻和隔,不管是亲情关系、婚姻关系、工作关系还是朋友关系, 都无法给予她生活的实感和生命的重量,她与生活及人群的距离感,让她无法建构起有温度和丰富纹理的生活,无法与世俗生活融为一体。
《桥洞里的云》也涉及现代之人尤其是青年一代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人物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失重感十分刺目。故事发生时间是在大学时代,在这个青春绚烂、激情燃烧的人生阶段,却处处充满颓丧感。不仅老师们忙于接私活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内容,学生们的自我放纵也令人触目惊心。“我”与韩冬几乎完全游离于校园生活之外的状态是对当前大学教育的某种反叛,当然也是一种自我放纵和放逐。不管是归因于学校环境,还是个人的主动选择,“我”与韩冬都与常态化的学校生活产生遥远的距离。我们既未能借助于教育体系获得成长,也没能建立起个人的自我价值体系。韩冬的沦落将那些充满荷尔蒙气息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击碎。
黄咏梅的《跑风》同样写了现代之人与故
乡、亲情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这种疏离感。玛丽(高茉莉)因为一只猫而延迟回乡,被哥哥斥为神经病。而她在故乡程式化表演一般的存在,体现出她与故乡及亲人之间的巨大隔膜。在当下和过去之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人物主体:玛丽和高茉莉,她们既是同一主体的两个不同阶段的分别指称,也可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特征的独立主体,是两种不同类型生活内容的象征载体。过去时间中的高茉莉仍然与故乡人事融为一体,而当下时间中的玛丽正在与故乡的遥望中与一只猫相依为命。在这里,现代人的孤独感跃然纸上,她犹如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失去了对于故乡人事的亲和感和主动体认的愿望。
杨怡芬的《有凤来仪》则通过叙述女性在现代职场和社会秩序中的困境和隐秘优势,写出了人的另外一种分裂。“我”与董小如、胡姐构成了一条隐秘的具有传承意味的线索,虽然存在年龄差距,但都通过相似的手段,利用了女性的性别优势实现了自己的功利意图。胡姐对“我”的利用,“我”对董小如的利用,并无本质差别,它既体现出职场的残酷性和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更深度体现出女性在现代职场和社会秩序中的特殊位置和命运困境。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立场变化,当胡姐试图利用“我”而稳固与李局的关系时,“我”的愤怒使我“浑身哆嗦”,但“我” 同样利用了董小如而实现了个人升迁的目的。这种前后变化并非转换自如,而是在内心激起巨大波澜。“照镜子的时候,我都不敢正眼看自己,就是在不得不对镜梳妆的时候,我都眼神闪烁。”这种内心的不安,正是不同的自我相互质疑的结果。
二、现代女性的情感困境
或许是与几位作家本身的性别相关,对于现代女性主体的情感关注和内在心理世界的勘察成为几位作家共同关注和书写的重要向度。
黄咏梅的《证据》非常细腻地写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困境。沈笛与大维的爱情颇符合现代男才女貌的婚姻特征,大维的才华、资本、地位、资源与沈笛的年轻、美貌、纯情似乎构成了一种各取所需的牢固共同体,但婚姻中的两人并未真正建构起情感意义上的共同体。沈笛犹如那只消失了的孤傲的蓝鲨,她并不甘心仅仅居于优渥的物质生活中, 她期待着一种有温度、有情感、有生活纹理的婚姻生活,但现实之境恰是另外一种状态,他们的婚姻生活是让位于名与利的,是以大维的事业为中心和参考标准的。因此,沈笛在婚姻中始终是被动的,从属的,失去自我的状态, 这成了笼罩在她精神和心理上的巨大阴影。《小姨》也是写女性的情感困境。小姨长期受到情感问题的困扰以至成了大龄剩女,那个在学生时代擦肩而过的师哥似乎是问题的根源,但当师哥再一次在生活中出现,小姨的个人问题的真正原因才凸显出来,不是擦肩而过的师哥使她长期保持单身,而是她对生活本身的态度构成了真正的障碍。“太麻烦了,谈恋爱,結婚,生子,造一个生命到这个乌七八糟的社会再受一次罪,有什么意思?”造成小姨生活困境的实际是这种生活态度,对婚姻的恐惧让她难以建构起正常的情感生活,也难以融入人群和大众, 小姨最终的发疯是对这种情感态度困境的命运隐喻。
杨怡芬的《乌贼骨》写了现代婚姻生活中的女性“困境”。女主角戴米与老公余诚有着世俗意义上近乎完美的家庭,父辈们有显赫的身份地位和富裕的财产,老公工作安稳、性格温和、周到体贴,儿子朗朗聪明可爱。但戴米就是无法安于生活,而是期待着生活的某种变化。她不停地学习、参加雅思考试,这些行为与其说是为了追求能力上的进步,不如说是为了追求生活的变化。她害怕生命老去,也害怕青春凋零。她挣扎着、焦虑着、幻想着。于是,与雷宇和范柳原的关系就在潜意识的期待中到来和发生了。她从世俗道德秩序中逃逸而出,完成了个人的越轨。但这种越轨的行为注定無法获得社会合法性,正如放置在行李箱底的乌贼骨只能被安放在隐秘的角落。但戴米所表征的躁动的、无处安放的女性仍然具有深刻的代表性和象征性。她表征着现代女性在婚姻中可能的分裂与挣扎,乌贼骨就是一个醒目的欲望符号,是女性内在精神动荡的象征。
柳营的《阁楼》更进一步地写到了现代女性的身体欲望和心理经验,并且将这种欲望以一种巧妙而隐蔽的方式进行了释放。年轻女子小梦与无名男子的婚外之情隐蔽地存在于道德伦理之外,但二人的忘情和瘾君子一样的状态, 又诠释着其存在的某种合理性。阁楼成了盛放欲望的容器,阁楼上的女人和男人是原始性、动物性的,他们遵循着自我的本能,释放着生命的激情。但这种隐秘的盛开注定只能在黑暗中进行,阁楼外的世界是道德性的、秩序性的。小梦最终的走出阁楼以及阁楼的被推倒, 预示着道德秩序对于个体欲望的收编,但“心里的那座阁楼却永远都是在的”。柳营在这里同样写出了无法被婚姻所含纳的女性的诉求,展现出女性在婚姻秩序前的犹疑、矛盾和挣扎。
三、父亲书写与形象重塑
文学中的父亲形象常被赋予诸多社会性内涵和象征性意义,父亲形象的塑造,有着神化和权力化的造神倾向,也有过现代文学以来的审父乃至弑父书写。而黄咏梅等女作家对父亲形象的塑造,则更注重从人本位角度出发,重新理解父亲以及父亲背后的历史生活和情感世界,重塑更加真实而纹路清晰的父亲形象,将当代文学中父亲形象的塑造推进到一个更加丰富的层次。
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重点写了父亲的情感世界。做货运司机的父亲曾经在跑车的路上发生出轨,与同样做货运司机的“四川婆”发生了隐秘的恋情。母亲去世后,父亲又遭遇了爱情骗子。几段不同的情感经历,构成了父亲的情感世界图景。小说没有把父亲放在一个神圣的位置去神化,从而有意识遮蔽一些逾出道德伦理的内容,也没有将父亲放置于道德伦理体系之下去审视和批判,而是持有一种理解和同情的态度,深入体察父亲的内心。既细腻写出了父亲在婚外情中的情感逻辑和心理动机, 也写出了晚年父亲因为生理和心理的变化所产生的对于爱情的奇妙态度。父亲既不是那个内含着诸多社会文化特征的父权符号,也不是被道德伦理体系所规训和禁锢的个体,而更多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自然人维度上的男性。《给猫留门》中的父亲老沈,也极具个性特征。年轻时的老沈讨厌养猫,曾经强行把儿子沈小安养的一只猫送走,给沈小安留下心理创伤。然而,到了面对下一代时,为了讨好孙女雅雅, 他竟然十分用心地去饲养雅雅喜欢的一只流浪猫。作品既写出了不同代际之间的微妙关系, 也写出了一个晚年父亲的忏悔心情。豆包的走失,让他充满深深的自责,这自责既是对孙女雅雅的,也是对儿子沈小安的。“他觉得自己就像那条咬钩的白条鱼,显然,他的挣扎要比它漫长而疼痛。”在这里,晚年父亲和青年父亲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既具有生理上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又具有精神上深刻而巨大的转折性和变动性。这是一个忏悔的父亲,是一个被疼痛所包裹的、温情复归的父亲形象。
杨怡芬的《过啊过啊,过奈何桥》塑造了一个饶有意味的父亲形象。父亲具有知识分子的显著特征,饱读诗书,同时讲究义气。但不幸的是,父亲因为一桩案子深陷牢狱长达 12 年,这成为一家人的心结和心病,奶奶为此含恨而去。时过境迁,子一代的我们要立志求一个说法,但父亲对此事却已淡然。作品围绕这一案件,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诸如坚强的奶奶,忍辱负重的妈妈、公社书记吴正德、“好友”丁叔,父亲的形象并非人物核心和重点笔墨所在,但父亲面对过往、面对历史的态度显现出一种特殊的气度和格局,父亲已然从历史所留下的巨大创痛之中走了出来,并对历史及其所涉之人抱有一种宽容的同情。这种态度让父亲与历史达成和解,也启发和影响着新一代的人。作品中的父亲形象与历史形成了对话关系,他以自身的疼痛承纳了历史的无理性,也以自身的宽容抚慰整体性的家庭伤痕。父亲连接起历史与当下,也连接起家庭与社会,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
总之,黄咏梅、祁媛、杨怡芬、柳营等的创作,无论是对于现代女性情感和欲望的深度探幽和表现,还是对于父亲形象的书写和重塑, 都一定程度上凸显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即个体诉求与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张力,喻示了在启蒙理性和技术加速主导的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异质性、矛盾性、复杂性,从不同角度呈现了隐秘的时代图景和人性图景,呈现了现代人崭新的存在形态和生活可能性,赋予了当代文学更深广的现实内涵和人性内涵。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