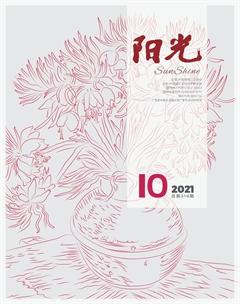一次缺少准备的旅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几件事凑到了一块儿,汇成一股合力,把我推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当年,宣传部办公经费没有严格的预算,报纸杂志,只要部长同意,订就是了,财务不会不给报销。我把雨后春笋般萌生出的各省文学期刊几乎全订了。
那天,翻看河南的《奔流》,翻着翻着,猛然间,我仿佛被电流击中,愣在了那里——我看到了刘庆邦的小说!小说标题和主要情节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与棉花有关,好像主人公是棉农。
后来,拙作发表,杂志上分明印着我的名字,卻远没有在《奔流》上第一次看到刘庆邦的名字那样激动和震撼。因为当时我认为,只要能发表小说,就证明人家是作家。作家和文学,高高在上,我须得仰视。可刘庆邦一下子把作家、文学和我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刘庆邦不是已经发表文学作品了吗?刘庆邦不已经是作家了吗?可他离我并不遥远呀!
1978年,在煤炭部《他们特别能战斗》编辑部工作的刘庆邦来淮南煤炭基地建设工地采访,我奉命接待。几天过去,通过交谈,我发现他除岁数比我小、来自农村外,其它经历和我非常相似:招工进了煤矿,经常被工会、宣传部借用写点儿东西,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编编节目等等。这么一了解,我就狂妄地不再把他看成京城大员:老家河南沈丘,离咱这儿几步远,下过煤窑,没读过大学中文系,不管他混成啥样,和尚不亲帽子亲,都是咱哥们儿!
正因为如此,看到刘庆邦会写小说,震撼之余,我的心思开始乱起来,翻来覆去地想:他可以写小说,难道我不能试试?
其时,我正在严肃地思考人生。
第一次思考人生是高中毕业之后。
1965年高中毕业,因为“不宜录取”,市教育局把我介绍到一所小学代课。靠教书糊口,我才不干呢!更何况是“代课”。之所以应承下来,目的是骑马找马,先干着再说。令人欣喜的是,没过多久,马找到了:一家煤炭基建企业奉调去贵州参加三线建设,急需用人。我一去,呈上高中毕业证书,填张表,干部说,字写得不错嘛,明天来!
当上工人了,具体干什么工种呢?
不仅了解我,也了解我家祖宗八代的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对我说,你最好当技术工人。
我记住了他的话。
可是,那会儿,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我是党的一块砖,爱往哪儿搬往哪儿搬。”服从分配!我最不想留在机关做科室练习生,偏偏把我留下了。
一个批次,招了几百个工人,不足十个高中毕业生。给高中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是党委书记。
书记宣布我到通风科,问:你知道瓦斯吗?我知道,学过的,瓦斯就是乙炔,但我不敢说。书记讲,瓦斯就是煤层和岩石里的气体,还有人放的屁。后一句是典型的画蛇添足,屁不是乙炔,是二氧化碳。我同样不敢讲。
满心不想去机关,看到领导对职工的文化程度如此重视,竟生出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我暗暗给自己定了个目标:用五年时间成为通风工程师。我开始在通风科工程师的指导下刻苦攻读技术书籍。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仍然能背诵技术书籍上的一些章节。比如,煤和瓦斯突出的前兆,书中写道:工作面凉风习习,煤大块大块地掉落,像有人抛掷一样,继而,煤层里响起闷雷般的声音,声音渐次响亮……
横空而来的“文革”彻底打碎了我的工程师梦。分配在机关工作的高中生被批判为旧党委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统统撵走,撵到生产一线……
一折腾就是十年。“文革”把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打碎了。我已经不再思考人生。好歹我有了饭碗,娶上了老婆,还要什么呢?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是哪儿吧!
之所以又一次严肃地思考人生是因为粉碎“四人帮”。
在我认为,粉碎“四人帮”不啻改天换地,一切都要重来。凡是不傻的人都要考虑未来。其时,我才三十岁,来日方长,不能混日子呀,总得有个谋生的技能吧!
我想到过考大学,可这些年没摸过教科书,能不能考取?一点儿底没有。再说,我已经结婚生子。俗话说:“被窝里四条腿,念书白日鬼。”我还念啥子书?还有,拍拍屁股去上学,两个孩子交给谁?老婆的肩膀担得起吗?
我又想央求领导把我调进计划、财务之类的业务处室,学门儿业务。我相信,习练一段时间,我会熟悉那里的工作。可那会儿,领导对我这个“刀笔小吏”使唤得得心应手,根本不可能答应我离开。
庆邦发表小说,仿佛一束光亮照进了我茫然的思绪中。
我朦朦胧胧地看见了一条路,并没有想这条路的深浅和艰辛。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坚定了学庆邦写小说的决心。
那时候,我供职于淮南煤炭基地建设指挥部党委宣传部。这家企业地专级,可以提拔处长,却没有权力把员工的身份由工人转变为干部。权力在市人事局。人事局规定,只有在生产一线担任职务的工人才有资格转变身份。
如此,我和指挥部机关另几位长期“以工代干”的伙计被派遣到了施工处。施工处的党委下发一纸文件,任命我们为掘进队副队长。
我所去的施工处正是当年招收我为工人的单位,那里的人从上到下我都熟悉。党委书记对我说,掘进队副队长吃几碗饭你是清楚的。我自然清楚。我从通风科被撵出去,撵到通风队。掘进队打硐子,我们送风、测瓦斯,天天肩挨着肩。塌方掉顶,我亲眼看到过掘进队的干部冒着掉落的石头爬上去接顶。石头砸在安全帽上当当作响——危险时刻掘进队干部是要玩儿命的。我哪儿是那块料!书记与我开玩笑,说,人家讲,你这次来镀金,只是转变个身份,哪够得上金,最多算是镀铜。政策非逼着我们作假,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名单在掘进队,开资在掘进队,人不用去,去了碍事,找个地方住下来,别瞎跑,别惹事,上级来考察,我就说你在哩。人事局文件一到,你立马滚蛋。
我住下来了,什么事也没有。天天打扑克、打麻将,输了脸上贴纸条,头上顶鞋底……渐渐的,我厌倦了,无心于牌局。刘庆邦发表小说的那期《奔流》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终于下了决心:写小说!
我构思的第一部小说名叫《畸形儿》,说的是一对儿右派夫妻,受尽折磨,为了生存,男的带着儿子,女的带着女儿,改名换姓,天各一方,从此再未相见。粉碎“四人帮”后,阴错阳差,儿子和女儿相识了,最要命的是他们相恋了,结婚了,生下了一个畸形儿。真相大白后,妈妈绝望地跳了江……
构思那会儿,越想越激动,这么曲里拐弯的故事难道不能让读者的眼泪夺眶而出?可还没写到一半儿,我自己反倒没有激情了,觉得我编的故事似曾相识,古往今来,不知道被重复了多少次。犹豫许久,一狠心,把写好的稿纸团巴团巴,扔了。
重起炉灶,写了一篇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作品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两万字。
因为心里没底,我没有勇气将作品寄出去。要不是又发生了一件事,那篇小说也许会被永远束之高阁,而且也不会再有我后来的小说。
与市文联的一位同志路遇。他突兀地问我,写不写小说?我愣住了——难道他知道我在写小说?没等我作答,他说,鲁彦周领着《清明》的一帮编辑带着几麻袋稿件来淮南编稿,他们问,淮南有没有人写小说?你要是有小说,赶快送去,人家快走了。
我的第一篇小说就这样到了《清明》编辑部。
因为稿件两万多字,编辑认为是中篇,同时认为我不具备驾驭中篇的能力,建议我就文中的情节结构一个短篇。
短篇发出来了。我一点儿也不兴奋,因为我知道作品得以发表出自于《清明》的答谢地主之意。论质量,这篇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登上当年比较火的《清明》。
不管怎么说,小说毕竟发表了,许多人看到了,看到的人并不管作品的质量如何,他们只得出一个结论:蒋法武这小子挺能,还会写小说!还有人见到我居然称我为作家!把我羞愧得恨不能钻到地缝里去。骑虎难下,我想不写都不成了。如果第一篇被毙,我很可能就不再写了。我是一个缺乏毅力的人。
第二篇小说脱稿后,往哪儿寄呢?又想到刘庆邦。于是寄给了《奔流》。
《奔流》很快给我回信,对作品给予较高评价,并且还让我帮他们组稿,组稿的对象是“如君之水平者”。
真正给我鼓舞的是第二篇小说。编辑的来信不知被我偷偷地读了多少遍。
我就这样写下去了,写小说,短篇、中篇、长篇,还写报告文学,电视文学剧本……
我喜欢一句话:“人生就是一次旅行,从出生到坟墓。”文学活动是漫长旅行的一个分支。
我稀里糊涂地搞起了文学。要是说我一点儿没有准备,也不尽然。我还是喜欢读书并且读过一些书的。生活在矿区,没见哪家有多少藏书,左邻右舍也鲜有读书人,当然没有人指导我读书,碰到什么书就读什么,只要读得下去。小学时,我读的书多为纸张泛黄的武侠小说和说书艺人的唱本。例如,一本写武则天的书,纸张黄得尤其厉害。这样的书,不敢拿回家,也不敢大明大驾地带到学校,只能在晚上凑到昏黄的路灯下读。书中有个情节,武则天和男人一夜后不满意便把男人杀了——为什么不满意?我不懂。杀的人太多,冤魂直冲斗牛宫,惊动了巡天的南极仙翁。南极仙翁拨开云雾一看,看到了躺在乱葬岗上的一个泼皮。这个泼皮因为勾搭女人——勾搭女人?干什么?我也不懂——被女人们的丈夫们打了个半死,扔在了乱葬岗。南极仙翁便拍了拍坐骑。坐骑是头叫驴。叫驴化作一股青烟,附在了泼皮的身上。奇迹出现了,泼皮的“阳物陡长三尺三”。阳物?我更糊涂了,以至于逮到谁问谁:什么叫阳物?初中时,读的书高档了一些:《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小城春秋》……真正接触名著,是在高三下学期。高三下学期,尽管老师私下里一再对我重复孟子的话“教不分类”,可我从方方面面的迹象判断大学的门对我已经关闭,我是不会被录取的。复课迎考,我只消做做样子,等着应付完高考——不敢不应付高考,因为当年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拿毕业证走人。我耗在了学校里。干什么呢?我有位同学的姐姐在一所中学图书馆工作,通过她,可以定期去借书。这一段时间,我看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杰克·伦敦的《海狼》、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可惜,我读这些书,只看热闹,不会看门道。书少,想看的人多,一本书给我阅读的时间最长两天,莫泊桑的《一生》甚至苛刻到让我一夜读完。如此读书,能读出什么门道?
读书应该是从事文学活动的最重要准备。我基本缺失。
倒是进入煤矿后,无意间习练了文字功力。
我刚入矿门的那会儿,高中生极少。我在通风队工人中算是最大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少,偏偏那时候不论大小单位都必须生产“文字”:编墙报,写决心书、大字报,替队领导起草大会发言稿,给目不识丁的师傅写家信……干这些事儿,舍我其谁?诸如此类的文字我写了太多,可这些东西与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终于与文学沾上边儿了。“文革”时,各单位都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巡回演出,今天你到我们这儿来,明天我到你们那儿去,周而复始,你方唱罢我登场。我莫名其妙地被领导指派去宣传队编节目。胆儿忒大,一天没干过,领导叫去就去了。三句半、对口词、表演唱、相声——我居然敢写相声!……写着,写着,我不满足了,斗胆写了一出独幕歌剧。写剧本最难的是首先要考虑角色,宣传队大姑娘小伙子拢共二十几口子,谁能演歌剧?能演什么角色?我必须量体裁衣,据此来编剧。到底还是写出来了。事也凑巧,当年贵州一位赫赫有名的大戏剧家(好像叫魏然)流落在六盘水,他看了我的剧本,很是夸奖了一番,说我的戏有人物、有矛盾、有冲突,好!当着我的面,他动笔修改,确实得佩服人家!改动的都是地方。经他动动手,剧本大大地上了一个台阶。
剧排出来后,居然惊动了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他们派员来录音,拿回去播放。一时间,大山旮旯儿里的高音喇叭都唱我的戏。我离开贵州后,这个戏还演了很长时间。
我“出名”了!以至于我从贵州回到淮南,淮南文化局(那时候文联还没恢复活动)很快就知道了我。
我的处女作应该是这出小戏吗?
上述冗长的叙述是我文学活动的所有准备。
当然不行!
鲁彦周先生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你喜欢哪位作家,就把他的所有作品和评论都找来,一本一本仔仔细细地读。
可惜,我没听他的话。我喜欢热闹,怕冷,担心沉溺于读书,一段时间没有作品,人家把我忘了。
底气严重不足,耍点儿小聪明,倚仗厚实的生活,在文学活动的旅行中跌跌撞撞地走了二十多年,没留下一部像样的作品。我还活着,作品已经悲哀地死去了。但我不后悔,因为文学,我多读了不少书,多走了许多地方,多接触了一些学识渊博且志趣高尚的人。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阳光》约我写这篇稿子,令我无比感动。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动笔了,调离煤矿也已二十年有余,他们居然还记得我!
《阳光》是供矿工阅读的刊物,我的这篇短文也是写给矿工中爱好文学的朋友们的。请原谅一位老人的絮叨,我希望爱好文学的矿工朋友汲取我的教训,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怕冷,不要圖热闹,要耐得住寂寞,读书,读书,读书,博览群书,好看的书读它个十几遍……先把基础打牢筑稳,如此,还愁写不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蒋法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当代》《花城》《清明》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二十余篇,出版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两部,拍摄电视剧共九集,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气场》《爷们哥们妯娌们》《瓦斯》《老婆奶奶丈母娘》《矿东村0号》,八级电视连续剧《黑脸汉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