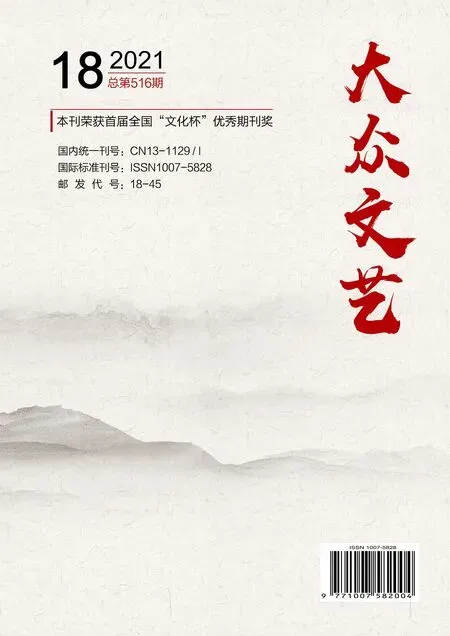“显与隐”:身份认同与叙事机制的耦合
——评影片《地久天长》的人物形象塑造
张 雪
(青岛大学,山东青岛 266071)
一、“显”于时代:多元化的叙事机制
影片《地久天长》运用叙事文本和想象空间存在着的顺序、时间和视角三种关系将影片30年里发生的故事用3个小时进行讲述,叙事机制多元化,叙事脉络清晰。
王小帅导演在采访时提道,影片的叙事抽掉了时间的存在,他是按照故事情节结构的发展及人物关系的变化,形成多时空交叠的叙事方式。由此可知,导演采用了阿尔贝•拉费所称之的“大摄像师”作为操纵电影叙事的机制,将故事发生的自然顺序与事件被叙述的顺序打乱。导演正是通过“大摄像师”操纵下的概要的非等时状态将30年的历史叙事放置到3个小时的影片中,使得叙事中的人物具有多重叙事的戏剧性与沧桑感。
影片将作为第一叙事层的现实时空和作为第二叙事层的过去时空进行了割裂式的表达,二者互不干扰,却又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合二为一”的作用。对于第一、二叙事层的转换,影片并没有采用淡入、淡出等技巧性剪辑,亦没有通过人物视点的直接式回忆。但是,通过运用长镜头、景深镜头对人物所处空间背景的塑造,能够迅速地将观众带到特定的年代,让观众感受到年代的真实。在第一叙事层中,荒凉的厂房,需渡河外出的住地是刘耀军和王丽云当下生活现状的真实写照,同时是他们内心对世界失去希望的体现。而在面对高耸林立的大楼时,所体现出的陌生感是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与世隔绝”的避世体现。第二叙事层中,轰鸣转动的机器,是他们勤劳工作的象征;街墙上大写的“四个现代化,一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子”是计划生育年代他们父母梦的断裂;辞退会议被淹没在人海的他们,是市场经济改革下成为“牺牲者”的必然。在第二叙事层中,苍茫的影像风格、多偏黄偏绿的低饱和度色调,失去阳光照耀的影像空间,是人物在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意识微弱的体现。
影片《地久天长》按照将叙事角度分为所知角度、视觉角度、听觉角度的方式来讲,无论三个角度中的哪个维度,导演都尽量使观众和人物保持统一,使摄影机与画面内容处于一个客观的叙事状态,不破坏人物的心理空间。这种处理方法,能够将站在史诗的立场见证主人公刘耀军和王丽云的成长与痛苦。种处理方法,能够将站在史诗的立场见证主人公刘耀军和王丽云的成长与痛苦。这种不断跳跃与交叉的时空关系,增强了观众在不同叙事时空的沉浸感,更直观的呈现出时代背景对于个体人物的影响。
总之,影片《地久天长》从顺序、时间、观看三个叙事角度,将时代的变迁、命运的无常、人物的渺小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隐”于内心:身份认同的模糊与缺失
陈国验在其著作《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对认同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此外,身份认同相关的概念有多种,根据对文献的梳理,此处主要从社会身份认同和个体身份认同的两个视角对刘耀军和王丽云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Tajfel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在群体的成员所具备的资格,以及这种资格在价值上和情感上的重要性。”而这一个体的认同体现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语境内,也就是说,文化身份对认同感的形成十分重要。显然,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的身份认同建构必然要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影片跨越了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刘耀军和王丽云的半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严打严抓时期的人心惶恐、改革开放时期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海热的浪潮以及21世纪房地产经济的兴起等近些年来象征着中国发展历程的事件。“文革”结束后的工厂筒子楼生活使得两家人成了挚友,而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两家人由一家主动辞职下海经商到另一方被迫远走他乡,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人生。即使多年后再相见,曾经美好的感情残存,但在小地方修车的刘耀军和搞房地产经济风生水起的沈光明注定再也不是一路人。刘耀军和王丽云从包头漂泊在福建二十多年,他们在那儿是听不懂异乡语言的异乡人。而回到了故乡后,面对故乡变化的天翻地覆,他们又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这种意义上,刘耀军和王丽云已经成了没有根的、孤独无依的浮萍。他们找不到以任何情感和价值融入社会群体的理由,他们的社会身份认同已经缺失。
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提出,“个体把自己扮演为某个角色,能从几个‘重要他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并把他们概括为一个‘泛化他人’。”这一理论基于人处于在社会角色的扮演阶段。也就是说,个人的身份认同的形成是和自己扮演的角色息息相关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父慈子孝、天伦之乐,更有“无后为大”的说法,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后代”即孩子对个体生命的重要性,也体现出父母这一角色在人生旅途的必要性。刘耀军和王丽云半生都在是否成为父母的波折中渡过,两次进医院使他们彻底告别了父母的身份。因为自我父母角色的缺失,他们无法将社会群体的目标融入自我,更不必说让自己扮演的角色被社会认同,因此他们无法形成完整的自我。失去自我意识的他们,选择放下一切,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游离一生。此时的他们内心已经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或许正如刘耀军所说“我们都是为了彼此活着”,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是想活着。以至于在王丽云发觉刘耀军的异常后,选择自杀的方式与世界和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们是“顽强”又不知意义、没有目的地活着。
诚然,无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个人的角度,刘耀军和王丽云因为失去孩子都无法完成他们的自我身份建构。于社会而言,他们是孤独的个体,彼此依靠;于个体而言,他们失去了成为父母的角色,不能构成心理的完整性。因此,他们以“活着,又好像没活着”的状态存在着。
三、“和”于当下:传统文化的彰显
由古至今,“和”一直融入在中华传统文化与思想中。无论是孔子在《论语》中谈道,做人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还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都表明了两位圣人对为人处世讲求“和谐”的人生观。而在影片《地久天长》中,“和”或者“和谐”的思想体现在刘耀军和王丽云善良、隐忍、避世、不争不抢的人物形象上。
影片中刘耀军和王丽云两次进医院,两次经历“失去孩子的痛苦”。医院楼道大大的“静”字,隔开的不仅是急救室前人物内心的悲痛的叫喊与楼道可怕的寂静,更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善良和世界对他们的不公。他们第一次进医院是计划生育时期,朋友李海燕在面临“情与法”的选择时,坚定地选择了“法”让王丽云打胎。尽管王丽云和刘耀军内心悲痛万分,但他们都没有直接的怪罪李海燕,疏远他们的朋友。王丽云选择用一句“对不起”诠释了自己的悲痛,而刘耀军则是一直怨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妻子和孩子。他们没有和往日的老朋友倾吐任何内心的不满,他们始终用隐忍、宽容的心来看待昔日的朋友。第二次进医院则是因为沈浩的无知和顽皮导致了刘星的溺水而亡。可以说,他们成为“失独”家庭与李海燕一家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30年后,面对即将到达生命尽头的李海燕,他们是那样的平和又具有文清,他们千里奔赴,来见李海燕最后一面。他们始终没有过直接的怨恨。最后导演用稳定的三角形构图来诠释沈浩坦白时两个人像水一般平静又波澜起伏的复杂心理,他们没有责备、没有谩骂。对往事的宽恕,亦是与自己的和解。
面对时代的冲击,他们没有选择继续抗争,而是用道家“道法自然”和“出世”的思想选择顺其自然。无论是计划生育的打胎、还是下岗时的被辞退,他们都没有主动和时代反抗,而是选择“逆来顺受”。养子“刘星”的到来,给了他们又一次成为父母的机会,他们是那样的欣喜和珍惜。但当他们面对养子“刘星”的离去时,他们没有阻挠,而是给了他象征社会身份的身份证,让他自由地奔走在自己的人生。当最后养子“刘星”带女朋友前来看望他们,他们更是表现出了绝对的热情和欢迎。影片最后的大团圆结局,是令人欣慰的,也是令人心疼的。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和往日的朋友还能说说笑笑,去看看昔日的家的模样,养子的归来又让他们拥有了父母的身份;心疼的是他们再也回不去了,他们离开前有星星的陪伴,一家人温馨无忧。而他们现在只能坐在星星的坟墓上,以酒浇愁。面对如今搞房地产经济事业有成的沈光明一家,他们无异于成了时代的弃儿。显然,眼前虚幻的美好无法弥补他们30年来绝望的心。
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尽管受尽命运的挫败,但他们仍然用儒、道中的“和”精神继续前行,选择了与世界和解、与自己和解、与命运和解。
综上所述,影片《地久天长》表现出的在时代变革下,人的弱小、无力,与生存的艰难,同样表明了导演王小帅始终未脱离对小人物生命状态的关注。“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导演通过对过去中国30年的历史变迁的反思,也体现了在当今新媒体快速变革的视域下,大众应该如何去审视自我的身份与情感寄托,才不会重现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导演将这个答案用最后的大团圆结局无形地展现了出来,那就是用心体会、解读中华传统文化包罗万象、交相融合的生命精神,找到自我生命意义的最高点,以防迷失在时代的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