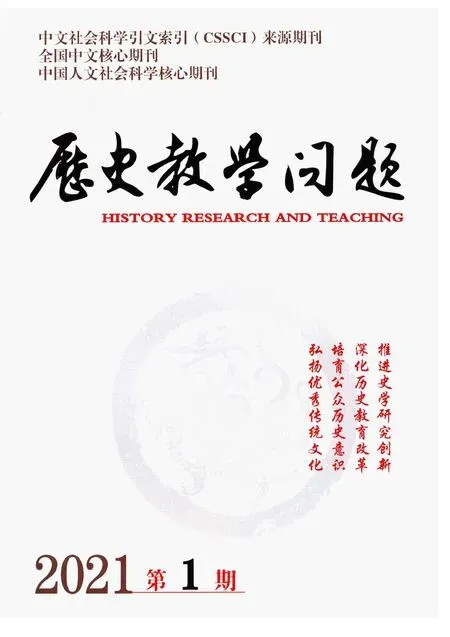吴泽先生早年诗歌、小品及木刻画
邬国义 搜辑整理


但是我又不愿顾虑这些,
五桂洞上杨五郎杨六郎的石像,
长城的古风叫我钦仰了,
我是想像那有些奇异的古溪。
再无力挨步迈进了,
疲乏地向土人买着五碗水,
同伙们团团的席地坐着,
白雾已渗入了旅人的心扉,
青苔是我们暂使的被垫。
引起落寞凄咽的旅愁的,
是那坡上一株萧条而含萌的腊梅。
我仰卧着感伤自身的渺小,
情绪在雾的弥漫里,
又随雾而变幻着。
浓雾里隐没了长城的脚,
看不见左右的台城和山峰;
于是身子开始向天空里浮,
长城向青天里奔走,
我像骑着了一条古老的活龙;
呵,惭愧的我不敢鸟瞰四空,
(什么我能向人类夸耀的,现在。)
牠,前脑已高高的翘在天风里,
尾巴不知还连锁在那个山涧里!
雪花儿在龙身上飞舞,
我的心弦开始向自然界哭诉,
双手裹住一衣屉洁白的雪花,
又悄悄地把帽子压紧了头发,
一群小白兔在蹼缩着。
这里是长城的顶巅了,
一个二丈开方的颓墙败墟,
墟边挂一幅雾的帘子,
我默默的被囚在天牢里,
狂风中我只无语地唏嘘!
墙齿上那多嘴的方方窟洞,
嫠妇般的喧叫着她的寂寞,
我无心去听这些闲话,唉!
饶舌的尽徘徊在台城的周绕!
徒然我也闲着!你诉说吧!
我默坐在墙脚下闭着眼嗷着牙!
“……”
“……”
“那末,这些灵魂还在家吗?”
“唔!她们哟,恐怕都失散了!”
(三)
山巅老树林里的风,
饶舌地诉说古旧的风光;
古柏也不耐烦的缄默不住了,
噜苏地呢喃那主人的坏话。
“我看惯这些破落户了,
你们的主人都是帝皇子孙,
比平民家里司阍,
要光荣的多吧!”
风嘲笑我无见识,
古柏也就不满意,
一个绕着楼阁走了,
一个盘坐着念佛度去了。
大殿里是冰冷而凄凉,
心似黑夜里怒奔的海浪,
椽株间发出低微的鹰啼;
我的头斜依那裸着的柱子上,
脑似乎要破裂但我不敢哭泣。
狂步上险绝的阁楼顶头,
我对成祖的石碑发着交响:
“仰慕你,古今的英豪?
从你亡魂的祭日到现在,
那人生的真谛找寻到甚么了?”
云雾冥冥的深山里,
暮色沉沉的浓林边,
风和古柏再不睨我一眼!
被摒弃的旧式的头盖呵!
满脑点滴黄褐色的劫灰。
思想在故事里奔腾了,
哦!伟大渗积的时间哟!
生着只该自己去践实吗?
(二十年来还是在摸索着。)
流浪流浪着,发现了什么呢?
自己的泥靴惊散了,
寄迹在落叶缘上的灰土。
看,前后脚印都变了样呢,
自然界永久是一幅历史画吗!
一九三四,五,七,于北平
当一个新的冀求里
(静宇、宪真、成壁:自从小伴侣们的队伍失散后,那心园里荒芜到怎样了?)
(北京《黄沙诗刊》第1号,1935年6月,北平黄沙诗社编)
疯狗
残冬的夜的狂飙,
在黄昏的树头上,
我见它
挟着灰土落叶,
怒奔在街头像只疯狗。
眦着眼看透了黑暗?
闷头在枯林里窜!
电线在呜咽高吼了,
但,牠懂的什么?
夜的街头上,
永恒地紧张着憎愤悲壮!
十一,一,黄昏归来后
(北京《黄沙诗刊》第1号,1935年6月,署名“瑶青”)
寻
(一)
流浪者在山野里,
或是在大海边走着。
狂歌一曲《浪淘沙》,
击断了喉头郁结的声带!
我更自由无牵挂了,
像浪心里奔腾的
一尾豪壮的穿山甲?
冲上万仞的山涧里,
但,又被囚在海峡边!
(二)
歌声去了永未回头来,
瘦长的影子紧溅着征泥。
高挂在天空的是轮月亮,
枯枝头也爬着一只夜鹰。
流浪者猖狂的走着,
追随月下的孤鹙。
走向那辽远的西北,
再沿着天柱
瞭望宇宙的究底!
一九三五年,北平。
(天津《诗歌月报》第1卷第2期,1935年6月)
天狗
褐色的少年袖襟上,
乡思在冬天更湿润了。
午夜里的心壁浸沐着思量,
一串太息在生的雾围里埋葬。
少年在轻绡的梦筵下,
眼上飞着沉色的金星,
希望星满袖屉灰白的落叶,
像只天狗狂吼着满天残星。
(天津《诗歌月报》第1卷第4期,1935年8月)
荷花庄的一晚
为母亲四十五周岁纪念作,并呈守乐姨丈、益之表叔,志念。泽
(一)
窗外愁雨点滴,
夜深了,
风在怒吼!
村角,三两只狗,
咬夜行人?小偷?
还是见了鬼!
一声声
拉长了尾音。
墙外是竹林,
林外有桑园,荒坟。
阵阵暴风霾雨,
簷水打上纸窗,
竹筲,爬倒地上
疯狂地怒叫。
悲愤满装着脑腔,
泪眼里,
哟!荒坟上
又浮起零落的鬼火,
红的,绿的,
三两,明灭:
(从竹林隙里射进纸窗,
又从纸窗洞里刺上了
怆腐的心房……)
凄凉的农村,
一颗征夫的怆心!
在此被魔鬼躏蔑的
第一故乡,
怎奈得?
今宵:
重宿旧时的家?
(二)
右房的油灯灰黄,
墙外的风雨如晦,
“呼—拉—拉”
又起了纺纱声!
“耀青,年年的冀待你。
现在也这么大啦,
你曾给你的家……?”
(妈!这能完全责备我吗?
现社会中卑污的一切,
你愿你的儿子去乞求吗?
要找回我们母子间的爱,
创造我们的家?
是在这现实的社会中,
讨乞得到的吗?
妈,能明白儿子的苦衷?)
“你的祖父,父亲,
为什么都早夭亡啊?
(是,都只是二十多岁,
被魔鬼迫(?)死的!)
寡妇孤儿谁来负责?
耕地的,是永被人摒弃的了!
惟恐你再重陷虎穴,
像祖父,父亲,三代一样。
我如何的欣喜你,
十二岁逃出本村去!
但,怎么越长大……
……确越……?……
今晚归来!!”
(妈,我不骗你,
爱我自己也爱别人,
我爱母亲更爱别人的母亲!
我要拯救母亲,
“妈,我们得毁灭
这块大屠场!
荷花庄,是屠场之所有者,
魔鬼的一方啊!”
妈!现在!你需要什么呢?
可是,今晚归来?……)
“呜—拉—”,
纺织声迟着发抖,
“天啊!冀待吧!
尽这付衰弱的肋骨……
耀青!我生着,
我永久同情你,爱护你,
但愿…………”
“咳…咳…咳咳…”
夜深,风雨一阵紧一阵,
右房的妈,
悲痛地啼泣呻吟!
突然,这急促的咳嗽声,
惊落了游子的灵魂。
(“天!保佑妈,永久康健下去,
妈!我想继续忤逆你十年哟!”)
“世界哟!光明何时交替过来?
这塔样高岸的
人间社会层呀!
坍塌吧!爆发吧!”
(三)
荷花庄上归来了
一位郁结的战士,
凶恶的气氛,团住了,
一簇破落的农村。
………………
冀望!
使囚卒越狱重捽法网!
一九三三年,作于常州荷花庄
一九三五年,八月录于北平北大
(天津《诗歌月报》第1卷第6期,1935年10月)
心的爆发
仍然牢锁着世界幸福的宫门?
魔鬼还是奏着绯梦的歌乐?
听蔷薇路上的淫语妖音,
看,这饥寒困迫号噪的乞者……
啊,满腔泛滥着热血,
脑海滚腾着髓汁的澎湃,
砰砰的脉搏,
新旧细胞也在斗杀。
不片刻的光景,
塞住了咽喉,
模糊了眼睛火冒烟腾,
眼前开发一个猩红的世界。
轰隆!辟拍!呼呜——枪声,炮声,
风,沙,土,石,在天空跳跃。
“杀呀!铁血里有自由的花!
反了吧!我们这鬼魔天下!”
热血沸滚了,江河激流,
大众的声浪振塌了山头,
劳苦群众们胜利,成功,万岁!
啊!血肉溅飞弥漫着赤血的云霞!
悠久氤氲着的真气,
今日混沌了这世界,
新的创造呵!
哟!心的爆发!
一九三五,三,五,中大军营。
(天津《诗歌月报》第2卷第1期,1935年11月)
故都乡思
——给故友蓉如
篱笆里的菊花
开了将要谢了!
徒然负着冷艳的性情,
主人早已远泊天涯。
深秋摧残了痴梦,
你何必低首苦思已往?
唉!园门久已塌废了,
主人旅途无恙?
游人站在竹棚下,
探望那三两的盆架,
无心欣赏着秋意吧:
那个像家园的篱笆!
(上海《中国学生》1935年第1卷第12期)
未碎的膜
(一)
团圞的脸,
团圞的腰,
一头黄发,
无数点凹凸的雀斑。
人家都叫她傻丫头,
其实她也有十多岁!
笨重的眼眶上,
终隐存着处女的愁恼。
她永是低头垂气的,
眼光不敢直射。
因为这个现实会使她害羞的。
坑床上横卧着
一个是分区里的警察。
另一个是他的妈……
两个睡在一边,
烟枪灯盘放在
床的中心。
白雾在屋里飞腾了,
警察的脸填在妈的胸口,
一口里抽烟,
一手夹在妈的双腿间。
妈的泪眼眯着笑了,
“小三子的爸真没有你好!……”
战抖的手在警察的腿上,
随着战抖的喉音撒娇?
“可是……你没有傻丫头……”
警察的眼光绕住了
丫头的臀部发狂,
丫头低垂着头,
小脚娘紧抱住警察的腰,
用干枯的嘴唇疯狗似的
在警察的脸部狂吻。
“胡说!……再来一个烟包!……”
………………………………
小脚娘儿老年的魔力,
这时再也破不了这紧张的恶结!
无数滴冷泪向心坎里浇;
脸,手,腿还在试施着
青春时候妖淫的手术?
时候是黄昏了。
小三子缩在墙角的板凳上,
饥饿的肚子搅乱了他的瞌睡;
“警察伯,烧饼!饽饽!
带了几个来?……
妈?咱们还不吃晚饭吗?……”
挨着床沿打着妈,警察
的四条铁般冷的腿!
大烟,面包?
性欲和贞操;
消逝了的青春呵!
生的憧憬,
人生的苦果永远如此矛盾!
(二)
小脚娘儿的脸确够年老,
小三子还只十岁!
小三子的爸是望了,
(在西城做煤活,
据说几年都不回来)
傻丫头的留得清白,
靠女婿过老,也不差!
反正傻丫头,终不会
有什么意外的?
小脚娘儿欣慰了,
花白的头发也飞了起来!
可是近来警察的要求,
无异,是一颗药炸弹,
毁灭,老年生活的寄托所?
警察聪敏的要挟,
小脚娘儿生命的钥匙;
每日的烧饼饽饽,烟灯,私门……
只有警察是她的保护神!
破了的迷梦!
绝望了的人生!
在郁结的喉头
突然嘶出哀啼。
她一手推开了警察,
抱住了小三子。
嚷到坑左边,
窜进了被窝。
缩做了一小团,
像只懒死猫。
小脚娘儿愤恨的爱小三子;
愤恨的答允警察的要求;
愤恨的牺牲了傻丫头;
愤恨在胸腔里澎湃。
千万只魔爪撕碎了气压。
(三)
东房里黑暗伸张了魔臂,
房外刮起了一阵狂风落叶。
抬凳椅子也殓头颈,
一个物件存着一个憧憬?
丫头在朦胧中,
悲伤的心警醒了恶梦。
突然,身上压来一堆肉体。
下体觉着猛烈的疼痛。
“妈哟!什么哟!救我!……”
脆弱的双手摸去
黑暗中隐出一个男子。
彼压着的双腿麻木了,
阴户口一阵肉的刺激,
可怖的润湿,热!
现社会人们的童真呢?
魔鬼爪下践踏了女性!
丫头挺着酸痛的腿,
迷失了肉的感觉!
她恍惚里想到西房的
小三子,妈的那?……
多恐怖的一只夜鹰,
多血心肠的母亲!
她也曾谅解过妈的苦衷,
更曾感激过警察们的好心?
(管保开烟灯,做私娼,
每天的几块饽饽和烧饼)
一幕幕现卑鄙的现实世界,
妈和警察的一切,
她卑视一切蹂躏妈的客人,
更鄙视她自己的妈!
但处女的心,懂些什么呢?
这—人生的矛盾,
肉体和生活的斗争,
永是不瞭解的恐怖的憧憬。
(四)
胡同里的夜狗在怒吼了,
煤炉残渣也在咆噪,
丫头,奋起最后一刻的反抗!
魔鬼的世界,看牠永存?!
纸窗隙里飞出一个粗汉的话音,
妈的,不成!究竟年龄太小。
一九三五、一一、十七,录早年作于北平中大
(天津《诗歌月报》第2卷第2期、第3期,1935年12月、1936年1月)
未完的斗争
——土地在咆哮了
六月的瓜棚边,
碧青的瓜田里,
中间糟蹋了半亩荒地;
成千成万的小伙子,
握着锄头,铁铲,镰刀;
赤着黑背脊,
挺起了铜炼的红臂骨,
每个人的血在奔流了,
有的一团心火郁结在脑海。
许多人踏坏了瓜藤,
把瓜棚围成一个半弧形。
弧形的中间有两个
不同样相的“人”!
一个是本村的三少爷;
一个是三少爷家里的
年长的雇工——阿毛儿。
三少爷半个头颅连着半个脖子,
半个脸部像泥抖的西瓜。
雪白粉嫩胸部腰部,
淌出血红的段段肚肠,
三少爷上月才从天堂回家,
今天确给阿毛逮进了地狱。
三少爷旁边卧着的就是阿毛
两只脚两只手反背的捆成两个结,
黑黑的膊臂胸口闪动着,
和尚头,圆滑滑的,
两只放着火光的眼,
放气吸气的“虎拉”的鼻,
一口火门似的嘴,
一颗头颅凸起千条青筋,
像火车头的煤锅炉
不知道要把手脚
推动到什么地方;
一把染着血和泥的切菜刀
在阿毛眼泪里发着
胜利的微笑。
大老爷竖起胡须,
二少爷,老太太们
拿着棍子扁担向
阿毛身上乱抽
阿毛娘叫天叫地地求泣!
周身凸起了条条血筋,
像发动机的节气管,
火门里燃烧的
那条红舌头在暴叫了,
“老爷紧着你的老骨头打呀!
俺!死了做鬼也不放活你们一个
我的妈,父亲,小细狗
活活的给你们迫着挨饿,
什么‘地租’‘帮工’?
穷人的活该‘贱骨头’
幸得我俩还有气力
来换你们的饭吃。
老爷!不知天大!
三少爷!狗X的。
还说是什么‘洋学生’,
昨晚又迫着我娘儿要强奸!
……………………”
一只眼珠直射在三少爷尸体上,
一溜烟又是慈悲的光芒,
扫射成群的围着看“戏”的
阿张,二大,雄郎……一伙子,
棍棒刺样的落在身上;
锅炉里的血液沸腾了:
“阿张,二大,发现你们的天良!
我阿毛杀人阿毛担当!
可是你们的妈,爸,妻,女
在这世界里谁来保障?
“娘儿,我死了,你还想做人的‘活’?
等待什么呀!傻女人!
绵羊在虎狼前摇尾乞怜吗?
去!干!………………”
火门,眼珠一道道铁线,
牵着阿毛娘做女英雄去。
瓜棚上那柄杀人的菜刀,
给阿毛娘一手夺了过来,
“狗老爷,你也有今天的末日哟!”
菜刀在瓜棚内起了血和泥的光,
小伙子群里的锄头,铁铲
一柄柄的向人头里飞扬!
一九三三年六月脱稿于故乡农庄,在一个雷雨急下的午夜
(北京《黄沙诗刊》第2号,1936年1月;又见《文艺月报》第1期,1937年1月)
二、小品
思囚
(一)
寂寞,死亡,沉静的空气,满塞住了囚狱般的旅寓。
闷在被窝里,听外面的声声爆竹,老丁卷着被儿向床里乱缩。
这样的一个除夕,为什么干自挖苦呢?我便决意跳出床来了。
我想今天不用脑了,想,一切也是徒然。还是把身心修养得无思无虑;不追忆,追忆是会伤感的;更不推理未来,前途的憧憬,又会添加烦恼的。今天,除夕了,我想决定不再多顾虑吧。
对面的墙壁上一位裸体的女像,坐在石块上,看海边的白鸥。我似乎发现了人类的神秘,聆会到自然的妙音。
我的忧究竟被什么消蚀了呢?女神呵!我现在不能礼赞你!
伟大的白鸥呵!我想和你同飞到海那边去……
我流泪暗泣了,我只徘徊在屋子里,为什么我不能把握我的脑袋?思想是长长不断的,我怎样过以后的日子?
(二)
钟表指着九点了。
老丁也怪会玩的:拿着白纸,上面写了“丁氏祖宗之神位”供在靠壁的桌子上。燃着一枝“芭兰香”插在桌缝里,一壶白干酒,三个隔着几星期的殭馒头,一枝一寸多长的残余下来的白洋烛,陈列着。他头发蓬蓬的一眼苦望着我,满脸惨笑的。
——小吴!他叫着我,我一壁看,一壁笑!微微地给他暗示。两个人目光交射着。钟在的塔的塔的走着。
——小吴,我们也来拜祖宗……
一缕缕的香烟,在房中飘渺。我再也不食不流泪,我再也不能不回忆,回忆到南国,家乡,忧!……
烛光在日里更是暗淡无光。游子的心呵!怎堪境遇的潦倒。
烛哟!
你的火焰莫苦嬲客魂吧!
沦落人,
那堪你,这油泪数行!
心底里发出飘渺的低吟,周身痉挛着,打了一个寒噤。
(三)
盛宴散后,酒,泛起了我可怖的思潮。老丁和我一样的,一晚上,不知如何诉说了他多少旅雁的悲怆。
我走到院子里。
我喜欢迷濛的夜里。为着希望创造我新的生命,我忧这无轮郭的黑影。
我的天真究竟消散在哪里去呢?我究竟是怎样的找回我现时应有的快乐呢?
年轻轻的倒像老人般的怪憧憬着世事,明瞭人生是怎样没生趣的玩意——于人于事使我抱着沉默,胆慓。生活像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死神底狰狞的脸具会到面前出现似的。
——这真是除夕!末日?为什么尽是黑暗?我向眼角里反映着的一个黑影追问。但是,没有声音来回答我。
——瑶青!你忧着黑暗吧!我总是这样向自己叫着。虚幻的心灵无形中会低微了恐怖的战慓和振荡。我似乎也留恋着黑暗。
我为什么要有脑袋?思想残破了我的青春!使我闯上一条萎靡的路?唉!我的脑袋呀,你太忍了!无韦地把我痛苦,沉沦,灭亡……
我知道思想在脑袋里长成的了。童年时的学安琪儿般的飞,吃甜的葡萄糖……现在,快乐的梦是不会再做到了。
我追求人间的忧,我更搜求人间的憎。忧,我也接收过的,人心的沙漠里已经使我憎……。然而我的美满的憧憬,是会被我的追求和搜求所灭亡的。
我知道我自己,我是应该被幸福摒弃的人了,我不再追求,我不该如此希望了。
我发现这世界的人间是没有纯忧的存在,所有的光被遮蔽了。我的手里捧着我的心瓶,走遍了沙漠的人心的世界。竟掉碎了牠呢?唉!
呵!光明在现社会可追求得到的吗?但是,我为什么跟着别人这样做呢?
我只需要创造。因为创造,总是彻底地走向光明的大道。
(四)
寒风刮着枯枝儿悲鸣,夜已是深沉的,坑一般的闷漆一般的黑。
啊!什么是我眼见到的世界的光辉,人类的生息?寒风挟了夫利沙粒在隔墙的胡同里乱窜,院里的树叶莎莎淅淅的哭啼着。周身寒气侵蚀,心琴不住地战地战慓。
啊!这古老的死城呵!这是除夕!这是除夕!
风来到院子里,挟着树叶,四壁乱窜。几声“督督”的寒柝里,消失了它的生命,灭亡了它的青春,埋葬吧,这深闇的黑坑!埋葬吧,这肮脏一切!
我醉后的心琴,是断弦了。为要把握这残破的生的余味,想唱出我游子残破的音调:——
啊!深夜的落英!
啊!断弦的心琴!
啊!残破的青春!
一九三四,八,二九,录早年作
(北京《进展月刊》第4卷第3、4期合刊,1935年5月1日;又见北京《文艺月报》第1期,1937年1月,署名“吴瑶青”)
三、木刻画
火酒烧毁了心窝——工人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