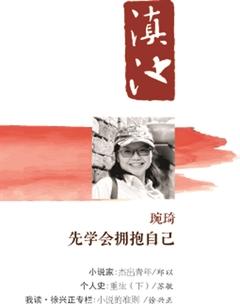张庆国论之二 因缘际会,微妙人生
蔡丽 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近年来注目云南当下文学批评和研究,发表论文几十篇,著有《当代云南文学批评论集》。
张庆国的小说创作很有自己的特点。这些年来,他的创作一直以相对均匀的速度推出,差不多时候推出一篇或者一部,隔两年又推出一篇,中篇居多。呈现出不急不缓的创作状态。没有说一段时间高潮爆发,一段时间又苦于找不到写作灵感这种事。他很平稳。读他的作品,总能感受到一份自在的滋味。作家的自在安稳感,不是阅读者本人的自在感。怎么解释呢。首先,你能感觉到他的写作非常自我,不怎么关注文坛的流行趋势,也不怎么去钻研什么样的创作更吸引眼球,不去尝试新的叙事手段、叙事语言,不管外国的哪个作家如何精彩咱们如何模仿,他就是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故事。甚至在作品中看不到一种刻意努力追求的、要让自己获得某种的意图。我猜这个作品到底如何他可能都不怎么去想,他只要自己觉得有意思,挺好,喜欢写就可以了。写作非常的自然。顺其自然,自得其乐。当然,我没有向张老师求证。我只是读他的作品之后获得的阅读感。这样的阅读感也的确很新鲜。目前而言,阅读大多数作家作品,你都能感受到作家的一种强烈的追求。作家通过他的人物,故事,整个结构设置,来传递出某种写作追求。他可以是主题的追求,也可以是叙事实验的追求,甚至是自我某种意识形态的追求,某个获奖的追求。读者在阅读中,除了感知作品人物,故事传递的人生欲望、思想,同时还感知创作者的人生欲望,思想。大家都知道,在写作中,作家个体意图、主叙事外的个体意图渗透多了,过于明显了当然不是好事,但很难避免。也不需要追求完全避免的所谓零叙事、纯客观。然而近些年来的创作,作家的某些意图,和现实利益相关的某些情绪,自身人性的某些欲望、思想渗透到作品里的现象确实比较突出。写的行为就显得很突出,甚至做作。张庆国给人的感觉,仿佛一个对生活充满好奇的人,抬个板凳坐在人们中间,温情脉脉地去注视,去观察,兴致盎然地去倾听,然后自己高高兴兴地去琢磨其中的情致,奥妙。获得一点心得体会,就开心极了。看到张庆国这种安然自在的、沉迷于故事,沉迷于人生情致的写作状态,就觉得很感慨,这种写作很纯粹。
张庆国的小说,在整体上给人轻盈之感,非常富有生活气息,读后使人觉得亲切舒适,如沐春风。他不去折腾恢弘壮丽,锣鼓梆敲的大人生,沉重的、苦涩的、残酷的、悲痛万分或者荒谬绝伦的,都不在他的作品里。他喜欢写平凡人物、小人生、副人生。无事生非的雨季,钥匙的烦恼。看看这样的标题。他的笔下多是普通人,身边人。报社的编辑,电台的主持,一般的上班族,邻居大妈大婶,单位领导下属。去单位上班,菜场买菜,下班接孩子,周末某个饭店聚个餐。偶尔去外地开个会——一个城市的主体上班族。看着这些人在小说里跑来跑去,忙这忙那,仿佛是看见自己。他主要关注的,不是要人命的、几年几十年的大事件,他喜欢注目的是饮食男女的那点心照不宣的暗生活,一如既往的生活里一点横生的枝蔓,一点意外引发的隐秘情事,一个小事件衍生的一堆小烦惱小事件。当然,可能也有要命的悲剧。但这悲剧来得突然,几乎令人不信,令人暗中想要篡改他作为小说的习惯性的精彩悲剧结局,而回到生活日常的庸俗黯淡的层面。比如《黑暗的火车》。而且,他的书写又是那样自然,行云流水般地,没有强调渲染的意思,没有突出刻画的意思,没有精心设计的意思。所以他笔下的人生,多半是切近的,安稳的,和谐的,对那一点生活的涟漪,人生小小不言的意外,作家总是带着一点戏谑,以及阔大的宽容和满怀的温情去描写他的人物,构筑他的人生小传奇。
一、气候左右下的人生关系
人物要出场,舞台得先准备好。在张庆国的小说里,人生故事展开的背景,人物活动的场所,写得鲜明生动。首先是城市。昆明这座小城,作家生活了一辈子的这座城市,是他的小说再自然不过的背景。有些作家的写作,会有意识地模糊背景,使地域的标志更具抽象性,有的作家的写作基本关注人但基本不关注城——他更倾心于故事氛围下的某种匹配场域。但张庆国的写作是偏于写实的,当下性的。老百姓城市大街上的生活表现。昆明城,昆明人的生活,几乎信手拈来。《钥匙的惊慌》展现城市寻常日子的一点小烦恼。对昆明的街道展开描写:“东寺街是昆明城仅存的三条历史最为久远的旧街之一,狭窄而绵长的街道,木板矮楼,低垂的爬满马浆草的瓦檐,拥挤的歪歪斜斜的铺面,使人觉得恍然爬上了时间的沉船。”寥寥数语,一条街的过去现在,历史未来,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而且,这不是去查资料写出来的大街,查资料写出来的大街有掉书袋之嫌疑。是一个城市的老居民几十年与这大街来来往往的生活感受,具体的陈述和描写都省略,只剩下大街予以人生的一种观感,干脆利落之中自有一份作者独有却又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气韵。
有些作家,现实的或者历史地关注城市与人这个主题的作家,他会很有意识地去塑造一座城市,刻画一座城市的性格,叙述这座城市的历史。他的城市书写,是和表现这座城市某个人物或者家族的历史,人生是两相配合、齐头并进的;为人作传,同时也为城市作传。作家和城市最终互相倚靠,共同留名于文学史。张国庆在这座城市生活,大部分小说也是写这座城里的人,奇特的就是他没有郑重其事地占有这座城市的意思。他写这座城市,偏于轻描淡写,显示出一个长期居住于此的人毫不经意然而又享受其中的感觉——不刻意,但着笔之处,又能够瞧出一个老居民的身份。“文庙大门口灯光闪耀,这个一百年前供着孔子的斯文殿堂现在是舞厅录像厅电子游戏室台球室等五花八门的时尚娱乐混杂之地。”一句话,就把昆明一著名地标的前世今生写得通通透透。
昆明城最具特色的,是它的季节混乱。为此,作家感受极为深刻:“昆明是一个季节错乱的城市,在数九寒天的日子里,天空一派明媚春色,满街的花木争奇斗艳,女孩子们穿着长裙和薄薄的紧身毛衣,噘着鲜红的嘴唇招摇过市。近日公园的露天冷饮摊生意兴隆,男女老少坐在刺目的阳光下高谈阔论,深情怀念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白雪飞扬的时刻。忽然一夜寒流偷袭,四月的大街阴风呼号,刀片一般锋利地割开行人的皮肤,暴雨如注,黑云低沉,冰雹穿过雨幕,像密集的子弹残忍地向四处惊逃的孩子们射击”。
昆明城无所谓春夏秋冬,天气说变就变,一天气温可以差距20度。老天爷大起大落,变化无常,影响着人们的行动人们的心情,也五行中造就无数奇特的关系,幻生无数意料之外的人生。昆明没有春夏秋冬,却有雨季和旱季。一年中雨季和旱季交替,全国上下热得一塌糊涂,昆明正是雨季的阴凉天,温度在18至25度之间。同样的,全国人民都冷得哆嗦,昆明天天艳阳高照,小伙子们可以穿短袖。同样,一天中温度可以相差15度,下雨即成冬天。头顶上这片天空如此神奇,如此变幻莫测,昆明人的生活就时常会有惊喜,会出意外。文学热爱的就是打破陈规,意外纷呈。昆明城的作家,是否应该比别处的作家更多些生活刺激的新鲜感?还是因为没有分明的四季而老是感觉混混沌沌日子没变化?
《无事生非的雨季》这篇小说,简单说来就是,都怪雨,因为雨。雨变成了一个顽皮的小孩,手里牵着三个木偶。小说从电台女主持和歌词作家之间关于雨的争论开始,拉扯出电台女主持和遥远的一张富康车内听播音的车主李二男之间的地下情。两人从相遇到亲密,别别扭扭,总算顺畅了。然而,一场暴雨从天而降,拉开了雨季的序幕。雨季让电台女主持特别烦心。因为,“骑车穿过街道上班变得相当艰难,塑料雨衣和橡胶雨鞋无论设计成任何花样百出的款式,对她来说都是累赘的丑陋的,持续不断的闷热和潮湿,使空气黏稠而令人厌烦,她与报社一个叫李二男的男人的幽会,也被一阵阵突如其来的疾风暴雨破坏,变得毫无规律。”然后,小说就进入到了李二男,女主持,二男老婆毛妹被雨丝牢牢牵扯的三角关系中。因为下雨,李二男与情人幽会找借口撒谎,引起了老婆毛妹的怀疑。因为下雨,女主持无法像往常一样坐情人的汽车上班,有规律地幽会,只能自己骑车或者坐公交上班,由此和情人生出烦闷。然后,我们看到,雨构成了三人之间神奇的拉锯战。下雨天,李二男去幼儿园接儿子,按时回到家和老婆团聚,老婆毛妹心情舒畅。晴朗天,老婆毛妹去接儿子,李二男去接情人,二人愉快地偷情。小说还有一个细节极富喜感。天空飘雨,空气寒凉,李二男酒醒,想起了家中的老婆儿子,拔步走向了同样孤单的情人。
这是一篇堪称神奇的小说。是一篇读完之后轻松愉快、细想之下让人惊呆的小说。你会讶异一个作家他居然想得出来。没有一个漫长的、毫无规律的雨季,怎么会有如此微妙奇特的三角关系?而只有一个作家太熟悉这样的气候,熟悉这种天气对人们生活的神秘无声的捣乱,才能够发掘出城市的独特气候对城市的独特人生的创造力!《无事生非的雨季》这篇小说的欠缺之处,是生活细节、人物细节展开得不够充分。它似乎粘着在吴雨和李二男之间近乎无事的情事,感觉到作者的笔在这里有点迟滞,陷在一个模糊的泥淖里拔不出来。文字行进了很久,而内容却比较稀薄。另一方面,它在生活细节,人物关联上的展开又匆促了,比如三个人因雨而生的较量,这种奇特的弹性会盛开怎样精彩绝伦的情节呢?又会在某一个雨丝绵绵或者大雨倾盆的时候,三个人,会有什么故事呢?读者在期待中。但写作停止了,写作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绽放。同时,小说中的几个次要人物也都极富个性,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某种生活癖性,却又在伸手可触的现实生活中,是既有个性的生动性又生活化的人物形象。小说描写这些人物,已经打好基础开好头,却又把他们轻飘飘地滑过去了。如果进一步对他们进行刻画,展开,按理应该构成某些令人叫绝的情节,但这几个次要人物没有站立起来,感觉是写作者拿眼细致打量了他们一阵,就把他们抛弃了,變成名副其实的次要。人物角色在小说中他不是主要身份,但并不表明写作者对他的写作就是轻描淡写不重视。次要人物、二号人物的精彩恰恰是很多经典作品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地方。如果这个小说继续前进一点,次要人物进一步展开,和主情节形成穿插,这部小说就更有意思了。
二、无意横生的枝节
生活按部就班,每个人似乎都在重复着一成不变的日常。然而,生活似乎又如天空的云霓一样,各种力量冲冲撞撞,有意无意之中,因缘际会神光离合,团生出异样的花朵,捏造出人们根本无法设想的形态。谁能预测天空飞动的云絮会幻化怎样奇美的风景?谁又能够预料生活沸腾的海洋会拥挤流变怎样奇怪的浪花?生活本身即在各式各样的创造中。《钥匙的惊慌》写防盗笼。安装防盗笼堪称中国特色。很多小城市极为流行。为居民楼老百姓装修房子必备。最近几年政府为整顿市容市貌严加打击,坚决制止和拆除,安装防盗笼的行为才有所收敛。可以说,它是小城市老百姓过日子曾经的最熟悉的最亲切的挚爱。《钥匙的惊慌》就写了一个人因为安装防盗笼而引发的一系列不大不小的纠扯。这篇小说语言流畅幽默,叙述描写生动传神。比如写花园酒家:“铁门进去,眼前出现一块平整的球场,餐馆的宽大门面气势磅礴地站立在球场边。只见四根花岗岩圆柱冲天而起,撑起了一条雪白耀眼的雕花长檐,长檐下的墙壁上,镶着一个个古代西方的美人和武士,球场另一侧,停满无数闪闪发光的轿车。三个打扮得像联合国维和部队士兵的小伙子戴着褐红色贝雷帽跑来跑去,在球场边满头大汗地指挥轿车出进。”这个花园酒店,滑稽、华丽,具体而富有陌生情趣,是一个很有现场感的描写。在一种轻松幽默略带反讽的语气中,小说生动地呈现了城市的日常世俗生活那种读者诸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然而细想却充满某种意蕴、情致、或者反讽荒诞意味的生活场景。 比如讲机关开会,小说写道:“以前开会人人拖拖拉拉,现在开会各处室的人跑步前进,好像去领钱,但目标不是财务室而是大会议室,会议室里人人争抢前五排的座位,为的是让厅长或处长很容易看到自己。连姓花的女人也抢坐第一排,姓花的女人按时出席厅里的大会,办公楼就真的一个人也找不到了,整座机关大楼除大会议室生气勃勃之外,其余的房间都一声不响完全死去。”开会这种事,是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件表面贴着枯燥乏味无聊严肃等标签,内里却充满种种人生、人性、灵魂的复杂性与包容性的事件。各种五花八门的会议,是人与人,现实关系、心理情感等争奇斗艳的好地盘。开会,日常又充满神秘紧张。开会是什么滋味,很多人都有独特体验,永生难忘。然而要把心中滋味,当时某种情境下的感觉说清楚明白,很不容易。一个热爱生活表现的作家,恐怕是绝对不能放过开会这样的好情节。比如写办公室领导和下属斗嘴,一男一女唇枪舌剑,语意暧昧模糊,绝不撕破脸皮,暗中确是语言艺术的交锋,俗世智慧的较量,隐隐涌动欲望的潜流。它可能不登大雅之堂,但这样的男女生活场景,确实是世俗生活真实而极富吸引力的一个面向。文学表现生活,人生的大起大落,尖锐的矛盾冲突,历史的风云际会,这些当然是重点,但平凡安稳人生里面关于活着的点点情致,人性欲望纤细柔美的展开,小小不言然而令人惊奇的智慧的生动瞬间,也是文学表现的重点。文学,不应当充满好奇心地去捕捉,发现那些在时间流里悄然绽放的绚丽的光影色斑么?一个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小场景,小细节,配上轻松幽默略带调谑的语言,使小说鲜活生动,情趣盎然。这是这篇小说取胜的地方。
在浓郁的小城生活气息中,小说逐渐进入到一个十分日常,却横生岔路;十分世俗,却似乎大有深意的人生故事。主人公李正,普通的机关办公室上班族,他正在为装不装防盗笼烦恼。他纠结的是,不装,有安全隐患。装了,怕钥匙忘了进不了家门。这真是左右为难。最后,他决定装。由装防盗笼,而引出进派出所被盘问,被老板骗,再被卷进同事花姓女人的个人生活,最终挨联防队员的打,被塞上警车的一系列倒霉事件。如果说《无事生非的雨季》核心仍旧是过日子。而《钥匙的烦恼》在几乎全包围的生活情节和细节中,展现的恰恰是从生活经验中折射而出的某种发现,一点哲理。
小说为此做了细致的铺垫。一开始,小说埋伏了一个细节,街上响起警笛声。警察抓坏人。这个生活不安全,需要时时提高警惕。主人公正为安全问题发愁哩。一开始,李正是不大想装的。旁边就是例子。处长家装了防盗笼,某一天确实忘了钥匙,于是的确出现了翻窗户不成而跌下楼摔死的悲剧。小说写了一句:“有人死了不好。”的确,读者看到这里,也觉得下手重了点,让人死了不好。主要作者是想要强调一点,安了防盗笼,人和人就被关进笼子,家和家就被锁住了,隔绝了。人心的门仿佛也被锁住了。原来家家户户开开敞敞,一个院子人来人往,四处乱串,亲如一家。但装了防盗笼,就显示出人人警惕,个个防范,他人既是地狱的意思来。这种生活没味道。
但安全第一。李正还有儿子。这就有了做防盗笼的决定。很寻常的事件。然而到了李正那里,寻常事件就自然而然平生枝节。——他抠门。小心翼翼,算盘打得很细致。过日子的人,算盘打得精,能赚点便宜。而李正就是为了赚点小便宜,陷入到一个笼子里的。为了赚点小便宜,他坚持要到老田的铺子做,结果,先是遭遇派出所的盘问,尔后又被黑店老板卷款携逃。李正这点赚小便宜的心还不接受教训,他掐指算了算,如果他去找同事花姓女人的男朋友做,那么,算上被老田骗走的钱,价格还是比市场便宜,于是,他又动心了。花姓女人本就不是省油的灯,李正这个老实男人跟她打交道,能赚么?俗话说,你吃他一顿饭,得给他干十顿饭的活。李正遇着的花姓女人正是这样——心不在焉地给李正帮忙,同时却要李正帮更大更多的忙。李正老实,注意,这是要害,这个人不会拐弯。本来,防盗笼也装好了,一切完事。然而,在东寺街这条古老的,阴沉沉的街道拐角,李正恰恰遇见了花姓女人的男朋友正挽着别的女孩拐进巷子。李正充满正义地追踪而去,却被抓小偷的治安联防队员一把擒住。
一个人在生活中小心谨慎,处处周密盘查,精打细算也是把日子过好、过得安稳的表现。然而,当李正将安全问题付诸行动时,他的人生撕开未知的口子,一步一步滑入不可知的暗道。陷入到安全的陷阱里。作者从安全问题出发,展现了越保险越不保险的生活哲理。一个人小心谨慎,安全意识过强,反而更危险。一个人计算太周密,过于苛刻,反而节外生枝,给自己带来无尽烦恼。这个轻快谐谑的钥匙故事背后,蕴含着作者的现实生活经验感知。小说的表层是鲜活的生活小故事,内里是对人生的一点经验认知。记得摄影里有一种复洗技术,影像叠加复洗,本来拍的是很具体的现场的人像风景,经过技术加工后,影像全是一片斑驳。影影绰绰,朦朦胧胧,原来的像似乎在,却又沉入背景,变形朦胧,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光斑和阴影的自在游戏。而摄影,其本质不就是光影艺术么。文学表现生活,似乎也是如此。这篇小说就是这样,现场故事下面,有一个“鬼”如影随形,当演员谢幕,它就从背景音乐声中凸显出来。
从生活事实,经验中升腾起来的人,人性,生活本质,它是灵活多变的,它永远不脱离生活的具体性乃至时间约束,它跟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教条化的生活哲理,生活教训往往形成鲜明的对抗,从而刷新我们的认识。而在生活经验的现场,我们才真正打开生活这扇门,看到人、人性的真面目。这样的时刻也是人们心灵的战场,真相和知识、理性和感性、现实自我和理想追求在这里肉搏,激发我们内在的人性,裸露出人本质的灵魂。生活和人之间互相的追逐、嬉戏呈现出无穷无尽的风景。文学创作应该有充分的兴致去呈现这种风景。张庆国的小说《黑暗的火车》即是这方面的代表。
三、暗处敞开的空间与生命
主人公赵明从昆明前往成都开会,顺便会会大学的那个女同学。计划是这样的。然而,暗生的情愫被一趟火车改变了。在日常的惯性的生活流里,火车,是一个充满意外、诱人伸张,激发故事的事物。把一群陌生人随机地,意外地拥挤到一个空间,并提供一个相对充分的时长,让人自然而然地碰撞,迸溅火花。人性在这样的意外而拥挤的陌生空间,会摊开怎样的风景?张爱玲有一篇小说《封锁》,探讨过这个议题。《封锁》的故事背景是在四十年代的上海。警笛一响,封锁了。四围惊慌,陷入黑暗。一群人在紧张恐惧的气氛中,被硬生生地塞进一个狭窄的空间,身体与身体无意碰撞。电车座位上的两个人,一男一女,在这凭空升腾起来的相遇中,在周遭的世俗庸常中升腾起纯净的、美丽的旋律,心心相映,惺惺相惜,展开灵魂的交流,寥寥数语,即是人性的柔美温暖。然后,警报解除,灯光一亮,两人又立刻回到日常的有距离的冷淡状态。这个小说凭空劈开了生活的另一个空间。黑暗中的火车,车厢里明明灭灭,对面的女人软语温存,语意模糊而充满情致,灯光下女人的身体近在咫尺,若影若现,一夜火车,赵明在丝丝缕缕的触碰中,逐渐陷入了对铺女人如水的目光。火车到站,女人捏了赵明一把,倏忽不见。下了火车的赵明只见到女人被一个男人接走的背影。
两个人的事到了这里,差不多就打住了。下面,我们大约可以预测的是赵明和女同学趁着开会展开的一段暧昧。假如故事就是这样发展,小说将会庸俗不堪,平淡无奇。小说的精彩之处,恰恰是“无处生云霓”。赵明因着心中对火车上成都女人的牵挂,而一再地委婉地逃避老同学的投怀送抱。然而老同学很有耐性,而且,显然对赵明情深意厚,她一再地尝试着点燃这个感情。赵明原本也是来赴这个约的。因此,他也不忍心不甘心老同学移情别恋。偏偏有第三者在旁边暗中起劲,趁火打劫。事情逐渐变成了各方情感、欲望黑暗中的较量。每一个人被这个人性的互动局面牵动着,任憑理智、欲望、情感的生机勃发。就赵明而言,心中两个女人打架,男人在边上威胁,昆明的家的温暖又时时提醒,僵持的时光枯燥乏味近乎人生的浪费,这个男人有点混乱,行为处事就神经质。小说在此处刻画人物,展现多人、人性的多个面向的暗中角力,极有耐心,纤毫毕至,生动传神。即举赵明为例。第一个小场景,女同学一见面,即将赵明堵在房间,步步紧逼。直接建议赵明睡一下。小说不失时机地补充了女同学和赵明当年的一场恋爱,女同学输就输在这个行为上,现在,女同学几乎是直奔目标,赵明呢?“赵明的心里轰然一声响,全身烧起来。”然而,火车上女人的身影在他心里抓挠,他先装傻,再语意含糊地找借口。实在女同学欺上身了,他“朝后坐到床上”。女同学看这个情行,收了收,准备走了。“赵明从床上滑下来,傻傻地跟她身后朝门边走……小心,赵明说,不要在我的房间里出事。”这一段描写,把赵明心中欲望升腾,对昔日恋人的渴忘心知肚明,然而又被火车上女人拉扯住手脚的这个微妙状态写得细致入微。
接下来,女同学一次又一次地撩起赵明的欲望,第二天广东人加入,在二人身边洞察秋毫,随时煽风点火。赵明和女同学在界限的边缘徘徊着,赵明快要抵抗不住啦。火車女人及时打来电话发出邀请。小说描写放下电话去赴约的赵明:
“赵明像少年一样双手发抖。”
“赵明现在是一个少年,惊慌失措,全身发软。对于一个少年来说,约会是令人心碎的场面,一块少女的手帕便可能引来致命的后果。”
“他从车里钻出来,一瘸一拐地朝李艳走去,战颤使他的双腿不听使唤,他的脸紧绷绷的,仿佛李艳身旁石像的脸。”
“李艳挽起了他的手臂。赵明眼前一黑,差点昏过去。”
我们都知道,赵明当然不是少年,他是个有家室的中年男人。但是,在女同学不断的撩拨下,赵明内心煎熬着,情与欲,放纵与节制,此处与彼处,已经在他的心里锣鼓翻天。他已经忍耐得太久,挣扎得太艰难。所以,当李艳电话约请,他的心在发抖,整个人处在失控状态,完全不能自已。张国庆做小说,最擅长的就是细腻功夫。这篇小说,人物雕镂的层层深入,心理状态的步步推进,各方力量刺激、制衡下的场面情形,内在的张力气氛的烘托,这个节奏精细、柔韧有力,把握得恰到好处。这是小说最精彩的地方。
同样精彩的是赵明、女同学以及广东人三人关系在几天的相处中戏剧性的逆转。没有大起大落,灵魂洗礼之类,氛围轻松幽默,看上去就是一出都市人生的轻喜剧。然小说的结局陡转急下,赵明被刺死。
这个结局让人挠心。下意识我们不接受这个结局。非常意外,溢出了生活的平静的日常。下意识我们会想,这个成都女人能把赵明怎么样呢?能出什么事呢?赵明已经警惕地,理智地拒绝了她。但是,生活的意外我们也说不清楚,意外嘛!它总是无处不在。而火车上的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终于将赵明按进幽深的黑暗。这是一个隐喻性的结局。生命的黑暗和黑暗的火车中暗生的黑暗的情愫,它们仿佛在生活的暗处开放的蓬勃的花朵,终究枯萎于黑暗,不能够进入阳光下平凡枯燥然而安稳的日子的地界。是的,人生某处敞开的异度空间,始终活跃在它的领域。小说的结局隐隐有一种警示的意味。
我们差不多要忽略悲剧,甚至,在创造的层面上,我们甚至忽略痛苦,抛弃生命的安全,接受熟悉的警示,目光依然喜滋滋地注视那黑暗的火车敞开的人生。那新鲜、丰富、处在创造力的人生迸发状态,那生机勃勃,活力四射,不同寻常,诗意绵延的生命活力绽放的状态。这,也许就是文学和现实人生真正的交汇点。张国庆的几篇小说,注目现实都市人生的轻喜剧,而从表现现实生活溢出的诗意层面,逐渐升华到对生命的流溢、敞开的诗意关注,写作是一步步加强,一步步更纯粹地提炼美,表现美的。与沉重的,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生相比,这样的人生书写清逸、飘灵,缺乏厚重感,但它确实是耐人寻味的。富有生动的日常生活气息而又芳香宜人的。在今天喜欢大主题,找意义,甚至努力去渲染某种价值和意义的人生表现追求中,这样的写作格局小巧精致,但确实是美的,明亮的、清纯的。我们从中看到汪曾祺的文学精神,张爱玲表现安稳人生的文学精神,这也难能可贵。
责任编辑 李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