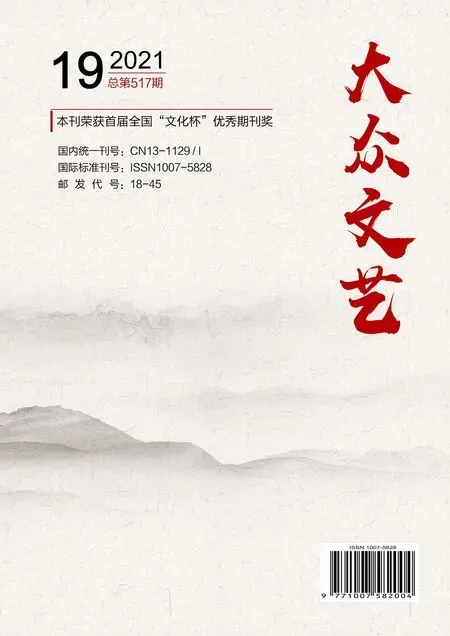美国音乐剧“去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
李茜茜
(外交学院,北京 100037)
美国音乐剧与爵士乐、美国电影并列被称为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最具美国特征和影响力的艺术形式,因为它们体现了美国诸多社会文化问题。其中,种族和族裔问题自美国音乐剧形成以来一直是剧目中一个重要题材,不仅包括白人与黑人间的隔阂,还涉及少数族裔在美国的困境。然而,美国音乐剧虽然从题材和内容来看经常是包容、平等、多元的,但本质上美国音乐剧主要将白人设为目标受众,大多数音乐剧也因此是以白人视角创作的。此现象可体现于音乐剧中对自由、梦想的表达。美国音乐剧倾向于由白人表达对自由和梦想的追求,因为事先设定的白人目标受众更能与白人角色产生共鸣。由此来看,美国音乐剧并不是彻底包容、平等、多元的。近年来,随着少数族裔在社会中地位的提高,音乐剧的目标受众发生了变化,创作者们也试图打破这种以白人视角为标准的族裔表现。2015年,以少数族裔演员为主的音乐剧《汉密尔顿》(Hamilton)上演,轰动全球,并在2016年摘夺11项托尼奖;2017年,音乐剧《乐队造访》(The Band’s Visit)上演,这部看似安静、默默无闻的以中东为背景的音乐剧在2018年获得10项托尼奖。值得关注的是,这两部音乐剧都意图打破视白人为标准、自然的观念。换句话说,这两部音乐剧运用了“去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方式,以寻求音乐剧本质上的族裔平等和多元。
一、“去白人常态化”族裔表现的理论基础
种族建构主义认为,种族的概念是人为主观定义的,它由族群的相貌特征、文化、地域因素组成,并不客观、固定,因为科学家并未在基因上找到族群之间的差异。这种主观的概念导致了种族阶级的产生,因为欧洲历史上在科技领域的领先造就了“白人”这个更为“优越”的种族,形成了白人特权。具体来说,“白人”的概念最早是在17世纪被欧洲人创造出来的,目的是否定黑人及其他族裔,即“他者”(“Other”),以使奴役变得正当。因此,白色人种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客观的定义。在白人特权的观念主导下,美国历史上将白色人种列为获得国籍的前提,但由于白色人种在定义上的模糊及不确定性,美国最高法院只能通过法官的主观判断来做出裁决。约翰·塔瑞尼安(John Tehranian)对比分析了1922年和1923年的两例由最高法院裁决的移民入籍经典案例,说明了法院在裁决时运用的不同参照标准。1922年,最高法院在裁决日裔移民大泽隆夫(Takao Ozawa)是否符合入籍条件时,将白人定义为人类学概念上的高加索人,认为日本族裔不属于白人。而在1923年裁决印度裔移民帕卡德·兴·辛德(Bhagat Singh Thind)是否符合入籍条件时,最高法院否认了“高加索人”的定义标准,转而认为应遵从普遍认知中的肤色标准,而辛德的肤色不够“白”,因此不属于白人。以上案例说明白色人种这个概念缺少客观定义,但在社会中却被普遍运用及利用,很大程度上成了“权力”和“优越”的代名词。
1965年之后,美国废除了一系列种族歧视的法律,但白人特权仍然存在。这种特权已逐渐从法律层面转向实际操作层面,因为“白色”仍被普遍看作为默认肤色,是自然、标准的。一般情况下,种族研究只针对非白人群体,隐含“黑人”“他者”和“少数”之义。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从文学的角度也说明了类似的问题。她指出,美国文学中非裔的存在总是装饰性的,美国文学向来只“关于”常态的白人世界。针对社会中因白色人种的概念而引起的种族不平等问题,波姬特·拉斯穆森(Birgit Rasmussen)等学者总结白色人种可能包含的含义如下。首先,白色人种是隐形、无标记的。此含义与之前提道的白人在实际操作层面的特权一致,认为人们普遍将白色人种看为常态。然而,萝丝·弗兰肯伯格(Ruth Frankenberg)批评认为此含义恰恰建立在认同白人为常态的观念之上,因为白色人种只在白人眼中是隐形的。第二,白人身份不包含任何内容,社会中也不存在任何“白人文化”。换句话说,叙述“白色人种”定义的句式不是“白人具备……特征”,而是“白人不具备……特征”。此观点解释了白色人种无标记的原因,但否认了白人领导的欧洲国家是通过文化殖民在全球扩张的可能性。第三,白色人种象征着系统上的特权及权力。这可体现于白人在住房供给、教育、就业等领域的优势。然而,此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没有区分白色人种内部的社会分化。例如,爱尔兰人虽属于白人,但其移民在美国历史上也饱受歧视。第四,因白人犯下的种族屠杀、奴役制及其他种族歧视罪行,有色人种将白人视为暴力和恐惧的象征。此含义强调了白人至上的危险性,但也同时在很多语境下显得过于极端。最后,白色人种的概念正当化了欧洲殖民和系统上的种族不平等。此观点认同了白色人种的概念是为异化“他者”而建构出来的说法。
根据以上白色人种的含义,人们可得出一种达到种族平等的方法,即“去白人常态化”,因为若人们不再将白色人种看成是常态、标准的,而只是一种肤色可能性,那么种族阶级将会逐渐被淡化,白人特权也将有可能消失。音乐剧中,“去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可体现于三方面。首先,音乐剧中需展现族裔、文化多元。因为白色人种不再是常态,音乐剧中就不应只有白人角色和白人文化。其次,非白人角色不应只是装饰性的。同样因为白人不是常态,音乐剧不应只将白人作为目标受众,只从白人视角创作。相反地,非白人角色也需要有足够空间进行有意义的表达,并且少数族裔应与白人有同等机会成为主角。最后,音乐剧应真正“关于”非白人族裔的生活和文化。此方面可被视为第二方面的补充,因为非装饰性的少数族裔角色需通过相应的场景与故事展现。真正“关于”非白人族裔生活和文化的音乐剧创作不应是白人对此族裔的刻板印象,而应是此族裔文化真实、可信的体现。由于白色人种定义上的不确定性,本文将其统一定义为斯坦利·利博森(Stanley Lieberson)所描述的“未加连词符的白人”(unhyphenated whites),即欧洲族裔,且不将自己看作某一特定族群的成员。
二、历史上美国音乐剧中“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
美国音乐剧是由多种原始的舞台音乐表演形式演变而来的,而其中一种表演形式则为“黑面表演”(blackface minstrelsy)。这种表演形式形成于19世纪初,在19世纪30年代时因托马斯·莱斯(Thomas Rice)的“吉米·克劳跳”(Jim Crow Jump)而变得受欢迎。在“黑面表演”中,白人演员将脸涂黑,像小丑般地跳舞,目的是取笑黑人。这种娱乐形式广泛受到工薪阶层白人的欢迎,因为它表现了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包括无知、懒惰和怯懦,这些刻板印象也成为奴隶制和白人至上观念合理化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黑面表演”反映了当时美国种族间的关系,也同时预示了族裔题材在美国音乐剧中的重要地位。
美国舞台音乐表演在20世纪上半叶发展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即音乐剧,而族裔也成了重要的题材之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族裔文化相互融合,族裔间的分界线也已逐渐变得模糊,但族裔的概念并没有因此被削弱。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解释认为此现象的原因在于人主观上对族裔的构建比客观上族裔间的区别本身重要。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在族裔建构的基础上提出了象征族裔身份的“族裔符号”(ethnic symbols)。他认为,族裔身份可以以象征的形式出现,因为族群通常是抽象的群体,是想象出来的。当人们将自己视为虚构群体中的一员时,人们需要在媒体中看到象征族裔文化传统的符号以满足身份归属感。族裔符号可包括传统节日、文化艺术品、传统风味菜、民族音乐、代表特定族裔的名人、成就等。与甘斯类似,理查德·阿尔巴(Richard Alba)提出了“族裔经历”(ethnic experiences),在族裔符号的基础上加入了以族裔为主导的特殊经历,比如与特定族裔人群建立的社交关系、因族裔身份而共同拥有的优势或共同遭遇的歧视等。音乐剧中的族裔表现往往是通过这些族裔符号和经历完成的,具体包括语言或口音、表演者的相貌、服饰、音乐及舞蹈形式、文化习俗、台词及歌词中对名人、成就的提及和剧中对族裔经历的表现。
历史上以族裔为题材的音乐剧看似是包容、平等、多元的,因为这些剧目常提倡种族平等并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但事实上,此类音乐剧常陷入“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误区,因为它们通常促进了少数族裔向白人社会的同化。典型的“白人常态化”族裔表现可体现于《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1957-1959)。《西区故事》讲述了一个类似《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两个对立的帮派为白人帮派“喷气机”(Jets)与波多黎各帮派“鲨鱼”(Sharks)。此剧以美式英语和爵士蓝调作为白人的标志,掺杂西班牙语的英语和节奏感很强的拉丁式音乐作为波多黎各族裔的标志,营造了族裔和文化多元的剧情环境,并以此来表达族裔间冲突的危险性,达到促进族裔间相互理解的目的。然而,剧中的族裔表现是基于“白人常态化”观念的。虽然剧目包含了族裔和文化多元,剧情叙事却仍为白人视角。沃伦·霍夫曼(Warren Hoffman)指出,音乐剧中有一类曲目可被称作“我想”类歌曲(“I want”songs),用来表达角色的抱负、梦想及对自由的追求,而只有重要的角色才有机会演唱此类歌曲。在《西区故事》中,“我想”类歌曲《该来则来》(“Something’s Coming”)由白人角色托尼(Tony)演唱,这也意味着波多黎各裔角色是装饰性的。除此之外,剧中对波多黎各族裔的表现是不真实、不可信的,因为创作者几乎不懂波多黎各文化,角色设计也完全基于白人对波多黎各族裔的刻板印象,将其男人描绘成罪犯,女人描绘成性欲的化身。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爵士蓝调本是黑人文化的代表,此剧却将其作为白人的标志,体现了“爵士蓝调是美国的,美国是白人的”这样的思维逻辑。通过这种“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西区故事》加强了少数族裔的异类感,此剧也因此背离了其削减族裔间冲突的初衷。
在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Civil Rights Act)通过之后,一些原先的白人音乐剧被制作成了全黑人音乐剧(allblack productions),并取得了票房上的成功。这些全黑人制作的目的是给黑人演员表演传统上白人角色的机会,以达到种族平等。但这些制作在族裔表现上并不是真正进步的,因为这些音乐剧内容不包含黑人文化,传统的白人角色也不会给黑人演员推广黑人文化的空间。因此,这些全黑人制作可被批评为舞台上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but equal)。霍夫曼指出,在讲述白人的社会环境时忽略种族的存在会加强白人是自然、标准的认知,假装种族不存在和种族不平等同样有问题。
近年来,一些美国音乐剧打破了这种传统的“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方式。下文将分析《汉密尔顿》(2015-)和《乐队造访》(2017-2019)这两部音乐剧,以说明这种新式的“去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方式。这两部音乐剧为近十年来获得托尼奖最多的音乐剧。在影响力方面,托尼奖可被视为美国戏剧和舞台剧的最高荣誉奖项,因此这些奖项赋予了《汉密尔顿》和《乐队造访》引领美国音乐剧潮流的潜能。因此,“去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方式也很可能成为美国音乐剧的趋势。
三、美国音乐剧中“去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
《汉密尔顿》与《乐队造访》均意图运用“去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方式表达对种族平等的追求,但这种表现方式也可引起不同的解读。对比来看,《汉密尔顿》更多在表演形式方面体现了“去白人常态化”,而《乐队造访》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其有所体现。因此,《乐队造访》较《汉密尔顿》在“去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上有更大的突破。
(一)《汉密尔顿》中“去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及其争议
音乐剧《汉密尔顿》由罗恩·彻诺(Ron Chernow)所著的《汉密尔顿传》改编而成,讲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人生和美国的建国史。此剧吸引了诸多学者的注意,因为剧中美国开国元勋的角色均由非裔及拉丁裔演员饰演。除此之外,剧中大多数曲目形式为嘻哈乐,而这种形式也被视为非裔文化。编剧及汉密尔顿的饰演者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希望有色人种也有参与美国建国史的权利,并称这部剧为“当代美国讲述的美国历史故事”。从选角开始,族裔就在《汉密尔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剧的演员招募单中明确列举了所有扮演主角演员的族裔可能性——非裔、拉丁裔、亚裔、原住民、中东裔、东南亚裔及太平洋岛民、族裔不明确或混血。招募单中“白色人种”的缺失标志着创作者们消除白人常态化的意图,这种做法也被赞美为百老汇舞台的革新,因为《汉密尔顿》为一部改变百老汇音乐形式、转变美国建国史叙事视角、让大众看到更新、更多元的美国的音乐剧。
《汉密尔顿》是族裔文化多元的。虽然主角全部由少数族裔演员饰演,一些次要角色可分配给白人,尤其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这个角色至今一直由白人饰演。此剧中的族裔差别是通过族裔符号实现的。说唱乐和节奏蓝调代表非裔及拉丁裔,传统百老汇风格和60年代英伦摇滚代表白色人种。除此之外,此剧加入了移民元素来增添族裔多元化。汉密尔顿被描绘成来自加勒比地区的移民,因为在彻诺所著的传记中提道,汉密尔顿将英属西印度群岛作为自己的出生地,并一直将自己看成在美国的异乡人。汉密尔顿移民的形象在《约克城》(“Yorktown”)曲目中被加深了,曲中他和法国拉法耶特侯爵(Lafayette)的一句词为“移民们,是我们完成的任务”(“Immigrants,/We get the job done”),从而强调了移民在美国历史中的贡献。
但《汉密尔顿》中所展现的多元化也存在一些争议。菲利普·马格内斯(Phillip Magness)指出,米兰达对汉密尔顿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汉密尔顿反对更自由的移民政策并支持1790年代末的《外国人和反煽动言论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而此法案延长了外国人取得美国国籍所需的居住年限并赋予了总统驱逐对美国有敌意的外国人的权利。此外,《汉密尔顿》对族裔的表现仍遵从了“非黑即白”的两极分化,并没有体现其他少数族裔的文化。例如,剧中不包含任何亚洲风格的曲目,而且虽然演员招募单中提到了亚裔,亚裔演员却几乎没有出现在剧中。在百老汇原始卡司中只有一位亚裔演员,即费丽帕·苏(Phillipa Soo),而她也很容易被视为白人,因为她是欧亚混血,相貌接近于白人,并且演唱的是代表白人的传统百老汇风格曲目。虽然亚裔移民潮发生在汉密尔顿时代之后,但因为《汉密尔顿》旨在以当代美国视角叙述美国建国史,即刻画后革命时代与当代美国的复杂族裔身份,亚裔也理应在剧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汉密尔顿》试图塑造族裔文化多元的美国,但其族裔表现仍不完全多元。
上文提道,《汉密尔顿》中的主角,即美国开国元勋,均由非裔及拉丁裔演员饰演,因此有色人种在剧中较白人有了更重要的地位,已不再是装饰性的。事实上,乔治三世是唯一一个预留给白人的角色。剧中,乔治三世被描绘成一个“小丑”,不断地做出滑稽动作并且不具备任何决定美国命运的能力。这样一来,由白人饰演的乔治三世与由非裔及拉丁裔演员饰演的美国开国元勋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同于历史上“白色人种”概念的形成,此剧将白人塑造成了“他者”。换言之,此剧将白人异化,从而强调族裔文化多元,并建立“非白人常态化”的环境。此外,《汉密尔顿》的创作者将“我想”类歌曲《我的机会》(“My Shot”)写给了“加勒比地区移民”汉密尔顿,这也意味着此剧的目标受众不再只是白人。
然而,《汉密尔顿》中的开国元勋角色是否能被看成非白人角色是存在争议的。一方面,历史上的汉密尔顿是法国人和苏格兰人的后裔,虽出生于加勒比地区,也应当被视为欧洲裔,即白人。此观点类似于对1960年代全黑人音乐剧制作的批评——《汉密尔顿》描述的是白人的社会环境,因此在描述中忽略种族的存在与种族不平等同样是不可取的。另有学者认为以被压迫族群演绎“施暴者”是很荒谬的,这就好比以犹太人饰演纳粹德国人。但另一方面,阿娅·罗曼诺(Aja Romano)认为,《汉密尔顿》并不关于真实的美国历史,而是根据彻诺所著传记改写的“同人文”(fanfic)。它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美国,并且将那些被遗忘的人重新写回了美国历史。因此,美国开国元勋的角色是非白人角色,此剧向一个几乎不承认非裔重要性的社会展现了其重要性。从这点来看,《汉密尔顿》中的主要角色是否可被视为非白人角色取决于观众的理解。
与上一点类似,《汉密尔顿》中对奴隶制的表现也引起了一定争议。一方观点认为,此剧对奴隶制含有讽刺态度。剧中几次明确提及了奴隶制,例如在《约克城》曲目中,汉密尔顿与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s)的一句台词为“若不结束奴隶制我们永远不会自由”(“We’ll never be free until we end slavery”);在《内阁第一次辩论》(“Cabinet Battle#1”)曲目中,汉密尔顿反驳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道:“让奴隶贩给你上一堂公民课,……,你还清债务因为你用奴隶工作”(“A civics lesson from a slaver/…/Your debts are paid cuz you don’t pay for labor”)。剧中也含有几次对奴隶制的暗示,例如当杰斐逊在《我错过了什么》(“What’d I Miss”)曲目中出场时,群演们正在饰演擦地的动作,其中一位起身接过他的包,象征了奴工;在《斯凯勒姐妹》(“The Schuyler Sisters”)曲目中,由少数族裔演员饰演的斯凯勒姐妹演唱道:“看看我们现在活下来是多么幸运”(“Look around at how/Lucky we are to be alive right now”),暗示了少数族裔活下来只应被归因于“幸运”,这也抨击了美国系统上对少数族裔的奴役。事实上,此剧在创作初期还包括一首名为《内阁第三次辩论》(“Cabinet Battle #3”)的曲目来专门讨论奴隶制,但此曲在制作后期被删除,因为创作者认为这样的讨论看起来是多余的,原因是由有色演员饰演白人本身就是对美国种族不平等的评论了,观众并不喜欢被说教。但另一方观点认为,剧中的角色原型均为白人,此剧因为没有涉及任何以黑人为原型的历史人物而抹去了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奴隶制度,《汉密尔顿》也因此不是真正“关于”黑人的。此剧还淡化了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例如,剧中主角之一的赫尔克里斯·穆利根(Hercules Mulligan)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是美方间谍,为独立作出重要贡献,而他的黑人奴隶卡托(Cato)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同样为美国独立作出重要贡献,但卡托却没有出现在剧中,也没有被提及。这样一来,《汉密尔顿》中“去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更多是形式上而并非内容上的。
(二)《乐队造访》中“去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及其争议
《乐队造访》讲述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发生的一个平常却温馨的故事。埃及亚历山大警察管弦乐团(Alexandria Ceremonial Police Orchestra)受邀前往以色列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的阿拉伯文化中心演出,但因为语言障碍,抵达了一个偏远的小村庄贝塔哈提克瓦(Bet Hatikva),得到了与以色列当地人交流的机会。虽然埃及和以色列在政治上有冲突,此剧却没有涉及任何政治内容,而是强调了人情纽带和不同文化间的共性,即音乐与爱。此剧同样运用了“去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方式,而且较《汉密尔顿》也有了一些进步。
《乐队造访》通过不同族裔符号体现了族裔文化多元,并且其对语言的运用使族裔符号真实可信。剧中,埃及角色通过阿拉伯语交流,以色列角色通过希伯来语交流,只有在双方相互交流时才使用英语,而英语也是带有口音且夹杂语法错误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此剧在美国上演,而大部分美国观众不懂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剧院也没有向观众提供字幕。这种方式加强了故事背景的真实性,同时也挑战了英语为自然、普遍的设定。沙朗·阿隆森-勒哈维(Sharon Aronson-Lehavi)称这种方式为语言表演行为(speech-act),因为此剧演员多在美国出生,他们需要学习剧中设定的口音。另外,剧中角色虽经常犯简单的英语语法错误,他们却能熟练运用英语修辞手法以做文字游戏。例如,在《欢迎来到偏僻小镇》(“Welcome to Nowhere”)曲目中,以色列当地人为了向埃及乐队解释佩塔提克瓦和贝塔哈提克瓦在发音上的区别,运用了一系列以B为头韵、与“无聊”(boring)同义的词汇——“barren,bullshit,bland,basically bleak and beige and blah,blah,blah”。犯简单语法错误的人几乎不可能运用这种复杂的修辞手法,因此,此剧在语言上的真实性是一种特殊加入的表演行为。
然而,剧中其他族裔符号的真实性略有不足,因为这些符号没有区分埃及和以色列的文化,而是将界限划分在中东和西方文化之间。比如,剧中提道了埃及歌手乌姆·库勒苏姆(Umm Kulthum)、埃及演员奥马尔·沙里夫(Omar Sharif)、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和美国电影音乐《月亮河》(“Moon River”),出现了象征埃及文化的阿拉伯打击乐器、厄乌德琴、象征西方文化的小提琴和小号,但象征以色列的族裔符号没有出现。除此之外,作曲者大卫·亚兹贝克(David Yazbek)将犹太克莱兹梅尔(Klezmer)音乐元素融入埃及音乐中,但克莱兹梅尔是东欧犹太传统,并不适用于以色列偏远村庄。因此,这些族裔符号的真实性还有所欠缺。
上文提道,《乐队造访》是发生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故事,将欧洲裔白人排除在故事叙事之外,因此非白人角色不再是装饰性的。虽然此剧在美国上演,但其故事本身与美国无关,因此美国观众更可能将剧中角色的族裔身份看为广义上的穆斯林裔与犹太裔,而非狭义上的埃及裔与以色列裔,而这两个族裔在美国均为饱受歧视的群体。罗瑟·戴姆宾(Russell Dembin)指出,犹太人在美国曾经历了几十年的白人待遇,但特朗普政府放纵白人至上主义及后纳粹主义,使犹太人变回了“他者”。穆斯林人的处境更差。自从911事件之后,他们一直被美国媒体塑造成危险、对社会有威胁的形象,使民众产生了恐伊斯兰情绪。而《乐队造访》没有以这种含有偏见的白人视角叙事,而是将这两个族裔刻画成追求爱与理想的普通人。例如,剧中埃及乐队指挥经受着丧子之痛,小号手努力帮助害羞的以色列年轻人追求心爱的女孩,一对以色列夫妇因为丈夫无抱负而争吵,而这些事件都极为普通,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正如此剧演员之一的珍妮特·达卡尔(Janet Dacal)所说,虽然故事没有发生在美国,但每个人都能与角色共情。编剧伊玛塔尔·摩西(Imatar Moses)也表示,当一切人为的边界和政治叙述都被去掉后,人只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乐队造访》试图淡化“族裔”的概念,通过强调人性而达到种族平等。
在身份认知方面,《乐队造访》也可被视为是真正“关于”中东文化的,因为它帮助中东裔演员找回了对自己族裔身份的认同感。《乐队造访》演员之一阿里埃尔·斯塔奇(Ari’el Stachel)表示,911事件之后,中东裔人在美国遭受歧视,因此中东裔演员一般只能接到饰演恐怖分子的角色。更多情况下,中东裔演员否认自己的族裔身份而去假扮黑人或拉丁裔人以得到那些电影、电视中为了体现多元而必须包含的“任何族裔”角色。而通过在《乐队造访》中的表演,斯塔奇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族裔身份认同感,因为中东裔角色没有被刻画成异类,而是一个普通人。同样,此剧演员之一沙朗·萨亚(Sharone Sayegh)也承认,通过《乐队造访》,她的中东身份与美国身份融合了。
因为现实中的中东政治环境并不像剧中展示的那样和谐,此剧有可能被视为对现实的逃避。但亚兹贝克认为,此剧在政治表达上的缄默恰恰能使其政治含义更深刻。可以说,《乐队造访》除一些族裔符号不准确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了“去白人常态化”。
四、结语
“去白人常态化”可被视为一种体现种族平等的方式。近年来,美国音乐剧中新式“去白人常态化”的族裔表现方式打破了一直以来音乐剧保有的白人视角,将白人异化及边缘化,从而在体现种族平等方面有所突破。2015年上演的《汉密尔顿》更多地从形式上挑战了白人为常态的观念,但从内容上看仍未犀利地挑战种族不平等的存在。相比之下,2017年上演的《乐队造访》从形式和内容上均未将白人作为中心,从而更好地体现了“去白人常态化”。因这两部音乐剧均获得多项托尼奖,它们很可能引领美国音乐剧中“去白人常态化”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