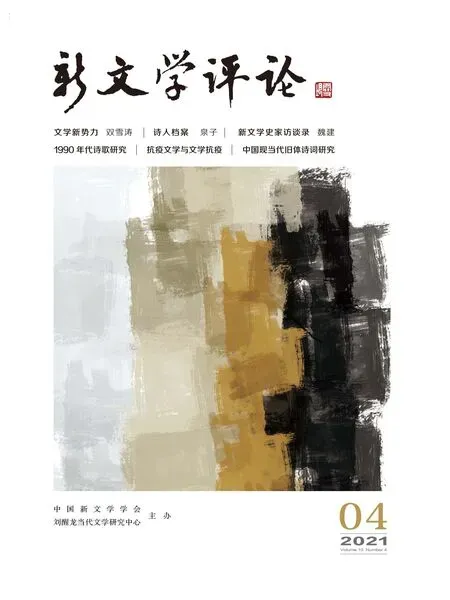在聋哑时代坚守梦想与自由
——双雪涛小说论
□ 陈劲松
[作者单位: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
先从双雪涛这个名字说起。我不是算命先生,无法通过这个名字窥出双雪涛此生命运,但我还是从他三十八年的成长历程和短短十年的创作生涯,看到了这个名字背后的某种玄机。“雪涛”为名,大雪寂寂,大水滔滔,一静一动,动静结合,加上“双”姓,共同构成了其姓名蕴含的双重寓意:他是安静的,谦卑的,与世无争的;他又是热烈的,豪迈的,激情奔放的。这样的人,看似沉默,实则充满爆发力。回望双雪涛的人生履历和创作经历,基本印证了我的上述判断。
言归正传。我喜欢读小说,但长期以来都是比较随性甚至慢人一拍的读者,多数时候遵循个人兴趣。因此,当大家都在畅谈李洱的《应物兄》的时候,我在重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老鬼的《血色黄昏》;当大家都在评论余华的《文城》的时候,我在细读余易木的《荒谬的故事》和南翔的《绿皮车》。我并无任何贬低《应物兄》和《文城》的意思,我只是想强调自己的阅读习惯尽量与市场和潮流保持一定距离。不过,这固然可以避免人云亦云,有时却难免错过某些值得一读的作家作品,譬如双雪涛。
坦率地说,《平原上的摩西》发表并获奖当年,我就已知道有位叫双雪涛的青年作家,但也仅限于此。我并没有着急去读这部小说,只是在心里想当然地自问:它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小说主人公名叫吴摩西)、须一瓜的《太阳黑子》(推理、悬疑风格的“罪与罚”)有什么关联吗?现在我当然知道,这三者之间皆无关联。后来,当他相继获得“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等国内诸多文学大奖并广受关注时,我还是没有读,我在等待一个合适机缘。终于,这个机缘到了,我找来他的所有小说通览。初读,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重读,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读,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我无意故弄玄虚,我想表达的其实是,双雪涛的小说难以一言以蔽之,充满了多种可能性,看似纷繁复杂,最终却归于宁静简单。如“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颁奖词所言:“城市的历史,个人的命运,自我的认知,他者的记忆,见证的是一代人的伤感和宿命、彷徨和执着。他的小说创新讲故事的方法,也伸张个人在生活中的省悟。尤其那种历经苦难与挫伤之后一点点积攒下来的信心和暖意,即便被双雪涛纤密的叙事所深藏,也依然感人至深。”这段精准的评语,既可视为双雪涛小说写作的价值观,也可看作其方法论。据此,大致可以勾勒出双雪涛小说写作的思维脉络:扎根故乡,致敬青春,反思时代,以文学的方式讲述历史,以冷峻的叙事书写变幻的人生,通过个体与群体的塑像,表达命运的艰难与无常,进而彰显作家对于芸芸众生的关怀与悲悯。
一、 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塑像
“我写的小说开始被人注意。他们说在这座北方的城市里有个奇怪的作家,写了好多奇怪的短篇小说,他的小说总是一片黑暗,没有一丝光亮,人们在他的小说里死去,他好像无动于衷一样继续书写主人公死掉之后的世界。”如果不加说明,读者多半以为这段话出自双雪涛之口,因为他曾谈及自己喜欢“以无休止的好奇写一切怪怪的东西”。但并不是。事实上,它的作者为李默,双雪涛长篇小说《聋哑时代》的主人公,小说中的身份也是一位小说家。人物及独白虽是虚构,熟悉双雪涛小说的读者却不难发现,李默的话几近道出了双雪涛早期的写作风格:色调冷峭,迷恋死亡,惯于构筑一个幽暗、无声的世界,譬如处女作《翅鬼》以及随后的长篇小说《天吾手记》、中篇小说《长眠》、短篇小说《跷跷板》等。这些作品之所以呈现上述特征,一方面和双雪涛师承余华、王小波、村上春树等作家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他自己的写作抱负有关: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塑像。
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人,双雪涛的写作不可避免地与东北大地发生密切关联。批评家谢有顺认为,作家应有自己的写作根据地。这个根据地,既是作家创作时面对的生活世界,也是作家思考时面对的精神世界(精神家园)。双雪涛的写作根据地,就是他生活了三十余年的东北,具体到城市是沈阳,再具体到更小的地标,则是艳粉街。双雪涛笔下的艳粉街,“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准确地说,不是一条街,而是一片被遗弃的旧城,属于通常所说的‘三不管’地带,进城的农民把这里作为起点,落魄的市民把这里当作退路。……好像沼泽地一样藏污纳垢,而又吐纳不息”。这与福克纳的“邮票般大小的故土”、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棣花街、苏童的香椿树街、徐则臣的花街一样,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个人情感色彩。双雪涛在小说中反复描绘的艳粉街,当然只是故事发生地或创作背景,映照的却是沈阳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人情世故。换句话说,透过双雪涛的艳粉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地域,抑或每个人的故乡。故乡的日新月异值得感怀,故乡的物是人非值得深思。自鲁迅以降,面对故乡,每一位作家的写作姿态、进入方式和表达经验各有差别,但彰显其中的真诚、悲欢和写作精神基本无异。无论是穿梭在沈阳的大街小巷,还是伫立于北京寓所的窗前,双雪涛对于东北的打量或回望,都时刻充满某种自觉和拳拳深情。文学中的东北在萧军、萧红时代已备受文坛关注,后来者迟子建的写作也极大丰富了东北文学。21世纪的今天,如何赓续这一写作传统并创造新的东北叙事,无疑是摆在双雪涛、班宇、张执等新生代青年作家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对此,双雪涛的选择是,在历史中反思现实,在群体中创造个体,在浪漫中表达悲观,在冷峻中体现温柔。而这一切,无不通过他笔下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故乡人来落到实处。
弗兰纳里·奥康纳认为,写作是一种发现。双雪涛对于故乡的发现琐碎而深入:“我身边有一些人确实是被忽略的,或者是被损害的,或者是没有被看见,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牺牲和付出被遗忘了。”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大多是底层小人物,他们苟延残喘于废弃的工厂、败落的街道,在工作中失业,在感情上失意,在生活里失败,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下逐渐成为时代边缘人,如果无人书写,他们注定成为籍籍无名者。故乡惨淡的现实,为双雪涛的写作提供了精神契机,也让他找到了自己作为作家的存在价值。这种发现在创作初期或许尚不明确,但随着创作和思考的成熟,一种为故乡小人物立传的写作抱负萦绕在脑海,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到了创作《平原上的摩西》时,作者的这种抱负愈发清晰自觉:“就是想反映一点东北人的思想、特有的行为习惯,尤其是几个大工厂,很少人去写。东北人下岗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那时抢五块钱就把人弄死了,这些人找不到地方挣钱,出了很大问题,但这段历史被遮蔽掉了,很多人不写。我想,那就我来吧,没别的出发点。”这颇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书写被遮蔽的历史,需要勇气,更需要笔力,拨开历史的尘垢与迷雾,显露故事与人物的本来面目,就像其短篇小说《跷跷板》结尾所言:“名字也许没有,话总该写上几句。”以此让无名者有名,为聋哑者发声。
于是,我们得以在《我的朋友安德烈》《北方化为乌有》《刺杀小说家》《走出格勒》《飞行家》《武术家》《杨广义》《长眠》《无赖》《心脏》《剧场》等众多作品中,看到走投无路的小说家、死于非命的工厂主、沉于幻想的小职工、迷茫困惑的中学生、穷困潦倒的诗人,还有被遗弃的孩子、女人或丈夫……各色小人物依次登场。他们的昔日生活虽不富足却也安稳,他们的未来人生虽不璀璨却也光明,可是,他们心中的安稳与光明,随着时代浪潮的击打戛然而止。经济改革、社会转型、城市变迁,这些宏大的词汇与他们曾经相距遥远,却仿佛在一夜之间和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那是一种被时代戏弄的苦闷,我从没问过他们,也许他们已经忘记了如何苦闷,从小到大被时代戏弄成性,到了那时候他们可能已经认命。”这是《聋哑时代》中父辈们的生活遭际,无疑是那一代人的命运缩影。雷蒙德·卡佛曾说:“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形容双雪涛笔下的故乡人呢?历史的洪流面前,无权无钱无势如他们,连随波逐流的机会都没有,就如《聋哑时代》中的李默、安娜、霍家麟,《光明堂》中的疯子廖澄湖、“少年犯”柳丁、姑鸟儿李淼,《刺杀小说家》中的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中的李斐,《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安德烈,《间距》中的“疯马”马峰,《跛人》中的刘一朵,《长眠》中的老萧,《无赖》中的老马,《走出格勒》中的老拉,《终点》中的张可心,《起夜》中的岳小旗,等等,唯有听天由命,被侮辱被损害。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小人物的被侮辱被损害,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生命层面,还包括精神层面;不仅仅是生活由安稳转向困顿,还包括理想由高远转向幻灭。一如《聋哑时代》中的艾小男对李默所说:“就算你付出很多,就算你对一个事情特别热爱和坚定,只要你是弱小的,纯粹的,天真的,生活还是会伤害你,毁灭你。”《飞行家》中的李明奇的父亲“文革”前已是市印刷厂副厂长,“文革”来临,受批斗自缢。作为长子的李明奇,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八个弟妹的重担。尽管一直过着逼仄的生活,在军工厂工作的他却有一个伟大梦想——造飞行器。屡试屡败后,他倒腾过煤,开过饭店,去云南贩过烟,还给蚁力神养过蚂蚁,后又办过舞蹈班,卖过安利纽崔莱,干过不少事情,始终没有成功。李明奇身上具有天真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理想总是与他背道而驰。他最终决定为理想献身的那一刻,让人无比感动:“气球升起来了,飞过打着红旗的红卫兵,飞过主席像的头顶,一直往高飞,开始是笔直的,后来向着斜上方飞去,终于消失在夜空里,什么也看不见了。”理想坍塌的年代,又有多少生命和信念“消失在夜空里”,什么也看不见了?
但消失不等于毁灭,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双雪涛只想努力记住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的悲欢离合。这让我想起了长篇小说《天吾手记》中,安歌失踪后的年头里,李天吾恪守自己当初对安歌的诺言:“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捍卫她,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把她遗忘,以后也不会,只要我还活着。”恰如作家在小说正文前引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那句话:“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互相遗忘。”让那些小人物免于被遗忘,为他们被侮辱被损害的短暂人生留下一些印记,这是双雪涛的写作抱负,看似渺小,实则阔大。
二、 在历史洪流中呈现复杂人性
双雪涛擅长讲故事。会讲故事的人未必能成为好的小说家,但好的小说家多半会讲故事。这和过去的民间说书艺人有着很大不同,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好的小说家在讲故事时,摒弃民间说书艺人对于故事人物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论,更加注重在芜杂的历史情境、喧嚣的社会现实中呈现复杂人性。具体而言,故乡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为双雪涛提供了无尽的写作资源;但在为身处历史洪流中的故乡小人物塑像时,双雪涛秉持一种客观的他者视角,走近他们却又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轻松对话,冷静观察,不虚美不隐恶,力求通过故事的精彩讲述呈现出他们人性的复杂。因此,双雪涛虽塑造了众多人物,但很难找出一个性格单调的人物。从早期的《翅鬼》《无赖》《我的朋友安德烈》《安娜》《大师》《刺杀小说家》,到后来的《天吾手记》《聋哑时代》《平原上的摩西》《光明堂》《飞行家》《北方化为乌有》,以及最近的《武术家》《Sen》《杨广义》《剧场》《猎人》《不间断的人》《刺客爱人》,无论直接以人物名字为题,还是以人物职业为题,貌似单刀直入,其实大有深意。
人性的复杂源于人心的复杂,人心的复杂源于时代和社会的风云变幻。双雪涛的小说大多聚焦于20世纪末的东北城乡。彼时,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国企倒闭和下岗潮席卷了整个东北大地,被时代“抛弃”的东北,逐渐步入历史的下半场,由此带给产业工人们的现实打击和精神创伤,至今难以疗愈。对此,双雪涛无意还原那段同样不失波澜壮阔的历史,亦无意为那段历史中的失意者简单疗伤。他毅然放弃了传统文学写作中的宏大叙事,调动自己的内心情感,选择自己熟悉的历史,并尽可能以最小的切点进入历史现场,悉心体会那些失意者在历史洪流中如何举步维艰,人心究竟怎样叵测,人性到底多么复杂。双雪涛的姿态是举重若轻的,没有用力过猛,这或许因为他一直也视自己为小人物,以小人物的声口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娓娓道来。
《翅鬼》虽是双雪涛的长篇处女作,却将历史洪流中的复杂人性呈现到极致。小说以充沛的想象力虚构了一个雪国,在这个国家,一些人因为另一些人多长了一对翅膀,就要把这些人从大到小赶尽杀绝,非得一些人坐在另一些人的尸体上,才觉得安全。前者是雪国人,后者则被称为翅鬼,从出生那天起就是囚犯,命不在自己手里。无论是雪国人还是翅鬼,都是谎话连篇。某天,国君遇刺身亡,太子婴野继位,对翅鬼实行招安,赐给他们名字和自由,将他们组建成翼灵军。然而,这不过是婴野的圈套,表面温文儒雅的他,内心十分阴险狡诈。他招安翅鬼的目的,不过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翅鬼萧朗,虽然侠义,却满肚子心机,凭着不择手段成了大将军和英雄,追求的只是牺牲其他翅鬼,让自己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婴野也好,萧朗也罢,“他们都那么聪明,不用看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可他们偏偏会把这个世界搞糟,他们对什么都没有悲悯,也没有一个时刻肯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他们习惯于把别人摆在自己的棋盘上,你吃我的,我吃你的,输了的大不了掀翻棋盘,不玩了”。这何尝不是今天的某种社会现实?《翅鬼》中的历史年代语焉不详,但这无关紧要,不管讲述的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历史是虚构的,贯穿其中的人性之复杂却是真实的。
随后,双雪涛在短短几年内创作了《我的朋友安德烈》《无赖》《刺杀小说家》《安娜》《大师》《聋哑时代》《平原上的摩西》《天吾手记》《光明堂》等一系列长中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双雪涛几乎将所有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设置于20世纪末的东北城乡。一方面,他通过具有历史感的故事叙述,强调历史与现实原本不过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历史的车轮滚滚,对于现实的碾压无可阻挡,一切现实又终将成为历史。另一方面,他好奇并执着于身处历史洪流中的底层小人物,面对历史车轮的碾压究竟有多大的精神承受力,他们的人性又有多大张力。《刺杀小说家》中的小说家,生活困顿,毫无名气,之所以引来杀身之祸,是因为他写小说的能力相当好。他在作品《心脏》里创造了一个新人物赤发鬼,而小说中发生在赤发鬼身上的事情,都会发生在一位老伯身上,每一件事都会应验,这让老伯很困扰,于是雇凶杀人。“在我心里无论是地位多悬殊的两个人,生命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既然一样,既然一定有一个要消失,我们希望你帮助我们让小说家消失掉。天平两端的东西一模一样,陌生人的生命,只不过其中一个上面又放了一笔钱上去,现在是这样的情况。”荒诞的现实,潜伏着人性的贪婪与黑暗。《光明堂》中的林牧师,《圣经》读了七遍,但他说自己也是个罪人,曾经伤过人,断了别人一条手臂,在牢里待了七年。就在他皈依上帝、虔心布道的时候,“少年犯”柳丁残忍谋害了他。而柳丁原本并非恶人,他杀林牧师的原因,不过为了能和他的老师一起去北京。其他人物如安德烈(《我的朋友安德烈》),安娜《安娜》,傅东心、李斐(《平原上的摩西》),安歌、穆天宁(《天吾手记》),老萧(《跛人》),老马(《无赖》),老拉(《走出格勒》),岳小旗(《起夜》),杨广义(《杨广义》),吕东(《猎人》)等,就像我们身边一个个熟悉的故乡人——人性总是被善和恶、美与丑纠缠着,天真而又自私,朴实而又狡黠,温和而又偏执。
近两年,双雪涛的写作进入沉淀期,公开发表的作品唯有《不间断的人》《刺客爱人》两篇。《不间断的人》体现了双雪涛的探索精神,他转而选择当下市场较热的人工智能题材,通过人心与科技、现实与想象的紧密结合,思考当代人的意识、情感与灵魂,怎样和未来的科技社会接轨。小说力图与时代有所呼应,如批评家黄德海所言,“不经意间展现出对社会和人心的独特理解”。所谓独特理解,折射的其实是科技时代的人心嬗变,背后映照的,依然还是时代变迁中的复杂人性。《刺客爱人》回归到双雪涛熟悉的写作模式,复杂的故事蕴含着复杂的人性。男主李页,一位在京城打拼的平面摄影师,罔顾追随多年的恋人姜丹为他们设计好的婚姻生活,和别的女人上床、结婚又很快离婚,多年后与姜丹再续前缘。女主马小千,表面上是一个不温不火的女演员、热衷平面摄影的女模特,私底下却是一个凭借身体赚取高额酬金的高级妓女。在李页和马小千身上,不难看到时代变化给他们的精神和心理打上的烙印,以及由此带来人性的复杂多变。
历史的洪流摧枯拉朽,而双雪涛写作的毕竟不是历史小说。在他那里,历史不过是一种个人记忆,一个引发写作灵感的契机,落脚到具体作品中,则是呈现复杂人性的一个视角、一种背景。大而言之,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小而言之,每一段历史都由个人史组成。故乡的亲人,爱人,曾经的同学,朋友,同事,还有曾听闻而没见过的陌生人,都在双雪涛笔下栩栩如生。双雪涛写出了他们的坚持与无奈,希望与失望,信念与迷茫,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陋。更重要的是,双雪涛潜入他们内心深处,发掘他们人性的多面与复杂。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人世间行走……卖弄自己并不牢固的幸福,自以为是地与人辩论,虚张声势的愤怒,发自内心的卑微,一边吵闹着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世界,一边为这个荒谬的世界添砖加瓦,让它变得一天比一天荒谬”(《聋哑时代》)。正是这种矛盾的世相心态,照见并加深了父辈和我们人性的复杂。
三、 让爱与梦想在卑微中重生
黑格尔曾说,历史是一堆灰烬,而灰烬深处有余温。对于双雪涛来说,为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塑像,进而在历史的洪流中呈现出他们人性的复杂,还只完成了写作的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关乎心灵世界,有着形而上的哲思,那就是:寻找并留住历史灰烬深处的余温,让冬夜不再寒冷,让光明驱散黑暗,让爱与梦想、尊严与自由在卑微和绝境里重生。正如“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颁奖词所褒扬的:“身为小说家,他锋利地划开了阴谋之下的纯真,躲闪之中的深情,让衰落的城市、渺小的边缘人,双双收复他们失落的自由和梦想、爱与尊严。”这种哲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灵魂,体现深度,提升高度,让作家更加理性地思考:“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和机制的原因,拥有话语权的,大多是混蛋;而柔软的,沉默的,坚持了那么一点自我的人,很多都沦为失败者。而事实上,一个好的世界,是所有人都在自己该在的位置。这也是我老写的东西,当世界丧失了正义性,一个人怎么活着才具有正义。”在正义匮乏的世界,给失败者找到活着的价值,这是双雪涛的温情与悲悯,也是他小说写作最核心的部分,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聋哑时代》里的艾小男,从李默家不辞而别后给他的短信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去生活,如果你不把你的灵魂交出去,它就消灭你的肉体。我终于认清了这个道理,活着就是一种交易。”信奉爱情一生只有一次的艾小男,最后选择离开自己唯一爱的人李默,并希望他“好好活着”,这是艾小男对爱与活着的理解,某种意义上,也传达了她对尊严和自由的向往。《天吾手记》中的安歌,同样在恋人李天吾面前选择了突然消失,而她之所以使自己义无反顾消失于熟悉的世界,只是因为“受不了当时的一切,如同割伤自己一样,以断然消失来表示对这个可笑世界抗拒,而我也是她所遗弃的这个可笑世界的一部分,也许是使这个世界最终完整的一块拼图”。后进生安歌对这个可笑世界的抗拒,亦体现了她对爱与活着、尊严和自由的个人追求。消失前,安歌给李天吾留下了一封信,只有一句话:“我希望我们都能活在自己最喜爱的时光里。”与其说这是安歌的希望,莫若说这是双雪涛对那些失败者的希望,就如国文老师黄国城给小久的信中所说:“不要轻易为了一些事情改变自己,目的并不重要,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如果人生的意义无法确定,那人生的过程就成了意义本身。”得了怪病的小久,整个人逐渐变淡,直至彻底消融在台北这座城市里。而她能够和变淡对抗的唯一办法,就是留下一本记录自己有着清晰形象、慢慢变淡然后消失的相册。多么卑微的想法!而那本相册,无疑成为小久人生的过程、活着的尊严最好的见证。在《天吾手记》后记中,双雪涛自述“这是一部跟朋友和爱人有关的小说”。这部小说的确围绕朋友与爱情展开叙述,但我从中读到的,还有梦想的坚守、活着的意义,以及爱与尊严在卑微中的高贵。
谈到自己的小说艺术时,双雪涛曾强调:“我的小说里面存有某些执念,可能是关于人本身的,比如尊严和自由。”不要轻视双雪涛的这种执念,对他笔下那些各种各样被城市遗弃的人来说,并无尊严和自由可言。不仅如此,尊严和自由的缺席,反映的恰恰是一个时代的人性黑洞和精神萎靡。张扬人的尊严和自由,彰显了双雪涛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与担当。须知,“在一个罪感麻木的时代,写出恶的自我审判,在一个人心黑暗的时代,写出心灵之光,在一个精神腐败的时代,写出一种值得信任的善和希望,这是今日写作真正的难度所在”。的确,罪感麻木、人心黑暗、精神腐败的时代,恶与绝望随处可见,但一个优秀的作家,必定能在恶与绝望之外,“写出一种值得信任的善和希望”。唯有善和希望,能催生人的爱和梦想,实现人的尊严和自由。《翅鬼》中,翅鬼们生来就是囚犯和奴隶,蜗居井下,受尽压迫,绝无活着的尊严和自由,但每个翅鬼心中都有一个飞行的梦想,这让他们在无边黑暗的幽谷中看到了一线光亮和希望。《飞行家》中,李明奇一生坎坷,却执着于造出飞行器,心中亦有一个飞行的梦想,全家人都相信他能造出来。最后他制作了一个热气球,梦想带家人飞到南美洲。在他看来,“做人要做拿破仑……做不了拿破仑,也要做哥伦布,要一直往前走。做人要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只能找到垃圾堆”。小工人身份的李明奇,或许讲不出什么豪言壮语,但他的这番话,俨然一套朴素的生存哲学。
《终点》是双雪涛目前最短的小说,不足千字,却在短小的篇幅中,将爱与梦想、尊严和自由的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饭店女工张可心,捡到一张银行卡。密码只能输三次,前面两次,一次是一个姐妹的手让火锅汤烫了,没钱治;一次是她老家的狗死了。第三次,是男朋友让她去洗浴中心工作。她坚决不去,并对男朋友说:“你别逼我,饭店多做几天,也能供你玩。”可男朋友非但不依不饶,还说出了这样的话:“你以为你那玩意是金的?告诉你,我一个人操得,人人都操得。”说完摔门走了。这一次,张可心输入自己的生日,没想到对了,卡里却只有一块钱,她等银行开门后取出来,回到家,“把两人的脏衣服洗了,找出方便面摆在桌上。然后收拾了自己的衣服,塞进箱子,拖着走到公车站”。她告诉汽车师傅要去终点,然而下一站就是终点。“终点不远。”小说就此结束。张可心虽然卑微,她对男朋友的爱毋庸置疑,但她的爱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关涉她的尊严和自由,断然不可逾越,哪怕自己一个人走向终点。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张可心面对诱惑而持守本心,不愿放弃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实属难能可贵,这其实也是双雪涛一以贯之的姿态:“我在小说里把身边这些挣扎的普通人,甚至一些有很大问题但努力保持自己尊严的人,尽量写得更好些,更温柔些。”从张可心身上,不难看出双雪涛的锦心。
2020年,“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在京揭晓,双雪涛以其短篇小说集《猎人》摘得首奖。颁奖词如是说:“我们看见了作者展现他个人写作风格与品质的最新成果。现实生活也许是十一种,也许是一种。它是凛冽的、锋利的,也是热血的、动人的。它是我们的软肋与伤痛。也是我们的光明所在。”凛冽与锋利中还有软肋,热血与动人中不乏伤痛,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可以看到光明在前。这是双雪涛的铁血丹心,也是他的写作信念。在作家孙甘露看来,“他所做的努力,一直也是很多作家所做的,就是从具体而微的描写中把个人的经验提升出来,使其获得一种普遍性”。从个人到普遍,当然没那么容易,中间隔着无数的山重水复,但也正是如此充满挑战,双雪涛的写作方可与更多青年作家的写作一起,为中国当代小说展示出新的可能性。
双雪涛多次谈到,自己犹如一个匠人,只想好好经营写作这门手艺。这种工匠精神值得敬佩,他也一直在探索更适合自己的写作道路和写作方式,其中的徘徊和不足在所难免。他曾坦言:“写的时候没想过什么写法,不知道为什么最终会写成现在的样子。”譬如《杨广义》,“它是自己长出来的小说”。又譬如《猎人》,“凭着直觉,就把它写出来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双雪涛确乎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灵感降临后文思如泉涌,与此同时,也许会给读者带来其写作风格、表现手法、人物形象等方面的似曾相识或雷同感。譬如,长篇小说《天吾手记》中的警察蒋不凡,和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中的警察蒋不凡,人物姓名与职业完全一样。又譬如,长篇小说《天吾手记》中的后进生安歌,和长篇小说《聋哑时代》中的坏学生安娜,人物姓名虽有一字之差,但两人的故事显然犹如孪生姐妹。中篇小说《光明堂》《飞行家》中的女主人公,前者叫张雅风,后者叫高雅风。短篇小说《跷跷板》《跛人》中的女主人公,名字相同(都叫刘一朵),性格相似(桀骜不驯),到了《猎人》,女主人公名字依然叫刘一朵。再譬如,中篇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和长篇小说《聋哑时代》第六章《霍家麟》,两者除了主人公姓名各异,整篇文字内容几乎雷同,究竟是一篇小说的两次发表,还是作家的自我重复,不得而知。其他类似的地方还有不少,无需再举例。所以,对于双雪涛而言,写作的思维定式一旦形成乃至稳固,如何创新与突破便成了摆在面前的重要问题。这实际也是每一位写作者都会遇到的瓶颈,相信双雪涛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正在努力寻求解决办法。
在《聋哑时代》最后,双雪涛写下了一个光明的结尾:“我应该再也不会被打败了。”借此总结双雪涛的写作,这既可看作一种理想主义,也昭示着未来充满希望。
注释:
①双雪涛:《聋哑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7页。
②双雪涛:《走出格勒》,见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第236页。
③双雪涛,鲁太光:《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
④双雪涛,鲁太光:《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
⑤双雪涛:《飞行家》,见小说集《飞行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页。
⑥双雪涛:《天吾手记》,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73页。
⑦双雪涛:《翅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3页。
⑧双雪涛:《刺杀小说家》,见小说集《飞行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页。
⑨双雪涛,走走:《“写小说的人,不能放过那道稍瞬即逝的光芒”》,《野草》2015年第3期。
⑩谢有顺:《文学的通见》,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