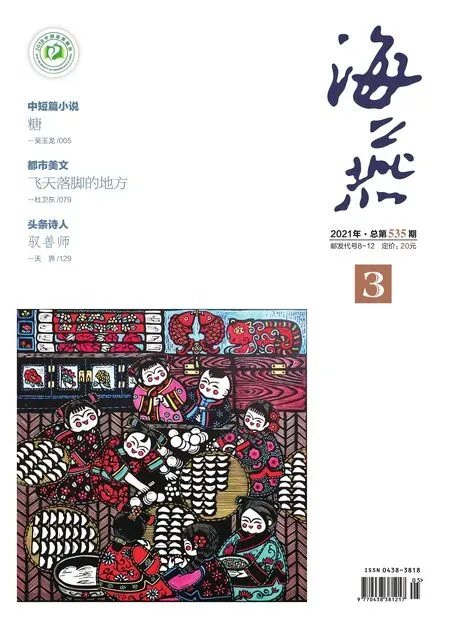辽河月辉映下的女性主义诗学
——论李箪短篇小说集《辽河月》
《辽河月》是李箪近十年创作、发表的短篇小说集萃。翻开小说集,你会讶异于柔美、苍凉的诗意题名掩盖下鲜明的女性主义写作色彩,更会讶异于中国大陆上世纪80年代兴起、90年代走向高潮的女性主义写作思潮,在辽西一隅五彩盘锦的新世纪回响。
执着的女性诗学意识
李箪小说中卓尔不群的女性意识与其说是一种叙事策略不如说是她的一种性别执念。《辽河月》中的许多女性人物执着于给自己作自画像。女性主人公往往有一种女巫的气质,能够先知式预见自己的命运。小说的叙事策略与人物的气质相一致,首先采用印象式议论语言对女性命运加以评说,然后才进入叙事环节。《形意》中的我“总是一副魂不守舍的状态,工作也不断地出错。”①《声名狼藉》开篇的诗性絮语“我是一枝尚未盛开就已凋零的花!我柔弱的肩承载着太多的不幸。我浓浓的爱意是漫天飘洒的细雨遮蔽晴日”②仿佛一个女性创伤的呢喃。《偏离》在题记中写道:“冰雪聪明的女子骨子里往往是透彻的愚蠢!别人一头雾水时她早已洞明于心,谁都一目了然的浅显事情她偏执迷不悟。这样的女人轻易不犯错,犯错就是大错。我就是这种女人。”③《纸画人生》中白雪以审美客体的形象出现:“白雪半裸着身体,一只美丽的花环拢住乌黑的长发,两条白丝巾缠绕着身体,一条围住胸肩,一条缠在腰臀。”④白雪去美院做写生模特,这一情节与形象是意味深长的。一百年前,丁玲《梦珂》中的梦珂,对抗着人们复杂的笑语和强制的干涉决绝地走进美院的教室,今天的白雪褪去花环和丝巾如同走上生命的祭坛。李然给白雪看了自己的画,“白雪的心一下子被击中,她做模特,展露人体,收集自己的画像,就像喜欢纸画上的完美,画家们有意无意地打开了箍紧她的银圈。”⑤“白雪太漂亮了,尽管她一出生就是残缺的”⑥,白雪先天的残缺是“第二性”的隐喻,而她为了获得完美镜像的献祭,所付出的代价正如王安忆在《妙妙》中所写,女性要完成自我的理想与信念,就得踏着自己的鲜血前进。女性自画像既是对女性生命意识的张扬,也是对父权制社会挫折回归的自我抚慰。
与女性相对的男性生命或者如家骆一样猥琐,或者如陆文魁一样无耻,或者如表哥一样懦弱,或者干脆像表嫂的死婴和小宝一样夭折,隐喻着父权制异化下男性生命的委顿与病态,无法像女性一样获得生命蓬勃的自由舒展。父权制的历史重负同样可以侵蚀女性生命。《花梨紫檀》中的姑母虽然生理性别是女性,但是社会性别已经成为伍尔夫《妇女的职业》中命名的“守护神”。“守护神是男权思维左右下的女性形象,她其实就是男性权威的化身,她的一举一动都按照男权社会的要求行事。”⑦伍尔夫认为杀死“守护神”“是一个妇女作家职业的一部分”⑧。姑母最后与花梨紫檀这些男权社会价值象征物一起葬身火海,是李箪杀死“守护神”的隐喻,只有杀死“守护神”,女性写作才能打破男性经验神话,进入女性独特经验的叙事空间。
封闭的女性诗学空间
近一个世纪前伍尔夫曾为女性呼吁“一间自己的屋子”,这一声冲破父权制压抑的喊声在中国大陆获得了跨民族和跨语言的热烈回应。上世纪80年代伊蕾的长诗《独身女人的卧室》石破天惊,引起了女性主义学界的巨大轰动。诗歌创造了“独身女人”的主体想象,独身女人成为女性文学的经典性人物型塑,“一个自由运动的独立的单子”“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精神实体”奠定了独身女人的叙事元精神。上世纪90年代陈染的《无处告别》、徐坤的《厨房》都将女性从婚姻中主动或被动抽离,女性主体以独立的姿态自立于世。而独身女人的卧室、厨房也成为女性文学的隐喻式空间意象。李箪小说呈现出明显的对这一浪潮的传承赓续。到了新世纪,《形意》中的厨房,不仅再现了为心爱的男人做饭的空间讽喻意义,也成为同性关系依赖轰然倒塌之后的避难所。李箪的女性空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带有超越于性别之上的普遍人际关系焦虑的时代色彩。《辽河湾》中的南大泡子虽然是开放的自然天地,但这个天地似乎是专属于“我”的秘密天堂,小宝作为男性生命的象征踏入其间就会毙命。《纸画人生》中母亲卧室永远紧闭的房门,同样闭锁着母女的精神和情感。《数数》中人情冷漠的豪宅虽然宽敞得没有边际却压抑得让人窒息。
女性的确获得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可是这屋子并没有给女性带来期待的自足,世界正在变得匪夷所思。女性结盟意识的松动使李箪对女性之间的关系持有与审视父权制一样的警惕目光。《形意》是对女性关系的解构与嘲讽,“我”在医院最好的朋友,我的小同乡、小学妹真真竟然隐瞒实情将自己的前夫介绍给离婚的“我”作为男朋友。原本同性之谊是躲避男权戕害的避难所,现在也与这个时代合谋,女性的最后一方天空坍塌,“我”的退路只有厨房——“厨房是女人遁世的最好去处”⑨。厨房隐喻的是一个与客厅的开放性公共空间相对的隔离的自我空间,空间意象在李箪这里获得了更多的封闭性和可疑性。《辽河月》的人物多是在封闭的自我空间里静默地成长,经历着一个女性神秘的生长周期,在兀自开落的日子里于某一天蓦然沦陷父权制的陷阱,开始女性生命的创伤历程,而这一切仿佛与理想、哲学、诗性无关,女性在现实和欲望的泥潭中挣扎无望。
迷人的女性诗学色彩
也许兼擅绘画与文学有关,艺术性天生地成为李箪小说迷人的色彩与线条。李箪的小说有一种北方文学中罕见的迷离的鬼魅气质——梦游一般的人物,形同迷雾的叙事氛围,明暗交叠的心理事实,叙事在真实与梦幻中无障碍出入,鬼气森然却欲罢不能。小说幽暗、鬼魅的深层动因来自于作家近于执念的女性意识,隐含着对父权制压抑下扭曲生命样态的批判。
《花梨紫檀》鬼魅、幽深的三进院落,心理变态的当家主母,色迷心窍的猥琐表哥,死婴的魔咒,月光树影下被亲生母亲敲碎的婴儿脑壳,被铁匠烧焦的灵蛇……这种审美感受倒是西南边地的女作家林白、杨映川的美学胎记,却与远在东北的李箪这里遥相呼应。《辽河湾》在江北水乡充满生命欢愉的静美天地之间铺展出一场人世的悲戚。为了将这悲戚渲染得足够沉痛,作家还给原本的欢愉加上一个趋于圆满的高潮——五个女儿之后儿子的降生,让“我”家的幸福达到极致。然而“福兮祸之所伏”,小宝终于在“我”的诅咒之下永远在苇塘里留下一道草绿色的背影。《纸画人生》是一篇唯美的女性叙事,在苍白的布景和人物上淋漓明艳的血的鲜红,将女性针刺一样的疼痛书写到极致。李箪笔下的女性形象无不来自创伤背景,她的小说在痛感书写上犹见功力,这种痛感让人不寒而栗。《偏离》是一个女性双重复仇的故事,辛竹对年幼的丽丽夺走父爱的仇视,人性的自私与阴暗在闪念之间使辛竹付诸谋杀丽丽的行动。此时的辛竹犹如《辽河湾》每日诅咒亲生弟弟的“我”,李箪对推进女性极端性时刻到来的紧张与恐怖运用了精到的戏剧笔法。丽丽因为辛竹不彻底的谋杀留下了终身性疾病,而她报复的方式是与辛竹的丈夫发生关系,摧毁辛竹的家庭,同时被摧毁的还有她继父的生命和亲生母亲的婚姻。《老二》在阴间——阳界、梦境——现实之间的自如穿梭往返,水粉色真丝内衣的欲望性意象,都生成了小说阴森哀艳的美学特征。
《辽河月》充盈着李箪对女性生命本能般的惊叹与赞美——美丽而充满灵性,纯良而坚韧勇敢。李箪借助短篇之间的穿插回闪,构建起完整的女性生命叙事:以少女时代——青年时代——妻性时代——母性时代的生命历程为经,以城市、乡村两大地理空间为纬,交织出女性生命时空的独特画卷,为女性主义诗学贡献了兼具独立性与对话性的辽宁声音。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⑨李箪:《辽河月》,沈阳出版社2020年版,第64、168、196、53、56、52、75页。
⑦荒林:《日常生活价值重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
⑧伍尔夫著,李新译:《妇女的职业》,《文化译丛》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