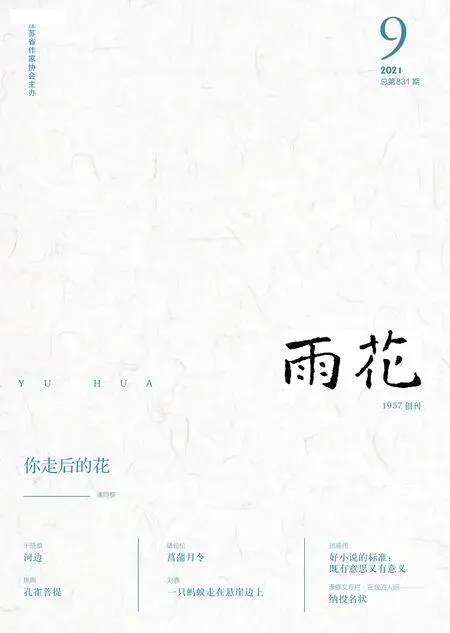浮世
智啊威
我瘫坐在床,隔窗听出他的河南口音,忙唤妻子把他请进来,好吃好喝招待了一番,然后泡上茶,把妻子支了出去。
我双眼湿润,拉住他的手,为了能让他给我留两包老鼠药,先是从日本人杀我二叔讲起,然后讲到河南闹饥荒,二哥和三妹相继饿死在母亲怀中,父亲拿出身上仅存的力气,草草埋了他们,然后转过脸对我说,你滚吧,出去寻口吃的,总比饿死在家里好。
那时候我才九岁,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抱着门口那棵歪脖子枣树不肯走,父亲就把我揍了一顿,我听到母亲在里屋哭,但自始至终没有走出来说一句挽留的话。一时间,我既绝望又伤心,从地上爬起来,抱着一个破烂包裹,咬着牙,在怨恨和泪水中离开了家。
我跟着逃荒的队伍,一路上都是骇人听闻的流言和惨景,大人们在说着“小孩子的肉嫩”“新坟被掘”“死尸已丢”之类的话。我心神不宁,再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半夜有人无意间碰我一下,都吓得我尖叫着从梦里跳出来,如临大敌。
风把干草和黄土吹起来,世界灰蒙蒙的,有时传来零星枪声,大家四散奔逃,慌不择路。有人倒下,被乱脚踩得惨不忍睹;有人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留下一群老弱病残,像浮萍一样,在无边无际的饥饿中漂浮、流动。
那时候的日子苦啊,逃荒路上,人像猪狗一样,吭哧吭哧,说死就死。后来听说战争停了,有人决定往回走,但我没有回去。我还恨着爹娘呢。这种强烈的恨意一直延续了很多年,但这是后话,我先拣重要的说。
我先是流落到三门峡的一个砖瓦厂。没有工钱,但主家管饭,我大喜,就昏天黑地干了起来。虽然每天下工后都筋疲力尽,但第二天,一觉醒来,依旧干劲十足!那时候我想着,一辈子就在这家砖瓦厂里度过也挺好,有饭吃,有床睡,没有战争、饥荒和逃亡,天堂也不过如此了吧!
每天工作间隙,我喜欢站在瓦库旁看师傅们做瓦,但并非如他们讥讽的那样是在偷偷学艺,我只是单纯喜欢看一块泥在他们手中舞蹈,然后出模成坯、入窑成瓦的那个过程。
渐渐地,也就跟刘师傅搭上了话。
有一天他冷不丁地走过来,问我是否愿意跟着他学做瓦。我放下砖坯,二话不说就给他磕了三个头。刘师傅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瓦匠,他能看上我,让我跟他学手艺,肯定是我家祖坟上冒了青烟。
做砖纯出力,做瓦则是一门手艺。我当时想,有了手艺,身在乱世也不至于饿死。因此我学得认真,有不懂的地方就及时问。平日里,别人休息,我就陪在刘师傅旁边帮他做点杂活或端茶倒水之类的事。本来三年后才会教授的真本事,刘师傅第二年就悉数传给了我。
他对我器重,我也不能给他丢脸啊。
夏天,太阳烤出我身上的油,在皮肤上“吱吱”响。即使这样,我也不歇息,依旧练泥、做坯、晾晒、装窑、加煤……刘师傅说了,瓦匠的高低,全在手上,而手上的功夫,需在千百万次制瓦过程中自己摸索、把握,提炼、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感觉来。
就这样,我在三门峡一做就是六年,手艺已不逊于刘师傅。有一天,我正在干活,刘师傅走过来说,小范啊,你走吧。
听到这话,我手里的瓦“啪嗒”掉在地上,碎成四瓣,眼泪也跟着涌了出来。小时候爹娘把我推出门,现在连刘师傅也要赶我走。
我双膝弯曲正要跪,刘师傅赶紧搀住了我。
我仰起脸,哽咽着说,师傅,我做错了事,你打我骂我都行,求求你别赶我走啊!
刘师傅一手搀我,一手从兜里掏出纸条,我这才知道,原来是刘师傅的一个师弟,姓朱,如今在陕西办了个砖瓦厂,正缺好手,特意来信聘请他前去助力。刘师傅那年已经五十多岁,老母亲八十多了,尚存一息,因此他不愿再往外走,就力荐了我。作为同门师兄,朱师傅对刘师傅的推荐深信不疑,很快就复信,留了地址,邀我即日前去。
离开三门峡那天,刘师傅和师娘一起送我。
我们出了北街,沿官路一直往前走。这么多年,刘师傅和师娘待我不薄,从我还是一个孩子时,他们便收我为徒,使我从掏苦力的队伍中解放出来,加入令人尊敬的手艺人的行列中。不仅如此,工作之余,刘师傅还教我识字,读他多年来一直随身携带的那几本圣贤书。若说起来,刘师傅出身可谓是书香门第,他父亲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加过光绪年间的殿试,后在地方上为官,一肚子忠君爱民的思想,渴望在政治上一展鸿鹄之志,但随着宣统退位,自己又深陷军阀的诡计中,偌大的家业,坍塌也就在一夜间。
家业倒了,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再待下去,连命都难保,刘家的族人在惊愕和绝望中四散逃命,从此零落四方。而曾经,那个众人见了都弯腰尊称一声“刘公子”的俊秀后生,为了果腹,最后竟沦为了骨瘦如柴的瓦匠刘师傅。
刘师傅为人敦厚、随和,几十年里,跟师娘从未红过一次脸,对我们这些徒弟也颇具耐心,待我尤其好一些,大概是我们经历相似,在小小年纪,便出来逃命躲灾。关于这一点,我没有询问过刘师傅。
现在,回忆起来,跟刘师傅和师兄弟们共处的那段时日,真是我这辈子最怀念的一段光阴。曾经,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我会永远跟随着刘师傅,为他养老送终。而直到他和师娘的身影被暮色遮蔽,我一个人走在黑黢黢的、去往陕西的路上,才突然意识到人世的虚幻。原本以为已经牢牢抓在手里的东西,某个时刻打开一看,那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一时间,我有点难以接受,眼泪就不争气地滚落了下来。
刘师傅告诉我,不要太感伤,又不是什么死别,来日方长,总还能再见到。刘师傅的话多少安慰了我一些。我拭去眼泪,一边走,一边想着,在陕西稳住脚后,一定要抽空回来看望师傅和师娘。
朱师傅待我也不错,只是身在异地,我变得愈加内向和寡言,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想念师傅和师娘,然后踏着月光,在砖瓦厂里漫无目的地游走,孤魂一般。有时候我就坐在砖垛上,望着月亮,嘴里喃喃着刘师傅曾给我讲授的苏轼的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以前背诵这首词时,没什么感觉,但情景和处境一变,所有复杂的况味便一下子都涌了上来。情绪难平,我就趁着煤油灯给刘师傅和师娘写信。刘师傅爱读古文,我就用古文写,每次他回信,都会把我的去信一并寄来,上面满是用朱笔批改标注的修辞和字句错误。我看了虽羞愧,但也温暖,仿佛还在他身边,听他当面教诲。
来到陕西后,我不愿结识新友,大部分精力和时间便都倾注在了做瓦上。“活做得漂亮、细致,人踏实、寡言。”这是大家对我的一致评价。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得到胡五爷的喜爱,后来他托朱师傅传话,意欲招我为上门女婿。
胡五爷是一个地主,膝下无子,育有一女,名“揽月”,出落得端庄可人,讲话柔声细语。朱师傅说罢,我的脸旋即红了,多年来,心在瓦上,还从未考虑过娶妻生子之类遥远的事。
“你可是修了八辈子的福!”朱师傅很替我开心,说胡家虽历经战乱,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至今还有良田百余亩……朱师傅讲这些时,眼里放着光。可我并不为此所动,也说不上原因。
我推脱说要给刘师傅去一封信,请他做主。朱师傅的脸顿时阴沉了下来,转瞬又变得和善地说道:也好,也好。
刘师傅迟迟没有复信,我提议给老家的爹娘也去一封,虽然多年不见,我也没有原谅他们,但入赘这等大事,作为儿子,还是应该告知他们一声。这一次,朱师傅没有说话,他眉头微皱,半晌后勉强点了点头。
而去往故乡的信依旧石沉大海。
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两封信,和往后数年我寄出的信,都被朱师傅和胡五爷悄悄拦了下来。而更过分的是,就在我犹疑不决之际,朱师傅还找人模仿着刘师傅的字迹给我回了信,信中除了祝贺,就是劝我尽快完婚。
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既然亲生爹娘不回信,我遵照师傅的意愿,也说得过去吧?
我跟揽月完婚几十年后才知道这些真相,但说真的,我对朱师傅竟生不起一丝怨恨。因为我知道,在那时,胡五爷若想演戏,没有人敢不配合着他玩。况且,朱师傅还经营着一家砖瓦厂,上上下下,几十号人跟着他吃饭,他自然不敢得罪胡五爷。只是,每当想到刘师傅临终之时反复念叨多年来我为什么没再给他写信,而他写给我的信我一封也没有再回时,心里总是难受万分,就一个人走出家门,站在山顶上,面朝师傅家的方向,大哭一场,然后擦干泪水,独自走回家中。
婚后,我的一举一动,始终都处在某种监控之中。不仅如此,连与外界通信的权利也被一双无形的手给剥夺了。而最令我无奈的就是对门的老鹿,即便在胡五爷去世之后,他依旧谨遵五爷的指示,对每一个走进村子的陌生人都严加监控,以防那些人把我从这里带走。
老鹿穿一件灰大褂,手里夹着烟。有人路过村子,给他递烟,他从来不接,依旧用冷漠而充满警惕的目光望着别人。
陌生人问老鹿:
“老乡,这是哪里啊?”
“不知道。”
“你在这里住多久啦?”
“不知道。”
“你家几口人啊?”
“不知道。”
“一只鸡几条腿啊?”
“不知道。”
你别以为老鹿是傻子,他比黄鼠狼都精!
当陌生人继续在村子里转悠,老鹿就会一直尾随,为了避免显得刻意,他一会儿假装在草垛后面撒尿,一会儿假装往山沟里面赶鸡,但那充满警惕的目光,一刻都不会从陌生人身上抽离。
后来,我和揽月有了孩子,随了胡姓,胡五爷喜笑颜开,但对我的监视仍不肯放松丝毫。可他越是这样,我越是想念那片土地:河南惠庄。
关于胡五爷,我这辈子只叫过他一声“岳父”,还是在我跟揽月的婚礼上,他满脸喜色,可当天晚上就把我唤到房间,一脸冷峻地说:往后,跟大伙一样,还是叫“五爷”。
他语气坚决、威严,我连连应诺,然后退出房间。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揽月和衣睡在我身边,黑暗中,我的眼泪一直流,她就一直帮我擦。她知道我心里委屈,在这个家里,我名义上是她的丈夫,实际上,不过是胡五爷手中的一个牵线木偶。
可是,我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怎能说结了婚,就要跟过去的师傅、朋友、亲人一刀两断,从此老死不再往来呢?我知道,胡五爷担心我再跟河南那边的亲朋有所牵扯,会产生动摇,某天抛下他们,独自离开。可我的孩子、妻子都在这,我跑回河南干什么呢?从我父亲把我赶出家门的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从今往后,我再也没有家了。
刘师傅的死讯给了我当头一击!那一年他才七十二岁,天落着小雨,地面湿滑,走着走着,整个人便栽到了坑里,当天晚上就断了气。
从多年不见的师弟口中得此噩耗,我感到浑身冰凉,继而躺在地上抱头痛哭,一边哭一边抽搐,像犯了羊角风,很多人围上来指指点点。
这件事把胡五爷气得不轻,说我丢尽了他的颜面,可我哪里还顾得了那么多?
那天我从地上爬起来,一口气跑到山顶,对着河南的方向跪下去,用力地给刘师傅磕了三个头。夜色中,我突然意识到,人啊,活在这浮世上,就像一片羽毛,在风中飘啊,飘啊,有时候落在院墙上,有时候落在荒草中,以为自己到家了,其实,那不过都是一个个暂居之地,很快,一阵风起,就又开始在空中飘来荡去了。
刘师傅去世半年后,师娘也跟着他的脚步走了,有一段时间,我想起河南,心里空落落的,像一片光秃秃的荒原上,正落着白茫茫的雪。
说来奇怪,有一年除夕晚上,我去集上办年货归来,听到一个孩子在哭喊爹娘。我左右望望,不见人影,就继续往前走,天越来越黑,山谷里有人放烟花,一束亮光冲天而起,在空中炸裂,山野瞬间明亮了一下,紧跟着又有烟花冲天而起。伴着一个稚嫩的嗓音对爹娘的呼唤,我的心也微微颤抖了起来,回过头,朝河南的方向望,视线中黑黢黢的,群山的暗影愈加厚重。
从那以后,我时常想到河南的爹娘和兄弟姐妹,而原本对他们的恨意,也渐渐被时间冲刷得无影无踪,尤其是在自己有了孩子,又经历了一次时代的大动荡之后,我多少也理解了一些为人父母的艰辛和不得已——若不是走投无路,哪个爹娘会狠下心,把自己的孩子往外面赶呢?
从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想回河南看看爹娘和兄妹,去师傅和师娘的坟前磕个头、烧个纸。
早些年,胡五爷是横在我与故乡之间的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而多年前,当他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时,这座大山轰然倒塌,河南变得触手可及。妻子说,你回去看看吧,你现在可以回去看看了!
孩子也说,爹,你回去看看吧,你现在终于可以回去看看了!
是啊,我终于可以回去看看了。但是,当我终于可以回去看看的时候,却又突然害怕和犹豫了起来。不回去,爹娘、兄妹们就一直活在我的记忆中,而一旦回去,就不得不接受某种悲哀的事实:爹娘已逝,而余下的兄弟姐妹,在频繁的动乱和饥饿中,还能活下几人?
说真的,我不敢细想,情愿一直活在自我的安慰和欺瞒中。
几十年来,我在这里结婚生子,但常常感到这里仅仅是一片暂居之地,我终究要回到生养我的那片土地上,尤其是发现自己身体里的零件在一件件罢工,死神的脸不停地闪现在睡梦中。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要抓紧回到故乡去,要埋入那里的泥土中。可有好几次,当我坐上返乡的车,却又突然产生了退缩之意。而2017年4月3日的那天早晨,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双腿废了,再也支撑不住身体。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妻子进来,抱着我说,没事的,谁都有这一天,不是还有我吗?
我哭得更凶了。从今往后,自己将像废人一样,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人照料,而返乡变得更加艰难和无期了。
躺在床上的日子里,我脑中时常闪现出炮火和饥饿交织的那段记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瑟瑟发抖,即便如此,现在都成了珍贵的记忆。而再看看自己残废的双腿,我突然觉得,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还不如早点死去。可有时候,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当我听出卖老鼠药的商贩的河南口音时,内心很激动,觉得自己梦寐以求的死,今天就要来了。可谁曾料想,他听完我的讲述后,借故去一趟厕所,就再也没回来。
那天傍晚,我趴在窗台上,透过铁窗,朝外望去:山冈上乌云密集,风尖叫着,在山谷中乱撞。大雨就要来了,而那个卖老鼠药的河南老乡早已不知所踪。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事儿也不怪他,要怪就怪我太实诚,为了让人家可怜我,给我留两包老鼠药,呜呜啦啦说了一大堆,甚至还直言不讳地说:老乡,请放心,你留的老鼠药我不会立刻吃,而是会在你走之后几天再吃,这样,谁也不会把我的死跟你联系到一块儿。如果你还不信任我,我甚至可以给你写个凭证,内容我都想好了:我的死,跟卖老鼠药的河南老乡毫无关系!
大雨骤降,山野氤氲一片,一只斑鸠紧紧抓着那根干枝,雨线细长、急促,朝它飞射而来,它缩着脑袋,站在冷雨中。
我的视线从它身上移开,投向烟雨混沌的山野,又想到那个悄悄溜走的河南老乡,一时间,失落的情绪紧紧地攥着我,越来越紧,仿佛要把我挤压成碎片。
而人一旦铁了心,死也不见得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事。
我的话是不是有点多了?本来我不想讲这么多,是你一直问,我才讲的。
说真的,本来我都不打算回来了,直到死的那一刻我都是这么想的,可是,当我的魂魄从肉身中脱离,孤零零地站在山坡上,听到从自己的葬礼上传来的唢呐声,凄清、嘹亮,在山谷中回响,直至消失,山野恢复死寂,我孑然一身,漫无目的地漂浮在山坡上,内心再次燃起返乡的冲动。
活着流落他乡,死后,魂魄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不然就会一直飘荡,像风中的草。
我已经走了很远的路,翻了很多座山,才来到朝思暮想的河南,可当我踏入这片土地后才发现,所有的光景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惠庄也不知所踪,我沿着记忆一边走,一边打听,正当四顾茫然的时候遇到了你,你的口音让我倍感激动和亲切,某一个瞬间我甚至觉得你就是我逝去的某位亲人,对此,你矢口否认,不过这没关系,你肯定知道惠庄在哪,因为你的口音和惠庄的人是那么相似,简直如出一辙!
所以,请不要再闪烁其词,因为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身上的肉像蜡液一样滴落,消失,很快就会彻底融化,和你一样,成为一具白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