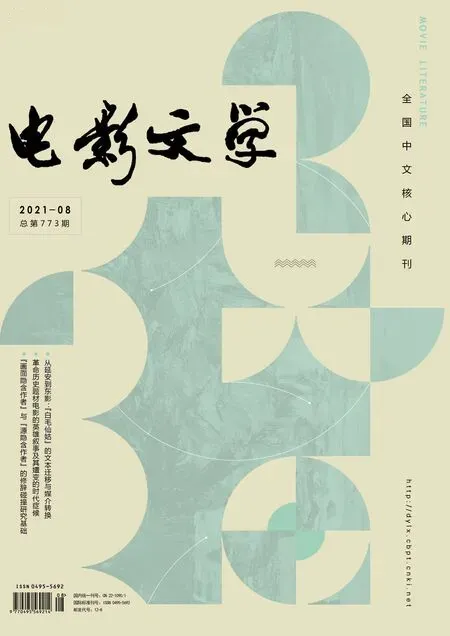论中国当代法治题材电影的叙事美学
颜研生
(广西警察学院公共基础教研部,广西 南宁 530028)
法治题材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法治状况的记录者和阐释者,法治题材电影叙事不仅动态呈现了当代法治进程,而且促进了法治的大众化,传播了法治文化。中国当代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立足当代法治语境,将当代法治进程中一些持久而普遍的问题进行影像化呈现,通过戏剧冲突的建构与法治问题的想象性解决,对法治现实做出思考、阐释或批判。法治叙事具有较强的现实性、艺术性、思想性和丰富的美学价值。研究中国当代法治题材电影,法治叙事所建构的叙事美学是我们应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真实美
艺术真实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原则,关于影像的真实性,罗伯特·考克尔指出,真实性一直是社会成员达成共识的社会思维产物,真实性成了我们能够产生各种各样反应的一种文化基础。法治题材电影艺术创作所呈现的真实性可以形成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真实美。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真实美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真实的案件与人物。从叙事内容来看,很多法治题材电影都是改编自真实的案件和人物,电影是对他们的艺术再现。在观影前,观众已对电影叙事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法治题材电影叙事就是要揭示真实,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巴赞指出,“景深镜头”能够保留现实空间的真实,而“长镜头”则可以保留时间的真实。法治题材电影主要通过镜头语言来揭示真实,法治叙事通过真实地再现空间和时间,艺术化地呈现真实的案件与人物,能够激发观众对相关法治事件和法治人物的思考,培养观众的法治心理和法治情感,提高观众的法治认同感。真实法治案件改编的法治题材电影通常能够产生强烈的真实感,形成真实美。如《天狗》描述了伤残军人李天狗担任护林员与当地黑恶势力的斗争,用生命和鲜血守护国有山林的故事。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来源于真实案件,能够产生真实美。《任长霞》《人民检察官》《法官妈妈》《真水无香》等法治题材电影都是以真实法治人物为原型,讲述的故事各不相同,呈现的法治内涵丰富多彩,但存在一个共同的叙事主题——这些法治人物承载了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点滴进步,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了中国法治进程。通过影片所呈现的真实案件与人物,观众可以感受到法治的进步与完善,感受到法律人的人格魅力。
第二,真实的空间。空间是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重要场所,它不仅为故事发生提供具体的场所,还为故事发展提供驱动力。叙事空间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而真实的空间可以营造出真实美。法治题材电影叙事对于真实地理空间的建构决定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在某种意义上与影片的叙事主题紧密关联,如《马背上的法庭》将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放在云南西北山区,暗含了送法下乡的叙事主题;《被告山杠爷》将故事置于四川乡村堆堆坪,呈现农村法治状况,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乡村法治进程的艰难与缓慢;《全民目击》则将故事发生地放在现代都市,通过庭审来透视现代都市生活。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真实地理空间是为叙事的法律属性服务。《执行》讲述了武定县一个普通农民在执行法院生效判决过程中发生的故事,故事不但由真人真事改编,而且在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人民法院进行了实景拍摄,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案件以及真实的空间必然能够产生一种真实美。此外,塑造警察形象、检察官形象以及律师形象的法治题材电影通常都会在公安机关、检察院以及律师事务所进行实地取景,这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呈现叙事的真实美,真实空间所营造的真实美往往能够体现导演的创作理念和价值追求。
第三,真实的细节。法律由细节组成,前后勾连的细节能够形成一个完整链接来呈现法律,而细节间的关联性和客观性又决定了法律的适用。电影细节叙事就是通过细微情节进行故事叙述,细节可以呈现剧情的内在因果关系,而法治的复杂性决定了细节叙事的多样性,其中细节的真实性尤为重要。法治题材电影叙事可以运用现代技术,将案件现场勘查、案情研判、抓捕犯罪嫌疑人、庭审现场等司法活动的细节呈现给观众,如《湄公河行动》中就以新闻实录形式向观众呈现抓捕和庭审糯康的真实场景,能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从而使观众产生真实感。电影的真实感能够促使观众宣泄情感和产生认同,进而形成真实的审美感受。为了能够实现真实美,法治题材电影叙事必须关注细节,否则细节失真,不仅影响叙事效果的实现,还会影响到观众的审美感受。有的法治题材电影叙事对细节把握不够,出现一些明显的硬伤,如按照英美法系刑事审判制度来设置公诉人与辩护人的席位,且公诉人和辩护人在法庭来回走动,不时到被告人和证人面前询问案情。《全民目击》中公诉人童涛随意离开座位前往被告席讯问被告人,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刑事审判规则,明显的法律硬伤无疑损害了影片的真实性。“真实”是观众评价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重要指标,符合基本法律规范、能够产生真实美的法治题材电影是“真实”的,反之则未能反映现实法治社会、不符合观众期待或认同的电影则不够“真实”。
作为现实主义电影的法治题材电影逼近真实,但又不等同于真实,而是在再现法治现实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表现电影创作者对现代法治的理解与认知。法治题材电影创作既要忠于现实,又要高于现实。法治题材电影呈现的“法”与现实中的“法”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决定了法治题材电影叙事所创造的真实只能是虚构的艺术真实。霍华德·苏伯指出:“人们走进电影院不是去看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去看一个对他们已知世界有所补偿的世界。”法治题材电影叙事加深了观众对日常法治生活的理解,同时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即电影创作者通过合理的艺术想象呈现的法律世界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期待。当然,这是一种基于艺术真实的审美幻象,对法治叙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和谐美
将审美理想归于和谐,用和谐限定美的本质,在东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提出“美是和谐”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强调的“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从中国“神人以和”到周来祥先生的辩证和谐,都在和谐关系下把握美的本质。法之美,美在和谐。从法律效力位阶上来看,法律等级可以分为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四个层级,它们的制作主体、适用范围、制作时间各不相同,但它们和谐一致、协调统一,很少见到法律之间相互矛盾、错漏百出。“没有法律体系的内部和谐与协调,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和和谐世界的追求就是没有法理依据的,我们也难以实现‘法之美’的胜景。”和谐统一的法律体系和协调有序的司法运作无疑呈现了法的和谐美。
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和谐美主要表现为在法律运作过程中各机关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有条不紊、协调一致中所产生的美。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执行需要多个司法机关通力协作完成。具体来看,主要包括现场勘查和现场访问阶段、案情分析和确定侦查范围阶段、调查访问和摸底排查阶段、审查犯罪嫌疑人阶段、拘捕和预审犯罪嫌疑人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和执行阶段等。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监狱等部门在不同阶段都能够相互协作,保证法律顺利实施。有的法治题材电影叙事就呈现了这种秩序和谐,表现出和谐美。如《解救吾先生》《特别追踪》都体现了司法机关内部协调以及不同司法机关通力合作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的权威,形成了电影叙事的和谐美。在《毒战》中,通过缉毒过程中各警种之间的有序合作,观众可体验到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和谐美。
法治题材电影叙事所呈现的和谐美还表现为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所谓天理,即天道,是人们心中不证自明的公理,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在法治题材电影中表现为坏人必须受到惩罚、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国法即国家制定的法律,这些法律内容不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是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依据。法治题材电影叙事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律规范,如法治题材电影叙事存在明显的法律硬伤,会影响法治题材电影叙事价值的实现。人情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言的民心、民意。在现代法治社会,天理、人情仍然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最基本行为规则和伦理要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情理是“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美学就是追求情理法的和谐统一,这一秩序和谐便是美的。具体来看,法治题材电影中的情理与法理有时存在一定的冲突,如在《被告山杠爷》中,堆堆坪的村民夯娃的媳妇脾气倔强、刁蛮泼辣,她多次殴打婆婆,被山杠爷捆起来游街示众。从堆堆坪的传统世俗来看,山杠爷的做法顺应民意和民心,是符合情理的,但山杠爷的做法有悖现代法治精神,涉嫌非法拘禁罪。这样情理与法理形成了碰撞,产生了矛盾,而堆堆坪的治理正是在冲突与对抗中走向和谐。随着检察机关的介入调查,堆堆坪开启了乡村法治,进而形成了一个和谐的乡土秩序。从影片所呈现的主题来看,这种和谐的乡土秩序无疑可以给观众带来审美愉悦,促进人们对法治问题的思考。
在法治题材电影叙事中,被破坏秩序的恢复、非正义行为的清除、惩恶扬善的实现、社会正义的彰显等均可以体现正义,都可以产生和谐美,如《五颗子弹》中狱警老马成功实现罪犯的转移、《黑梦》中对传销违法行为的依法治理、《刺儿头》中戒毒少年戒掉毒瘾重塑人生等“大团圆”结局都体现了和谐美。法具有规范作用和定分止争的功能,稳定、协调、监督、保障是法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价值规范使法呈现出和谐表征,也是法治题材电影叙事能够形成和谐美的原因所在。
三、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暴力美
暴力即损害他人人身、财产等权利的强暴行为。暴力是电影叙事的重要元素,特别是在刑事类法治题材电影叙事中,犯罪嫌疑人的暴力与执法者的反暴力往往是叙事的直接动力。有学者指出,“一方面,暴力推进叙事体现在犯罪残暴行为中,暴力本身即是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载体,在犯罪人残暴的行为中出现。另一方面,暴力推进叙事同时也体现在打击犯罪的反犯罪活动中,暴力也常是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打击犯罪、惩罚罪恶、重建法治权威的媒介”。暴力在推进电影叙事的同时,也可以呈现一定的美感,进而形成叙事的暴力美。在某种意义上,法治题材电影叙事所呈现的暴力美是“将实际的暴力行为转化为具有表现性的艺术形式化的暴力,即暴力的艺术形式化”。
约翰·科纳指出,暴力电影可以分“冷静型”和“兴奋型”两种叙事效果。“冷静型”暴力影片指的是通过剪辑、机位等技术手段,制造一种目睹现实中的暴力场景的感觉。影片可以调动观众在接触现实场面时所诉诸的伦理观念。而“兴奋型”暴力片的目的是制作一种鲜明的唯美感觉。它可以给某些旨在享受美感而非伦理观念的观众制造快感。法治题材电影以冷静理性的视角来呈现现代法治进程,法治题材电影中的暴力叙事效果以“冷静型”暴力为主,体现其背后的叙事伦理要求。在法治题材电影中,暴力主要体现为打斗、杀戮、血腥、武器、伤害,其中身体伤害往往能够产生震惊或者震撼的叙事效果。如《雪暴》中韩晓松被悍匪射杀、王康浩与人在小酒馆里的互殴、老大向聋子挥下的斧头、老二被狩猎夹夹到双腿以及最后小木屋里的几人的射杀和斗殴,这些节奏凌厉的暴力场景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进而转为一种暴力审美体验。暴力行为能够使人在破坏或力量对抗中获得美感,这主要在于满足人内心潜在的攻击欲望,同时又可以释放日常生活的压力,宣泄了愤懑情绪。
从功能上来看,暴力不但可以推动叙事发展,而且还可以塑造人物形象和体现叙事主题。如《暴裂无声》的哑巴矿工张保民脾气火暴,喜欢动手解决问题。他找寻儿子失踪的过程中,对蛮横霸道的昌万年等人以暴制暴死磕到底,塑造了一个极富正义感的父亲形象。在法治社会,以暴制暴显然不为法律所提倡,但是作为一种私力救济方式,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暴力在影片中可以阐释为张保民的道德责任,这种基本的社会伦理要求符合观众的一般认知和心理期待。在《沉默的证人》中,法医为保留证据与犯罪嫌疑人的殊死搏斗,观众由此可以体验到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暴力美。在《刑警队长》中,司法机关或执法者对犯罪嫌疑人给予暴力惩罚,这体现了法律的惩罚功能,还反映了善恶相报的伦理文化,能够使观众获得道德上的满足感和法治上的认同感。
艺术的暴力来源于生活的暴力,暴力永远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动物性本能,也必然会伴随人类历史发展。影像中的暴力都是虚构的,观众对法治题材电影所呈现的暴力现象或暴力美津津乐道,但对法治现实生活暴力事件基本是零容忍,这表明现代法治社会建立在基本的伦理价值观之上。需要注意的是,影像中的暴力行为对未成年人的心智发展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法治题材电影暴力叙事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暴力美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暴而美,即通过暴力铺陈来呈现暴力美感,这也是法治题材电影暴力叙事所追求的目标。
四、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正义美
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法一直被视为维护和促进正义的艺术和工具。何为正义,不同的研究者对正义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关于正义的不同阐释中,总有一点是相同或相近的,那就是将正义阐释为公平地对待他人和公平地分配财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道德上的善。法律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则是正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奥古斯丁指出:“没有正义的法律不是法律。”美学家桑塔亚那认为:“正义的价值,如果不是派生的和功利的,就必须是固有的,或者说审美的。”因此,正义具有天然的审美属性,法治题材电影叙事能够形成正义美。
关于正义美的概念,王定金在《审美大辞典》中将它定义为,“正义美是指人具有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的美好品质,是人的内在的正义感同具体的言行所表现出来的美”。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正义美是法美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法治题材电影叙事最重要的审美类型。在法治题材电影叙事中,正义美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具体来看,法治题材电影叙事的正义美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追求正义的行动中。在法治题材电影叙事中,正义美体现于行动。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民众等追求正义和维护法律价值的具体行动可以产生美。如《知心法官》中的法官黄志丽在桩基案中秉公执法,最终使工程施工监理公司受到法律制裁,实现了公平正义。《我是检察官》中的石俊峰在办理特大红豆杉盗伐、贩卖事件中铁面无私,决不姑息违法,使涉嫌犯罪的亲哥哥受到法律惩罚。《刑警队长》中刑警队长不畏困难,历经挫折,终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民工律师大圣》中大圣自学法律成了律师,与包工头打官司,最终替自己和工友讨回工资,伸张了正义。《湄公河行动》以真实故事为蓝本,讲述了中国缉毒警察境外维权执法的故事。2011年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流域遇害,中国同胞惨遭杀害,甚至被诋毁为犯罪分子,为了查明血腥冤案的真相,中国缉毒警察不远千里,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将幕后黑手糯康抓获归案绳之以法,维护了我国公民的权益,展现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气概和决心,彰显了国家正义,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高刚、方新武等缉毒警察是正义的代言人,影片围绕他们的行动来进行正义叙事。在导演林超贤看来,“正义是偿还罪孽”,血债血偿、有罪必偿也是世俗世界的共识,导演围绕朴素的正义观来安排故事情节。中国缉毒警察为何不惜付出较大代价也要将毒贩糯康等人绳之以法,叙事动力主要来源于中国政府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的决心及能力,这无疑是个强大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理由,不仅可以呈现出较大的社会宏观效应,还可以安慰遇难者家属,给予人文关怀。
第二,追求正义的人格中。培根说:“就是因为有了正义感,人才成为人,而不成为狼。”正义感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法官为例,法官是正义的代言人,浩然正义所形成的法官人格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中国古代,包拯、海瑞等人秉公执法、不畏权贵、不徇私情,他们在追求正义中谱写了一首首正义之歌,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正义的人格美。在中国当代法治进程中,涌现出了袁月全、宋鱼水、邹碧华等优秀法官,他们廉洁执法、秉公办案、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崇高的人格。埃里希指出:“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茶乡法官》《白鹿塬法官》《巡回法官》《邹碧华》等法治题材电影均呈现了心怀正义、公正裁判的法官形象,使观众通过法官的正义人格体验正义美。此外,检察官、警察、律师等法律人在追求正义中都体现了高尚的人格美,如《检察官》《无法证明》《一个人的派出所》《特警队》《实习律师》等法治题材电影叙事均通过人格美来呈现正义美。
第三,实现正义的结果中。一般而言,正义的实现是以清除非正义为前提。在法治题材电影叙事中,正义方通常开始力量单薄,而邪恶方通常力量强大,在悬殊对比之下,正义方要历经各种磨难,甚至会一度绝望而产生放弃的念想,但总会有第三方力量给予一定的帮助,使事件峰回路转发生决定性的转机,最终正义方战胜邪恶方赢得胜利。斯米尔指出:“正义和善良一定会战胜邪恶,这是永恒、绝对的必然。”“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种叙事取向符合违法必究的现代法治理念。法治题材电影通过讲述正义的实现,能够产生正义美。如《追凶十九年》讲述了从1999年起在偏远小城发生多起强奸命案,警察刘一波和搭档何晨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历经19年终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正义结果的实现无疑是美的,在法治题材电影叙事中呈现为正义美。在法治题材电影中,除了司法救济,还存在当事人通过私力救济实现个体正义。这里所采用的“私力救济”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专业词汇,而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实施自卫行为或者自助行为来救济自己的一种行为方式。《追凶者也》中宋老二被警方误认为是摩的司机被杀案的犯罪嫌疑人,为了洗脱嫌疑,他踏上寻找真凶的惊险之路,最终协助警方抓获真凶,洗脱嫌疑。《你是凶手》中身患绝症的白兰逐一拨打购买保健品名单上的电话,最后通过声音识别锁定了绑架杀害其女儿的真凶。上述两个叙事人物均是通过正当防卫或私力救济的方式实现了个体正义,法治题材电影中民众的正义叙事在一定程度体现了公力救济的不及时或不完善,这促进人们对如何完善法治以及法治如何保障民众权益问题的思考。
法治题材电影叙事可以放弃现实逻辑,通过各种叙事技巧和蒙太奇手法呈现正义,使正义被“看见”。“影像中的正义来自一种对正义的想象。这种想象通过影片中人物间的博弈,同时满足观众对道德、伦理与情感诉求。”观众通过审美体验把握法治题材电影所蕴含的正义主题,形成审美正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是朴素的实质正义,是最基本的价值观和正义感。惩恶扬善是基本的社会伦理,这是法治题材电影叙事伦理要表达和呈现的内容,也是法治题材电影叙事实现审美正义的必然要求。
结 语
中国当代法治题材电影叙事可以呈现出真实美、和谐美、暴力美、正义美等叙事美学,能够使观众在接受过程中开启理智、愉悦身心,获得审美快感,陶冶性情。通过审美体验和审美感悟,观众可以加深对法治的认知,形成趋美抑恶的审美情感。“基于情感的诗性正义能够给我们带来道德上的感召,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同情的姿态去关心那些弱者;而文学性的视角则拓展了我们的经验边界,使得我们能够以更加全面和更加人性的态度去对待人和人性。”法治题材电影叙事所呈现的叙事美学能够通过情感结构培育观众的人文情怀、法治心态、法治人格与法治情感,形成审美正义,促进法治信仰的建立和法治社会的构建。因此,应充分研究法治叙事所建构的叙事美学,探讨法治叙事对于法治社会建构的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