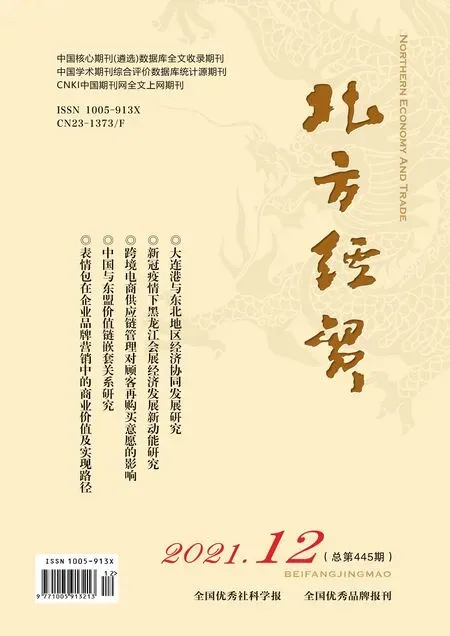消费视域下主体性的规训与治理
吴玉彬,倪明宇
(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赣南 341000)
一、消费社会中的规训——现代社会的非预期后果
在二战后欧洲经济恢复的“黄金时代”,西欧处于冷战前线,同时是消费品种类繁盛的大市场。此时欧洲面临社会动荡,各类广告、新发明等不断重构欧洲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与认知,“福利国家”与自由市场的期许使得欧洲社会呈现一种丰盛和动荡的复杂景象。而鲍德里亚反驳加尔布雷斯赋予“消费社会”一种充足、华美的商品社会景象,而是一种商品总量极大充裕而产生的假象:“‘物质丰盛的社会’与‘物质匮乏的社会’并不存在……因为不管哪种社会……都既建立在结构性过剩也确立在结构性匮乏的基础之上”;[1]其次,“消费社会”本身是一种新体系——“符号体系”产生的象征,它意味着人对物的认识被物本身所掌控,或者说就“物”而言人除了赋予它们意义之外少有作用,甚至可以离开人而完成“意义”的自我运行。作为在生活与市场分离、传统家庭的解体和个体化过程中的个体,其不得不独立面临社会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中的就业市场和各类社会交往规则事实上创造出一种制度化的人生模式:“个体化的私人生活愈发严重而明显地依赖于社会状况。这样的生活彻底脱离了人们的亲自掌控……制度性生命历程模式叠加在了等级的、阶级文化的或家庭的人生节律之上……这种新的模式体现为进入或退出教育体系,加入或退出雇佣劳动。”[2]在工业社会作为国家治理、经济运行、社会活动中最为核心的家庭结构也受到冲击并逐渐演化为以个体形式独自面对生活,此时“符号系统”自我运转力量相较于越来越势单力孤的个体而言更为强大。海量外在信息和事物的支配使不同职业间的认知、专业知识和活动范围差距不断增大,并在因分配不均产生的巨大差异下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体不仅陷入物质生活贫困,同时陷入认知贫困,难以理解社会中出现的多样化理念和新事物。经济分工以统一标准、提高生产力、减少损耗与成本作为目标,但个体是以全身心形式参与社会生活,需要对不同可能影响自身生活的事物做出解释以保证认知与客观事实的统一,个体认知成本反而不断上升,个体间联合成本不断增加,而这部分成本并不被资本家所承担,使得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和生活中的个人面对日益增大的压力。
福柯论述的“规训”更倾向于在身体驯顺的基础上产生其他包括社会控制在内的影响,是由特定主体通过一定组织形式和规则完成的。基于“消费社会”中具有仿真性而非基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关系,个体间不同的认知能力和有限活动范围中的交流使个体难以溯及事物本源。因此,这种依靠符号自身运作完成意义构建全过程的体系将每个人都变作彼此的“监视者”与“规训者”,使个体之间更难以创造可被人所操控且广泛认可的动态社会规则,同时原先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成为“物体系”的功能承担者,而规训方法就是具有“散点监视”意义的符号社会规则。
二、全景敞视主义的演化———“物体系”的“散点监视”
“物体系”是鲍德里亚在符号体系理论中提出的概念,指不需要人直接参与便可自身完成意义构建过程的物自身所形成的体系。“散点监视”指依靠社会中多个个体作为点状形式存在,通过特定社会交往规则以完成彼此近乎完全了解的监视形式。前现代的监视活动往往是特定主体主动进行,以达成对目标客体的行动了解或威慑等效果。随着社会分工不断发展,客观世界复杂化使得个人与组织对社会的理解能力日益减退,最终造成“规训”形式可能脱离以人作为手段和目标的现象,“物体系”的自我运作使事物成为一个个节点来充当人类行动的观察者与监视者。而“散点监视”作为前现代依靠有限社会交往主体构建的一种透明形式逐渐在更为发达的商品社会中得到更大范围实现,且这一过程逐渐脱离单个个体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体的消费活动和社交活动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拓展,个体所面临的社会交往规则日益复杂,个体角色的多元化使个体难以掌握和认知社会互动规则的发展倾向,甚至成为不同互动规则体系中的要件而非目的。“物体系”一定程度上否认了“人”这一社会关系集合作为社会互动目的的状况,将个体置于活动的中心,将社会规则构建的各类事物、过程等置于观察和评判位置,最终将“物体系”从物意义的自我构建延伸至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体活动规则原先是由个体在生产、社会实践中不断构建,但此时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已经让以“个体化”的社会成员难以单独承担分析与比较在社会发展、规则演化过程的成本,因此退而求其次利用这个体系,成为彼此的“监视者”。“物体系——全景敞视”过程由符号完成“社会关系”构建,人首先通过主观认知赋予物以意义,物通过意义和作用完成自我建构,形成有效运作的体系。但物的意义在不同个体的使用和新文化形式出现过程中多样化,最终超越个体的主观意识掌握能力,从而成为“全景敞视”的组成部分,因此众多无法团结的个体不得不在物所创造的新规则下生存,使“物体系——全景敞视”形成相互促进、自我运作的闭环过程。社会治理直接面对基层的众多个体,然而个体在现代生活中不断寻求自身的独立性,在社会交互中了解更多传统社会化过程所难以提供的信息、规范和物品,使得社会治理必须了解基层社会的新规范构建过程。因此物的发展与丰富并不必然为社会治理提供更多便利,反而可能成为束缚个体行动的存在。新规范在“物体系——全景敞视”过程中并不完全受制于原先由众多个体的交互所塑造的社会关系和规则,使得社会治理工作必须拨开因反客为主的物所创造的虚假社会关系,寻找社会关系中的真实,能够有效完成政府与个体的双向互动,保证在减少干扰个体活力的同时完成社会动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消费社会”与“物体系”相互助长的进程同样影响到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同样面对欧美社会曾经历的演化过程,同时面对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刘飏、王泽辰[3]指出,中国社会内部出现包括“城乡”“高低”之分的消费结构性差异问题,是构建良好社会发展环境必须解决的障碍。在文化交流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消费文化产生了剧烈变化,“物体系”的建构则如影随形,如快餐文化的冲击和精致的消费生活方式出现:“继肯德基之后陆续进入北京市场的西式快餐厅,使消费者很快认识到干净、明快和舒适是这些快餐厅的重要特征。”[4]“典雅且时髦的消费已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消费知识本身也成为一种商品。”[5]肖瑛[6]则从社会交往形式入手,指出传统差序格局在与现代生活交织中,使得现代公共生活偏向等差化、私人化。新的社会关系演化则有可能在使公共生活偏向私人化过程中,同时消解原先文化形态下的意义塑造过程,为中国社会行动者的社会关系塑造、认知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中国社会与行动者的特殊性同样为中国社会摆脱物体系带来的新规训形式创造条件。
中国社会治理需要激发基层的自主性,前提是保证基层民众对客观世界和主观认知的统一,成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认知的主动构建者而非被动接受者。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消费主义观念日益盛行,规避这种依靠物来证明人的价值观念是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工作。作为政府,社会治理需要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物体系”的客观存在会干扰政府的视野;作为民众,社会治理需要有力的独立思考能力,“物体系”的客观存在会撕裂个体的认知。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无论个体或政府均应当尽力避免或减少落入“符号体系”所编织的陷阱。
三、社会治理中的行动者——“规训”与“自主”并存
个体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流动性增强而面临自身愈发独立于原先社会群体、减少社会支持的现象。市场经济为社会中各个主体提供更多便利,但同时减少他们理解世界的可能性。“散点监视”是鲍曼对较为原始社会形态的社会关系认知,在有限交往范围内产生的高密度人际关系,使得彼此之间少有秘密,且共享高度统一的社会交往准则。而现代工业社会,尤其是互联网得到广泛应用后,个体可以通过更为便捷的方式了解其他社会成员,并产生更多种类的小群体内部社会交往规则。而“物体系”的力量也通过个体更为广泛的交往产生传导,以流行的消费品、广告、社会宣传等形式影响全社会,“散点监视”形式通过“物体系”的力量加强了以消费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个体间监督。新的散点监视形式不仅影响个体自主交往能力的提升,为人的认知行为增加负担,同时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因为物所建构与控制的社会准则日益脱离政府和个体的掌控,成为客观规则本身的一部分而难以剥离。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治理工作需要重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个体认知社会结构的能力;同时提升政府的社会干预能力,为社会发展提供矫正力量,从而保持社会发展动力的持续性。
第一,加强家风建设,提高社会关系网络的自主力量。“符号体系”本身是社会中千万行动者所共同构建的社会规则网络,而工业生产方式和市场制度将其不断复杂化,最终束缚普通行动者。行动者自身必须有意识地参与构建与解构“符号体系”过程,鲍德里亚指出:“拒绝永远不能还命,拒绝事实上生活在长期还债的义务中,生活在劳动的缓慢死亡中”。如传统的“哭坟”活动是一种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的祭祀活动,它可以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进行,通过亲人好友的痛哭乃至一定程度上癫狂的行动表达并宣泄他们的痛苦,最终消去生与死的情感界限,将家户关系通过共同活动加强。这类传统社会习俗和家庭文化以情感为基础,凝聚起传统“礼”的社会规范,是社会自主性的重要表现,其文化与制度形式的传承同样可以在现代社会治理工作中产生有益影响。正如杨善华[7]指出,中国的家本位文化纵贯中国历史,是社会组织和个体发展的重要力量,加强家文化建设有助于家庭成员的相互支持。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其认知能力受限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其抵御冲击的能力同样依靠其所生长的初级群体。家庭作为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单位,通过加强家风教育,提高个体自主性力量,提升个体认知能力和抵御外部风险能力,有助于改善社会治理工作效果。
第二,改善行政能力,提升政府对基层发展的有效关切。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承担统合社会全体成员的重要职责。社会是由个体行动所形成的产物,并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律、功能与结构,政府应当高屋建瓴,对客观事物发展进行引导并发动基层教育工作,明确社会支持网络发展的重要性。政府应当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了解人民可能面临的潜在危害,并及时给出可行举措。“物体系”的存在意味着个人作为个体化的单子,难以面对“客观文化”的负面影响。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产劳动所产生的剩余并不足以支撑大多数人了解消费主义和“物体系”的危害,因此政府有责任在引导社会团结中作出积极行动。
第三,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提升社会主体认知能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类思维方式与社会理念不断涌现,这是因为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巨大变革,同时社会成员经历来自国内外动态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基础教育深化普及,民众对国内外事物认知能力逐渐提升,越来越多人希望主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便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明确,当教育抓住本质和事物发展的历史沿革时,便能更为有效地以少带多,从而推动个体了解社会发展的过程。正如米尔斯所言,“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8]。个体与政府应当在社会发展程度日益提高的同时提升自身认知客观世界变化的能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更好适应社会生活,推动社会治理工作进一步改善。
四、结论
在生产力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社会分工与产品的复杂程度超出个体甚至政府的认知能力,对个体活动和社会治理提出新挑战,政府与个人所面对的社会规则逐渐被商品所包围并重塑。“物体系”借助消费市场的力量不断生长,进而产生社会关系的分裂状态,使得物体系的功能性替代人的主体性地位,并借助人际关系节约交往成本的现实需要,最终社会规则的塑造超出人的控制范围。作为现代社会中逐渐分散的个体,彼此认知的产生更多基于自身生活实践与生命历程,超越了传统家庭和工作单位的塑造,为尽可能减少比较生活各类行动的成本而较易陷入认知孤立状态。在众多孤立个体面临的社会规则变动中,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人为本;政府应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促进自身治理能力和治理技术现代化;个体主动通过传统社会关系形式及现代分工协作建立社会交往网络,认知了解复杂符号背后的实在社会关系变化。综合政府与个体的力量,结合各类治理技术,能够有效促进社会成员超越符号体系构建的“虚假陷阱”,回到人与人的真实社会关系,从而减少因物的反客为主造成的损害。科学技术与物质丰富为民众生活、社会治理工作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不能忽视其潜在对个体主体性的可能危害,尤其是在社会互动规则构建过程中的影响。